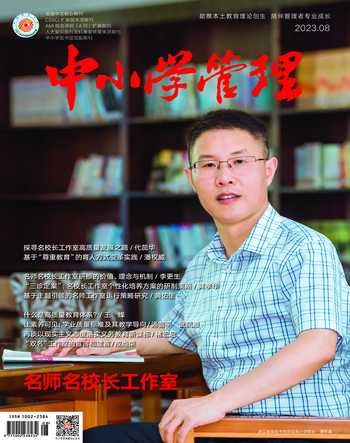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领导力的定位与提升
杨秀伟 张宇帆 李祥
摘要基于萨乔万尼的校长领导力理论框架,审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领导力的定位,包括融入乡村文化振兴的文化领导力、回应乡村振兴诉求的象征领导力、彰显专业支持引领的教育领导力、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人际领导力、促进教师扎根乡村的技术领导力。针对现实问题及影响因素,提出提升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领导力迫切需要优化有吸引力的制度环境,构建科学有效的培养培训体系,营造协同合作的支持氛围,内砺自我实现的成长动力。
关键词 校长领导力;乡村小规模学校;文化领导力;象征领导力;教育领导力;人际领导力;技术领导力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384(2023)08-0044-05
乡村兴必先学校兴,学校兴必先校长强。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教育力量,鄉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备受关注。乡村小规模学校是指在校生不足100人的乡村小学和教学点,其数量众多,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仅小学教学点就达7.69万个。[1]由于发展要素的不确定性和发展环境的特殊性,处在我国教育体系“神经末梢”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对校长领导力有着独特诉求,而校长领导力对学校质量提升的决定性作用也尤为凸显。
乡村小规模学校与乡村社会是共生共荣的融合发展关系,脱离了乡村社会发展需要必然会走向衰亡。在乡村振兴视域下,进一步厘清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领导力的基本特征与着力点,对提升乡村小规模学校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领导力的定位分析
校长领导力即校长以自身专业知识、经验、能力和人格品质等,推动学校发展和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萨乔万尼根据领导力的对象和方式,把校长领导力分为技术领导力、人际领导力、教育领导力、象征领导力和文化领导力五个维度。[2]依据这一理论框架,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学校面临的要求与挑战,我们从以下五个方面审视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领导力的基本定位。
其一,积极融入乡村文化振兴的文化领导力。陶行知先生说:“乡村学校是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应担当起乡村生活的“乡贤”角色,对内通过各种有效方式传播学校办学的价值观念,对外作为乡风文明的传播者和乡村文化建设的推动者,将乡村小规模学校办成乡土人文的新坐标,推动学校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深度融合。
其二,主动回应乡村振兴诉求的象征领导力。乡村振兴有助于转变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城市化办学倾向,使得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主体地位回归成为可能。通过战略规划和系列象征性活动,传播学校教育理念,增进学校成员服务乡村的精神和融入乡村的信念,是校长象征领导力的功能体现。
其三,充分彰显专业支持引领的教育领导力。在“二元权力”结构的学校组织中,校长的影响力来自外部的科层权威和内部的专业权威。由于乡村环境的特殊性、资源的局限性和教师人数偏少,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的科层权威并不明显。实践中,他们往往要承担大量和其他教师性质相同的工作,其领导力更多体现在对乡村教育振兴的引领和专业支持上。
其四,深入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人际领导力。乡村小规模学校所处的乡土情境中,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和家长文化水平、生育观念以及乡村家庭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制约着乡村家长在家校协同上的参与;另一方面,教师来源的区域多元化和“走教”方式等,使教师成为乡村社区的陌生人。因此,校长应发挥驾驭学校社会人力资源、整合内外部资源的人际领导力,借力加强“家长学校”建设工作等政策机制,建立并调动起家长、校友、社区专业人士等参与学校育人的强大社会支持系统,破解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教育孤岛”现象。
其五,着力促进教师扎根乡村的技术领导力。校长技术领导力即校长完善学校日常管理制度、流程等管理工具和管理技能的能力。在乡村小规模学校公共生活中,校长自身的分配权力往往也很小,所以应更注重人与人之间感情和心灵的互动,制度建设要以尊重、信任和民主为基础,方能营造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的环境。
二、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领导力的方向迷失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保留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3]但现实中,乡村小规模学校学生流失严重,甚至有些百年乡村老校也被迫停止办学。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乏力,面临生存危机,校长领导力的方向迷失是无法回避的原因之一。
其一,文化领导力的乡村偏离。文化领导力是校长在培育学校核心价值观、建立学校道德秩序中的感召能力。乡村小规模学校理应传承和形塑乡风文明,利用独特的乡土资源办出特色。然而,在城市化教育文化裹挟下,乡村文化的教育意义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有学者提出,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在学校发展实践中一味地模仿城市文化,在学校核心价值形塑、校园文化建设、课程内容选择、校本研修等方面丢掉了乡土文化的“本色”和“底色”。[4]
其二,象征领导力的动力薄弱。象征领导力是校长在确立和传播学校愿景、目标价值的过程中,对师生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所产生的影响力。一方面,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较高的流动性阻滞了这种愿景传播的可能。另一方面,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愿景自身还处于“离农化”和“适农化”的价值论争中,乡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和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诉求并非始终一致。由此,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的象征领导力陷入动力薄弱和方向不明的困境。
其三,教育领导力的专业缺失。教育领导力通常强调校长对课程与教学的支持与指导能力。有研究表明,校长致力于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建设,对教师专业成长和学生学业成就有显著影响。[5]但在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承担大量具体教育教学事务,一些校长资历较浅,在具体的教学上未必能起到引领与指导作用。
其四,人际领导力的主体缺位。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的人际领导力重心应着力在家校社协同育人,而实践中乡村小规模学校与乡村社区却日渐疏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乡村小规模学校处于“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下;另一方面是因为家长本身文化水平相对普遍较低、教育观念落后,很多家长忙于生计缺少对孩子的陪伴,而学校在家校合作方面也存在认识不足和畏难情绪。问题的背后折射出校长人际领导力的主体缺席。
其五,技术领导力的人文淡化。重物轻人是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技术领导力人文淡化的具体表现。乡村小规模学校处于教育层级的最底端,校长扮演着政策落实的执行者角色,在行政系统的问责话语体系中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影响,更多地只是完成任务的发号施令者,往往漠视了教师对精神安慰和人文关怀的需要。任务、问责成为校长和教师之间交流的媒介,久而久之,干群鸿沟加深,一些校长甚至陷入学校教学秩序失衡但却无计可施的境地。
三、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领导力培育的影响因素
乡村小规模学校置身于乡村社会环境,校长领导力的培育与提升,自然深受城乡二元体制、乡村社会环境和学校内部生态等复杂因素影响。
其一,激励机制体系拉动乏力,弱化职业吸引力。基于推拉理论视角,如果把乡村教育资源的贫瘠、环境条件的艰苦和发展空间的受限等不利因素视为推动优秀校长离开的推力,那么政策保障和激励制度则是吸引和留住优秀校长的拉力。当拉力弱于推力时,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职业吸引力不足,校长就容易流失。近年来,国家层面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文件,确立了校长培养培训、职级制改革和管理办法等制度。然而,实际情况是政策的实施和落地滞后,政策的引力明显不敌乡村环境艰苦的推力。
其二,培训体系不够系统科学,虚化专业支持力。校长的专业水平其实是校长领导力作用于教育教学实践场域的综合表现,而针对性、系统性的培训是提升校长专业水平的有效手段。自2010年“国培计划”项目实施以来,包含校长在内的乡村教师有了更多机会走出大山,接受新知识、新技能和新理念的培训,其力度、密度、高度空前,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这些培训在执行环节上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培训内容上倾向理论化,针对性不足;培训方式上偏向讲授式,形式单一;培训对象选拔上惯于简单化,以完成指标任务为目标,或以学校意愿性和积极性来安排,导致参训机会分布不均,出现随意性安排和系统性培训不足等问题。
其三,环境支持存在阻滞,降低自我效能感。社会心理学认为,人对工作的自我效能感影响着其目标选择、工作动机和努力程度。然而,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农村家长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教育观念落后、教育能力不足,乡村教育资源贫乏……多重“硬伤”作用下,校长无力或无心办学已成常态。
其四,个人内生动力不足,削弱个人感召力。在强烈的成就动机下,丰富自身学识,提高专业素质与综合能力,提升个人修养和魅力,校长才会富有感召力。专业知识和能力来源于学习和实践。然而,有针对中学校长的调查显示,坚持每天花一定时间读书的校长不多,有的校长没有读书的习惯。[6]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的读书状况也不容乐观。校长不读书,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校长的内生动力不足。
四、立足乡村振兴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领导力生成路径
基于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领导力的定位分析,针对现实问题与影响因素,我们建议从以下四方面着手培育、提升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领导力。
1. 优化具有引力的制度环境,厚植利于教育家型校长脱颖而出的组织土壤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能否在组织中实现个人需要,极大影响着个体的努力与付出程度。当下的制度优化,重点在选拔任用制度和激励保障制度,难点在考核评估制度。
首先,优化选拔任用制度。在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的选拔任用中,要克服任人唯亲的痼疾,建立从单一的“组织考察”选拔到多种方式并存的多维识才机制,综合运用校内推选、校外选派、竞争(聘)上岗、公开选拔(聘)等方式。
其次,优化激励保障制度。如罗尔斯主张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7]保障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待遇需要补偿机制。一是注重精神荣誉的激励。可借鉴对连续在乡村工作满25年、30年的乡村教师授予荣誉证书的办法,对达到一定任职年限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颁发相应的证书,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二是强化专业发展的激励。各级评优评先、荣誉称号评选和职称晋级要照顾到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要为其搭建成长平台,并将其纳入校长梯队培养中。三是健全绩效工资的激励。应加快落实校长职级制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薪酬体系,实行校长绩效工资单独核算,从彼多此少的“零和博弈”转向校长和教师的“双赢合作”。同时,实行“差序化”和“阶梯式”工资配套政策,“差序化”是指校长工资应根据学校边远程度体现出明显的“差序化”格局,“阶梯式”是指依据服务乡村年限划分不同档次。四是突出关心爱护的激励。对作出一定贡献的校长,可从政策上帮其解决如夫妻两地分居、子女入学等后顾之忧。
再次,优化考核评估制度。针对校长的考核,需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强化过程性考核,注重增值性考核,健全综合性考核,避免“事后”出台标准的“突击考核”“材料考核”等;同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以此作为对校长培养培训、奖优驱劣、提拔任用的依据,由此提升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的职业荣誉感。
综合运用以上机制,才能形成良性循环的校长领导力培育制度环境。
2. 构建科学有效的培养培训体系,提升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的专业素养
科学有效的培训是校长增长专业知识、提升专业技能、升华专业情感不可或缺的途径,有助于校长领导力从迷失到复归。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要统筹“国培”“省培”等培训资源,建立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培训档案,强化培训的跟踪性、持续性、系统性。
在培训对象上,重点建立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培训台账,推动培训资源向乡村倾斜。在培训内容上,围绕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领导力各维度的方向偏离问题,科学设计培训内容;注重实践性知识,搭建经验分享的平台;扭转“向城性”的城市文化价值取向,回归乡村教育的“乡土性”;重视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培训方式上,基于培训主体和培训内容的特点,采取讲座培训、影子(跟岗)培训、研究式项目化培训等相结合,促进培训方式多样化和培训效果可视化。此外,还要注重运用项目式学习和基于目标场景设计要素学习的理念与方法,以乡村小规模学校自身的问题、目标项目或特色项目为逻辑起点,以专项课题为学习载体,以校长和教师组成的项目团队為主体,教育行政部门和培训机构提供场景要素支持,建立起长效的主体内在需要的研究性学习机制,推动学习成果有效转化。
3. 营造协同合作的环境支持氛围,提高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的自我效能感
在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支持下,人的成就动机会被激发,进而形成坚定的职业信念。创设高水平的组织支持氛围,有助于激发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的成就动机,提升其效能感。
在教育主管部门支持方面,上级部门应鼓励和支持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依法大胆工作,做校长坚强的“后盾”。在教师支持方面,要在“县管校聘”的框架下赋予校长更多的教师任用权,还要引导教师树立支持校长管理育人的自觉意识。在家长支持方面,要引导家长充分利用各种渠道,更新教育观念,改进育儿方法;同时吸引家长通过家长委员会以正式或非正式方式经常性主动与学校沟通合作,形成教育的一致性。在“村两委”和社会机构支持方面,各级名师名校长工作室或其他社会性教育专业团体,要建立吸引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加入的机制,形成专业发展共同体;“村两委”要通过多种方式吸纳校长以“新乡贤”身份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支持校长利用乡村资源,促进乡村资源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4. 内砺自我实现的成长动力,修炼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的多维领导力
校长领导力的提升主要依赖于其内生动力的自我培育。基于乡村振兴的时代诉求,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水平、领导风格、品德修养,以优化技术领导力、人际领导力、教育领导力为基础,以培育象征领导力和文化领导力为追求,实现自身领导力的整体提升。
一是强化技术领导力的人文关怀。在学校制度形成过程中,校长要尊重教师的主体地位,致力于建构民主性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制度语境体系。
二是注重人际领导力的家校协同。校长要发挥乡村学校之于乡村家长的社会教育作用,促进家校协同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三是加强教育领导力的专业支持。校长既要基于问题导向,结合学校教師少的现实,构建实践交流、反思对话、相互促进的校际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又要担当起“临床实践者”“行家里手”的专家角色。
四是发挥象征领导力的示范意义。校长要直面师资不稳定、资源要素保障难的现实,重新定位学校价值,并通过具有意义生成、赋予性质的象征性活动和校长象征性行为的诠释,引导师生对学校价值定位的理解、认同和追随。此外,在目标公众中,基于关键事件筹划形式多样的公共活动,传播学校发展愿景,借以建立学校在乡民中的声誉和信誉,增进乡民对学校的信任和信心,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学生流失甚至促进部分学生回流。
五是重塑文化领导力的价值取向。校长需要构建可视化系统、精神系统和执行系统三位一体且独具乡村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路径,建立积极向上的组织行为准则和价值规范,引导学校成员成为“自我领导者”,自觉将学校办学理念内化为精神追求。同时,乡村为乡村学校的特色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文化传承和实践天地,而乡村学校肩负涵养乡村文明、助力乡村振兴的公共使命。因此,校长要用好乡村“宝贝”,构建极具乡土性的特色校园文化,为打造“小而优、小而精、小而美”的优质乡村小规模学校而努力。
校长的素质决定着学校的发展水平。培育和提升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领导力,迫切需要优化有利于教育家型校长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构建科学、精准、有效的支持校长专业化发展的培训体系,建设高水平的支持环境,更要激发校长炽热的教育情怀、坚定的教育信念和崇高的使命担当。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B/OL].(2023-07-05)[2023-07-10]. 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307/ t20230705_1067278.html.
[2] Sergiovanni,T. Leadership and excellence in schooling[J]. Educational Leadership,1984,41(5):4-13.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EB/OL].(2021-01-04)[2023-02-21].https://www.gov.cn/ 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
[4] 周晔,徐好好.乡村校长的文化使命:让乡土文化滋养乡村学校发展[J].中小学管理,2021(2):18-20.
[5] Nedim Ozdemir.Principal Leaderhip and StudentsAchievement:Mediated Pathways of Professional Community and TeachersInstructional Practices[J].KEDI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2019(1):81-104.
[6] 林文瑞,郑鸿明.中学校长读书状况的调查研究[J].中小学校长,2013(5):48-50.
[7]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4.
(编辑 齐 风)
注释:① 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YJCZH060)、2023年度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国式现代化引领贵州特色教育强省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GZGXRW144)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