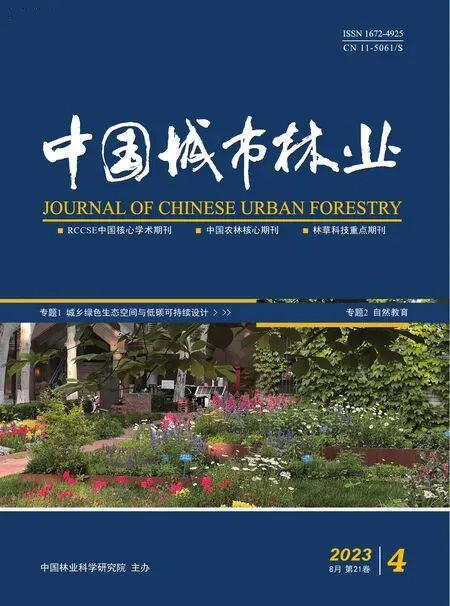从园记看宋代私家园林中生产性植物的应用*
谷光灿 王丽瑶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重庆市 400044
中国古典园林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但生产作为其起源功能之一不应被忽视[1]。本研究希望跳出目前从审美视角看待古典园林的习惯,探索还原宋代私家园林中生产性的原貌,而植物是人类重要的生存资料,是实现园林生产性的重要载体。2014年6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农业:生产性植物(对IAS16和IAS41的修订)》中对生产性植物进行了正式定义,即生产性植物是活的植物,用于生产或供应产品;预计在多个周期产出产品;作为农产品被出售的可能性很小,偶发的残余物出售除外[2]。参考以上定义,将本研究中的生产性植物定义为可以产出农产品,为人们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活的植物,主要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以及用来出售获利,不包括自然生长或人工培植用来盈利的观赏植物。
以往学界对生产性植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园林,且不多。以“园林”和“生产性植物”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仅检索出37条结果,且多将其作为“生产性景观的组成要素”进行探讨,如宋继华[3]研究了生产性景观中植物的应用。作为生产性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食景观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贺慧[4]等探究了通过社区花园可食景观的营造来构建社区传染性疾病防疫圈和蔬菜供应缓冲链。对于古典园林的生产性,张敏霞[5]曾梳理了中国传统园林中生产现象的发展变迁,但限于篇幅及研究内容,仅将变迁情况作为一个章节,并未对传统园林的生产性展开深入探讨。
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园林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也不例外。园林史论也称宋代园林已发展成熟[1],其造园方式、栽培技术等各方面都较为完善,并且出现了大量植物类专著,如《全芳备祖》《洛阳花木记》《洛阳牡丹记》《范村梅谱》等。宋代的农业生产也获得了大发展,北宋政权建立后奖励垦耕、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工具与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作物产量;经济作物种植扩大,其商品化程度也得到加强[6]。发展到后来,果树、蔬菜和观赏花木种植开始脱离粮食生产成为经营性农业的独立部门[7]。北宋“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8];南宋临安东门外一望无际都是菜园,“车驾行在临安,土人谚云: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盖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9];一些城市因种植花卉而闻名,如洛阳因牡丹著名;药用植物的栽培品种数量是前朝的两倍之多,且更加专业化、规模化[10]。宋代园林与农业的发展,为生产性植物在园林中的应用提供了极大的有利条件,因此,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园林上也有所反映。王柳丹[11]将宋代园林中的农业景观作为探究宋代农业景观文化及审美的支撑材料,并未对其进行针对性研究。综上所述,在宋代园林中,作为园林原始功能的生产性样貌是如何呈现的尚不明晰,并且根据柯律格的研究,明代中后期,人们对园林观赏性的重视逐渐甚于生产性,园林美学成为胜利的一方[12],因而有理由相信,在宋代园林中应该不乏生产性。康琦[13]对宋代私家园林中的植物造景进行了探讨,但仅对食用和药用植物的种类进行了列举,在种植方式、技术、特点方面针对的是用来生产或观赏的所有植物,且讨论观赏植物的比重较大,未能展示宋代私家园林中生产性植物的各方面样貌。因此,本研究对宋代园林的生产性进行梳理,探究宋代私家园林中生产性植物的原貌,以期为现代园林中生产性植物的运用提供参考。
1 园记的抽取
宋代的私家园林遗迹十分匮乏,且植物要素经过长时间的更迭变化,已与原貌相差甚大,不足以作为本研究的材料。描绘园林的宋画数量也不多,能体现私家园林生产性植物的作品更少,且辨别部分生产性植物难度较大,因此宋画也不太适宜作为研究材料。在文学作品中,相较于诗词中对园林只言片语的描写,园记更加详细地记录了园林中的地形营造、水系处理、植物配置、建筑空间等多方面信息。相较于宋代之前的朝代,宋代留存下来的园记相对丰富,是比较合适、容易获取的研究材料。
首先,以《全宋文》中392篇私家园记[13-14]、《洛阳名园记》中18篇私家园记[15]以及《癸辛杂识》中33篇私家园记[16]共443篇园记作为研究材料。其次,对明确体现植物生产性的园记进行抽取,选取园记至少需要满足以下一个条件:1)有确切文字表明人在食用、采摘、利用植物或劳作,如《休亭赋》的“凿池灌园以为笾豆”[17]、《薛氏乐安庄园亭记》的“沈浮瓜李”[18];2)具有一定规模且在人们普遍认知中具有生产功能的植物,如《盘洲记》中“木瓜以为径,桃李以为屏”[19];3)含有果、蔬、药等字眼,如《介立亭记》中“筑小畦以莳果蔬”[20]。最后,研读摘录园记中包含植物种类、种植规模、种植方式、利用方式以及与其他要素关系的文字,并标记出只出现今人熟悉的生产性植物名称如桃、李等。
2 园记的研读摘录结果
2.1 摘录结果概况
根据以上研读筛选方法,得到明确体现植物生产性的园记79篇,其中《全宋文》69篇、《洛阳名园记》3篇、《癸辛杂识·吴兴园圃》7篇,如表1所示。未明确体现植物生产性的园记47篇,其中《全宋文》46篇,《癸辛杂识·吴兴园圃》1篇。

表1 宋代私家园记筛选结果[13-16]
以上79篇园记共记录了77座园林,其中北宋30座,南宋47座。园址可考的园林有65座,从今天的地理位置来看,位于浙江、江西的园林最多,共31座,将近一半;其次为河南、安徽、江苏,共20座;川渝、福建、广东有较少分布;山东、山西、北京分别有1座。南方的园林远远多于北方,并多集中在长江流域,契合宋代长江流域经济、农业发达的史实。
根据园记名称(表1):可确定所属类型的园林有62座;以园来命名的园林22座;以建筑为核心的园林以亭与堂居首,分别有10座;其他还包括庄、圃、洲、轩、庵等类型,占比较小。
本研究将生产性植物分为食用、药用、居家用3类。居家用生产性植物仅出现在3篇园记中,如《乐圃记》写道“桑柘可蚕,麻纻可缉”[21];《农隐记》记述“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供丝麻”[22];《耦耕堂记》 有“植材千章”[23]之句。以上均体现植物供丝麻、供材的作用。
宋人在私家园林中种植生产性植物,不仅供自家食用,还会宴请村邻亲朋,有6篇园记对此进行了记录,如朱长文[21]在乐圃中“摽梅沈李,剥瓜断壶,以娱宾友,以约亲属”;黄裳[24]记录了其友的园林,“宾客至止,捕鱼于池,摘果于林,破榖于场,趋雉于野,酒觥碁局,为宾客欢,涟漪之上,尽日而后已”;潘畤[25]记录了他在月林堂的午后,“折莲取菱芡、瓜果以侑村醪,杂坐茂树修竹间,有杜陵‘共醉终同卧竹根’意味”。
2.2 植物种类
经过抽取筛选,共统计出59种有具体名称的植物,分为果、蔬、药、粮4大类,其中果有21种,蔬有17种,药有19种,粮有2种,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宋代私家园林可食植物种类[13-16]
表2中部分植物仅古今称谓不同,卢橘即枇杷,藿是豆叶,薤是藠头,独椹是黄芪,戎葵也就是蜀葵。菘是古代对白菜的称谓[26]。关于秫,《古今注》曰:“稻之黏者为秫”[27],园记中,秫多用来酿酒,如《大愚堂记》中有“种秫以备酒材”[28]。
未明确体现植物生产性的园记中,多次出现了包括桃、李、梅、荷等在内的生产性植物。在443篇原始研究材料中,34.3%都出现了竹,由于竹种类繁多,形态差别大,且园记中大多未记录竹的种类,此次暂不对竹作讨论。
在抽取出的园记中,出现具体蔬菜或者蔬字的有30篇,出现具体水果或者果字的有36篇,出现具体药类和药字的有16篇。据笔者推测,果类出现多于蔬类或许是因为果类经济性高,且多为木本,对种植技术专业性、土地面积等方面的要求相对较低,观赏价值和单株产量一般高于蔬菜。而粮食作物出现较少的原因是园外有专门种植粮食的土地。
2.3 种植规模
种植规模可以直观地反映生产性。从宋代私家园记中总结出4种表达生产性植物规模的方式,即用面积表达、用数量表达、通过种植方式表达以及通过利用方式表达。
用面积表达生产性植物规模的关键词语为:亩、顷、里、畦、畹、区、弓。采用这种方式表达规模的有9篇园记。可明确计算出面积的有赵氏清华园的“秫田二顷”[16]为13.33 hm2;《朋溪双莲记》中植莲的十亩大池[29],约6 667 m2。或用距离单位表示面积,如叶氏石林中“大抵北山一径,产杨梅,盛夏之际,十余里间,朱实离离,不减闽中荔枝也”[16],《稼轩记》中“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30],十弓为17.93 m。畦和畹在古代也表示面积,一畦为3.33 hm2,一畹为2.0 hm2,但置于原文中考虑,那么独乐园的“百有二十畦,杂莳草药”[31]中一百二十畦为400 hm2,《芗林铭》的“蓺兰九畹”[32]中九畹为18 hm2,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认为以上两篇园记中的畦和畹不作面积单位,而作为种植场地。另外,归仁园“南有桃李弥望”[15]虽未直接描写桃李种植面积,但“弥望”一词意为一望无际,侧面反映了植物规模之大;莲花庄“荷花盛开时,锦云百顷”[16]100顷为1 hm2,显然这是作者的夸张描写手法。
用数量直接表达生产性植物种植规模的关键词语有:十、百、千、万等,量词如种、株、本、章等,还有用盛、林等字间接表达数量。在采用这种表达方式的22篇园记中,能明确得出植物规模的植物数量最多的为葛氏草堂中的“植竹桧果花几万本”[33];单一种类植物数量最多的是来喜园中的“有桑千株”[34]以及《东篱记》 中的“植千叶白芙蕖”[35]。章参政嘉林园“桑林、果树甚盛”[16]是对数量的间接表达。
通过种植方式表明植物规模的关键词语有:圃、畦、杂、田、畴、畛、区、坞等,这些词反映了在某种特定的场地内,生产性植物形成了一定规模。通过此种方式体现规模的园记有22篇。这些园林中,种植场地大多被划分为一块块方形的区域,“分沟裂畦,种种莳植于其间”[36];或在路径两边种植,如“蹊分桃李”[37]。
通过利用方式表达的园记如《安老堂记》中“郭内之圃足以给葅茹”[38],《荷嘉坞记》中“我秫我田,亦足以酿”[39],植物足以作为日常蔬食、酿酒材料,必然具有相当规模而不会是一两株。
2.4 种植方式
按植物种植种类进行划分,分为同种种植、同类种植、间种杂植3种。
同种种植,指相同名称的植物规模种植,有26座园林采用此方式。较为典型的如赵氏菊坡园“中岛植菊至百种”[16];《野堂记》记载的“桃、杏、李、来禽,列植区分”[40];《盘洲记》记录了洪适根据植物生长习性进行种植“西瓜有坡,木鳖有棚”[19]。
同类种植,即同为果、蔬、药、或粮的植物共同种植,有18座园林运用这种方式。独乐园中“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杂莳草药”[31]。为了辨别草药品种,司马光为不同草药制作了标牌;《来喜园记》中明确写道“蔬有畦,药有陇,芰有沼,藕有渠”[34]。
间种杂植,即不同类植物混合种植的方式,仅有4座园林运用。王禹偁[41]在野兴亭中“杂以蔬果,间以花卉”;吴儆[42]在竹洲中“借地于邻,复得一亩许,杂种戎葵、枸杞、四时之蔬、地黄、荆芥、闲居适用之物”。
2.5 植物与其他要素的营造关系
2.5.1 与地形的关系
宋人种植生产性植物,或顺应地形,或改造地形。薛氏乐安庄园亭“庄西北隅据垣乘高,下列蔬圃,时使老圃村童,引水溉畦,名曰‘瞻蔬台’”[18],园林利用高差营造了观赏生产性植物的空间;在西园中,何恪[43]对生产性植物的营造顺应了原有地形,“依山升降而畦之,艺以杞菊”“堂外地数十亩,其平如掌,梅杏李柰橘柚各植以类,而坞列之”。《二亭记》记载“钱塘关氏于其居之右地积土为坂,伐石为坛,而蓺以药”[44],反映了园主为种植草药而对地形进行了处理。
2.5.2 与建筑的关系
一些园林将生产性植物种植在建筑附近,方便采摘。竹洲“庵之前种桃李卢橘杨梅之属,迟之数年,可以馈宾客及邻里”[42];刘安上[45]将父老乡邻赠予他的花卉、药果“杂植亭之左右,以备采掇服食”;九华药圃“药斋居中,用药之书聚焉;药轩在北,治药之器具焉”[46],便于滕润之对药草的利用。还有园主根据植物的生产性对场地进行命名,例如司马光的采药圃、薛俅的瞻蔬台、洪载的小桃源,甚至从一些园记的名字,像《稼轩记》《观莳园记》,可直接看出园林的生产性。
2.5.3 与水体的关系
生产性植物与水体结合,或水体为植物生境,如合州苏氏北园“堂后凿池种藕”[47];或围绕水体配置植物,如《牧庄记》记录蜀阜园“环池四面宜枨宜橘,宜葡萄,宜来禽安石榴之类,亦无不种”[48]。
2.5.4 与石类的关系
九华药圃中园主“择九华之药可以种者种之,可以移者移之,分畦以别其品,立石以识其名”[46],这里的“石”并非用来观赏的置石,而是用来标记药草名称的“铭牌”。
2.5.5 与其他植物的关系
司马光[31]在独乐园中将观赏植物与生产性植物相结合,把竹作为藤本药草的攀援架,“植竹于其前,夹道如步廊,皆以蔓药覆之”,藤本的药草弥合了竹干之间的间隙,增强了步廊的围合感。
3 宋代士人对生产性植物种植的影响
3.1 园主身份以士人居多
考察所选的77座私家园林,能够确定园主姓名身份的园林有72座,其中园主为士人的有59座,包括司马光的独乐园、苏辙的颍川居、辛弃疾的带湖居所、陆游的三山别业等著名文人的园林,也包括童仲光的盘隐园、杨平叔的善圃等普通士人的园林,表明士人的确是宋代私家园林的重要所有者。另外,园主为名门贵族的园林仅有8座,其余园主为道士、郡人和医者。园主为士人的园林有21座为园主亲笔作记,园主非士人的园林仅有2座的园记作者为园主。
3.2 士人生产观念的影响
园林中生产性植物的呈现,受士人土地资源利用观念的影响。士人不仅将园林作为观赏游憩场所,而且还想从园林中获取生产性利益以及生活资料。比如,司马光崇尚节俭,不同流俗,以他当时的身份,完全可以建造更大的园林,但他仅用地1.33 hm2建独乐园,在满城种花的风气下莳药百余畦,反映出对园林生产性的看重;再如,朱长文作为家中长者,为让族中子弟安心受教,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为此他在乐圃中种植了足以供衣食的植物。
3.3 士人收入的影响
宋代国家对士人提供优厚待遇,加之当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49],使得士人群体拥有相当面积的土地,为建造园林提供了条件。在上述园记考察结果中,不乏面积很大的私家园林,如章参政嘉林园可达二顷,即13.3 hm2;南沈尚书园百余亩;能容纳几万株植物的葛氏草堂,种植十里杨梅的叶氏石林,必然规模相当庞大。
3.4 士人养生习惯的影响
宋代士人多关注医学,并注重养生,多有食素、种药的习惯,他们认为药食同源,追求素食就是追求清高淡泊的品行[10,50],因此多有在园林中种植食用和药用植物的情况。园记考察中发现,南方种植生产性植物的私家园林远远多于北方,与张洁琨[50]研究中南方士人食素现象多于北方的结论是相符的。晏殊在《中园赋》中记录了中园包括果蔬药草在内的60余种植物、刘克庄在《小孤山记》中记载了林公遇的林氏园植梅数百株、钱时在《牧庄记》记载了自己的蜀阜园果木林立的盛景,以上作者均为食素士人。另外,陆游的三山别业中蔬菜约10种、果树约11种,在布局上,有东园(农作园)、南圃(南园)、西圃(药园)、北圃(蔬菜园)[51]。陆游有4篇名为《种菜》的诗篇,如“引水何妨蓺芥菘,圃功自古补三农。恨君不见岷山芋,藏蓄犹堪过岁凶”,还有题为《蔬食》 《治圃》的诗歌,甚至有组诗《蔬圃绝句》(七首)《蔬园杂咏》(五首)[52],表明他对食蔬种蔬的赞美和喜爱。
4 结论
通过对宋代私家园林生产性植物各方面情况的提炼展示和举例,可以发现宋代有超过1/4的私家园林都种植了生产性植物,这些园林大多分布于长江流域中下游。在这些园林中,生产性植物甚至和观赏植物间种在一起,表明其审美功能和生产功能并没有严格区分,其功能以食用和药用为主。植物种类主要为果、蔬与药,其中出现最多的种类是果。植物的种植规模极为灵活,并没有精确的范围。被采用最多的种植方式为同种种植,其次为同类种植,间种杂植最少。园主营造其他相关要素时,目的是如何使生产性植物发挥最大的价值。士人是园主中的重要群体,其生产观念、收入以及养生习惯都推动着生产性植物在私家园林中的种植。宋代私家园林的生产性植物具有丰富多彩的全貌,从种类到与其他要素的配置方式都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