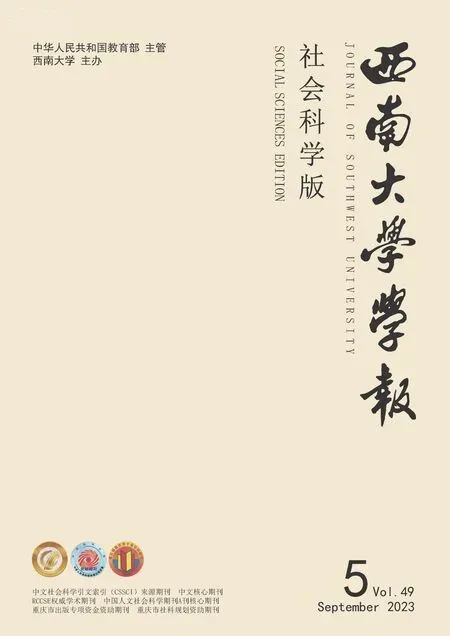石门坎苗文文献概况与研究展望
黄 秀 蓉,潘 源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 重庆 400715)
一、石门坎苗文的创制与发展
石门坎苗文(亦称“老苗文”或“柏格理苗文”),一般认为由英籍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Samuel Pollard)带领苗、汉人士,在1905年使用苗族服饰上的一些图案符号、一些用以记事的古老符号与部分大写拉丁字母,创制出一种以贵州威宁石门坎苗语语音为标准音的拼音文字。但也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如民国时人王建光曾经撰文说明,认为石门坎苗文的创制者并非西方传教士柏格理等人,而是“苗人的先进者张岳汉先生”[1]。这套文字,有着如下一些典型特点[2]:每个字(音节)由一个大字母(声母)和一个小字母(韵母)组成,小字母的大小只有大字母的四分之一,字母的书写具有汉字楷体的一般特征;音节的声调用小字母在大字母的不同方向来表示(正上方、正下方、右侧的上、中、下),零声母音节根据其声调的高低直接写小字母。石门坎苗文的创制,集中了苗族、汉族、西方传教士等不同人群的智慧,吸收了苗族传统文化、汉字结构、西方拉丁字母大写形式等诸多文化要素。随着石门坎苗文的出现,一个神话开始在乌蒙苗区传播,即苗族以前丢失的文字现在找到了,这套文字从苗族衣裙中被重新恢复出来,正是祖先遗失的文字。因此,新创制的文字很快获得乌蒙苗族的认同,也获得了传播与使用的力量。可以说,石门坎苗文的创制,开启乌蒙山区(包括滇东北、黔西北以及川南地区)苗族(1)乌蒙地区的苗族,基本都属于苗语西部方言,主要包括自称为“阿卯”(汉族等他称为“花苗”)的滇东北次方言群体与自称为“蒙”(汉族等他称为“青苗”“白苗”等)的川黔滇次方言群体。石门坎苗文的主要使用群体是“阿卯”群体,少部分川黔滇次方言的“蒙”群体也有使用。人民进入文字社会的新时代。千百年来乌蒙苗族群体传统文化从口耳相授的语音传承转变为既表音又表意的文字传承,现实中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也由“古歌”“刺绣”“结绳记事”“刻木为契”等原始记录转变为方便快捷的文字记录。石门坎苗文的创制及在乌蒙地区的推广使用,在一定历史时期促进了该区域苗族人口素质的提升、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乌蒙地区的苗族群体及其他群体(2)该地区的其他民族如东部傈僳人以及彝族的诺苏支系、拉卡人,都曾用石门坎苗文来记述本族群语言,尤其是在宗教文献中更为典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一百多年过去了,石门坎苗文至今仍然在这些地区被广泛使用。它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符号,而更多地承载了该地区苗族人民百年来的文化传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成为广大苗族同胞的精神依托。
石门坎苗文在初创时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因此,按照语言文字的一般发展规律,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石门坎苗文被不断地修订,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版本,主要包括:(一)初创时期的版本;(二)1932年杨荣新、杨荣辉、王明基等人修订的版本;(三)1949年文字改革版本;(四)1980年代“规范苗文”版本。除了以上四个版本,还有一些人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石门坎苗文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改,并形成一些文献,但并没有得到其他使用者的采用。总的来说,石门坎苗文各个时期的版本略有差异,但都是在初创版本上的增益与改定,主要包括声调的增加与位置的调整、苗语声韵母的增加以及非苗语韵母的增加、浊音符号的增加,等等。因为不同版本的石门坎苗文在文字表现形式上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创文字的逐步发展与完善过程。
从初创时期开始,石门坎苗文就被广泛用于基督教宗教文献的翻译与宗教仪式活动、学校教育、交流沟通以及记事、记账等日常生产生活,形成了大量的石门坎苗文文献。如此丰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石门坎苗文文献,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它的研究,更是几乎无人涉及的空白领域。目前所见,只有东人达《黔滇川老苗文的创制及其历史作用》[3]、王永华《滇东北老苗文的历史与现实探索》较为集中地对石门坎苗文的发展历史及部分苗文文献进行了介绍[4]。杨云惠等《滇东北次方言老苗文与苗文谱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上、下)对使用石门坎苗文字母创制苗文乐谱进行了研究[5]。其他诸如杨凤华、熊玉有《中国西部苗文文献综述》[6]、蒙昌配等《中外比较视域下的世界苗文研究史——世界苗学谱系梳理研究之一隅》[7]、Joakim Enwall的AMythBecomeReality:HistoryandDevelopmentoftheMiaoWrittenLanguage(《神话成为现实:苗文之历史与发展》)[8]等论著,大多把石门坎苗文置于西部方言苗族乃至于整个苗族语言文字史中进行介绍,并没有凸显石门坎苗文文献自身的特殊性与重要意义,也没有对现存文献的文本类型、内容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石门坎苗文文献现状及对石门坎苗文文献的未来研究趋势进行简要概述与分析。挂一漏万,敬请补充指正。
二、清末民国时期石门坎苗文文献概述
石门坎苗文的初创目的是在乌蒙苗族区域传播基督教信仰。因此,现存初创时期的石门坎苗文文献,几乎都为基督教宗教文献的苗文译本。发展到后来,石门坎苗文逐渐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推广。清末民国时期,石门坎苗文文献主要包括了如下几类:一类是基督教经书与赞美诗的苗文译本;一类是苗文教材;一类是记录苗族传统文化的苗文读本;一类是记录苗族传统歌谣的苗文文献;一类是介绍生活常识与科普知识的读本;一类是苗文报刊;一类是新创制的苗文歌曲,包括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苗文歌曲、苗文翻译的抗战歌曲以及苗文翻译的革命歌曲等,内容非常丰富。
(一)清末民国时期石门坎苗文翻译的基督教宗教文献
石门坎苗文创制后,最早被用于基督教宗教文献的翻译。因此,清末民国时期现存石门坎苗文文献中以基督教宗教文献居多。最早的宗教文献应是1908年翻译的花苗《约翰福音》[9],该书为大英圣书公会在上海印制并发放给花苗基督教信徒,全书共计124页。稍后有1910年的《马可福音》[10]、1912年的《马太福音》[11]相继被以石门坎苗文译出并在乌蒙苗族中流传使用。1915年《使徒行传》[12]以石门坎苗文译出,仍然由大英圣书公会在上海印制,全书共计106页。1925年,王慧明、杨明清编译《川苗福音诗》,收录《马可福音》中赞美诗80首,附有苗文音乐乐谱和苗文大小字母表。1936年,基督教《新约全书》[13]以石门坎苗文完整译出并印刷出版,石门坎苗文也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同年,王树德、王正科、杨荣新等再次以石门坎苗文翻译出了《川苗福音诗》。1947年杨荣新重译《新约全书》[14],由中华圣经会石印发行。
石门坎苗文在基督教宗教领域的应用,不仅仅限于乌蒙地区的苗族,也为该地区其他信仰基督教的人群所借用,用以记音他们的语言,形成了又一批基督教宗教文献。这部分文献主要包括1912年大英圣书公会为东部傈僳人信教群众编印的《马太福音》[15](全书128页)、1917年的《路加福音》[16](全书136页),以及1928年的《使徒行传》[17](全书192页)。1912年大英圣书公会为拉卡信教群众编印《马太福音》[18](全书96页)。1923年大英圣书公会为彝族诺苏支系信教群众编印《路加福音》[19](全书157页),1926年又为他们编印《使徒行传》[20](全书200页),等等。用石门坎苗文字符来为苗族以外的其他人群翻译基督教宗教文献,这对石门坎苗文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资料,一直到今天,滇中滇北一些信仰基督教的非苗少数族群仍然还在使用石门坎苗文翻译的基督教宗教文献。
(二)清末民国时期石门坎苗文编印的教材
随着乌蒙苗族各地教堂的兴建,与之相伴的各地教会学校也随之兴盛。清末民国时期乌蒙苗区的教会学校,是中国最早实行男、女合校的学校,也是最早实行汉、苗双语教学的学校。石门坎苗文创制以后,就被用作苗语教学的载体在各个教会教学以及平民夜校中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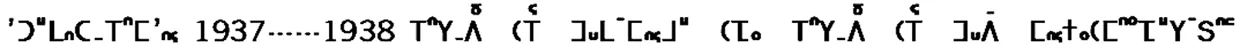
此外,民国时期乌蒙苗区的各地学校,也有专门以苗族历史及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石门坎苗文教材,如《花苗新课本》等,这些苗文教材主要以苗族口传历史、民间故事以及传统歌谣为主要内容,在学习石门坎苗文的同时,苗族传统文化也得以传承。二十世纪30年代由著名苗族教育学家朱焕章先生编写的汉文版《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22](又名《滇黔苗民夜读课本》),也部分翻译成石门坎苗文,供成年苗族人在夜校学习时使用。(4)团队目前还没有收集到石门坎苗文版的《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但TSHH先生告知是有的。访谈对象:TSHH;访谈时间:2023年1月24日;访谈地点:云南昆明TSHH家中。在学校教育之外的平民教育中,柏格理等人还用石门坎苗文编写了《苗语基础课本》《苗族原始读本》等教材。《苗族原始读本》作为苗族成人扫盲课本,采用了通俗的问答形式,介绍一些自然与生活知识。
(三)清末民国时期其他历史文化及社会经济的苗文文献
存世清末民国时期关于乌蒙苗族历史文化及社会经济的石门坎苗文文献,不如前述基督教宗教文献丰富,主要有如下一些:
1.碑刻谱牒类
在历史文化及社会经济领域里,现存最早的石门坎苗文文献应是一幅苗文石刻。该石刻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红土地镇新乐村委会(原名法者),文字刻在一块高约3米、宽约2.5米的红砂石上,全文共56个字符,分为三个部分,被称为“罗家沟摩崖苗文石刻”。该石刻的主要内容朱文光先生译为:“基噶这块地(原是)窝卡尼阿(这个人)耕种,狗年张成兴到达这里后由(张成兴)耕种。这些字我不会写,是上帝教我写的……(刻字时间是)狗年蛇月十二日,属羊这天刻这些字。……(有人会因)刻了这些字感激我们。”朱文光先生在仔细对该文本进行研究后,认为该石刻就是乌蒙苗族传说中的“阿尤黑的写字岩”,是由苗族起义军首领阿尤黑(张成兴/才)与他的好友于1911年制作[23]。
1914年,石门坎光华小学修建了由昭通人士李国钧撰写的“溯源碑”。此碑两面分别雕刻石门坎苗文与汉文,主要记录基督教在花苗群体中的传播史。两年后,石门坎苗族群众再次以新创之苗文再立新碑——“苗族信教史碑”,讲述花苗群体的历史和基督教带给苗族的“新生活”。此两块碑刻的原碑已不复存在,但其内容已被记录下来,经后人重修后现存于石门坎的石房子内。
石门坎苗文的倡导者之一柏格理于1915年在石门坎逝世并葬于此地。石门坎苗族为其修建了坟墓。现在所见的柏格理墓碑上,有石门坎苗文记录这位传教士传奇的一生。另一英国传教士高志华于1938年逝于石门坎,苗族群众为其修墓立碑,碑文以石门坎苗文简述其一生事迹。
乌蒙地区苗族在石门坎苗文创制之前,没有自己的文字,家族世系只能依靠口传记忆。石门坎苗文创制出来后,一些家族开始用文字记录自己家族的世系,现存最早的石门坎苗文家谱为《张汉阿尤亥家谱》(内部资料)。该家谱在1944年用石门坎苗文整理编撰,1963年重修,2020年再次修订(5)《张汉阿尤亥家谱》的2020年修订版已主要使用汉文。。
2.苗文词汇汇编类
石门坎苗文一经创制,便在乌蒙地区的苗族群体以及其他群体中传播开来,为了便于推广使用,部分苗族知识分子以及西方在石门坎的传教士便开始了用石门坎苗文汇编苗文词汇的工作,现今存世的民国时期石门坎苗文词汇汇编主要有以下两类:
一是苗族知识分子王建光曾经编著过一本苗汉对照的《苗文单字汇》,记录了在生产生活中使用的主要苗文词汇。全书共计34页,记录苗文单字词超过一千多个[24]。
一是英国传教士张绍乔和张继乔于20世纪30、40年代在石门坎地区生活时,在当地苗族人民的帮助下,用石门坎苗文字符收录整理了大部分的传统苗语词汇,并在回到英国后将这些石门坎苗文词汇翻译成了英文(6)该苗文词汇手册现在并没有正式出版,笔者已收集到电子版。。在该苗文词汇汇编中,收集了大量的中古苗语词汇,是我们了解“阿卯”支系苗族的语言从近代以前向现代转换的非常有用的关键性资料。
3.传统文化汇编类
在20世纪30年代,苗族知识分子王明基、杨荣新等人开始收集乌蒙苗族的古歌、传说故事、童话寓言以及民俗文化,并以石门坎苗文加以记录,形成两册珍贵文献。1936年,英籍牧师王树德离开石门坎时,带走了这些苗文资料,其中一册在战乱中散失。50年代前后,基督教循道公会英籍教牧人员从乌蒙地区撤离中国时,又带走一批民国时期用石门坎苗文收集整理的民间文学资料,其中张绍乔(R.Garry.Parsons)、张继乔(R.Kenneth.Parsons)兄弟带走的较为完整。二人回国,用了将近三十年时间,将这些资料系统整理归类并译成英文(其中一部分还译成了拉丁苗文),并于20世纪80年代在计算机专家的协助下,开发出石门坎苗文的计算机文字处理系统。2001年,二位张先生专门创建网站,(7)该网站由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负责营运。将其花费毕生精力整理好的“中国西部苗族古歌故事集”放在该网站上,供感兴趣的人士自由下载。
“中国西部苗族古歌故事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创世纪与人类早期:洪水故事、开荒故事以及巫医传说”,此部分共计52首诗歌。第二部分“苗族历史:早期首领、与华夏集团的冲突、失去家园、迁到诺地(Nuo)、部漏(Byu-no)与骚漏(Sao-no)的英雄传说、后来的事件和最近的迁徙”,此部分共计65首诗歌。第三部分“聪明与愚蠢:人与动物的故事、回报:华夏背景里的诗歌叙事——人与动物的互变、关于老虎的故事”,此部分共计85首诗歌。第四部分“苗族的社会生活:传统婚俗与婚礼歌、情歌、私奔歌、吊唁歌,神灵崇拜与神灵崇拜歌”,此部分共计75首诗歌。此故事集,几乎涵盖了近代以前乌蒙地区苗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们今天研究乌蒙地区苗族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4.翻译和创制的歌曲类
在清末民国时期,苗族知识分子阶层利用石门坎苗文翻译并创作出相当多的歌谣,在各个学校以及民间传唱,成为石门坎苗文在民间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翻译类歌曲主要有两类:一是对《圣经》赞美诗的翻译,存世文献主要有基督教赞美诗(1914年),该书为77页的印刷本。1936年时,杨荣新等人再次用石门坎苗文译出新版赞美诗,该书为石印,共74页。1938年,杨志成等人用石门坎苗文符号设计了7个音乐简谱符号,翻译出苗文版《赞美诗》,共收录基督教诗歌275首。到1940年,韩杰翻译苗文版《颂赞诗歌》,共收基督教赞美诗歌289首。二是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苗族知识分子杨荣新等人以石门坎苗文翻译了大量的汉文抗日歌曲以及革命歌曲,包括但不限于《流亡三部曲》《开路先锋》《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等。
创作类歌曲主要有:朱焕章的《苗族有许多还未觉醒》《孤儿歌》《私立石门坎中学校歌》,李正明的《走走走》《唤醒民族奋进》《恶霸抓兵歌》《伤心歌》《思念故乡》《江山美如画》《大箐林有雷鸡》《潮水与风飘来》《天上有只鹰》,张文明的《打铁要自己腰身硬》,韩正明的《要让女孩读书》《到石门坎去读书》,王明基《可怜的盲人》《时间就像花开》,杨荣新等人《思念我家乡》,等等。这些用石门坎苗文创作的歌曲,从形式上看,既继承了苗族传统古歌自由式的特点,又吸收了汉文诗词注重韵律的特点,得以在乌蒙苗族中广泛传唱。
事实上,清末民国时期石门坎苗文的应用范围,远不止以上几类,随着学校教育与平民教育的逐渐普及,60%以上的乌蒙苗族群众都能较为熟练地使用石门坎苗文(8)访谈对象:TSHH;访谈地点:昆明TSHH家中;访谈时间:2023年1月24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更多的关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苗文文献产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对一些重要的政府文件的翻译,包括王建明等人对《总理遗嘱》的石门坎苗文翻译[25],以及《三民主义》与《中国之命运》的石门坎苗文翻译[26]。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其他一些因素,一些以石门坎苗文书写的民间文献已经永远消失了,比如在1930年代曾经由石门坎教会创立并发行的《苗文月刊》,一度成为以石门坎为中心的川黔滇苗族地区的主要信息来源,但是至今没有发现任何一期刊物的原件,成为不能弥补的巨大遗憾。
三、新中国成立后石门坎苗文文献概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1月,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省,乌蒙地区的苗族群众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的到来,在欢迎人民解放军的旗帜上便有以石门坎苗文书写的“人民解放军是苗族人民的救星”字样(9)此资料为一幅黑白照片,因为拍摄角度问题,苗文字符不是非常清晰。。人民政权完全接管西南边区后,党中央开始关注并推进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乌蒙苗族地区广泛使用的石门坎苗文,继续得以使用。1956年后,中国中央政府为中国三大方言区的苗族各创制了一套苗文,同属于西部方言区的乌蒙地区不同支系苗族,自此有了三套苗文,即川滇黔次方言苗文、滇东北次方言苗文(拉丁字母新苗文)以及石门坎苗文(老苗文)。前两套苗文属于拉丁字母苗文,由人民政府统一推广使用。石门坎苗文则一直处于民间层面使用的状态。
到20世纪80年代初,滇中滇北地区的苗族知识分子集合在一起,对石门坎苗文进行了规范整理,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石门坎苗文存在的问题,称之为“规范石门坎苗文”(简称“规范苗文”,下同)。“规范苗文”获得云南省少数民族语委会的官方支持,在滇中滇北苗族地区推广使用。此后,石门坎苗文的使用开始出现区域性差异,即黔西北、滇东北区域的苗族在民间层面仍然使用石门坎苗文,而滇中和滇北的苗族则开始使用“规范苗文”,形成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文献。
(一)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苗文翻译文献
用石门坎苗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文件的翻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已开始。1951年,杨荣新和张有伦受命来到重庆,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份重要的文件翻译成石门坎苗文并随即在乌蒙苗族地区颁行,以在广大苗族人民群众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同时,他们还用石门坎苗文译出了《对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应有的认识》等文件。这些重要文件的翻译,为乌蒙地区苗族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滇东北次方言拉丁苗文以及川黔滇次方言苗文创制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党中央和政府文件的翻译,就几乎没有使用石门坎苗文了。
“规范苗文”产生后,开始被用来翻译各类重要的政府文件以及中华优秀文化读物,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云南少数民族对外交际手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明读本·传统美德》《一家人过好日子》,等等。这些政府文件以及中华优秀文化读物有效宣传了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对促进民族地方发展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对苗族传统文化进行整理的文献
在1956年滇东北拉丁苗文创制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苗语小组使用石门坎苗文在威宁地区收集了一些苗文资料。20世纪50年代后期,威宁的韩绍刚等人也用石门坎苗文收集了一批民间文学资料。张斐然、杨忠德用老苗文整理油印了一套30年代收集的古歌资料。另有课题组收集的一小部分珍贵的私人书信是这一时期石门坎苗文文献的代表。2007年,毕节市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组织人员,以苗、汉、英三语形式出版了英国张绍乔、张继乔先生收集的苗族民间故事,书名为《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27]。杨体耀先生用石门坎苗文收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集》(内部资料),不但包括了大量的苗族民间故事,还把在苗族地区流传的部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民间故事也收入其中,体现了石门坎苗文在不同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另有部分基督教经书继续出版发行,包括1988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发行的《苗文新约全书》[28],2010年云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云南省基督教协会编印《苗文颂主圣歌》等。2019年,杨世武主编的《西部苗族古老歌》[29]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是最新出版的石门坎苗文文献。
(三)反映乌蒙地区苗族社会经济情况的文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民族地区的教育情况,在为各民族创制文字的同时,开始在民族地区学校推行民、汉双语教学。在20世纪80年代后,滇中、滇北地区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始使用“规范苗文”编写小学教材,主要包括如下一些:1988年的《苗语文课本》(第一、二册)、1988年《苗文数学课本》(第一册)、人教版系列小学教材(一年级《数学》上下册、一至六年级《语文》上下册、一至四年级《小学语文教辅》上下册)。与教材配套的还有2012年的《小学生苗汉成语词典》以及2015年的《小学语文词语手册》。“规范苗文”教材的出版与使用,促进了石门坎苗文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
除了政府官方对“规范苗文”的推行外,一些苗族知识分子开始以个人的力量来推动石门坎苗文的传承。近些年来,昆明的陶绍虎陆续编印了《苗文初步》(内部资料)、《大花苗石门坎语音初探》(内部资料)、《花苗文简略导学》(内部资料)等石门坎苗文教材,免费提供给愿意学习石门坎苗文的人士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乌蒙地区的苗族知识分子开始用石门坎苗文收集一些苗族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资料,在各个方面均有体现。张文德编撰了《苗族中草药》(内部资料)(10)张文德在编撰《苗族中草药》,对石门坎苗文进行了一些基于他自己理解的改进。因此,这本《苗族中草药》中所使用的石门坎苗文,既不同于以往各个版本的苗文,也不同于滇中滇北地区的“规范苗文”,比较难于理解。、朱文光编撰了《阿卯迁徙史》(苗汉双语,内部资料)、《滇中苗族草药》(2卷,苗汉双语,内部资料)。另有一些创作或翻译歌曲集,如1982年宜良县文化馆编印的《苗族创作翻译歌曲选》(内部资料)、2001年编印的《苗族歌曲选》(内部资料)、2001年张建明编印的《苗族歌曲选》(内部资料)、2004年杨体耀选编的《百年苗族歌曲选(1905—2005)》(内部资料),等等。这些以石门坎苗文编印的各种歌曲集,虽然没有公开出版发行,而是以内部资料的方式在乌蒙地区苗族群体之间流通,为石门坎苗文的传承和发展做了较大的贡献。
另外,在乌蒙苗族地区民间社会交往中,也产生了不少石门坎苗文文献,主要包括一些私人信件、借条等经济文书以及门联、宣传标语、各种告示、广告,等等。这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乌蒙苗族在当代的生活状况,为我们分析当下乌蒙地区苗族的发展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资料。
四、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特点
由于石门坎苗文并不是由专门的语言学人士创制,其创制、使用时间也较短,和其他种类文字的文献相比,石门坎苗文文献具有一些区别性的特点。
(一)石门坎苗文文献文字的不规范性特征
由于石门坎苗文既不是纯粹的拉丁字母文字,也不是汉文这样的象形符号文字,而是二者加上苗族传统记事符号综合而成,加之苗语的音调复杂,共计八个调位,这导致石门坎苗文在初创时期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尤其是不能对石门坎苗语进行全面记音的缺陷。一些使用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初创的石门坎苗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形成了不同时期的版本。这些不同的版本中,有的有浊音符号,有的没有;有的是五个调位,有的是六个调位,有的是八个调位,调位的位置也在发生着变化,如此等等。即使是相同的基督教宗教文献,在不同时期的石门坎苗文译本,所使用的苗文也有一定的差异。且因为苗文本身的不规范性,导致它所记述的事情一旦脱离原文语境,便会表现出极大的歧义。甚至出现有的使用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石门坎苗文进行一定的改进,然后用改进苗文写出来的文献,别的读者完全不能理解的情况。石门坎苗文的不规范性,给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二)石门坎苗文文献的阶段性特征
石门坎苗文创制的最初目的,是推进基督教在乌蒙苗区的传播,但随着文字的推广使用,石门坎苗文逐渐超越了最初为宗教服务的目的,在该区域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存创制初期的文献,绝大多数为翻译的基督教宗教文献,主要包括新旧《圣经》的章节翻译、整本翻译、赞美诗翻译等内容。早期教会学校的苗文教材,也多是为了帮助苗民学习基督教经书而编写。此时期关于乌蒙苗区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石门坎苗文文献极为少见。民国中后期开始,除了继续以改进后的石门坎苗文翻译基督教宗教文献外,记录乌蒙苗族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苗文文献以及反映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文献才开始出现,并成为这一时期石门坎苗文文献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类型出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包括苗族传统文化的收集整理与反映当代乌蒙山区苗族社会生活发展等各个方面。
(三)石门坎苗文文献的民间性特征
由于石门坎苗文属于民间自创文字,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官方政府的承认,没有在政府层面推行。因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石门坎苗文都只在乌蒙山区民间使用,所形成的文献,除了基督教宗教文献的译本之外,内容大多为苗族传统文化的收集整理与乌蒙苗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关。民国时期有小部分文献为对一些重要汉文文献的翻译,如《总理遗嘱》《三民主义》以及《中国之命运》等,但这些文献的翻译,几乎都是苗族精英知识分子的自发行为,并不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官方行为,仍然只能归类为民间文献。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规范苗文”的推广,有部分文献是官方推动的汉文文献翻译,包括一些重要政府文件,这部分的石门坎苗文文献体现出了特殊的与时事和官方政策的极大关联性。同时,小学教材翻译为“规范苗文”本,也只在滇中、滇北片区推行,并没有覆盖到石门坎苗文使用的中心区域。总的来讲,石门坎苗文文献在整体性质上是属于民间文献而不是官方文献。
五、石门坎苗文文献研究展望
通过以上简单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石门坎苗文文献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非常值得我们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我们结合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石门坎苗文文字本身的发展、文献的类型及文献内容的具体阐释进行深度研究,以便于石门坎苗文在当代的传承发展及乌蒙山区苗族的乡村振兴。
(一)石门坎苗文文字发展研究
不同时期的石门坎苗文文献,其文字表现形式是有差异的,尤其是后来的“规范苗文”,跟早期几个版本的苗文差异更大。因此,利用不同时期石门坎苗文文献,全面而深入研究石门坎苗文文字的发展过程,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从语音、词汇、词法到句法,都值得进行细致的研究。在对这部分内容进行研究时,需要借助语言学、文字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比如梁佳雪等人《东川罗家沟摩崖苗文石刻考释》这篇文章,就对该石刻中苗文的语音、语义进行了考释,厘清了初创时期石门坎苗文与1932年版本的一些差异及其改进情况[30]。这是笔者所见唯一一篇使用不同时期文献对石门坎苗文文字发展的研究。石门坎苗文文字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即使到现在,仍然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且由于不同区域的使用群体对石门坎苗文的认知与情感差异,导致最新近且为云南省政府官方推行的“规范苗文”只能局限于滇中滇北苗族地区。因此,使用不同时期的文献,利用语言学、文字学的理论与方法,推动石门坎苗文文字的深入研究,便成为推动石门坎苗文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除了文字发展的研究,现存石门坎苗文文献也为滇东北次方言中古苗语向近现代苗语的转换提供了实证性的研究材料。英国人张绍乔和张继乔在民国后期收集了花苗群体的大量语言材料,把当时大部分的中古苗语词汇进行了收集,后来编撰成为《苗英词典》(内部资料)。到了21世纪早期,贵州毕节王维阳新编并出版了《苗汉词典》,可以通过对这两套词典中的石门坎苗文词汇进行对比研究,以探求滇东北次方言苗语在中古代向近代转换时期的变化。
(二)石门坎苗文文献类型研究
现存石门坎苗文文献,数量较多,内容各异,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对这些文献进行分类。就目前所收集到的石门坎苗文文献来看,按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宗教型文献、碑刻谱牒型文献、传统文化型文献、社会经济生活型文献、政治型文献以及教育型文献等几大类型。但是在具体的分类中,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借用文献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进行更进一步的细分。之后对分类的不同文献进行编目以显示文献的基本信息。再对不同类型的文献,采用不同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石门坎苗文文献内容研究
对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研究,除了文字发展、类型学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对文献所记载内容的研究。石门坎苗文文献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滇黔川交界区域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族群近一百多年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发掘与全面的研究。
1.石门坎苗文被创制以后,其使用对象主要是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群体在使用,但部分川黔滇次方言的苗族群体、部分彝族诺苏与拉卡支系以及部分东部傈僳人也在用石门坎苗文来记音,发展出了系列石门坎苗文文献。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去探究清末民国时期以来该区域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他们在长期的交往交流过程中,如何通过同一文字体系来建构对不同群体的认知并达到区域范围内的和谐共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探求以乌蒙苗族群体为代表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在近代以来如何与中原华夏汉民族进行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完全融入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的历史过程。
2.现存石门坎苗文文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翻译文献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一是对基督教宗教文献的翻译,一是对汉文文献的翻译。基督教宗教文献所承载的是当今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汉文文献承载着当今中华文化的主要内容。用石门坎苗文对基督教经典与汉文文献的翻译,无可避免地会将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中的核心文化要素传播进入石门坎苗文的使用群体。于是,百年来乌蒙苗族群体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关系,与汉民族乃至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关系,都是需要我们进行重点研究的对象。中西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在一百多年前乌蒙山区的苗乡得以如火如荼地推进,对于当地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发展,势必带来极大的影响。这些差异极大的因素是如何在历史的场景中,作用于一个古老民族群体的现代重生,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事实。在对该问题进行深挖的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对百年来乌蒙苗族的自我族群建构与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认同的研究,把乌蒙山区苗族百年来的国家化历程进行清楚地阐释。
3.石门坎苗文文献中还包括了很大部分乌蒙苗族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内容。石门坎苗文被创制后,历史上长期以口耳相传的苗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终于以自己的文字被记录下来。因为皈依基督教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对西南边疆民族的“同化教育”,乌蒙山区苗族的部分传统文化如祖先崇拜、万物有灵崇拜以及“跳月婚恋习俗”等,在民国时期就已经趋于消失。幸有时人的有意收集整理,这些趋于消失的传统文化得以文字的形式留存下来。这些文字记忆的传统文化可与当今乌蒙苗族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此厘清乌蒙苗族百年来的文化变迁与发展情况,为当代的乡村振兴提供历史的借鉴。
4.现存石门坎苗文文献中也包含了部分乌蒙苗族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内容。对这部分文献内容的研究,应与乌蒙山区的相关文物遗存相结合,与当代民族学人类学乃至于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材料相结合,深入阐释乌蒙山区社会经济文化的特质,为分析百年来乌蒙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以及乌蒙苗族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研究提供支撑。
六、石门坎苗文文献研究应遵循的一些原则
今天,我们在对石门坎苗文文献进行收集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如下一些主要原则:
一是对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研究,不要局限于单一区域,要有跨区域的视野,把整个乌蒙苗区置于当时中国环境乃至于整个世界环境中,使用比较的方法进行阐释,才能理解为何僻处中国西南内陆高寒山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能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如此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文化变迁。
二是对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研究,不要局限于石门坎苗文文献自身,要使用相关多语种文献,要与同时代英文文献、汉文文献以及其他相关语种文献进行互证研究,以比较的视角构建多语种大文献学科视野。同时,要把石门坎苗文文献研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与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进行关联,构建大历史的学科视野。对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研究,应强调其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乃至于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对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研究,要服务于当今乡村振兴的国家大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当前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与考验。百年前乌蒙地区苗族乡村社会发生的巨变,由此出现了民国时期中国“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31]的奇观。百年前石门坎的乡村文化运动与建设取得的成果,能否为我们今天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建设提供一些历史借鉴,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四是对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研究,亦要服务于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大计。滇黔川交界地区使用石门坎苗文的花苗群体,是苗族的一个主要支系,是整体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现存石门坎苗文对汉文文献的翻译、石门坎苗文翻译的抗日歌曲、石门坎苗文创制的歌曲等等,都在表达着这些文献的翻译者或创作者对中华民族这一更高层次民族共同体的认同(11)现存石门坎苗文文献,绝大部分创作者或译者,都是精通苗、汉双语的花苗人士。。石门坎苗文字符亦为周边其他少数族群所使用,显示着石门坎苗文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我们今天的研究,也要沿着这一早已开辟的路径继续深入扩展,以石门坎苗文文献为个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创新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