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观近代报刊之侠女传记
高春花 魏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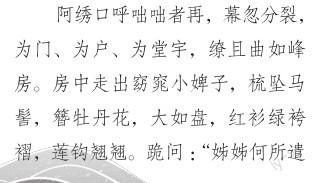

《莺花杂志》是1915年2月由孙静庵和夫人胡旡闷编辑,发行于上海的女性文学刊物。在数量众多的近代报刊中,《莺花杂志》以刊载众多与女性相关内容脱颖而出,“出版以来,荷蒙各界欢迎,早以风行一时。自第二期出版未及一月,销数已达五千份”(《莺花杂志》第三期《莺花杂志特别广告》)。杂志名称源于唐人诗句“莺花不管兴亡恨”(《莺花杂志编辑大意》),看似不关兴亡,实际却暗含着“于现今风俗可法可戒”“形容社会之黑暗”(《本社特别启事》)的意味。杂志设置栏目众多,其中《异人传》和《白莲教轶闻》两个栏目刊登《记侠女韦十一娘剑论》《寇阿绣小史》《筝娘艳史》三篇女侠传记。这两个栏目分属“稗海丛编”,作者在《本社特别启示》中有对这一大类的论说,“取古今中外英雄豪杰、美人名士、奇人侠客之遗闻佚事,足以廉顽立懦,于历史上有关系,及青年立志有裨益者,精心结构,择要采录,且多为短篇”,也就是说编者在设置以及选取题材时是存教化之目的,三篇侠女传记的择取自然也包含此意。当然,启示中所描述的只是编者的美好愿景,实际编选的篇目是否如编者所说的“精心结构”“择要采录”,又是否达到编者所预想的“廉顽立懦”的目的等诸多问题是需要仔细的考量的。
《记侠女韦十一娘剑论》与《韦十一娘传》
《记侠女韦十一娘剑论》发表于《莺花杂志》第一期,作者署“静庵”,即该杂志的创办者孙静庵,以字行,名寰镜,江苏无锡人,曾任《警钟时报》主笔,撰有《栖霞阁野乘》等;小说之后有署名“独笑”的评语,说“用笔如唐人小说家文,论剑术亦精,是近小说家第一手”。独笑是近代著名报人庞树松,苏州最早的一种报纸《独立报》的创办人之一,庚子事变时,成立了苏州第一个文社“三千剑气文社”,之后又加入南社。
韦十一娘的记载最早可上溯到明代胡汝嘉《韦十一娘传》,收入潘之恒《亘史·外纪》卷三(明天启六年鸾啸轩刻本)。将《莺花杂志》中的《记侠女韦十一娘剑论》与胡汝嘉的《韦十一娘传》比照,二者正文完全一致,改变的只有题目与小说之后的评语。潘之恒在校录《韦十一娘传》之后曾有评语:“此秣陵胡太史笔,似托以诟当事者,如唐小说家文,乃论剑术则精矣。”将这段评语与庞树松的评语比照,其移花接木的色彩是比较明显的。至最后一句“是近代小说家第一手”的评语也是无从说起,因为静庵并非小说的原创者。
《莺花杂志》刊载女性传记是其特色之一,编者将这一篇目放在“异人传”栏目中却唯独在题目中舍弃了之前的传记色彩明显的题目,将其改为《记侠女韦十一娘剑论》,应该也是注意到剑论一段在这篇小说中的重要性。对于韦十一娘故事的改变早已有之,凌濛初在天启七年(1627)刻《初刻拍案惊奇》,第四卷收入《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岗纵谈侠》就据此改编。篇末凌濛初说:“此是吾朝成化年间事。秣陵胡太史汝嘉有《韦十一娘传》。”可见,凌濛初在撰写这篇小说之时,《韦十一娘传》已经成书在前;民国七年(1918),古越东帆(蔡东藩)出版《客中消遣录》第二卷第一篇收入《韦十一娘传》,删除了论剑的一大段议论文字。蔡东藩书籍出版时间与《莺花杂志》比较接近,对于论剑一段的态度却与静庵截然不同,所以问题的核心最终就落在对于云岗剑论一段的看法上。
韦十一娘的剑论
剑论一段在小说中所占篇幅较长,但却是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不惜篇幅,赘列于下:
韦曰:“剑不始于唐,亦不绝于宋。自黄帝受符于玄女,而此术遂兴。风后习之,因破蚩尤。帝以术神奇,恐人妄用,又上帝之戒甚严,以是不敢宣言,而口授一二诚笃者,故其传未尝绝,而亦未广也。其后张良募之,以击秦皇,梁王遣之,以刺袁盎,公孙述之杀来、岑,李师道之伤武元衡,皆此术也。此术既绝,唐之藩镇有相仿效,延至奇异,而一时枉利之人,皆为之用,故独见称耳,而不知实犯大戒,诸人旋亦就禍,无怪也。尔时先师复申前戒,大抵不得妄传人妄杀人,不得为不义使而戕善人,不得杀人而居其名,此最戒之大者也。故元昊所遣,不敢贼韩魏公;苗刘所遣,不敢刺张德远,盖犹有畏心,顾前戒耳。”程曰:“史称黄帝与蚩尤战,不言有术;张良遣力士,亦不言术;梁主、公孙述、李师道所遣盗耳,亦何术之有?”韦曰:“公误矣,此正所谓不敢居其名者也。蚩尤生象异形,且有奇术,岂战陈可得;始皇拥万乘,仆从之盛可知,且秦法甚严,固无敢击之,亦未有击之而得脱者。至于袁盎官近侍,来、岑为大帅,武相位台衡,而或取之万众之中,直戕之辇毂之下,非有神术,何以臻此?且武相之死,取其颅骨去,何其暇裕哉!此在史传,公不详玩之耳。”程曰:“史固有之,如太史公所传刺客,岂其非人乎?至荆轲则病其剑术疏,岂诸人固有得也?”韦又曰:“史迁非也,秦诚无道,天所命也。纵有剑术,将安施乎?李、聂诸人,血气雄耳,此而谓之术,则凡世之拼死杀人,而以身殉之者,孰非术哉?”程曰:“昆仑磨勒如何?”曰:“是特粗浅者耳,聂隐娘、红线斯至妙者也。磨勒以形用,但能历险阻、试矫健耳。隐娘辈以神用,其机玄妙,鬼神莫窥,针孔可度,皮郛可藏,倏忽千里,往来无迹,岂得无术?”程曰:“吾观虬髯客函仇人首而食之也,是术之所施,固在仇乎?”韦曰:“不然,虬髯之事,寓言耳,虽仇亦有曲直,若我诚负,则亦不敢也。”“然则子之所仇,孰为最?”曰:“世之为守令而虐使小民,贪其贿又戕其命者;世之为监司而张大威权,悦奉己而害正直者;将帅殖货不勤戎务,而因偾国事者;宰相树私党,去异己,而使贤不肖倒置者,此皆吾术所必诛者也。若夫舞文之吏,武断之豪,则有刑宰主之;忤逆之子,负心之徒,则有雷部司之,我不与也。”程曰:“杀之之状如何?何我未前闻也。”韦笑曰:“岂可令君知也。凡此之辈,重者或径取其首领及其妻子,次者或入其咽,断其喉,或伤其心,使其家但知为暴卒,而不得其由;或以术摄其魂,使其侘漈失志而殁;或以术迷其家,使之丑秽迭出,愤郁而死。其时未至者,但假之神异梦寐,以惊惧之而已。”
剑论这一段主要强调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剑术历史悠久;第二,剑术传之有道,“不得妄传人,妄杀人,不得为不义使而戕善人,不得杀人而居其名”;第三,剑术以玄妙为尊;第四,仇有曲直,必诛者有四类,“世之为守令,而虐使小民,贪其贿又戕其命者;世之为监司而张大威权,悦奉己而害正直者;将帅殖货不勤戎务,而因偾国事者;宰相树私党去异己,而使贤不肖倒置者”。胡汝嘉在写作这部小说时,“以言事忤政府外调”,以此“托以诟当事者”,所以这部小说是作者有所寄托而写,其中对于侠术的一段论述中,最重要的就是强调所必须诛杀的四类人,这四类人都是为官不思其职者,这其中寄托的意味是比较明显的。凌濛初在改写小说时没有对这段论说进行改变,其改变比较大的地方是在小说开篇加了一段赞语:
红线下世,毒哉仙仙。隐娘出没,跨黑白卫。香丸袅袅,游刃香烟。崔妾白练,夜半忽失。侠妪条裂,宅众神耳。贾妻断婴,离恨以豁。解洵娶妇,川陆毕具。三鬟携珠,塔户严扃。车中飞度,只余一口。
赞语之后,凌濛初一一列举赞语之中所列女子,他认为三鬟女子与车中女子“有些盗贼意思”(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四)其余的几位都是“报仇雪耻,救难解危”,其中红线与聂隐娘在《韦十一娘传》中提到过,属于作者比较赞赏的,其余的香丸女子的香丸、侠妪的黑绫条子的神秘之术应该也在作者赞赏之列,至于崔妾与贾人妻报仇之后杀子而去,解洵妇杀夫离去的情形肯定不在上文提到的必诛之列。除此,凌濛初在韦十一娘的赞语中说“试听韦娘一席话,须知正直乃为真”,强调了侠义中的正直因素,在侠义的范畴中又增加一重新的解读。《莺花杂志》全文收录了《韦十一娘传》的内容,并将题目加以修改,突出剑论,至少可以说明编者对于这一段论述的认同。在近代中国,将不思其职的官员列入必诛之列,又何尝不是静庵这位晚清志士的心愿呢!
《寇阿绣小史》《筝娘艳史》:侠女之术
《莺花杂志》“白莲教佚闻”栏目刊登了《筝娘艳史》(第二期)与《寇阿绣小史》(第三期)两篇女侠传,作者署“浣春女士”,行实不詳。这两篇均出自《夜雨秋灯续录》卷三。《筝娘艳史》原题“筝娘”,两相比照,除题目改变之外,约有十二处字句的修改,比如“遣于归”改为“遣嫁”。其中有一处比较重要就是开篇第一句删去了与筝娘身份相关的“角抵戏”几字;《寇阿绣小史》修改的比较多,原题《秦二官》,题目改变,小说的主人公也发生变化,所以小说的开篇去掉了《秦二官》起首对于秦二官的介绍,主人公的名字也略做修改,寇阿良变为寇阿绣;秦二官的名字也没有在小说中出现,而是以秦生代之。另外,《寇阿绣小史》删去了阿良给秦生吃媚药和与经狱官狎戏两个细节:
每夕必命二官狎,而二官颓然枕上告疲。女出红丸与之吞吐,上媚药也。
当女之缚诣市曹也,经狱官某唱名,女斜侧其眸,顾之一粲。某归而痛哭曰:“寇阿良,绝色也。不能身交,当以魂殉。”是夕,见女果盈盈入衙斋,颠倒淫躯,犹陈杂艺,已而与某欢狎,若忘其为刑之余者。由是夜夜来。一夕,自摘其首置几上,出梳作盘龙髻。某在帐中见之,惊而大呼,遂绝。
从《秦二官》到《寇阿绣小史》,细节上有一定程度的净化。《韦十一娘传》中对于红线、聂隐娘等人来无影去无踪的幻术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两篇女侠传中也强调了女侠之术,不过此处的术与《韦十一娘传》中提到的术又有差别,兼具白莲教的幻术色彩与角抵戏的技艺成分。
《筝娘艳史》中直接提到幻术的有四处,一处是筝娘的父亲“教以运气吐纳诸术,能翘纤足作商羊舞。飞行突上柳梢头,不为之堕,堕亦三跃而下,从不假纤手,挽柔条轻借力”;一处是筝娘征亲时,七尺男儿都不能撼动其丝毫,众人怀疑其恐有“贴地术”;一处是筝娘嫁为人妇之后,床下掘土得金银,是“老父以幻术运资,寄床下三尺土矣”;还有一处是文末,白莲教事发,其父陷狱,筝娘弟弟被救出,冒生姓,“筝娘授之以枪棒,而不与之以术,至守将以终”。
《寇阿绣小史》开篇说阿绣“其母潜教之练气轻身法,能以纤足走索、儛絙、承瓮、蹋梯、弄盆子诸戏”,之后她与秦生约会时,也是“自鸳瓦上行”“未闻其响”,以至于秦生感慨其“仙踪何殊聂隐”,阿绣谦虚地说这是“小术耳”。小说中表演的梯云术一段比较能代表其幻术之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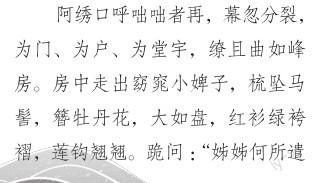

在这场表演中,阿绣能够驱使婢子,婢子又能用梯云术,上召王母侍从歌舞表演,上演一场光怪陆离的表演,其中杂技的成分是比较明显的。上文提及的筝娘也善角抵戏,浣春女士在作改变时似乎比较在意将角抵戏的出现,所以将筝娘开端的角抵戏几个字直接删去,其中可能也有弱化杂技色彩的原因。阿绣与筝娘都是善于飞檐走壁的江湖儿女,两个人又都与白莲教有联系,不过结局不同,筝娘家人因白莲教陷狱,弟弟被救出之后,筝娘不再教其幻术,得以善终;阿绣则因杀戮其夫而被凌迟于扬州市上。
三篇传记中的女侠性格各异,或带有隐士色彩而高谈阔论,或身怀绝技最终回归相夫教子的路径,或者凭借绝技而肆意追逐情爱而不得善终。编者将视野回放于古代的稗官野史,从中抽绎出这三位色彩各异的侠女自然与女侠传记数量不多有关,但从题材的择取上也能折射出近代女性希图走出传统藩篱而又有所犹疑的现实状况。古代女侠在近代报刊中重获绚烂,实现复刻;近代女性的风姿通过女侠的复刻以及报刊的新媒介得以展现。快意恩仇、伸张正义等侠客特质被赋予新的特质,时代转型时期女性的声音也借此得以表达。
《莺花杂志》在出版三期之后便再无音讯,其关于女侠的传记就此戛然而止。近代报刊中女性传记数目繁多,如独笑发表于《余兴》第13期的《客串胡旡闷小传》,少蝉发表于《滑稽时报》第三期的《祝英台小传》,行乐发表于《礼拜六》第66期的《英花小传》等等。女侠传记是女性传记中的一个部分,尤其是在《莺花杂志》这样一种以刊发与女性相关的杂志之中自然不能缺少女侠一类。侠女传记关涉着侠女与女性传记两个方面。对侠女的关注与报纸的办刊宗旨有关,也与近代风云变幻的社会状况对女侠特质的呼唤有关。关注近代报刊上的这类女侠传记时,考辨源流是重要任务之一,抛开源头去分析相关问题最终的结论都意义甚微。
(作者简介:高春花,文学博士,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魏旭,牡丹江师范学院2020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