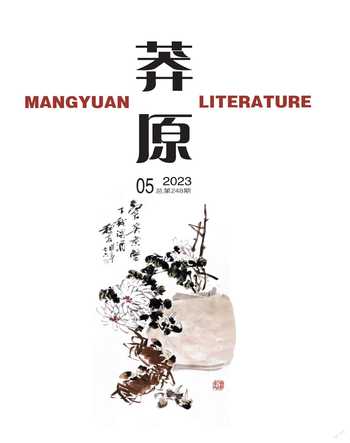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孔会侠
每次谈到读书,李佩甫都由衷感恩,他说:“是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回望李佩甫的写作之路,确实如此。
1976年,李佩甫技校毕业,顺理成章地被分配到许昌市第二机床厂。可是,这个刚当上工人的青年,却在年底写了个短篇小说,寄给 《河南文艺》,竟意外地收到了编辑的回信,还谈了修改意见。虽然,修改后的稿子最终未被刊用,但李佩甫的写作热情却鼓胀起来,一发不可收。不久,他的作品获得发表,他也被邀请去省里参加讨论会,还被借调到南丁筹办的 《莽原》杂志社当了编辑。
前脚踏进工厂的大门,命运之手就把他拉到了另一条更合适的路上,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这是个从童年起就热爱阅读的孩子,在岁月中悄悄准备好的志趣发力了,自然而然地把他推到作家这个位置来。
一个终生勤勉诚恳的学习者,终会成为时间愿意帮助的人。
生活还有另外的样子
李佩甫记忆清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说岳全传》。那是小学三年级时,他在姥姥家找到的残缺本。如饥似渴连蒙带猜的阅读后,他对文字世界的好奇与向往浓烈起来。后来,他用螺丝糖、酸杏、橡皮或者从姥姥家带回来的蝈蝈笼等,跟一个同学交换书看,那同学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家中藏书丰富。在夜晚的煤油灯下,李佩甫大量进补能找到的精神食粮,连环画、“三红一创”、《三侠五义》《聊斋志异》和大量的苏俄文学作品……偶尔,他还能读到一些欧美作家的小说。在这些作品当中,李佩甫最难以忘怀 《古丽雅的道路》,作者是苏联女作家叶·伊琳娜,译者是儿童文学方面的著名翻译家任溶溶。下乡当知青后,劳动强度极大,但佩甫对文字世界的痴迷不减,他贪婪地扫荡完其他知青带的书,甚至包括 《护理学》 等一些与文学无关的书籍,实在无书可读了,他就工工整整地在本子上抄 《新华字典》。
这一阶段是李佩甫生命中无可替代、具有铸型作用的岁月。那些经阅读而得来的信息,不知不觉渗透进少年的头脑,充实、塑造着他的精神世界,初步形成了他的思维观念和对应然世界的构想。
李佩甫的小说世界,有一个理想社会的基本图景作为底色或参照,是他审视社会现实、批判人性人情的标尺。这图像难以准确具体地描述,但有几个核心特征清晰可辨:社会运行公正、平等、仁义、有序,人们活得衣食无忧,友爱互助,有尊严,讲道德,愿奉献(这是不知不觉浸入他骨血的儒文化)。因此,李佩甫的小说,以紧贴时代变迁的中原生存为主要叙述内容,但在呈现实际生活之外,还顾及到了延伸出现实的那些可贵部分,那是他对应然世界的思索和期望,也是他小说的关键意义所在:心存应然,寄寓文中,以期产生照见、更正现实的力量;反映现实,而不止于现实,还有他对现实的否定、进一步建设的谏言和希冀。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城的灯》,刘汉香是他在中原大地高高挂起的精神灯塔,放射出耀眼的精神光芒,照亮了一大片灰暗中的乡村。李佩甫更渴望的,是照亮每一位翻开书页的读者。刘汉香这个形象,就来源于他早期的阅读经验,比如古丽雅,比如王宝钏。
小说是人们喜欢的文体,它容量大,空间相对开阔自由,作者可以虚构出多于、高于现实世界的部分,可以置放进时代匮乏的宝贵东西,还可以收藏作者的思想、情绪和隐秘心事,可以曲折地借尸还魂,说出不宜道来的态度和判断。
知道了文学的高度在哪里
试想一下,如果,李佩甫这代50后作家们,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吃进山一样压到面前的外国文学作品,他们的创作面貌会是什么样?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作家的黄金阅读期,他们张开所有的毛孔,吸收不同时期外国文学作品和大量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文化营养。《荷马史诗》 和 《堂吉诃德》、但丁、歌德、拜伦、卡夫卡、托尔斯泰、艾特玛托夫、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贝克特、尼采、弗洛伊德等,蜂拥而至,李佩甫应接不暇,大口吞咽着成分繁杂的“洋面包”。尽管,他那时感到消化起来有困难,但是,他知道了文学的高度在哪里。
知道了文学的高度,就有了把自己的创作放进去衡量的坐标系,不会因一两篇文章叫好而轻易知足自得,志存高远眼里有峰顶的人,知道每一行文字都是向上的阶梯,唯有步步踏实地走,坚持不懈。
文字的上行,靠堆积作品量行不通,主要靠认识的不断提升。20世纪80年代,李佩甫跟同代作家一样,一边借鉴摸索着习作,一边苦苦琢磨自己在基本问题“写什么怎么写”上如何做,自己要在文学版图的哪个位置嵌进个人的独特存在。这个过程不可省略,很痛苦,考验人、折磨人。后来,李佩甫有了自己的领悟——“思想不能掉下来”“让认识照亮生活”,这让引领、旁观他们这代作家成长的南丁先生心里暗暗称赞:“别看他不吭不哈,寡言少语,却有心计,有大志,内秀呢。”
创作的核心是认识,认识的境界决定作品可能抵达的高度。阅读——阅读书籍、阅读世事,然后专注思考,是形成认识的途径。后来,李佩甫大量阅读历史类、社会类书籍,还大量看地方志,凡是能找到的都认真看,他自觉地将阅读面积扩大、深化 (间以大量行走),以不断丰富经验、提升认识。
20世纪80年代末至2000年之前,李佩甫写出了长篇和中短篇小说代表作:《金屋》《羊的门》《黑蜻蜓》《无边无际的早晨》 等,追根究底地将人的生活与历史、社会之间的生成关系,以“植物/土壤”来寓言,塑造出了映射中国生存规则和时代发展风潮的典型人物呼天成、杨如意等,让人至今感慨唏嘘。
因为文学作品可以是“镜与灯”,能体现出“人类想象力及精神生活的高度和极限”,所以,尽管李佩甫这些作品已经引起广泛讨论和大量肯定,他还是紧张,高度警惕,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保持在线上,不要下落。他知道,文字滑下去容易,再上来就困难了,要付出許多心力,还不见得如愿。
凡事不能松一口劲儿
写到经验消耗和叙述可能都用得差不多时,作家就到了“瓶颈期”,作品难以创新,而读者因为对他们的接受和信任,反而寄予了更高期望值。这个艰难的尬境如何突破?
《羊的门》后,李佩甫就和同代的其他50后作家一样,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瓶颈期”。他们八仙过海各施拳脚,希望能顺利度过。有些作家大幅度扩展写作的经验范围,努力维持作品持续发表或出版的在场状态,但能提供的新东西却少之又少;有些作家加大学习和思考,更加沉静专注,让自己无论如何始终保持“学习——探讨——发现”的良好状态,期望获得新的能量,冲过这一关。
“凡事不能松一口劲儿”,日复一日地自我砥砺、不断生长,突破写作上的难关,才会有可能。
新世纪之后的李佩甫,从对历史、社会发展与人们生活关系的追问,过渡到了对命运的追问。当记忆中耳闻目睹过的人和事儿在心中来回翻腾时,他渐渐觉得,环境与人的关系也并不绝对,有些事情,不在因果链条的解释范畴。有些人的遭遇,前后关系明确清晰;有些人的景况,却不合逻辑,难以理喻。困惑越来越多,他开始大量钻研关于命相的书籍,将书中的信息和记忆中的具体人对照着琢磨,却难以印证。他“像是得了魔怔,完全陷进去了”,困惑有增无减。怎么解释呢?这命?
《生命册》 就是在这个过程暂时落定后的追问。尽管,仍然是关照中原人的时代生存,但他着力的重心,已不仅是环境与人的关系,而是细述了许多人在长及一生的经历中真实有力却难明所以的生命状态或者命运。是为《生命册》。
从 《羊的门》 到 《生命册》,其间的转移虽然不彻底,但李佩甫在调整和突破上付出的努力,可以想见。
李佩甫的写作,得益于他能专注,少旁骛,肯下功夫,许多在别人那里轻易能挂碍、诱惑或逼压的东西,在他这里不好发挥作用。不甘流俗,从不懈怠,尽可能保障创作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在处世上难以周全(有时,人情交往中大家以为应当、正常的日常温暖,可能都会给不起)。
不能两全,有得有失,从来都是。想清楚了就好,有什么呢?
近些年来,李佩甫多次强调阅读的清洗作用。我猜,或许是越来越多为谋生不讲吃相没有底线的事情,让他强烈地感到,重视生存和实际利益的人们,已经让大家的共生空间灰尘弥漫,很难找到“一片叶子是干净的”。因此,读者认为《生命册》中的吴志鹏并不是能和呼天成、刘汉香并列的典型形象,但李佩甫对他格外重视、情有独钟。他觉得吴志鹏是“通过大量阅读,通过知识不断清洗自己,认识自己”的人。
阅读之于李佩甫,早已经内化为生活习惯,内化为生命需要了,像柴米油盐一样。李佩甫已切身体会到孔子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重要和美妙了。阅读,增长知识、丰富调整思想,甚至助力写作,都是其次;阅读的终极,是为了善化携带着不堪人性行走世间的“无毛两足动物”。那些封存着人类顶端智慧的经典书籍,字字句句都负载着希望的谆谆教诲。
但是,不听真知灼见的存在好似虚无,不信或表演性的嘴上信,让慈悲劝诫和老实较真的人一样,沦为社会中被冷落、被歧视的愚人愚言。孔子如果站在现在的人群中,特别满意地赞许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特别天真自得地宣示自己“朝闻道,夕死可矣”,很可能哪个人随便接上一句,恐怕都是“傻吧?脑子没病吧?”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李佩甫在《文学的标尺》中的心声:“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沙盘。作家面对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生活,我们思考的時间还远远不够。当一个民族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思维语言先导的时候,是很悲哀也是很痛苦的……”
责任编辑 刘钰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