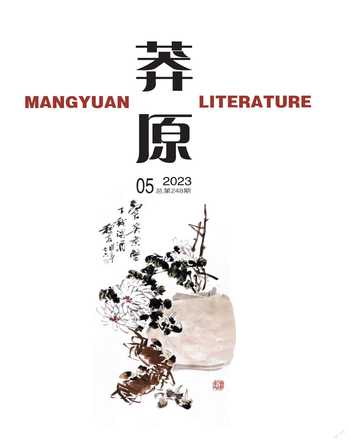归圈的马
了一容
早晨,喀纳斯河谷里浓雾弥漫,马道上都是白花花的寒霜。
牧马的巴郎子哈儿猫着腰从帐篷里钻出来,严冬的寒气使他打了一个喷嚏。这时,雾气散开了,好像不是被河谷里的冷风吹散了,而是被哈儿一个喷嚏吹跑了。他望向喀纳斯河谷,密集的松树冠在淡去的雾气中显得苍苍莽莽,似乎蕴藏着一种孤傲顽强的生命力,在冬季牧草的衬托下,显现出一种凝重而深沉的样子。
哈儿目光扫视了一眼草原,野梭梭草的叶子已经枯萎了,这是马儿们喜欢吃的牧草之一。还有野谷莠子,这种牧草油性大,马儿们吃到嘴里有嚼劲儿。而这种不长不短的马冰草,马儿擩进嘴巴后,头颅会一甩一甩自草丛中扯下来,如啃西瓜的豁鼻子娃娃,呲溜呲溜几下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至于那种芦子草,样子像芦苇,但没有芦苇那么粗壮,这种草得割回去用铡刀铡碎后,马才喜欢……牧草一进入冬季,就收敛起一贯张扬的性格,归于天然质朴。万物一理,草原上一茬又一茬的牧草,在奉献出自己全部的能量之后,便回归于泥土,真的是土里来,土里埋,化作养分,来年孕育出新的生命在草原上继续绽放。
在暴风雪来临之前,峡谷里的牧草依然可供马群啃食。有些野草是坚韧抗寒的,适合在冬季生存。比如毛毛草,茎叶柔嫩,牛羊爱啃食,马儿们也特喜欢吃。
头马大特级正在距离帐篷较近的草坡上吃草。它抬起头,用宝石般的眼睛看看哈儿,发一声低低的短嘶,又低头啃食起来。一只野鸡被马鸣声惊醒,把塞进黄鼠洞里的脑袋拽出来,见天已大亮,自己竟置身于一匹马的蹄子下面,便仓皇跳出了茅草丛,扑棱棱飞起来。哈儿望见野鸡的尾翼在天空中色彩绚丽,一直瞅着它消失于峡谷远处。草原上有一些傻傻的飞禽,像野鸡、斑子、呱啦鸡等,危险的时候会先把脑袋藏在草丛或洞穴里。这无异于门背后头吃馍馍,自己哄自己,后果也是严重的,狐狸和狼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们叼走了。
此刻,马儿们也都你一声我一声地嘶鸣起来,凌乱如此起彼伏的配乐。马群有一个特点,只要头马发出嘶鸣,其余的马就会随声附和。
一派混沌的天际,阴森森的云层开始可怕地涌动,吸入鼻腔里的空气像被冻得硬邦邦的马粪,这是温度骤然降低的标志。昨天晚上,努努按照马群主人艾布的吩咐,赶到草场,在暴风雪来临之前,帮哈儿把马群赶回圈马谷冬窝子的圈马场。他们都是艾布家的牧人。艾布的马群是周围草场上发展最快的一支,因为他雇了个尽职尽责的牧马人哈儿。
哈儿转身钻进帐篷。努努是昨晚赶过来的,已经睡了一夜,此时他把头调了个方向,用羊毛毡捂住脑袋,又扯起了长长的鼾声,如转动的石磨子,轰隆隆,轰隆隆。瞌睡没根,越捂越深——哈儿想起老辈人留下的话。再不叫醒他,这个家伙不知道要睡到几时去。不能再让努努睡了,会误事的,眼看暴风雪就要来了。
“努努、努努,快醒醒,暴风雪就要来了,咱们要抓紧时间把马群赶回圈马谷去!”哈儿喊叫着。努努揉着惺忪的睡眼,仿佛刚从女儿国跑出来似的,笑嘻嘻地翻身起来。两个人开始一道收拾东西,熄灭了炉火,才一前一后走出帐篷。
“再见啦,我的牦牛毡房!”哈儿站在帐篷门前祷告着,并走上前去,亲吻了一下毡包,表示由衷的感激。一切都有生命,它是活着的。哈儿想。现在,他们要离开这里了,他对这座曾为他遮风挡雨的栖身之所,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起码的告别仪式还是要有的,就像牧人们感激草原一样,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跪下来,亲吻养育了他们、并给了他们一切的大地。
两个人把帐篷的门帘放下来,用一块长木板压住,又用缝在门帘上的绳子绑牢,踅住帐篷的门,这样就算是把门“锁”上了。
这种草场上的临时帐篷,是用一二十根木椽、一卷牦牛毡子,外加一个顶棚搭建的,简陋但实用。这种毡房,在草原上就是一个临时住所,主人离开的时候,也不会拆除,只需把门帘放下来,上面压一溜儿木板用绳子绑着就行了。远方的旅人来到帐篷跟前,可以自己解开绳子,拿下木板,卷起门帘进去歇息,也可以在里面找点馕以及包尔萨克来饱食一顿。包尔萨克内地人都叫果果,是用鸡蛋、牛奶和面粉加工而成的,吃起来外酥内软,当地的牧人还会放入草原上的蜂蜜,所以比油条和麻花还好吃。旅人们吃饱了肚子,索性就躺在帐篷里美美睡一觉,再走向他们的目的地。草原上的人搭建这样的毡房,离开时还会留下些食物,为过往旅人和周围的牧人们无偿提供服务。草原上的人是无私的,这也是他们能够在辽阔的大草原上世代生存的原因。旅人们走出帐篷之后,即使碰上帐篷的主人,只需打声招呼就行了。
有个旅人曾问过哈儿:“帐篷这样子没有人看管,就不怕小偷吗?”
哈儿摇摇头说:“草原上是没有小偷的。”
当然帐篷里面也不会放什么贵重的物品,即使有小偷从远方来,进了帐篷,也只会在简陋的帐篷中感受到一丝人间的温暖和真情。
小偷没来,暴风雪就要来了。
这两天,马群里有好几匹骒马眼看就要诞马驹子了,尤其是玉狮子这匹白马,分娩已经迫在眉睫,倘若被风雪困在草场上,老马和马驹子都有被冻死的风险。
哈儿和努努捆绑好随身携带的行李,去牵来了一匹脚力好,经常驮运装备的枣骝马。二人把行李搭在枣骝马的背上,枣骝马便通人性地朝着圈马谷的方向前行。哈儿随之打了一声唿哨,健硕的黑豹便闻声跑来,这是哈儿的坐骑,他一跃就跳到黑豹光滑的背上,策马冲上山坡。哈儿把所有跑远的马匹一个个拦回来,马群被哈儿驱赶着,开始走向那条去往圈马谷的通道上。
黑豹是一匹远近闻名的快馬,它身上没有一丁点赘肉,力气惊人,速度迅疾,跑起来像一头灵敏的豹子,四只蹄子都不落地。哈儿骑着它参加过叼羊大赛,还在大赛上夺了冠呢。记得刚驯黑豹时,有几个驯马师用套马索拽它,都被它拖倒在地,它从山梁上一跃而过,像一道黑色的闪电,把人们惊得张大嘴巴半天都合不拢。它有豹子的速度和激情,又有乌黑水溜的皮毛,于是圈马谷的人就叫它黑豹了。后来,黑豹被哈儿驯服了。马是认人的,就只允许哈儿一个人骑它,别人都骑不了,谁骑摔谁。
哈儿骑在黑豹的背上,显得那么英武。嘴里十分得意地吼着:“嘚儿,驾!”他纵马奔
驰,驱赶着马群。
努努骑的大青马也是一匹快马,自是不甘落后,紧紧追了上来。群马的蹄子在草原的峡谷地带奔跑着,踩踏出洪流般隆隆的回音,尘土地中弥漫着干干的地椒子的味道。
哈儿和努努赶着马群从山坡上行到喀纳斯河边沿时,跟草原上的一群牧人相遇了。有犟板筋尔里,有红眼睛拉西,还有一朵红玫瑰阿依努尔,他们都赶着马群,要在暴风雪来临之前归圈。
还离得很远,红眼睛拉西就在马背上喊叫开了:“阿达西(兄弟、哥们),快点走啊,暴风雪就要来了!”
而犟板筋尔里只是粗放地吼:“嗷,嗬嗬——嗷,嗬嗬——”
明眸皓齿的阿依努尔则在马背上含蓄地笑着,她脖子上系着的红围巾,像一簇燃烧的火。
这样,马群就自然而然地汇合到了一起,声势也更加浩大了,草地上的尘土被扬起三尺多高,连马蹄子和马尾巴都看不清了,远远地,只看得见或雄强粗犷或优雅高贵的一匹匹骏马的轮廓。
他们都放牧着各自的马群。在草原上,牧马人经常会把马群混到一起,大家把这叫合群。马喜欢合群,人也喜欢合群呀。无论是人还是马,合群以后,如果相处融洽,相互之间就很少产生矛盾,也从不打架撕咬。
但也有个别的马,经常会离群索居,躲在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独自啃食牧草或活动,这种马一般都与众不同。
马儿们合群是因为马群里有它们喜欢的儿马或骒马。它们横冲直撞,疯了似的跑入对方的马群中去,为的就是要寻找跟追逐它们心仪的对象。有时候,儿马为了某个骒马会隔山架岭奔跑翻越几十道梁湾,也要撵着跟人家的马匹合群去;有些骒马在动情的时节,马圈都圈不住了,只要哨见那健壮风流的儿马的影子,哪怕是听见声音、闻到气味,就会急切地用蹄子刨着地面,猛然掼开马圈的门,或者腾空而起,从马圈围栏上跃过去,撒着欢子去追赶令它血脉偾张的儿马。这就叫脱圈。骒马脱圈,儿马也会脱圈。
哈儿那匹头马大特级,就曾一次次地脱圈,脱圈后出去就会把别人家的骒马拐回来。浑身雪白的骒马玉狮子也曾脱圈,但玉狮子脱圈以后,不去别处,只会跑进阿依努尔家的马群里,去寻找它苦苦相恋的那匹大叔级别的儿马“大教授”。阿依努尔称这匹儿马为“大教授”,是因为它平时显得儒雅随和,还有几许斯文和清高。虽然“大教授”看上去已经不年轻了,但它成熟稳健,不像许多年轻儿马那样浮躁孟浪,玉狮子看见它,或者偶尔听见它的嘶鸣,就控制不住激情澎湃,一准会追上去,靠在“大教授”的身边吃草,显得非常安详和幸福。这两匹马,年龄相差悬殊,但它们之间的隐秘情感让人难以捉摸,就如一对耳鬓厮磨坠入爱海无法自拔的情侣。所以,马儿脱圈、脱群,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牧人们谁也不会为之大惊小怪。当然,牲口不论脱圈多久,终归是要被找回来归圈的。
但人不一样,人有时候“脱圈”了,时间一久,就再也回不去了。拉西的哥哥有一次背着他嫂子出去找了个年轻女人,带到草场上的帐篷里去了,结果被那女人的男朋友发现了,堵到帐篷里把他哥的两颗门牙都打掉了,脸也打肿了。他哥怕丢人,给草场上的人说是喝醉酒从马背上跌下来摔的。跟拉西的哥哥相反,哈儿的邻居是一位美丽的少妇,她男人常年在外打工,她就被一个跑江湖的拐跑了,人家玩够了,就抛弃了她。她感觉回不去了,又找了一个牧马人,结果生下孩子后,她卻开始嫌弃牧马人了,说:“你永远只是个放马的,啥时候能好起来呢?”那个老实本分的牧马人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放马的,再不要想着我能发达啦。”女人不屑一顾,说:“那咱俩还过啥呢?干脆你放你的马,我走我的人。”就又“脱圈”了。到了下一站,又给人家生了一个孩子,不知因何起了矛盾,再次“脱圈”……她就这样每“脱圈”一次,便给人家生一个娃娃,“脱圈”一次,便给人家生一个娃娃,一路上生了五六个孩子。但是她生下孩子后,说走就走了,似乎习以为常,丝毫没有什么留恋。
努努对哈儿、拉西和尔里唏嘘说:“这种经常脱圈的人,大多命运都很苦,永远没有一个真正的归宿,也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心上人。”
以前,巴郎子们每次见到阿依努尔,就要撵着人家把马群合到一起,于是,大家男男女女围成一个圆圈,开始一场热闹非凡的麦西热普(草原上一种娱乐活动)。大家热烈欢快地跳起舞来。舞蹈是草原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真实的生活写照。阿依努尔的舞姿有时候好像是在挤奶,有时候好像是在骑马。大家先是看她跳,等她跳累了,就让她歇着,纷纷跳给她看。哈儿和努努、拉西、尔里他们的舞姿也各具特色——哈儿模仿着雄鹰的卓尔不群,孤独地傲视天地,它时而盘旋,时而展翅高飞,抑或俯冲捕猎;努努则模仿起棕熊来,傻里傻气的憨态令人捧腹大笑;拉西和尔里模仿马的走、跑、跳,都甚是逼真。还有模仿收割牧草及农作物的,模仿套马、狩猎的,种种形态,各展风情,统统都释放出澎湃的热情,展现着自然的天性。这就是草原上的人对待生活的样子,他们说唱就唱、说跳就跳,性格里有着火一样燃烧的激情。
在整个过程中,大家都希望得到阿依努尔的青睐。一场舞蹈下来,尽管人人都累得满头大汗,浑身冒着热气,但看到阿依努尔开心得欢呼雀跃,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除了麦西热普,大家在赶马去往草场时,也赛马。阿依努尔押着马群走在前面,他们各自拦定自己的坐骑,等阿依努尔赶着马群走得很远时,她会高高地挥一下手里的红围巾,喊一声:“开始,跑!”于是,大家放开自己的马,一猛子蹿了出去。赛程就是从出发地到达阿依努尔跟前的距离,大家把这个叫“押杠子”,看谁的马跑得快,谁先到达阿依努尔跟前,角逐出一位冠军骑手。刚开始,众人的坐骑会磕磕碰碰地撞在一起,但是跑上一截,距离就慢慢拉开了。这时候哈儿那匹黑豹的优势就出来了,哈儿感觉自己犹如在云彩里,似乎变成一片轻盈的羽毛,在天上乘风疾飞。别的骑手只感觉眼前划过一个黑影,如流星似的,一眨眼黑豹就冲到前面去了。哈儿总是第一个跑到阿依努尔跟前。阿依努尔竖起大拇指,哈儿感到非常自豪,心里有一种晕晕乎乎的醉氧感。那些落在后面的马还在吭哧吭哧地做最后的冲刺,有的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松松垮垮地颠簸过来。
他们还爱在牧野里玩叼羊。没有羊,就拿谁的棉袄代替。草原上把棉袄叫裹肚子,阿依努尔是裁判,随着她那银铃般的口令发出,大家便策马扬鞭,草场上马蹄声碎,嘶鸣声响彻云霄,选手们对那件无辜的裹肚子你扯我拽,还有人忽然冲出来趁火打劫,大家各自展示高超的骑技,都想获得阿依努尔的赞许。很快,那件顶替羊的裹肚子就被选手们撕扯破了,烂棉花嘟嘟噜噜冒出来,就像羊毛一样在草地上四散飞舞。经过一番热血沸腾的激烈角逐,往往努努手里拿着一半裹肚子,另一半在桀骜不驯的哈儿手里。两人平分秋色,各自昂着头坐在热气腾腾的马背上嘿嘿地笑,谁也不甘平庸。阿依努尔在一旁咯咯咯乐个不停,她一直都是这么纯粹率真啊。
眼下,什么也玩不成了。暴风雪就要来了,马群先要从喀纳斯河的冰面上走过去,才能尽早到达圈马谷的冬窝子。有几匹骒马肚子里怀着马驹子,眼看快要诞生了,不能使它们在冰面上摔倒流产,所以,要在冰上铺撒一层浮土防止马蹄打滑。哈儿跳下马背,用脚踢了踢地面,冬季的草原,土地被冻得像板结了似的,他只好用放牧时随身携带的剁铲一下一下挖土,挖下大的土疙瘩,运到冰面上摔碎。大家拦马的拦马,在冰面上铺路的铺路。河面上的冰冻得实实的,像混凝土浇筑的一样坚固。尔里拿着土块跑了两步,猛然跐溜溜地滑将过去,他打跐溜滑的水平很高。很快,冰面上该撒浮土的地方都已经撒上了,大家保护着怀有马驹子的骒马陆续到了河对面。尤其是骒马玉狮子,它的肚子撑得越来越大,坠得越来越低,它显得很劳累,走路很吃力。这是它第一次怀马驹子,怀的就是阿依努尔家那匹“大教授”的种。哈儿格外留心玉狮子的状态,他想,它今儿不生,也许就在明儿了,以他的经验,反正就是这一半天时间了。在这一点上,小伙子们一改往日的彪悍和粗犷,变得无比细腻,一举一动都充满了关爱和柔情。等怀着马驹子的骒马安全过了河,才把大批的马群陆续赶到河对面。有些马匹在过河时,蹄子在冰面上会时不时一撇一捺地打滑溜,那东倒西歪的样子令人又担忧又想笑。但马儿总算相继穿过了光滑的冰面,很快汇入对岸的马群里去了。
这时,大家松了一口气,纷纷重新跨上马背。还没走多远,就听见大风把河谷里的树冠刮得发出一种呜哇呜哇鬼哭狼嚎的声音。大家在马背上也被大风吹得东倒西歪。哈儿抬起头来,望见零零星星的雪花已经在天上飞舞着,落在他脸上的雪片像一些虫子,痒痒的,但刹那间就融化成了水珠,顺着面颊流下来。不大一会儿,雪花变得密集起来,落在马背上的雪花,有些钻入马儿的鬃毛里去了,有些则在马耳朵的尖尖上挂着,晶莹剔透,就像一个个可爱的小精灵。
这时候,河谷里的草原,树林,冰冻的河面,还有群马,都被漫天飞舞的雪花包裹着。时间仿佛静止了,只有那些银色的精灵在绵密地传递着神秘的箴言,整个河谷看上去犹如一个童话世界。哈儿看着那雪花在天上舞蹈,联想到草原上那古老的弹布尔,天地传来如泣如诉的旋律,那洋洋洒洒的雪,演绎着草原峡谷里千百年的荣辱盛衰。
努努勒转马头,叫了一声:“哈儿,你发什么愣,快走,暴风雪太猛了。”
哈儿回过神来,他担心地看看阿依努尔那骑在红马背上纤巧的背影,策马靠过去,像守护神一样与她并排而行。风更大了,雪更猛了。人喊马嘶,大家都奔前顾后,关照着每一个人和每一匹马。
天擦黑的时候,大家才安全到达圈马谷的冬窝子。万幸,怀孕的马儿都安安全全到家了。合在一起的马儿们知趣地自动分开了群,各自回到自家的马圈。那些怕冻的马匹一进圈就赶紧钻入马棚里去了。
阿依努尔给哈儿打着招呼:“嗨,哈儿,玉狮子下了马驹子,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啊!”
哈儿点了点头,应了一声,一直目送阿依努尔消失在风雪中。
狂风怒号着,卷起地上和天上的雪一起肆虐着整个圈马谷。尽管风雪交加,但圈马谷处在一个环形的山谷下面,像一个受保护的安乐窝。
夜里,哈儿起来了几次,他拿着手电筒,见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比他小时候读到的 《水浒传》 中林冲雪夜上梁山时的雪还要大,还要猛。他住的板棚门口都快要被雪壅塞住了,他狠命拉开门,用门背后的铁锹清理开通往马棚的路,一面给马儿们添夜草,一面观察那几匹怀了驹子的骒马,尤其是玉狮子,如果不出他所料,它诞马驹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果然,玉狮子吭哧吭哧的,不断轻声嘶鸣,并伴有时断时续的呻吟,它神情不安,显得特别难受,一会儿卧倒了,一会儿又站立起来,在马棚里不停折腾着,看样子马上就要诞马驹子了。哈儿不想叫醒熟睡中的艾布和努努他们,经历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他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应付得了。
哈儿跑出马棚,抱来了一捆干麦草,接着燃亮一支蜡烛,放在马槽边上。他看到玉狮子异常吃力,好像它肚子疼得无法忍受了。世上的生灵都一样,人也好,动物也罢,临产时肚子不疼是不可能的,因为就是要通过这疼痛,才能使得身体的各个骨缝、骨卯逐渐打开,才能让肌肉变得柔软和松弛,才能顺利地完成分娩。说白了,小马驹几乎就是从骒马的骨头缝隙里挤出来的,这个过程必然疼痛。但母爱是伟大的,再疼,也要翻过这一道坎、度过这一道关,这样对一匹骒马而言就算功德圆满了。这就是生命的造化,天道的造化。
哈儿站在玉狮子的身边,时而抱抱它那曾经高傲昂扬的头,时而摸摸它那柔顺的鬃,耐心地安慰着它,并为它暗暗打气和鼓劲。也许是哈儿的安抚和鼓励起到了作用,玉狮子不再那么害怕、紧张和无助了,它虚起眼睛,浑身都在用力;它的后腿努力地撇开着,在不停地用力,它每呼吸一口气,肚子就会明显地一鼓一缩。哈儿握着拳头的手也一紧一松,在一旁憋着气为玉狮子加油。在一霎一霎的阵痛中,在紧张而绝望的挣扎中,新生的小马驹先伸出了两只前蹄;接着,头部附于前蹄的上面也令人欣喜地出来了;然后,小马驹裹着胎衣,随着流出的羊水一起慢慢滑了出来;玉狮子捯动着蹄子,眼皮沉重得有些抬不起来了,一张一翕的;终于,随着最后的一股子羊水流出来,小马驹顺利地降到了世上,胎盘自己竟然一下子拽断了,半截胎衣尚留在玉狮子的身体里。这时候,玉獅子的肚子仿佛突然被腾空了,一下子瘪了,凹进去了,它用疲惫不堪的目光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孩子,眼睛突然又睁大了,释放出惊讶的慈悲的亮光。
近处有几匹马也都兴奋地望了望小马驹。
马棚外面的风发出更加悲壮苍凉的吼声,雪依旧在下。哈儿抹掉了马驹子嘴巴上一点黏腻的东西,忙用蜡烛点燃干麦草,生起了一小团火,让小马驹在充满温情的空间里沐浴人间第一缕温暖的光。玉狮子仿佛恢复了一些力气,回过头来,咴咴地轻声呼唤着小马驹。小马驹的颜色和它妈妈一样,一身纯白,是一匹没有一点杂色的儿马驹子。这在哈儿的意料之中,又像是在他预料之外。
时间不长,儿马驹子就能够站起来找着吃奶了。玉狮子用嘴巴轻轻地拱着马驹子,哈儿用毛巾蘸了水,又把毛巾在火上烤热,把玉狮子的奶头擦了一遍,开始一下一下地捋着,这样,奶水会下得更快,奶量会更充沛,能让小马驹很快获得养分,增强体质。
许多人都不知道骒马究竟有几个奶头——动物们的奶头是由它们生育幼崽的多寡而定的,这就是天道的神奇。骒马和人是一样的,生有两个奶嘴;而乳牛是四个奶嘴;下崽儿越多的动物,自然乳头相应就更多一些,有些就像排扣一样密集。自然万物,最合乎自然规律,细细品味,不由得让人心生敬畏。
就这样,在这个暴风雪的夜晚,哈儿放牧的马群中又添了一匹新生的儿马,马群的队伍变得更加壮大了,有着一派欣欣向荣的好前景。
牧人家诞了马驹,如同添丁进口一样,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想想也是啊,一个生命的到来是多么的神奇和偶然,这样的偶然充满了缘分,也好像一种宿命,当然是值得庆幸、也值得庆贺的事情。在草原上生活的人,离不开马,他们祈盼的就是一个六畜兴旺的好光景呢。
玉狮子给家中立下了大功。为了让玉狮子恢复体力,让小马驹吃到充足的母奶,哈儿又单独给玉狮子喂了一些燕麦和油渣。他仔细打量着新生的小马驹,想到这是玉狮子跟阿依努尔家的“大教授”爱情的结晶,不由会心地笑了。哈儿想,明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快快跑到阿依努尔家,向她报告这个喜讯——“大教授”做父亲了,儿马是一匹英俊的白马王子。
哈儿不由一阵一阵的激动,他似乎有些等不到天亮了。
外面,风很大,雪依旧很猛。
责任编辑 刘钰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