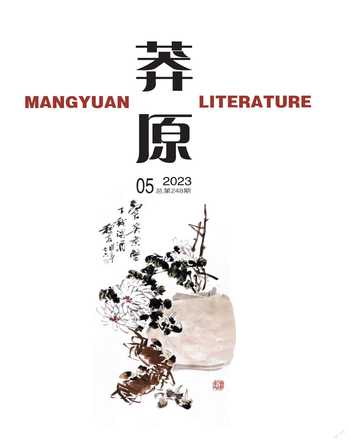大山故事
邱仙萍
背 山
我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刚到这个城市时两手空空,靠着自己的两只脚,一刻不停地在钢筋水泥的皱褶里奔波搜寻,一分一厘地丰满着自己的身体,也膨胀着自己的欲望。
钱可真是个怪东西,腰包里但凡有几个钢镚,就总惦记着有机会鸡生蛋、蛋生鸡,它拼命想往外面蹦,迫不及待要冲出笼子。本来想放它出来吃口食,或者让它去招个亲,带回个小鸡崽,哪里知道鸡崽没有带回来,下蛋的鸡都被人炖锅吃了。
对于人到中年的女人来说,最残忍的不是岁月流逝,冯唐易老,也不是雀斑多了,皱纹深了,腰肢粗大,肌肉下垂,甚至不是经历了婚姻的背叛和职场上的打压,而是一夜之间被抄底了,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倏然发现,人不但不能承受欲望之重,也难以承受一贫如洗之轻。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我像一只丧家犬一样四处流浪,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只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分,出来透一口气,看看头顶的白月光。
我觉得自己快完了,每天看着桥下的流水发呆。我问自己,难道就这么翘了吗?但心里的自己很坚决地反驳:翘什么翘,死哪有这么容易的?欠下的债得还,未了的情要了,该承担的责任得承担,即便要死,也得死个清清白白、干干净净。我去咨询一个相熟的医生,问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医生朋友说,这世界上的人都有不同的抑郁,只是到症的程度却没那么容易。他问我睡眠怎样,我说不想那些钱能睡得呼呼的,一想到那些钱就睡不着了。医生朋友说你还是没放下啊。我说那怎么才能放下呢?医生朋友说,要想放下过去,就得背起当下。走吧,和我一起去背山吧。
这位朋友姓李,是弘一法师的后裔。弘一法师在俗时,有年冬天,大雪纷飞,好友许幻园站在门外喊出李叔同和叶子小姐,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挥泪而别。李叔同看着昔日好友孑然远去的背影,在雪里站了很久。随后,返身回到屋内,让叶子小姐弹琴,他便含泪写下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朋友约我去背山的那天,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落魄失意的许幻园。
背山的地方在杭州临安的昭明禅寺,海拔近1500米。昭明禅寺建于南朝梁大通年间,是昭明太子萧统修禅的地方。萧统是梁武帝长子,被宫廷太监鲍邈之诬陷后,其郁难平,不见梁帝,跋山涉水来到临安东天目山,就在这里读书、修禅。因为读书太过用神,心血枯竭,导致双目俱瞽。禅师志公取东天目、西天目两峰石池水洗眼,才得复明。东西天目山上至今还保留有洗眼池。作为千年古寺,除了常住的僧徒,也有善男信女们来此小住短修。
在昭明寺院修行,人们每天凌晨两点半起床,三点至六点为早课时间,六点早斋,七点到十一点出坡;下午一点半到六点还要出坡,晚上修晚课,九点半熄灯。男众女众住客房,是分开在不同院子的。我们到时,小客房已经满员了,就住在四五十人的大寮房,上下通铺,日常安排都由寮长负责。
寺院有很多规矩,用斋饭的时候由出家和尚带领进入,有一定的仪式。二十分鐘后出家人离开,普通居士不必穿海青,但进食前要默念十声佛号,然后围着圆桌吃斋饭;公筷夹菜,吃饭时止语,需要添饭可用手势,吃完后用少量开水冲洗碗内,要全部喝下,不能浪费一点一滴一粒;当然,更不得带入酒水、荤腥等。
上午、下午出坡就是劳动,可以帮助食堂捡菜洗菜,或者去背山。常住的修行人都有固定的部门,短住的人一般都是去背山。因寺庙在山上,一应所需运到山下的中转站,便无法再用车辆往上运输,需要用人力把这些物品运上山去,粮米、蔬菜、日用品,包括修缮寺院施工用的一砖一瓦,都是出家师父和各地义工背上山的,这就叫“背山”。背山的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一个箩筐,一件工作服,一筐筐从山腰背上山,大部分背山的修行者都十分专注,或一声声念着佛号或听着清幽的佛乐独自前行,背山的过程中不攀谈,不驻留。
我忽然心有所悟,这“背山”,就是卸去心中的包袱,放下嗔恨纠结,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些能够承受的事情,不仅是一种义工,也是一种别样的修行,是修行者对自己身心的磨炼,也是与灵魂的交流对话。生命有不能承受之轻,也有不能承受之重,比起精神上的负累,身体上的劳作并不是最沉重的。
那天,我背着盛着蔬菜、米面的箩筐,跟着前面背着黄砂、砖瓦的修行者,差不多同样的节奏,沿着山路,默默地拾级而上,往事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浮现——我从小在山里长大,挖猪草,背柴火,那猪草和柴火有的时候堆得高高的,能高过半个人,人站立起来都很困难,一路踉踉跄跄的,几乎都是靠着拄杖支撑前行。从粮食学校毕业后,我在全县最大的国营面粉厂打包车间干过,24小时三班倒,一班要连续干8个小时。麦子经过初筛、细筛、脱壳、脱麸、磨研等各道加工程序,到我这里是成品装袋、过磅称重、缝口踩线再送往传送带,所有步骤要在一分钟内完成。面粉50斤一包,一个小时打60个包,接、拎、缝、甩,3000斤面粉就从我手里过去了。所以,对于背山,我刚开始并没太过在意。
可没过多大一会儿,我的脸上就淌满了汗水,衣服已经黏哒哒地贴在了脊背上。前面一位穿着海青的师父把身体弯成一张弓,那砖瓦堆得像是一摞小山,估计得有百十斤,箩筐的背带勒进他肩膀里,我很想递给他一块毛巾垫一垫,但是想起寺院有禁语的规定,不能交流,便只好作罢。当我弯下身体匍匐前行时,眼睛只能看着脚下不大的一块地方,心想,这应该是我和大地距离最近的时候吧,因为目无所视,心里便少了许多杂念,好像能听到心对山的忏悔。
一个个穿着海青衣服的背山信众踏着青石台阶缓缓而上,几乎悄无声息。这里有身体伤痛久患痼疾的,有心灵受伤支离破碎的,有放下碎念想求清净的,也有积德行善修炼自己的,每个背山的人各有各的心事,但大家的脸上都很安详平和,有一种不沾烟尘的宁静;彼此之间既不问来处,也不问归期,谁也不知道你是谁,来自哪里,去往何处,谁也不问谁的身份和职业,像是一滴水融入湖里,像一株植物隐没林中,大家颔首静默,秘而不语。
山即是佛,佛即是山,在巍巍大山面前,我们只是一粒草芥。不知道是我们在背山,还是山在拥抱温暖着我们。
师傅归山
走到半山腰,抬眼仰望,有几只飞鸟拍打着翅膀,倏然而过,它们越过松林和山岗,向着山顶飞去。我突然想到我师傅,他总把自己比成一只飞鸟,觉得能越过前面万水千山。现在想来,人生路上山重水复,谁能像鸟一样一往无前啊。
五年前的一个冬夜,师傅走了,我们把他送回故乡,从此后是彻底隐归在大山深处了。
师傅姓方,是他把我从县城报社引荐到省城来的。第一次见到方师傅,是在一个会议上,明明是一个普通的会议,但是他似乎面对着千军万马,拿着一部大相机,卖力地跑前跑后,上下左右,时而蹲时而跪地寻找拍摄角度。
我们的报纸是对开大版,我和师傅负责区域经济版面的采訪和编辑,每周一个整版,隔个两三天就要下县市采访组稿,节奏非常快,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很多同事都不看好师傅,嫌他身上带着浓重的土腥味儿。他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摄影记者,吃饭速度极快,吃相却不好看,会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衣服也穿得不讲究,皱里巴几的,经常从外面回来还沾满了泥巴和污渍。但在师傅这里,一进入拍摄现场,就像进入了阵地,打开相机的镜头,就像拉开了枪栓。只有站在离前线最近的地方,才能拍出最好的照片。好几次在台风中抗洪抢险,师傅都像个勇士一样,一马当先,该下水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扑通”一声跳下去,咔咔咔的快门声,如机枪一样清脆。我很喜欢师傅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从此就跟定了他。
2001年12月,我们去师傅的老家浙江遂昌采访竹炭行业。那个时候竹炭在很多人眼中,还说不清个所以然,国内用户很少,大部分是通过外贸出口到日本,用于水库清理除污。因而,产品空间小,利润低,更没有自己的品牌。连续几天,我们白天走访遂昌所有的竹炭行业,晚上把这些企业召集起来开会。一个礼拜下来,师傅和我说,山里都是宝啊,竹炭产业一定会有很好的前景,我们要为家乡人民做点事情,要做民族的竹炭产业,要有自己的品牌。他让我给遂昌的竹炭品牌取个好名字,我想了一会儿,说:“那就取名叫卖炭翁吧。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白居易这首诗,恰如现在竹炭行业的写照。”方师傅听了之后,当场眼睛就亮了,夸我这个名字起得恰如其分。遂昌的冬夜,白露渐霜,风吹得竹子哗哗响,山里温度很低。我们几个人在屋子里一边烤火,一边畅想和规划,大家越说越兴奋,似乎看到了遂昌的竹炭,已然成为一块块珍贵的乌金,销往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第二天一早,师傅就打电话给在北京报社的弟弟,在最短时间内,注册了“卖炭翁”商标。
“卖炭翁”商标注册成功后,一炮打响。不久,方师傅就在杭州曙光路开了第一家竹炭专卖店“卖炭翁”。三个月后,衢州政府部门想成立竹炭产业园区,希望方师傅把“卖炭翁”商标品牌转让给他们,开价30万。师傅没有犹豫,当下就同意了。我说:“师傅,我帮你取了卖炭翁这个名字,你总得请我吃个饭吧?”师傅问想吃什么?我说,得吃个最贵的,你看,现在“卖炭翁”这个品牌一下子就卖了30万,你要不请我吃个海参鲍鱼什么的,至少得吃个鱼头土鸡炖锅吧?师傅笑了笑,说:“口腹之欲,不足为福;五谷杂
粮,才是根本。我请你吃碗面吧。”
报社的同事们都知道,要让师傅请吃饭,是比较困难的。外人都觉得他抠门吝啬,后来跟他时间长了,我才知道是他的出身和修为,养成了节俭的品性。
二十多年前从丽水到杭州,要绕道金华,开车得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小时。记得有一次我和师傅从丽水回杭州,偏偏那天下起了暴雨,雨水铺天盖地泼着,我和师傅艰难地开着车,道路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的,轮胎蹦蹦跳跳,汽车像是汪洋大海里一艘摇摆的小船。雨哗哗的,像是一盆盆水倒在我们的车上,前方视线像是被一层纸蒙着,根本看不清道路,只是凭直觉在行驶。我们开的是一辆破旧的桑塔纳,我都怀疑师傅是不是弄了一辆报废车回来。车子像老牛一样呼哧呼哧,偏偏刮雨器又坏了,瓢泼大雨中,没有了刮雨器,就是盲人骑马。我们打着双闪,行驶在一段偏僻的道路上,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一户人家都看不见,更别说汽车修理店了。雨实在太大了,师傅不时停下车,让我用抹布把挡风玻璃上的水擦掉,可前面刚擦完,后面很快又铺满了,我只能不断地下车擦玻璃。忽然,我发现只是刮雨器和底部连接处的螺丝掉了,那天我正好扎着马尾巴,扎头发的橡皮圈是很结实的。便撸下发绳,用橡皮圈把刮雨器和底部绑定了。师傅一试,还别说,挺好用的,那刮雨器重新启动起来,左右卖力地刮着。师傅高兴地说:“还是你这丫头聪明。”
过了半个月,我和师傅下乡采访,又遇到了下雨天,发现刮雨器上还是绑着我的橡皮头圈,我很奇怪地问师傅,怎么还没有去修理?他说:“正要和你说这个事,你去批发市场买一打这样的头圈给我,挺好用的,不用去修理店了,费那钱干嘛。”
从2002年开始,“卖炭翁”渐渐红了起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大媒体,再到网络,纷纷对“卖炭翁”做了报道,一时风光无限,风头无二,仅仅在广州,两年之内,“卖炭翁”的专卖店就有48家,在全国,“卖炭翁”开了上千家店。就在这时,因为报社对报纸进行改版,加上总部从杭州搬迁到宁波等因素,原来的同事们纷纷各奔前程。见我无处可去,师傅通过他在省城的朋友,介绍我来到了杭州。而师傅索性离开了媒体,回到家乡办实体做企业,真正地伐薪烧炭做卖炭翁去了。按照师傅的说法,山里的日子,日头慢,月亮圆,比城里敦实。
那之后,我和师傅也少了联系,只是能通过他的微信朋友圈,知道他整日很忙,竹炭生意也越做越红火了。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师傅的电话,说山里的烧炭佬进城了,在杭州呢。我开玩笑说,这回是来请我吃饭的吧?他问我想吃什么,我说那总要吃个好的,贵的。他说,贵的不一定就是好的,什么时候你去遂昌山里了,我请你吃炖锅,地衣烧豆腐,竹笋炖兔子,还有用碱木灰做的黄米粿,都是山珍美味啊。那天,我们还是吃的面。
可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师傅吃的最后一顿饭,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也是通过微信,知道师傅爱上了骑行,经常清晨就起来骑行三十公里上山,晚上还要骑行四五十公里下山,他像只鹰一样,逡巡在山与山之间,看云水飞鸟投林,看大雪一夜白了山头。师傅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战士、一个骑士,无畏、勇敢,活着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炭火。那天,傍晚时还看了师傅的朋友圈,岂料两个小时后,就出事了。当天晚上,细雨飘零,晦暗阴冷,师傅骑车下山的路上,遭遇了车祸,两辆货车压在了他身上。也有人说,第一辆货车从他身上碾过的时候,司机没有停下来,仗着天黑无人逃逸了。师傅当时还是有气息的,只是第二辆货车还是和第一辆一样,货车司机没有停车施救。可以想象,在那样冷那样暗的夜,师傅绝望地躺在冰冷的地上,血汩汩流着,渗进了雨水和泥土里,无法动弹,无法发声,像被判了死刑的囚犯一样,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该是多么无助、多么絕望啊!谁能知道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师傅在想什么呢?谁又能知道几分钟后,第二辆车接着从他身上碾压而过!
我不知道那个暗黑冰冷的夜,密布的乌云是否会睁开一条眼缝,但我想那个时候,肯定有一颗流星,在师傅的头顶倏然坠落。
送别师傅那天,是腊八,相传是佛祖释迦牟尼成道之日。早上,天空已然飘起了雪花,那几天正是最冷的时候,失散多年久没联系的同仁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要送师傅最后一程。大家想给他立个碑,刻个碑文,去征求师傅弟弟的意见。师傅的弟弟也是媒体人,说就不要立碑了,省下的钱就捐给当地学校吧。我知道师傅是同意这么做的,不过碑文还是写了,凭他的性格,估计也想给自己的人生作个最后的总结,能在大家的心里上个头条,想必他是高兴的。
他不喜欢享受,也不愿意享受,
师傅把自己活成了一头斗牛,总是对命运竖起不甘的犄角,却总是用力过猛,被命运折断了;师傅把自己活成了一只飞鸟,想飞越高山大川,但是山高水险,他终未抵达理想的终点;但师傅是把自己活成了一块石碑,树在了生他养他的大山上。
山后山前
站在天目山,回望我的老家桐庐,恍惚间我觉得只是从山后走到了山前,山后是昨天的历史,山前是今天的现实。
那天,大姐打电话给我,说村里想把山脚下的伍公庙修起来,让我也出一份钱。我说该出。伍子胥是我心中敬慕的英雄,当年能到我的家乡,那是缘分;何况,重修伍公庙,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也是家乡父老乡亲的福分。
据桐庐县微志记载:“伍公庙,位于百岁严村南侧,钟洛公路旁。该庙始建于何朝何代已无可查考,祠中供奉伍子胥。”在我儿时印象里,伍公庙就在大姐的屋子旁边,只是年久失修,早就成了一地残垣碎瓦。不过,大姐倒是没有遗忘和冷落这位英雄,平日里清理打扫,逢年过节供香点烛,表达着后辈对先贤的敬仰之情。
春秋战国之交,伍子胥生于楚国,自幼性格刚强,文武兼修,智勇双全,及成年,仕吴国大夫,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谋略家,更是个藐视王权、疾恶如仇、张扬个性的传奇式人物。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兄伍尚都为楚国忠臣,却被楚平王加害。他为报父兄之仇避难出逃,一路颠沛流离,历尽艰难险阻,来到塘源村田坞口,遇到早年跟伍举公(伍子胥祖父)当差,后在楚国青华宫任守吏的查华。伍子胥随查华从田坞口往岭上走,由于山路崎岖,再加上风雪交加,伍子胥与坐骑不慎落入沟底,马蹄踩踏之处,后被分水当地人称“马迹孔”。
我大哥就是在分水五云山读的中学,每到周末,要从雪峰岭翻山越岭回家。有一天,大哥在岭上遇到一只大狗追着他不放,情急之下,他脱下一只凉鞋掷向大狗,结果鞋子被那狗给叼走了。当时,一双凉鞋得一块多钱,鞋子是新买的,大哥自然心疼得不行,捶胸顿足,想从狗嘴里夺回凉鞋,又害怕被狗咬,最后只好悻悻然放弃,光着脚走回家中。每每说起那段往事,大哥总会扯起伍子胥,说正是查华送伍子胥走上岭岗时,见满山积雪,此处山岭才得了“雪峰岭”的名字。
伍子胥与查华作别,继续策马前行,到了严村、夏塘,但见云雾缭绕,古亭鹤立,溪水浩荡,像一条盘龙蜿蜒而去。伍子胥站在岭峰上,近处的板栗树叶子上积满了白雪,像一朵朵盛开的棉花;远处的群山峦岗银装素裹,路上的马蹄印早已被大雪覆盖,料想追兵再也无法辨认其踪迹,从此可以摆脱一路追击,可东山再起图谋大业。想到这里,伍子胥不禁仰天大笑,抽出七星剑,手舞足蹈,纵声高歌:“剑光灿灿兮生清风,仰天长歌兮震长空。员兮员兮脱樊笼,欢庆更生兮乐无穷。”此后,伍子胥歌舞之处被人们称为“歌舞岭”,岭上的村子就叫了“歌舞村”。
说到歌舞村,还有一则被当地人都津津乐道的轶闻趣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杭州知青下放到桐庐,大家按照公社名字各自选择扎根的去处。知青们一看横村,想,横看成岭侧成峰,肯定偏僻,都没有选,又看到九岭,也不行,一座岭已经够呛,这九岭连环,只怕这辈子也走不出去了,还是没有人选;然后就看到了歌舞这个地名——这个名字好啊,载歌载舞,舞榭歌台,莺歌燕舞,歌舞升平,知青们想到了许多美妙而浪漫的词语。好,就这个地方了,大家抢着要去。可总不能都去唱歌跳舞,横村、九岭也得有人去呀,于是抓阄,把命运交给那些小纸团。结果到了地方一看,还真是造化弄人,事与愿违——选了横村、九岭公社的,一个个眉开眼笑,原来横村和九岭距离县城不过十里多地,热个身就走到了,条件自然比较好,经济也相对发达;而那个叫“歌舞”的公社,不但跟歌舞一点不搭边,连车子都没有直接到的,从县城去歌舞,要先坐大巴,再坐拖拉机,然后步行,没有一天到不了,是桐庐当时最偏僻、海拔最高的公社之一,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都非常艰苦。
我有两个舅舅在歌舞村,一个姑妈在子胥村。山高路险,小时候每到春节,我和哥哥、姐姐们去舅舅、姑妈家拜年,母亲都要掇拾一些衣物、糕点让我们带去。舅舅家还算稍近一点,走七八里地就能到了,早上起得晚也能赶上中饭;但是去姑妈家,就得起个大早,还要住一晚才能回来。姑妈家在高山上,从山脚到山顶,要走两个多小时,平日里买个油盐酱醋都是从山下背上去的。因为偏僻,山下通电的时候,山上还在点煤油灯。姑妈轻易不下山,见到我们亲热得不行,一边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羊腿、腊肉招待我们,一边抹着眼泪,怪自己嫁到了这么高的山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歌舞到洛口埠的班车还没有开通,山里的学生要到分水、毕浦读书,全是靠两条腿走路。我十二岁去五六十里外的毕浦中学读书,每次都要带足一个礼拜吃的梅干菜和大米。有一次下雪,我足足走了七八个小时才回到家。
歌舞中学设在高峰村。谁也没有想到,这所简陋的高山上的中学,到了新世纪,竟出了好几位身价过亿、几十亿、上百亿的富翁。如今,全中国的老百姓差不多每天都要跟“三通一达”打交道——中通的赖梅松、申通的陈德军、圆通的张小娟,都是歌舞中学85届同一个班的同学;韵达的聂腾云,也是这所学校走出来的;除了“三通一达”的老总,还有十几个身价上亿的快递老板,也曾在这所学校就读。时任歌舞校长的许云龙说:“这是一代人的梦想,他们是一群有理想、肯奋斗的人,他们用快递改变了这个世界。”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山高水险,阻塞的是交通,却挡不住他们理想的翅膀。我甚至想,“三通一达”肯定不是他们开办公司时取的名字,这名字像种子一样,早就播在了他们心里,在儿时玩耍的河畔沟边,在上学放学的坎坷路上,在为买一本作业而不得的翘首盼望中,“通”和“达”已经花儿一样开放了,芬芳着他们的理想,引领着他们的脚步,终于走出了大山,走遍了全中国,走向了全世界!
1996年,我去歌舞乡天井村采访,这是桐庐县唯一没有通公路的行政村,真像天井一样高耸在海拔九百五十米的山顶。我沿着一条羊肠小道攀沿上去,几乎爬了半天时间。村书记苦笑着向我介绍,天井村是光棍村,村里大大小小有几十个光棍,村里的姑娘都想嫁出去,外边的姑娘却不肯嫁进来,有的人外出打工对象都谈好五六年了,可人家姑娘说公路不通就别来娶亲……这公路,村里已经修了八年了,钱也花了四十多万,还搭进去三条性命,可修到了第八个年头,最后一段一百米的山洞却难倒了大家,村里实在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了……
在村委办公室,我看到了一本厚厚的记账簿。全村四百八十人,除了孩子和五保户,所有人的名字都在上面。这些年来,村民卖茶叶、木材的钱,几乎都花在这条路上了。为了修路,每户人家都被掏空了。村里的一些老人,从来没有下过山,没有坐过汽车,小朋友们更没有见过火车,有个小朋友问我,火车是不是长得和拖拉机一样。
我在天井村住了几天,走访了很多村民,回来写了一个长篇通讯 《最后的一百米》,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后来经过多方努力,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天井岭第二年终于通车了。
路通了,山里人就一步跨进了新世纪——2002年,中通快递成立,掌门人就是天井村的赖梅松。谁能想到,天井村会走出一个中国快递的巨头!现在的天井村,碧山环绕,洋房林立,车道是山区罕见的双向六车道。在赖梅松心里,路,是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情结。中通发展起来以后,他为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斥巨资修了这条通天坦途。
歌舞现在归并到了钟山乡,是“中国民营快递之乡”。从夏塘村、天井村、子胥村这些偏僻的山村里,走出了四大快递巨头,“三通一达”已遍布全国,他们的脚步已经走向了世界,走进了千家万户。然而,无论走得再远,他们的根还扎在山里,站在城市的霓虹灯下,回望家乡的山山岭岭,他们永远记得那是他们出发的原点,是他们寄托初心的地方。
如今的歌舞,成了名副其实的“载歌载舞、歌舞升平”的福地。
前几天回老家,遇上大表哥来看我父母,带来了茶油、番薯粉等很多自家的山货。大表哥开着农用车,红光满面,精神十足。他说,从前下一趟山,都是肩背手提的,现在交通方便了,一脚油门,就从山上到了山下。年輕人在杭州、上海、武汉、深圳等地做快递物流,平日里各忙各的,都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来;年纪大一点的不想外出,在村里捯饬捯饬也有收入。现在农村不比以前,只要勤快一点,不用外出打工,像表哥这样,每年赚个七万八万都没有问题。春季茶叶,夏季高山西瓜,秋季山茶油,门前屋后的鱼塘里再养点鱼,山里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很满足。
大表哥七十多岁,我父母八十八岁,虽然隔着一辈,也都是古稀、耄耋之人了。他们坐在院子里说这话时,正是初秋时节,对面坡上的油茶花,洁白如雪,纷纷扬扬,整座大山都充满了柔情蜜意。
有那么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人心里都有一座山,走不出去时,山压在我们身上,是我们在背山,感受到的是生命不堪之重;走出来了,山还在心里,却是山在背着我们,山是大地的肩膀和母亲的胸怀,我们一直受着山的恩宠和滋养,三餐四季,从未远离。
责任编辑 吴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