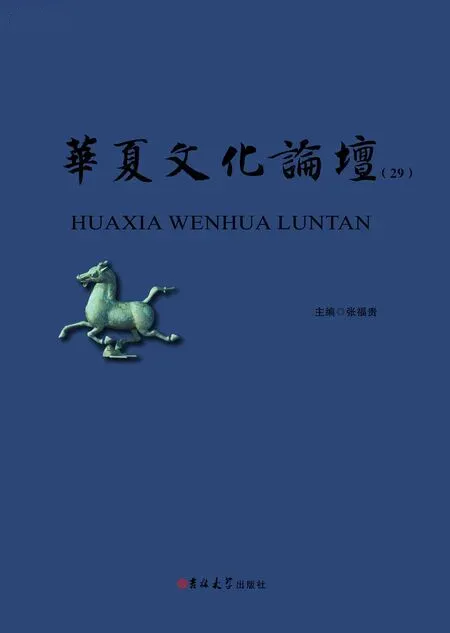绝望与希望边缘的声音
——青年鲁迅的“文艺运动”与G.F.瓦兹画作《希望》
王 路
【内容提要】“幻灯片事件”之后,鲁迅离开仙台来到东京,计划以文艺改变愚弱的国民精神,这场预想中的“文艺运动”以杂志《新生》的创办为开端。彼时鲁迅的精神体验正是他为第一期《新生》所选插图,英国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瓦兹的油画《希望》所象征的。“希望”这一主题关联着鲁迅在不同生命情境下对自身与民族存在状态的思考,观察画作《希望》所产生的视觉经验和审美体验作为周树人对文艺“原初的激情”,从主题、内容与表现手法上都对“文艺运动”时期的鲁迅产生了一定影响,无疑是构成“文学家”鲁迅的诸多要素之一。
1906年,鲁迅离开仙台来到东京,计划以文艺改变愚弱的国民精神。这场预想中的“文艺运动”①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及自己“弃医从文”的经历说:“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以一本杂志的创办为开端,杂志命名为“新生”,意为“新的生命”。虽因“资本的逃走”《新生》未能成行,但此间创作的几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了《河南》杂志上,翻译的外国小说也结为《域外小说集》出版发行,学界常以此探察鲁迅“文艺运动”时期的思想。如北冈正子认为《摩罗诗力说》的内容超越了批评和介绍的领域,包含着鲁迅文学的出发原点的成分,其观点也关系到鲁迅“文艺运动”思想的核心。②[日]北冈正子:《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3页。据许寿裳回忆,《新生》的外文名并未采用现代英文词汇,而是取自但丁长诗《新生》的拉丁文“Vita Nova”。③许寿裳:《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5页。在但丁的《新生》中,诗人在天国真理的化身贝阿特丽丝的引导下进入天堂,获得新生。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摩罗诗力说》中所示鲁迅的“文艺运动”主旨:在人类精神发展中寻求救国救民方策。就此而言,“幻灯片事件”可谓鲁迅探寻救国救民思想的转折点,如《野草》中《希望》一篇所陈述,自此之后鲁迅开始否定和怀疑此前所歌唱的“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复仇”,内心陷入了空虚。空虚绝望之后,他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文艺,于希望与绝望的边缘“动吭一呼”,期待“闻者兴起,争天拒俗”“精神深感后世人心”。①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这种状态正是鲁迅为第一期《新生》所选插图,英国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瓦兹的油画《希望》所象征的。孙郁曾在《鲁迅藏画录》中这样描述瓦兹的油画《希望》:“那里灰暗中的闪亮,犹如夜中的电光,抖动着惊异的美。人在被囚禁的时候,还沉浸在幻想里,不甘于精神的沉落,也正是留学日本时的鲁迅的状态。”②孙郁:《鲁迅藏画录》,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46页。鲁迅是在什么情境下看到这幅画?为什么选取这幅画作为第一期《新生》的插画?画作的象征手法以及表现内容对鲁迅有着怎样的触动?对于这些问题学界尚未有文章进行专门探究。从《摩罗诗力说》中可知,诗、绘画、科学是鲁迅“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往的研究在关注这一时期的鲁迅时,仅将其看做文学史事件,留学生周树人对周边世界的感知与互动似乎被鲁迅的光芒笼罩,从而遮蔽了一些细节性的问题。毫无疑问,在这场“延迟”的“文艺运动”中,青年留学生周树人的视觉经验作为对于文艺原初的激情是构成“文学家”鲁迅的诸多要素之一。以此观之,作为《新生》插图的英国象征主义画家瓦兹画作《希望》与留学生周树人的关系探究,既为观察早期鲁迅思想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亦能兼顾日本乃至世界文化对其的影响,或将更深层次挖掘鲁迅“文艺运动”时期思想甚至文学原点中被忽略的一面。
一、“摩罗诗人”与瓦兹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谈及《新生》杂志时说:“鲁迅的《新生》杂志终于没有办成,但计划早已定好,有些具体的办法也已有了。……第一期的插画也已拟定,是十九世纪画家瓦支的油画,题云‘希望’,画作一个诗人,包着眼睛,抱了竖琴,跪在地球上面。英国出版的《瓦支画集》买有一册,材料就出在这里边。”③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止庵校订,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11页。
乔治·弗雷德里克·瓦兹(George Frederic Watts 1817—1904)是19世纪下叶英国象征派画家,《希望》是其“生命之屋”系列的其中一幅(其他两幅分别为《爱》与《生命》)。1904年瓦兹去世后日本《美术新报》开始了对他作品的连载,《希望》与其他七幅作品一起刊出。④见《美术新报》1904年第10、12、13期。[Fuji Shozo,“The Origins of Lu Xun’s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Watts’ and Petofi’s Hop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sletter,Vol.5,No.1/2(Spring/Fall 1979):8-16.]至1907年,日本出现了一股“瓦兹热”,艺术类与文学类杂志陆续刊登有关他的文章,包括《希望》在内的许多作品被用于印刷封面或者画册。①[日]陆伟荣:中国の近代美术と日本——20世纪日中关系の一断面,冈山市:大学教育出版,2007年,第161页。自幼对美术有着浓厚兴趣的鲁迅一定也受到了这股“瓦兹热”的影响,故而将《希望》作为第一期《新生》的插图。因早期鲁迅材料有限,无法确定鲁迅最初是在哪本书或者杂志上看到瓦兹的油画《希望》的。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曾对这一问题做过细致考察:他从鲁迅和周作人留学期间常去的丸善书店着手,查阅1905到1907年间亦即《新生》筹备期间丸善书店发行的用以发布重要书籍广告的《学灯》杂志,发现在这期间《学灯》发布的书籍广告中有关瓦兹的只有一本G.F.Watts,是伦敦出版社出版的“纽恩斯艺术图书馆系列”(Newnes Art Library)中的一册。丸善书店共发布了四次有关G.F.Watts的书籍广告,其中一次是有关书已售罄的提示。②Fuji Shozo,“The Origins of Lu Xun’s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Watts’ and Petofi’s Hop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sletter,Vol.5,No.1/2(Spring/Fall 1979):8-16.丸善书店是当时日本最具规模的外文书店,鲁迅和周作人多从这里获取西方文艺书籍,这本G.F.Watts很有可能就是周作人所说的“英国出版的《瓦支画集》”。
“纽恩斯艺术图书馆系列”出版的G.F.Watts除复制了瓦兹的部分著名作品外,还包括W.K.West为瓦兹所作的传记以及Romualdo Pantini的一篇题为《乔治·弗雷德里克·瓦兹的艺术》的文章。传记细致梳理了有关瓦兹的几乎所有资料,被认为是最完整的瓦兹传记;文章则围绕“思想的画家”展开对于瓦兹作品与艺术观念的评论。文中Romualdo Pantini引用瓦兹自己的话概括他的艺术观念:“我的目的与其说是要画出能使人赏心悦目的画,倒不如说是要提出一种伟大的思想,使人联想到想象力和心灵,唤起人类最美好和最崇高的一切。”③G.F.Watts(London: George Newnes Limited,1905),p.21.与瓦兹同时代的英国文学评论家G.K.切斯特顿在“流行艺术图书馆系列”出版的G.F.Watts认为:在瓦兹那里,希望是朦胧的、微妙的也是不朽的,瓦兹的精神信仰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怀疑主义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享乐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当信条崩塌众神似乎被瓦解以至消失时,他始终没有退缩,并以画作传达灵魂的坚不可摧。④Chesterton G.K.,G.F.Watts(London:The Ballantyne Press,1904),p.13.可以发现,瓦兹的自我观与摩罗诗人“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⑤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的性格十分相似,他以作品传达思想继而召唤人类崇高精神的艺术观与先觉者摩罗诗人通过文艺作品的情感感染力唤醒民众“自觉”精神的审美交流过程也非常相似。
“文艺运动”时期鲁迅的文学思想包含着一个理想的摩罗诗人和一般读者群众的审美交流模式。摩罗诗人以文艺作品的情感感染力为中介唤醒民众,使民众在耳濡目染下感动兴发、产生作为“人”的自觉,民众以“自觉”的精神回应诗人,诗人与民众达到共情和理解,彼此之间没有隔阂,完成一个完整的审美交流过程。鲁迅的“文艺运动”以此关系展开,正如周作人在《哀弦篇》中所说:“民以诗人为导师,诗人亦视民如一体。”①独应:《哀弦篇》,《河南》,1908年第9期。这一时期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并非鲁迅所独有,然鲁迅的“文艺运动”与梁启超的单向灌输式的政治宣传小说以及章太炎为“一新士风,提升革命主体之道德”②林少阳:《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4页。的“文”之革命有着根本的区别。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一文中谈到鲁迅当年和梁启超的新小说运动的渊源说:“梁任公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见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紧接着强调:“不过这只是不看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③周作人:《瓜豆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162页。可见鲁迅重视的是文艺作品潜移默化的感染力,相较于一般的“启蒙主义”,超越了单向度的关系,包含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情感互动。与章太炎的文学观分歧亦见于此,据许寿裳回忆,章太炎曾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的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黯然不服,在课后对许寿裳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别,《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④许寿裳:《鲁迅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第30页。好的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通常也具备很好的思想或情感感染力,这种对文艺作品审美情感交流力量的寄托与期待贯穿鲁迅的整个文学生命,他的小说、散文、杂文无一不具有这种特质。
使人产生移情的快感的,除了文学,还有美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谈及美术时认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他还引用爱尔兰诗人道登的话:“美术文章之杰出于世者,观诵而后,似无裨于人间者,往往有之。然吾人乐于观诵,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⑤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3页。鲁迅看中的是文学与艺术的“无用之用”,文艺作品首先应具备完善的审美品质,之后才能发挥感动人心的力量。“摩罗诗力”来自摩罗诗人的刚健不挠、抱诚守真的“心声”,这种“心声”又承载着鲁迅改造国民精神的希望。作为19世纪英国象征主义绘画代表人物的瓦兹,处于逐渐瓦解的旧时期和缓慢展开的新时期交替的阶段,同样在思考自身的存在状态,以期通过绘画表达自己与世俗恶习或不道德行为的决裂,他在绝望的边缘以反叛的姿态发出最后的希望之声。摩罗诗人通过文艺作品情感的力量感染并唤醒麻木的民众,瓦兹通过画作去启示某些神秘的寓言和思想活动,他们都相信通过发扬精神上的善可以期待美好时代的到来。这是先觉者在试图使用艺术来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其原初的动力是对于“人”的存在与价值的思考。
二、瓦兹《希望》:青年鲁迅的“自画像”
在G.F.Watts一书中Romualdo Pantini对油画《希望》描述如下:“这幅画不需要标题。眼睛上缠着绷带的年轻女孩优雅地斜坐在地球上,呈现出正在倾听的姿态。她左手握着仅剩下一根琴弦的七弦琴,其他断了的琴弦飘扬在微风中,但是对于盲女来说,那根在神秘暗光中震动的琴弦发出的声音,就是整个生命。”①G.F.Watts(London:George Newnes Limited,1905),p.21.Romualdo Pantini的描述显然结合了瓦兹本人对这幅画的解释,1904年日本《美术新报》刊登瓦兹作品目录时,在《希望》一画下标注了瓦兹自己的一句话:“希望不是简单的期待,它类似于用仅剩的一根弦演奏出的乐曲。”②Fuji Shozo,“The Origins of Lu Xun’s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Watts’ and Petofi’s Hop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sletter,Vol.5,No.1/2(Spring/Fall 1979):8-16.《希望》是集中体现了瓦兹的反叛精神与象征意义的代表作,在欧洲古典绘画中,“希望”这一主题多被描绘成一名年轻的女性手中拿着一朵花或一个锚,意指上帝的恩典③希望在基督教中被描绘为锚是源自《圣经》,《希伯来书》 第六卷第19段:“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Tromans Nicholas,Hope: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Victorian Icon(Compton,Surrey:Watts Gallery,2011),p.11.](如托马斯·劳伦斯的《如希望的乔治亚娜·玛利亚·莱斯特》)。而在瓦兹这里,“希望”与上帝的教义无关,表现为个体的行动与自我完善。瓦兹处于19世纪末经济萧条时期的英国,彼时作为基督教教义的“希望”的概念开始被普遍质疑,建立在尼采怀疑主义基础上的新哲学流派甚至认为“希望”是一种徒劳的努力。④Warner Malcolm,The Victorians: British Painting 1837–1901(Washington D.C.:National Gallery of Art,1996),P.30.在此基础上,瓦兹对希望进行重新构想与描绘,呈现出于绝望边缘发出希望之声的全新的希望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回忆中的画面是“一个诗人,包着眼睛,抱了竖琴,跪在地球上面”⑤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止庵校订,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11页。。或许女孩弹奏七弦琴的造型与摩罗诗人以先觉之声唤醒沉睡民众的形象相似,周作人把女孩理解为诗人。但将象征画作主题“希望”的琴弦细节忽略,从视觉经验上体现出周作人在审美情感甚至美术观上与鲁迅的差异。鲁迅选择油画《希望》作为《新生》插图,深层次原因是收到了瓦兹所传达的“绝望中抱持希望抗争”的含义,通过画面中美的精神、个性的力量与拒俗的气象感受到了移情的快感。
1907年日本美术界形成“瓦兹热”的艺术风潮,此时鲁迅已决定弃医从文,正处于民族出路的探索时期,刚从“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苦闷和挣扎中走出,寄希望于文艺运动。在观看这幅画时,自我与外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在鲁迅那里一定是产生了复杂的关联。我们不妨暂且排除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搁置瓦兹本人的艺术观与自我观,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屈原式民族忧愤为情感基调,去靠近鲁迅凝视这幅画时的视觉经验。它是一幅超现实的图景,位于画面中央屈坐在地球上的女孩与昏暗的背景相映成彰,犹如黑夜中的亮光,首先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力。绑着绷带的眼睛与女孩脸上忧郁的表情营造了绝望、压抑的氛围,细腻柔和的笔触与沉郁的氛围配合得恰到好处。她如对待新生的婴儿般紧紧抱着仅剩一根琴弦的七弦琴。七弦琴是古希腊抒情诗女神厄拉托的象征,其音质清纯犹如来自天界的声音,被认为是最崇高的音调。眼盲但表情坚定平和的女孩寄希望于这把损坏而未完全破坏的七弦琴,期待仅剩的一根琴弦能够弹奏出打破寂静的乐曲,以改变这暗郁的世界。在《摩罗诗力说》的结尾,鲁迅引用柯罗连科《最后的光芒》中的场景:一个西伯利亚的少年在跟一位老人学读书,书中描写樱花和黄莺,但是在西伯利亚的寒冷气候下,不会有这种植物和鸟。少年不能理解,老人便解释说:“那些黄莺就是栖息在樱花枝上,放开歌喉,引吭唱出美丽悦耳的歌声的鸟儿啊!”少年便陷入了沉思。在这段小插曲之后,鲁迅对《摩罗诗力说》进行了总结:“然夫,少年处萧条之中,即不诚闻其好音,亦当得先觉之诠解;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①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03页。沉思着聆听摩罗诗人声音的鲁迅,恰似画中女孩聆听仅剩一根琴弦的七弦琴演奏出的乐曲。
对于留学生周树人来说,瓦兹的《希望》既像一面镜子,又像一幅自画像。前者使他回想起过去充满热情和希望的“血腥的歌声”,后者让他看到了处于绝望边缘仍期待听到希望之声的现在。最初的希望源于对自身以及民族状态的思考,这种思考大概可追溯至南京矿路学堂时期,彼时受《天演论》的启示加之民族、家庭、个人的危机感,青年鲁迅意识到一种“自立”“自强”“自主”的生命的力。此期所刻“文章误我”“戎马书生”“戛剑生”三枚图章正是这种民族情感的直接表达。②陈朴:《鲁迅与篆刻》,《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7期。后来他借“戛剑生”之名抒写客子之愁③如《戛剑生杂记》(1898年),《庚子送灶即事》(1901年),《祭书神文》(1901年),《和仲弟送别元韵》(1901年)。见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7、533、534、536页。,并在《自题小像》中将乡愁上升至家国情怀,表现出“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屈原式民族忧愤。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与希望通过某种途径干预的紧迫感构成青年鲁迅最初希望的一体两面,同时也形成鲁迅生命中的根本矛盾。作为先觉者的青年周树人起初试图以科学启发国民革命意识,并在日本科幻小说流行趋势的影响下,以古典小说的样式译介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幻小说。后又希望以现代医学打破国民的迷信思想、增进其对科学的信仰,帮助不幸和勇敢的人们战胜困苦和死亡。直到“幻灯片事件”,鲁迅开始深刻认识到国民的愚弱,对灵魂的拯救重于躯壳,科学的启示、摩罗诗人的启发以及民族传统文化血液中的屈子式“发愤抒情”、司马氏的“桀骜”、嵇康的反叛独立精神,使其意识到文艺转移国民性情的巨大力量。这条路是否能够走通,中国的文化情境下能否出现“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的民众教导者,在面对社会群众的现实时,鲁迅的心中也不免产生疑惑。G.K.切斯特顿描述《希望》一画道:“与其说画的名称‘希望’是作品的本质,不如说它是一个警句”④Chesterton G.K.,G.F.Watts(London:The Ballantyne Press,1904),p.49.,被誉为时代“先知”的瓦兹通过象征的表达方式,传达给鲁迅一个有关“希望”的古老且神秘的寓言:处于绝望与希望边缘发出的声音,不只需要反抗与拒俗的先觉者精神,还要承担玉石俱焚的风险。此后《新生》的夭折、辛亥革命的失败均一一验证了鲁迅的困惑。在晚清革命时代,作为先觉者和革命者的诗人与一般民众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复杂而充满矛盾对立的,鲁迅意识到自己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中国也不可能出现摩罗诗人式的精神界战士。多年以后,他在散文诗《希望》中,将这段青春时期的“希望”称作“自欺的希望”。他在反思中自我否定但又未全盘否定,因而在《坟》中为这段过去的激昂造了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埋藏一面留恋。
需要说明的是,瓦兹的《希望》实际上有两个版本,原作是私人收藏,现在看到的版本是作为复制品在1897年赠予泰特的,现存于英国泰特美术馆。据泰特美术馆介绍,按照那个时代的工作室惯例,后一版本的《希望》很有可能是由助手西尔·肖特着手进行,瓦兹作以补充。瓦兹认为第二幅《希望》是更好的版本,并于1889年在南肯辛顿博物馆和巴黎世界博览会展出。这一版本绘画的笔触更加柔和,女孩脸上的表情也更神秘。与之前版本不同的是,瓦兹去掉了天空中的星星,而星星可以说是画中唯一乐观的表达。①https://www.tate.org.uk/art/artworks/watts-hope-n01640,访问日期:2022年12月1日。虽然是细节的修改,但星星的删去使得整个画面更协调,更加鲜明地突出了“绝望中的希望”的主题。油画《希望》在瓦兹去世之前即已在美术界产生一定影响,流传最广的应为画家本人较满意且公之于众的第二幅,而不是作私人收藏的第一版本。日本《美术新报》连载的以及纽恩斯图书馆系列出版的G.F.Watts中介绍的均为第二版本,可以确定鲁迅为《新生》所选的是第二幅《希望》。女孩的世界没有任何光亮,恰如处在困顿和疑惑中的留学生周树人,他们的“希望”(前者寄托于用残损的七弦琴演奏出的乐曲,后者表现为以情感感染力唤醒国民的“文艺运动”),都不是简单的期待,是处于绝望与希望的边缘发出的声音。
青年留学生周树人,游走于文化特殊性(中国历史境况)与跨文化性中,新的视觉话语在无形中通过感官影响和建构着他的知性。《摩罗诗力说》作于1907年,或许在确定《新生》插图之前,也有可能在其后,或者同时发生也不无可能。实质上这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透过瓦兹和摩罗诗人之间的相似性,《希望》表现的内容与鲁迅所处状态的契合,可看到西方文艺思潮通过日本这一文化场域对青年鲁迅思想的影响。不管是英国画家瓦兹影响了鲁迅“摩罗诗人”形象的构建,还是美、个性、拒俗的评判标准促使鲁迅选择了瓦兹的《希望》作为《新生》插图,其中均可见出鲁迅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独特思考。
三、从《新生》插图到《域外小说集》封面
《新生》最终因“担当文字的人”与“承担资本的人”相继离开夭亡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回忆起这段往事道:“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②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作为少数先觉者被冷落的悲剧,此时的鲁迅并未完全体认到社会历史方面的因素,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意识到在革命的潮流来临时,一切停留在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势必被众声喧哗的浪潮所淹没。留学生周树人虽然悲观、焦灼、苦恼,但并未放弃“文艺运动”的希望,也正是因为还未对世界完全失望,他开始反思自身并继续积聚力量等待时机。接受《河南》杂志的约稿后,鲁迅似乎找到了丢失的阵地,先后发表了《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系列论文,与周作人的《论文学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哀弦篇》,以及许寿裳长文《兴国精神之史曜》一起从科学、历史、哲学、政治、美学、文学各个角度系统评介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凝视中国传统思想中应该否定的负面东西,以否定认识为媒介寻找批判的武器,直击传统思想的糟粕。但这些还远远不够,设想中的“文艺运动”还应注重文艺作品本身的审美特质与思想倾向,鲁迅本着“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思想积极翻译介绍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1920年鲁迅为重刊的《域外小说集》撰写新的序言道:“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①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翻译外国新文学的工作实质上从初到东京弘文学院时期便已开始。②1903年先后发表了《哀尘》《斯巴达之魂》《说鈤》《中国地质略论》《月界旅行》《地底旅行》6篇译作。
《域外小说集》的出版使得《新生》的梦想逐渐付诸实现,这本翻译小说集的封面却并未使用当时为《新生》所选的插图。作为第一本自己出版的书,封面由鲁迅亲自设计。纸张上选用了触感细腻温暖的日本罗纱纸,灰绿色的底色衬托下,上端印有一幅长方形的插画。画中一名着古希腊装的女子正在弹奏七弦琴,她的眼睛望向远方海平面上冉冉升起的朝阳,插画下方是由陈师曾用篆字书写的书名,似与书中古奥的译笔相呼应。西洋风的插画与古朴的汉字相称,呈现出现代的意味。鲁迅在序言中称赞道:“至若装订新异,纸张精致,亦近日小说所未睹也。”③鲁迅:《〈域外小说集〉第一册》,《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5页。言语中可见对《域外小说集》封面装帧的满意。有学者指出,封面图案画出自《来自外国语》1905年第4卷插图,并认为选择这幅画是因为对鲁迅而言,“诗人、少女/文艺女神、竖琴等意象包含了‘文学作为新声、心声与希望’的内涵,象征了‘异域文术新宗’,也寓意歌德、屈尔施讷所倡导的‘世界文学’”④崔文东:《青年鲁迅与德语“世界文学”——〈域外小说集〉材源考》,《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最初触动青年鲁迅的或许只是七弦琴、女人及其所表征的“希望”主题。怀抱乐器的女性形象是与瓦兹同时代画家罗塞蒂后期作品的特色,也在维多利亚时代象征派画家中较为流行,具有美感、诗歌、激情或者音乐等象征意义。⑤Charlotte Purkis,“Listening for the Sublime:Aural-Visual Improvisa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Musical Art,”Tate Papers,no.1,(Autumn 2010),https://www.tate.org.uk/research/publications/tatepapers/14/listening-for-the-sublime-aural-visual-improvisations-in-nineteenth-century-musical-art,accessed 26 August 2020.这种象征性的表现手法对20世纪初的日本美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以弹奏乐器的女性形象插画附以中国汉字的书籍装帧形式渐渐成为一种潮流,如博文馆发行的《文章世界》,以及森鸥外《十人十话》封面①[日]陆伟荣:中国の近代美术と日本——20世纪日中关系の一断面,冈山市:大学教育出版,2007年,第162页。(见图3、图4)。鲁迅受此现代感日本书籍装帧潮流影响,兼顾文艺转移国民性情的主旨,设计了《域外小说集》的封面。

图1 乔治·弗雷德里克·瓦兹画作《希望》(1886年,英国不列颠泰特美术馆藏)

图2 鲁迅《域外小说集》(1909年,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图3 《文章世界》(1906年,早稻田大学藏)

图4 森鸥外《十人十话》(1911年,早稻田大学藏)
与瓦兹的《希望》不同的是,《域外小说集》封面中悲伤暗郁的感觉似乎已全无踪迹,女孩弹奏着象征美感与诗的七弦琴迎接升起的太阳,朝阳照亮了黑暗,给人一种光明世界的预感。或许是在《河南》杂志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使鲁迅看到了重新燃起的希望之火;抑或是在俄国与东欧弱小国家的叫喊和反抗中得到了民族出路的启示。原本几乎幻灭的梦想得以实现,丢失的阵地再度在眼前展开。鲁迅和周作人酝酿了一个大体计划,首先选择与中国现实切近的作家和作品,这些作家大部分来自俄国、北欧和东欧,译法上则采取直译的手法。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写道:“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人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②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可见彼时周氏兄弟对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怀着巨大的希望。周作人曾回忆起他和鲁迅当年对于俄国和波兰等国的文学的狂热,“为的是佩服它的求自由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学”③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止庵校订,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75页。。鲁迅和周作人经过自觉选择而从事的翻译工作实质上也是一种表现译者个性与思想的创作,他们透过选择题材与资料传达自己的情感与思想,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具有象征性质的文艺实践。
从瓦兹《希望》到《域外小说集》封面,在视觉效果上摒弃了色彩、光影、笔触所营造的情感氛围,代之以超越外表的纯粹的内在力量和想象。对插图、封面选择的视觉性变化不可分割地与鲁迅思想的微妙变化相连。《新生》时期他一度倾心于浪漫主义文学,至《域外小说集》时期,开始欣赏安特莱夫、迦尔洵深刻的社会性以及他们具有高度凝聚力的象征手法。以《域外小说集》时期的审美倾向观之,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采用象征的手法并非偶然。两幅“希望”主题的画作与《新生》的夭亡以及《域外小说集》的受挫,暗示了青年鲁迅追寻“希望”的苦难旅程。多年以后,他在散文诗《希望》中说:“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域外小说集》的滞销使鲁迅自此陷入了无边的寂寞和悲哀,先觉者不被民众理解的现实使他意识到要实现文学的“无用之用”,理想的审美情感交流结构还需要理想的民众回应。他借裴多菲之口揭露“希望”对“我”的欺骗,并表示彼时自己内心的希望之火已奄奄一息:“希望是甚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④鲁迅:《希望》,《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82页。
四、结语
“于绝望的边缘发出希望之声”,是瓦兹画作《希望》所表现的主题,也是弃医从文之后试图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的先觉者鲁迅自身生存状态的写照。无论是作为医学生留学日本的青年周树人,还是希冀以文艺的力量唤醒国民的先觉者,或者陷入寂寞彷徨无地的绝望者,以及绝望地独自对抗暗夜的精神界战士,都从未放弃“生”的希望,始终在思考自身与国家、民族的生存状态。“希望”这一主题关联着鲁迅在不同生命情境下对自身与民族存在状态的思考。瓦兹画作《希望》从主题、内容与表现手法上都对“文艺运动”时期的鲁迅给予了启示,在鲁迅思考“希望”之初通过情感感染力影响了他用以发挥文艺“无用之用”的“审美交流结构”的建构。“希望不是简单的期待,它类似于用仅剩的一根弦演奏出的乐曲”是瓦兹关于希望的寓言,正像摩罗诗人握拨一弹便能使人觉醒的心声,也如鲁迅空虚暗夜中的希望之盾。青年鲁迅、瓦兹、摩罗诗人都在绝望之中抱持着希望,并在希望的引导下走向自我完善。《新生》流产之后,鲁迅的“文艺运动”并未结束,从《新生》插图与《域外小说集》封面的选择中可通过视觉性窥探鲁迅思想的微妙转变。象征主义的视觉经验从《新生》时期起便对鲁迅产生了多样且不可预见的意义,翻译象征主义文学作品不仅仅出于自觉的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是自我情感的象征式表达,从表现手法上为《狂人日记》以至《野草》等作品埋下了象征主义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