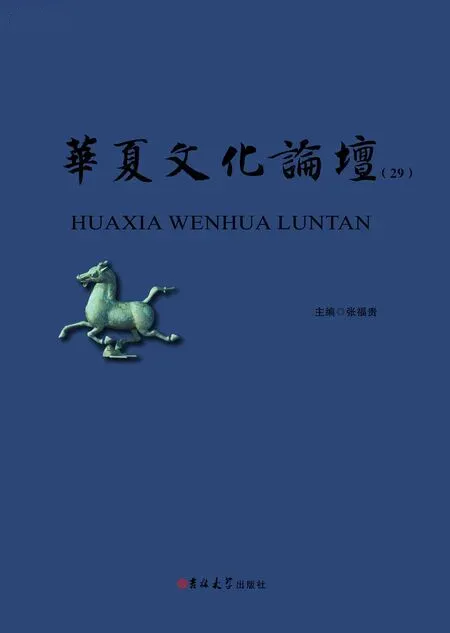超工业化景观:从斯蒂格勒的象征理论到东北工业文创建构
鞠惠冰 王丽媛
【内容提要】以东北工业文创为代表的工业文创热潮重新开发和定义了旧有的工业遗产,并在新时代语境下孕育出了新的社会景观。本文从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象征理论出发,结合传播学视角从假象领域和个体感知两个方面对东北工业文创呈现的动态图景进行剖析,进一步考察超工业化景观中技术和美学的共生、整体和个体的同频、个体和个体的联结,以及被重新规划整合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一、问题导入:东北工业文创呈现的社会景观
21世纪以来,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记忆的形成、传播和再造等环节正在被全面重塑,工业社会原有的社会系统结构和社会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工业文创热潮重新开发和定义了旧有的工业遗产,并在新时代语境下搭建起具有复杂时间客体的假象领域,展示了工业发展中的新旧技术更迭和过渡,弥合了由工业技术带来的文化认知分裂,工业历史记忆被重新书写。正如斯蒂格勒在《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的序言中写道的那样:“我们时代的特征就是工业技术对象征控制的把持。”超工业时代的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在统一的意志下整合,技术和美学在空间表现的想象张力里共生,整体和个体在时间客体的蒙太奇拼接中同频,个体和个体在共通的知觉中滋生友爱,新旧技术、新旧城市的分隔线被一种“集体记忆”下的集体计划替代,社会关系被重新整合,社会秩序被重新规划。
由于丰富的工业遗产资源和城市发展的迫切需求,我国东北地区工业文创的转换极为迅速。多种多样的文创形式将工业制造的具体生产技艺和物质空间进行了艺术化改造,使得工业技艺技术转化为被用来展示和再开发利用的工业文化符号,并改变了传统的围绕着工业生产的人与物的关系,文创空间呈现出来的新的社会景观将抽离出来的象征符号进行了分离和重组,使之成为被观览的“博览物”,个体也被媒介技术嵌入“博览物”的展示和传播中……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能只是忙于欣赏技术所带来的新的繁荣景象,更要思考的是,新的技术是如何改变了工业文创的媒介属性和媒介特征,象征表达是如何重塑和定义当下的工业精神和历史记忆,个体是如何在技术座架下感知社会和认知自我的……这需要一套新的逻辑来重新认识东北工业文创呈现的动态图景,以及其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所呈现出的超工业化景观。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斯蒂格勒的象征理论开启对东北工业文创社会景观的全新解构,通过文献分析和访谈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把握东北工业文创动态图景这一研究主体,沿着象征信息流动的传播链条捕捉动态图景中的传播端“假象领域”和接收端“个体感知”。并以此为切入点,分别对东北工业文创所呈现的假象领域和领域中个体的感知型接收状况进行深入剖析,探讨东北工业文创所呈现的超工业化景观的典型性和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将斯蒂格勒的思考和疑问引入对东北工业文创的考察研究中,延展出一些新的思考:多形态的东北工业文创构建了一个怎样的假象领域?多形态的记忆工程技术/媒介技术是如何将假象领域构建起来的?在假象领域中,共时记忆、集体记忆是否会将个体意识吞没,造成个体失去差异性和主动性?东北工业文创是消费主义和技术逻辑下对“文化工业”品的复刻,还是有着旺盛生命力和人文关怀的新型文化形式?
二、理论框架:斯蒂格勒的超工业化景观
(一)理论基础:斯蒂格勒的记忆持存与象征理论
斯蒂格勒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人的历史性存在是从技术的出现起始的,即人的历史存在是在工具的制造与使用过程中被发明出来的。工具(技术)既是劳动、计划和超前的对象,同时也是保留这些经验和后种系生成结果的记忆载体,是保存出现在人体之外的物性存留。①张一兵:《人的延异:后种系生成中的发明——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解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3期。从古至今,记忆持存在不断存留和传播人类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形态变化和丰富的意识层次。随着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兴起和网络化,原本的工业体系构序结构被改变,技术体系、记忆术体系乃至世界化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融合到了一起,承载着深层次的技术逻辑和复杂的社会关系:记忆工程技术成为技术体系核心,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数字化全球记忆体系,个体通过感知接入持存装置在集体记忆中被重新发现,人与技术在数字化信息传播中共生共长……新的社会文化、社会景观应运而生。
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第三卷中写道:“世界自我投映所借助机制的拓展具有前所未有的实效性,并促生了一个新的假象领域,努力为‘大写的我们’提供了新天地。”在新技术基础上构建的社会景观中,斯蒂格勒理论中的三种持存都被多形态的媒介技术纳入融合,由此对时空的时序结构进行排列重组,构建起复杂的时间客体:“第一持存是意识留存在时间流的现在之上的东西”①张一兵:《好莱坞文化殖民的隐性逻辑——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构境论解读》,《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对应着个体的原生记忆,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体对事物本身的直观感知;在此基础上的第二持存是通过个体主动选择过滤之后保存下来的持存,对应着想象力重塑的“当下”呈现;第三持存则对应着人类物种拥有的第三种记忆——技术的记忆,因此在第三持存的记录工业中,技术被赋予了超前意识,以“先将来时”的存在状态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结构进行了分解和重构。由此,过去发生的现实可以转化为现在的真实发生,过去的不可能可以预言未来的可能。在经历这一复杂时间客体时,个体感知波动迅速被持存装置捕捉,生命的流逝和记录的重放相互融合,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界线在同感中消融,表演与现实边界消失,生活与蒙太奇虚构同质化,想象和感知换位,原生记忆、第二记忆、第三记忆(持存)相互混合……历史和现实的桥接中新的假象领域被建立起来,同时感知性的互动中个体在共生网络中紧密相连。
(二)分析视角:假象领域的建构和个体感知的反馈
斯蒂格勒所说的“新的假象领域”,正是在飞速发展的新技术座架下产生的社会景观的呈现载体。根据斯蒂格勒的理论,当前时代新的社会景观正在逐步形成,这种景观表层是由象征符号搭建的具有复杂时间客体的假象领域,深层结构则是由技术逻辑主导的经济文化衍变。沿着象征信息流动的传播链条,可以发现媒介技术作为景观动态发展的核心,一方面占据着叙事主动性,把持着复合型记忆持存建构起具有统一意志的假象领域,另一方面“将不在场的个体即时转换为在场的状态”②[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5页。,使得个体意识畅通无阻地接入媒介技术的叙事逻辑。
在这个假象领域中,媒介技术通过网络的形式架构起社会的存在情境,肩负着塑造社会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重任。斯蒂格勒所说的具有实效性的拓展空间是假象领域媒介空间的重要基础,沿着这一拓展路径可以还原出世界自我投射的取向选择和媒介空间的变化过程。同时在多形态媒介构成的假象领域中,媒介技术全面介入时间观念,将过去的线性时间打碎,转变为碎片化的、原子式的、分散的、光点式的点状时间,又使得“物性机械流和时间客体的时间流相互叠合”③张一兵:《好莱坞文化殖民的隐性逻辑——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构境论解读》,《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沿着复合型的记忆持存对时间的重组和拼接的路径,可以窥得其背后的深层技术逻辑和发展趋向。社会记忆正是在媒介空间和媒介时间的双重维度中流动,顺着媒介网络将历史记忆植入社会场景从而驱动个体行动。对社会集体记忆的流动进行解构,能够在工业发展中的新旧技术更迭和过渡中找到精神复兴的源头和动力,鼓舞青年重建城市文化。
在假象领域“空间—时间—记忆”的架构下,个体的跨感觉通道(intermodal perception)①Charles Spence,“Crossmodal correspondences:A tutorial review,”Atten,Percep Psychophys,Volume 73,Issue 4,2011,PP.971-995.被最大限度地打通,象征性表达“原始地介入他者的感觉性问题中”②[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页。,使得个体意识的复杂时间客体性凸显,更容易接入“大写的我们”这一集体记忆。斯蒂格勒认为个体之所以对假象领域产生认同,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在于人类的意识本身的结构具有“由运动构成的时间进行蒙太奇剪辑”的特征,个体意识“会不断把位于这些客体之前的物体形象投射到这些客体之上”。从个体感知反馈反观假象领域,能够对比得出技术记忆的前摄和后摄的变化特点,也能够更加直观地比较出社会关系的位移和文化发展方向。
(三)理论适配性:东北工业文创社会景观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
从斯蒂格勒的象征理论看东北工业文创,其所呈现出的超工业化景观具有典型性与特殊性。斯蒂格勒从人与技术的关系出发,对超工业化景观进行了深层次的考察和剖析,在其理论中超工业化景观集中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新技术发展驱动复合型记忆持存构建新的假象领域;第二,个体化过程服从于集体性的同感和友爱,集体记忆接入个体意识;第三,强大的技术基础进一步放大了技术逻辑,技术成为社会座架,孕育出新的文化形态。受历史原因和现实需求的影响,我国东北工业文创在物质基础、动力、文化三个层面均充分展现出了双重工业技术逻辑和历史性的优势,较为完整地呈现出超工业化景观的全貌。在物质层面,东北工业文创依托于工业遗产原址进行重建,调用大量的工业品和艺术复制品等实物客体配合多形态的媒介进行展演,为假象领域提供了丰富的象征符号资源和记忆工程技术基础,假象领域的时间和空间得以更好的延展;在动力层面,东北经济发展和城市复兴的迫切需求使得个体以更加积极的心态主动地连接集体记忆,迅速催生出统一的“工业精神”认同;在文化层面,东北曾经辉煌的历史记忆和振奋人心的工业精神为新的城市文化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使得象征符号的意义历史真实在场,个体更容易信服和归属于集体记忆。
同时,斯蒂格勒也就这样的社会景观进行了批判与反思:首先,他认为服从于技术逻辑的超工业化景观,孕育着新的社会控制形式,被制造出来的共时记忆会使个体意识陷入焦虑与迷失,原始自恋毁灭的尽头将会是个体化的丧失。其次,技术逻辑下的社会景观也暗含着新的脆弱性。因为被制造出来的同感和友爱过于依赖媒介技术网络,不稳定的技术波动很容易激起新的信任危机。最后,他认为在由技术逻辑构建的假象领域中,象征表达被工业生产逻辑裹挟,服务于消费主义,大量象征符号的在场更是暗示着意义的缺场,象征的贫困和文化的虚无将成为新的文化困境。根据斯蒂格勒的批判和反思,对东北工业文创发展历程与消费主义下的象征表达进行对比,能够发现其物质文化基础和动力机制与消费主义下的象征表达均有所不同,所以其所孕育的超工业化景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三、假象领域的建构:时空交错中的共有记忆重建
(一)空间的交叠重构
在假象领域中,多种的工业实物客体结合媒体影像技术,以“视错觉”的表现方式被个体感知,将个体拉入东北工业的“场域”中,从而完成媒介空间的交叠重构。作为东北工业文创代表之一的中国工业博物馆(即原沈阳铸造博物馆)就是依托于沈阳铸造厂旧址进行了改造和扩建,成为历史重演的物理空间。这里的建造者巧妙地将建筑原貌、工业机器、工业产物及其复制品、创意设计品在媒介空间的光影中聚集起来,围绕着统一的“工业精神”的核心,将实物客体改造成为工业记忆的承载体,从而开辟了工业历史的艺术空间。在这些被保留和修复的车间梁柱构架下,工业文物和复制品、创意设计被陈列放置,生产场景被通过各种方式局部还原,工业文创利用“视错觉”最大限度地完成从视觉空间到想象空间的延展。根据被保留下来的不完全的历史记忆和集体想象,工业文创空间内部又被切割成不同的主题展览,同一主题展览中持存装置聚合为统一的意义指向,使得“错觉”中的历史记忆映射到具象的物品上来,让抽象的工业精神变得真实可感,纵向拓展了主题的历史空间和艺术空间。而这些相对独立的媒介空间又由充满着工业生产影像资料的长廊连接起来,保证了媒介叙事从文创场景展演的工业生产到历史记忆的工业生产的连续性。在纵深感极强的情境壁画和实时影像的背景中,感知空间在光影交叠中不断延展,被延展的空间又相互交叠完成了整个空间的联结。连续性的保证使得真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内在距离缩短,个体所能感知到的历史感和年代感都具化为目之所及的钢铁楼梯、钢铁栏杆、墙面和齿轮配件等特色工业元素,这使得个体感知变得更加的直接、敏锐,个体身在其中犹如“身临其境”。“图像优于存在,所见先于真实”①李简瑷:《后现代电影: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奇观》,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页。,观望即为“眺望”,这种空间奇观便在感知的“视错觉”式的整合中形成了。
(二)时间的拼接整合
东北工业文创的数字化媒介形式对应着相对独立的时间客体,其通过非线性的跳转和编辑连接起假象领域内不同的时间客体结构,打乱了原本的时间构序,自由地对历史时间和现实时间、个体时间和集体时间进行“剪辑”,从而完成媒介时间的拼接整合。德波在阐释景观的循环时间时写道:“社会只知道永久性的现存……它不是把时间视作什么东西的流失,而是把时间视为什么东西的返回。”②[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页。斯蒂格勒则是更加激进地提出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我称为工业时间客体的时代”③[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8页。。在这样的模式下,“流动的时间意识被否定”,超工业化景观组织起符合其需要的循环景观时间,控制记忆持存技术制造出多层次的时间客体,从而在个体意识中植入总体意识,将个体共时化。在东北工业文创的超工业化景观中,每一个工业文物和展示品都脱离了其工业价值甚至是物理意义,成为一种历史记忆的能指,它们配合着影像和媒体的交互技术,被制造为一种工业时间客体,并借助媒介技术的特性在人的感官上延伸,实现工业时间客体和个体意识时间两者的流动同步,达成“与意识一样流动顺畅”①[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5页。。同时,在城市和技术急速发展的时代语境中,出于对流通的急切需要,能指的具象形式被统一地标准化处理。数字化媒介所制造的象征符号使得假象领域和领域中文化传播的路径更加灵活、丰富。大量的工业文物及其仿制品作为原生持存的实体性重现则扩充了时间客体带给个体的感知觉,使得个体的意识时间顺着假象领域时间客体的流动而流动。数字化的灵活性和被扩充的感知觉共同塑造了景观中的“时间积木”②[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0页。,并通过对一块块“时间积木”的拼接和重组,为假象领域制造感知上的真实性和沉浸感,连接历史记忆和个体意识,激发个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记忆的集体重建
东北工业文创充分调动历史记忆,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联结个体感知,使个体深度沉浸在“全息”的场景中,接收时间和空间的记忆传达,将个人经历、城市历史、祖辈记忆重组,从而完成共时记忆的集体重建。媒介技术展现出的空间和时间特性,使个体能全方位感知记忆信息,迅速打通个体跨感觉通道,想象体验感知的有效性或真实性被最大限度放大,进而个体记忆中的“集体无意识”被激发。卡尔·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深深地隐藏在社会个体的无意识深处,包含了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所积累的先验产物,并过滤沉淀至基因中。尽管个体记忆存在差异,但存在于基因与意识深处的“集体无意识”会使得个体记忆在总体上具有一般内在相似性。东北工业文创的景观中,厂房、设备、产品这些以凝固形式被保藏的过去的文化,是被凝视、辨别的物体,也是能够引起沉思和回忆的记忆对象。它们唤醒了人们意识中对城市的历史或是个人相似经历的感知,这种感知围绕着“工业文化”积聚成一种“集体记忆”,不断放大个体间的同感,并结合多形态记忆持存制造的共时感,最大限度地在两者基础之上建立起友爱。③[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0页。而这种友爱影响着人们对东北社会关系变革的重新认知,影响着人们关于东北城市归属感、认同感的重新定义。
同时,“集体记忆”和同感之下的友爱经由意识的内化后反过来推动着东北工业文创超工业化景观中“集体计划”的达成。正如德波在《景观社会》中写道:“借助于‘集体计划’寻求重建由零碎物和废弃物等元素构成的复杂的新艺术环境,已在都市生活的整合艺术废料或美学技术形式的混合物的企图表达被看到”④[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9页。——东北工业文创将工业遗产零碎物和废弃物等元素在新的博物馆或创意的美学技术形式下混合,形成一种新的表达,这种表达是一种反思式的表达,一种开放式的过渡和衔接,一种建立在深深沉浸于对东北工业精神的认同感之上的向往和期待。而在这样的向往和期待中,“东北工业文化复兴”的话语设置应运而生,与“东北振兴”的城市发展目标一起,向青年人发出召唤。
四、个体感知的反馈:集体感召下的不同感知呈现
(一)历史的记录载体
东北工业文创园多依托于工业旧址进行改造,在光影重叠的媒介空间中,历史记忆与现实空间交错重合,将东北工业生产场景“还原”。个体置身其中时,感官被全方位调动,旧时的历史记忆和生活经历被最大限度地激发,极具标志性的实物客体带着个体找回真实的生活化回忆,在此基础上从自身生活出发回溯到更为宏大的历史图景。多媒介同屏叙事的工业文创成为个体调取历史记忆的记录载体。例如中国工业博物馆布景以等比例还原了沈阳铁西区生产厂房的全貌,真实直观地展现出工业区的生产生活场景。对于曾经在工业城市中生活、工作的个体而言,置身于这样的文创空间中,能够吸引其迅速回忆起曾经铁西区的生活记忆和社会图景。行走在铁轨改造成的小路上,恍然间仿佛回到了东北工业的繁荣时期,历史记忆在工业文创不间断的“全息”投放中逐渐清晰。

图1 中国工业博物馆内部场景展示①沈阳工业博物馆官方公众号:《铸造馆》,2017年12月14日,ht t ps://mp.wei x i n.qq.com/s/ab96j8oyifYlfoZOk2CKAA,访问日期:2021年8月15日。
东北工业文创充分调动多形态的记忆持存装置。从实物客体形态的小人书到满是影像记录的长廊,再到媒体交互的艺术创作……所见所及都成为工业文化传播的象征符号,同时也成为东北工业记忆的承载体,不断激活和固化个体意识中旧有的东北记忆和东北印象,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重新构序。频繁来到工业文创园参观的个体无意识地反复接收了假象领域的象征信息,激活和固化了脑海中旧时的沈阳记忆和沈阳印象,同样的记忆持存同时承载了个体经历与城市历史。个人的记忆与经历似乎在这里与整座城市的历史和命运相交融,一本“小人书”便可以串联出铁西区整体的历史面貌,而从一处工业文创园便可以映射出沈阳历史文化的全貌。同时,东北城市中的个体面对集体记忆时展现出了极强的主动性,这可以从个体对东北辉煌历史的追忆和对东北城市的眷恋中得到体现。
(二)地方的精神标志
“长期以来,巴洛克艺术在艺术创作的世界丢失的统一性,在某种意义上在今天对过去艺术总体的批发消费中被重新发现……意味着其艺术世界的终结。”①[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8页。东北工业文化在当下批量加工的文创产品中被重新发现,并在假象领域中达成统一。这种统一一方面呼应了斯蒂格勒所说的持存的“先将来时”——其记录了东北工业文化辉煌历史的逝去;另一方面也使得东北工业的辉煌历史对当下东北工业发展产生正向的互文性影响,东北工业文化的历史记忆被重新发现,艺术创作被终结,都意味着新的历史文化正在孕育。在经历了文化区分之后,被设想的地方主义意识出现,并尝试“锻造物理空间上的真实领土形态”②[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8页。。共时和同感催生出集体计划,将城市零碎物和废弃物等元素在新的博物馆/创意图景的美学技术形式下进一步混合,形成一种新的表达,从而铸造“社会的完整个性”,肯定地方精神标志的价值,推动真正的城市复兴。

图2 中国工业博物馆展出的文字影像资料③沈阳工业博物馆官方公众号:《通史馆》,2017年12月14日,ht t ps://mp.wei x i n.qq.com/s/esoSlxNCE9S5r2PxfWYTaQ,访问日期:2021年8月15日。
在东北城市复兴的需求驱动下,个体本身带着强烈的自主意识进入假象领域,也带着同样强烈的城市文化自豪感寻找、接入假象领域所呈现出的集体记忆,并企图将东北辉煌的工业历史和工业精神在新的时代背景中唤醒。东北工业文创在这样的合力下成为东北地区的精神标志,文创所转化的象征符号在这种畅通的互动中孕育着同感和友爱,并在同感和友爱之上建立文化认同,在新时代的文化景观呼唤城市复兴。对东北工业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驱动着个体沿着老工业基地遗址的路线对东北工业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游览和考察,借力于技术记忆的“先将来时”的性质,个体在东北工业的辉煌历史中寻找东北城市发展的资源库,在对时间的回溯中望见了通向未来的辉煌道路,新的梦想和旧的文化在统一的城市精神下被整合,新的媒介技术和旧的工业精神结合起来集中呈现出地方精神的价值与活力。同时,受访者对东北工业文创所创造的假象领域中的历史呈现表达出赞许和认同,积极参与城市集体计划,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积极地传播地方历史精神——向访者推荐其他工业文创园区、对东北工业历史进行文化研究,主动融入多层次的时间客体,表达和传播东北工业文化精神。
(三)城市的新兴文化
当下的东北工业文创形式较为多样,例如某种文化形态的周边类商品或是文化场景空间的实景式还原……这些不同的文创形式都是东北工业文化衍生出的新兴文化,其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影响城市的精神气质,为城市人群开辟出新的文化生长空间。对东北工业文创产业园进行实地考察,能够直观地发现其作为工业遗产的社会功能正在经历转换。文创园成为个体娱乐休闲的“栖息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儿童、孩子等成为文创文化的体验者,新一代的人们在这新旧交叠的空间中经历着回顾与展望。

图3 南岭1932—长春水文化生态园①水石设计官网:《长春水文化生态园》,2019年,https://www.shuishi.com/en/works/1155.html?region=1,访问日期:2021年8月20日。
在工业遗产的社会功能转化的同时,旧有的象征符号重组为新的文化形式,其构建的空间成为个体休闲栖息地——这对于年长者来说,是将旧有的工业文化记忆打造为了新型的休闲空间;相反,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在他们司空见惯的休闲空间中填充进了他们并不熟悉的“新内容”。新旧交叠的组合吸引个体聚集,不同个体在这片空间产生不同的文化体验,城市的新兴文化在新旧生活观念的碰撞中滋长。南岭1932—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原址为伪满时期建造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承载着长春市80年间供水文化记忆。生态园在老建筑群落和生态绿地的基础上,将净水厂原有的“水管”“水阀”等代表性元素与秋千、滑梯等儿童游乐设施组合起来,满足了市民休闲娱乐的文化需求;并通过孩子对工业元素组合的好奇和追问,将关于长春净水厂的历史记忆注入孩子的城市印象中,从而实现了新旧元素沟通互动。这些组合产生的文化意义赋予了场景特定的美学趣味,又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生活的乐趣。生态园在完成物理空间上的“集聚”的同时,也促使个体在关于“净水厂”的工业象征符号沟通中形成新的社交关系,进而完成文化生活的聚集,城市的新兴生活方式和新兴文化在记忆持存装置搭建的“休闲空间”中被构建起来。另外,新型的记忆装置和历史呈现形式使得个体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解读象征符号,激励个体拥抱新科技、新生活与新文化。
五、结语
工业时代,城市发展围绕着工业生产形成了独特的工业景观;如今,东北工业文创作为工业时代遗留产物活化后的城市图景,集中展现了技术与美学、整体与个体的共生关系,其呈现出的超工业化景观也逐渐趋于成熟:随着媒介技术的愈发成熟,不同形态的媒介形式之间的特异性被消解,媒介时空的整合更加连续完整;同时,城市对于工业文创的正向反馈也鼓舞了个体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接纳共时的集体记忆,“大写的我们”在假象领域不断壮大。在此基础上,个体间的友善被不断放大、关系更加紧密,“集体记忆”和同感之下的友爱又经由意识内化后反过来推动着东北工业文创超工业化景观中“集体计划”的达成,激发个体不断自发尝试将工业元素以创意或美学的形式进行重新整合,开辟新的城市成长空间,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表达。
在逐渐成熟的超工业化景观中,东北人特别是东北青年人也在工业文创塑造的集体记忆中不断地寻找自我。近年来东北经济发展的不景气以及媒体所塑造的东北地域刻板印象使得东北人开始对城市发展道路产生迷茫,特别是东北青年群体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并且企图“逃离”东北。而东北工业文创所展现出来的工业精神和文化历史为青年人提供了诸多个体范例,青年人的自我怀疑能够逐渐在集体文化历史所提供的个体范例中得到了安放,并在共时和同感的友爱的感召下融入“大写的我们”。他们逐渐坚信东北工业的辉煌历史对当下东北发展产生的互文性影响,坚信东北将会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并以强烈的文化自信心和工业奋斗精神对抗现有的社会焦虑和危机,主动承担起城市复兴的重任。
然而,这种新的社会记忆的形成、传播和再造过程的技术逻辑体现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路径值得深究——原因在于假象领域在“塑造自己整个环境的社会”①[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3页。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发展出了定形自己真实领土的特殊技术”,也就是说每种意识形态最后都锻造形成了物理空间上的真实领土形态。麦克卢汉和鲍德里亚预言中的仿真社会正在逐步成型,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之间的界线逐渐消解,人们需要时刻警惕软性的、无形的社会控制,积极应对斯蒂格勒所指出的超工业化时代所出现的困境。比如要对象征符号的流通过程进行把控,警惕“象征的贫困”困境。要认识到,东北工业文创在呈现上越是聚焦于当代社会需求和消费者喜好,越是依赖对其他城市传播模式的僵化学习,就越是容易忽略自己文化本身的存在和特点,失去自身独特的突破出口,最终在文创大潮中 “泯然众人”。正如《景观社会》中,居伊·德波写道:“他越是凝视,他看到的越少;他越是接受承认自己处于需求的主导图像中,越是不能理解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欲望。”再如个体要时刻保持主动性,在真实的历史记忆和工业精神上营造友爱和同感,与消费主义驱动下的个体化丧失区别开来。最重要的是,要持续对人与技术关系进行深层思考,不断创新东北工业文创的媒介技术呈现,推动建设新型的社会文化景观,平衡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在新的技术时代构建新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