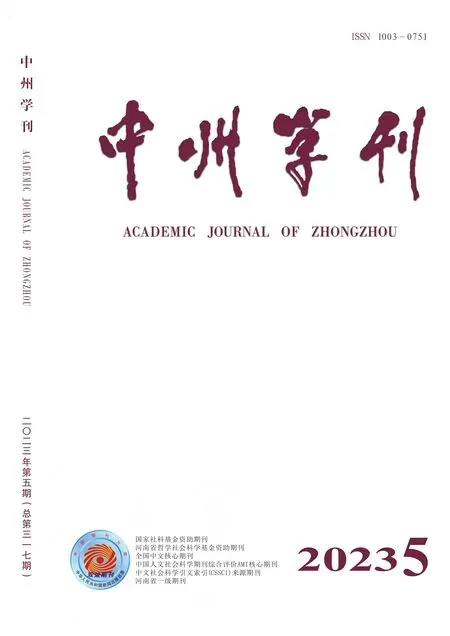道、理与普遍性超越
沈顺福
超越不仅是宗教领域中的重要现象,也是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最近若干年,中国学术界热烈地讨论着中国传统思想是否存在超越等问题。比如,牟宗三主张中国有内在超越:“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义。天道贯注于人身之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这时天道又是内在的(Immanent)……天道一方面是超越的(Transcendent),另一方面又是内在的。”[1]中国传统观念中不仅有超越观念,而且还是内在超越。中国思想有内在超越的观点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也有一些学者如郝大伟、安乐哲等,反对此说。他们认为:“严格说来,超越与内在的对立本身产生于我们安格鲁—欧陆的传统。”[2]从而不承认中国传统中含有超越观念。中国传统思想中是否有超越观念?如果有,它属于什么性质的形态,达到了怎样的水平?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蕴含着普遍之道与超越之理的观念,这些概念与观念从普遍性存在的角度将人从自然的私意的存在者转变为道德的存在,从而实现了人的新生与超越,这种道德超越乃是一种普遍性超越;中国传统儒家的普遍性超越并不彻底或完整,它依然有所不足。
一、日常生活:自然性与任意性
按照传统儒家的观点,人的生存以心为本,即人的自然生命开始于人心,心动便是活着,且人的行为也开始于人心,行动既是心动。这种作为生存本原的心,在先秦儒家那里至少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正当行为之本原的“本心”[3]205,另一类是作为邪恶举止之本的“利心”[4]64。前者以孟子为代表,后者以荀子为代表。孟子认为人天生有四种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3]59人天生固有四心,分别是仁、义、礼、智等儒家人道之起点。“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3]59“四端”是本原,生存是扩充本有的“四端”之心,其结果是成就仁、义、礼、智,这便是孟子的性本论。性本论以四心为性,为生存之本。
荀子肯定了人心的主导作用。荀子曰:“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4]206人心是天君,是一切活动的主宰者。这便是人心做主。在此基础上,荀子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人类自然生存的另一个向度,即趋恶的可能性。荀子曰:“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4]291人天生有各种欲望,包括私意的“利心”。在私意之心的驱使下,人的自然生存不仅各自为政,而且可能相互冲突,以至于将人类带入灾难中:“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4]289人天生有“好利”之心、喜好(“疾恶”)之情和“耳目之欲”。这三者共同构成人性。由于这些天生材质具有带来灾难即向恶的倾向,因此都不好。或者说,人的天生之性是“邪污之气”[4]252或“不肖”[4]12之材。如果任由这些不好的材质肆意发展,必将带来灾难甚至灭亡。因此,自然的私意之心及其活动并不可靠。
自然而私意之心及其活动的不足在宋明理学时期得到了充分揭示。程颐、程颢认为自然的“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个翻车,流转动摇,无须臾停,所感万端。又如悬镜空中,无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5]52-53。自然的、私意的人心如同空洞之物,因为它内中虚空而不实,因此并不可靠或稳定。这便是“人心则危而易陷”[5]2009,即人心危险。朱熹进一步解释曰:“人心者,气质之心也,可为善,可为不善。”[5]2013气质的、私意的人心有可能是善良的,也可能是邪恶的。既然有邪恶的可能,那就表明人心有危险。危险的人心很容易将人带向邪恶:“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谓之危者,危险,欲堕未堕之间,若无道心以御之,则一向入于邪恶,又不止于危也。”[6]2010因此,容易堕落的人心需要被拯救。尽管王阳明认为人天生禀赋良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7]6但在自然状态下,普通人的心灵常常被浊气所充斥,从而遮蔽了自身的良知。自然而私意的人心及其活动并不可靠,它需要被拯救,拯救的工具便是普遍之道与超越之理,拯救的方法便是理学所说的功夫(工夫)。
这种需要被处理的人心,在荀子那里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即它能够选择。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其物也杂博,其情之至也不贰。”[4]265人心具有能动性,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这种能够选择的人心,在现代哲学中,人们通常称之为意志。这种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的最重要功能便是确定行为的目标。理性人的行为总是在追求什么,即“在所有的行为与理性选择中,目的便是善,因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人们才会做某事”[8]。理性人的活动通常有目的。目的的确定便是人类理性的主要工作之一。这种确定目的的任务便是意志。“另一种人类专属并由此而区别于野兽的官能便是意志。借助于这种内在动力的意志,人类放弃那些最不适合于自己的、转而选择那些最喜欢的东西。”[9]理性人通过自己的意志来确定自己的对象并进而发动自己的行为。意志是人类自主性行为的驱动者,或曰第一推动力:“意志则是通过规则范畴来决定自己的因果关系的动力。”[10]32从自然界的因果关系法则来说,意志是理性人行为的原因,也是动力源。
作为动力源的意志可以分为两种或两个阶段,即自然的任意意志(willkür)和超越的自由意志(Will)。在自然阶段,意志和人的欲望几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康德认为:“所有的感性的实践法则将意志决定原理置于低级的欲望上。如果没有纯粹形式的意志法则来决定意志,我们便无法产生较为高级的欲望。”[10]22如果没有纯粹形式的意志法则来规范,这种自然的意志和欲望没有什么区别。此阶段的意志感性常常受到感情的影响:“选择的意志,臣服于慈善情感(虽然并非被其所决定,因而也是自由的),暗示了一种出自于主体的希望。这种希望常常与纯粹客观决定性原理相悖。”[10]32自然意志常常受到人的自然情感的影响,从而做出一些不符合道德法则的举动。这时的意志和欲望相近,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私意的。这种私意的意志及其活动常常是不可靠的。“在人的高级理智机构中,选择性意志被正确地设想为一种不能制定一种同时也是客观的行为准则的能力。”[10]32自然意志并不能制定可靠的行为准则,它“站在形式的超验原理和质料的经验的动机之间,如同站在两条道路之间,它必须被某个东西所决定。当一个行为出自于义务时,质料原理被从中抽出,它必须被意愿的形式化原理所决定”[11]。这种两可的自然意志,需要被决定。或者说,康德并不相信人的自然意志。康德说:“这种趋向于邪恶的事情,只有在其偏离了道德律才会出现于主观基础中。由于这种趋向普遍存在于人类,我们可以说这便是人类自然的、向恶的本性。进一步来说,产生于自然的意志的能或不能、采用或不采用道德律而成为其准则,便叫作好心或坏心。”[12]人天生的意志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于是,如何改造我们的意志,端正人心,使之成为道德行为的基础,便成为一项重要任务。自然的、私意的意志需要被约束、被规范。规范私意的心灵的工具便是道德规则。
二、社会秩序与道德规则
人不仅是个体生物,而且是社会性存在,即“人能群”[4]104。人是一种群体性存在,或者说,人伦社会是一个整体性存在。整体性存在的核心是秩序(order),即只有秩序才能确保整体的正常运作或存在,因此,秩序成为整体的最重要内容。即便是在动物界,“秩序也是必须的:它可以有效地避免为了寻求食物而产生的争斗和纠纷”[13]148。秩序是整体存在的基础,尤其是对于独立个体人所形成的社会,如果没有秩序,便是一盘散沙,必将一事无成。人类只能生存于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14]。卢梭说:“社会秩序,作为神圣权利,是一切其他权利的基础。”[15]387只有秩序社会才能确保利益与权利。
保证秩序的工具便是规范即rule。Order和rule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作为动词的命令、统治,另一个便是作为名词的秩序、规范。我们只能通过命令、规范等形式才能确保秩序。这些规则的正式形式是法律或制度。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法律也包括道德律。道德律是确保人类社会秩序与稳定的基本形式。社会秩序的产生依赖于“惯例”[15]387。这种“惯例”也包含道德。道德的原义(希腊语的ethos、拉丁语的moral)便指”风俗习惯”[16]。风俗习惯通常指某种文化传统中的、固定的、秩序的行为集合。它们并非自然的活动,而是某种有规则的行为。这种规则产生的基础便是作为契约的法律或制度。例如,现实中的政体便借助于“那些常设的法律,将其公布于众,而不是某些临时的命令。它只能仰仗通过那些刚正不阿的法官在法律的规定下裁决争议,甚至可以平息外交纠纷以确保团体免受侵凌。这些做法的目的便是为了人们的和平、安全和公共利益”[17]156-157。法律确保社会秩序。“不是管理者,而是法律才是国家的根本。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其成员才能保留自然自由的权利。”[15]358法律制度是政体如国家最重要的运作形式。
运用最广泛的规则还是道德规则。费希特以“普遍的伦理性”[18]233来描述道德,即道德法则是普遍的法则。这种普遍法则的目的便是协调:“我们必须去寻求与别人的判断相协调。由于各方都不缺少良心,因此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因此所有人都希望也不得不希望一个目标,说服别人而不让自己被别人的意见所说服。最终,他们必须达成一致结果,因为理性是单一的。到那时,一个绝对禁令的结果便成为双方保持别人的外在自由的义务。由此来看,所有人能够且被允许去意愿决定别人的信条。”[18]233道德法则是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接受的共同的准则。或者说,只有道德法则才能够协调整体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秩序中,道德法则是普遍的规范,人人皆应该接受和遵循。“‘说服别人’的目的并不是一个人独有的,而是公共目的。每一个人都被设想有这个目的,因此,将这个目的当作所有人的目的便是所有人的目的,正如人们意愿普遍的道德教化一样。首先,这可以用来团结所有人。”[18]235道德法则能够团结所有人并形成一个整体。在费希特看来,普遍法则所主导的人类行为可以有效避免突出个体私意的意志的个人主义倾向。简单地说,普遍法则可以规范、约束私意的意志。
规则的最重要功能是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成为义务的行为。从词源学来看,义务概念,“古代斯多亚学派用的希腊语是καθηκον,拉丁语则是officium。这个拉丁语的英语形式是office。这两个词,意思是一样的”[9]27。也就是说,义务和office(办公室、职位等)相关。义务概念便可以解读为:身处某个特定的职位所必须完成的行为。普芬道夫说:“它(义务)是人的特定行为。这种行为通常遵循某种行为人必须遵循的规范性法则。”[9]27义务是一种必然行为。当我们建立一个制度、形成一个群体来确保自己的权利时,我们便将自己交给了这个契约关联的整体,承担了相应的义务。这种规定便是法则或规则。“习俗和法律的加入是必要的,以便将权利对应于义务、正义归还给该得的人。”[15]399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们的权利和利益。有一定的义务便享有一定的权利。洛克说:“平等状态下,所有的权力和司法是相对应的,即没有人比别人享有更多的权利。很显然,那些天生的同等和同类的存在者,享有一样的官能,相互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没有谁臣服于谁。除非他们的头通过自己的宣言来表明自己的心愿,让他们同意通过一种显而易见的、清晰的任命形式,享有一个主管的权利。”[17]101保护人们的财产不受侵犯不仅是一个人的权利,而且也是国家等政体的义务。义务不仅是一种行为,而且是一种合乎规则的行为。“那些确定不可见的边界的规定便是法律。这种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人们以及每一个体获得了稳定而自由的空间。”[13]148法律便是那个确定的界限。德语法律(Gesetz)词根是setzen,便是设置,法律指那些“被设置”的东西。法律是人为的、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这种合乎规则的行为的运作结果便是秩序的社会出现,即当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的行为完全遵循一定的规则时,这个社会便是有秩序的、稳定的、整体性的存在体。在这个存在体中,所有成员的行为皆符合规则。规则确保了秩序的、稳定的整体的存在。对于家庭来说,对家规的遵循可以确保家庭和美;对于国家来说,对国家法律的遵循可以确保国家政治稳定;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对道德规则的遵循可以确保天下太平。这便是传统儒家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皆依据于作为规则的道和作为法则的理,即只有普遍之道与超越之理一起发挥作用才能够保障修齐治平,普遍的道或德的目的便是确保秩序的整体存在。
三、作为公共规则的道
整体性秩序依赖于规则,包括道德规则。这种普遍性规则或行为原理,中国传统儒家常常称之为道。《说文解字》曰:“道,所行道也。”[19]道指道路,所谓道路主要指人们的行走之径,通过它,人们可以到达某个目的地。因此,人们后来将某种能够使人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方法、途径等叫作道。道的原始观念本身便蕴含着价值评价,即道的正当性。道不仅是道路、方法,而且是正确的方法,是某种正确的行为原理。荀子曰:“道也者,治之经理也。”[4]281道是治理天下的纲领性、普遍性原则。道是正确的行为原理,作为规则的道是人们合理行为的原理,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或者说,道不是某个特定的原理、规范或方法,而是某类行为的公共原理,如“仲尼之道”[3]94便是所有的成就圣贤的行为原理。道是“公道”[4]157,公道是某类行为的共同原理。朱熹曰:“此意思才无私意间隔,便自见得人与己一,物与己一,公道自流行。”[6]111物与自己相统一便是公道流行,公道便是普遍之道。或者说,儒家的仁义之道是普遍之道。普遍之道是公共规则,具有公共性。正是这个公共之道能够将私意的个体的活动整合为一个有秩序的、有机的整体。
对普遍之道的接受与遵循发生于人的心灵,儒家称之为心术。荀子曰:“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则合于道人而不合于不道之人矣。”[4]263心术即让自然而私意的人心接受公共的仁义之道,并最终依赖于仁义之道来主宰它的活动。荀子曰:“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4]281道、心、说、辞构成四层结构,其中心象道、心合道,最终道决定心。以心合道、心从于道,最终可以成形而神化:“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4]28以公共的仁义之道来改造人们私意的心灵。
公共的仁义之道对私意的心灵改造过程,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看,便是外在的道德规则被行为者的心灵所接受,并转换为某个道德行为的准则的过程。康德首次区别了道德规则(或者说法则)和道德准则。其中,“道德律,由于它对于所有的理性与意志存在者而言普遍有效,因此,它只能是客观的、必然的”[10]36。康德所理解的道德律其实是道德规则,它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客观的。当某个客观的道德规则被人心接受时,这一客观的道德规则便转化为主观的道德准则。康德说:“准则是意志的主观基础。其客观基础便是实践法则。假如理性具备完全的力量来掌控欲望的话,这个客观基础,作为实践基础或原理,便可以主观地服务于所有的理性者。”[11]400道德规则是客观的,道德准则是主观的。当客观的道德规则被人心所接受后,客观规则便转换为主观的准则。
客观规则向主观准则的转化,既可以叫作接受,也可以叫作约束。康德说:“假如意志自身不能够遵循理性——这也是人类常有的事情——,那么,那些被视为客观必然的行为便具有了主观任意性。这种客观法则对意志的决定行为便是约束。”[11]412-413自然的意志常常是私意的。我们必须借用某些客观规则来规范我们的私意意志,这种能够规范我们的私意意志的规则表现为准则。准则来源于客观规则,或者说,它是规则的主观形态。通过主观的准则,道德规则实现了对人的意志的管理,即意志接受规则的约束与规定:“完全善良的意志一定臣服于客观法则。”[11]414客观规则一旦进入了人们的主观便转化为某种行为的准则。“准则是一个行动的主观原理,且必须与客观原理即客观法则区别开来。前者包含了理性根据主体的条件(通常出于无知或自身的偏好)而设定的实践规则,这样它便成为一个原理。主体依据这个原理而行为。但是,法则也是客观原理,对所有理性存在者都有效。法则是应该如此行为的命令的基础。”[11]420-421我们将客观规则转化为主观规则后,这一准则便成为某种行为的“主意”[7]4并引导着我们的行为。对于人的主观意志来说,这种内含客观规则的主导之意便是“(来自理性的)命令”[11]413。这种命令体现了意志与客观规则(法则)之间的关系。在主观意志中,准则是最重要的内容。以客观法则为内容的规则最终通过准则决定了意志的活动,这便是主观性必然。康德说:“有必要说明一下,这种道德必然性是主观的,即它是一种要求,而不是客观的义务。义务不会去假设某个东西的存在。”[10]125这种必然性最终对我们的心灵产生了约束,从而形成正确的主意或意志。
在这种正确的心灵或意志的主导下,我们不仅可以做出正确的行为,而且最终形成了道德世界。道德的世界以普遍规则为基础。荀子曰:“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4]104-105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整体性社会,原因在于“分”和“义”。“义”决定了“分”、形成了“群”。其中的“义”便可以理解为道德规则。作为道德规则的“义”能够将一个个的人分门别类,最后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便形成了人类社会。人伦社会的形成基础便是公共的规则,通过这些规则即道,人类超越了自身的私意,转变为符合公共秩序的道德人。对于人的生存来说,这种转折无疑具有革命性意义。
四、普遍之理对存在的超越
作为规则的道并非一种空洞的观念,而是一种有内容的观念。它的内容,在理学家那里,便是作为法则的理。二程曰:“观其所恒,谓观日月之久照、四时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观此,则天地万物之情理可见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识之?”[5]862圣人之道之所以永恒,在于其背后的天理。公共之道依赖于普遍而绝对之理,如果说道是一种普遍的规则,那么,理便是其客观依据。朱熹曰:“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20]理是道的所以然。道理关系是经验的规则与超越的法则之间的关系。道即科学命题,理便是该命题所指称的客观法则。故朱熹曰:“看来‘道’字,只是晓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乱兴亡事变,圣贤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晓得所以然,谓之道。”[6]2218道意味着知晓,即作为概念的道表达了某种认识如命题。该命题是对客观的、实在的法则的描述。这种客观而实在之法则便是所以然之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理便是那只“看不见的手”[21],掌管着人们的经济活动。这种“看不见的手”便是经济活动的法则,或曰经济活动之理。正是这种普遍而绝对的法则即理,为作为规则的道的合法性提供了存在论的证明:道是符合客观法则(理)的规则。
超越之理的出场彻底改变了人类生存的性质,即人类从自然人转向道理人。这种转向,用现代哲学的话说便是超越。汉语的超越观念来源于西方的Transcendence。其形容词有两种,即transcendent(超越的)和transcendental(超越性的)。康德说:“我将把那些……超越于这些限度的原理叫做超越(transcendent)原理……我们所提出的纯粹理智原理,即必须是经验的,而不能够被当作超越性使用,即它们不适用于经验领域之外的事物。能够消除这些限度、让我们合法地逾越它们的原理便是超越原理。”[22]235-236超越于我们的经验和感性世界的存在,包括其存在方式等,都是超越的(transcendent)。这种超越性质类似于理学家所说的“形而上”。当这些超越实体参与人类的经验之后,我们的经验瞬间便发生了转变,即从自然性存在转变为超越性(transcendental)存在。康德定义说:“我将那些讨论那些超验知识模式所能够讨论的对象之外对象的讨论知识叫做超越性的(transcendental)。这类概念体系便被叫做超越性哲学。”[22]43用经验知识或模式来处理经验之外的存在的方式便是超越性的方式。比如,“在超越性审美判断中,我们已经证明:我在时间和空间中所直观到的全部事物,即我们的可能的经验对象,不是别的,正是现象,即仅仅是一种表象。这些表象,虽然以广延性和变化性而呈现于我们,却不是能够离开我们思想的自身。我把这一原理叫做超越性观念论。超越性实在论却相反,它认为我们的感官所提供的存在依赖于它们自身,即这些表象产生于事物自身”[22]338-339。康德所建构的超越性观念论既不是贝克莱式的唯心主义(idealism),也不是传统的实在论(realism),而是二者的综合。康德的超越观念包含两项内容,即超越的和超越性的。存在因为超越的实体(如物自体)的加入而转变为超越性存在。
这种改变存在性质的超越实体,在理学那里便是理。理学家认为,理是“形而上”[6]3或超越的实体,而自然的人心则是“形而下者”[6]3,类似于经验存在。当形而上之理进入了形而下之心中时,自然的人心瞬间发生了性质转变,成为合“理”的道心。朱熹曰:“道心是义理上发出来底,人心是人身上发出来底。”[6]2011道心是气质人心与超越之理的结合,理学家把这种转变机制叫作功夫。功夫的内容便是自然人心与超越之理的结合,即“心与理一”[6]85。比如,诚意的功夫便是通过纯洁人的自然气质、让性澄明或物理在场。
理的在场彻底改变了人类生存的性质。朱熹曰:“‘诚意是人鬼关!’诚得来是人,诚不得是鬼。”[6]298功夫的结果是让自然人成为道理人。在功夫之前,人仅仅是生物,与鬼无异。当超越之理与气质之心相遇时,人便从鬼变成了符合人类本性的道理人。自然的行为便发生了性质转变,即从自然存在转变为含“理”的存在。事物有理:“理则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6]82顺从道心而产生的行为,即事与物,便是合理的存在。比如忠孝,父子有父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6]83。父子君臣之间有确定的行为原理,比如忠与孝。理便是让忠孝等行为原理获得合法性的东西。有了这个理,此行为便是合理的,反之便是不合理的,理是行为规则的终极性依据。作为终极性依据的理的出场,彻底改变了生存的性质,即它让生存具备了合“理”性。
超越之理为普遍之道的合法性提供辩护,得到了超越之理的辩护,普遍之道便可能会被人心所接受,并转化为行为人的“主意”。在这个“主意”主导之下,人们模糊了自己的私意,反而将自己视为某个群体的一员,从而将自身行为归纳进那个群体的整体中并成为该整体之一。“只有通过可能的交替理智的关系,我才能将我的经验世界与别人的经验世界统一起来,同时通过这些意识流来充实我的经验世界。”[23]个体自身因为这个反思获得的整体性意识而成为全体的一分子,从而完成了由私意人与自然人向社会人与道德人的转变。其中的理又叫德。朱熹曰:“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24]性、理在人便为德,故“道”“理”的意思与“道”“德”的内涵基本一致,道理即道德。天理参与的超越将私意而自然的个体生存转变为遵守公共秩序的道德人。从自然人走向道德人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超越。
余论:普遍性超越及其风险
人不仅是理性的个体存在者,而且是社会存在者。理性存在者的活动不仅是个体的、独立的、私意的行为,同时也必须符合社会存在、团体存在。为了确保整体社会的秩序,我们必须拥有一套有利于秩序的规则,包括道德法则和法律。这种规则,中国传统哲学称之为道。道即公共规则。这种公共规则之道并非空洞的概念,而是有所指,其所指便是客观而超越的法则,理学家称之为理。正是这种超越之理与公共之道一起确保了秩序的整体的存在。在公共道理的共同作用下,自然的个体人转变为道德人,这种革命性转变便是生存的超越。主导超越的力量便是普遍性的道与理,这种超越因此是一种普遍性超越。这便是中国传统儒家的超越类型,即普遍性超越。
普遍性超越由超越之理与公共之道共同完成,其中,超越之理超越于我们的经验。一旦我们用经验来面对或处理它时,超越之理便会转换为经验性存在即道。在儒家那里,道常常是可以知晓的,比如,“朝闻道,夕死可矣”[25]40中的道,“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20]14中的“道”,便是可以闻知之的、经验性的观念。在经验视域,超越之理转换为经验之道,成为某种抽象的观念或规则(广义的规则包含科学命题与社会规范等)。道是理的经验形态,这种客观之法向主观之则的转换隐藏在人类的经验思维之中,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我们并不知晓这个过程。在不知二者区别的基础上,人们常常将超越的法则即理与经验的规则即道,混为一谈,以为经验之道(如科学命题)便是超越之理(自然法则)。由此,主导普遍性超越的法则之理悄悄地转换为经验的规则之道,即人们常常以普遍之道来取代超越之理。这种转换或取代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它会将客观必然性悄悄地转换为某种主观必然性,客观而中立之理转变为某人所认可的规则即道,如儒家的仁义之道等。客观的法则转变为主观的必然规定,在转换过程中,法则即理失去了自身的客观性或中立性,转而成为某人所认可的规则即道。这便是普遍性超越所面临的风险,传统儒家的命运便是这个风险的最好诠释。统治者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威与话语权威,将由理转换而来的道进行垄断的解释,如将忠道直接解释为对某个君主的忠诚,以为忠诚于君王便是忠,否则便是不忠等。偏爱公共存在的儒家思想由此沦落为少数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压迫民众的帮凶。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儒家“伪善”[26],无疑是注意到了传统儒家所面临的这一风险。
那么,如何弥补这一风险呢?这便需要自主性出场。道德的普遍性超越不仅需要普遍的道与理,而且离不开自主的主体对道与理的选择。也只有自主性的个体性在场,普遍性超越才能最终完成,即真正的超越乃是一个由个体自主发动的个体性行为,在这个个体性行为中,某种蕴含着普遍而超越之理的道被选中而成为该行为的法则。在法则之下,该行为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道德,即法则的遵循确保该行为能够融入社会。与此同时,这个行为产生于自主的个体,是个体的自由的行为。这样,这种由个体自主发动的行为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道德的。个体与社会、自由与道德获得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