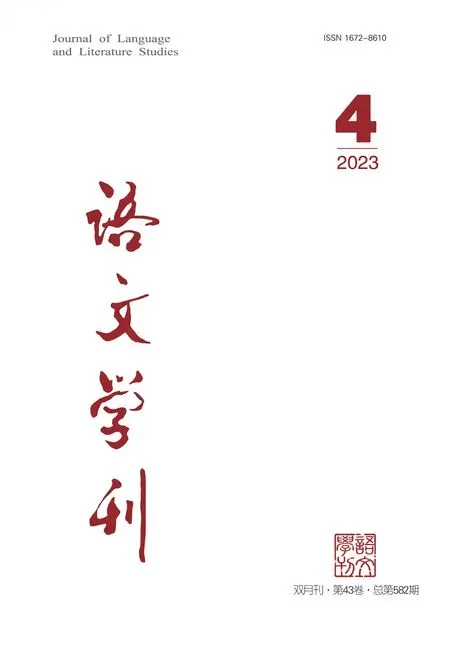从“文体通变观”论《知音》之诠释法则与效用
陈秀美
(宏国德霖科技大学园艺系暨通识教育中心,台湾 新北)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从“文体通变观”论《知音》之诠释法则与效用着手。此乃笔者在研究《文心雕龙》这部“文体理论”专书之“文体通变观”视角下,提出刘勰这部书从文体构成要素、源流规律、创作与批评法则,以及文学史观等,都隐含着“文体通变”的核心观念。这一文学观念,是在“结构性动态历程”中建构一套具未来性、有机性与理想性的文学理论体系。然截至目前,多数人解读《知音》“六观”时,还是不自觉地以“静态化”“知识化”的诠释模式,因而容易忽略刘勰“知音观”的辩证性,以及“六观”的通变性“文体批评”诠释法则与效用,此乃本文的研究动机。然进入本文论题前,有几个基本预设,须先做说明。
第一,所谓“通变性”,简言之即为“辩证性”而言,在刘勰“文体通变观”里,其对“通变”一词的运用,约可呈现出三类的议题:一是,他面对古代文学传统时,对于各种类体在变动历程中,所呈现之客观“通变”现象的描述,例如其“规范性”体制及体式的“变”,及其“殊变性”体貌的“通”;这是刘勰对过去文学传统的体察。二是,他用“通变”一词,针对各别类体进行“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诠释。因此“通变”一词隐含刘勰对各种类体之变与通的轨迹:例如何者变?何者通?或何以会变?何以会通?或者是变与通之间,如何形成其辩证性关系?……这些属于诠释文体变动性轨迹的问题。三是,他借由“通变”一词来规范文学作家当有“通变性”法则,亦即是诠释如何“通其变”,如何“变其通”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道。准此,“通变”一词,实际上是隐含“辩证性”思维,是本文的基本预设之一。
第二,所谓“文体通变观”,是以后设研究进入,探讨刘勰诠释“文体”之历史现象的“通变性”等相关问题,所提出的文体主张与立场。故其端极落在“通变”,研究对象也就是“通变”。最终要解决的是“文体通变”的法则与文学历史的轨迹,以及创作与批评的相关问题。故“文体通变观”论证的对象是“通变”,而限定范畴则落在“文体”上,借以探讨刘勰是如何运用“通变”观念来诠释其所认知的“文体”起源、演变的历史现象,以及相应的创作、批评的通变性法则[1]。
准此,刘勰面对文学历史的基本思维,是立基在“过去、现代、未来”的文学历程上,以其“文体通变”的辩证思维,反思“文学传统”的文体承变现象与“近代辞人”的文体流弊问题,作为提出“未来”理想文体的典范依据。所以他的“文体通变观”实际上是一套以“主客辩证融合”为视角的“通变性”文学观,其中除了涵盖刘勰对过去与现在文学进行“实际批评”之外,最重要的是提出《知音》“六观”,所建构的客观性“文体批评”。所以《知音》篇包含鉴赏论的“实际批评”,以及理论性的“文体批评”两部分,也是本文基本预设之一。
第三,所谓“文体批评”是指以文体(体制、体貌、体式、体要)的知识作为“批评”理论依据。所以在“批评”的过程中,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基本上已预设了“文体”知识,是作为诠释或评价“作品”的基准。在传统主观的“印象式批评”模式中,确实存在“主观”“攻击”与“武断”的结论式评价特色。然这种主观体悟的“批评”模式,是无法从中得到完美解决之道的;在文学发展脉络中,直至六朝刘勰提出“六观”说,才出现客观的文体批评方法,此一方面须透过文体通变的诠释视角,方能明确体现刘勰这套系统化、体系化的文学批评法则。
从立场与观点来看,论“文体创作”时,是以“作者”的立场、观点,论作者“文心”与“文体规范”之间的“通变性”关系;而论“文体批评”时,则是以“批评者”“读者”的立场观点,来看刘勰“通变性”批评之目的、方法,或任务与效用等。其实这些观点,都是要站在“研究者”的诠释视野,必须进行议题上的区分。若就《文心雕龙》这本经典而言,刘勰既是“批评者”(读者),也是“作者”,其立场与观点是兼具“研究者”与“创作者”的角色,于是在刘勰的“文体批评”中自然呈现出“相互性”关系。故在解读《文心雕龙》的“文本”时,一方面要注意做好这两者有不同的诠释立场与观点的区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两者的相互性关系。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学活动中,“读者”也是“作者”之主观意识的身份转换,这也是本文的基本预设之一。
此外,刘勰《知音》的前行研究里,学者有主张“情志批评”,也有认为是“文体批评”。如蔡英俊《“知音”探源——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理念之一》云:“‘知音’所指涉的理解活动,是两个主体之间相互了解、相互感通的融浃状态,而且这种相互感知的过程,似乎不需要透过任何外在的言辩予以明示;创作者与鉴赏者双方都沉静地进行内在情志的沟通、理解活动。”[2]130就如其所言,“知音”是两个主体间“相互感知的过程”,“似乎”不需要透过外在的言辩给予阐明,就能使“创作者”与“鉴赏者”(读者)两个主体进行内在“情志”的沟通与理解。然而蔡氏的论述焦点显然是从《知音》篇前半部阐述“鉴赏论”活动的模式立论,也就是“创作者”与“鉴赏者”双方的主体“情志”互动与创发,探“知音”之源,论“知音其难哉”的文学鉴赏问题,并非是在刘勰《知音》“六观”探讨与建构上,所以“知音”问题就容易成为一种主观性的“情志批评”框架。
在前行研究中,提出刘勰《知音》“六观”是“文体批评”的代表论著,应是颜崑阳的《文心雕龙“知音”观念析论》,颜氏认为“知音”的论述立场与观点,都是从“文体批评”进入,因此他先探究“知音”一词的原典出处,进行“知音”概念与观念的界定,再就“知音”观念蕴含的文学“批评”观念谈刘勰“六观”的客观批评法,强调“六观”非“情志批评”,而是“文体批评”的理论体系①。因此就文学总体观之,“六观”是文学批评中的“文体批评”范畴。
故全文将以颜崑阳《文心雕龙“知音”观念析论》为基础,开展全文的论述,并不从现代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上找依据,而是直接从《文心雕龙》的文本分析进入,重新建构刘勰“六观”之“文体批评”的通变性效用。
二、“博观”之养与“六观”之术的通变性关系
本文的基本假定是“主体情性”与“文体规范”之间,是一种相互辩证的依存关系。因此预设批评者之“博观”与文体批评之“六观”间,有着“通变性”关系存在,唯有如此才能阐明刘勰《知音》所言之“六观”,实为客观“文体批评”之法则;由此方能掌握刘勰从反思文学传统的批评法后,顺着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体批评”观念,点出六朝从主观情性之“实际批评”进入的文体批评现象,否则容易流于主观,造成批评上的偏见问题。诚如颜崑阳所言:
六朝文学批评的主要趋向乃是文体论的批评,以文体知识作为批评的理论依据,……当时这种文体论的实际批评虽颇为兴盛,却很少有人从批评者的立场,提出一套客观性、系统性、有效性的批评方法,因此批评的结果往往由于主观成见与认知不足而造成严重的偏差。在这趋势中,刘勰以“知音”指称文学批评活动,而提出“六观”这套客观性、系统性、有效性的批评方法与判断标准。……刘勰提出这套“六观”批评方法与判断标准,其最大的价值意义,是让文体论的批评有客观的规范可循,而由作者与作品立场所建构的文体知识,不但可以落实在“创作”的指道上,同时也可以落实在“批评”的指道上,而形成一套作者、作品、读者“系统整合”的文体论[2]238-239。
我们从颜氏的研究成果看来,他提供以下几个论述的知识基础:一是,六朝文学批评的主要趋向:是借由文体论的批评来评估“文学作品”的优劣。二是,因为在文体的实际批评中,很少人以“批评者”的立场建构出一套客观、系统、有效的文学批评法则。因此其结果往往流于主观成见,或认知不足之憾。三是,刘勰提出的“六观”批评方法与判断标准,其实是一套“主客辩证融合”的批评法则,既提供作者“创作”上的指道,也能让“批评”落实为作者、作品与读者的“系统整合”。然而颜氏对位六观之位置与其如何运作的批评法则,并未深入说明与建构,因此给予本文一个反思与研究的空间。
此外,刘勰在《知音》中反省当代文学所面对的困境时,云: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3]888。
故就文学发展的轨迹而言,魏晋六朝文学在类体的形构与样态的表现上,是一个“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的时代,然而文章之体虽多,但在语言修辞的表达上,或质朴,或文饰,或内容(质),或形式(文)互有交替,加上每个人的写作各有偏好,所以“批评者”不能“圆该”,就不能有全面性的观察,所以“慷慨者”听到“逆声击节”就赞赏,“酝借者”见到细致含蓄就高兴得手舞足蹈,“浮慧者”一见绮丽就动心,“爱奇者”追求诡奇惊耸,刘勰所描述的这些人都是以个人“主观”好恶出发,因此自然造成“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等“以管窥天”之弊。
因此从刘勰论述的语境看来,这些既是“创作”问题,也是“批评”问题,且容易造成以偏概全之“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遗憾,这正是六朝时期的文学问题;而刘勰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在作者,或读者必须具备“博观”之养与“圆该”之心,才能体察外在的“万端之变”。故从刘勰的观点看来,想要实现这样的理想性,必须从“文体通变”的观点上找方法,才能使创作与批评避免“各执一隅”之憾。张少康“知音论”中明白点出:
刘勰认为要展开正确的文学批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一则文学作品本身门类众多,品种复杂,……要正确地鉴别其优劣,实在不容易的。二则批评者的状况也各不相同,爱憎好恶悬殊极大,……历史上的文学批评存在着主观、片面、浅薄等许多不良倾向[4]246。
由上可知,刘勰面对的“文评”环境,确实是一个“主观、片面、浅薄”之文学批评的时代。此外,所有文学作品发展到六朝时期,开始从原本的文学创作实践的时代,转入建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新时代,原因是先秦以来文学历史的累积,促使众多作品可以分析、归纳、反省、建构。正因如此才会出现“篇章杂沓,质文交加”后,会有主观、片面、浅薄的批评乱象;再加上“古来知音,多贱今而思古”。因此导致人人自叹“知音其难哉”。就如刘勰所言当时“文人相轻”“贵古贱今者”“信伪迷真”,导致“文学批评”的缺失。这样的缺失,要用“六观”的客观批评法则,方能补救其弊。但什么样的人,能够善用“六观”批评法呢?刘勰在《知音》告诉我们“圆照之象,务先博观”: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4]888。
可见,刘勰一方面从主体“通变”之文心的“博观”进入,来反省时人之弊时,提出其“圆该”的理想性,就在“操千曲”“观千剑”之“博观”的养成,才能使批评者具备“博观”的学养条件,作为文体批评之依据。这是在进入实际作品批评时,才能呈现出批评者“操之”与“观之”之方法运用,再借由“六观”批评法则,来解决主观批评可能带来各说各话的困境。因此在进行“六观”批评法之前,必须先将批评者“博观”与“六观”做一些定位,因为两者之间存在通变性法则。
三、“六观”之术与“通变观”之关系
承前所述,本文预设“文体通变观”是《文心雕龙》全书的核心观点,因此“通变”一词成为全书的关键性语词。一方面刘勰在创作论里,用《通变》篇来论文体创作的法则,另一方面他又在鉴赏论中提出《知音》篇“六观”里,强调“三观通变”的文体批评法。可见刘勰“通变”一词的多元性,但不变的是“通变”一词中所隐含的辩证特性。此外,刘勰提出批评者的“博观”之说,强调观览文学作品之“文情”,唯在“六观”。可见这中间隐含着“主客辩证融合”的通变性。
故本文在此论述重点,先厘析“六观”之义,再谈其与“通变观”的关系。然而在探讨刘勰“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问题时,不免让人心中产生一些疑问:一是,什么是“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宫商”?二是,刘勰的“观”是指“创作者”“批评者”,还是两者皆是?三是,这“一观、二观、三观、四观、五观、六观”彼此之间,是否具有一种形构上或逻辑上的关系?然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除了厘析“六观”之义外,就是“六观”作为客观文体批评之“术”时,这一套客观性、系统性、有效性的文体批评方法。然每一观在彼此之间,是否有依循什么法则、结构,作为客观批评与鉴赏作品的模式?
准此,本文预设这六个“观”之间,具有一种互为依存的通变性关系。就如颜崑阳在“位体”的诠释里所言:
魏晋六朝的“文体”观念绝不只是脱离“内容”而纯为“形式”的意义。所谓“位体”当然也不只是脱离内容,而纯为语言形式的巧构[2]227。
这是颜氏从“辩证性”的文体观念,提出来的看法。此一看法在强调“六观”不可脱离主观与客观、本质与形构、内容与形式,且不可忽略其“互为依存”的通变性。因此以下本文将借由颜崑阳与张少康的观点,来厘析“六观”之义,再进一步探讨“通变观”与“六观”之文体批评的关系。
“一观位体”之义。前人说法纷纭,然简言之,其乃指探讨作者如何掌握“名理有常”“规略文统”“因情立体”“情理设位”。张少康认为“是指要考察文学作品的体裁风格和它包含的情理是否相契合”[3]249。从张氏的说法看来,这是需要从辩证的“通变性”思维下,才能进行作品之“体”是否运用恰当,如此才能确立“文体”的定位。所以“通变观”与“观位体”之关系:乃指在“文体通变观”下,才能使批评者掌握“名理有常”“规略文统”“因情立体”之道,进而观察到“文学作品的体裁风格和它包含的情理是否相契合”。
“二观置辞”之义。则是指观察章句安排,探讨作者怎样安章宅句,著意镕裁而言。张少康认为,“是指文辞运用是否能充分表达内容。……置辞是否妥当,是和内容密切联系的。而不是只看它是否华丽”[3]249-250。在此亦显张氏对“观置辞”须要兼顾内容与形式之密切联系,这也是具有“通变性”的辩证关系。所以“通变观”与“观置辞”之关系,是指在“文体通变观”下,方能使批评者掌握到作品中作者如何安章宅句、著意镕裁之“文辞运用是否能充分表达内容”,以合乎常体与文统的规范。
“三观通变”之义。则是探讨作者(作品)怎样“资于故实”“酌于新声”“宜宏大体”“洞晓情变”。张少康认为“是指要考察文学作品在处理继承和创新方面是否做到了在通的基础上有变,在认真继承前代文学优秀传统的前提下,有所创造,有所发展,作出新的贡献”[3]250。其所述“观通变”之辩证性,就更不用说了。所以“通变观”与“观通变”之关系:则是指在“文体通变观”下,才能使批评者观察到作者是如何实践“资于故实”“酌于新声”“洞晓情变”,以及作品在文学传统脉络中的“通变”发展现象。
“四观奇正”之义。是指观察作品执正驭奇的手法,掌握其奇正的变化规律。张少康认为“是指内容是否纯正、形式是否华美,以及两者的关系处理得是否正确。……考察文学作品是‘执正以驭奇’呢,还是‘逐奇而失正’”[3]250。在张氏的观点中,“观奇正”一样,也是从“通变性”的辩证依存关系来观。所以“通变观”与“观奇正”之关系:是指在“文体通变观”下,批评者才能分辨文学作品里的“奇正”变化规律,掌握“执正以驭奇”,逐奇而不失其正的通变性法则。
“五观事义”之义。是就观察作品中作者如何借由征引故实事类、引用成辞,使其情感、思想得以适切表达。张少康认为“观事类”,“是指要考察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客观内容与作家主观情志是否协调。亦即作品中思想内容的客观因素是否统一。……如果是运用典故,还有是否确切的问题。”[3]250-251由此可见,张氏所言“观事义”之“协调”“统一”“确切”等说法,都是具有“通变性”之依存关系。所以“通变观”与“观事义”之关系:是指在“文体通变观”下,批评者才能观察到作者是如何借由征引故实事类、引用成辞,使其情感、思想得以适切表达;故透过“观事义”评断文学作品中“客观内容与作家主观情志是否协调”。
“六观宫商”之义。是指分析作品中的声律,以及作者如何同声相应、异音相从而音节协调。张少康的说法“是指文学作品的声律美问题。声律美关键是能否做到有和、韵之美。同时声律也能体现作者的感情状态”[3]251。这里所言“有和、韵之美”与“声律体现作者感情”说,同样也具有“通变性”的辩证效用。“通变观”与“观宫商”之关系:是指在“文体通变观”下,才能使批评者体察到文学作品中,作者是如何让声律在“通变之术”的运作下,同声相应、异音相从,达成音节的协调。
我们可以发现“观”字,所指的是谁在“观”,就会产生不同的“通变性”效用。所以观察刘勰《知音》的论述语境时,发现刘勰“六观”之“观”,既可以站在“创作者”立场,来确保创作实践历程的书写法则,也可以站在“批评者”观点,来进行文本阅读后的文体批评。所以这个“观”可以指作者,也可以指批评者(读者)。但是无论是从作者、作品还是从读者的立场来看,“位体”是第一要务,批评时不能“因情立体”又如何能“即体成势”?这是一个“观”者必先“规略文统,宜宏大体”的关键。
从作者之创作,或读者之批评的角度观之,“位体”能确立而后才能进一步面对“置辞”的选择或表现状态;正因不同类体的性质与功能,也各自有别,所以在确定“位体”的前提下安置“辞采”,才能使“文采”与“情性”,能在客观规范与主观抒情间,获得最适切的表现,就如刘勰《丽辞》所言:“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3]661但是要能让“位体”“置辞”表现得宜的关键,则是在文体的“通变观”运用。此一“通变观”是面对古代文学传统时,对于各种“类体”之间,本就存在着“变动历程”的“通变”现象,以此观察其所批评之作品,能否既符合常体之规范,又具作者文体创变之效用。
综上所述,“通变观”与“六观”之文体批评法则的关系,都是在刘勰“文体通变观”下,批评者培养出“博观”之文心主体,才能作为恰当操作“六观”文体批评之“术”。这样的结构关系图,如下所示。

通变观与六观的关系图
由此可见,刘勰的“六观”是一套“主客辩证融合”的文体批评法。我们可以看到刘勰从“文体通变观”之“观”,来统摄文体之“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宫商”之“术”。而这“六观”在批评之术的实践中,呈现的是彼此间“相互依存”的通变性辩证关系,这就是刘勰为何说“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之故。然一般论刘勰“六观说”时,往往将其与“博观”之说,分别立论。如此一来,刘勰的“六观”容易被导向“个殊”的批评法,忽略刘勰的文体批评是从“实际批评”进入,借由主观文心之“博观”之观与客观文体之术的“六观”结合,形成其“主客辩证融合”的“通变性”效用。
四、论刘勰“文体批评”之通变性诠释法则
承前所述,刘勰在“六观”的文体批评视角下,面对文学传统,或对前代文学的批评,他是如何进行文体批评的“实际批判”操作,作为他评价判准与应用依据?刘勰在《议对》云:“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刘勰的“文体批评”是建立在其文体通变的“结构历程文学观”上,他不但要回应古代传统中“已存在”的文学问题,并且致力在挽救当代“正在发生”的文学危机;更要以古代作品之典范,来指引未来“将创生”的文学范型。因此刘勰的“观通变”,是指探讨作者(作品)怎样“资于故实”“酌于新声”“宜宏大体”“洞晓情变”,这样的文学批评主张是从考察文学作品之继承与创新,作为建构一套具有客观性、辩证性的文体批评的“通变性”法则。
然无论是从综观《文心雕龙》全书,或是从其《通变》“赞曰”所言“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3]570,都可以看到文体是以运转不停的变动性规律存在,因此每一天都有可能发展出创新的变化成果。这样的辩证性一方面强调“变”是文学持久、永续发展的原动力,另一方面也强调“通”是使其不匮乏的历史依据。从创作与批评者的立场观之,人在适应当代的需求,要趋附时势的同时,也要有果断明确的自我判断能力,才能观察到文坛氛围的转变,掌握眼前时机而不怯懦。
因此刘勰提出“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之“观通变”的批评法则。首先来谈“望今制奇”的批评法则,这是刘勰从“社会向度”的观点,所做之文学环境的反思,认为“文学”在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氛围中,其本身的形构与规律存在着不断被变化与更新的现象;这是他在《通变》所言“日新其业”之义。因此观察当代对文学传统之继承与创新的发展趋势,是其面对当代文体“创变”之现象的另一种判准。
从批评者的诠释视角观之,他要随时具备历时性与并时性的辩证性思维。所以刘勰在《时序》中特别强调的“质文沿时,崇替在选”之道,指出批评者必须将文学放回到文学传统的脉络中,才能顺着每个时代的“变化”需求,体察其有时“质”、有时“文”之变动性发展的文学现象;并且从文学历史看到文学被推崇、被替代的关键,乃维系在人的主观选择之上,因此具有“通变文学观”的批评者,必须具有两个批评视野:一是,观察到客观文体存在着“质文沿时”的变动规律;二是,点出人为主观判断的“崇替在选”,如帝王的提倡,也是造成“日新其业”的原因。这些都是批评者“望今制奇”必须要培育出来的素养。
其次,来谈“参古定法”的批评法则,这是刘勰从“历史向度”的视域,观察到中国文学传统之中,“文学”本就具有一套形构与规律,这就是他在《通变》所言“文律运周”之说。基于这样的观点,批评者在“采故实于前代”(《议对》)时,会有以下两种省思。
一是,批评者本身要能具备“参古定法”的“通变”思维,并在心中有一个文学的图谱:文学是不间断运行的动态形构与规律的图谱。所以要培养出像圣人“鉴周日月,妙极机神”(《征圣》)的文学视角,才能通晓日月“周遍”之理,体察“机神”巧妙之变化。使其批评视角能见文章之规矩,而且所思所得都能符合文学“常体”之规范。因此批评者必须要能“通晓常体”,这是刘勰在《通变》中特别强调“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的道理。因此唯有能从“故实”的典范中通晓“常体”,才能使其批评判准的视野“思合符契”。
二是,刘勰所主张之“参古定法”,乃强调文学要从古代传统中找寻可供后学模习的理想典范。这个典范就是如前文的论述,不仅指“五经”之文,还指各类体中的典范之作,即《明诗》以下的“选文以定篇”。故刘勰的“还宗经诰”之说,是要强调批评者具备“因本道流”的批评视野。这是他从根源性立论:一方面借由“文体源流规律”的论述,提出“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之文,乃是“论说辞序”“诏策章奏”“赋颂歌赞”“铭诔箴祝”“纪传盟檄”等类体之“首、源、本、端、根”。另一方面从“文体构成要素”的论述,提出经典文章所具备之“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等特色,亦是后代从事文学创作或批评的典范标准。由此可见,批评者要能具备这些批评素养,才能借由“参古”来订定创作,或批评的法则,这样的思维模式即具备了“通变性”的思维。然而,刘勰提出这些批评判准的目的,乃在对应当时文体解散与矫讹翻浅的文学乱象。就如其《通变》所云:
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茜;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3]569。
刘勰以“练青濯绛,必归蓝茜”为例,强调提炼青色一定要用蓝草,提炼赤色一定要用茜草,这里指出回归根本之道的意思,目的就是用来说明:若想矫正当时“文体解散”与“文质失衡”所带来的伪体、讹体之弊,或想改变当时浮浅的文风,就必须从“还宗经诰”做起,这是一个创作者或批评者能在“质文之间”做出最完善的斟酌,在“雅俗之际”做出最妥当的安排。刘勰认为这样的人就可以跟他谈论“通变”之道。因为他具备批评者“通变”的视野,能从文学传统的“相循”与“因革”中,因其“果断”与“无怯”的批评态度,使其批评能在“参古定法”之中,既能掌握文化传统之历史向度的“趋时”法则,又能顺应当代社会之社会向度的原则。
准此,刘勰所谓“望今制奇”:所要“望”的是观察当前文学作品的发展趋势,才能有“制奇”的策略。换言之,它一方面可作为创作法则之一,另一方面亦可作为批评者的批评判准。“参古定法”是从参酌“古代典范之作”作为标准,这一方面可作为创作者创变的典范依据,另一方面亦可作为批评者评判的标准。所以在“文体通变”的批评观点下,批评者在体察文体“日新其业”的事实时,其内心在“观通变于当今”(《议对》)时,必然要做好两方面的心理准备与期待:一是,要从“适应当代”之文学需求,体察创作者“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通变》)的创变性,作为文体“恒存”的原动力;结合文学传统中“质文代变”之“因革”规律,做好“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圣》)之文体批评的判准。二是,要有“创变未来”的文学期待,从体察作者个人性情才气的“殊变”特性,掌握其“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的创作,预设“变则其久,通则不乏”(《通变》)之文体批评的未来理想。
五、刘勰“六观”之文体批评的实践效用
形成于魏晋六朝的“文体批评”与汉代所形成的“情志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两种主要型态[5]16。刘勰从“实际批评”进入,提出其“六观”的客观文体批评法则外,从其“六观”的通变性,可以看他实际应用在古代文学的类体考察上,因此刘勰除了在《序志》提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写作方法外,更借由这样的书写原则进行其对各种“类体”的实际评价。例如《明诗》至《书记》等篇章中,运用“体制”批评、“类体”批评、“时体”批评等面向,进行其“六观”的通变性批评效用。
第一,“体制”批评的通变性效用。“体制”是文体中最具象的文学形构,因此是文类之“显性”的形构要素,在文学发展中逐渐被型塑出的文体规范,也就是前文所论的“常体”观念。在各类文体的批评中,“体制”批评是针对某一文类是否合乎该类文章之“体制成规”的实际批评。例如《颂赞》所言:
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又崔瑗文学,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3]1161-162。
这段文本指出班固《车骑将军窦宪北征颂》与傅毅《西征颂》,由于书写时太过铺叙事实,因而没有遵守“颂体”的体制成规,而把“颂”写成了“序”“引”之类,刘勰评其因为“褒过而谬体”。此外,崔瑗的《南阳文学颂》与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都致力在序文的优美,反而使得“颂”的主文变得太过“简约”;这也是刘勰从“六观”的批评法则,做“体制”批评的通变性效用。
第二,“类体”批评的通变性效用。“类体”是指某一文类的理想体式,是刘勰《明诗》至《书记》中的批评主轴,基本上其“类体”批评,所关怀的是某一篇、某一家、某一代之作品是否实现其文类之体式,以及其彼此间是否有优劣高下的差别。如《哀吊》所云:
赋宪之谥,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事均夭枉,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暨汉武封禅,而霍嬗暴亡,帝伤而作诗,亦哀辞之类矣。降及后汉,汝阳主亡,崔瑗哀辞,始变前式。然履突鬼门,怪而不辞,驾龙乘云,仙而不哀[3]239。
以上这段文本是刘勰从“哀体”之文类的理想体式,提出其评“哀”之正体与讹体的论述。刘勰释名以章义地提出“短折曰哀”,“悲实依心,故曰哀”之类体定义,认为哀辞所写的是感伤少年夭折,就像苗不能开花,因此自古以来就是让人读来悲恸的文章。纵然是通达之人也会因为感情太过浓烈,而迷失写作的规范。所以哀辞纵然间隔千载,还是能把哀伤寄托在文辞中传达情思。
因此从他对诗人作《黄鸟》来表达对秦穆公时,“三良殉秦”之“夭枉”的悲哀,不就是诗人之“哀辞”的反思,以及他对汉武帝封禅时,因为霍去病之子的“暴亡”而感伤作诗,应属“哀辞之类”的看法;都是以“短折曰哀”的类体评判标准为依据,进而批评崔瑗因“汝阳主亡”所作的哀辞,开始改变此一“类体”的写作体式,出现“怪而不辞”“仙而不哀”等变而失其体式的浮夸、讹谬之体。这是刘勰从其“六观”的批评法则,针对“类体”在实际作品的变化与发展中,所进行之“类体”批评的通变性效用。
第三,在“家数”批评的通变性效用。“家数”是指一家之体貌。刘勰在“选文以定篇”或论作者之“才略”时,最常运用的就是借由“类体”的基准,进行“一家之体”的文体批评,借以评断其作品的优劣高下;就以刘勰《诠赋》所言之“辞赋之英杰”与“魏晋之赋首”为例,其云: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挺拔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彥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3]138。
刘勰评荀子“结隐语,事数自环”,宋玉“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司马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以此类推,贾谊、王褒、班固、张衡、扬雄、王延寿等十家都是“辞赋之英杰”。而王粲、徐幹、左思、潘安、陆机、成公绥、郭璞、袁宏都是“魏晋之赋首”。这是刘勰从“辞赋”之类体的基准,进行“家体”的评判,是刘勰从“六观”的批评法则,针对各家数的特色,所进行之“家体”批评的通变性效用。
第四,在“时体”批评的通变性效用。“时体”是指某一时代的文学体式,这是指同一时期之文学的共同特征。在刘勰“结构历程”的文学观里,评论某一时期之文学体式,是其建构“文体通变观”中重要的一环。因此就如其《时序》所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是刘勰针对各个历代之文体的“通变”因素与规律,所提出之“时体”的“文变”与“兴废”,他认为“文变染乎世情”是“时体”受社会向度的影响结果,而“兴废系乎时序”则是“时体”在历史向度下的因素。他就是以这样的“结构历程”文学观,作为时体批评的基准。就如他在《明诗》所云: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3]84-85。
从以上文本,可以看到晋代文学之“稍入轻绮”;东晋文学“溺乎玄风”;刘宋初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这些针对时代文学之特征,所提出的“时体”批评中,可以看到刘勰运用“六观”的批评法则,点出“时体”因变的发展现象,做出文体因革流弊的评断,这就是刘勰在“时体”批评的通变性效用。
六、结 论
综合前述,本文预设“文体通变观”是刘勰《文心雕龙》全书的核心观点,在此观点下,重新反思《知音》“六观”的通变性批评法则。这是刘勰所要对治六朝“文体解散”与“文质失衡”的问题,所提出的一套“通变性”的批评法则。本文认为从创作的“通变性”法则中,可以体察“文体规范”对“作者文心”的“制约性”规范,也可以一窥作者“文心”的通变性思维,对“文体规范”所产生的“创变性”,然而在古代“作者”即“读者”的情况下,主观的“作者文心”与客观“文体规范”之间,所形成的“主客辩证融合”的通变性关系,当然也成为读者文体批评的“通变性”法则。
此外,这“六观”的批评法则,是刘勰文体批评理论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截至目前,还没有人能真正善用刘勰这套“六观”批评法。所以本文先从批评者的“博观”与《知音》“六观”的通变性谈起,再论“六观”之义与“通变观”之关系;并在此基础之上,从“通变观”论刘勰文体批评的辩证法则。故在刘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批评准则下,可以看到文学从过去、现在、未来,像一条历史的洪流,因此论“六观”这样的文体批评,是不能脱离“世情”与“时序”的变化,六者不能分开来谈,因为这是一个“六位一体”的,而且批评者必须掌握其“通变性”的文体批评法则,才能善用“六观”,使其达成文体批评的效用。此乃本文借由刘勰《文心雕龙》文本,检视他实践“六观”之“文体批评”的通变性效用。
【注释】
①颜崑阳:《文心雕龙“知音”观念析论》:“六朝文学批评的主要趋向是:‘文体论的批评’。所谓‘文体论的批评’,即是以文体知识作为批评的主要理论依据,而其批评的终极标的也是在乎诠释或评价作品是否完满地实现某一文体的美学标准。因此,当时的文学家在批评方面最卓著的表现大约有两个层次:一是文体知识的建构;二是运用文体知识实际地对某一作品予以批评。这显然是批评理论与实际批评相关的运作。……文体论的批评,虽然也考虑到文学的主体性,但此种主体性的要求完全不同于两汉笺释诗骚之求解的作者情志。其间主要的差异有二:(一)两汉笺释所求解的作者情志,指涉的是在某一特定个别发生的事实经验中,作者心里的感受或意图,因此这‘情志’是发生性的,是特别性的,每一作品的‘情志’皆不相同。但是在文体的批评中,所谓主体情性,指涉的却是对某一主体性情概括性的、类型性的描述。……(二)情志批评,其终极标的是从作品以寻求作者的情志;而文体批评却是从作者的性情以理解作品的体貌。作者性情不是批评的终极标的,而只是作者理解作品的参考条件。因此,前者是读者→作品→作者(情志)的批评历程;而后者则是读者→作者(性情)→作品(文体)的批评历程。”(《六朝文学观念丛论》,台北:正中书局,1993:215-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