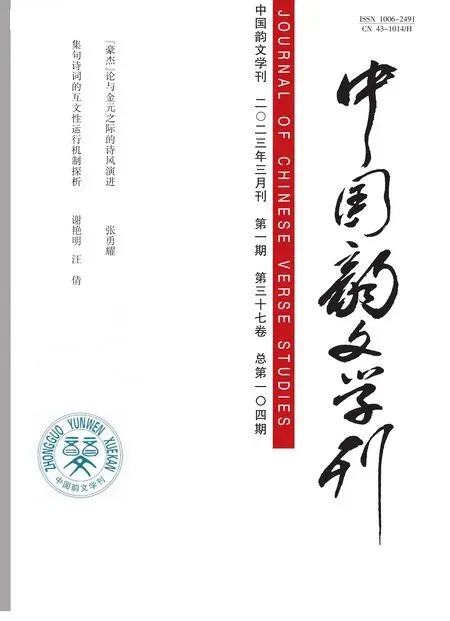“豪杰”论与金元之际的诗风演进
张勇耀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豪杰”是近年明清之际学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显性话题,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易堂诸子等一批具有豪杰精神的作家学者凸显于研究领域(1)相关论文如赵园《明清之际文人的豪杰向慕与理想人格追寻——以易堂诸子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赖玉芹《晚明清初豪杰人格的渐次形成》,《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2期;陈友乔《试论顾炎武的豪杰人格》,《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孟新东《黄宗羲的豪杰理想及其诗学安顿》,《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李伟波《颜元的豪杰人格及其经世转向》,《实学文化丛书——传统实学与现代新实学文化(四)》,中国言实出版社2018年版等。,令人瞩目。而在金元易代之际,“豪杰”同样是高频关键词。胡传志教授2000年发表于《文学评论》的论文《金代文学特征论》指出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金末豪杰作家大量涌现”,作者指出,“这些豪杰式作家使金末文学避免了亡国之音低迷的哀吟伤叹”,“避免了末代文学习见的狭小枯窘”,“即使悲哀,也是强者的悲哀,能在悲哀中见出郁勃的力量”,而这“对后代也产生一种特殊的影响”。[1]该文对金末文学这一重要特征的揭示可谓振聋发聩,但由于篇幅较短,一些有价值的话题都没有充分展开,因而尚有可继续探讨的空间。本文就以金元之际普遍的尚豪风气对诗学的影响为视角,对这一现象及其与元代诗学走向的关系加以考察。
一 豪杰诗人并起与金元之际的诗坛风貌
《金代文学特征论》一文列出了金末“慷慨任气的诗中豪侠”作家十余人,有酒后“啸歌裼袒,出礼法外”的李纯甫;“遇不平,则疾恶之气见于颜间,或嚼齿大骂不休”的雷渊;“善谈论,气质豪爽”的张珏;“性本豪俊,好酒任气”的阎长言;“为人不顾细谨,有幽并豪侠之风”的高永;以王若虚为代表的“林下四友”;“性野逸,不修威仪”,贵人延客时“麻衣草屦,足胫赤露,坦然于其间,剧谈豪饮,旁若无人”的辛愿;“旷达不羁,好以奇节自许”“高亢不肯一世”“有幽并豪侠歌谣慷慨之气”的李汾;和议未成而被宋人目为“中州豪士”的王渥;被郝经评为“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的元好问;等等。当然这一名单还可以补充,元好问《中州集》诗人小传、刘祁《归潜志》中写到了诸多有着豪杰言行的作家,如“好横策危坐,掉头吟讽,幅巾奋袖,谈辞如云”[2](P1956)的刘昂霄,被授官后“与人交一语不相入,则径去不返顾”[2](P1532)的麻九畴,“为人刚直,豪迈不群”的“挺特之士”[3](P11)宋九嘉,尚气使酒,喝醉后“虽王公大人嫚骂不恤”[3](P20)的李夷,还有让近臣畏惧的“挺然一时直士”[3](P36)陈规,等等。这些诗人全都性格鲜明、卓荦不凡。也正是由于元好问、刘祁等人对金元之际诗人群体豪杰特质的反复书写,“豪杰”这一高频关键词得以由点成面,构成了具有总括性的时代图景。
金元之际文人对金末豪杰士风也有着清醒的认知,如元好问说:“迄今论天下士,至之纯与雷御史希颜,则以中州豪杰数之。”[2](P1121)评价李纯甫、雷渊都是“中州豪杰”。李纯甫去世后他在《李屏山挽章二首》中说:“中州豪杰今谁望,拟唤巫阳起醉魂。”[4](P229)担心再不会有李纯甫一样的中州豪杰。李纯甫生前也以豪杰自期,曾有自赞云:“躯干短小而芥视九州,形容寝陋而蚁虱公侯,语言蹇吃而连环可解,笔札讹痴而挽回万牛。宁为时所弃,不为名所囚。是何人也耶?吾所学者净名庄周。”[3](P7)豪杰之气流溢于字里行间。文人之间的相互推扬与激励,共同形成了金末崇尚豪杰的社会风气。张珏去世后,元好问作《氵隱水》诗云:“裴回功名会,脱落豪侠窟。中州有士论,指与雷李屈。”[4](P225)“豪侠窟”即豪侠丛生的士人社会,“中州士论”正是社会思潮的代名词。元代中后期修成的《金史》也以“豪杰”论及金末文人,如在人物传赞中说:“韩玉、冯璧、李献甫、雷渊,皆金季豪杰之士也。”[5](P2574)所称道的四位人物,都是《中州集》收录有作品的诗人。他们在金末政坛多有建树:李献甫在对夏外交中援引故事,使“夏使语塞而和议定”[5](P2572);冯璧历仕章宗、卫绍王、宣宗、哀宗四朝,刚直不阿,多次弹劾权贵,尤以御史任上制服凶暴的牙吾塔为元代史臣称道[5](P2570);雷渊疾恶如仇,正气凛然,“弹劾不避权贵,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誉,奸豪不法者立棰杀之”,使权贵敛避,闾巷间多画其像以镇奸邪[5](P2573),刘祁也评价雷渊为“真豪士”[3](P11)。元好问、刘祁及元代史臣对金末豪杰作家的评定,使金末文坛呈现出一种总体上的豪杰气象。
金末最具豪杰气质的布衣诗人,无疑非李汾与王郁莫属。李汾屡试不第,因才被荐入史馆做抄写,但他与这里的氛围格格不入。元好问记载,正当史馆诸大佬难以下笔,他“正襟危坐,读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数百言,音吐洪畅,旁若无人。既毕,顾四坐,漫为一语云:看!”终遭同僚驱逐。此后他又有一个惊天举动,“寻入关,明年驱数马来京师,日以马价佐欢。道逢怨家,则画地大数而去”[2](P2488)。王郁和李汾颇有几分相似,不但给自己写了一篇《王子小传》突出自己“好议论,尚气,自以为儒中侠。所向敢为,不以毁誉易心,又自能继大事”的豪杰人格,还说自己经李献能扬誉后“名始满天下”[3](P23),认为自己“名满天下”,可见有足够的自信。刘祁记载了李汾与王郁具有极高相似度的一则典故,说李献能评价李汾“上颇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间全不晓人事”,有人认为这句话评价的是王郁,而李汾听说后,大笑着说“此政谓我也”[3](P100)。金亡后,元好问在《醉中送陈季渊》诗中说“李汾王郁俱灰尘,天意乃在溵阳陈”,将李汾和王郁作为豪杰诗人的代表,认为陕西人陈邃可以继之,“舌吐万里唾一世,眼高四海空无人”[4](P1490),这正是对李汾、王郁豪杰特质的反观与确认。
金末豪杰文人还有一个相似的人格特征是“耿耿自信”。如元好问《中州集》中对其师郝天挺及“三知己”中辛愿、李汾的书写:
(郝天挺)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宁落薄而死,终不傍贵人之门。[2](P2299)
(辛愿)落落自拔,耿耿自信,百穷而不悯,百辱而不沮,任重道远,若将死而后已者三十年。[2](P2461)
(李汾)虽辞旨危苦,而耿耿自信者故在,郁郁不平者不能掩。[2](P2489)
元好问之师郝天挺曾入中都太学,科举不第,卫绍王时期世乱后归乡,不再应考,以教授为业;辛愿贞祐元年(1213)受高廷玉案牵连,被讯掠后人以其名为讳,不敢与交,“不二三年,日事大狼狈”;李汾则屡试不第,由于个性,一份史官抄写的工作都难以维持,流离中又与家人失散。他们都是游离于金朝科举体制外的布衣文人,元好问以简要几笔,写出了三人遭际坎坷而“耿耿自信”的精神特质。清人李祖陶读到写郝天挺句云:“读此四语,予为之慨然。”读到写李汾句云:“读此令人起立。”[6]这些豪杰诗人的精神气度令人肃然起敬。
“豪杰”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刚”,然而至刚易折,金末豪杰诗人的大量死难,是金元之际文学史甚至中国整部文学史的巨大损失。但可以肯定的是,从金亡后到忽必烈即位前(1234—1260)的近三十年间,“豪杰”依然是诗坛主调。这一时期的豪杰诗人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在金末战争中艰难生存下来的作家,他们流寓各处,在战争造成文化破坏和文明断裂的时代,将金末豪杰以道自任、救亡拯溺的精神带到了元初;二是金亡时尚在童年,在前金士人培养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二代文士,他们继续着对金元之际士人豪杰特质的揭示,并很好地继承了他们前辈的精神气象,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生发出新的意义。
二代文士对金源前辈豪杰特质的评定,可见于元氏弟子王恽、郝经、魏初等人的作品中。王恽《员先生传》写到金元之际诗人员炎,“褐衣麻屦,酒近酣,巨梃权膝上,掉头吟讽,歌谣慷慨之气,轩轶四座。素不能骑,众人强之辄色变堕地”;杨奂任课南课税所长官时征聘他出仕,他“挂布囊,腋下杖巨梃”,直入杨奂“凫雁行立”的办公场所,说:“杨使君不相知,置我于此,几为老罴所噬。此汝酤镪持取,吾不能为汝再辱。”于是“揖而去”[7](P2313)。员炎豪放不羁的个性,颇与金末“为人不顾细谨,有幽并豪侠之风”的高永,贵人延客时“麻衣草屦,足胫赤露,坦然于其间,剧谈豪饮,旁若无人”的辛愿,“旷达不羁”“高亢不肯一世”的李汾,被赐及第进入翰林弃之如敝屣的麻九畴等人颇为类似。《员先生传》文末还为同为陕人的奇士撖举作附传,说撖举青年时期本为农夫,忽能作诗,“其豪侈之况,侪辈属和,终不能及”;曾与他相见于燕市酒楼,“浮大白数行,径出步炉间。嘤嘤然忽作露蚓声”,突然返身抓着他的胳膊说有诗相赠,赠诗中有“气凌太华五千仞,诗绕国风三百篇”之句[7](P2314),人物言行都透着豪放不羁之气。钟嗣成《录鬼簿》将撖举列入“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学者考证他当生于金元光元年(1222)至正大三年(1226)之间[8],则与王恽为同辈。
二代文士郝经同样与前辈豪杰文士多有交接。他在《房山先生墓铭》中写到金末名士刘百熙,金亡后依附真定史天泽,往来燕赵间,每于花朝月夕,他便“浩歌绵唱,音节豪宕,声满天地,观者倾侧,以为异人”[9](P913),正是金末豪杰文士之遗。郝经又有《义士》诗,写到一位豪杰文人晋古,生于燕赵豪士辈出之地,穿着道士服离家云游,与王若虚、白华、魏璠、元好问等名流都有交往;在民生艰难之际,他周急援难,“凡孤弱顿踬,莫能自致,往往赖之以济”[9](P55-56)。这位晋古以“布褐”而有天下志的形象,正是对金末李汾、王郁等人的精神接续。约在乃马真后四年(1245)前后,24岁左右的郝经前往燕京,结转识了诸多燕京名流,多年后他在写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市)的《秋思》组诗六首其五中云:“弱冠燕市游,许与皆豪英。百匝红锦围,酒海横长鲸。醉倚蓟丘竹,长啸秋风生。有时按策坐,谈天复谈兵。划破天心胸,四座一时倾。”[9](P95)在江南的羁旅愁思中,他怀想当年在燕京所结交许与的都是“豪英”,宴聚纵饮,醉歌长啸。有时围坐,谈天谈兵,不时有奇语妙策,引得四座狂呼。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聚居燕京的豪英正是金末北渡的豪杰文士。正是这样的场景与豪情的熏陶感染,增加了郝经胸中的浩荡之气,使他成为元初豪杰作家的最佳接棒人。
元好问弟子魏初有词《满江红·为张右丞寿》,可以看作是对金元之际豪杰文人张文谦的人格画像:
天造云雷,问谁是中原豪杰。人尽道,青钱万选,使君高节。自有胸中兵十万,不须更事张仪舌。看千秋金镜,一编书心如铁。 天下利,君能说。天下病,君能切。要十分做满,黑头勋业。乐府新诗三百首,篇篇落纸挥冰雪。更醉来鲸吸,卷秋波,杯中月。[10](P702)
张文谦(1216—1283)金亡时18岁,由同学刘秉忠推荐给忽必烈,受到忽必烈的重用,曾受命治理邢州,成绩斐然。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文谦为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诏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11](P2463),魏初词正作于这一时期。词作上阕称道张文谦为易代之际的中原豪杰,一身正气,不贪财货,熟知天下形势,无须如张仪一样费尽唇舌便能轻松为君王出谋划策。下阕则赞张文谦文韬武略,正与《元史》本传所记相符,并且道出张文谦人格之豪与诗风之豪的内外一致。这是金末豪杰诗学的传承,可惜张文谦诗词散佚。
在元人关于元初诗学风貌的评价体系中,正是这样一批由金入元的豪杰文士,为诗坛带来豪杰气象。元初虞集作于大德七年(1303)的《田氏先友翰墨序》中,列出了一批豪杰作家的名单,当时他的好友田衍将其父田文鼎收集的元初作家作品编辑后请虞集作序,虞集“读其辞而悲之,盖其愤郁哀壮称,余所谓豪杰者多在是”。他详列的“豪杰”名单有杨弘道、王磐、姚枢、徒单公履、高鸣、张豸、赵复、杨云鹏(一作杨鹏)、撖举(一作橄举、阚举)、刘百熙、平玄、郭可畀、杨果、薛玄、曹居一、杜仁杰、赵著、张朴、田文鼎、史垩二十人。[12](P565-566)这二十人中除平玄、郭可畀、张朴、田文鼎、史垩无作品传世外,其余都是金元之际颇可称道的诗人。当然这个名单是以当时保存的作品为依据的。其中赵复是金亡次年(1235)被俘北上的宋儒,二十人中唯一的非金源文人。虞集还直接评价了一些人的豪杰特质,如撖举“关东人,不羁,诗有律”,赵著“燕人,大侠”[12](P565)等。作为对元好问、刘祁、郝经、王恽、魏初等人豪杰诗人评定的补充和延伸,这个名单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正是金元之际豪杰文人大量涌现和崇尚豪杰的社会风气,对有元一代豪杰话语的方向性影响。
豪杰诗人并起是金末文坛的重要特征。从蒙金战争开始(1211)到金亡(1234)二十余年间,诗人们流离困顿而不失耿耿自信,呈现出相似而又各具特色的豪杰气象。金亡后,幸存诗人与他们的子弟后学将这种精神气象带到了元初,两代文士为挽救残破的时局、重建文明秩序奔走呼号,他们激越迈往的豪杰之气,不但影响到了金元之际文学的总体风貌,也为元代诗学的格局与走向奠定了基础。
二 豪杰气象与金元之际诗歌的尚豪特征
作家是时代的风向标,一批作家共有的特征和气质足可以形成一个时代的主流风貌。《四库全书总目》的《中州集》提要说金末文学“实在宋末江湖诸派之上”[13](P1706),正是对豪杰气象的肯定。元初文学也正是沿着这一风格继续前行,两代人的豪杰之气,形成了尚豪文学取向,对各体文学都产生了显见影响,其中对诗歌的影响尤为突出。
应该说,雄豪劲健是金诗的总体特色。陶玉禾《金诗选·例言 》即指出“金诗有本色,其华赡不及元人,然莽苍悲凉,不为妩媚,行墨间自露幽并豪杰之气”,“有廓清摧陷之功”,都突出了金诗总体的豪健风格。他又拈出金诗的代表性作者,说“金诗中气骨苍劲、体制最高者,推刘迎无党、李汾长源、辛愿敬之、麻革信之”[14],所举除刘迎是中期诗人外,其余都是南渡后诗人,也即他所说的“莽苍悲凉”与“幽并豪杰之气”,更多指向金末诗人。检文献可知,金元之际以豪健著称的诗人不在少数,如元好问评价冯璧“诗笔清峻,似其为人”[2](P1459),高永“诗豪宕谲怪,不为法度所窘”[2](P2310);刘祁评价张珏,“人以为不减李长吉”,李夷“作诗尤劲壮,多奇语”[3](P20);郝经说赵秉文诗“云烟恣挥洒,乾坤快歌咏”[9](P50),元好问诗“天才清赡,邃婉高古,沉郁太和,力出意外”[9](P908);清人陈凤梧《郝文公陵川文集序》评价郝经之诗“汪洋滂沛,如大河东注,一泻千里;抑扬起伏,如太行诸峰,层见叠出”[9](P1065);等等。但金元之际诗歌的“豪杰之气”还可以细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在金宣宗年间,宰相术虎高琪专政,打压士人,“专以威刑肃物,士大夫被捃摭者,笞辱与徒隶等”[2](P2198),而且“凡有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3](P73),士人气不得伸,形之于诗,所呈现出的特征可以名之为“压抑的豪放”;二是从金哀宗即位到蒙古军队长驱河南之前,士人的用世之心与救亡愿望相结合,诗歌特征可以名之为“激昂的豪放”;三是金亡国前后十年,社稷丘墟之悲与荆棘铜驼之叹,诗歌的风格可名之为“沉痛的豪放”;四是蒙古宪宗时期至忽必烈在位初期,这一时期诗风上承金末余风,并呈现出代际传递的特点。
“压抑的豪放”,不妨以李纯甫、冯璧、雷渊书写登封会善寺怪松的同题诗为例。兴定三年(1219),43岁的李纯甫因不满术虎高琪专政,辞官隐于嵩州伊川,曾游登封会善寺。会善寺有一棵形状奇特的老松,司马光《王君贶宣徽垂示嵩山祈雪诗十章,合为一篇以酬之》诗有“会善庭隅千岁松,一根二股凌寒空”[15](P112)句书写怪松的形状,元好问《会善寺》诗也有“长松想是前朝物,及见诸孙赋黍离”[4](P142)句感叹北宋的亡国与历史的无常。李纯甫所作《怪松谣》,似乎无意于回顾这棵老松的历史,而是着力于描摹它的“现在”,也即这棵老松在他眼前心中的当下形态。前四句云:“阿谁栽汝来几时?轮囷拥肿苍虬姿。鳞皴百怪雄牙髭,拏空夭矫蟠枯枝。”破空而问,突兀惊怖,一棵外形奇特的老松被他写得张牙舞爪、剑拔弩张;后六句云:“试与摩挲定何似,怒我枨触须髯张。壮士囚缚不得住,神物世间无着处。提防夜半雷破山,尾血淋漓飞却去。”[2](P1173-1174)诗歌写得怒张飞动,结尾的想象尤其惊心动魄,表达着诗人希望打破沉闷的时局,抗争出离的愿望,而怪松的扭曲变形正是诗人压抑内心的写照。
冯璧、雷渊同赋怪松在宣宗元光年间(1222—1223),同游的还有兴定五年(1221)考中进士,不就选而退归嵩山的年轻文人元好问。冯璧于元光元年(1222)致仕,“居嵩山龙潭者十余年,诸生从之游与四方问遗者不绝,赋诗饮酒,放浪山水间,人望以为神仙焉”[2](P1459)。对于赋怪松的背景,冯璧说“元光间,予在上龙潭,每春秋二仲月,往往与元、雷游历嵩少诸蓝”[2](P1479),同游登封的会善寺应该即在此间。雷渊、冯璧写怪松的诗歌虽然怒张之气不及李纯甫,却也颇可见出豪杰诗人本色:
物生自有常,怪特物之病。
嗟嗟此老苍,怪怪生魁柄。
侏儒蹙髀股,宿瘤拥腮颈。
蜿蜒蛟龙戏,腾掷豸区虎竞。
须髯喜张磔,意气怒狂迸。
匠石求栋楹,节目足讥评。
刍荛急薪槱,坚悍空盼瞪。
静言观倚伏,未易相吊庆。
虽违时世用,顾免斤斧横。
阳秋莫荣悴,岁月何究竟。
盘盘曲则全,挺挺独也正。
小草误扫迹,伏神还守性。
傥随天中景,广宇共庥映。[2](P1689—1690)
(雷渊《会善寺怪松》)
嵩高地气灵,花木竞妍秀。
玉峰西南趾,有松独怪陋。
偃蹇如蟠螭,奋迅如攫兽。
叶劲须髯张,皮古鳞甲皱。
菌蠢藤瘿怒,支离笻节瘦。
月上虬影揺,风度雨声骤。
子落慰枯禅,枝樛碍飞鼬。
盘根万乘器,平盖千岁寿。
樵斤幸免寻,厦匠矧肯构。
龙化会有时,天旱期汝救。[2](P1487)
(冯璧《同希颜怪松》)
从年龄来看,雷渊(1183—1231)当时40岁左右,冯璧(1162—1240)已有60岁,但二人诗歌所呈现的豪迈气度却极为相似。除了极尽描绘怪松形态之怪,更多表达了诗人心曲,可谓以诗见性。一个“怒”字,李纯甫、雷渊、冯璧三人皆用。“怒我枨触须髯张”是李纯甫内心压抑情感的投射,“须髯喜张磔,意气怒狂迸”是雷渊描述的怪松向外张扬的豪杰意气,“叶劲须髯张,皮古鳞甲皱。菌蠢藤瘿怒,支离笻节瘦”则是冯璧所看到的怪松虽然苍老却依然勃发的生命张扬。雷渊的“盘盘曲则全,挺挺独也正”,是他对松树外形与内在精神的对比化描述,这正是他的自画像;冯璧的“盘根万乘器,平盖千岁寿”,则是他以松自比的生命坦荡。但与李纯甫希望雷霆霹雳打破沉寂的世界不同,雷渊、冯璧二诗都为松树因外形怪陋而得以保全表示庆贺,并在诗末将情感与愿望落脚于希望松树能够伏神守性,庇荫世人,造福世间。雷渊所谓“傥随天中景,广宇共庥映”,冯璧所谓“龙化会有时,天旱期汝救”又与二人从政中抑强扶弱、惠济民生的豪杰言行形成了照映。三人诗歌的豪杰特色,还在于用词的生新硬峭。如雷渊诗末的“庥映”一词,此前文学作品中未见,应该是雷渊的首创,2000年版《汉语大词典》对这一词语的解释,例证即引雷渊之诗:“庥映:遮盖。金雷渊《会善寺松》诗:‘广宇共庥映。’”[16](P1230)他们由于豪杰人格而对语汇的大胆创造于此可见一斑。
“激昂的豪放”可以李汾、元好问作为代表。李汾诗如《雪中过虎牢》:
萧萧行李戛弓刀,踏雪行人过虎牢。
广武山川哀阮籍,黄河襟带控成皋。
身经戎马心逾壮,天入风霜气更豪。
横槊赋诗男子事,征西谁为谢诸曹。[2](P2510)
这首诗正可看作金末为救亡奔走的李汾的自画像。在李汾的自我书写中,一位流离困顿而精神强毅的豪杰文士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位布衣文士行李萧然,却挟带着弓刀踏雪而行。叠加着历史战争典故的虎牢关和成皋故城,雄浑阔大的黄河,阮籍“世无英雄”的慨叹,都使诗歌透出冷冽悲壮之感。诗末二句真正道出诗人心事,那就是如曹操一样“横槊赋诗”,在实现天下之志的同时吟诗作赋,达到人生志向与文学风格的高度统一。李汾以七律见长,王士禛《渔洋诗话》中说唯刘迎的歌行与“李汾长源之七言律为《中州集》之冠”[17](P4813-4814);而一向对金诗给予苛评的明人胡应麟,也说“李汾长源在诸人中稍有气格”,并举其七律如“紫禁衣冠朝玉马,青楼阡陌瞰铜驼”“汴水波光摇落日,太行山色照中原”“日晚豺狼横路出,天寒雕鹗傍人飞”“昆仑劫火惊人代,瀛海风涛撼客槎”等句,说如果不是“年未四十而卒”(2)李汾去世时41岁,参薛瑞兆《新编全金诗》的考订,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439页。,其成就“当出元裕之上”[18](P330)。
元好问写于哀宗出逃前的诗歌,也大多属于此类“激昂的豪放”风格。清人陶玉禾评点元好问作于正大四年(1227)的《去岁君远游送仲梁出山》一诗,认为“遗山空阔豪宕,意气横逸,波澜起伏,自行自止,不以粗率为奇,不以雕搜为巧。而其中纵横变化,不可端倪”,并说“其长篇大章皆应如是观”[14]。潘德舆则指出元好问善写“大句”,说“自李、杜后,诗遂无大句”[19](P119),元好问却于四百年后有志追复。“大句”不但在于景物之雄浑、时间之邈远,而且妙在纵横变化。郝经评价其师元好问诗歌的特点是“巧缛而不见斧凿痕”,陶玉禾则认为“巧缛”不足以称遗山,“其独绝处,正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曲折变化,惟意所及。律句格法,严密而纵横洒落,绝去雕饰,有龙跳虎卧之观。不特独步两朝,即在唐、宋间,亦足自竖一帜”[14]。这一点也得到了日本学者小松直之进的认同,在大正八年(1919)所编《遗山诗选》的序言中,他称“遗山之于诗,气格清隽,如鹰隼搏空;沉博伟丽,如骤雨开晴。而飘渺者,高古者,随其体变化,可喜可骇,使人叹嗟不已矣”[20]。而元好问正是携带着这样的豪放纵横之气为元代诗歌开山。如写于乃马真后二年(1243)七月的古体长诗《游龙山》,陶玉禾评价“一气挥斥,纵横尽意,有骏马下坡之势。自是才力豪横,非可仿佛”[14],正是对元好问入元后豪放诗风的确认。
元初诗风在豪放层面最得元好问真传的无疑是郝经,并且颇有出蓝之姿,这也是上列第四阶段的豪放特征;第三阶段“沉痛的豪放”,也即金亡后以元好问为代表的丧乱诗,这一点研究较多,不再赘述。关于第四阶段的豪放诗风,顾嗣立说:“元兴,承金宋之季,遗山元裕之以鸿朗高华之作振起于中州,而郝伯常、刘梦吉之徒继之。”(《元诗选初集·丙集》袁桷小传)[21](P593)也即由元好问开启的“鸿朗高华”特征,由他的弟子后学郝经、刘因等人承续。刘因比郝经小二十多岁,平生未见过元好问,郝经却是亲承教泽,并对元好问其人其诗有着深切理解的。郝经诗歌的雄浑苍劲、笔力纵横,一方面得自于对元好问诗歌精神的领会,另一方面也与他“慨然以羽翼斯文为己任”的使命意识,以及深厚的理学涵染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他“发为议论,高视前古”,“于辞以理为主,雄浑有气”(卢挚《元故翰林侍讲学士国信使郝公神道碑》)[9](P1149),成为元初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高标。如写于北觐途中,以塞北风物和历史感怀为主题的《沙陀行》《居庸行》《化城行》《入燕行》《白沟行》等歌行体诗,都写得境界阔大、雄浑有气。《入燕行》开篇写景:“南风绿尽燕南草,一桁青山翠如扫。骊珠昼擘沧海门,王气夜塞居庸道。”继而转入历史感怀:“荆卿虽云事不就,气压咸阳与俱灭。何如石晋割燕云,呼人作父为人臣。偷生一时快一已,遂使王气南北分。”[9](P197)将空间的宏阔与历史的纵深相联系,出语豪迈。郝经诗歌大多如此,气象宏大,语势淋漓,使人读来热血沸腾。对于郝经的诗歌特点,查洪德先生概括为有“沉郁顿挫之体,清新警策之神,震撼纵恣之力,喷薄雄猛之气”[22](P201),颇为准确形象。
金元之际作家的豪杰之气也影响到词和散文等文体。就词而言,在所谓“豪放”“婉约”二分法中,金元之际的词多可归入“豪放”;而金末时事激发下文人普遍存在的豪杰情结及金亡后的家国之悲,又增加了这一时期词的豪放特征。彭国忠、刘锋杰编注,余恕诚校读的《豪放词》一书,于金词选入15人22首词,其中经历蒙金战争者有赵秉文、李献能、折元礼、高永、高宪、王渥、段克己、段成己、元好问9人共15首,占到了所选金词的68%强,即便如此,未入选而有豪放风格者不在少数;于元初北方词人选入刘秉忠、白朴、胡祗遹、王恽、姚燧、刘因、鲜于枢7人8首词,可以看作金末豪放词风的延续。散文方面,金元之际散文雄豪劲健的特征也非常明显,如金末雷渊“博学有雄气,为文章专法韩昌黎,尤长于叙事”[3](P10);梁持胜“文章豪放,有作者风”[3](P48);王郁“为文闳肆奇古,动辄数千百言,法柳柳州”[3](P22);高永“文辞豪放,长于论事”[3](P27);等等。作家们的豪杰气质使他们更多推重和效仿韩愈和柳宗元,而他们对韩愈的重视也影响到了元好问、杨奂以及二代文人郝经、姚燧等人的散文创作取向(3)可参看魏崇武《论蒙元初期散文的宗韩之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
正因为金元之际作家普遍的豪杰特质和他们文学创作中的尚豪取向,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出以雄豪劲健为主体的风格特征,并对元初文学起到了开山定调的作用。
三 元初尚豪诗风的转型与“粗豪”批判
豪杰气象与尚豪取向是元初文学的底色,但以更综合的视野来看,我们还应该看到元代文学走的其实是一条由豪放向平易演进的路线。元末蒋易总结元诗的发展过程,认为元初诗坛的特征是“熙熙乎,澹澹乎,典实和平,蔼然有贞观、上元气象”(蒋易《徐长卿望乡诗序》)[23](48册,P132),所指应该是忽必烈即位后庙堂文学的总体特征。这一特征形成的过程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从创作层面看,元初豪杰作家经历了风格的转型;从理论层面看,对“粗豪”文风的反思与批判,在由尚豪向平易文风演进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创作层面,影响易代之际文学风格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政治形势的逐渐稳定,易代文人必然会从末世激愤、亡国悲慨中走出,在对新政权的认同中回归到对文学内部规律的强调,自觉调整此前由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而使文学出现的“变音”。这在入元第一代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元好问晚年诗歌渐造平和,如去世前一年(1256)所作的《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游龙泉》诗:“风色澄鲜称野情,居僧闻客喜相迎。藤垂石磴云添润,泉漱山根玉有声。庭树老于临济寺,霜林浑是汉家营。明年此日知何处,莫惜题诗记姓名。”[4](P1475)山水之美与人情之暖使诗歌呈现出平和朗亮的特点。小松直之进于末二句批点云:“七、八深慨入老境。明年九月四日,先生竟不起,此句便为谶者,叹噫。”[20]好心情之下竟然创造了一个“诗谶”。元好问晚年性格之平易,还可以从时人的评价中得到印证,如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说他“性乐易,好奖进后学,春风和气隐然眉睫间”[24](P453),郝经《元遗山真赞》则评价说“其才清以新,其气夷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9](P597),都是时际承平所形成的人生态度的转变,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带动了他诗文风格的转型。学者提出元好问“平易”文风可以追溯至金末赵秉文,“王若虚承赵秉文之平易,雷渊承李纯甫之奇古,两种文风在元好问身上得以调和,但总体走向是以平易为主”[22](P63),之后通过其弟子王恽的理论和实践发扬光大,王恽继承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的“中和”努力,“用其诗文成果有意带动这一风潮”[25](P127),有一定道理。事实上自从中统元年(1260)郝经南下之后,无论是郝经磅礴淋漓的诗文风格还是他对尚豪文学理论的大声疾呼,都有随他而南下的倾向,但由于他在南方所在之处的封闭性,也并未对南方文坛产生影响;而北方文坛则在王磐、王恽等典雅平易派的带领下文风逐渐转型,并在南北统一后融合了南方文风的工丽雅致,向中期诗风演进。
这种风格转型存在于这一时期大部分作家的创作中。如元好问的好友杨果,金末李遹《赠中山杨果正卿》诗说“中山公子文章雄”[2](P1310),其风格特征正与金末总体的雄豪之风相呼应;而元初却以“蕴藉”“谐谑”著称。王恽在《故南塘处士宋公墓志铭》说“蕴藉如杨西庵,才鉴若姚雪斋,王鹿庵之品洁一世”[7](P2332)云云,《元史》本传则说他“性聪敏,美风姿,工文章,尤长于乐府。外若沉默,内怀智用,善谐谑,闻者绝倒”[11](P2574)。与他同时代的杜仁杰也说:“杨西庵,侠黠谈谐之雄者也,世人不知其然。不肖何有,竞负天下滑稽之名,杨何深而仆何浅也!”(王恽《紫溪岭》诗注)[7](P1511)写有套曲《庄家不识勾栏》的杜仁杰,入元后同样以滑稽知名,但与杨果相比竟自愧不如,这一形象与那个“文章雄”的“中山公子”相去甚远。王恽还提到的他“品洁一世”的老师王磐(鹿庵),金时名王采苓,师从麻九畴,与王郁为友,应该也属于尚豪一路,但入元后他是典型的平和雅正派,李谦《鹿庵先生墓碑》说他“为文冲粹典雅,得体裁之正”,“诗则述事遣情,闲逸豪宕,不拘一律”,[26](P257)所言“豪宕”或还保留着金末遗风。又杨奂诗,清人吴乔《围炉诗话》举其《录汴梁宫人语》《读汝南遗事》《长安感怀》等诗,认为这些诗“优柔含蓄”,并得出了“大抵金人诗胜于(南)宋人”[27](P2084-2085)的结论,所举诗都作于金亡之后,属于经过元初风格转型后的金诗。吴乔对杨奂诗的风格评价,也说明金元之际诗风超越南宋末并非因其豪健,而是因其“优柔含蓄”。又李庭的同年好友郭镐(1194—1268),金亡后“流转于兵尘者五十余载”(李庭《祭亡友郭周卿文》)[28](2册,P184),大德四年(1300)他的诗文集刊刻时,王恽看到他的诗文“温醇典雅,曲尽己意”,都意在“造乎中和醇正之域”,“于中和中做精神”(王恽《遗安郭先生文集引》)。[7](P2051)当然对这一时期入元作家风格之变的考察,也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的话题。
理论层面,对“宋金余习”(按时间顺序应该是“金宋余习”)的改造是元代文学修正南北末世积弊,从而形成与时代相适应的成熟文风的重要路径。元中后期的苏天爵在《书吴子高诗稿后》中说:“我国家平定中国,士踵金宋余习,文辞率粗豪衰苶,涿郡卢公始以清新飘逸为之倡。”[29](P495)其中的“宋余习”指的是“衰苶”,“金余习”指的是“粗豪”。苏天爵之说应该承欧阳玄而来,欧阳玄说:“皇元混一之初,金、宋旧儒布列馆阁,然其文气,高者倔强,下者委靡,时见余习。”(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丁集》虞集小传引欧阳玄语)[21](P843)这里“倔强”应该与“粗豪”同义。这一说法到清代仍有响应,顾嗣立《寒厅诗话》说:“元诗承宋、金之际,西北倡自元遗山,而郝陵川、刘静修之徒继之,至中统、至元而大盛,然粗豪之习时所不免。”[27](P4530)金元之际作家普遍的豪杰人格,易代之际的时代氛围,都是导致创作“粗豪”的一些因素。
事实上,对金末作家的粗豪批判在元初即已凸显,应该说与时际承平后文人审美趣味的改变有关。对金末豪杰作家的重新评定,较早见于元好问元初为杜仁杰所作的《逃空丝竹集引》中,元好问借为杜仁杰诗文集作序的机会,反思李汾、麻九畴的诗风,认为南渡后,李汾七律“清壮顿挫,能动揺人心,高处往往不减唐人”,然而“失在无穰茹”;麻九畴的七言学习陆龟蒙,“所谓陵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者,皆略有之”,并且“病在少持择”[30](P1522)。“穰茹”本是酿酒之法,指以秸秆覆盖器皿。元好问说李汾诗“无穰茹”,也即没有包裹,偏于直露。(4)释义参考胡传志《金代诗论辑存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08页。这正是李汾豪杰诗风所导致的诗病。对于麻九畴崇尚的晚唐诗人陆龟蒙,元好问是有特殊情结的,他在聊城期间曾校补家藏的陆龟蒙《笠泽丛书》,在后记中一方面批评其“多愤激之辞而少敦厚之义”,“标置太高、分别太甚、锼刻太苦、讥骂太过”,一方面又对其“始则陵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卒之造平淡而后已”(元好问《校笠泽丛书后记》)[30](P328)的创作取向表示欣赏。元好问认为麻九畴诗略有陆龟蒙的“陵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却没有达到“造平淡”的境界,并且“少持择”,选词炼句不够谨严。这也与麻九畴“天资野逸,高骞自便,与人交一语不相入,则径去不返顾”的豪杰人格有关。这是人格之豪带给文学创作的不利因素,但在金末以豪相尚的社会风气下,这一点很少被提出或者被意识到;金亡后渐至承平,也没有了官场事务,对文学的品评便更多回到了文学自身的规律。以这种心态和视角回顾金末友人的作品,就会有新的发现。
这种反思也见于杨弘道写于元初的作品中。他在《变古乐府小序》中写道:“元光、正大间,李长源、王飞伯辈竞效乐府歌诗,沿袭陈烂,殊无意味。”批判的背景是他所见到的三篇“以旧题为律诗道今日事”[31](P463)的乐府作品,认为前所未见,是诗格之一变,相较而言,李汾、王郁的乐府诗是效仿古乐府而作,缺乏新意。李汾、王郁性格相似,都以豪放不羁、流离困顿而不失耿耿自信著称。杨弘道金末与二人也都有交游,还曾作有《调李长源》诗给李汾:“何时一斗凤鸣酒,满酌与君洗不平。男儿年少鬓如漆,日落胭脂坡上行。”[31](P456)详其诗意,应该是李汾被逐出史馆时的送行之作。又作有《送王飞伯》诗给王郁:“吟诗何所得?白发早生头。始觉虚名误,应为达士羞。梁园遇飞伯,俊气挟清秋。嵩路引归思,因余故少留。”[31](P424)可见二人交谊深厚,杨弘道对王郁的“俊气挟清秋”也极为赏爱。因而他对于金末死难的两位好友诗风的批判,出发点与元好问批判李汾、麻九畴类似,都是回到文学本位进行反思。
李治元初所作笔记《敬斋古今黈》有两则对周昂、宋九嘉的批判之语。前者是对周昂《题鲁直墨迹》一诗“诗律如提十万兵,东坡直欲避时名。须知笔墨浑闲事,犹与先生抵死争”一诗的批判,指出“周深于文者,此诗亦以世俗之口量前人之心也”,他要指出这一点,“以喻世之不知山谷者”[32](P181)。这是对金代文学中的黄庭坚批判的反拨。周昂虽然战殁于金宣宗迁都汴梁之前,但他在宣宗南迁后依然很有影响,尤其是他的文学思想通过外甥王若虚的《滹南诗话》在元初产生了重要影响。王若虚的《滹南诗话》对黄庭坚的批判毫不相贷,如他批判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是“特剽窃之黠者耳”,指出“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为富,点化陈腐为新”[33](P493),批评可谓狠重,也成为黄庭坚诗歌接受史上的著名观点。李治对前辈王若虚非常敬重,王若虚去世后《滹南遗老集》刊行,李治为作序引,极为推重;但他对周昂批判黄庭坚之诗的反对,还是通过笔记予以表达。后者是对宋九嘉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说不出于孔氏前,二恨词学之士多好译经润文,三恨大才而攻异端”之说的批判,李治认为,佛老异端固所当恨,学士大夫译经润文是儒学之先务,“何足訾乎?”李治认为真正可恨的是那些“剥削诗书中一二语,重摹而复写之,以为文之至”者,以此反思那些“世之为文之士”,他又担心那些仰慕宋九嘉的青年人“有弃经之实,而专从事于词藻之华”[32](P86)。周昂、宋九嘉都是金代卓有影响的豪杰作家,李治的反思与批判,同样是元初存世作家对金源一代尤其是金末文学风气的反思和矫正。
郝经文风的汪洋恣肆,在元初也有质疑者。王恽《庭芝评郝奉使文》引李庭芝评论郝经的话“陵川固才高学博,但出入韩文,未甚熟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余尝度之,韩文世所重者,其要非一。今李之于郝所以云云者,岂以韩丰而不逾一辞,约而不失一字,郝之返是者极多?不然,是择焉不精,明理未至,杂以非圣之言故也。”[7](P2133)李庭芝是南宋两淮置制使,中统二年(1261)郝经初到真州时,李庭芝曾赠郝经扬州琼花,郝经为作《琼花赋》;卢挚《郝公神道碑》记载郝经被扣真州与李庭芝有关,郝经刚过淮河,“李璮辄潜师侵宋,两淮制置李庭芝寓书于公,蔑以欵兵,馆留真州,藉为口实”[9](P1148),郝经有书答复,陈述边将行为与使者无关。宋亡后,李庭芝被俘不屈死。李庭芝与郝经为敌方,他评价郝经文章风格之语如何传入北方被王恽看到,不得而知,重点在于王恽对此观点表示认同,他猜测李庭芝所说的郝经学韩愈而不至,可能的原因是在繁简处理上不能像韩愈一样严谨自如,或者是“择焉不精,明理未至,杂以非圣”。王恽与郝经同出元好问之门,宪宗四年(1254)二人曾相会于卫州,“始觌清扬,重于夙契。把酒论交,笑谈游艺”[7](P2742),王恽作有《送郝伯常归保塞》:“书剑南辞杞国天,一欢倾倒酒炉边。凤麟瑞质惊千古,江海词源浩百川。吾道莫伤今日否,斯文将付后来传。骊驹歌断青山暮,愧未长游从马迁。”[7](P617)二人谈论文艺,王恽为郝经的“凤麟瑞质”和“江海词源”惊叹,二人为“吾道”的失落共伤,王恽遗憾与郝经相处时间太短。至元十三年(1276)郝经去世后,王恽又写有《哭郝内翰奉使》《祭郝奉使墓文》《壮士吟题郝奉使所书手卷》等诗文,情深谊重。《哭郝内翰奉使》中“义契重于平昔友,斯文公与后来盟。苦心问学唐韩愈,全节归来汉子卿”[7](P667),前二句呼应二十多年前两人相会时“一欢倾倒酒垆边”“新文将付后来传”等句,后二句称扬郝经问学的精深像韩愈一样,出使南宋全节归来又像汉代的苏武。由此可见王恽对郝经有着深厚的感情,将郝经与韩愈作比或也含有郝经文学韩愈的时评。他对李庭芝评论郝经之语的引述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应该也是从文学本位出发。
除了批判,元好问也试图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如在蒙古海迷失后元年(1249)所作的《杨叔能小亨集引》中,他反对诗歌流露出“伤谗疾恶不平之气”,认为即使有这样的情绪,也要用“婉”“缓”的方式来表述,所谓“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30](P1023)。他还列出了自己学诗时曾自警的十余条,“无怨怼,无谑浪,无骜狠,无崖异,无狡讦……无为薄恶所移,无为正人端士所不道”[30](P1025)等。在次年所作《陶然集诗序》中,又指出了时下“钝滞僻涩,浅露浮躁,狂纵淫靡,诡诞琐碎,陈腐为病”[30](P1150),这些都应该是“粗豪”的具体表现。元好问也曾看到刘秉忠诗律之粗,不过相信“他日自细去”,并将自己编的诗学著作《锦机》赠给刘秉忠(5)刘秉忠《读遗山诗》“蜀锦丝头从此细”句注:“盖遗山见愚狂作,寄语世昌曰:‘他日自细去。’既而赐到《锦机》,故此及之也。”《全元诗》第3册,第133—134页。。元好问《与张仲杰郎中论文》中也写道:“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功夫到方圆,言语通眷属。”[4](P1346)这些应该都是元好问在有意识地矫正金末诗风的“粗豪”之弊。顾嗣立认为元好问的创作也有效地矫正了宋金“粗豪”余习,其《题元百家诗选二十首》其一:“雄深出入少陵间,金宋粗豪一笔删。恢复中原板荡后,黄金端合铸遗山。”[34](P298)可以看出他未将元好问列入“粗豪”之列。
结 论
金元之际“豪杰”作家大量涌现,作家普遍的“豪杰”情结,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既与东汉末年建安诸子的崛起相辉映,又与唐末五代、南宋末年的诗坛风貌形成鲜明对比。两代诗人的尚豪审美取向,使这一时期的诗坛呈现出鲜明的豪杰特征。而到元初承平之后,易代作家自身诗风所发生的改变,以及他们对金末有悖于文学规律的文学现象的反思,又自觉带动文学进行革新。正如查洪德先生在《元代文学通论》中所说:“金代平易一派为主流,元初则奇崛一派为主导。但这种主导是暂时的,越到后来,越表现出向平易发展的态势,逐渐与元中期由南方文人倡导的平易正大文风合流。”[35](P386)元诗也正是在修正金元之际尚豪取向带来的“粗豪”之弊的基础上,向中期的典雅清和、平易正大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