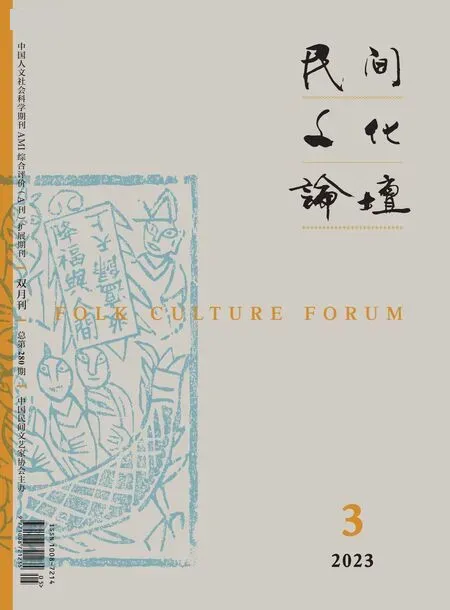“国家”与“边地”之间
—— 清代以降滇西仪式背后的乡村权力
张柏惠
学界以往在讨论明清时期地方文化发生改变的过程时,往往强调的是士大夫文化的以“礼”化“俗”。在其描述中,这个“礼”是王朝标准化的礼制(广义上包括礼拜仪式、服饰、建筑风格,以及文书格调和标准等),是国家在文字权力扩张过程中“强加”给地方的“礼”;“俗”则是地方旧有的礼仪传统,他们代表着地方民众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然而,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推进,可以看到,在明清时期,之所以国家的“礼”能顺利地在地方推行,主要是因为民间的“俗”选择“主动”靠近,而地方也往往形成“礼”“俗”共存的格局。那么民间的“俗”是经由什么媒介从而与国家的礼教产生关联的?国家与地方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些“文化中介”群体?这些中介是什么样的社会群体?明清时期,各地文化中介之职能由不同的社会群体承担,中介的机制也有相当大的地域差别。其中,以何炳棣、张仲礼、费孝通、吴晗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士绅群体是王朝国家与地方之间最重要的媒介。①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在区域社会史的相关研究中,通过士绅等中介群体的带动,地方文化向精英化靠拢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士绅等中介群体为何甘心扮演皇权执行者的角色?这些中介群体为什么要让地方文化向精英化靠拢?精英化的过程对于各地方的历史意义究竟是什么、有何不同?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观察点切入并对不同的区域展开研究时,往往会得到不尽相同的答案。
社区的庙宇(或是神明信仰)是地方之“俗”的重要标识,而围绕着这些庙宇(或是神明信仰)所建立的拜祭系统在空间及社区人群的生活中通常是通过仪式来体现的。因此,仪式是研究者观察地方文化的一个切入点,通过仪式分析不仅能够勾勒出社区内部的关系,还能够看到超越社区边界更大的地域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仪式发生变化的过程本身也与社区历史发展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动以及地方所经历的历史过程相呼应。
对于地方仪式的历史解读,刘志伟、罗一星等学者围绕着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北帝信仰仪式所展开的研究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就笔者上述的提问,在他们的讨论中能够找寻到一些回答。罗一星通过对佛山地区四大祭祀仪式的细致论述展现了社区内部的关系:北帝坐祠堂的仪式与八图土著之间的共享关系和社区特权;北帝巡游与佛山社区的等级关系;“烧大爆”与不同地缘群体的关系;乡饮酒礼与侨居者、土著民的关系。①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刘志伟则通过对北帝仪式的分析讨论了地方与国家的互动关系。②刘志伟:《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北帝崇拜的一个解释》,《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107—125 页。他谈到,祭祀北帝的仪式既展现了上层士绅和下层乡民之间不同的文化行为和态度,同时也体现了两者互相影响、互相适应的一面。
华南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答案,那么对于西南而言,答案又是如何的呢?本文旨在通过对现今依旧留存于滇西绮罗乡的“打保境”仪式的考察来探寻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绮罗乡与打保境仪式
绮罗乡现今隶属于云南省西南部的腾冲市,其下辖三个自然村——上绮罗村、中绮罗村及下绮罗村。③绮罗乡所在的滇西地区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是一个“极边区”,然而,对于东南亚地区而言,却是一个通往内地的“核心”地区,是东南亚往来贸易的中心之一。历代统治政权将腾冲设置为管理滇西地区的行政中心,视其为滇西地区的门户。绮罗乡早期的历史较少有文字等记录留存,村落所在的大盈江流域,在明王朝入驻西南以前已有土人进行开发并形成了一些聚落。④陈文纂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342 页。万历《云南通志》以及《徐霞客游记》中均有“矣罗村”的记录,可推知,在明代时,“绮罗”已经发展成为众人熟知的规模较为完备的聚落了。⑤李中溪纂修:《(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寺观·永昌军民府》,《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二十一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影印本,第309 页;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九上·滇游日记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1002 页。入清后,腾冲全境被划分为十八个“练”,“绮罗练”便是其中一“练”,而绮罗乡则是该练的主体部分。进入民国后,腾冲地方改设五个大区,绮罗乡分属于第二区。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腾冲光复后,绮罗乡改为直属腾冲县政府,新中国成立后,又历经几次行政划分的更改。
随着定居人口的增加以及村落规模的拓展,“矣罗村”在清朝初年时便已分划为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上、中、下三个部分。村落中的一部分巷道使用姓氏来命名,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巷道旧名的延续。绮罗乡现留存的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主要公共建筑为上绮罗村的妙光寺建筑群、段氏宗祠,中绮罗村的观音寺,下绮罗村的文昌宫建筑群、水映寺、靖澜寺(现只残存房屋的梁架部分)、绮罗图书馆、河边李氏宗祠、青齐李氏宗祠以及尹氏宗祠。
在自然地理上,绮罗乡位于腾冲城东南4 公里处,地势北高南低,东西为开阔的田野,是一个平坝地区。自明代至今,绮罗乡大部分乡民的生计方式以务农为主,种植作物多为水稻,一年一季。①腾冲西边的德宏地区,即明、清时期的土司地区,同样以水稻种植为主,因气候条件不同一年则可以收获两季。为了补贴家用,一部分乡民会选择在冬春之际往返缅甸进行贸易。②李根源、刘楚湘纂,许秋芳主编:《民国腾冲县志稿·卷十七·农政·土壤及农时》,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 年,第324 页。从腾冲城出发,经过绮罗乡之后,便是多条通往缅甸的主要交通干线,因此,该乡“走夷方”从事商业贸易之人颇多。③李根源、刘楚湘纂,许秋芳主编:《民国腾冲县志稿·卷二十四·礼俗·习尚》,第441 页。
绮罗乡每年最重要的仪式是立秋前的“打保境”。“打保境”又唤作“秧苗保境”“消灾保境”。举行该仪式是为了祈祷风调雨顺,秧苗长势顺利,无病虫害,能够获得丰收,同时达到消除地方灾祸、清吉平安的作用。该仪式每年在立秋前的两三天举办,与农事紧密相连。立秋前的日子是腾冲地区插完秧后的农闲时间,因此乡民得以有时间参与地方上的祭祀活动,同时也可以为此后的秋收做准备。在绮罗乡乡民的记忆中,新中国成立以前举办打保境时,四乡八邻齐聚,人山人海,转经队伍所过之处,人们夹道观看、欢呼。届时还有卖小吃、小玩意儿,走亲戚,谈生意的,场面十分热闹。然而,打保境既不是绮罗乡独有的一个仪式,也不是整个腾冲地区的乡、镇都举办的仪式活动。打保境仪式主要由城关镇(即腾冲城)及其周围的和顺乡、绮罗乡、洞山乡、玉璧村以及个别虽然远离腾冲核心区,但是人口稠密且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固东镇的顺利村等举办。
关于打保境仪式,官方史书以及历代民间文献中均没有确切且详细的记载。同样,腾冲其他举办打保境仪式的乡、镇亦不知仪式确切的起始时间。打保境仪式的一个核心部分是洞经队的演出,绮罗乡洞经队的成立则可以明确地追溯到清代的道光年间。据此可以判断,绮罗乡举行打保境的仪式最迟不会晚于道光时期。
早期的仪式,现在不易得见,但从如今保留下来的科仪文书、仪式表演以及对洞经队老成员的访谈中,仍然能够辨析仪式中所表达的地域社会关系,从仪式的变化中也能看到社区历史发展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动。④笔者在田野考察中共搜集到绮罗乡洞经队用于举行打保境仪式的科仪文书共34 本,这些科仪文书均为老旧的手抄本,大多年代不详。其中《打保境功德名录》为光绪六年(1880 年)抄本;《大洞治瘟宝录》为民国八年(1919 年)抄本;《太上洞玄灵宝拔度救苦谈章》为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抄本。因为民间信仰仪式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借助身体动作、语言表达等形塑的一种社会文化。在仪式中,地域社会里的不同人群依照其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分别表现其各自的身份、地位与诉求。不同人群在不同时间依序登台演出,这便是地域社会人群关系、权力变迁的一种表达。
绮罗乡每年打保境多在立秋前的两三天开始举行,整个打保境仪式共持续四天。仪式第一天的内容包括“熏坛”“荡秽”“礼请诸真”,即清理经坛,荡除污秽,并将请帖送往天上的众神,请众神第二天来参加保境大会,目的是为第二天打保境活动的正式开始做准备。第二天的仪式意味着保境活动的正式开始,主要内容包括“宣读仪注榜”“迎神”“谈演《大洞仙经》上卷”“讃灯”“接亡”“设诸天科”。第三天的仪节包括“开坛”“谈演《大洞仙经》中卷”,期间包括“迎十供养”“转经抬阁”“谈演八卦”“设斋(或是设醮)”。第四天是打保境仪式的最后一天,主要包括“开坛”“谈演《大洞仙经》下卷”“拔亡”“送亡”“送圣”。除了“转经抬阁”这个部分,所有的仪节均是在同一庙宇中主要由洞经队成员及承首来完成,1918 年以前,主要仪节是在下绮罗村的文昌宫内完成,1918 年以后至今则改为在上绮罗村的妙光寺内举行。
整个打保境仪式过程中最热闹且最能体现社区整合并明确其“边界”的环节便是“转经抬阁”。①因腾冲县政府的安全管理要求,2000 年前后绮罗乡被迫取消了“转经抬阁”,所有仪节表演改由在庙里进行,因此现今已看不到“转经抬阁”的表演。转经前,经长宣读“起朝”表文,示意诸位神仙也跟着一起转经,焚表后正式开始转经。转经队伍所要经过的乡里的主要巷道都会提前摆好香案。转经队伍沿村边大路转走,按顺序依次经过上绮罗村的妙光寺(起点)、中绮罗村的观音寺以及下绮罗村的文昌宫和水映寺(终点)。走在转经队伍最前面的人群举着皇伞,扛立着风旗,边走边敲锣打鼓。洞经队成员同样列于队伍前端开道,并随走随演洞经音乐,承首则手捧香炉紧随其后。除此之外,巡游的队伍中还包括高抬阁②高抬阁的构造,用木料堆成假山的形象,再用细铁丝互相连接起来,假山配置花草。下面是四方形的木架,中间立一根用铁做成的拐杆。上面放置一个小台子,供人站在上面。台杆上以十二三岁的男童装扮成白蛇、仙女、姜太公等人物。,地抬阁③即地上走着的装扮人物,人物选自戏曲中的角色,如唐僧、笑和尚。,水谶棚④用一个木架子搭着,前后各一个人抬着,中间搭成一个篷子。外面一个人打着大钵,棚里的那个人打着鼓。,大提炉四个,香亭⑤用竹子扎成的亭子,中间放着香炉烧香。,以及人装扮的马、赵、温、康四帅⑥“马”即马天君(马灵耀);“赵”即赵公明(财神);“温”即温天君(雷神化身,消除瘟疫);“康”即康元帅。四帅各骑一匹马,手持刀枪、宝杵等法器。、太岁和鬼王。在转经抬阁的过程中,巡游队伍要转到当年担任承首的家里上一道“镇宅表”。转经队伍每经过一个大巷口,承首都要进一炷香,并鸣铁炮三响。待由上绮罗村转到中绮罗村的观音寺时,队伍停下,由经长去寺里上一道表文,后又转到下绮罗村的文昌宫同样上一道表文,最后队伍到达下绮罗村的水映寺,上完表文后,抬阁、四帅等装扮者卸装,巡游队伍解散,表示转经结束。据乡民们回忆,转经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全乡的男女老少都会夹道观看,场面十分热闹。
二、国家礼仪的地方化与士绅的文化中介功能
参与整个打保境仪式筹划、表演的人员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整个仪式每年主要、固定的参与者,洞经队成员。第二类是承首、相邦者、转经队伍扮演者等不固定人员。绮罗乡洞经队的成员是仪式专家,负责指导祭品摆放等准备工作,引导整个仪式过程,使得四天的活动井然有序。同时,他们还是各部经典的唱诵者以及洞经音乐的主要演奏者。
根据笔者对绮罗乡洞经队新、老成员的访谈以及绮罗乡历任洞经队经长的记录,绮罗乡洞经队最初成立于下绮罗村,组织创立者以及第一任经长名叫李含英。⑦李含英是下绮罗村河边李氏宗族的成员,道光初年的举人,在他的主持下河边李氏亦在道光年间开始正式建设宗族。洞经会成立时取名为“桂香会”,新中国成立前充任桂香会会员者除了必须是绮罗乡人士外,还必须具备儒生身份。洞经队现任成员均拥有“一技之长”,而这些技能往往都受教于老一辈的洞经队成员。新成员中的一部分人需要向老会员学习如何撰写祭文以及行礼(包括唱礼和诵读祭文),另外一部分则需要学习如何弹奏乐器以及奏唱洞经音乐。成为洞经队成员并不意味着是选择了一个职业或是从事一个行当,绮罗乡洞经队成员大多是“兼职”参与桂香会的活动。在整个打保境期间,他们是沟通神明的仪式专家,并以文昌帝君座下弟子自居,这种能够与神明沟通的资格便是借助“入会”以及“师承关系”进行传递的。洞经队成员在仪式中的地位,类似于道士在道教科仪,僧侣在佛教科仪中的地位。
从道光年间开始,以李含英为首的士绅群体便借助洞经演奏参与到了这个本地的重大仪式当中,成为仪式表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此以后,他们通过主持仪式强固了这个群体在乡里的权势。根据乡里的老人所述,新中国成立以前乡里的读书人家都会争相把小孩送去洞经会学习,而洞经会成员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更受到乡民们的尊敬并且在乡里拥有很高的地位。
传说李含英将洞经引入绮罗乡的契机是其离乡赴京参加会试,他在离乡期间习得洞经后便引荐回乡。故事的真实性无法考证,但这个传说却透露出洞经不是腾冲本土而是外来事物的信息。腾冲地区同样拥有洞经组织及打保境仪式的,如和顺乡、洞山乡等,他们关于洞经会成立的传说亦大致表明洞经是由外地传入腾冲的。①对于洞经传入腾冲地区的时间与地点各乡的说法均不同,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南京传入说”,即明朝初年由南京到腾的移民传入;二、“鹤庆、大理传入说”,即清代中叶由大理地区传入。(参看郭朝庭、闵承龙、毛三:《保山洞经初探》,《今日民族》2007 年第12 期;腾冲县文管所、腾冲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普查组:《腾冲打保境调查报告》,2005 年5 月20 日。)以往的研究显示,洞经音乐以及洞经会自明代以来便在云南流布开来,谈演洞经具体起于何时以及源于何方均无明确的史料记载。②据学者们的调查研究,云南最早成立的洞经会大概是洱海地区下关的“三元社”和大理的“叶榆社”,两会成立于明中期,此后洞经会组织便逐渐扩散到云南诸地。一般的说法是随着明朝在云南开疆拓土后,洞经音乐及洞经组织便由南京、四川等地传入云南,随后以大理为中心向周边传播、拓展,云南的洞经会组织因谈演《文昌大洞仙经》而得名。③关于洞经会在云南的缘起,从现有的学术成果看主要有三种说法:一、以王兴平《文昌崇拜与洞经音乐》(《音乐探索》,1996 年第2 期)一文为代表的著述认为元末明初时由江南移民和士兵带入洞经音乐,随后云南相继组成了洞经会;二、以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儒道释三教的复合性文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一书为代表的著述认为洞经传入云南的时间大约在明初洪武年间,由南京、四川等地传入,在嘉靖九年时大理率先成立了三元社和叶榆社两个洞经会,随后洞经会组织扩散到云南诸地。三、以何显耀《古乐遗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为代表的著述认为洞经音乐与洞经会起源于云南大理。
根据一些学者对云南昆明、大理、楚雄、建水等地洞经会调查的情况来看,云南地区洞经会的成员在明清时期几乎都是有功名的儒生。④参看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儒道释三教的复合性文化》,第1—16 页。同样,新入会的洞经会成员向老一辈的成员学习,老成员以口传心授的方法教学工尺谱,锣鼓经或“朗当谱”。有些成员采取跟班听学的方法,修习满三年后便可当选司事,邀人摆坛,参加洞经会内部组织的“考试”合格后才算正式会员。⑤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儒道释三教的复合性文化》,第27 页。
洞经队成员在仪式中的分工都十分明确,一人担任“通赞”,该人需精通礼仪程序,负责发号施令,引导礼仪的完成。一人担任“陪赞”,负责协助通赞发号施令。一人担任“纠仪”(或称“监经”或“督坛”),该职位通常多由老成公正的绅耆充任,负责纠察违规者。洞经队其余成员担任首座、副座、上座、下座等,负责乐器的弹奏。⑥“首座”一般位于左班之首,实为谈演的总指挥,负责起调毕曲、曲牌转接等谈演。“副座”位于右班之首,实为谈演之副指挥,该人精通经籍,负责经典谈诵讲读,散引领唱等。上席位置一般在堂内左、右班第2—6 座,操演各种乐器(武乐)。下席位于堂外左右班第1—4 座,操演各种乐器(文乐)。(参看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儒道释三教的复合性文化》,第27—28 页)绮罗乡洞经队的成员在打保境仪式中虽然几乎没有这些“专称”,但是他们的“分工”却都带有上述那些“普遍性”的特征。四个“朝席”是谈演的总指挥,负责曲调的节拍以及经文的诵唱。其中右班的首席是整个仪式中最为关键的人物,他负责起调、毕曲、曲牌转接、散引领唱以及仪式的表演与主持。整个绮罗乡洞经队除了有在堂上参与仪式表演的成员外,另有专门负责书写文书的“文书长”,负责各个仪节供品、经场布置的专员,引导承首及善信进行拜祭的专员以及纠仪的“督察员”。这些绮罗乡洞经队成员在仪式中的“职责分工”又与州县层级王朝礼仪中的“通赞”“引赞”“司正”“乐生”等十分相似。
如若翻检明清《会典》以及明清地方志所记载的州县层级所举行的仪式规程,可发现绮罗乡的打保境仪式和明清王朝礼仪涉及的程式与司仪所喊的口令等多有相似重叠之处。州县层级所举行的仪式是民众最容易接触到的王朝礼仪,如祭祀孔子、关帝、社稷的仪式,乡饮酒礼仪式等,在明清各种政书与地方志中都有详略不等的记载。①明清王朝的祭祀礼仪及其仪注可参看《明会典》、《大清会典》的记载,对于州县层级的礼仪,地方志中的记录较之《明会典》与《大清会典》更为详细,云南方志中乾隆十四年所编《新兴州志》对乡饮宾礼的程式作了详细的记录。(任中宜纂修:《(乾隆)新兴州志卷八典礼》,《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26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年影印本,第550—551 页。)明清时期州县层级的众多仪式的程式有很多相似之处,比较打保境仪式与乡饮宾礼仪式,可以看到从司仪的选用与职责,礼仪的程式以及口令都十分相似。只不过在时间上王朝礼仪的一个过程完成往往比较短暂,整个打保境仪式完成持续时间较长,如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打保境的仪式在循环往复的上演明清王朝礼仪的基本程式框架。但是,打保境的仪式又并非都是照搬王朝礼仪。从仪节来看,打保境仪式又与文庙的释奠礼等王朝礼仪有所重叠。文庙释奠礼的主要仪节包括:迎神、三献礼、饮福受胙、彻馔、送神、望燎(焚祝帛)。②刘永华:《明清时期的礼生与王朝礼仪》,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著:《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9 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245—257 页。而打保境的主要仪节中也包括迎神、三献礼(虽然献的都为素食)、饮福受胙、彻馔、送神、焚表文等。即使打保境仪式期间穿插了其他仪节,但是其主要的仪节安排及顺序仍然与王朝的礼仪有诸多重叠之处。当然,将地方与国家礼仪的仪式作比对,并不是说打保境仪式就是对明、清王朝礼仪的直接复制,而是说它的形成受到了王朝国家礼仪的影响或是借鉴了国家礼仪。从仪式的结构看,文庙释奠仪式和明清时期的其他朝廷祭祀仪式比较相似,释奠仪大体上是郊祀仪的简化。③刘永华:《明清时期的礼生与王朝礼仪》,第245—257 页。无疑州县层面举行的仪式成为了王朝礼仪向民间渗透的最重要的渠道。
既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充任桂香会的洞经队成员都必须是地方儒生,那么他们其中一部分人或多或少都参与或是观摩过地方衙门所举行的祭祀孔子、关帝、社稷、乡饮酒礼等王朝礼仪,自然对官方祭祀的程序耳熟能详。王朝礼仪的公开性与易复制性又让这些地方精英得以将这套礼仪运用到地方的仪式当中,而这个过程也是国家礼仪地方化的一个过程。
但是,必须注意到的是这些儒生对于王朝礼仪的复制显然也是有限度的,从打保境仪式中选用的科仪文书、所拜请的神明以及经场的布置等来看,打保境仪式更多的是融合了大量道教、佛教以及民间宗教的礼仪传统。从洞经队队员所使用的各种科仪文书的内容来看,大多都是从道教的各种“经典”中直接抄录使用的,仪式的几个重要仪节(例如“八卦”的谈演)也是源自道教。
虽然洞经队成员均自称所属儒教,但是从整个打保境仪式期间要求断绝荤茹、停止俗事以及向各位圣真献上的拜祭品来看,是与儒教的“血祀牲祭”截然不同的。设醮(设斋)、度亡等仪节安排同样也与儒家的祭祀无关。因此,这些士大夫虽然将王朝的礼仪“挪用”了一些加入到打保境仪式之中,但是绮罗乡地方仪式的主体内容仍杂糅了道教、佛教以及民间宗教的礼仪。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绮罗乡洞经会的成立使得绮罗乡打保境仪式带有了浓重的“精英化”色彩,如上所述,这体现在了洞经会的成员极力地将地方仪式与中原儒家文化以及王朝国家的礼仪建立某种关系,主动让其“精英化”。从下绮罗村文昌宫中所保留的明清历朝儒生的题名碑可以看到,自乾隆以来,绮罗乡的儒生人数迅速增加,而嘉庆、道光时期更是绮罗乡乃至整个腾冲核心区域宗族建设蓬勃发展的时期。①《科甲题名碑》,现存于下绮罗村文昌宫内。若将地方的种种变化与洞经会在村落仪式中的加入关联起来,或许可以认为地方仪式的“精英化”是此时士绅阶层扩张的另一个产物,更是因为乾隆中期爆发“清缅战事”后,致使滇西边地族群关系紧张,从而使内地人群对于汉人身份以及国家认同的不断加强。
另一方面,之所以这些士绅愿意充当“中介”并借助洞经会谈演等活动融入地方的信仰仪式之中,是因为他们心中有数,知道中央的权力可以为地方所用,于是模仿着王朝国家的礼仪来向村落人群展示他们在社区中的至高地位,由此开始获得对于地方“掌控”的权力。
三、仪式背后的权力更替与地域社会关系
整个打保境仪式中除了洞经队成员外,“承首”是另一类关键人物。承首的人选每年都不是固定的(不同于洞经会成员的长期选任),通常在仪式开始前的半个月就已选定,一般由一到两人担任。他(或他们)在仪式中充任主祭者,是献祭主体,更是整个社区的代表。每年打保境活动的经费大部分由当年的承首以及村民捐献,其中承首为主要的出资者。虽然担任承首对被选任者自身的财力要求较高,但是并非有钱的人家都能被选为承首,承首的选任还要看该户是否在村落内乃至地方上具有威望,品行是否端正等。乡民们认为,能够担任承首的人都是在社区中有权势并且掌握话语权的人,反过来说,充任承首亦是在打保境仪式中公开向乡民们显示其宗族在社区中地位的一种表达方式。
整个打保境仪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承首与洞经队成员的密切配合,他们是整个仪式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能动主体。在承担“引赞”职责的洞经队成员的引导中,承首代表社区通过上香、点灯、献祭等方式与神明进行直接地沟通。虽然洞经队成员在实际生活中为社区的成员,但是在举办打保境的仪式时,这些洞经队成员的身份是文昌帝君在人间的弟子,他们作为第三方,是连接神明与社区的桥梁,职责是组织、主持、表演整个礼仪,而不是像承首一般以社区代表的身份与神明进行沟通。
据洞经队成员以及乡民们的回忆,新中国成立前,绮罗乡的承首多出自那些建有宗族者,那么,充任承首亦是宗族显示他们在村落中拥有权威的方式之一。在打保境仪式的转经抬阁仪节中,转经的队伍在巡游时要特别绕到当年担任承首的家门处,并由洞经经长上一道“镇宅表”,这是担任承首者享有的“特权”,意在向社区人群表明承首所属的宗族在社区的地位。
在社区发展的过程中必定包含着不同人群的兴衰隆替,承首及洞经队成员的选任即是社区内部权力更迭的表现。
按照绮罗乡洞经队成员的追溯及历任经长的记录,第一任洞经会经长李含英去世后,并没有人立即接任会长一职,直到“咸同事变”平息后的光绪年间,才有名叫许庄廷者接任经长职位。许庄廷为中绮罗村许家巷人,此人是李含英麾下的洞经学员中最为出色者,他先后在腾冲地区传教洞经。但是后来由于许庄廷赴缅甸经商,再未回绮罗乡,于是萧应祉接任,成为第三任经长。萧应祉是中绮罗村贡生萧琇如的次子,曾在光绪年间获得监生的功名。①《科甲题名碑》,现存于下绮罗村文昌宫内。继萧应祉后,第四任经长为黄兴忠,他是上绮罗村黄家巷人,生于清末,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亦赴缅甸经商,未归。新中国成立前,上绮罗村栗树园人李大纲接任了第五任经长,然而在他接任后不久,洞经队便发生了分裂,分为两队,即上、中绮罗村一队,下绮罗村一队。
两个洞经会在当时约定,由上、中绮罗村的洞经队负责每年的打保境仪式,下绮罗村的洞经队则负责村里的另一个重要仪式——朝斗。但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由于各种“浪潮”,乡里的仪式被迫停办,两个洞经会也停止了活动,直到1979 年,在第六任经长杨正林的组织下,上绮罗村的洞经队才得以恢复,自此他们重新开始负责整个乡里所有仪式的举办。自1979 年以来,共有5 人担任过绮罗乡洞经会的经长,他们均为上绮罗村的村民。
从绮罗乡洞经队自清中期至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经长人员的来源以及桂香会的裂变来看,掌控地方权势以及话语权的力量从清中期的下绮罗村逐渐转移到了民国末年的上绮罗村。这种权力的更替一部分是由于社区内部的激烈竞争所使然,另一部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随着国家新一轮的政权更替,下绮罗村的大部分精英势力远走他乡、逐渐消逝,从而导致社区人群权势重心的转移,而这种社区权力重心的转移显然投射在了洞经会的组织变动之上。
放眼腾冲地区,同样,大部分财势较大的宗族在民国年间相继移居缅甸,随着人群势力的转移,在缅甸地区,洞经会组织逐渐成立。至民国末年,腾冲人在缅甸成立的洞经会组织有“当阳桂香会”“瓦城(曼德勒)桂香会”等。②杨大禹、李正:《历史和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85 页。新中国成立后,腾冲地区的洞经活动逐渐停办了,而在缅甸的活动则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缅甸的洞经会与腾冲地区的一些洞经会一直保持着往来关系,洞经会成为了身在国外的人群与本土家乡联系的一道桥梁,也成为缅甸地区华人在异乡维系关系的一个纽带。
回到打保境仪式,虽然现今已不再举行转经、抬阁的仪节,并且由于市政道路的改建已经无法再复刻出当年巡游的路线。但是,无论村中的道路怎么变化,十分明确的是,巡游队伍必从上绮罗村的妙光寺出发,且顺次经过中绮罗村的观音寺和下绮罗村的文昌宫和水映寺。从这些庙宇留存的碑刻中可知,清初至清中叶时绮罗乡的乡民对它们进行了一番修复扩建工作,这些修建活动不仅明确了绮罗乡中大姓家族对于各寺庙的掌控,更明确了妙光寺、观音寺和水映寺分别作为上、中、下三个聚落核心庙宇的地位。③乾隆四十八年《常住田碑》,碑存上绮罗村妙光寺内;《妙光寺碑记》,碑存上绮罗村妙光寺内,该碑为2007 年新立。乾隆三十二年《重修观音寺碑记》,碑存中绮罗村观音寺内;乾隆三十年《水映寺碑记》,碑存下绮罗村水映寺内;乾隆五年《文昌宫常住田碑》,碑存腾冲市绮罗乡下绮罗村文昌宫。清初至清中叶时,绮罗乡还未开始建构宗族,因此人群的关系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组织;清中叶开始建构宗族后,人群的关系则逐渐变为以共同祖先作为依据的地域群体,于宗族组织而言,祖先只是依据,重点是成员对祖先的认同而不是成员是否与祖先有相同的血缘。然而,不同于前三者,下绮罗村的文昌宫是跨越社区内部边界的存在,是整个绮罗乡共享的一个庙宇,但是,它在功能上只属于村落中的士绅阶层。
因为四个村庙是绮罗乡的核心庙宇,所以成为仪式巡游路线的必经点。当巡游队伍达到村落的核心庙宇时,都要由洞经经长进入庙中上一道表文。这一举措既明确了绮罗乡内部各村落的存在又建立了它们之间的关联,使得社区祭祀系统得以统合。另外,转经队伍在巡游时每经过村落的一个大巷口,承首都要进一炷香,并鸣铁炮三响,这一举动亦是社区在地理空间上统合的表达。
显然,在清初时,社区内部已经开始产生分化,但绮罗乡为何还能保持其整体性呢?明清鼎革后,腾越州全境被划分为十八个练,按照《州志》所载,各“练”下直接统辖各“甲”,而每个甲之下又有一个到几个不等的村、寨,从十八练各甲的相对地理位置来看,几乎都是按照地域进行划分的。①屠述濂纂修:《(乾隆)腾越州志》卷二《疆域·村寨》,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影印本,第28—32 页。绮罗练是腾越州十八练的其中一练,其下囊括了好几个村寨,除了现今绮罗乡的主体部分,还包括了距离绮罗乡较远的田心、栗柴坝、瞿家营、冷饭寨等四个村寨。行政的设置使得绮罗乡在清代时仍保持成为一体。转经抬阁的仪节整合着社区内部的“三村”与“四庙”,使得绮罗乡在实质上还是一个整体并以此呼应“练”的格局。至道光年间,由于边地野夷滋扰过甚,腾越厅为了加强防范,以各“练”为基础采取了一些措施。②赵端礼纂,陈宗海修:《(光绪)腾越厅志》卷十一《武备志·边防》,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影印本,第181—183 页。“练”的格局因为地区局势的动荡及设置的补充、增加而变得越发重要。
在社区发展中必定包含着很多的冲突与矛盾,祭祀仪式的安排,则可以成为村落不同人群用于调整和确认相互关系的一种手段。转经、抬阁仪节的安排,除了拥有其功能性的表达——强化绮罗练作为一个整体外,更是全乡人一年一度的一个狂欢节日,社区成员在此仪式中增加着彼此之间的认同感。
四、结论
绮罗乡的士绅在道光年间成立了洞经“桂香会”并成功加入到村落的仪式之中,此举改变着村落权力的体系,更是士绅阶层力量扩张的体现。洞经队成员将王朝礼仪的元素引入到打保境仪式之中,成为了仪式主持的主体,由此参与到村落内部人群关系的建构当中。
清初绮罗练的设置使得绮罗乡内各个村落在行政上以一个整体而存在,但从各大姓对妙光寺、观音寺与水映寺等村落中心庙宇的修建活动又可以看到,绮罗乡在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逐步分化为上、中、下三个聚落。乡民们通过举行打保境仪式整合着“三村”与“四庙”,从而增加了全乡人对于彼此之间的认同感,使得绮罗练在实质上保持着整体性。同样,在社区发展的过程中也必定有很多的冲突与矛盾,仪式的举行则可以成为村落不同人群用于调整和确认彼此关系的一种手段。
前辈学者所提出的士绅功能论的一个缺陷在于过度强调士绅阶层的中介作用,从而使得研究者在理解和认识乡村权力关系的时候往往容易局限在对国家政权与地方精英之间权力变动的讨论之上。士绅功能论者对于乡村权力运作的讨论主要是将关注点放在国家与士绅之间的关系之上,并没有横向考虑村落内部的其他权力结构以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此自动忽视了村落中其他的权力关系。显然,士绅功能论不能完全解释乡村权力关系的运作。
在绮罗乡的历史发展中,这些介于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乡村精英——不论是士绅还是其他身份者,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宗族利益,促使他们去参加科举从而拥有儒生身份的动力大多不是对国家效忠,而是这个身份所带来的社会地位以及地位所代表的权力。虽然洞经会的成员完全是由参与科举考试的儒生组成,但是洞经会成员的选任与国家、地方政府完全无关,同时他们所进行的活动也并不是以替国家控制乡村为目的。因此,由儒生组成的桂香会并不是王朝教化的推行者,王朝的礼仪以及国家最上层赋予他们的地位只不过是这些儒生能够成功参与到村落的仪式之中从而掌握话语权的筹码。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控制关系,乡村精英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也并不是与地方对立而趋附于国家政权的存在。
带有儒生身份的洞经会成员以本地的方式将国家的“礼”融入到地方的“俗”之中,不是国家强权的干预,而是地方社会给国家以应有的尊敬与认同,并且将之整合到地方的礼仪之中,“地方社会心中有数,知道中央权力可以为地方所用,于是屈从于中央”①科大卫:《明清社会和礼仪》,曾宪冠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112 页。。在萧公权所描述的中国乡村中,国家权力必须无处不在,这是帝国控制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但是应该看到,这个目标的实现必须有民众的主动参与,而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也确实是在村民们的“主动与共同的行动下”完成的。地方用来维护传统与利益的行为,经常以拉近自己与国家关系的方式实现,而民间性的文化创造与地方认同的营造,往往就是国家整合机制的形成过程。②刘志伟:《讲述乡村故事》,收入《借题发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123 页。此外,从绮罗乡的案例中亦可以看到,导致乡村权力变迁的因素是多元的,乡村权力存在于错综复杂、不同维度的社会关系之中,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只是这众多维度中的一维,不同时期、不同因素所形成的权力关系才共同形塑了那时的乡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