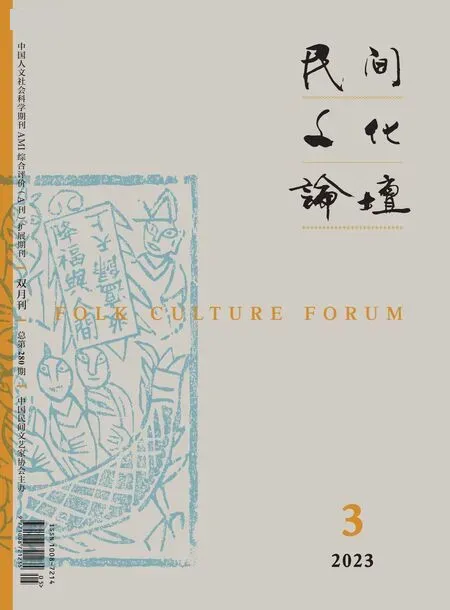走向个人生活世界
—— 民俗学研究路径与口述史学方法论再思考
蒙锦贤
英国历史学家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指出,“口述史就像历史本身一样古老。”①[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25 页。口述史学和民俗学都可追溯至远古时期的口头传统,但作为学科的民俗学比口述史学早出现了一百年。②曲彦斌:《略论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方法论的关联——民俗学视野的口述史学》,《社会科学战线》,2003 年第4 期。20 世纪60 年代,口述史学在欧美国家兴起,芝加哥社会学家们创造性地使用“直接访谈、参与观察、文献研究、绘图和统计”③[英] 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第69 页。等方法进行城市社会的生活史研究,继而口述访谈的方法被广泛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民俗学等领域。20 世纪欧洲国家的口述史学兴起与民族主义、民俗资料收集等活动紧密相关,芬兰为了系统搜集民俗学的资料而开展田野调查,还为此设立了档案馆。④同上,第75、77 页。口述史学在西方国家的诞生、发展和兴起与民俗学的资料搜集紧密相关,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较为相近,因此口述史学在学科话语的建设中,免不了强调与民俗学的和而不同之处,如唐纳德·里奇(Donald A.Ritchie)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中便专设“口述历史与民俗学有什么不同?”⑤[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邱霞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 年,第30 页。的问答,但民俗学早已习惯这种难以撇清的学科异同论调,反而更坦然地接受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积极谋求学科研究范式转向的过程中,较早地借鉴了口述史学的方法论。
口述史学与民俗学也存在明显差异。杨雁斌认为“历史与文化的交叉点则是二者最为明显的相异之处”⑥杨雁斌:《口述史学百年透视(下)》,《国外社会科学》,1998 年第3 期。。虽然民俗学和历史学都关注社会文化,但学术研究的着眼点、落脚点皆存在差异,即口述史学侧重研究文化历程,而民俗学研究文化现象,传统口述史学家的基本原则是寻找史实,而民俗学家更注重民众塑造叙事的模式。①[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邱霞译,第30 页。从研究对象来看,口述史学的确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民俗文化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由于口述史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不同,必然导致访谈的方式与内容产生差异,但二者的研究视角、方法和理念都在不断发生转变。例如,20 世纪60 年代历史学家为了研究非洲史,开发了“适用于口头传述的学术方法”②[英]约翰·托什:《口述史》,吴英译,见定宜庄等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6—17 页。,口述史学家也开始注重作为民俗学固有研究对象的口头传统。口述史学与民俗学在方法论上的互相借鉴与吸收,势必也会导致学科边界的模糊,但这种转变也有利于推动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发展。民俗学与口述史学存在紧密的交互关系,随着民俗学更加注重对个人生活世界的研究,在田野访谈的方法论层面与口述史学能够更好地实现有效对接,并有基于自身的学术理念拓展口述史学方法论的趋势。
一、民俗学与口述史学的交互作用
民俗学对何谓“民”“俗”的问题展开了持久的讨论,在学者的反复梳理中呈现出了固定的学术史脉络,最终“民”的界定被泛化为指称所有人的“公民”,而民俗学的关注对象也从民俗事象转向民众主体及其日常生活。对于人的研究必然要进行田野访谈,因此口述史学的方法论对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仅是为了弥补地方文献的欠缺,亦可完善民俗学田野访谈的方法论,正如曲彦斌所言:“口述史学的出现对于民俗学而言,既是对本学科田野调查方法论的支持,同样也提供了技术层面、方法论乃至科学观念方面的借鉴与变革。”③曲彦斌:《略论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方法论的关联——民俗学视野的口述史学》,《社会科学战线》,2003 年第4 期。口述资料的运用是民俗学与口述史学发生关联的最早途径,民俗学使用口述资料呈现地方社会的历史变迁,分析和阐释村落民众叙事的内在逻辑,抑或采用“地方文献与口述史互补”④董晓萍:《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老字号——地方文献与口述史互补的研究过程与方法》,《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8 年第1 期。的方式分析民俗事象和建构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此外,民俗学与口述史学的关系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一是在方法论层面比较口述史学与民俗学的关系,如探讨二者在性质、对象、目的、方法和方法论上的关联和差异;二是借鉴口述史学的理念,为现代民俗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三是在技术层面运用口述史学的方法开展非遗传承人的个案研究,以及对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反思。其中冯骥才等主编《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一书借鉴了口述史学在访谈、写作、保存、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原则和方法,并提出构建“传承人口述史”的理论体系,做出兼具生动性与学术性的口述史等愿景。⑤冯骥才等主编,郭平、祝昇慧、冯莉著:《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后记”,北京:华文出版社,2016 年,第415、417 页。
纵观民俗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口述史学对民俗学的记忆、传承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记忆”与“传承”是“民俗传统”的两个面向,记忆是民俗传统的表征及其传承方式,而“传承”则是民俗主体的实践行为。⑥穆昭阳:《个人实践、记忆与民俗传统的传承》,《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2 期。“记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热门关键词,以岩本通弥为代表的日本民俗学家较早地进行了相关研究,他认为记忆是民俗的本质,因此记忆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应然的正当性,于是他规避民俗、常民和传承等词汇,从“记忆”的角度给民俗学重下定义,强调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无文字的系统,只能通过访谈记录的方法转化为书面文本。①[日]岩本通弥著:《作为方法的记忆——民俗学研究中“记忆”概念的有效性》,王晓葵译,《文化遗产》,2010 年第4期。王晓葵也认为,“民俗学以口头传承和身体传承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访谈记录为主要方法,这些特点都和记忆论有亲和性。”②王晓葵:《记忆论与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 年第2期。然而,民俗学在“记忆”研究方面,习惯于采取将口述资料与文献史料互补论证的研究方式,以描写村落社会、地方社会和民俗生活的历史变迁,成了历史学研究范式的附庸,这正是岩本通弥所批判的:“妨碍记忆研究在民俗学中展开的最大障碍是民俗学和历史学、文献记录的关系。”③[日]岩本通弥著:《作为方法的记忆——民俗学研究中“记忆”概念的有效性》,王晓葵译,《文化遗产》,2010 年第4期。
“记忆”的面向是过去,往昔的民俗生活可以运用口述史学的方法实现民俗志书写与研究。在记忆研究方面,王晓葵的“灾害民俗学”可谓独树一帜,他指出:“当‘事件’通过‘记忆’转换成‘传承行为’,而成为民俗学关注的对象的时候,民俗学就有了关注灾害这样的社会重大问题的契机。”④王晓葵:《灾害民俗志:灾害研究的民俗学视角与方法》,《民间文化论坛》,2019 年第5 期。民俗学在研究灾害记忆时势必要对事件的经历者进行访谈,记录和分析受访者的个人经历和身体经验,那么口述史学的访谈方法就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田野访谈过程中也会存在许多问题,马潇通过大量的口述资料呈现了春节习俗在1949 年至1989 年的变迁,在使用口述史学访谈方法时,他意识到:“受访者的叙述中含有其自身对变迁的梳理和重构,他们以什么样的叙述方式和叙事逻辑来整理他们的记忆,可能取决于他们如何感受以及为解释这个感受而找到的因果联系。”⑤马潇:《口述记忆中的春节习俗变迁(1949—1989)》,《民俗研究》,2006 年第4 期。由于口述史学与民俗学都要解决记忆的可塑性和主观性问题,只有结合民众的个人生活史,才能认知个人叙事的内在逻辑,以寻求基本事实。
相较于记忆研究而言,民俗学更注重传承研究。民俗学以“记忆论”的方式进行传承机制的研究,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方面,口述史学的方法论具有了较为广阔的发挥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生产者多为民俗学者,所以民俗学的学术理念深刻影响着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的探讨,例如民俗学的语境研究转向,促使民俗学强调非遗的口述史研究要“借助社会语境分析,赋予非遗口述史以多层级的文化意义”⑥李海云:《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口述史研究的适用与拓展》,《民俗研究》,2014 年第4 期。。潘刚、马知遥不仅强调传承人口述史场景,而且以原生性作为“传承人口述史的评判标准”⑦潘刚、马知遥:《民俗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原则与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1 期。。又如刘铁梁提出的“身体民俗学”“日常交流实践”直接被运用于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的反思。民俗学者意识到“传承人口述史是对传承人身体性保护的重要方法”⑧马知遥、潘刚:《传承人口述史的身体经验价值》,《民俗研究》,2015 年第5 期。,强调要注重传承人的身体经验和情感,注重传承人口述史访谈的“交际沟通”和“主体间互动”,⑨王拓:《技艺与记忆:“非遗”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的建构维度——以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档案的建立为例》,《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4 年第1 期。并试图以对话、交流为核心建构了“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理论模型”⑩毛晓帅:《建构传承人口述史的理论模型——评冯骥才主编〈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齐鲁艺苑》, 2020 年第3 期。。
综上所述,不论是民俗事象研究、村落记忆研究,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民俗学领域都积极借鉴和运用了口述史学的方法论,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史研究深受民俗学研究理念更迭的影响。虽然民俗学的传承人口述史研究在学术理念上实现了自我突破,但在工作方法和细则的技术层面仍需进一步借鉴口述史学的方法论。需要追问的是,利用口述资料进行研究就是口述史学的研究吗?民俗学界显然存在乱用“口述史”概念的问题,需要谨慎对待口述史学的基本概念、方法和原则。近年来,民俗学倡导个人叙事、个人生活史、自我民族志、叙述自我等学术理念,使得走向个人生活世界的研究路径更为明晰,如何正确运用、修正和拓展口述史学的访谈方法也成了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走向个人生活世界将是口述史学与民俗学在方法论层面实现对接的有效路径,通过口述史学与民俗学的访谈方法相结合,兼顾文献研究、民族志研究的方法,民俗学将获得研究“民”和“生活世界”的有效路径与方法。
二、民俗学与口述史学的对接路径
民俗学的关注对象从民俗事象到民众主体,从集体到个人,逐渐认识到将“个人”作为田野的意义。如中村贵认为“口述史的‘田野’不仅是指具体的调查地点,而是在受访者的人生经历与记忆背后的历史与社会背景”①[日]中村贵:《追寻主观性事实:口述史在现代民俗学应用的方法与思考》,《文化遗产》,2016 年第6 期。,他反思了“民俗学的采风比口述史学更强调现场的、实时性的‘话语语境’”②曲彦斌:《略论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方法论的关联——民俗学视野的口述史学》,《社会科学战线》,2003 年第4 期。这一观点,认为物理空间虽然会对访谈效果产生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了解受访谈者的文化背景,从而更好地共同创造口述资料。由此他提出“作为‘方法’的口述史更着重个人的‘主观性事实’,而不是阐明‘客观事实’”③[日]中村贵:《追寻主观性事实:口述史在现代民俗学应用的方法与思考》,《文化遗产》,2016 年第6 期。,并试图将日常生活的研究延伸至民众的精神层面。这暗含着一种“眼光向内”的视角转变,从共同体、集体和空泛的“民众”落实到富有情感的个人身上,研究的范围也会从民众生活的地方社会,转变为个体生活的宿舍、家庭或工作单位,呈现更出更加微观的社会结构。这种学术主张与施爱东所讨论的“微民俗”和“低微理论”较为相近,只有着眼于社会毛细血管的最小单位,即“个人”的研究,才能形成具有方法论的学术理论,而非抽象的学术主张。④施爱东:《讲故事的民俗学:非常事件的正常解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3 期。
口述史学对于个人经历的诉求一直是非常明确的,民俗学却较少地将眼光停留在个人身上,倾向于透过个人或群体呈现外在的“生活世界”,抑或从个人叙事中抽离出建构村落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的要素。门田岳久等认识到“传统”之下的个人总是被共同体掩盖的事实,“当人们从共同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个体’的身份生活时,这个问题(自我认同)才突显出来。”⑤[日]门田岳久著:《叙述自我——关于民俗学的“自反性”》,中村贵、程亮译,《文化遗产》,2017 年第5 期。步入当代社会的个人一定程度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个人能够认知自我行为的实践意识,而非源于无自觉的惯习。个人叙述自我的意识逐渐突显,使得田野访谈的主体与客体、主动与被动关系变得更为动态和复杂,对当下与未来的民俗学田野访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正是菅丰提出“新在野之学”⑥陆薇薇:《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民俗研究》,2017 年第3 期。的现实基础。
民俗学一直在借鉴和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而口述史学与民族志的区别,除了研究对象有土著(原始人)和普通人(常民)之别,还在于研究方法上对个人关注与呈现的程度。民族志的调查方法可以使用观察、记录和分析的方法进行深描,而口述史学是“对某些个体之过去的口述证词即记录与解释”①高琴:《民族志和口述史的内在类同》,《民俗研究》,2001 年第1 期。,所以口述史学家必须与当事人进行互动式访谈,口述资料的使用也得经过受访者本人的准许。虽然诞生较晚的口述史学借鉴了人类学的田野访谈方法,但在强调普通人的主体性,注重个人的价值方面,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反而是受到口述史学的启发。口述史学创造的观照个人或群体的较为系统、科学的访谈方法和工作原则,至今仍被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广泛借鉴和运用。虽然民俗学推崇深入访谈,但最终的文本对个人的呈现是较为欠缺的,更多是去呈现从个体叙事中剥离出来,再生产出反映集体记忆、共同体文化传统的文本。当然,随着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民众的主体性已经备受关注。王加华提出个人生活史的研究路径与方法,进一步将“个人”从“民众”的概念中解放了出来:“事实上,作为一种由民众所承载的整体性生活文化,只有将‘俗’放到具体的民众身上,才能真正做到还‘俗’于‘民’,才能做到对民俗主体的真正观照。而个人生活史研究,恰可以将破碎、零散的民俗事象重又聚合于作为主体的‘民’身上……因此,由‘群体’转向‘个人’,或许是未来民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②王加华:《个人生活史:一种民俗学研究路径的讨论与分析》,《民俗研究》,2020 年第2 期。
实际上,民俗学聚焦于“个人”的研究路径并非偶然,民俗学者早已在田野中发现了民众主体的能动性,并认识到个人生活史的重要性。刘铁梁在提出“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时曾指出,“结合个人生活史的书写,能在最大程度上把人们的感受表达出来,也就是感受的民俗志。”③刘铁梁:《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 年第2 期。他基于“身体民俗学”的视角,提出“个人叙事”的概念,进一步强调民俗学对于“个人的关怀”④刘铁梁:《身体民俗学视角下的个人叙事——以中国春节为例》,《民俗研究》,2015 年第2 期。,又基于“实践民俗学”的视角,提出了“交流式民俗志”的概念,并将“个人叙事”与“口述史”的概念作了区分:
近些年受历史学影响,我们有时爱用“口述史”这个词指称我们在田野作业中通过访谈得到的一种资料,即受访者讲出的个人生活经历以及对周围社会中人和事的所见所闻。民俗学最近开始把这种口述资料叫做“个人叙事”,认为它不仅是历史研究所需要的资料,而且是日常交流实践的一种话语类型和个人记忆历史的方式。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反过来也影响了访谈现场交谈内容和所记录下来的叙事文本上的差异,无论是话题方向、叙述框架,还是细节描述和表达的灵活性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⑤刘铁梁:《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民俗研究》,2019 年第1 期。
学界对“口述史”的定义存在颇多争论,主要有四种不同维度的界定,即历史、社会、方法和资料。⑥朱义明:《口述史的概念厘定与研究向度》,周晓虹、朱义明、吴晓萍:《“口述史研究”专题》,《南京社会科学》,2019 年第12 期。刘铁梁论及的“口述史”概念明显指向了资料的维度,而非获得口述资料的访谈方法。基于学科研究取向的不同,强调两种口述资料在内容上的差异无可厚非,但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民俗学的“个人叙事”概念,将个人的关怀从“感受”拓展到“交流与对话”,从而与口述史学所强调的“互动性原则”不谋而合。
口述访谈与一般闲谈或谈话的形式很不一样,口述访谈具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它是一个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双向交流的过程,而非研究者单一的研究过程。即便是在访谈的口述过程中,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也需要通过不断的、持续的思想互动和感情交流,相互配合,才能实现对对象的研究,建构出被研究者话语的意义。①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44 页。
口述史学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双向交流”过程,而不是研究者单向的研究过程,或被研究者单向的叙述活动。因此,民俗学界对于“个人叙事”的阐述使得作为“一个连续体相反的两端”②[美]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3 版),邱霞译,第30 页。的民俗学与口述史学实现了对接,二者在访谈对象(个人)和方法(互动式访谈)上实现了统一,这是二者在方法论层面上实现有效对话的条件,也是民俗学为口述史学提供自身的理论创见的基础。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叙事”被学界归属于口述史学的范畴,如黄永林、韩成艳认为:“口述史与口述传统,前者是经历,是个人叙事,而后者则是记忆,是集体记忆和表述。”③黄永林、韩成艳:《民俗学的当代性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2 期。而刘铁梁对“个人叙事”的概念界定,不仅囊括了口述史和口述传统,甚至将日常实践的交流话语也纳入进来,成为了更宽泛的叙事范畴。通过访谈者与被访谈者双向交流互动,共同生产口述资料的访谈取向有两种:一是具有文化取向的民俗学访谈,通常借助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方法,注重当下的文化现象;二是具有历史研究取向的口述史学访谈,注重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尤其是民俗事象消亡或传承的历史脉络,从文化历程中更好地理解当下民众的叙事与行动逻辑。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俗学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实物资料、文献资料与民众的口述资料同等重要,民俗学访谈与口述史学访谈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在同一语境中互相结合、交叉使用,既关心民众的生活境遇与个人情感,又注重个人生活史与村落传统,同时兼顾过去与当下、主观与客观、文化历程与文化现象,最后在叙事辨伪与话语分析的基础上,更好地研究个人及其生活世界。
三、民俗学对口述史学方法论的拓展趋势
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逐渐泛化为“日常生活”等抽象的概念之后,如何着手研究成了一个难题,张翠霞认为:“尽管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学科范式转换中一直强调对文化主体的关注和研究,但究竟如何研究民俗之‘民’,如何去认识和理解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民俗学至今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与方法。”④张翠霞:《常人方法学与民俗学“生活世界”研究策略——从民俗学研究范畴和范式转换谈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5 期。实际上,作者提供的“常人方法论”对民俗学研究至关重要,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常人方法论“不仅关注普通人,而且将普通人看作是具有行动力的个人”⑤同上。,对“个人”及其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关注,能够使得田野调查的方法更加具有切实可行的探讨方向,即把握动态情境中的个人行为及其日常生活,诸如常人方法论的“破坏性试验”“索引表达”“会话分析”和“陌生化”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直接指向田野访谈的方法论的“会话分析”。
“会话”意味着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对话与交流,“会话事实”也会因交流情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研究者要获得符合实际情况的有效信息,必须了解受访者的个人生活史和社会背景,充分考虑影响访谈的各种因素。因此,研究者与具有“觉识性”的个人展开对话、交流与互动时,都要注重受访者的“生命状态”,包括“个体的经历体验、个体的自我认知、个体的情感状态、个体的自我塑造、个体的生命感受、个体的自我认同等方面”①朱义明:《口述史的概念厘定与研究向度》,周晓虹、朱义明、吴晓萍:《“口述史研究”专题》,《南京社会科学》,2019 年第12 期。。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个人,无时无刻不被结构于历史和社会之中,个人创造和建构历史的能动行为具有强烈的“自反性”,对个人的生命状态及其生活语境进行访谈尤为重要,恰如刘晓春所说:“以‘语境中的民俗’为研究范式的学者,则开始注意到传承民俗生活的活生生的人。日常生活中的人、民俗过程中的人、个人的生活史、个人的民俗知识等等。”②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 年第2 期。
走向个人生活世界只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并非最终的研究目的。口述史学家借助个人对历史事件的经历、感受、记忆和评价来印证历史史实和解释历史,并书写出鲜活、生动的历史,社会学家则是从社会的视角去发现个人,揭示社会变动对个体的生命历程的影响,那么民俗学通过个人生活史去探讨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如何研究“民”“民俗”和“生活世界”的答案,王加华给出了回答:“从操作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对俗民个体生命历程及其生活‘语境’做多方位的深入访谈、参与观察与尽可能全面的了解,然后以其标志性特征为主线进行呈现,最终在此基础上透视其背后的整体社会生活与文化。”③王加华:《个人生活史:一种民俗学研究路径的讨论与分析》,《民俗研究》,2020 年第2 期。将田野调查的对象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是为了寻求具有可操作性、可行性的研究方法,从而探讨历史事实、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文化等,这正是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路径,犹如郭于华借鉴布迪厄的理论提出“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④郭于华:《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诉苦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6 页。,阐明了个体的社会性,也启发我们关注个体是研究社会的路径与方法。
民俗学在个人访谈与研究的问题上,能够为口述史学提供什么方法论呢?21 世纪以来,中国民俗学者已经具备较强的理论意识,在田野调查、民俗志书写与研究方面更强调民众的主体性,倡导构建良好的田野关系,深入民众的内心世界。例如,张青仁在评价《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一书时说:“同是作为民众感受的表达,民俗与口述史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与民俗一样,包含个人感受的口述史正是研究者理解民众、感受生活的基本方式。基于此,在《杂吧地》一书中,岳永逸不再纠结于口述史的主观与客观、真与假的问题,而是以一种人文的姿态倾听这些在杂吧地上谋生的艺人的声音的。”⑤张青仁:《口述史、人文关怀与学术反思——评〈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民俗研究》,2012 年第3 期。岳永逸提出生命参与式的口述史书写范式,强调访谈者与受访者互为主体性,研究者可以在口述史书写中表达人文关怀,口述者的自我认同也能得到尊重,充分体现出民俗学者对口述史学研究范式的拓展与创新。历史学、社会学和民俗学都关注田野中的“个人”,但历史学更注重客观史实,社会学更关注社会事实,所以二者在田野访谈中追求“中立”“不介入”的原则,访谈者通过精心策划问题,开展结构式或半结构式访谈,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导角色,在无结构式访谈中尽量避免被访谈者的情感倾述。实际上,历史学、社会学的口述访谈刻意祛除的“情感”维度,恰好是民俗学田野访谈的着力点,一些民族志的书写已经认识到情感阐释的难能可贵之处。
近年来,民俗学注重受访者的情感表达,追求有温度、贴心的、共情的田野,张士闪提出“有温度的田野”,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开展了六届学术工作坊,①石玉洁:《“论道稷下:当代田野研究的祛魅与多样化”论坛顺利举办》,《民俗研究》,2020 年第1 期。对于访谈关系、对话与交流等问题,民俗学具有为口述史学提供理论创见的正当性。例如,刁统菊长期从事田野方法论教学与实践,早已对个人、自我十分关注,她通过自我民族志的方式反思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学术伦理问题,②刁统菊:《民俗学学术伦理追问:谁给了我们窥探的权利?——从个人田野研究的困惑谈起》,《民俗研究》,2013 年第6 期。还基于对22 位民俗学者的访谈和个人经验,从性别视角探讨女性民俗学者在田野作业中的优势与劣势,③刁统菊:《女性民俗学者、田野作业与社会性别制度——基于对22 位民俗学者的访谈和个人的田野经验》,《民族文学研究》,2017 年第4 期。继而提出感受、入户的访谈方法,强调通过一个个的“个人故事”引向社会全体的分析路径。④刁统菊:《感受、入户与个体故事:对民俗学田野伦理的思考》,《民俗研究》,2020 年第2 期。女性民俗学者注重个人经验、兼具“自反性”的田野研究,将助益于田野访谈方法论的构建,解决女性访谈者如何趋利避害等问题,女性民俗学者“选择关注一些不被男性学者所重视的与日常性、情感性相关的信息作为材料,结合个人经验主体性的描述与分析来探讨这些琐碎细小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性、文化性的指涉”⑤张晓佳:《民族志中的女性经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7 页。,也将拓展口述史学的情感研究取向。
综上所述,历史学、社会学的访谈追求中立、不介入的原则,但文献记载、传记、自传都无法避免社会记忆、讲述机制带来的真实性悖论,只能通过多重验证和叙事分析的方法不断贴近史实与社会本质,而在探求主观性事实、情感研究的方法论上,民俗学能够为口述史学提供理论创见。随着民俗学的理论意识不断增强,田野访谈的方法论也在不断深入,民众的主体性在语境研究、日常生活研究的过程中不断被突显,“个人”的发现也使得访谈方法论更加注重主体间的互动性与情感性。民俗学提倡具有人文关怀的田野调查与研究范式,提出理解、对话、感受、交流、共情、贴心、有温度等充满温情与正能量的学术概念,在访谈关系、访谈方法、田野伦理和书写范式的方法论创新和个案研究方面,将为构建作为跨学科方法的口述史学贡献自身的理论智慧和学科力量。
结 语
口述史学的研究一直聚焦于个人经验,个人记忆是亲历者对于社会历史的真实认知、情感体验和价值判断,可以作为论证社会事实的根据,也能对档案资料进行证伪。个人的生活世界被结构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个人的观念、价值和行为受到集体行动、社会结构的影响和制约,但“人们的联结和共同行动同样可以对结构进行再生产”⑥周海燕:《个体经验如何进入“大写的历史”:口述史研究的效度及其分析框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6 期。。因此,个人叙事能透析个人与群体、社会的互动关系,通过个体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思考、选择和行动,能够理解群体认同与行动的逻辑。只有将个人叙事与集体行为、社会事件和“大历史”联系起来,才能检验和体现个人叙事的价值。
虽然历史学、社会学和民俗学都经由走向个人生活世界的研究路径,探讨文字文献之外的可能性事实,但三个学科的研究旨趣各不相同:历史学注重追求个人叙事背后的历史史实,社会学关注群体或共同体的文化现象,比如,知青群体、农民工群体、妇女群体等,而民俗学更多地是呈现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案例,比如,基于某某村某赤脚医生、某木工的个人生活史,探讨其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生存境遇或生存策略等。虽然民俗学的田野研究见到了活生生的个人,但不拘泥于呈现琐碎的个人经历才是关键,研究者需要利用“共同体”的桥接作用,抓住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互动关系,从共同体的视角进行个人生活史的研究,将有益于帮助我们理解个体记忆的建构与重塑等问题。
走向个人生活世界并非民俗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而是作为一种方法,个人生活史的提出,为究竟如何研究“民”和“生活世界”等抽象的命题提供了具有操作性、可行性的路径。中国民俗学在田野访谈、民俗志书写与研究方面逐渐突显民众的主体性,在探讨如何做好语境中的田野访谈时,进一步提出注重“主观性事实”和“情感”研究的新取向,在如何建立良好的田野关系、如何与民众进行交流等问题上具有提供访谈方法论的潜力。近年来,田野访谈的方法论探讨在民俗学领域逐渐升温,但多为宏观上的学术倡议,虽然学界已经致力于构建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但民俗学可提供的方法论还存在诸多不足,仍需借助走向个人生活世界的突破口,继续借鉴、反思和拓展口述史学的方法论,进一步形成独具学科特色且具有广泛借鉴意义的田野研究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