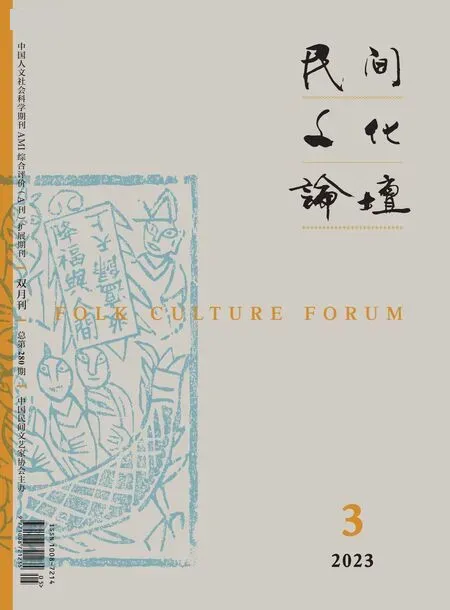盘活学术遗产:经典译读的几点说明
岳永逸
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或许是当下不少学术期刊开设有翻译国外学者学术论文专栏的原因。对于中国人用外文写的学术专著,学界也有回译成中文的传统。然而,无论发表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人用外文写的堪称经典的学术论文,一直少有翻译。当然,对这些国人用外文写的学术论文,同行或者也难免有“骗骗外国人”的先在认知。1948 年,对发表在辅仁大学外文刊物《民俗学志》(Folklore Studies)上中国学者的文章,杨堃(1901—1998)就曾有“似仅对于不能阅读中文的读者,方觉有用”的淡然。①杨堃:《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六期,1948 年。然而,不论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此类论文中不乏佳作,甚或经典。这就是眼前这组译文“剑走偏锋”的原因。
作为国内历史悠久且重要的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专业期刊,《民间文化论坛》在2019 年第1 期刊载了赵卫邦1942 年发表在《民俗学志》创刊号上的《扶箕之起源及发展》(“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the Fu Chi”)的中文译文,以此再现学术过往,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秉承这一办刊传统,本次推出这组“经典”译文分别来自于20 世纪前半叶燕京大学(燕大)的外文刊物《燕京社会学界》(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作者分别是学界前辈李安宅(1900—1985)、赵承信(1907—1959)和廖泰初(1910—2000)。
1935 年,辅仁大学创办了《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学界对于这一外文刊物研究颇多,甚至可以说是海内外汉学研究的重头。而同为在京创办的外文刊物,对稍晚些的《燕京社会学界》和《民俗学志》,学界的研究则付之阙如。①要提及的是,张志娟曾以《民俗学志》为中心,梳理过辅仁大学的民俗学教学和研究;《民俗学志》也是张爽梳理中国人类学辅仁传统的基本材料;顾钧则介绍过《燕京社会学界》的基本情况。分别参见张志娟:《北京辅仁大学的民俗学教学与研究——以〈民俗学志〉(1942—1948)为中心》,《民俗研究》,2014 年第5 期;张爽:《中国人类学的辅仁传统(1925—1952)》,卓新平编:《基督宗教研究》,第29 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21 年;顾钧:《英文〈燕京社会学界〉管窥》,《中华读书报》2021 年1 月6 日第14 版。
二
作为燕京学派的游离者,不可忽视且独树一帜的社会科学家,李安宅在民俗学、语言学、美学、哲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工作等多个学科都有着重要的贡献。②岳永逸:《“口耳”之学:燕京札记》,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 年,第171—233 页;岳永逸、熊诗维:《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工作的架构与实践:以蒋旨昂为中心》,《社会建设》,2022 年第2 期。就民俗学而言,1929 年李安宅就开始翻译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1884—1942)的论文《巫术科学与宗教》(“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并在马氏的亲自授意之下将该文与马氏的《原始心理与神话》(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合并翻译出版。③李安宅:《人类学与中国文化:〈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译本序》,《社会研究》,总第一一四期,1936 年。这即后来反复再版的经典译本——《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④Bronislaw Malinowski:《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
1931 年5 月,李安宅翻译出版了弗雷泽(J. G. Frazer, 1854—1941)《金枝》(The Golden Bough)的第三章,书名是《交感巫术的心理学》。⑤[英]弗兰柔:《交感巫术的心理学》,李安宅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年。该书包括巫术的原理、感致巫术或模仿巫术、染触巫术和术士的进步四个章节。事实上,1930 年,李安宅就按此章框架和主旨发表了《巫术问题的解析》,内容包括巫术的原理与种类、感致巫术、染触巫术和巫术在历史上的地位四个小节。⑥李安宅:《巫术问题的解析》,《社会问题》,第一卷,1930 年第1 期。他对《金枝》这一核心章节的翻译和“交感巫术”“模仿巫术”“染触巫术”等核心概念的精准翻译,为后来中文学界对《金枝》的进一步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20 世纪30 年代中期的燕大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而言,李安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1936 年,访美归来的李安宅同时担任了燕大社会学系中、英文机关刊物《社会学界》和《燕京社会学界》的主编。1938 年,在燕大法学院给本院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三系本科生编订的《社会科学概论选读》这本六百多页的读本中,李安宅的《语言思想与事物》《巫术与宗教》《巫术的分析》《介绍社会科学集成》四篇在列,⑦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编:《社会科学概论选读》,燕京大学法学院印行,1938 年,第1—8、418—426、562—567 页。而吴文藻(1901—1985)仅有《社区的意义》一篇入选。
本次翻译了李安宅的《中国社会科学实地研究的必要性》(“Notes on the Necessity of Field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 in China”)。这篇与田野调查有关。对当下学界更盛行的“田野调查”或“田野研究”,李安宅当年更常用的术语是“实地研究”。对他而言,实地研究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方法论;而且中国不仅仅是研究的对象,更是能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科学前进的一种方法。该文是1938 年李安宅在《燕京社会学界》创刊号给“随感录”(Notes and Queries)①将“Notes and Queries”意译为“随感录”的原因将另文专述。在此,要特别感谢周越、梁永佳、刘春勇、游自荧、钱霖亮和熊威等海内外师友的帮助和启迪。专栏写的首篇文章。对该专栏的主旨,李安宅在其专文前写有如下说明:
本期刊此专栏旨在为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一个阵地(clearing house),或者说交流平台,并希望由此能在社会科学中产生某种合作精神,以及在研究领域出现更多的协调努力。任何人均可通过这一专栏提出问题,以非正式的方式形成新的想法,就关心的科学资料或研究项目进行简短的交流。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个人或机构的消息,在此都有一席之地。编者在本专栏率先尝试性地阐述了对中国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的看法,希望我们刊物的订阅者能就此在期刊上展开讨论。②Li, An-che.“Notes on the Necessity of Field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 1, No.1 (1938), p. 122.
“率先尝试性地阐述对中国实地研究的看法”,完全是李安宅谦虚的表达。此前,李安宅不仅仅深深震撼于马林诺夫斯基完全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志,而且还有了亲身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对祖尼印第安人进行为期三个月调查的具体实践。③Li, An-che.“Zuñi: Some Observations and Quer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39, No.1 (1937), pp.62-76.他也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对印第安人进行科学研究的中国人,并让美国同行震惊,以至于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 1881—1955)称赞他:“You gave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everyone a Chair.”④陈波:《李安宅:回忆海外访学》,《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6 辑,2010 年。因为对马氏田野调查方法的推崇,他不仅翻译其《巫术宗教神话与科学》,还不遗余力地翻译了马氏的《两性社会学》(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⑤[英]B. Malinowski:《两性社会学》,李安宅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而对重在测量的“体质人类学”多少有些不以为然。
在《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译本序”中,李安宅反复强调用人类学实地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和边疆地区,以有效服务于国家的必要性。他认为,重“古董”的考古学和重测量、数据的体质人类学,远没有直面真人及其生活的文化人类学重要,并将实地研究郑重地称为“实学”。⑥李安宅:《人类学与中国文化:〈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译本序》,《社会研究》,第一一四期,1936 年。在对祖尼印第安人的实地研究中,李安宅明确声称要练就的是一种“文化洞察力”(a cultural perspective)。他写道:
一个人只有学会区分以孤立的文化现象作为判断依据与以各种综合性的相关社会关系作为判断依据的差别,将自己的文化模式绝对化,尊重另一种文化模式,承认它的存在与意义的差别、旧的机械论物竞天择的本质与外来入侵文化体系的渗透张力的差别,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文化洞察力和做到客观公允。⑦李安宅:《祖尼人:一些观察与质疑》,张叔宁译,见乔健编著:《印第安人的诵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49 页;Li, An-che. “Zuñi: Some Observations and Quer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39, No.1 (1937), p.63.
在《中国社会科学实地研究的必要性》中,李安宅强调的群体协作且调研者互为主角而展开的整体性的田野研究,也充分落实到稍后赵承信、杨堃、黄迪(1910—?)等主导的燕大社会学师生在平郊村这个“社会学实验室”的实验之中。不仅是社会学系,郑林庄(1908—1985)等经济学系的师生也深度参与到平郊村的社会学实验之中,而燕大理学院的学生在实验启动时就参与了对平郊村地理位置的测绘。①就完全以平郊村这个社会学实验室为研究对象的19 篇燕大学士毕业论文的具体统计,可参阅岳永逸《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201—202 页。
1948 年,有了在甘肃、四川以及云南等地更加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之后,李安宅在《太平洋季刊》(Pacific Affairs)上发文时,就已经不再仅仅是呼吁强调实地研究——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而是直接将“中国”视为能推动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进步的“一种基本方法”。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李安宅在该文中已经明确提出了指向公民原则(civic principle)的中国发展应有的“多元一体”(unity in diversity)模式。同时他也强调:在中西的互动中,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新的技术技能和在比家庭或部落更大的社会群体中共同生活的能力的同时,并非一定要抛弃传统的社会遗产;而在丰富内心的方式上,西方则应向中国学习,从而平衡其对商业成功的过度强调。
对他而言,公民原则应该是以家庭主义(familism)为轴的汉人社会和以部落主义(tribalism)为基础的边民社会两种本土文化的共有目标。在两种社会实现这一共有目标的过程中,基于比家庭主义更广泛的部落主义,可能会刺激汉人社会增强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从而更广泛地接受民间歌舞等边疆文化,使自身变得丰富起来。当然,汉人可以为边民提供现代教育和医疗技术等。因此,李安宅明确指出:
与其分裂集约化农业和游牧业,或者以牺牲其中任何一种文化为代价统一两种文化,不如工业主义和公民原则将综合所有这些有用的传统特征从而创造出新的综合体。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越多元,通过相互依存而不是通过统治实现的政治—经济统一的前景就越可观。基本模式将是“多元一体”。②Li, An-Che. “China: A Fundamental Approach”, Pacific Affairs, Vol. 21, No. 1 (1948), p. 63.
三
与李安宅一样,对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燕大社会学而言,1930 年在燕大社会学系本科毕业的赵承信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是20 世纪前半叶中国重要的社会学家与人口学家。本科毕业后,赵承信自费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次年,他转入密西根大学。1933 年4 月,赵承信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从分隔到整合:对中国的区位学研究》(“An Ecological Study of China from Segmentation to Integration”)。③Chao, Ch'eng Hsin. An Ecological Study of China from Segmentation to Integra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33.毕业后,他回到母校燕大任教。卢沟桥事变后,赵承信接替南下的吴文藻成为燕大社会学系主任,全面主导了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前八家村)的建设和实践。1938 年,他接替去了甘肃的李安宅,编纂完成燕大法学院的《社会科学概论选读》。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与张东荪(1886—1973)、赵紫宸(1888—1979)、洪煨莲(1893—1980)、陆志韦(1894—1970)等燕大同仁被日寇拘押达半年之久。出狱后,根据亲身经历与观察,赵承信写出了融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于一体的《狱中杂记:一个社会学的诠释》。①赵承信:《狱中杂记》,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 年。同样是写被日寇关押的狱中经历,神学家赵紫宸的写作就与赵承信明显不同。参阅赵紫宸:《系狱记》,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8 年。1945 年,燕大在北京复校后,北上的林耀华(1910—2000)出任社会学系主任,赵承信则接手法学院院长。同时,他主导的平郊村这一社会学实验室的工作也得以快速恢复。
之所以在《民间文化论坛》这本以民俗学为本位的刊物译载赵承信的这篇《作为社会学实验室的平郊村》②Chao, Ch'eng-Hsin. “P'ing-chiao-tsun as A Social Laboratory: The Process of Social Cooperation in the Solution of Similar and Common Problems of the Population of A Peiping Suburban Villag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 IV, No.1 (1948),pp.121-153.,原因有二:1.与李安宅一样,赵承信强调实地研究的重要性,而且比李安宅更进一步地将研究者自身田野调查的历程纳入观察和研究的范畴。2.在他主导的1938—1941 年平郊村这个社会学实验室的前期,由于杨堃加盟燕大社会学系,推进社区—功能论在燕大师生研究中落地的平郊村这一社会学实验室同时,也是杨堃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民俗学”的演练场。在相当意义上,正是这一实验室实验工作的有序展开,中国民俗学的“社会学的民俗学派”才最终得以形成。对此,早在1948 年,杨堃就有着清楚的自白。③杨堃:《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六期,1948 年。对杨堃指导的社会学的民俗学的系列成果的进一步研究,可参阅岳永逸:《庙宇宗教、四大门与王奶奶:功能论视角下的燕大乡土宗教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8 年第1 期;《器具与房舍:中国民具学探微》,《民族艺术》,2019 年第4 期。关于社会学的民俗学更系统的研究,可参阅岳永逸:《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年。
换言之,要了解今天众所周知的李慰祖《四大门》④李慰祖:《四大门》,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 年;《四大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亦可参阅Li, Wei-tsu. “On the Cult of the Four Sacred Animals(Szu Ta Men 四大门) in the Neighborhood Of Peking”, Folklore Studies, Vol.7 (1948), pp.1-94.这样的社会学的民俗学经典究竟怎样生产出来的,赵承信关于平郊村这个社会学实验室的设计、展开的总结、自省就重要莫名。而且,正如我曾指出的那样,燕大师生对平郊村的群体性研究实际前后持续了近二十年,一直到1950 年才完全终止。时至今日,无论对侧重经验研究的中国社会学还是中国民俗学而言,这都是罕见的。⑤岳永逸:《为了忘“缺”的记忆:社会学的民俗学》,《读书》,2021 年第6 期。但是,除对诸如《四大门》等当年平郊村这一社会学实验室个别实验成果作为资料引用,以浇自己胸中块垒且不多的学术著述外,⑥如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127—173 页。学界对作为学术事件和学术史实的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都少有研究。
1948 年,赵承信还用中文撰写了一篇回顾平郊村研究进程的文章《平郊村研究的进程》。⑦赵承信:《平郊村研究的进程》,《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1948 年。虽然是同一主题,但中文和英文文章却各有侧重。英文文章不仅写作时间的跨度长,而且基于已有的调查研究对作为社会学实验室的平郊村有着更加充分的观察与呈现,尤其是呈现了平郊村“解决相似和共同问题中的社会协作过程”,以说明动变中的平郊村的非自足性。其基于饥饿(因缺乏而生的身体不适感)、社会秩序、神圣秩序、传承与变革、社会交往、城市化、个体化这八个方面的写作架构,紧扣了平郊村这个北平郊区村落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演进的真实图景。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城乡关系、个体心性,对汉人社会的民俗志或民族志的写作而言,其将人文区位学化为无形的“裸写”风格也不无典范意义。此外,这篇英文文章对1945 年前后两个阶段对平郊村田野调查展开方式的不同也有明确的说明,并多了中文文章中少有的详实案例,诸如如何维系快要中断的田野关系、把社会学课堂开设到田野现场的快慰等。
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在目前学界难得的对平郊村这一学术史实的两项扎实的研究中,著者均未曾注意到赵承信本人对平郊村社会学实验总结与反思性的英文论文。①杭苏红:《精神与物质:民国时期乡村家庭研究的另类路径——杨堃及其学生的平郊村调查》,《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6 期;安邵凡:《重访平郊村——20 世纪40 年代华北城郊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呈现与历史学细读》,《开放时代》,2020 年第3 期。就当下学界多点开花且不乏群体性长期蹲点的田野调查而言,赵承信对平郊村这一社会学实验室的“自白”除不言而喻的史料性之外,应该也不无学术、学理上的参考价值,就是对于当下高校的社会学的教学也不无借鉴意义。
同是田野调查,廖泰初1948 年刊发在《燕京社会学界》上的《抗战中和抗战后的成都学徒》②Liao, T’ai-ch’u. “The Apprentices in Chengdu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 IV, No. 1 (1948),pp. 89-106.一文,明显更类似民族志或者说民俗志,主要是经验事实的直接呈现。无论对于当下的社会学还是民俗学而言,廖泰初这一名字显然较之李安宅、赵承信两个名字更加陌生。确实,廖泰初主要研究教育,本科和硕士都毕业于燕大教育学系。但是,与其他同时代多数研究教育的人不同,廖泰初始终在有意识地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
1935 年,廖泰初在燕大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定县的实验:一个历史发展的研究与评价》。③廖泰初:《定县的实验:一个历史发展的研究与评价》,燕京大学研究院教育学系硕士毕业论文,1935 年。该文是对晏阳初掌舵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全面评估,不乏锋芒。为了更好地完成这篇论文,他专程到定县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进行参与式观察。在稍后对自己硕士毕业论文研究方法的回顾中,廖泰初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还将田野调查“硬”译为“居住调查法”。④廖泰初:《我研究“定县实验”的方法和经过》,《社会研究》,第六十八期,1935 年;《从定县的经验说到农村社会调查的缺欠和补救的方法》,《社会研究》,第一〇三期,1935 年;《再论“居住调查法”答叶君》,《益世报》1936 年6月18 日,第十二版。在山东汶上县调查近一年后,廖泰初在1936 年完成了《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一书。该书同样是基于“社区”(community)的研究,且将教育,无论是私塾还是新式学堂——洋学,都视为一种社会制度进行整体性研究,强调其功能。⑤廖泰初:《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自序”,内部印刷,1936 年,第4 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廖泰初到了在华西坝复校的燕大,同时任职于教育学系和社会学系,继续研究他一直关注的教育问题,将在汶上县私塾和新学堂的对比研究拓展到成都。⑥Liao, T’ai-ch’u. “Rural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A Study of Old-fashioned Chinese Schools (Szu Shu) in Shantung and Szechuan”,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 IV, No. 2 (1948), pp. 19-67.显然,廖泰初对成都的学徒的兴趣,与他对那个动荡年代始终处于变迁中的中国教育现状的思考紧密相关。对廖泰初而言,(小)手工业、作坊中的“师徒”,即学徒制,无疑是有着价值和意义并不同于私塾和新学堂的另一种教育制度。而且,他明确指出:这种教育不仅是要学习某种赖以谋生的具体的技术或技艺,更要学习“一切的基础——生活的艺术(the art of living)”①Liao, T'ai-ch'u. “The Apprentices in Chengdu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 IV, No. 1 (1948),p. 100.,即更要学习如何做人或者说人生的态度。所以,对抗战中和抗战后成都的学徒的研究,廖泰初同样是基于社区和个体生命历程有序展开的。
对当下正在展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运动而言,身体技艺以及记忆的传承与保护几乎占据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半壁江山。廖泰初七十多年前对学徒制的观察,无疑给我们当下的非遗运动提供了难得的历时性资料。而且,在文尾他明确指出:尽管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和手工业不冲突,但是仍须“采用一种全然不同的视角,培养年轻的技术工人和商人,以更好的合作与组织发展出更好的生产,从而迎接正在到来的机器时代”②id. p. 106.。这些识见,无疑是具前瞻性与中肯性的。当然,廖泰初这些带有世界眼光的前瞻性认知在那个年代并不是孤例。1945 年,廖泰初的燕大校友,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蒋旨昂(1911—1970)就有着类似的思考。蒋旨昂认为:小手工业、手工艺与机器生产,是“相成”互补的关系;配合调适、渗透普遍和吸收采用,应该是发展我国原本有着价值的小工业的三大原则;然而,本着人本主义精神,用机器生产取代只为极少数人享乐而制作的哪怕美的手工业品,从而让多数人有较长时间的自由以享受丰满的人生,也是发展小手工业——欢迎机器生产的应有之义。③蒋旨昂:《发展吾国小工业之途径》,《中农月刊》,1945 年第11 期。
四
虽然完全是不同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但与赵承信对平郊村村民处理相似和共同问题中的社会协作过程的描述和对平郊村的非自足性的强调一样,廖泰初对“更好的合作与组织”的工人和商人的期待、蒋旨昂对多数人有较长时间的自由以享受丰满的人生的愿景,都不同程度地指向了将中国视为世界社会科学的一种基本方法的李安宅所强调的“公民原则”。他们都在或明或暗地强调自己研究对象的世界性、变动性,强调中国走向工业社会、都市文明的必然趋势,强调“多元一体”模式对发展前行的应有之义。换言之,这些前辈基于实地调查的脚踏实地的学术写作,不但有着“观天下”的宽广的国际视野,还有着促进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富足安康的“忧天下”的厚重的人本主义情怀。这一人本主义情怀,使得20 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学有着浓郁的人文学底色。在那目的明确的数十年的本土化历程中,与民俗学、人类学交相互融的中国社会学,既没有当下中国主流社会学唯我独尊的楚河汉界,也没有以“上帝之眼”对科学属性的自我标榜。④在对“利费之辩”这一20 世纪晚期巅峰对决的精彩释读中,梁永佳对社会学的人文性与科学性有着细腻的诠释。参阅梁永佳《殊途同归:费孝通与利奇之辩》,《民俗研究》,2022 年第6 期。当然,李安宅、赵承信、廖泰初、蒋旨昂他们当年看重的理想化的公民原则,是以20 世纪前半叶发达的工业国家、都市社会为参照的。
继往开来!学术自信、自立和自强应该从熟悉学术遗产开始。如果外国人的中国民俗研究可以丰富充实中国民俗学的内涵与外延,⑤岳永逸:《“土著”之学:辅仁札记》,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 年,第83—94 页。那么上述这些中国人展示自我,主动与外国学界交流互动,且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优秀的非汉语写作就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这就需要“洋为中用”和“出口转内销”的并行不悖,需要古今中西学术遗产的并重。如此,中国的才是世界的,世界的才是中国的,学术强国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雄浑的内在驱动力。
正是出于这一基本认知,数年前我曾忽悠同好共读叶德礼(Matthias Eder,1902—1980)、贺登崧(Willem Grootaers,1911—1999)、司礼义(Paul Serruys,1912—1999),也敦促学生读译了赵卫邦、李世瑜的英文论文。这两年,在我给研究生开设的“现代民俗学”和“民俗学经典导读”两门课上,我给学生们推荐了本栏目的这些文章。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师生有着多次讨论、斟酌。为了更好理解原文,我们也适当添加了些补充性的“译注”。但是,译文肯定仍存诸多不足,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也愿读者在阅读这些译文,或者按图索骥地阅读英文原文之后,同样有“经典”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