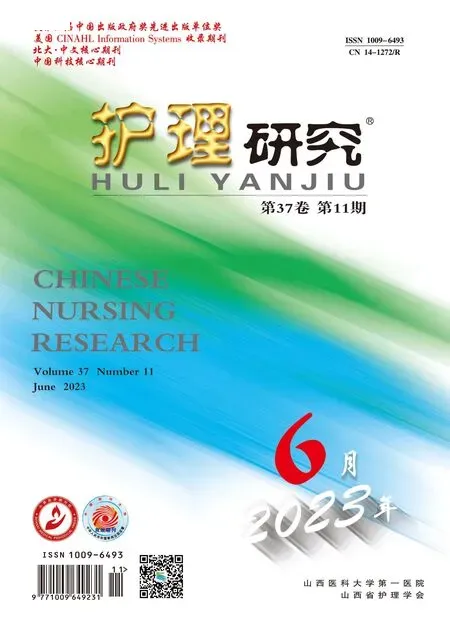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孤独感研究进展
井滕滕,段嘉宜,魏绍辉
1.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山西 030001;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痴呆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脑部病变,临床表现为记忆、理解、判断、推理、计算和抽象思维等多种认知功能障碍,伴有幻觉、妄想、行为紊乱和人格改变等精神行为症状,是导致老年人残疾和护理依赖的主要原因[1]。目前,全球约有5 000 万人罹患痴呆症,预计到2050 年痴呆病人将增加到1.52 亿人[2]。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进程中,痴呆病人数量不断增加,约占全球痴呆总人数的1/4[3]。我国超过90%的痴呆病人由家庭照顾者提供非正式护理[4],长期照顾的压力以及日益增长的照料需求逐渐加重照顾者负担,使之出现疲劳、痛苦、焦虑、抑郁、社会孤立、孤独等身心问题。研究发现,孤独感与焦虑、抑郁、自杀意念等心理健康问题有关,并且会增加冠心病、脑卒中、痴呆等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5]。目前,国内关于孤独感的研究多集中于儿童[6]、青少年[7]、老年人[8]等正常人群及癌症[9]、糖尿病[10]、精神分裂症[11]等疾病人群,针对家庭照顾者这一特殊人群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对国内外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孤独感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为制定相关策略减轻家庭照顾者孤独感,提高病人及家庭照顾者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1 孤独感概念
孤独感的概念最早由Leokamer 提出,指个体心理情绪的体验,是社会人际交往技能、认知能力或交流能力等均发生广泛性迟缓的一种现象[8]。随后,众多学者对孤独感的概念进行了界定。Sullivan 等[12]认为孤独感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与人际亲密需求没有满足有关。有研究者认为孤独感是个体觉知到人际关系不良,自己渴望交往,但实际的交往水平未达到预期效果时的心理体验[13],并将孤独感划分为社交孤独及情感孤独两个维度。社交孤独感与缺乏社交互动有关,而情感孤独感与人际关系缺乏质量或失去人际关系有关。这两个概念强调孤独感的情感层面,认为孤独是对社交需求未满足的反应。还有研究者认为孤独感是个体期望的社会关系与实际存在落差时产生的不愉快体验[14]。此观点既突出了孤独的情感体验,又强调了孤独感的认知加工过程,将孤独感的产生归因于个体对自身所感受到的人际交往现状感到不满。国内学者朱智贤[15]将孤独和孤独感分开界定,认为孤独是一种主观感知的与社会隔离而只身孤立的心理状态,而孤独感是人处在某种陌生、封闭或特殊的环境中产生的一种孤单、寂寞、不愉快的情感。
关于孤独感的概念尚无统一界定,不同研究者对孤独感有不同的诠释。但是,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孤独感是由于缺乏良好人际关系引起的;孤独感是一种主观体验,不同于社会孤立的客观状态;孤独感是不愉快、痛苦的情感体验。
2 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孤独感现状
2.1 孤独感发生率 孤独感在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人群中较为普遍,且发生率远高于非照顾者人群。质性研究发现,孤独感是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照料经历的一部分,照顾任务会影响照顾者的社交活动,使其社会联系减少,且因病人无法与其正常沟通,亲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减少,多数照顾者存在孤独感受[16⁃17]。Victor等[18]在改善痴呆症体验和增强积极生活(IDEAL)队列研究项目中对1 283 名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的孤独感进行基线调查发现,43.7%的照顾者有中度孤独感,17.7%的照顾者有重度孤独感,超过三分之二的照顾者存在独孤感。此外,Peavy 等[19]研究发现,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的孤独感发生率显著高于非照顾者,在调查的36 名家庭照顾者中,58%的照顾者报告有中度孤独感,6%有重度孤独感,3%有极重度孤独感,而在40名非照顾者中,仅35%的个体报告有中度孤独感。由此可见,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是孤独感的高发人群,且程度较重,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积极开展孤独感评估工作,识别其风险因素,制定相关措施以降低其孤独感。
2.2 孤独感对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的影响 Beeson等[20]对242 名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进行横断面研究发现,照顾者孤独感与抑郁水平呈正相关(P<0.001),照顾者报告的孤独感越高,其抑郁症状越明显。来自英国老龄化的纵向研究(ELSA)[21]数据表明,痴呆配偶照顾者基线时的孤独感与随访时的抑郁症状呈正相关,孤独感是抑郁的重要预测因素,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更容易发生抑郁症状,而孤独感起中介作用,解释了总效应的34%。孤独感不仅会增加照顾者的抑郁症状,相关研究发现,孤独感是焦虑、抑郁、疼痛及疲劳症状群的共同危险因素,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的孤独感水平越高,越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疼痛及疲劳症状[22⁃23];此外,孤独感越高,照顾者感知到的压力水平越高[19],孤独感水平高的照顾者更容易采取不当的方式应对照料压力,如运动锻炼减少、睡眠质量不佳、产生自杀意念等[22,24]。孤独感会加剧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的压力反应,增加焦虑、抑郁、疲劳、疼痛等身心健康问题的发生风险,严重影响照顾者的生活质量。提示医务工作者应重点关注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的孤独感现状,以孤独感为干预靶点,减轻照顾者的压力反应,缓解其焦虑、抑郁、疲劳等症状。目前国内较少有针对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孤独感的相关研究,尚不清楚我国痴呆病人照顾者孤独感的发生现状。因此,医护人员应积极识别和筛查存在孤独感的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预防或降低照顾者孤独感,以提升其生活质量,促进身心健康。
3 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孤独感的影响因素
3.1 人口学因素 年龄、性别、居住环境是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孤独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年龄与照顾者孤独感显著相关,年龄越大,照顾者的孤独感水平越高,这可能与年龄增加、身体机能减退、心理状况易受干扰有关[18,25]。Beeson[26]研究发现,受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女性在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往往承担更多照顾责任,花费更多的时间照料病人,自由时间受限,社交互动及休闲活动减少,容易产生社会隔离,孤独感水平高于男性。Bramboeck 等[25]研究报道,男性照顾者的孤独感水平高于女性。也有研究指出,照顾者孤独感在性别上没有差异[27]。性别对痴呆照顾者孤独感的影响尚存在争议,仍需进一步研究。此外,研究发现,与痴呆病人一同居住的照顾者孤独感水平高于分开居住的照顾者[25]。分析原因可能为:与病人一同居住的照顾者感知到的亲密关系剥夺、自我丧失更多,更容易产生情感孤独。年龄较大,与病人一同居住的照顾者多为病人配偶,提示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痴呆配偶照顾者,及时采取措施干预,降低其孤独感。
3.2 疾病因素 一项质性研究报道,随着疾病进展,痴呆病人逐渐丧失自理能力,并且会出现幻觉、妄想、激越行为,照顾者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照料病人,社交网络规模及社会交往频率减少,容易产生孤独感[28]。但量性研究发现,痴呆严重程度低时,照顾者孤独感水平更高[25]。原因可能为:痴呆初期,照顾者不能马上接受病情,不知道如何护理病人,容易产生悲伤、无助感,在疾病第一阶段照顾者孤独感最为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照顾者的照顾胜任感增强,逐渐适应这种状态,孤独感水平有所下降。因此,医护人员应及早对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提供相关支持,帮助其适应照顾角色,以降低照顾者的孤独感受,提升其生活质量。
3.3 社会支持因素 一项阿尔茨海默病照顾者心理健康与感知社会支持关系的调查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是孤独感的保护因素,感知的社会支持越高,孤独感水平越低[29]。另一项研究也证实,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孤独感越低;此外,该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高的个体,休闲活动时间更多,社会支持不仅直接作用于孤独感,还通过休闲活动间接影响孤独感[30]。社会支持能够缓冲护理相关压力源对个人负面情绪的影响,增加照顾者的社会支持有助于减少孤立感并改善心理健康。我国医疗保健制度尚不完善,痴呆症相关的卫生服务缺乏,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的社会支持水平普遍低于国内常模[31]。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及医疗机构应该加快完善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系统,增加照顾者社会融入、社会参与程度,以减轻照顾者孤独感。
3.4 关系质量因素 多项研究显示,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之间的关系质量是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孤独感的风险因素,关系质量越差,照顾者越容易感到孤独[18,20,32]。可能与关系质量差的病人⁃照顾者二元组报告的共享活动及互惠较少,照顾者感知的亲密关系剥夺较多有关[20]。压力过程模型提出,与护理相关的压力源增加了照顾者产生不良身心健康结果的风险。其中一种压力源为关系剥夺或亲密交流的剥夺,包括随着痴呆症进展而失去的亲密关系[33]。因此,当前关系质量差、亲密程度低以及自痴呆症发作后二人关系亲密程度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孤独感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这提示临床医护工作者应重视痴呆病人与其家庭照顾者的相互关系,制定干预措施改善痴呆病人及照顾者的关系,例如为照顾者提供一份以改善沟通交流方式为主要内容的宣教册或视频,开展病人⁃照顾者双方喜欢的活动,鼓励二者共享闲暇时光,增加病人与照顾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增进二者之间的积极关系。
4 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孤独感的干预策略
国内外有关孤独感的干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对家庭照顾者的研究较少,主要包括同伴支持、正念训练、音乐疗法等干预措施。
4.1 同伴支持 同伴支持是指具有相似经验或体验的人们在生活、社会及情感等方面的互帮互助[34]。Stewart 等[35]对47 名阿尔茨海默病及19 名脑卒中家庭照顾者实施一对一的电话同伴支持,主要内容为信息支持(疾病信息、可用资源等)、肯定支持(建议、反馈、积极强化等)、情感支持(移情、倾听等),每周20 次,每次15~60 min;干预结果表明,同伴支持有助于提升家庭照顾者的应对技能、护理能力和信心,减轻照顾负担及孤独感。Smith 等[36]采用混合性研究方法对同伴支持小组中16 名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进行调查,定性结果显示,拥有相似照顾经历的同伴为照顾者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支持,同伴之间的人际互动(交流、分享、鼓励)可缓解照顾压力,减轻孤独感;定量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前后照顾者感知的社会支持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孤独感比较差异虽无统计学意义,但呈下降趋势。同伴支持为照顾者提供了额外的支持系统,一对一模式及小组模式这两种类型的同伴支持均可以减轻家庭照顾者的孤独感受。其中小组模式的同伴支持作为一种集体活动,能加大照顾者的社交网络、小组之间的交流互动,能让照顾者找回常态、归属感,更能缓解社交隔离所带来的孤独感。但开展该活动时需同时将医护人员、支持者及照顾者聚集在一起,对时间、地点要求较高,会降低照顾者的参与度。这提示研究者应探索新的同伴支持模式,如基于互联网的同伴支持模式,利用信息技术为照顾者提供远程、及时、便利、延续的支持。
4.2 正念训练 正念训练是一种心理干预方法,主要是通过训练培养个体的觉知力,在练习中引导个体有意识、非评判地觉察当下,学会接纳[37]。已有研究证实,正念训练可以减轻个体的孤独感,增加日常生活中的社交互动,提高沟通和关系满意度[38⁃39]。Tkatch 等[40]招募了40 名家庭照顾者参与为期8 周的在线正念冥想训练,干预结束后发现,照顾者的负担、感知压力、焦虑和孤独感明显减少。此研究进一步证实,正念训练可以减轻家庭照顾者的孤独感。但该研究未报道家庭照顾者的类型且样本量较少、缺乏对照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目前有关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的正念干预研究多关注于照顾负担、感知压力及焦虑、抑郁水平等[37,41],涉及孤独感的研究较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证实正念训练对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孤独感的作用。
4.3 音乐疗法 音乐疗法是指由专业的音乐治疗师使用音乐或音乐元素满足参与者身体、心理与社会需求的治疗方法,分为主动音乐疗法及被动音乐疗法两类,即主动参与歌唱、乐器演奏和音乐创作,以及被动聆听两种干预形式[42]。单独针对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的干预较少,多将痴呆病人⁃照顾者看作一个二元单位进行音乐治疗。SftB(singing for the brain)是阿尔茨海默病协会为痴呆病人及其照顾者开发的团体音乐活动,多个病人⁃照顾者二人组形成一个团体,在音乐治疗师指导下进行歌曲演唱、乐器演奏等活动。Osman等[43]招募10 对参加两次及以上SftB 音乐疗法的痴呆病人⁃照顾者进行访谈发现,照顾者表示音乐疗法有助于增进人际互动,建立支持性社交网络,减轻照顾压力,缓解孤独感。Clark 等[44]对12 组痴呆病人⁃照顾者实施治疗性团体歌唱(TGS)干预,包括音乐聆听、独唱、和声、乐器演奏、动作舞蹈、音乐创作等内容,每次约120 min,干预20 次后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了解参与者的感受,结果发现TGS 可以改善照顾者与病人之间的沟通,重建彼此亲密关系,增进关系质量,同时有助于增强参与者的社交自信,增加社会互动,减轻照顾者⁃病人二人组的社会孤立,缓解孤独感。音乐疗法成本低廉、风险低,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干预措施。但有关音乐疗法的效果评价多以质性研究为主,缺乏量性研究数据,且试验设计不够完善,多数研究样本量较少,采用自身前后测量的方式进行比较,缺乏横向对比研究。未来应进行大样本、多中心、高质量的随机对照研究,完善相应的评价指标,尤其是客观指标,以证明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5 小结
目前,有关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孤独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局限:①以质性研究为主,缺乏量性研究数据;②孤独感影响因素研究不全面,缺乏相应的理论框架,未来应加大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全面、深入探讨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孤独感特征及影响因素;③干预性研究较少,且研究设计不够完善,干预结果有待进一步明确。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的孤独感发生率高、程度重,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然而,我国较少有研究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孤独感的报道,未来应参考国外相关研究经验,并结合我国文化背景开展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孤独感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