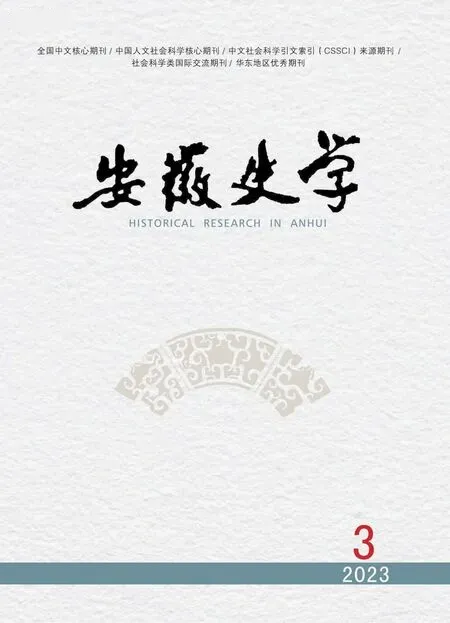思想启蒙的两种取向之争
——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生育节制讨论的历史阐释
魏万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2488)
中国人生育控制观念古已有之,但1922年美国女权主义者桑格夫人(Margaret Higgins Sanger)来华宣传“科学节育法”却意义非凡。她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等地做了多次有关节育的演讲,“象这样大规模有意识、有目的地并从近代科学的意义上全面阐述节育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梁景和:《五四时期“生育节制”思潮述略》,《史学月刊》1996年第3期,第49—50页。此后各种节育理论大量涌入中国,讨论逐渐深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节育运动逐步兴起,1937年以后,随着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救亡”彻底压倒“启蒙”,节育运动淡出历史舞台。对20世纪20年代还作为思想启蒙的优生节育讨论进行研究,可以有效揭示思想启蒙的内在困境。
民国时期的“生育节制”拥有诸多名称,如“节育”“制育”“产儿制限”“生育制裁”等,按照现代人口学奠基者之一陈达的定义——“生育节制是用理智来管束生育的一种方法”(2)陈达:《我们应该提倡生育节制吗?》,《清华周刊》1931年第35卷第7期,第473页。,着眼点在于子女数目的控制,与独身和绝育有明确不同。(3)陈长蘅:《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319页。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对民国时期的生育节制展开研究。(4)代表作如王奇生:《近代中国节育运动述略》,《人口研究》1990年第5期。王奇生把民国时期的节育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桑格夫人来华的1922年之后的整个二十年代为发端和宣传的阶段,三十年代之后则为从宣传走向实践的阶段,此后的民国节育运动研究多沿用这一分期方法。大多数研究者从人口与节育、性道德与节育、妇女与节育、优生与节育等四个方面展开讨论。(5)如一些学位论文,包树芳:《民国时期节育思潮初探》,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周丽妲:《生育观念在近代以来的嬗变——以节制生育运动为基点展开论述》,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李春霞:《论近代中国生育节制思想》,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冯思奇:《民国时期生育节制思想及实践研究》,安徽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俞莲实:《民国时期城市生育节制运动的研究——以北京、上海、南京为重点》,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等。本文试图通过文本分析揭示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在个体取向和国族取向上的差异,进而探讨思想启蒙内在的逻辑困境。
一、生育节制讨论的兴起
优生节育问题的提出与近代中国城市新市民群体的兴起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密切相关。传统生育观念与小农经济相联,之所以提倡“多子多福”,主要因为较多的男性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有益。在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中,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城市兴起,新的城市居民与小农社会变得疏远,他们有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价值观,因此便有了对自身和后代的新期盼。
在新兴的“准市民群体”中,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是他们中的重要成员。在教育方面,他们至少都接受过小学或者中学的教育,优秀者还接受过大学的教育(6)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1—582页。,在工作方面,他们因受教育水平较高而获得一份体面的非体力工作,依靠工资来维持生活;在工作之余,他们重视娱乐和享受,吹箫、唱歌、弹琴、看电影、游公园、逛百货公司等;(7)朱邦兴等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在住宅方面,他们住在新型的城市住宅里,这些城市住宅面积小而紧凑,但设施配备则完全依照现代住宅的标准,适于小家庭或单身的生活;(8)江文君:《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321页。在家庭方面,他们厌恶传统的家长制的大家庭,提倡核心家庭,向往婚姻的幸福和美满,以及小家庭的美好生活。(9)江文君:《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321页。社会新阶层的出现引起了观念的深刻转变,生育节制逐步成为可讨论的话题。这一阶层不愿拿出足够多的精力和财力来养育孩子,居住空间的逼仄也需要考虑家庭成员数量;崇尚自我的新价值观更不愿受“传宗接代”思想的束缚。对于这些新的城市居民来说,新生活方式和观念的转变,使得生育节制在他们看来越来越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种必要了。(10)如在《生活》上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就表达了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住宅、工作的压力下对于节育的需求。参见隐:《受经济压迫而想到节育的一位青年》,《生活》1926年第2卷第7期,第54页。
马尔萨斯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是生育节制讨论兴起的理论基础。1880年,京师同文馆毕业生汪凤藻翻译《富国策》,简要介绍了马尔萨斯主义,之后又有维新派严复和梁启超等人在著作中对马尔萨斯主义的介绍。(11)参见[英]托马斯·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66页。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93页。时人之所以关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多半受进化论的影响。到了二十年代,新马尔萨斯主义传入中国。新马尔萨斯主义提出通过科学的、人为的避妊即生育节制来限制人口数量,弥补了马尔萨斯主义“不近人情”地限制人口措施的缺点,由此得到了学者们广泛关注。这些学者发现了生育节制对于解决人口问题之外的其他领域同样颇有价值,这成为生育节制讨论的历史背景。
中国知识分子在这场讨论中的情绪可以用“羡憎交织”来概括。面对已然“现代化”的西方,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正视人口和人种的问题。桑格夫人同情地将黄种人无节制的生育作为其野蛮落后的根源,她在演讲中说道:“在中国,我们目睹了人口过剩这一民族悲剧的最后一幕。这是一个匍匐在尘埃中的伟大帝国。中国,这个拥有艺术、哲学的神秘源泉和世界上最深邃的智慧的国家,已经被黄种人的不良生育和恶性繁殖打垮。”(12)Margaret Sanger, “Birth control in China and Japan”,speech delivered on October 30,1922 in Carnegie Hall,New York.https://documents.alexanderstreet.com/d/1003811409.一些知识分子在参与节育讨论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成了西方节育论者塑造的这种“东方”印象的参与者。即使是抵制节育论者也无形中将孱弱的黄种人与先进且优秀的白种人作对标。动物学家陈兼善就指出,白种人与其他有色人种抗争,“获得优势,立于支配者之地位”,因此有色人种更不能够“拾人牙慧讲什么产儿限制,以至于人口衰减,那末有色人种,真是为白人底奴隶了。”(13)陈兼善:《优生学和几个性的问题》,《民铎》1924年第5卷第4期,第9页。周建人更是将民族衰退的重要原因归结为在与强大民族接触时无法适应被强大民族所改变的环境,“近来许多不开化的民族,和白种接触以后,白人虽不扑灭他们,他们自己也会衰颓。这是真的,你如将不进化的民族的土地改做纽约、伦敦般的都会,土人反不能存活其间了。”(14)周建人:《读中国之优生问题》,《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8期,第16—17页。同时,面对西方话语成为讨论的主流话语,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憎恶的,试图守卫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有人列出了反节育的几类卫道士立场:上天有好生之德;人少何以卫国家;节育有违人伦,以此抵制新思潮。(15)晓风:《生育节制问题》,《民国日报·妇女评论》1922年第39期,第1页。两种情绪恰恰是“后发强制性国家”卷入现代化进程后的普遍情绪。
生育节制讨论既讨论了节育对个人(尤其是妇女)解放的效用,也讨论了节育对社会发展、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论战双方围绕生育观、婚恋观与性观念、女性地位与权利等话题展开讨论。
二、个体层面的生育节制讨论
“五四”时期“科学”成为主流话语,知识分子呼吁转变生育观念,正是借助“科学”之名。无论是革除不人道、不健康的旧生育观念,抑或是对传统观念的再阐发,科学话语始终贯穿在节育与生育观念的讨论中,新生育观之“新”即在它是“科学的”生育。
鉴于女性承受着来自社会观念与家族生活两方面的压力,这是主张生育节制的出发点,所以新生育观与旧生育观针锋相对。旧生育观包括三方面,即重视传宗接代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强调添丁增口的“多子多福”和含有性别歧视意味的“重男轻女”。(16)郑永福、吕美颐:《中国妇女通史(民国卷)》,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471页。新生育观明确地批评这种传统生育观对于妇女健康和幼儿成长的伤害,节育论者同时也批判中国古代控制子女数量的办法——弃婴、溺婴、堕胎等。桑格夫人的科学节育法——在妻子危险期以外同房的节欲法、对男子生殖器官的生育能力进行干预的断种法和在同房过程中用特定器具或药物阻碍受孕的机械法,这些方法受到中国节育论者的推崇,被认为是更人道、更科学、更安全的节育方法,而传统节育方法都是野蛮、反科学的。(17)周建人:《产儿制限概说》,《东方杂志》1922年第19卷第7号,第14—15页。
也有人重新从传统生育观中寻找积极遗产,以此作为新生育观的基础,虽然与节育论者观念不同,但也对传统节育观进行修正,优生学家潘光旦便是典型。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除了被称为“天择”即残酷的自然选择之外,潘光旦更重视和推崇的是“化择”即文化或社会选择。他认为西学东渐以前,中国传统中已经有一些“化择”的因素,它们有明显的优生效果,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把传宗接代放在个人幸福之前,虽然不利于个人权利的伸张,但对宗族延续和幼儿养育具有保障作用,而传宗接代的重要性是西方优生学者近来才认识到的。(18)潘光旦:《中国之优生问题》,《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22号,第17—20页。
婚恋观和性观念是节育讨论的突破口。婚姻目的被认为是值得审视的问题。传统的婚恋观被概括为“婚姻的本质是生育”,节育论者支持婚后节育,认定生育只是“婚姻下可能有的现象和质料,决不是婚姻的要素”(19)陈德徵:《婚姻和生育》,《妇女杂志》1922年第8卷第6号,第86页。,传宗接代不是夫妻的义务。潘光旦则反对这种“本质论”的节育观,他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打比方,认为从性行为到生育的过程中,因与果本是紧密关联的,但人既然是趋乐避苦的,节育方法的引入便会使人们轻而易举地把性的娱乐与繁衍后代的责任相分离,造成不良影响。所以节育论者可能只是借助女性权利的由头伸张其他方面的权利,“主张生育限制最力者大都为女权运动中之激烈分子,往往假借‘母性之自由获得’之大名义,而推广其一般的女权。”(20)潘光旦:《生育限制与优生学》,《妇女杂志》1925年第11卷第10号,第1561页。夏丏尊则针锋相对地认为婚姻不应该单纯为生育服务,主张将性与生育分离,因为婚姻和生育都无法真正确立起男女间性道德的“自觉”。(21)丏尊:《生殖的节制:欢迎桑格夫人来华》,《民国日报·妇女评论》1922年第38期,第1页。这种道德自觉与传统的“贞操”观迥然不同,它不再依靠“法律名誉等消极的外来制裁”,而是“必须积极的从根本上入手,如实施青年男女的性教育,提倡恋爱的神圣,尊重女子的人格”,此外还要一改性道德完全由妇女单方面遵守的旧观念,提倡由男女双方共同负起义务。(22)瑟庐:《产儿制限与中国》,《妇女杂志》1922年第8卷第6号,第12、13页。以往敏感的话题在“科学话语”加持下得以光明正大地讨论,很多人听完桑格夫人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后,直观的感受是,“‘性’的事情,原来还是值得用科学方法去讨论的啊”。(23)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10页。以张竞生为代表的本土性学学者主张科学认知“性”的问题,对中国人的性体验进行了一次科学大调查,编写了《性史》。无论是对婚恋要义的探讨,还是对性这一敏感问题的大胆辩护,主流论者在围绕节育展开讨论时,都有意用科学认识性问题,尽量避免用盲目的价值判断直接封堵讨论这些话题的可能,使更多人对于婚姻、爱情和性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放。这些讨论渗透出鲜明的启蒙色彩,如两性平等、个人自由与责任相联系的观念等。这从侧面说明,五四启蒙的新文化、新思想已逐渐融进学者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中,成为他们论域的内在组成部分。
生育节制讨论所涉及的最重要的对象是女性群体,女性权利是节育讨论的重中之重。在节育讨论的语境下,“生育”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过程,它被看作围绕这个生理过程所展开的种种活动,包括受孕、生产、养育等,妇女承担从生到养的沉重负担,甚至面临生命危险。一些人把生育看作“人类的天职”(24)罗齐南:《中山先生论人口问题之讨论》,《现代评论》1926年第3卷第72期,第20页。,以此反对节育对以往自然生育秩序的颠覆。节育论者则大多从女性关怀出发,围绕妇女的生理感受、社会追求展开讨论。无论是以实际经验为证,还是用严谨的医学原理支撑,支持减轻女子繁重生育负担的论者都表现出对女性艰辛生育感受的理解。(25)本来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的论者是女性,但实际上出现了“女性声音的缺失”,详见马姝:《“桑格热”之后》,《读书》2022年第9期,第131页。从已有史料来看,事实大体如此,除了刘王立明等少数新女性知识分子发论,节育讨论主要由男性知识分子掌控。生育关乎女性的健康和幸福,但过于频繁的生育却往往给她们带来苦恼和危险,《妇女杂志》1931年初发表的一篇来信很能代表当时女性的感受,一位名叫黄秀芬的女士发出了“生育的机器要做到几时为止”的质问。(26)黄秀芬:《生育的机器要做到几时为止呢》,《妇女杂志》1931年第17卷第1号,第221页。由于传统生育观念的束缚和不具备科学有效的避孕措施,女性往往无法真正掌握生育主动权。节育论者对此十分同情,指出生育自主对女性身体大有裨益,相比于宗法社会中接二连三而中间几乎无喘息时间的生育重负,节育可以减少频繁生育对母体的伤害;而且男子也应该认识到,女性的身体也同样是血肉之躯,不能贪图性享受,无视“妇女在这样接连不休的生育下要忍受多少的苦痛”。(27)金仲华:《节制生育与妇人生理的解放》,《妇女杂志》1931年第17卷第9号,第6页。在强调平等、理解与关怀的基础上,节育论者要求实现女性对生育自主权的掌控,经常就妇女解放发表见解的陈望道提出,女子求幸福、争解放的基础之一就是“母性自决”,即“对于让几个人来做自己底儿女的事,女性也必然可以自己底意志决定”。(28)陈望道:《母性自决》,《陈望道全集》第5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
民国时期逐渐壮大的新女性群体希望突破“闺阁女子”的旧身份,通过受教育改变自我,争取男女平权。然而,生育的过程以及生育后的抚养责任很重,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仍然占据主流,这些都使年轻妇女事业败给了家庭事务。节育论者认为,如果妇女无休止地承担生育和养育的繁重工作,就会阻碍新女性自身发展,也阻碍社会进步。有人认为“妇女的被束缚,是无教育,经济依赖男子及不能替社会服务等应有的结果”,但节育论者则认为这是颠倒因果,事实上是教育不足、经济不独立导致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而社会没有给妇女获得教育、经济独立的机会,因为这些机会都被年轻时早婚、早育、频育的压力排挤流失。(29)瑟庐:《产儿制限与中国》,《妇女杂志》1922年第8卷第6号,第12、13页。生育节制成为提升妇女社会地位的必要前提,只有在减轻生育负担的基础上,妇女才可能摆脱“生殖机器”的束缚,尽情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实现从照顾家庭到奉献社会的人生意义的量级跃升。(30)西滢:《闲话》,《现代评论》1926年第3卷第74期,第7页。
可是,生育节制需要经受的最有力辩难,并非来自对“生育”本身的不同观点。在讨论生育节制的价值时,这场思想启蒙不由自主地面临从个体转向集体的难题,在社会、国家、民族这一层面上讨论生育节制比性启蒙、女性权利等问题占有更大的分量,并且几乎覆盖了所有反节育论者的论说。
三、国族取向上的生育节制讨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个家庭的状况与变化都是社会整体发展状况的微缩图景。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民国时期社会经济的新发展也反映到城市小家庭的新变化中。在知识分子生育节制的讨论中,生育越来越被看作是不仅关系到一家一户幸福或烦恼的事务,更是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的大事。
由于社会缺乏健全的生育保障措施(31)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国民党官方才拟定了一系列奖励生育的具体方案,详见俞莲实:《民国时期城市生育节制运动的研究——以北京、上海、南京为重点》,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311—318页。,即使对城市家庭来说,频繁生养幼儿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也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周建人认为,频繁生育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即频繁生育——母亲难以离家谋生,用于孩子的开销渐增——经济压力增加,父母对收入需求急迫——母亲与较大的儿童为生活所迫做工,工人增加导致工资下降——孩子失去求学以增长能力的机会。(32)周建人:《产儿制限概说》,《东方杂志》1922年第19卷第7号,第12—13页。因此节育才是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的良方。在节育论者看来,一个家庭内子女过多存在拖垮家庭财富的风险,一个社会中人口过剩也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人口学家在进行社会调查和数据分析后,认识到中国面临着“人满之患”,而判定人满为患的依据便是“生活程度”的高低和“生活竞争”的剧烈程度。(33)陈达:《我们应该提倡生育节制吗?》,《清华周刊》1931年第35卷第7期,第473、471—472页。他们信服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原理,认为在“人口超过物质所能供给的限度”(34)丏尊:《生殖的节制:欢迎桑格夫人来华》,《民国日报·妇女评论》1922年第38期,第1页。情况下,不对人口预先进行人为干预,各种天灾或人祸就会用更残酷的方式“抑制”人口,人满为患的危害会越积越重,形成人口增加——食物供应紧张——天灾人祸限制人口——人口又增加的恶性循环。(35)陈达:《我们应该提倡生育节制吗?》,《清华周刊》1931年第35卷第7期,第473、471—472页。大力倡导生育节制的人口学家陈长衡做出警告:无节制生育无异于民族的“自杀”。维持“适中的人口密度”,即不断调整国家人口,以使其达到适中的程度,为此,需要使大众认识到人口适中的重要性,使每个人负起维持适当生育量的责任。(36)陈长蘅:《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第90页。
随着生育问题越来越多地被置于公领域探讨,论战双方将其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与民族复兴的高度来审视,主要讨论集中在人口“数量”与“质量”之争上。新马尔萨斯主义是节育论的理论基础,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和节育论者大多从人口过剩、妇女受压迫和人口素质低劣的不良影响等方面立论。反节育论者主要围绕马尔萨斯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展开批判。譬如临终前的孙中山就对“蛊惑人心”的马尔萨斯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认为马尔萨斯主义所谓人口多于资源的观点,实际上为列强们在世界上大肆侵略扩张提供了依据。现如今的中国之所以还没有被吞并,正是因为列强人少而中国人多。一旦推行节育政策,中国人口减少,更难抵抗外来侵略。孙中山对生产力的进步充满信心,相信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中国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37)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存在忧虑“人满之患”与担心人口增长过慢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前者主要是在1924年以前阐发的,1924年,孙中山人口思想突然转向鼓励生育。具体参见胡绳武、戴鞍钢:《试论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学术研究》1996年第10期。很多人支持这一说法,认为鼓励生育才能保障民族的生存安全,民数及其增长率绝不可落后,否则终会丢掉中国庞大人口这一为数不多的优势,沦落到灭国亡种的境地。在本民族的外部威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外国人口一天天的增添,中国人口一天天的减削,推知百千年之后,会被天演公例淘汰无余的危险”。(38)罗齐南:《中山先生论人口问题之讨论》,《现代评论》1926年第3卷第72期,第20页。由于当时中国官方没有做过整体系统的、值得信服的人口统计工作,因而学者在讨论人口增长快慢问题时,往往只能依据实际感受、局部的田野调查和国外学者不见得可靠的数据,这就为展开广泛讨论提供了可能。有论者更进一步指出,节育这种西来学说背后可能隐藏着不良动机,中国贫弱的真正根源,是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和压榨,节育思想帮帝国主义掩饰了这个祸根,“而反到归罪于中国女人太会养小孩子”,中国坚决不可以推行节育,因为“在中国生活程度低,人民智识文化低,医药卫生毫不讲求,就是少养几个孩子,死亡率未必能减低,寿命未必能延长,结果人口定然会大大的减少,正是给人家以殖民可能的机会。”(39)张履鸾:《江宁县四百八十一家人口调查的研究》,中国社会学社编:《中国人口问题》,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342页。相反,人口增殖不仅可抵御外侮,还利于国家发展。1927年,中国近代著名乡村教育家杨效春就抓住了马尔萨斯主义致命的五大缺点,对“中国人口问题”做了有高度倾向性的总结,他认为一国人口的多寡与国势强弱、经济贫富、文化高下、国防力量和个人幸福都有密切关系,这五方面的进步都需要大量的人口作为后盾,他以此批判生育节制主张,节育甚至被他斥责为“民族自杀之策”。(40)杨效春:《对于时论“中国人口问题”的总答辩》,《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22号,第14、17—18页。杨文指出,第一,人口增加并不必然比食物增加快,生产力和科技进步将大大加快粮食生产增速;第二,资源分配的矛盾不在资源与人口的比例,而是资源分配不公的结果,是国际和国内的双重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分配才导致了民族衰弱、平民贫困;第三,马尔萨斯对天灾人祸抑制人口的解释过于单一;第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假设了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然而发展生产力和促进财富增长的办法还很多;第五,人口与资源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人口增加即劳力加多亦可使生产增加,且人多则生存竞争激烈,可使人类事业益超发达”。
节育论者否定自己是为了节育而节育,他们更看重的是人口“质量”的提升,拥有一群高素质的国民才更是民族发展的福祉,为此宁可削减新生人口的数量,以追求少而精的人口结构。不同的是,他们选择了一条与人口增量论者大异其趣的路径。一方面,他们认为那种把人口数量看作国家强大标志的观念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新要求,在当前国际舞台上,一个民族的强弱“不在乎数量的多寡,而在乎质地的优良”。(41)瑟庐:《产儿制限与中国》,《妇女杂志》1922年第8卷第6号,第12页。量的优势无法保障国家安全,否则无法解释人口数量庞大的中国屡受人口数量远少于中国的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欺凌。另一方面,人口增量论着眼民族发展的全局性因素,希望尽快加添人口总量,以达到抗衡强敌的效用。但这恰为节育论者所反对,他们拒绝从“上帝视角”考虑国家的人口问题,而是着眼于个体发展的实际,认为给予个体更充分的发展机会是提升国民贡献国家能力的前提。如与抚养五、六个孩子相比,只抚养两个孩子的家庭利于为孩子提供更充裕的生活条件,每个孩子能够分得更多父母的照料,获得更充分的教育,“这样,如果只有子女二人,他们就成了二个健全有用的国民,要是有了五六个,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反而低落了。”(42)西滢:《闲话》,《现代评论》1926年第3卷第74期,第7页。
虽然节育论者和增量论者存在路径上的分歧,但节育论者无意通过支持节育来否定增量论者的民族救亡愿望。恰恰相反,节育论者试图在人口增量与提质之间达成某种妥协,以证明数量与“质量”并不矛盾,进而说明优化生育与民族发展正相关。因为少生与优生不仅不会危及种族繁衍的总体局面,还会减少导致人口增长乏力的因素,如灾祸对人口的抑制、生育中发生的意外等。他们相信多数女子具有与生俱来的强烈母性,人类具有繁衍后代的本能要求。所以即使实行了节育,也“绝不致种族会自杀的”。(43)周建人:《产儿制限概说》,《东方杂志》1922年第19卷第7号,第17页。可见节育论者力图实现的是国民在量与质两方面的优化,只不过更倾向于把提“质”放在优先地位。
四、两种取向展示的启蒙窘境
纵观20世纪20年代的生育节制讨论,可以发现一些显著的特点。一方面,作为个体取向的生育节制,虽然在节育的理论、方法以及围绕节育的婚姻、家庭、性、权利等问题,立论双方的观点和态度千差万别,从极端反对、怀疑否定,到部分认同、极力宣传皆大有人在,但对于那些节育论者而言,他们多侧重于从思想解放、个人发展出发,逐步上升到社会改良、民族壮大。他们要求先破除传统植根于人们头脑中的旧观念,如多子多福、无后为大、民庶则国必强等旧价值观。他们强调个人发展是国家强大的前提,希望通过生育节制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故而倾向于强调个人“权利”。而反节育论者则倾向于从国家和民族安全的角度出发,把民族生存作为高于一切的立场,个人的解放不能触动民族、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倾向于“欲享权利必先尽义务”(44)宋国宾:《节育问题之我见》,《医药学》1927年第4卷第6期,第26页。,强调种族繁衍的优先性。个体取向上的生育节制讨论,正是两种不同侧重点最典型的例证。
论战双方在差异中蕴含着共性,这种共性在个人解放方面并不显著,而当生育问题与更为宏大的国家和民族前途问题联系起来时,观点相左的论者竟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了趋同的话语,即加强对国民生育行为的指导,以合理的生育方针来挽救国家危机,谋求民族复兴。围绕国族层面展开的节育讨论包含了内部发展与外部威胁两种视角。对于民族的内部发展,他们共同担心的问题是“民族自杀”,只不过节育论者从马尔萨斯主义出发,担心“人满为患”的后果,即无节制的生育造成天灾人祸对人口的残酷抑制;反节育论者则重新拾起古老的民庶则国强观念,重视“民数”或“民量”,并以新的方式阐释庞大的人口基数对于现代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价值。至于民族外部威胁,他们都把列强侵略势力视为中国生存的严重威胁,如何保证本民族能在强敌侵略与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强大起来,是他们思考生育与人口问题的共同着眼点。节育论者重视“民质”,强调现代国际竞争的新形势,认为仅仅鼓励“民数”增加不能改变中国孱弱的现状。尽管如此,他们也在努力寻找消解“民质”与“民数”间矛盾的办法,力图实现中国人口质与量的全面发展。这又从侧面印证出,双方论者在其思想内核中并不存在显著分歧,民族救亡成了他们阐发节育观的共同旨归,在这一点上,“救亡”压倒了“启蒙”。
理论走向实践的第一个误区,便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相悖。一些人对节育实践抱着盲目的乐观,邵力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生育节制释疑》中,他认为生育节制的理论更重要,实践则是其次。只要经过理论上的研究发现确有节育的需要,决不怕没有适应这个需要的方法。(45)邵力子:《生育节制释疑》,《民国日报·妇女评论》1922年第39期,第3页。邵显然将节育实践想得太过简单。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节育的群众基础还十分薄弱,甚至有人怀疑节育方法的有效性:“今日所见产儿制限方法不下十余种,其中殆无十分有效而且无害者。即使有比较的确实方法,无绝对可靠者。”(46)刘以祥:《答“再讲产儿制限与性道德”》,《晨报副刊》1925年5月7日。这些对于节育实践的反思,确实反映了当时社会条件下推行节育的困难。任何一种新思潮的传入,都必须考虑其本土适应性的问题。在节育讨论之初,一些欢欣鼓舞的支持者把节育奉为救世的唯一良方。鼓吹节育可以解决一系列因人口过剩引发的社会问题,丝毫没有考虑到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差异,以及节育在妇女解放事业中可以发挥作用的限度。这就造成了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严重背离,所以事后来看,“这种科学的知识有赖于正常医者的研究介绍。然而我国医者并未注意到这方面,而无知的秘密堕胎却乘着机会发展的很厉害了。”(47)金仲华:《节制生育与妇人生理的解放》,《妇女杂志》1931年第17卷第9号,第10页。
理论必须“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物质力量”,开展节育启蒙的社会主体都是社会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民众则是作为被启蒙的“社会客体”出现,节育理论在“掌握群众”的过程中陷入了两难。正如进入实践阶段,一些有识之士才认识到,理论上,知识分子是有知识、有智慧、有才学的人,是社会中的“优质”人口,“实在是我们健全种族起见要保存繁殖的”,只有知识分子在人口中的占比不会锐减,人种的“质量”才能有所保障。但现实却是,基本上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在采取生育节制,而其他社会群体却未接触过或不愿节育,那些“一般不负责任的糊涂虫”,却在“拼命的作大量的生育工作”。(48)柯象峰:《中国人口问题与生育节制》,《政问周刊》1936年第11期,第9页。长此以往则社会中的“优质”人口将会越减越少,而社会中的“非优质人口”却继续多产,人种的素质就将每况愈下,形成所谓的“反优生”现象。事实上,此前潘光旦就阐释了这种现象,如果单纯相信“天择律”,强调人与人天生就有智愚贤不肖之分,先天条件远比后天环境塑造重要,那么那“优质”的人就应该多生,而新马尔萨斯主义与桑格夫人的生育节制论忽视了固有文化形成的路径依赖,体弱多病者反而更加需要延续烟火,这样就会导致“反选择”现象的出现。(49)潘光旦:《中国之优生问题》,《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22号,第17—18页。
精英主导与大众运动的悖论是另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中国的节育思想受到西方节育思想启迪,后者萌芽于中产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中,其本身就带有精英色彩。节育讨论本身就是社会精英推动的启蒙运动,而为数不多的亲身宣传推广者和履践队伍也主要由精英组成。因此,节育论争中充满了精英声音、精英视角和精英偏见是容易理解的。如果将阶级分析的视角引入节育的讨论,探究节育的阶级属性和适用范围,便容易理解将其转变为大众运动的窘境。进入30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成一些知识分子的新理论武器,有人就指出,是生产关系决定了贫穷、失业、战争和盗窃等罪恶,而不是人口过剩。提倡生育节制无疑是为资本主义制度遮掩矛盾,生育节制只是资本主义制度苟延残喘的办法,却是工人阶级的“悲惨呼号”。节育唯一从根本上站得住脚的理由就是其对优生的功效,但这种优生是“防止不健全的人的生育”,而绝不是那种鼓励上层生育而要求下层节育的“优生”。“如果节育运动是完全站在真正的人类优生学基础上而被提倡,那么他不应该根据甚么人口过剩和贫苦的人因为经济困难而应节育等等理由,更不应该根据知识高低和现有社会地位高下来决定人类之种的优劣,并以此为节育的标准。”(50)陈碧云:《现代妇女节育运动的解剖》,《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15号,第5—6页。周建人也明确将节育定位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需求”。而小资产阶级之所以推崇节育,是因为“小资产阶级想维持他的阶级地位,不能不叫儿女受相当的教育,而他的经济状况,又限制他给子女受教育的能力”。与此相比,在上的富人不需忧虑养育子女的负担,而在下的无产阶级则忙于生计,无暇关注节育,更没有经济能力负担节育措施。周建人破除了节育的“泛阶级”神话,他不仅把握住节育的受众群体,也鲜明地指出了在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推行节育的局限性。对于备受压迫的妇女群体来说,节育以减少生养孩子的负担当然是可取的,“不应当把这题目过于夸张,以为只要用生育节制的方法就可以解决各种重要的社会问题了,就在妇女方面,也决不是只要普遍的实行避孕就能得到解放的”,仅有生育上的解放远不能实现妇女完全的解放,“在妇女解放上也只占一个极小的部分”。(51)克士(周建人):《关于生育节制》,《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5号,第92页。这样一来,以少数人的意见指导一个在民众主观意识上损害自身利益的启蒙运动,自然会在大多数民众的漠然无视中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