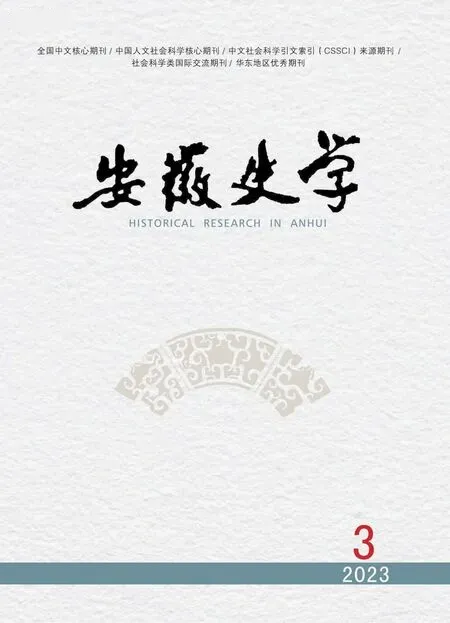坟产习惯及其在中国近代法律变革中之境遇
蔡晓荣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中国传统社会素重祖先崇拜,祖先之坟墓,一直被世人视为神圣之所。坟墓及其周围一定范围内之土地或山丘,一般称为墓田坟山。此外,为便于祭祀,坟墓之上或其周边也可能设置相应的构筑物,加之惑于风水,坟墓抑或坟山又多以风水林荫蔽之。凡墓田坟山,凡坟墓相关构筑物,凡风水林,可概括地称为坟产。另,坟墓中的“陪葬物”乃至逝者之“尸身”,有时亦视为广义上的坟产。关于坟产保护,长久以来,在民间社会存在各种禁忌和习惯。坟产所涉之诸种权利,事实上是传统社会一种重要的习惯权利。
清末以迄民国,以欧日民法典为样本构建起来的新式物权法律体系,仅将坟产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不动产加以调整,且无任何特别之规定,故无法完全涵摄坟产习惯在传统社会衍生出的诸种权利。职是之故,在坟产诉讼司法实践中,有时审判机关仍不得不衡诸固有习惯对此类讼案进行裁处,而坟产诉讼折射出的习惯权利与新式法律之紧张关系,则一直伴其始终。
就本论题既有之相关研究来看,学者对前近代,尤其是明清时期坟山纠纷的类型、特点及其引发的诉讼问题,已有较多论及(1)参见高楠、宋燕鹏:《墓田上诉:一项南宋民间诉讼类型的考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张小也:《清代的坟山争讼——以徐士林〈守皖谳词〉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韩秀桃:《明清徽州民间坟山纠纷的初步分析》,曾宪义主编:《法律文化研究》第4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166页,等。,亦有学者撰文对坟产所涉之风水兴讼现象予以探讨。(2)参见刘冰雪:《清代风水争讼研究——以坟葬纠纷为例》,《政法论坛》2012年第4期;魏顺光:《从清代坟山风水争讼透视中国法律文化之殊相》,《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不过学界对于近代以来坟山或坟产所涉法律问题,则明显关注不够。(3)管见所及,主要有王志龙:《近代安庆地区的坟地纠纷研究》,《中国农史》2014年第2期;刘昕杰、毛春雨:《传统权利的去精神化境遇:民国坟产纠纷的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5期,等。总体言之,学界对传统社会坟产所涉习惯权利的具体内涵及表现形式,理论上的概括和阐析涉及甚少,而坟产习惯在中国近代法律变革中之境遇,亦未得到充分讨论。本文旨在初步勾勒传统社会坟产习惯的大体概貌,并揭示坟产所涉习惯权利的丰富内涵,然后再剖析坟产这一特殊形态的不动产,其相关习惯权利在近代法律变革中被限缩为一种法定物权后,坟产秩序变动在民间法律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呈现的复杂面相。
一、传统社会的坟产保护相关民事习惯
秦代之前,关于坟墓保护之法律规定,尚难觅见。然相关史料表明,自汉代后法律已对坟产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性举措。如西汉衡山王刘赐“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有司请逮治衡山王”。(4)《汉书》上册,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534页。南北朝时,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北巡,“至阴山。有故冢毁废,诏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归仁。自今有穿坟垅者,斩之。’”。(5)《北史》卷2《魏本纪第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及至唐代,唐律设置专门罪名,对盗耕墓田、毁人坟墓,以及盗葬等严重侵害坟墓权利之行为科以刑罚。《唐律疏议·户婚·盗耕人墓田》规定:“诸盗耕人墓田,杖一百;伤坟者,徒一年。即盗葬他人田者,笞五十;墓田,加一等。仍令移葬。”对于盗伐坟地荫木,《唐律疏议·贼盗·盗园陵内草木》亦规定:“诸盗园陵内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盗他人墓茔内树者,杖一百。”(6)长孙无忌等著、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6—247、355页。宋代除因袭唐律上述律文外,复规定坟墓所涉土地、林木等不得典卖。如哲宗元祐六年(1091)刑部言:“墓田及田内材木土石,不许典、卖及非理毁伐,违者杖一百。”(7)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6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904页。元代法律也有相似规定。《通制条格》载皇庆二年(1313)圣旨云:“百姓每的子孙每将祖上的坟茔并树木卖与人的也有,更掘了骨殖将坟茔卖与人的也有。今后卖的买的并牙人每根底要罪过。”(8)黄时鉴点校:《通制条格》,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明清两代均严禁“盗葬”和盗伐他人坟地荫木,违者论罪。《大明律·刑律·贼盗》“发冢”条明确规定:
凡发掘坟冢,见棺椁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开棺椁见尸者,绞;发而未至棺椁者,杖一百,徒三年。招魂而葬亦是。若冢先穿陷及未殡埋,而盗尸柩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开棺椁见尸者,亦绞。其盗取器物砖石者,计赃,准凡盗论,免刺。若卑幼发尊长坟冢者,同凡人论;开棺见尸者,斩。若弃尸卖坟地者,罪亦如之。(9)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27页。
“盗园陵林木”条亦规定:“凡盗园陵内树木者,皆杖一百,徒三年。若盗他人坟茔内树木者,杖八十。”(10)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27页。《大清律例·刑律·贼盗》“发冢”条和“盗园陵林木”条几乎完全复制了以上律文。(11)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410、372页。此外,清代还专设“条例”,严禁子孙将祖坟山地朦胧投献或私捏文契典卖:“若子孙将公共祖坟山地,朦胧投献王府及内外官豪势要之家,私捏文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田地给还应得之人……其受投献家长并管庄人,参究治罪。”(12)沈之奇著,怀效锋、李俊点校:《大清律辑注》,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以上为各朝关于坟产保护之立法概略,可见其相关规定较为简赅。清代司法档案和判牍、民间各类族谱族规,尤其是民初民事习惯调查报告,载有大量各地关涉坟产之民事习惯。这些习惯规范,较之于国家法涉及面更广,内容也更为丰富,其与国家法共同构成传统社会维护坟产秩序的规则体系。要言之,这些民事习惯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其一,坟地权属确认。关于坟地的权属凭证,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大清律例》增例如下:“凡民人告争坟山,近年者以印契为凭,如系远年之业,须将山地字号、亩数及库贮鳞册并完粮印串,逐一丈勘查对,果相符合即断令管业。若查勘不符,又无完粮印串,其所执远年旧契及碑谱等项,均不得执为凭据,即将滥控侵占之人,按例治罪。”(13)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3页。以上规定过于生硬,导致司法实践及民间习惯往往突破此项规定,采取更为灵活的坟地权属认定办法。如清代判牍《槐卿政迹》载:萧姓和刘姓因坟山争讼,萧姓仅有族谱为凭,“与例据不符”,但知县沈衍庆仍“揆情度理”,“断令该山坟墓树株俱归萧姓醮掌经理”。(14)杨一凡、徐立志主编:《历代判例判牍》第10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207页。另如福建光泽县习惯:“远年坟山,多无契据,而凭家谱管业。”安徽各地,多用“宗谱刊载坟地境界”。直隶清苑县习惯:“持有茔地图即足为茔地所有权之确证。”江西乐安县习惯:坟地权属及其范围,“以墓碑、界碑为凭”。(15)胡旭晟等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226、18、258,151、366、18、28—29、61、68、76、91、111—116、151、156、158、260、320、380—381,367、379,236、242、301、306、321页。由是可见,依据各地习惯,确认坟地权属之凭证,除印契外,复有族谱、茔地图、墓碑、界碑等。
其二,坟地的交易流转。传统的孝亲伦理要求子孙永远固守祖宗坟地,因此坟地在一般情况下被限制成为买卖的标的物。但民间因贫而典售坟地之现象,亦不能免。不过就各地习惯而言,坟地的交易和流转规则,仍与其他田土交易存在显著差别。如山西祁县和陕西长安县习惯:“坟地只准典质,不准绝卖,即典质契约载有回赎年限者,逾限亦得回赎。”直隶、黑龙江、山东、福建、陕西、江西等所属各县,原则上亦禁止坟地绝卖,即便是典卖,仍遵奉“卖地留坟”,或允许卖主日后葬坟之惯行。(16)胡旭晟等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226、18、258,151、366、18、28—29、61、68、76、91、111—116、151、156、158、260、320、380—381,367、379,236、242、301、306、321页。“卖地留坟”习惯的存在,一则由于长期以来法律对坟地买卖进行严厉打击,典售坟地时将茔地所有权予以保留,可规避法律制裁;二则因民间普遍信仰“风水”之说,随意迁坟不仅有悖礼教孝义,而且可能贻害子孙。
其三,“讨送阴地”。中国传统文化素重“入土为安”,贫困无地之人,为安葬亲属,只得向他人讨要一坟之地,这就促使民间“讨送阴地”习惯的出现。如陕西商南县习惯:“民间贫乏之人,寸土皆无,设遇家族死亡,即须央人到地主(指佃户对地主言)或亲朋处讨土埋葬。”该省镇巴县习惯:“贫乏之人无力购买坟地,则须向有余地之人讨地葬坟,地主出立送字,亦有不立字据者。”(17)胡旭晟等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226、18、258,151、366、18、28—29、61、68、76、91、111—116、151、156、158、260、320、380—381,367、379,236、242、301、306、321页。从他人处讨得阴地,并不意味着讨地人获得了坟地的所有权,原土地所有人只不过给予其小块土地内的“葬坟权”,以及将来按时祭扫之权。
其四,坟地风水。风水信仰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认知系统,并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的文化与生活世界的一部分”。(18)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坟地作为祖先的体魄安放之所,关乎后代能否浸润祖先遗泽,故民间对于坟地风水的选择及其维护,一向极为慎重。如明嘉靖年间安徽绩溪《积庆坊葛氏族谱》载:“祖宗风水,子孙无许盗葬”,“求葬者罚银一两,许葬者罚银一两”。(19)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安徽当涂县习惯:“居民于公共祖坟山内,不准族人进葬新坟,盖一经添葬,即伤害公共风水。”江西赣南各县,坟墓“无论前后左右距离远近,苟他人工作有碍风水,必群起争之,因而酿成刑事者不少。”福建连城、闽清,以及湖南益阳等县习惯:新筑之坟与他人旧坟,前后左右应相隔一定距离,尤其不许“骑龙跨穴”。(20)胡旭晟等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226、18、258,151、366、18、28—29、61、68、76、91、111—116、151、156、158、260、320、380—381,367、379,236、242、301、306、321页。民初湖南湘潭《谭氏族规》规定:后葬之坟,“上下左右必离先葬者两丈五尺”,“永不得骑头牵脚、拦龙截脉、劈坟伤棺及盗葬插葬等弊。如违,经族长集议,登时掘出,轻按家法惩罚,重则送县究办”。(21)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下册,第791、841页。此外,坟地风水除涉及盗葬和坟地相邻关系外,民间尚有“风水树”“风水山”之禁约。巴县档案载:乾隆三十五年(1770),唐应坤因王仲一等“砍伐祖坟后千百年护蓄风水大黄连古树一根,惊犯祖坟”,将其具控案下。后约邻陈仕荣等劝王仲一将所砍之树退还唐应坤,并呈状官府请求息讼,蒙巴县县令首肯。(22)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292页。热河一带,因关乎风水,坟墓周围古树禁止砍伐;坟围相近之山,不准开取土石,官府勒诸碑石,悬为例禁。(23)施沛生编:《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2编《物权·关于共有权之习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第41页。民初安徽《黄山迁源王氏宗谱》亦载:“坟山树木,所以庇护风水,须时培植……如有侵伐损坏,责在当事人。”(24)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下册,第791、841页。
二、坟产所涉诸习惯权利
由于传统中国并无今日形式意义上之民法,故未催生出民事权利这一现代民法所特有的概念。在此,我们姑且概括地将坟产习惯所衍生出的诸种权利谓为习惯权利。所谓习惯权利,是指“经过长期的、连续的、普遍的社会实践而形成,并得到社会公认与共同信守,获得一定的社会道德权威与社会义务保证的习惯规则中所确认的一种社会自发性的权利”。(25)郭道晖:《法理学精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大致归纳,坟产所涉习惯权利,约有以下数端:
(一)坟地所有权
作为坟产主体之坟地,除具有安葬功能,亦为一种重要的土地资源,而民间也存在诸多关于坟地权属确认的习惯规范。张小也指出:“清代坟山争讼的复杂性深刻地反映了土地权利的特点”。“坟山的归属基本上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固定态势,证明权利的则是种种民间习惯。”(26)张小也:《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29页。需强调的是,传统社会的坟地所有权,虽然具有某些当代民法中“不动产所有权”的表征,但与后者仍不能等同视之。其最突出的差别,即一般情况下坟主后代无权对坟地进行典质、买卖和随意处分。质言之,坟地所有权是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不动产所有权。
其一,坟主后代无权处分作为共有产权的坟地。祖坟与祠堂、祀产、族谱等共同构成了宗族的实体元素,并在宗族内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27)冯尔康:《清代宗族祖坟述略》,《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由于聚族而居,坟地的占有往往以宗族为单位,由坟主后代或家族实行共同占有。“民间的墓田最初是家庭中的普通用地,一旦作为墓田,为了保证其专项用途,便要一代一代整体传继下去,不分割也不典卖。”(28)邢铁:《宋代的墓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故作为坟主后代的个体,其任意处分坟地或出卖旧穴,当然也会受到其他家族成员的阻挠甚至强力干涉。福建安溪钟山《易氏宗谱》载有一起明万历年间盗卖坟山事例:“易乔俊先年与兄西泉用银买得产山土名均竹一所,各择风水一穴。今俊因欠银用度,愿将已葬风水迁起”,卖与他人造坟。“易氏宗亲为此屡赴道府控究,并费银赎回了乔俊的献批及盗卖旧穴字批。乔俊等也奔逃德化”。(29)安溪钟山《易氏宗谱》(民国四年重修刻本),转引自陈进国:《风水信仰与乡族秩序的议约化》,詹石窗总主编:《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第8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59—460页。再如光绪年间安徽《黄山仙源村杜氏家法二十二条》规定:“祖坟前后左右私卖与人,未葬者责令赎回,已葬者送官惩治、请令迁移外,仍罄其家产以抵讼费,讼结后其人逐出境外,永不许归宗。”(30)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下册,第546页。以上载述,生动地展示了传统宗族力量如何对坟产交易形成了有力制约。
其二,坟主后代迁葬鬻坟,既有悖伦理孝道,亦破坏自家风水。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元素,故崇祀祖先、保护祖坟,亦成为后代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清代乡约有云:“盖德莫大于泽及枯骨,惨莫甚于侵削荒坟。平世子孙无有不祭扫其先茔,保全其祖垄者。”(31)一凡藏书馆文献编委员编:《古代乡约及乡治法律文献十种》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但是,在风水信仰盛行的社会氛围下,坟地风水极易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富者艳羡他人吉穴欲得之,贫者为存活而迁葬鬻坟,这使得坟地有时难免成为交易的对象。但出售坟地之行为,与传统孝悌观念相悖,亦遭到社会的强烈谴责。对于卖主而言,将祖坟起葬他迁,亦恐破坏自家风水,若非万般无奈,不会轻易为之。
(二)上坟祭扫地役权
地役权为近代中国舶自大陆法系物权法中的一个法律概念,中国固有法中并无形式上的对应物。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民间仍存在涉及通行、流水、放牧等事实意义上的地役权。中国传统社会类似于地役权方面的民事习惯,最具特色者为“上坟祭扫权”。坟墓是子孙后代对已逝先人进行祭扫之所,从私法意义上看,“坟茔所表现之人格性权利本质当属于祭祀权,但其物化形态之权利则属于无期性、无偿性土地用益物权”。(32)刘云生:《物权法》,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为保护祖坟,并确保祭扫活动能定期和长久地进行,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又衍生出“卖地留坟”这一特有习惯,即出卖田地时对祖坟地进行保留,同时亦保留坟地主人经过他人土地定期上坟祭扫的权利,这本质上是一项特别的“地役权”。此外,前已述及,民间尚有“讨送阴地”之习惯。此种情况下,送阴地人虽仍享有该块土地的所有权,但讨得阴地之人实际上获得对该地所葬之坟进行祭扫的地役权。
(三)逝者及其后代人格权
人格是道德、社会及精神的存在。人格权究其实质为一种“受尊重权”。(33)曹相见:《人格权支配权说质疑》,《当代法学》2021年第5期。坟墓系祖先崇拜之物化载体,在乡土社会,在一般民众心目中,逝去之先祖虽已入土为安,但仍具有某种隐性的人格,仍应获得应有的尊重。因此,“祖坟是被人格化的独立于后代个人财产的特殊遗存”。(34)肖泽晟:《坟主后代对祖坟的权益》,《法学》2009年第7期。同时,祖墓除安放祖先体魄外,对于活着之后代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即祖坟乃子孙对先祖寄托哀思、“奉先思孝”的载体,并关乎后代的人格尊严。所以墓主的人格权,又进一步投射于其后代身上,转变为其仍然活着之后代的人格权益。民间习惯对于毁坟、侵葬等有着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即隐含着保护坟墓主人及其后代人格权这一价值考量。由是观之,逝者及其后代的人格权,构成了坟产所涉习惯权利中精神性权益的重要内容。
(四)风水权
风水权并非现代民法上的概念,准确地说,其只是中国传统社会依据民间信仰和民事习惯所形成的一种精神性权益。风水观念内蕴着一种独特的文化逻辑和意义图式。就中国传统社会的风水信仰及习俗来看,祖坟“地相的吉凶或管理的良否被认为左右着子孙的命脉”(35)[日]滋贺秀三著,张建国、李力译:《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从而决定着整个家族的兴衰。坟产所涉之风水权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坟墓及其周边之风水荫木不得随意砍伐。如遮荫风水的坟木被他人无故砍伐,坟主后代必群起而攻之;其二,坟地涉及的风水相邻权不容侵害。维护祖坟风水,如制止外族或本族成员的“侵葬”“盗葬”,以及对祖坟风水的“截脉”行为,是全体家族成员的共同义务。由于祖坟可以充分满足戚属获得风水荫庇的利益想象,故亦承载着某种不容他人侵害的精神性权益。与坟产相关的风水信仰,作为一种乡族的社会记忆,成为家族成员所认同的文化象征和意义秩序,有效地安排并制约着乡族社会一些功利性的坟产物权变动行为。
三、坟产习惯权利在中国近代物权立法中的限缩
中国近代的物权立法,肇始于清末之《大清民律草案》,经由民国《民律草案》的承袭,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中华民国民法》的颁布和施行,一个正式的、形式上较为完备的物权法律体系得以最终确立。中国近代的物权立法主要以德日等国民法典为蓝本,虽对固有法中的所有权、永佃权、典权、质、押等物权性内容有一定关照,但忽略之处甚多。以坟产而言,其被纳入一般意义上的不动产范畴后,附着于坟产之上的部分习惯权利直接转化为法定物权,但较之于其他不动产所体现出的若干特有之习惯权利,则被剥离于新式法律之外。
宣统三年(1911)完成之《大清民律草案》,其“物权编”第一章通则第987条首倡“物权法定原则”,该条规定:“物权,于本律及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不得创设。”(36)杨立新点校:《大清民律草案 民国民律草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下文对《大清民律草案》“物权编”之说明,参见该页及其以下部分。第二章所有权部分,详尽规定了不动产之取得、转让、登记等事项,不动产之使用、收益、处分各项权能,以及不动产相邻关系、共有关系等。第三章和第五章就地上权和地役权分别予以规定。第六章规定了不动产的抵押和质押行为及其法律效力。第七章对不动产的占有进行了细致规定。依据上述立法框架,坟产亦被硬性地纳入到一个整体意义上的不动产物权法律体系中进行调整,并与土地等其他不动产同质化,完全限缩为一种法定物权,而附着于坟产的诸多习惯权利,尤其是精神性权益,则游离于这个欧日版的物权制度之外。
1925年至1926年间完成之民国《民律草案》,其“物权编”在编纂体例和具体内容上对前次草案进行了以下修订:删除前草案“物权编”第六章“担保物权”部分,将抵押权、质权各立一章,并增设典权一章。(37)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748、770页。典权的纳入,说明立法者对固有民事习惯已更为重视,但其对坟产典质的特殊性,并未予以任何特别规定。
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1929年10月30日第202次会议提出《民法物权编立法原则》十五条,其第一条明确指出:“物权除于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外,不得创设。”该条“说明”亦称:“物权有对抗一般之效力,若许其以契约或依习惯随意创设,有害公益。”(38)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748、770页。嗣后公布的《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编”第757条,遂完全复制前述第一条原则之表述,事实上再次重申“物权法定原则”(39)吴经熊主编:《中华民国六法理由判解汇编》第2册,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48年版,第657页。下文对《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编”之说明,均参见该页及其以下部分。,这使得未被纳入法定物权范围内,与坟产相关的其他习惯权利,在立法层面仍被排除。此外,在其他各章所涉之不动产所有权、地上权、地役权、抵押权、典权等相关规定中,亦未对坟产予以任何特别规定。尤须注意的是,《民法物权编起草说明书》虽指出,“我国祠堂、祭田、合伙等,均为公同共有关系,此编按照立法原则,并参酌我国固有习惯”,“设公同共有之规定”。(40)台湾“司法行政部”编:《中华民国民法制定史料汇编》下册,1976年印行,第574页。然揆诸其公同共有之相关法条,仍是将坟产的公同共有问题,纳入一般意义上的不动产公同共有关系中进行调整,从而抹除了坟产公同共有关系的特殊性。总体言之,《中华民国民法》一如前两次草案,仅抽象出坟产与其他不动产相同的部分物权性内容,对坟产所涉其余习惯权利,未作任何区别性对待。
传统社会坟产所涉诸习惯权利,虽以物为载体,但内嵌了财产性权益和精神性权益两方面内容。中国近代的物权立法,将坟产视同为一般意义上的不动产,既缩小了其财产性权益的范围,也基本排除了坟产所涉精神性权益。展开而言,仅坟产所涉部分习惯权利上升为法定物权,其余大部分,如坟产人格权益、祭扫地役权、特殊共有权、风水权等,在新的物权法律体系中基本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四、中国近代坟产诉讼中涉及坟产习惯之裁判
由于民间习惯的顽强存续能力,导致近代贩自欧日的新式物权法律制度,在应对那些由来已久的坟产纠纷及诉讼时,面临着“制度供给不足”的困境。近代以来的坟产诉讼实践表明,坟产习惯权利与法定物权事实上呈现一种相互冲突、相互妥协,又彼此胶着的势态,其在一种程度上展示了坟产习惯在中国近代法律变革中所面临的一种尴尬境遇。
(一)民初大理院对坟产习惯的折衷安置
民初司法实践中,因《大清民律草案》未及施行,司法机构关于物权事项之裁判主要援用“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但后者涉及坟产之规定甚少,于此法制转型时期,民初大理院遂参酌固有习惯,并糅以大陆法系物权法理,借助判决例和解释例将坟产习惯加以折衷安置。
第一,将“坟”与“坟地”的产权进行分离,并一定程度上认可旧契、碑、谱等对坟产权属的证明效力。在固有习惯中,“坟”与其附着之土地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坟冢是确认坟地产权的实体存在。近代移植于大陆法系的不动产物权理论,只明确了土地的不动产权利属性,“坟”是否可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动产,实践中仍生疑义。民初大理院在审理坟地讼案时,确认了“坟”亦为一种可与“坟地”彼此分离的特殊不动产,并将此作为裁判坟地纠纷的法理依据。如大理院八年(1919)上字第679号判例要旨谓:“坟与地并非必属于同一人所有,苟能证明此地属甲派所有,即不能因其地内葬有乙派下之祖坟,遂谓其所有权业已移转。”本案中,上告人胡应柳等与被上告人胡尚厅等诉争坟地内有坟茔20余冢,被上告人诉称,该地所厝之坟均系其祖坟,有业簿及粮串为凭。上告人辩称,该地所厝坟茔除盗葬有被上告人祖坟一冢外,其余均系自家祖坟,有业簿、粮串、宗谱等为凭。大理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应调阅宗谱,查明讼争地内坟茔究为何人祖坟,再审核业簿及粮串,参考其他凭证,认定该地历来由何人管业。同时亦强调:坟与地并不必然属于同一人所有。如有地属于被上告人之证明,固不能因地内多葬上告人之祖坟,即认为该地所有权归上告人。(41)黄源盛辑纂:《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物权编》上册,台北犁斋社2012年版,第257—259、426—427、541—544页。大理院十年(1921)上字第50号判决例则再次重申这一裁判要旨:“坟之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非绝对不可分离,如自己土地内葬有他人坟茔,确系年湮代远者,自不能不许其认坟祭扫。”(42)郭卫编、吴宏耀等点校:《大理院判决例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341,347、351页。在以上两则判例中,大理院巧妙折衷物权法理和固有民事习惯,肯定“坟”亦为一种可与地相分离的特殊不动产,且坟主后代享有对坟茔进行祭扫的地役权。
另,大理院九年(1920)统字第1255号解释例,就无契据坟山产权之确认予以详细叙明:“证明不动产所有权,固不以契据为唯一之方法。即如历来完全行使所有权之事实,及其他曾经合法移转之证明,亦可据为证凭。”(43)郭卫编著、吴宏耀等点校:《民国大理院解释例全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64—965、856—857、1074页。大理院十五年(1926)上字第959号判决例,亦斟酌各地习惯,创制了“告争远年坟山不以执有完粮印串及山地字号亩数为限”这一判例要旨。(44)郭卫编、吴宏耀等点校:《大理院判决例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341,347、351页。
第二,依据物权法理,明确了坟产的公同共有性质,同时赋予其一定的特殊意义。坟产往往以一种公同共有的产权样态呈现,作为坟主后代的个体成员,无权私自处分坟产。大理院在司法实践中,亦借助判决例界定了坟产的公同共有性质。大理院四年(1915)上字第1816号判例要旨谓:“茔田之性质,在现行法上亦属公同共有,而非分别共有,在公同关系存续中,原不准共有人之一人处分其应有之分。”本案中,上告人石玉书与被上告人石翁氏因卖田涉讼。被上告人称讼争田亩系其独有,石玉叶私自盗卖给上告人,对于被上告人当然不发生法律效力。上告人则称讼争田亩系石玉叶祖上茔田,虽属石玉叶与被上告人共有,石玉叶出卖其应有之分,于法当然有效。大理院审理后认为:茔田之性质,属公同共有而非分别共有,石玉叶擅卖其应有之分,于法自非有效。(45)黄源盛辑纂:《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物权编》上册,台北犁斋社2012年版,第257—259、426—427、541—544页。此后,大理院四年(1915)上字第2267号判例要旨又进一步细化了上述规定,其谓:“茔地为公同共有性质,非遇有必要情形,经派下各房全体同意,或已有确定判决后,不准分析让与或为其他处分行为,违者其处分行为无效。”当然,坟产的公同共有关系,并不限于坟地,还包括坟茔树木。如大理院九年(1920)上字第903号判例要旨规定:“祖茔树木,非子孙全体同意,不得砍卖。”(46)郭卫编、吴宏耀等点校:《大理院判决例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341,347、351页。以上判例要旨,与固有习惯关于坟产共有关系之旨趣互为暗合。
需指出的是,大理院在肯定坟产公同共有性质的同时,又依循固有习惯将公共坟山进葬作为一种特殊情形予以区别对待。在大理院十五年(1926)上字第963号判决例中,涉讼坟山为公共殡葬之地,上告人应保山为祖母营葬,被上告人应国桢等进行阻拦,两造因此涉讼。大理院审理后认为:“公同共有之祖茔山地,各共有人能否进葬,应以向来有无进葬事例或特别规约为断,与通常处分公同共有物概须得他共有人同意之情形,原不相同。”(47)黄源盛辑纂:《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物权编》上册,台北犁斋社2012年版,第257—259、426—427、541—544页。
第三,衡诸习惯和情理,肯定了“坟”的身份权属性。“坟”与现代民法一般意义上的物不同,其蕴含着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精神性权益。换言之,“坟”其实是一种身份权或人格权益的外在表现形式。清末民初的物权立法,虽然依照大陆法系物权法理将坟产的精神性权益予以剥离,但民初大理院仍采取了一种务实的裁判取向,肯定了“坟”的身份权属性。如大理院六年(1917)抗字第75号判决例,认定两造争执坟内尸体案件,其第一审应由地方审判厅受理,初级审判厅无管辖权。大理院八年(1919)统字第1085号解释例,则依上述见解对坟产的诉讼管辖权进行扩大解释,强调两造争“坟”之诉讼,“仍系亲属事件,应归地方管辖”。(48)郭卫编著、吴宏耀等点校:《民国大理院解释例全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64—965、856—857、1074页。这实际上将诉争对象,由“争尸”扩大为“争坟”。其后,大理院九年(1920)统字第1425号解释例,又就争坟与争地之诉讼管辖权再作释明:“凡坟山争执,涉及祖坟,依照大理院解释,固属亲属事件,应归地方辖管,但遇有山地经界涉讼,并不以解决坟冢为前提,则在第一审固得分别判决。”(49)郭卫编著、吴宏耀等点校:《民国大理院解释例全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64—965、856—857、1074页。以上解释例虽然主要针对诉讼程序问题,将“争坟”之诉与“争地”之诉的诉讼管辖权加以区分,然究其本意,实际上是肯定“坟”的身份权属性。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裁判对坟产习惯适用的限制与妥协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中华民国民法》颁布实施后,司法机关对于坟产讼案之裁判,一方面依据新的物权法及其原理对坟产习惯的适用范间加以限制,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兼顾民间行之已久的社会惯习,对部分坟产习惯进行有限确认。
1.坟产习惯适用范围在司法实践中的进一步限缩
首先,坟产诉讼被限定为财产类诉讼,坟产的身份权属性被彻底排除。坟产争讼一般涉及两种情况:一为告争土地权,二为系争尸骸之所属。民初大理院认为第二种情形为涉及亲属关系的人身权诉讼,适用特别程序由地方审判厅管辖。但南京国民政府修正民事诉讼律对此并无明文规定,湖南高等法院就其究应适用何项程序,曾呈函最高法院请求解释。最高法院以十七年(1928)第99号解释令复函称:“系争尸骸案件,在现行民诉律并无特别规定,自属通常诉讼。”(50)《解释系争尸骸之坟山涉讼适用何项程序函》,《最高法院公报》第2期,1928年9月1日,第240—241页。最高法院就谢培成等与皮戬谷等因确认坟茔所有权涉讼所为十七年(1928)民事上字第858号判例,亦纠正了湖南高等法院将该案认定为人事(身份权)诉讼的判决。其判例要旨称:“坟地诉讼虽有时涉及坟内尸体,在现行法上无认为人事诉讼之根据。”(51)郭卫、周定枚编:《最高法院民事判例汇刊》第3期,上海法学书局1934年版,第18—19页。以上解释令和判例,将两造诉争坟内尸骸之案件,亦划归普通诉讼范畴,完全否定了坟产的身份权属性。
其次,对坟产的公同共有性质进行了限缩解释。如最高法院于1933年7月判决之黄炳祥等与傅朝明等因确认山场共有权上诉案中,两造在讼争之苻家山各葬有祖坟,黄炳祥等将该山之一部卖给陈平甫添葬,傅朝明等出而讼争。本案争议焦点为:两造系争坟山究竟为普通共有,抑或为公同共有。最高法院依据《中华民国民法》第819条,即“各共有人得自由处分其应有部分”之规定,认为该共有坟山系普通共有,各共有人得自由处分其应有部分,并据此判决傅朝明等败诉。(52)《黄炳祥等与傅朝明等因确认山场共有权及请迁坟事件上诉案》,《司法公报》第97期,1933年11月18日,第17—19页。该判例中,最高法院并未将坟产完全视同为公同共有,而是根据具体证据将坟产分为公同共有和普通共有两种情形,并且认为普通共有的坟产,各共有人得自由处分其应有部分,事实上扩张了坟产共有人对坟产的处分权。
2.部分坟产习惯在司法实践中仍得到有限确认
《中华民国民法》所确立的物权法律体系,难以完全涵摄与坟产相关的习惯权利,这又使得司法机构在应对复杂多绪的坟产诉讼时,被迫采取一种妥协姿态,对部分坟产习惯进行有限确认。
其一,并未完全否认坟产的精神性权益。最高法院二十四年(1935)民事上字第2657号判例要旨称:“当事人以应否迁坟为诉讼标的者,仍为财产权上之诉讼”,“惟葬坟之地因与通常使用方法不同,在当事人间,恒于普通地价之外,含有精神上之价值,故计算上诉利益时,亦应将此项价值一并计入”。(53)《最高法院民事判例》,《法律评论(北京)》第13卷第13—14期合刊,1936年2月2日,第49页。该判例要旨肯定了坟产包含有坟产所有人的精神性权益。
其二,对于坟产权属的确认,亦在一定程度上关照了固有习惯。如最高法院十七年(1928)民事上字第731号判例要旨称:“坟茔所有权与坟茔以外之山地所有权原属各别独立。”(54)《浙江童樟银等与朱中芳等因确认坟上所有权涉讼上告一案》,《最高法院公报》第3期,1929年3月1日,第9页。该判例要旨事实上仍认可坟茔之所有权可以独立于坟地所有权,其与民初大理院的裁判思路如出一辙。安徽高等法院十九年(1930)三字第83号判决亦明确指出,讼争山场究属何造所有,应以该山场内之坟墓为何姓所有作为判决的先决条件。(55)《安徽高等法院民事判决:十九年三字第八三号》,《安徽高等法院公报》第5—7期合刊,1930年6月,第108—109页。此判决强调了“坟”与坟地应作为一个不动产整体看待的观点,与民间习惯中的坟地权属确认办法互为暗合。
其三,对禁止侵葬和坟茔禁步之民间习惯采取了一种迎合态度。在安徽高等法院二十一年(1932)三字第50号判决中,余传宣与曹植本堂就迁坟涉讼,安徽高等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讼争坟山为曹植本堂私产,他人不得自由进葬,并判令余传宣将所葬之坟起迁。(56)《安徽高等法院民事判决:二十一年三字第五O号》,《安徽高等法院公报》第3卷第1—2期合刊,1932年6月,第146—148页。在1937年湖南湘乡县的一起请求迁坟讼案中,李相云以李玉辉新葬之坟在其祖坟坟禁范围内有碍风水为由,向湘乡县司法处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李玉辉迁坟。湘乡县司法处经审理认为,李玉辉所葬新坟确在李相云祖坟坟禁以内,遂判令李玉辉起坟迁葬。李玉辉不服上诉至湖南高等法院,但湖南高等法院仍以同样理由驳回其上诉。(57)《湘乡县政府裁荣福与宋星堂等13起坟山纠纷案》,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28-14-260。固有习惯严禁在他人坟地侵葬,亦对坟禁事项有着明确的可操作的规定。以上案例表明,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司法实践中,对上述习惯权利,仍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维护。
结 语
传统中国基于自身独特的祀祖传统和文化观念,在民间长期的坟葬实践中,衍生出系列与坟产相关的习惯规范。从民事法律的角度观之,这些与坟产相关的民事习惯,并非仅停留于客观事实层面,而是以一种习惯权利的形式维系着乡土社会的坟产秩序,调整着民间围绕着坟产处置和保护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近代以后,经由大陆法系物权制度的示范和牵引,中国最终在法典层面确定了一个在形式上较为完备的物权保护体系。这种新式的物权法律体系,又对基层社会的坟产秩序产生以下两种影响:一方面,“立法活动可能会废止自然形成的约定和惯例”(58)[意]布鲁诺·莱奥尼等著,秋风译:《自由与法律》,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坟产所涉之部分习惯权利,尤其是精神性权益,从法律层面被剥离;另一方面,成文法的简约化目标及立法技术又可能导致立法阙漏,当这种立法阙漏难以通过扩展性解释来加以弥补时,面对复杂的坟产诉讼,为实现坟产法律关系的有效调整,有时裁判者只能委诸固有习惯进行裁处,从而使得部分坟产习惯在司法实践中仍具有某种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