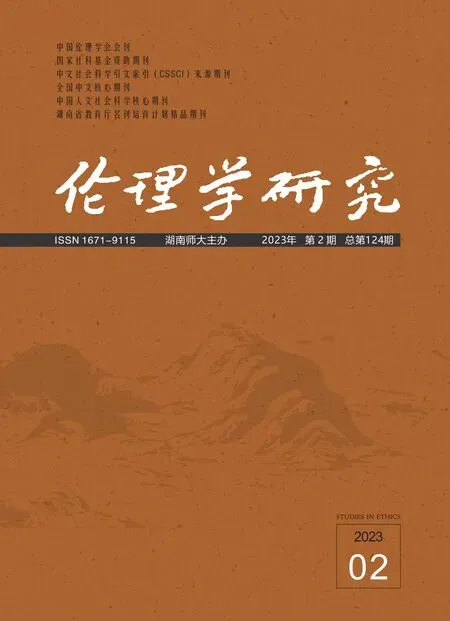约纳斯克服“人的形象”危机的两条路径
何振乾
人的形象问题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从希腊哲学传统到希伯来基督教传统,自笛卡儿以降,无数哲学家对“人的形象”(the image of man)进行着锲而不舍的界定,构成了一部曲折的思想史。自20 世纪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一批具有后现代视野的哲学家开启了反思现代性和现代哲学传统的思想历程,如西奥多·阿多诺、汉娜·阿伦特、汉斯·约纳斯和龚特尔·安德尔斯等,他们结合对现代技术的哲学批判,对人的形象进行了全新省思。本文以约纳斯为例讨论他克服“人的形象”现代危机的独特方案,亦即技术批判与责任伦理路径①约纳斯克服人的形象危机的两条路径既有不同的语境、方法和进路,又有一以贯之的立场和旨趣。概言之,解构性的筹备(技术批判)与建构性的解答(伦理诊断)共塑了完整路径。。
在约纳斯看来,技术时代的人类面临着一场存在论意义上的危机,即“人的形象”危机。该局面肇始于现代技术对人类存在的几乎一切领域的强力侵入,“技术已成为地球上全部人类存在的一个核心且紧迫的问题”[1](1)。技术-社会进步论,尤其是“技术乌托邦”(technical utopia),颠覆了启蒙哲学关于人的形象的现代神话,人的主体地位、在世处境、自我理解及其与存在者整体的关联诸领域,都在技术“希望”(hoffnung)中反遭危机②约纳斯视恩斯特·布洛赫为现代乌托邦的代言人,他以“责任原理”(Prinzip Verantwortung)反对后者的“希望原理”(Prinzip Hoffnung),二人立场殊异,但在未来伦理学的可能性视域下,“责任”、“恐惧”和“希望”在道德情感、方法论和乌托邦的人本主义边界诸层面仍可协调。。对人的形象的哲学反思与危机克服的有效行动迫切同一,其关键在于坚持“保存与保护”的原则,既规范人类行为尤其是技术活动的边界,又拯救关涉人的存在及存在之意义的形而上学观念。
我们有必要澄清人的形象问题的当代意蕴:其一,形象危机为何且如何在技术语境中集中显现?其二,约纳斯的理论诊断即责任伦理学的合法性如何确立?其三,新伦理学的责任主体如何建构,对道德实践有何意义?只有充分阐释以上诸题,我们才能回应技术时代“人的形象何为”与“人的本体论责任何以可能”的根本追问。
一、技术批判视域内“人的形象”危机
对人的形象问题的省思是审视西方哲学历程的一个特殊视角。自笛卡儿尤其是启蒙哲学以降,“人的形象”逐步脱离了上帝创造与神性自我的束缚,作为人的“理念”(idea)“本质”(nature)的外观和显现,代表着理性主体对“属人方式存在”(being qua man)的言说,在认识上享有客观事实的地位,在实践中则是一种根本性规范。在20 世纪警示科学技术危机的思潮中,约纳斯继胡塞尔、海德格尔之后,强调“人的形象”已深陷危机。他通过对医学技术、技术进步论和技术乌托邦的考察揭示了形象危机的多重面向,揭示了现代性反思的深具代表性的技术批判路径。
作为现代性事件的“人的形象”,其实质是人性与自然、自然与价值的二元论。二元论释放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潜能,但也造成了自然与人性的双重虚无。这一嬗变源于17 世纪以来科学革命所引发的西方思想的唯物主义转向[2](19),其成果之一即对自然内在目的的剥夺。“价值中立”原则和工具理性的滥用使自然堕入“冷漠”(indifferent)的深渊。自然丧失了内在价值,提供着科学分析和技术操作的对象物,它在物质-生产领域的丰沛实以精神和自由的匮乏为代价。自然的形象进而从神的造物、母亲(Mater)、沃饶的大地(家园)沦落到仅用来满足人类福祉的资源库[3](128)。另一方面,以“知识即力量”为代表的科学-技术乐观主义在加强人的权能时,亦令主体深陷存在的无家可归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制使得医学的伦理边界被模糊化,重构人的“自然进化遗产”(人体基因组)事实上已侵入公共议程。概言之,自然的人与人化的自然不再享有古希腊作为自足的“善本身”(good-initself)的可能,也失去了中世纪的神性光辉(恩典),而彻底沦为技术逻辑的对象化一环。
约纳斯的技术批判立足于他将虚无主义断定为西方文明之内在症结的识见。自古代晚期诺斯替宗教(the gnostic religion)的“反宇宙主义”强音后[4](296),这种思想痼疾以主流(或潜流)的形式持续生成、转捩。技术时代的境况在于,灵知主义“世界观”(Weltanschauung)中人之内在自我即“普纽玛”(pneuma)[4](301),无望于求助一个超验的、反自然的神即“佩雷若玛”(das Pleroma)的救渡,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只能以技术制造属人的一切:技术宰制的世界与技术-人。随着科学世界观为“现代进步”扫清了观念道路,技术潜能为技术-社会向善论提供了动力,技术乌托邦旋即突破思辨与实践的界限,成为“世俗化末世论”(a secularized eschatology)的施工图[5](15-16)。在此背景下,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对立成为20 世纪思想史的内在特征之一,约纳斯的技术批判则饱含警示。
首先,新医学提供了一种希望:在祛魅世界中以高技术设计、加工人的完美形象。现代宏大叙事以野心勃勃的进步论反对一切创世神话和前定和谐体系,“原始圆满”观念被“还可以更好”的技术逻辑所替代。生物技术使身体这个自然遗产成为“未来的遗传对策(基因外科)的可能性对象”[1](164)。约纳斯警示我们,要审慎面对医学上的诸可操作性,因为它直接涉及存在的开端与终结,触及我们做人的终极问题[6](97)。在医学领域,除去为了对象健康的治疗术,关于人的乌托邦从“灵魂不朽”下降到“身体不死”,进而要求更强大的技术魔力。随着形象观念失去本质规定,人的基因以功利标准被组织、编排、改造,形象被情境化地假定与重构。更重要的是,技术操作意味着人本身不再具有伦理价值即自足的“善”,而须经由技术改善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与人和自然的位格、意义相分离的价值恰好表明了一种去价值的虚无。约纳斯强调,当技术人以自身为对象而意图自我改造时,“可能预示着对人的征服”,即“技术对自然最后的剥夺”[5](15)。
其次,在技术-社会进步论中,Homo faber 的内涵由“匠人”转变为“技术人”,这标志着技术逻辑由外在物性向内在主体的僭越——既是对人的主体性干预,也是技术自主性的萌芽。约纳斯断言,“技术人”胜过了“智人”(homo sapiens)[5](9)。人对技术大工程的依赖以健全主体向一般对象物的沦丧为代价,约纳斯对现代技术与传统机械技术的考察提供了例证。第一,机械技术向对象物(无生命质料)的自然属性施加“克服”力,此活动的意向性从属于主体;现代生物技术则将人的身体“非人化”,通过剥夺其价值与尊严来获得伦理议程的许可。第二,技术逻辑的僭越消解了传统技术观的人类中心论倾向。前现代情境中,人和“对象-物”的价值边界不可逾越。人的存在自身为善;物的“‘有用性’是对‘人的利益’而言的”[1](134)。在此,“人只能作为目的而不能作为手段”可引申出:技术活动中“人即主体”的第一原则不可动摇,内在目的是人区别于其他存在者的根本特征。现代境况则表明,技术的内在动力即“进步强制”有着超越人的意志的潜能。技术自主性一旦实现,就意味着技术逻辑对人性的遮蔽,技术不仅关涉人的生活方式,还将重塑人的形象。这种危险“甚至是和潜在的形而上学意义的一次决裂”[1](129)。
最后,技术乌托邦要求重新定义“人”,但“真正的人尚未实现”这一论断必然导致人性尤其是当下人性的缺位。布洛赫阐明了“希望原理”作为哲学的根本命题,其核心乃是一种“尚未存在的存在论”(die Ontologie des Noch-Nicht-Seins)。“S 尚未是P”(S is not yet P)构成了人类进步的内在动力,成为P 是S 尚未但能够且应当达到的,借此S 才真正成其自身[5](199)。当P 指涉“真正的人”,“尚未本体论”就构成了乌托邦原型:环境的压迫造成了“尚未”事实,人性的超越与完满实现是社会大工程的使命。但这种未来主义蕴含着虚无危险,即认为“本性之恶”(the old Adam)所规定的人的形象是贫乏的、有待解放的,进而过去的都是暂时的、缺乏最终价值的“史前史”(prehistory)。基于此,“当下”在本体论上沦为“未来”的附属:一种必要的过程、手段甚至牺牲品①约纳斯关于“当下”的思辨有三个情境,一是批评海德格尔此在存在论中“当下”的价值缺失,二是揭示新陈代谢活动中“当下”的生存论意蕴,三是阐发责任伦理中“当下”的人与未来同胞的伦理关系。据此,约纳斯既突出了存在者个体当下的生存意义与时间性之维,也关切到他与未来人类的伦理关联。。
概言之,技术乌托邦这种更为绝望的虚无主义是人的形象丧失源初意义后的现代产物。在海德格尔“此在”趋向本真性的行动“把这种绝对形式主义的决断上升为最高的道德准则”之时[7](192),在布洛赫“一切过去史都是真正的人的史前史”论断和对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构想中[5](143),约纳斯都敏锐地察觉到了危机。现代乌托邦力图以技术(作为最佳方式)创造性地实现“人间天堂”,但其内在危险即海德格尔意义上技术作为存在者之用对存在真理的遗忘,约纳斯将此进一步揭示为人的形象的现代虚无主义。
二、责任伦理的理论诊断与创见
由于“人的形象”现代危机无法在技术批判视域内完全暴露与克服,约纳斯因此以责任伦理寻求积极的诊断路径。为了有力回应现代技术症候群,新伦理学必须合法且有效地要求人类承担一种存在论责任。约纳斯通过重新阐释自然目的论和客观价值论,主张自然厌恶生存的无目的,存在拒斥善本身的虚无。他将“责任命令”(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奠基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存在论之上,在克服形象危机中开启了伦理学的未来视域和超越“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的可能。
约纳斯的伦理诊断超出了规范伦理和应用伦理的一般界限。传统伦理学和当代技术伦理无法应对人的形象困境,前者过于狭隘和无力,后者则过分膨胀和强力。在技术大赌博中,“有一个形而上学层面……一种‘绝对’,作为至高而又易受诘难的责任,把保护它自身的完整性这个最高职责加诸我们”[5](33)。责任伦理需要“绝对”(absolute)来维护,由此才能从形而上学基底展开其现实创造性,亦即我们行为的原则和规范。约纳斯将“绝对”概念阐释为关于“存在”(being)的生存论和价值论。走出虚无主义的关键在于,活生生的自然与有机体表明存在克服了虚空,它是内在目的和客观价值的源头,亦是人的责任根基。存在自行发出“应该-去-存在”(Ought-to-be)的命令,道德主体的伦理回应则彰显着人的自由,亦即负责任的在世存在。
技术批判要求伦理诊断超出传统伦理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同时代性局限,基于自然和历史的价值向度,去追问“人曾经生存的基础、未来生存的权利和现在生存的伦理责任”[8](69)。责任伦理的奠基既需要寻求生命现象和理性事实的双重辩护,还需保障存在发出道德命令的权利,达到“是”(Sein)与“应当”(Sollen)的统一。换言之,只有确立价值的客观实在性,“保护存在的约束性责任才能产生”[9](13)。约纳斯的伦理诊疗主要在于对自然目的论和客观价值论的创新。
约纳斯考察了技术人工物、主体性存在者(有机体)、前意识的自然界三个领域的目的论状况。他以“连续性原则”确证了目的以潜在抑或实现(生命)的方式在自然整体中生成。首先,有效性目的表征在有机体的生命活动中,自由寓于生存而非形而上学的主体即“自我”的先验统一,其最初形式源于新陈代谢。“有机体就物质而言并非同一的,但它通过不滞留同一物质而使自我持存。”[10](76)间接性、功能性的形式同一使得有机体从与物质的直接同一中获得解放,进而由物质领域的因果必然性进入到生命自由领域。其次,约纳斯将无主体的主体性即广义的精神要素寄托于生命的原始欲望乃至其物质基础中。前意识的自然界通过有机体来显现自身,“它以非主体性的形式将目的或类似物泊入自身”[11](92)。自然界的内在目的呈现出丰富的现实性、差异性和生成性。约纳斯并未诉诸自然拟人论或科学还原论,而是扩展了目的的一般领域,“把它从显而易见的主体性顶峰扩展到隐蔽于其中的存在的原野”[5](71)。最终,在人这里,内在目的凭借自我意识和意志力量充分彰显,具化为技术人工物中的意向性投射,乃至泛滥为乌托邦构想。
约纳斯以“善本身”概念澄清伦理学的价值基础,进而确立责任命令的合法性。首先,善的或有价值的事物,“当它本身如此,而不单单承蒙某人的欲望、需求或选择时,其观念便指涉这种事物:它存在的可能性即蕴含着存在或成为现实的要求”[5](79)。有别于屈从于主体欲求和技术逻辑的善,只有客观性的善才具有伦理自足性,责任命令只能由后者发出。善本身的内涵即目的性,亦即“拥有任何目的的纯粹能力”[5](80)。精神要素在自然界的广泛存有显明了目的能力的普遍性,善本身在自然中被连贯地要求、生成和实现。自然并非冷漠深渊,它既是人性的目的论开端,也是生命内在价值的源头,蕴含着伦理的可能。
其次,存在的“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回应了善本身的“应该”。责任伦理由本体向实践的下降在于:善本身自行要求实现进而对行动者(agent)发出“应该”的诉求。存在与“应该存在”的勾连体现在善本身和践行善的主体意志的共同在场。一方面,存在关切自身并抵制“虚无”(nihil)。存在与非存在的殊异乃“诸价值中最基本的价值,第一个普遍的‘是’”[5](81)。“是”作为源初价值(善本身)的自我肯定,乃行为价值(诸善)之所以可能的源头和依据。另一方面,存在的优越性并非先验阐明,而在有机体的生存中显现或被体验为“应该存在”。主体性愈完善,存在的要求愈被感知为责任命令而非自我保全冲动。约纳斯指明,在生与死的对位中,“存在的自我肯定成了个体存在者独自的努力”[5](82)。有机体与生俱来处于必死性与时间性之中。借助新陈代谢这个积极的自我整合,“生命赋予了‘个体’术语以实质:只有它才能产生个体的本体论概念,而不唯是现象学概念”[10](79)。存在的自我肯定通过生命活动实现为主体的伦理关切和自然价值的丰沛。约纳斯在此克服了以机械论为代表的“死亡本体论”(ontology of death)之窠臼[10](11),赋予了伦理学观照生命现象的新视域。
最后,责任伦理须达成从“意愿”(willing)到“义务”(obligation)的转变,需确证责任是以人的方式存在的本体论负担。自然界自发生成目的性存在(生命),有机体的自我保存发自本能,唯就人而言,内向性目的才可能展开为道德诉求。传统伦理学不必以“应该存在”为第一律令,现代人则颠覆了自然目的的实现方式。善良意志和志向伦理无力向技术资本主义要求一种新责任:以“俭省”“克制”“适度”为美德,去关切自然和人类的未来。约纳斯表明,就人而言,“存在”盲目的自我规定的“是”获得了义务性力量,恰是缘于人的自由[11](106)。由新陈代谢到自我意识,主体性存在者体现着“生命进化中的进步原则”,作为自然内在目的性的最高成果,人的自由实践不得不回应伦理召唤。在责任伦理视域下,“应该存在”要求人关切生命的共同利益,这是自然与人性相统一的“法”,伦理行动则成就了人的“义”。概言之,“人是我们所知的能承担责任的唯一存在者”[9](101),承担责任是以人的方式存在的根本特征。
伦理诊断揭示了形象危机的深层维度:自然目的的最高实现(人的自由意志)在技术宰制中反过来威胁着目的性的其他可能形式——有机体乃至自然整体的长久生存。“唯独在人那里,力量才通过知识和主观意志从自然中解放出来,才能变成对人和自身而言是致命的东西。”[11](163)知识和技术-权力的新量级代表了主体性神话的过度施行,人的形象危机要求我们构想责任主体的现代重建和负责任的道德实践。
三、责任主体的伦理重建与道德实践
奥斯威辛事件宣示了启蒙运动和理性生活指南,亦即现代性价值的脆弱性,“人们需要恢复负责任的规范和原则,重提责任问题并为之辩护”[3](1-2)。政治灾难和技术风险的双重困境反映了危机的紧迫性,自然与人性的双重虚无表明理性神话特别是主体性形而上学被工具理性和技术宰制所消解。为了有效落实责任命令,约纳斯以“责任主体”充实了人的形象,以责任感和敬畏感激发道德行为。在反思现代性中探寻“思”对“在”的责任和此在对世界的伦理关切,是约纳斯思想的独特品格,也是他对主体性哲学的嬗变。
重建责任主体需要对与约纳斯相关联的人的形象观念做一检视。在奥古斯丁神正论中,上帝保证了创世完满和世界秩序的善,恶的存在归因于人对自由意志的滥用。行动者被规定为自由意志与罪责的双重承担者,作为上帝形象(形式)的实存展开,人的义即遵从绝对者的召唤。近代科学技术和启蒙理性加强了人的权能,“主体性”成为哲学的标志性观念。主体意识的觉醒带来了人从神性、自然、宇宙诸绝对者领地中的解放;但人与神圣秩序的疏离也意味着主体“不可能将责任推给另外一个什么主管”[12](52)。康德在实践自由层面以理性的自律确立了义务论的道德主体。“理性事实”(Faktum der Vernunft)为道德法则提供了根据,意志的自由决断保证着有限理性存在者的行动出于法则。但恰如马克思·韦伯所言,与“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相比,“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缺乏对行为后果的重视[12](51)①甘绍平先生将Gesinnungsethik 译为“良知伦理”,实则译为“信念伦理”或“志向伦理”更为妥帖。。在风险重重的技术时代,人类行为的危险后果使“存在”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约纳斯的思想使命在于为技术时代的责任实践张本②约纳斯使用duty 与responsibility 时多有混同,前者多指具体责任,后者指抽象的责任本身。我们还需指明response 的希伯来传统,即回应上帝的召唤、圣言、命令。责任伦理涉及“回应”的主要语境有:有机体回应自然的目的性;人对存在之命令的回应;人以道德行动回应“不再全能”的上帝之召唤,亦即完成恩典的当代实现。。责任主体仍坐落于自由基石,但“生命现象”(the phenomenon of life)而非理性事实占据了存在论阐释的优先地位,人的形象由此在实践中打破了人类中心论枷锁。
对人的形象的现代阐明应立足于新的生存论视域。海德格尔指明,“这个时代是由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来规定的:人成为存在者的尺度和中心。人是一切存在者的基础,以现代说法,就是一切对象化和可表象性的基础,即Subiectum[一般主体]”[13](699)。人作为存在者整体的中心将世界构造为属人的图像,必然导致自然与主体陷入双重虚无。约纳斯指出,“西方宗教与形而上学将其对先验独特性的认可诉诸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偏好”[5](137)。就自然界而言,“对其他生命的侵犯原本即属于生命王国”[5](137)。人的特权在于通过理性的自我赋能,将普遍的生命法则人类中心化。意识哲学及其自由理论向来囿于主体性的先验阐明,但在约纳斯看来,一切生命体的意志、欲望和意向性都是主体性的体现。安德尔斯则以技术批判视域直言,“物是自由的,不自由的是人”[3](23)。在生存论视域中,有机体是自由的,主体的形式表现为实存的丰富性,前意识的自然界则以非主体性形式为精神奠基,为客观目的乃至善本身提供可能性。
首先,约纳斯将承担责任的可能奠基在人的本体论能力之上,这是重建责任主体的关键。“自由”在近代哲学中褪除了消极特征,“人的意志决断不再是罪恶的根源,而是成就至善的内在根据”[14](133)。在生命现象学中,人的自由形式既与植物(新陈代谢、敏感性)、动物(运动、知觉与情感)表现出存在之链的连续性,具有共通的物质自然目的论方面的内向性特征[10](90),也具有二元论的特殊性,即人所独有的意识、意志和思维的自明性,蕴含着责任的原初能力。约纳斯反转了康德“你能够是因为你应该”的说法,技术语境中“你能够、你行动、你应该”的因果链表明,自由的外在施行必然伴随着对世界的责任。责任不仅是“一个行动主体的自由之负担”[9](101),甚至是全人类的必然负担。“人类必须存在”乃是责任的首要律令[5](43)。责任律令既有未来向度,也以危机的形式反转了“幸福”与“存在”、权利与义务的伦理优先性,亦即我们有义务首先保障未来同胞能够践行“他们真正成为人的责任”[5](42),而非事关幸福的权利。
其次,在责任伦理中,道德主体乃是实践理性和自由意志兼而统一的行动者。近代哲学倾向于将人思想为“理性-非理性”的共存体。理性存在者的至善形象使得对人的非理性部分(意志、本能、情感、欲望等)的压抑与统治成为道德法则的内在要求,道德行为需要排除非理性本能的干扰。“意志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will)对“理性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reason)的翻转代表了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内部张力[15](9)。只有在实践中,主体才能是现实的、完整的、活生生的行动者。在约纳斯这里,实践理性不再具备对道德情感的压倒性优先,二者毋宁在“存在”的客观事态下保持着伦理行动中的统一和功能性协调。“存在(或其实例)向不被自我私利、愚钝蒙蔽的视界敞开着,它能够很好地灌输敬畏”,存在借助主体的情感支撑道德法则,法则“命令我们尊敬存在内在的呼唤”[5](89-90)。道德法则既非实践理性的自我规定,亦非敬畏的原因或对象,对道德行为的最终辩护来自存在蕴含的善本身,主体的责任由此具有客观实在性。另一方面,为使主体在行动中义不容辞且心甘情愿回应责任命令,道德情感作为“激发意志的心理学基础”就必须补充义务的理性基础[5](85)。
最后,在责任主体的道德实践中,“对至善之爱”必须让位于“责任”与“敬畏”(reverence)的道德情感。以“至善”(summum bonum)为道德实践的至高目标预设了本体论上的完美观念,“它必然超出时间之外,以永恒的魅力面对着我们的必死性”[5](87)。哲学史上以至善之爱充实道德行动的典例不胜枚举:犹太人“敬畏上帝”(fear of the Lord)的诫命、柏拉图对理念的“爱欲”(eros)、斯宾诺莎对上帝的“知性之爱”(amor dei intellectualis)、康德对道德法则的“敬重”(reverentia)等[5](87),布洛赫乌托邦中对完美的人、真正的人的“希望”亦属此列。在责任行动中,意志的形式规则将其优先性让位于事物本身的状态,其典型即成年人面对婴儿时焕发的道德感,“你去看,就会知道”(look and you know)[5](131)。不朽的目标以其绝对价值吸引有限的行动者(有死者)的爱与献身,相形之下,今日的责任对象则是短暂的易逝者。这易逝者在现代性危机中指向技术宰制的诸存在者——有机体、未来人类乃至自然,它们出于“自身权利”(in its own right)而是其所是、理当存在。它们被责任主体感知、察觉到其纯粹的、脆弱的生存诉求,从而激发后者的义务。通过敬畏感与责任感,责任命令不再是一种他律要求,责任就是主体对存在的专注、对世界的关切,进而为了客体的尊严而行动。较之对“人的形象”的纯粹思辨,责任伦理反复强调:思想的现实创造性就在于人对责任命令的回应,亦即面向存在之现实的自由-责任之行动。
小结
约纳斯直面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在回应和拯救人的形象危机中展开了责任伦理的构建。他将责任命令引入伦理学,确证了存在和自然对道德主体发出命令的合法性,从而以责任主体充实和丰富人的形象意蕴。概言之,约纳斯提示我们:存在对非存在具有本体论和价值论的绝对优先性,它内在地命令我们决不能妨害人类的长久生存,这是技术时代的绝对律令。其次,约纳斯重赋自然以目的和价值,内在目的性和价值根据(善)由此从人的主体性顶峰下降到有机体的生存活动即生命现象中,这一工作试图消弭自然与人性、是与应当、理性和意志、生命和死亡的二元对峙,要求人类积极关切自然之家。此外,我们须审慎看待现代技术与技术乌托邦,以长远目光看护人与自然的形象。
约纳斯的努力仍面临不少诘难与困境,诸如:责任原则并非一种充分的道德原则;责任命令与人的自由意志存在张力,伦理行为由个体自愿到普遍义务是一个难题;自然的内在目的论带有古老的泛灵论色彩,在祛魅时代难以为理性话语体系所接受;责任伦理的应用面临一系列现实困境,集体性的政治实体即去乌托邦的责任政府和责任社会实为另一种乌托邦。此外,约纳斯的主体性反思并不彻底,“责任总还被信心十足的主体那极强大的形象所遮挡”,要求人们用道德力量反抗或抵偿技术力量,实为“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自我苛求”[3](141)。但毋庸置疑的是,约纳斯为我们同时提供了启示与警钟:正是人的伦理行动使“存在”面对“非存在”的威胁时实现为“应当存在”,而人的形象危机已迫使我们不得不回应责任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