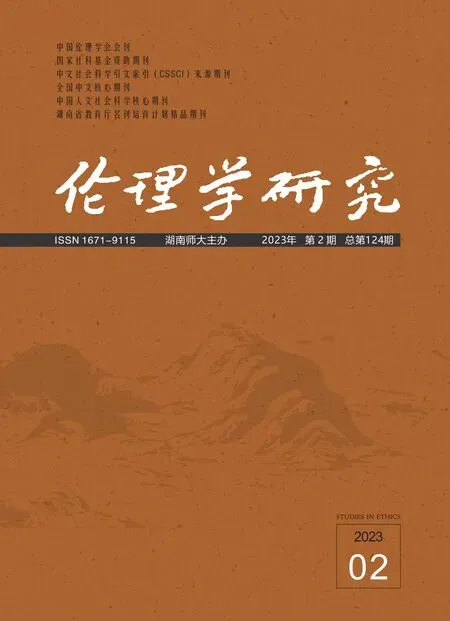自由概念的证成与演绎
——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三章的先验结构
钱 康
导论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以下简称《奠基》)第三章中的证明任务通常都被认为是对定言命令的可能性进行演绎。尽管康德并没有在《奠基》中明确地提到这种演绎是“先验演绎”,但有学者认为,《奠基》第三章中的演绎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演绎具有类似的功能[1](273-274),亦即证明定言命令和道德性的客观实在性和有效性[2](28)[3](172)[4](120)。在第一节中,康德将对定言命令式的可能性演绎与一种“自由概念从纯粹实践理性出发的演绎”(AA 4:447)①本文对康德文献的征引皆以普鲁士科学院版《康德全集》(Akademie-Ausgabe: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为准,引文出处除《纯粹理性批判》采用惯例的A、B 版页码以外皆以全集版缩写卷数+页码的形式标注。联系在了一起。在经过一系列论证之后,康德于第四节中宣布这一演绎的结论:“这样,定言命令就是可能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自由的理念使我成为一个理知世界的成员”(AA 4:45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由概念是定言命令之可能性的基础。尽管学界对于康德在《奠基》第三章中关于自由概念的论证与演绎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就自由概念与定言命令的演绎在论证上的结构关系而言,学界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即自由概念,尤其是在第三章第一节中被提出的积极的自由概念,是之后的定言命令的演绎的必要前提和准备工作[1](283)[5](199)[6](153)。但是这一结构却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批评[7](55,67),即使是比较同情康德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一自由的预设中存在无法避免的论证上的问题[1](285-293)[3](179)。
接下来我就将具体分析自由概念与定言命令的演绎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这种基于自由概念的预设的论证结构存在的问题。之后,我将引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方法论”中提到的一种与“数学的”论证截然不同的“哲学的”论证方法。我将证明,从这种先验方法论的视角出发去考察自由概念与定言命令的演绎之间的关系,可以回避之前提到的一些逻辑问题,并且由此可以回应一些对《奠基》第三章的论证结构的批评。
一、对自由概念的证明及其与定言命令演绎之间的关系
康德在第一节中对积极的自由概念的论述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康德在一种消极的自由概念之外引入了自由的积极概念:消极的自由概念体现为对自然必然性的独立性,它是一种“不依赖于外来的规定它的原因而起作用时”的因果性。其次,康德认为这种对自由的消极说明“无助于看出它的本质”。与此相对的是自由的积极概念,康德将其定义为是“尽管不是意志按照自然法则的一种属性,但却并不因此而是根本无法则的,反而必须是一种依照不变法则的因果性”。再次,康德将这种不同于自然法则的另一种“不变法则”等同于他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道德原则,即自律原则。因为“除了自律之外,亦即除了意志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法则的那种属性之外,意志的自由还能是什么东西呢?”最后,康德得出结论,“一个自由意志和一个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是一回事”(AA 4:447)。在这一系列论述中,康德的核心观点可以被总结为自由的积极概念与道德性之间的同一性,因此这一论题在学界也被称为“同一性命题”(Identitätsthese/identity thesis)或“分析性命题”(Analytizitätsthese)[3](174),因为只要意志自由被预设了,那么“仅仅通过分析其概念,就可以从中得出道德及其原则”(AA 4:447)。
自由与道德性的“分析性命题”通常都被视为康德在《奠基》第三章中对定言命令进行演绎的前提或准备,但这一命题本身并不是演绎的对象。舍内克(Dieter Schönecker)和伍德(Allen Wood)论证,如果“分析性命题”属于演绎的一部分,那这个演绎应该在第二节就已经结束了,而事实是康德直到第四节(AA 4:454)才第一次宣布了演绎的成功[3](173)[6](155)。路德维希(Bernd Ludwig)提出,这个所谓的“分析性命题”甚至都不是一个“命题”,而只是一种不需要为其提供论证的“阐释性的判断”(Erläuterungsurteil)[8](199)。尽管阿利森(Henry Allison)反对舍内克的观点,并认为康德需要为自由与道德性的同一性命题①阿利森将同一性命题称为“互惠性命题”(reciprocity thesis)。提供一个额外的演绎[1](275),但阿利森也并不反对将同一性命题视为是对定言命令的演绎的基础和必要前提[1](283)。
以上这些关于自由概念的讨论与《奠基》第三章的证明结构的解读会带来以下两个结果:其一,无论康德是否需要对同一性命题提供演绎,他对这一命题的论证或说明总是独立于第三章的主体结构,亦即独立于对定言命令的演绎。其二,既然同一性命题被视为演绎的前提条件或准备,那么这一命题的有效性也就会影响到之后的演绎效力。也就是说,如果康德不能为自由和道德的同一性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成,那就意味着康德对定言命令的演绎是失败的——因为如果演绎建立在一个可疑的前提之上,那定言命令的有效性和客观现实性的证成也就只是空中楼阁。
然而,基于这些解读,康德不得不为同一性命题提供证成以保证演绎的有效性,但显然至少在《奠基》中康德并没有为这一命题提供充分的论证。康德在第三章第一节仅仅用了一页左右的篇幅(AA 4:446—447)就完成了对这一命题的说明,而这一过于简短的说明也存在不可避免的论证上的问题。尽管无论是阿利森还是舍内克都通过引证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3](178-181)或《实践理性批判》[1](285-293)中的一些观点作为补充,以试图重构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对于积极的自由概念以及同一性命题的论证,但是他们最终都不得不承认,康德的论证无论如何都存在着某些无法得到进一步说明和解释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要素,这使得一种对同一性命题的彻底证成变得不可能。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康德无论在任何文本中都无法解释为什么自由概念必须是一种合法则的因果性(gesetzmäßige Kausalität)而不能是一种纯粹任意的无法则性(bloß willkürlichen Gesetzlosigkeit)。舍内克和阿利森都认为康德无法为这一形而上学命题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明,而这一证明对于同一性命题的论证而言是必要的[1](287)[3](181)。阿美利克斯(Ameriks)甚至因此将康德对自由的积极概念的论述称为是一些未经批判的“关于自由的相对粗糙的信念”(some relatively crude beliefs about freedom)[7](69)。
在康德学界中,对这一问题有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首先就是以伊尔廷(Karl-Heinz Ilting)和路德维希为代表的解读,他们认为康德根本就不需要为自由的积极概念提供形而上学上的证明,因为道德性的现实性并不需要依靠自由的积极概念才能够得到证明,而是能够通过普通的人类理性直接被认识[8](99,101)[9](126)。另一种解决方案在目前学界接受度更广:既然康德无法为自由的积极概念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明,那么人们可以由此认为康德在《奠基》中的论证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出发为道德与自由进行论证的一种失败尝试,而这种失败的尝试在之后的《实践理性批判》中被一种基于“理性事实理论”(Faktumslehre)的更加实践的论证所取代①这种解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康德学界的主流,可以参见Dieter Henrich,“Die Deduktion des Sittengesetzes”,in Alexander Schwan(Hg.),Denken im Schatten des Nihilismus,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75;Karl Ameriks,Kant’s Elliptical Pa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Dieter Schönecker,“Kants Moral Intuitionism:The Fact of Reason and Moral Predispositions”,Kant Studies Online,2013;Paul Guyer,Kant’s“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8.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一解读提出挑战,并试图论证康德在《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论证结构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并不存在论证策略上的转变。关于这类解读可以参见Michael Wolff,“Warum das Faktum der Vernunft ein Faktum ist:Auflösung einiger Verständnisschwierigkeiten in Kants Grundlegung der Moral”,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Vol.57,No.4,2009;Owen Ware,“Kant’s Deductions of Morality and Freedom”,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47,No.1,2017;Deryck Beyleveld and Marcus Düwell,The Sole Fact of Pure Reason:Kant’s Quasi-Ontological Argument for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De Gruyter,2020.。
这两种解决方案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康德对道德哲学的奠基工作进行辩护,但它们也都会遇到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首先在第一种解读中,康德似乎是将对道德性和自由概念的奠基建立在某种道德直觉主义或理性心理学之上,而这与批判哲学与先验演绎的方法不相容。在第二种解读中,虽然康德实践哲学可能在之后的《实践理性批判》中能够得到辩护,但如果代价是牺牲《奠基》的合理性,这也不符合康德的本意,毕竟康德没有在任何地方明确地宣称他放弃了《奠基》中的论证并转向《实践理性批判》中的理性事实理论。
最重要的是,这两种方案事实上都回避了真正的问题,亦即康德对于自由概念的论证的有效性。在这两种方案中,这一论证都被单纯视为失败的,或者根本就是没必要的。但是,如果自由概念对于康德在《奠基》中的演绎工作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那么很难想象康德只花了寥寥数笔就草率地将这个概念引入并作为道德法则的可能性基础。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种不尽如人意的论证安排归结为康德在术语使用和下定义方面的粗心大意,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能够令严肃的康德研究者感到满意的答案。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利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方法论中的哲学资源,以求在先验哲学的语境中还原和重构康德对于自由的积极概念的论述,以及它与定言命令的演绎之间的关系。
二、作为“哲学式定义”的同一性命题
康德对于定言命令的演绎之所以饱受诟病,似乎是由于作为论证起点的自由概念本身缺乏充分的证成。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设想另一种可能,亦即康德在《奠基》第三章第一节中根本就没有将自由概念的导出视为一个需要被论证的对象——或许它是一个不能被证明的前提,或许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定义?不过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康德对定言命令的演绎最终只能被追溯到一个无法得到进一步证明的前提之上,因而康德不能算是为道德性提供了彻底的证明。不过康德从来都没有尝试为人类理性提供彻底的证明,无论是在其思辨运用还是在实践运用中。比如在范畴的先验演绎中,“我思必须能够伴随我的一切表象”(B 132)这一最基本的前提就无法得到直接的证明。康德只能间接证明如果没有这一命题,那么对于在直观中被给予的杂多的综合就不一定必须发生在我们的意识中,那么意识的综合统一也就不是对象被表象的必要条件,因而一种基于统觉的综合统一的原理也就不一定适用于一切表象,最终一种认识的先天综合判断就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康德在范畴的先验演绎中尽管证明了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但他也并没有直接论证作为其前提的统觉的客观实在性。康德并没有将这种论证的不彻底性视为是一种论证的失败,毕竟统觉的综合统一性归根结底就是人类认知能力的自发性(Spontanität),而这种自发性是康德批判哲学的起点,亦即在哲学领域进行哥白尼式革命的设想。也就是说,康德的任务并不是去直接论证我们确实具有认识或行动上的自发性,这无非只是康德的一种“假定”(annehmen)或“尝试”(versuch)(B XVI)。康德哲学真正的任务是通过这种尝试去论证人类获得并扩展先天的理性知识的可能性,亦即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现在,既然康德认为先天的理性知识包括对对象及其概念进行规定的理论知识,也包括在此之外还要将其“现实地创造出来”的实践知识(B IV-X),那么这段分析就同样适用于康德在《奠基》第三章第一节中的论述。
现在,康德提出自由“必须是一种依照不变法则的因果性”,因为“若不然,一种自由意志就是胡说八道”。这与其说一种论证,不如说是对他的基本哲学立场和出发点的重申。也就是说,如果自由不被设定成一种合法则的因果性,那么一种普遍有效的意志的规则就根本不会存在。因此康德在《奠基》第三章中提出这个论述应该被重构为一个条件句:如果可能存在对人类意志有效的普遍道德法则,那自由就必须被设定为一种合法则的因果性。既然如此,基于自由概念对定言命令的演绎是不是建立在一个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立场之上,就不能单纯根据康德在第一节中是否为这个概念的导出提供了充分的论证而得出结论。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系统性地考察《奠基》第三章中的演绎的证明架构,尤其是这个被预设的自由概念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现在我们预设康德在《奠基》第三章第一节中关于自由与道德的同一性命题不是一个需要被论证的对象,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命题是作为一种定义而被预先提出的。既然如此,为了考察同一性命题是不是独断性的定义,我们就有必要对康德哲学的先验方法论展开研究,尤其是对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纯粹理性在独断应用中的训练”一章中关于“定义”(Definition)在哲学和数学领域内的不同作用进行分析。
在这一章中,康德的目的是讨论一种为了在哲学中寻找确定性的“独断的方法”(dogmatische Methode)(B 741)。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导言中就指出:“批判并不与理性在其作为科学的纯粹知识中的独断方法对立(因为这种知识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独断的,即从可靠的先天原则出发严格地证明的)。”(B XXXV)换句话说,康德在这里就是要讨论如何能够在哲学中从可靠的先天原则出发为哲学的对象提供严格的证明。
康德指出:“哲学的知识是出自概念的理性知识,而数学的知识则是出自概念之构造的理性知识。”(B 741)而构造一个概念就是先天地展示与该概念相应的直观。但是这种对客体的直观在以质料为对象的哲学中是永远不可能先天地被把握的,因为质料“除了经验性的直观之外不能在任何别的直观中表现”(B 742—743)。正是由于在哲学和数学之间存在这种区别,两种知识领域之中对理性的运用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哲学是按照概念进行论证的理性应用,而数学则是通过构造概念进行直观的理性应用(B 747)。这种差别首先就体现在哲学和数学对“下定义”的不同理解。康德指出,数学家对“定义”的使用无法被哲学家参考和模仿:“哲学的定义只是被给予的概念的阐释,而数学的定义则是原始地形成的概念的构造。”(B 758)因此,既然在哲学中的定义是“对已被给予的概念的分析,所以这些概念就是先行的,尽管它们还只是混乱的,而不完备的阐释先行于完备的阐释,以至于我们在达到完备的阐释亦即达到定义之前,就能够从我们得之于一种尚不完备的分析的一些特征中事先推论出某些东西;一言以蔽之,在哲学中定义作为精确的明晰性必须宁可是结束工作,而不是开始工作”(B 758—759)。既然康德在之前就已经提到,哲学是一种关于概念的认识,而定义恰恰就是从对于概念的分析或认识中被得出的,那么在哲学中,一种完备的定义就应该是结束的标志,而不应当被视为对于哲学工作的出发点的要求。我们只有在对对象有足够认识的情况下才能对其作出完备的定义。与此相反,数学本身是一种对概念进行构造的科学,因此它自然就是要从一个定义开始。
既然哲学能够被允许从一种不完备的定义开始,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康德不需要为这一定义提供充分的证成呢?康德在一个注释中明确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哲学充斥着错误的定义……但是,既然就(分析的)种种要素所及,总是可以很好且可靠地利用它们,所以有缺陷的定义,亦即真正说来还不是定义、但除此之外却是真实的、从而是向定义接近的命题,就可以得到有益的应用了。定义在数学中是既定的,而在哲学中则是有待改善的。”(B 759 Fn)①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即使哲学的定义通常来说在一开始都是不完善和有缺陷的,康德也并没有因此否定它的意义。重要的是,这种定义尽管有缺陷但在哲学上也是“很好且可靠地”被利用的。因此康德指出,哲学定义相对于数学定义的不完善性不是为了贬低哲学定义作为一种科学方法的地位,而是为了劝说读者根本就不要在哲学工作的开始阶段就期待一种完备的定义。不过这也不意味着哲学可以始终满足于一个有缺陷的定义,或是能够天马行空地提出任何定义而不需要为它提供证明。康德强调了哲学的定义是需要在之后的论证中逐渐得到完善的。至于哲学的定义应该如何得到完善,我们可以在下面这段引文中找到线索。基于跟在定义的情况中同样的理由,康德也认为在哲学中不存在数学意义上的公理:“哲学没有公理,也绝不可以如此绝对地规定它的先天原理,而是必须承认通过缜密的演绎来为它就这些先天原理而言的权限作辩护。”(B 761—762)也就是说,无论是对于定义还是对于公理,在哲学中这些先行于论证的对对象及其原则所进行的规定都应该在一种“缜密的演绎”中得到对其权限的辩护。
总而言之,哲学中的定义并不需要有绝对的正确性和完备的证明,但通过之后的演绎对其提供的证成也使它有别于单纯独断的宣称。哲学上那种先行的“定义”比起描述性的论断更像是一种实用的论证策略,尤其是当我们对需要被处理的对象缺乏直观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一种虽然不完善但却能使我们的论证得以继续发展的定义开始。
以上关于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定义”的分析可以被应用到我们当前的论题,亦即康德在《奠基》第三章第一节中对自由积极概念的定义。如果这个饱受诟病的对于合法则的、绝对的自由概念的论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证,而仅仅是一种实用的哲学式的定义,那么在前文中提到的那些针对这一概念的批评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尽管康德不能为自由概念的定义提供一种具有数学式的精确性和明晰性的论证,但他仍然需要为这一概念的合法性提供说明,尽管这种证成并不是在当下,而是在之后的演绎中完成的。《奠基》第三章的哲学任务并不开始于对自由概念的完备的证明,而是开始于一个或许有缺陷的定义,只不过只有在这个定义之下我们才有可能继续拓展实践理性的运用。自由的积极概念是一个为了定言命令的演绎而被找到的“更丰富、更能产生结果”(AA 4:446)的概念。
因此,康德对自由的积极概念的导出绝不能被视为一个区别于之后的定言命令演绎的独立论证。尽管康德没有直接宣称对自由概念的导出也属于第三章中的演绎的一部分,我们也应该认为对这一论述的相对完备的证成应该在之后的演绎中去寻找。也就是说,当康德通过之后的论证表明,基于自由的积极概念能够使对定言命令的可能性演绎得以完成,这也就意味着自由的积极概念这一个在形而上学上无法得到充分证明的概念在其实践运用中“更能产生结果”。
这样看来,康德在《奠基》第三章第一节中提出的自由和道德的同一性命题就更像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范导性原则,而不是实在论意义上的描述性命题。尤其是康德在“先验方法论”中强调:“方法永远能够是系统的。因为我们的理性(在主观上)本身是一个体系,但是在它的纯粹应用中,借助纯然的概念,它却只是一个按照统一性的原理进行研究的体系而已……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对我们的能力状态的一种批判,看我们是否在任何地方都能进行建筑,以及我们用自己拥有的材料(纯粹先天概念)能够把我们的建筑物建多高。”(B 765—766)在这段引文中,康德将理性借助先天概念的纯粹应用视为一种系统的哲学方法,而康德哲学的任务就是为这种理性能力的运用提供一种批判,以确定我们理性能力的界限和范围。这种借助理性批判而为其合法要求(Rechtsanspruch)提供证成(Rechtfertigung)的论证方式正好符合康德对于“先验演绎”的原初定义①参见《纯粹理性批判》的“论一般先验演绎的原则”一节(B 116—124)。另外关于“先验演绎”与“批判”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见Dieter Henrich,“Die Deduktion des Sittengesetzes”,in Alexander Schwan(Hg.),Denken im Schatten des Nihilismus,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75.。恰好在《奠基》第三章的第五节中,康德也在讨论自由的理念合法要求(AA 4:457),因此就有学者提出,除了在第四节中提到的一种基于自由的理念对定言命令式的可能性进行演绎之外,康德在第五节中还有另一个专门针对自由理念本身的演绎[10](60-62)。那么,为了说明康德关于自由理念的定义不是一种独断的教条或未经批判的信念,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在第五节中重构出康德为自由理念提供的演绎。
三、实践哲学的界限以及对自由理念的先验演绎
与《奠基》第三章的前四节相比,第五节“论实践哲学的最后界限”长久以来在康德学界中的关注度并不高②这一情况在近年有所改变,可以参见Heiner F.Klemme,“Freiheit oder Fatalismus?Kants positive und negative Deduktion der Idee der Freiheit in der Grundlegung”,in Heiko Puls(Hg.),Kants Rechtfertigung des Sittengesetzes in Grundlegung III:Deduktion Oder Faktum?,De Gruyter,2014;Frederick Rauscher,“Die äusserste Grenze all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und die Einschränkungen der Deduktion in Grundlegung III”,in Dieter Schönecker(Hg.),Kants Begründung von Freiheit und Moral in Grundlegung III,Mentis,2015.关于第五节的二手文献的综述可以参见Heiko Puls,Sittliches Bewusstsein und Kategorischer Imperativ in Kants Grundlegung:Ein Kommentar zum dritten Abschnitt,De Gruyter,2016,p.220.在国内学者中,刘作也洞见性地指出了第五节与定言命令演绎之间的关系(刘作:《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与定言命令演绎》,《现代哲学》2022 年第1 期)。。因为根据一些主流观点,康德在第三章中的演绎工作在第三节或第四节里就已经完成了,而第五节仅仅是对之前论证的一种“总结”(resümieren)[11](299)或是一种“额外说明”(zusätzliche Erklärung)[3](198-199),因此在第三章的论证中不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通过之前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康德在第一节中提出一种与道德性一致的自由的理念之后,他就以此为出发点开始论证定言命令的可能性,并且在第四节里成功宣称:“这样,定言命令式就是可能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自由的理念使我成为一个理知世界的成员。”(AA 4:454)既然康德在这之前并没有为自由的理念提供充分的证明,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先行的哲学定义而提出,这也就意味着,直到第四节为止,康德为定言命令的可能性所提供的演绎就只是一个基于自由理念的有条件的论证。而要想彻底证明定言命令的可能性,康德就需要在第五节里为这个作为条件或前提的自由理念提供一个演绎以说明其合法性。
尽管如此,康德却在第五节第一段中就给读者泼了一盆冷水,他说:“自由只是理性的一个理念,其客观实在性就自身而言是可疑的。”(AA 4:455)在稍后的段落中康德甚至宣称“人们绝不能理解自由如何可能”。这至少意味着自由理念无论如何都不能在经验实在性的意义上得到证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康德完全无法为自由概念提供任何证成(Rechtfertigung)。既然康德现在需要为一个并不指涉经验对象的理性的理念提供证成,那我们就有必要先来看一下康德关于一种一般而言的对理性理念进行证成的方法。
在《纯粹理性批判》“论人类理性的自然辩证法的终极意图”一节中,康德讨论了对于纯粹理性的理念的先验演绎①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大量文本依据可以证明康德是将“证成”(Rechtfertigung)和“演绎”(Deduktion)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的,二者都指涉一种基于先验原则的对于概念或判断的客观有效性的证明,参见A 97 与B 116、117、122、124,尤其是AA 5:46。。康德首先强调了这种先验演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为“不对一个先天概念进行过先验的演绎,人们就不能可靠地使用它。纯粹理性的种种理念……如果应当至少有一些——哪怕是不确定的——客观有效性,并且不仅仅表现空的思想物的话,那就绝对必须有一种它们的演绎是可能的,即使它远远不同于人们对范畴能够采取的那种演绎”(B 697—698)。这段引文可以很好被用来反驳那些认为康德不需要为自由的理念提供证成的观点,同时也能反驳那些认为《奠基》第三章中的演绎工作在第四节中就已经结束的观点。很显然,康德无论如何都需要在第五节中为自由的理念提供一种证成,尽管这个概念并没有经验意义上的客观现实性。但是问题在于,康德也承认,对这种纯粹理念的演绎不能像对范畴的演绎那样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康德就需要为理念的先验演绎重新划定一套规范和标准。
既然先验演绎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先天概念能够与对象发生关系的方式的解释”,那么对于理念的先验演绎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确认其对象。康德指出,“某物是作为一个绝对的对象还是作为一个理念中的对象被给予我的理性,这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我的概念去规定对象;在第二种情况下,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图型……它仅仅被用来让我们凭借与这个理念的关系根据其系统的统一性来表现其他对象,从而间接地表现它们”(B 698)。也就是说,理性对于其对象有两种处理方式,其一是直接去“规定”对象,其二是仅仅将其视为一个“图型”而服务于系统的统一性。
康德对理性的两种对象之间的区分暗示了,既然理性以不同的方式与对象发生关系,那么对这种关系的解释亦即演绎自然也就有不同的方法和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性的纯粹理念对于客观有效性或现实性的合法性要求(Rechtsanspruch)与那些直接关涉经验对象的概念对于客观有效性的要求是不同的。康德指出,纯然理念的“客观实在性不应当在于它直截了当地与一个对象相关(因为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不能为其客观的有效性辩解),而在于它仅仅是一个一般事物的概念按照最大的理性统一性的条件安排的图型,这个图型只被用来在我们理性的经验性应用中保持最大的系统统一性”(B 698)。这就意味着,与纯粹知性概念不同,纯粹理性的理念的客观实在性并不在于与经验对象的必然联系之中,而我们也根本无法证明这一点,毕竟在纯然理念中并不能找到被给予的经验直观。与此相对,纯粹理念的客观有效性就体现在一种为理性的经验运用提供系统统一性的图型法中。康德为此也给出了具体的解释:“以这样的方式,理念真正说来只是一个启迪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明示性的概念,它所说明的不是一个对象有什么性状,而是我们应当如何在它的引导下去寻找一般经验的对象的性状和联结。”(B 698—699)既然纯粹理念只是一个启迪性(heuristisch)的概念,而且并不直接涉及与经验对象的联结,而仅仅是一种方法论式的“引导”,那么对于这样的理念的先验演绎自然也就应该有不同于知性概念的标准:“思辨理性所有理念的先验演绎,不是作为我们的知识扩展到与经验所能给予的对象的建构性原则,而是作为一般经验知识的杂多之系统统一性的范导性原则,经验知识由此在自己的界限之内,与没有这样的理念、仅仅通过知性原理的应用所可能发生的相比,将得到更多的培植和纠正”(B 699)。也就是说,作为对理念的先验演绎,需要考察的不是我们能否靠这样的理念认识到超出经验对象之外的东西,而是考察是否能依据这种理念,更好地在知性所及的经验界限内恰当地扩展我们的知识。
尽管在这段引文中康德将他的讨论限制在纯粹理性的思辨运用中,但我们仍然可以尝试从中总结出一些可以被用在理性的实践运用中的要素。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将对一切思辨理性的理念的先验演绎的原则总结为以下两点:
(1)思辨理性的理念应当以图型的方式提供经验知识的系统性,并且因此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扩展经验知识。
(2)思辨理性的理念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反(zuwider sein)经验知识。
以上这两点就是思辨理性的理念演绎的原则,也就是说,只要证明了这两点,就可以算是为理念完成了演绎或证成,亦即证明了我们对这样一种理念使用的合法性。由于第一条原则的要点在于说明理念对经验知识的有用性,而第二条则在于说明其与经验知识的无矛盾性,因此我们可以将对理念的先验演绎的一般原则抽象概括为理念的“有用性”和“无矛盾性”。
现在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两个标准,尝试将这种一般原则应用到实践理性的领域中,也就是康德在《奠基》第三章第五节中对于自由的理念的演绎。首先关于第一条原则,亦即“有用性”原则对于思辨理性而言体现在以范导性的方式对经验知识的扩展提供帮助上。而在实践哲学领域中,理性的目的并不在于扩展知识,而在于将先天知识“现实地创造出来”(wirklich zu machen)(B X)。因此对于实践理性的理念而言,它的有用性就应该在于对这种“现实的创造”,亦即在意志依据理性的先天原则决定我们行动的情况中,提供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康德强调:“在实践方面,自由的小径却是唯一使得有可能在我们的所作所为方面运用其理性的道路”(AA 4:455—456)。也就是说,自由理念的有用性就体现在他对于理性的实践运用的这种唯一的可能性中。这一点也体现在康德在第四节里对于定言命令的可能性演绎中:“定言命令式就是可能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自由的理念使我成为一个理知世界的成员。”(AA 4:454)关于自由的理念在这种可能性演绎中具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康德学界仍存在极为复杂的争议。不过,普尔斯(Heiko Puls)关于理性的自发性在定言命令的演绎中的作用的解读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普尔斯认为,康德在AA 4:452 中通过一种实践理性理念的范导性运用,为我们将自己视为知性世界的成员提供了论证基础,进而解决了定言命令的可能性问题①参见Heiko Puls,Sittliches Bewusstsein und Kategorischer Imperativ in Kants Grundlegung:Ein Kommentar zum dritten Abschnitt,De Gruyter,2016,pp.214—216.类似的关于自由理念和定言命令演绎的解读也可以参见Rocco Porcheddu,“Das Verhältnis von theoretischer und praktischer Freiheit in der Deduktion des kategorischen Imperativs”,in Jürgen Stolzenberg &Fred Rush(Hrsg.),Internationales Jahrbuch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De Gruyter,2013.。因此我们可以说,康德在第五节之前就已经通过对定言命令的成功演绎证明了自由理念的“有用性”:它能够通过一种范导性功能为实践理性的运用提供积极的作用。
关于第二点,亦即“无矛盾性”,康德在第五节中给出了很明确的观点:“人类理性必须假定,在同一些人类行为的自由和自然必然性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矛盾”(AA 4:456)。那么现在我们就能重构出康德对自由理念的先验演绎应该有的证明架构了:为了给自由理念提供证成,康德需要证明它的“有用性”和“无矛盾性”。既然它之于理性的实践运用的“有用性”已经在之前的章节中被证明了,那么康德在第五节中的任务就是要为自由理念与自然必然性的“不矛盾性”提供证明。在这里康德提到自由和自然必然性之间的冲突产生了一种“理性的辩证法”(AA 4:455)。米歇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指出,这一表述暗示了,对这一冲突的解决已经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自由与自然的二律背反的解决(B 560—586)中被给出了[12](309-310)。而在《奠基》中康德就不需要为此提供额外的论证,只需要再次强调,由于理论理性的界限使得我们无法直接证明自由的实在性,同时也无法彻底否定它,因此“最精妙的哲学与最普通的人类理性一样,都不可能用玄想去除自由”(AA 4:455—456)。
这样我们也就能更好地理解康德的这一表述:“所以,人类理性必须假定,在同一些人类行为的自由和必然性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矛盾。”(AA 4:456)现在看来,这句话中的“必须”其实并没有规范性的意涵,也不指涉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与其说康德是想强调人类的本质必须在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意义上被视为是理性存在者,不如说康德在这里只是指出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保证理性的实践运用,就必须要有一种自由的理念;而现在康德能够证明我们没有办法否定自由,那么我们就必须假定自由与自然之间不存在矛盾。因此,即使是在第五节的演绎中,也并没有一种经验意义上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概念的实在性得到证明。康德无非只是证明了在第一节中预先提出的对于自由的定义在方法论上的合法性。
既然康德已经证明了自由理念对于理性的实践运用的有用性,同时也证明了自由概念与自然必然性的无矛盾性,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已经完成了对自由理念的演绎。这一演绎事实上是基于实践理性的“内部界限”,也就是知性与理性在处理对象上的差别,以及理性的实践运用与理论运用之间的差别而完成的。
结语
现在我们能够回应在本文第一节中提到的那些针对康德的自由理念的批判了。首先,既然康德在第一节中关于自由理念的表述——尤其是将积极的自由概念等同于道德性的所谓“同一性命题”——本质上并不是一种论证,而只是一种出于特定目的的定义,那么他就没必要为对这些表述在形而上学上的不完满性承担责任。其次,康德对于自由的定义尽管在第一节中是先行且独断的,但是如果将《奠基》第三章的论证结构视为一个在先验方法论的架构之下的系统性的论证整体的话,那么对于自由的定义在这一论证的结尾处能够得到恰当的批判与证成:在关于自由概念的使用限度得到界定的同时,它的合法性需求也得到了证成。于是,康德在《奠基》第三章第一节中为自由概念提出的定义尽管是不完满的,但它并不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预设,也不是一种理性主义传统下关于自由的粗糙信念。康德关于自由理念的论述采用了一种名为“下定义”的先验哲学特有的哲学方法。只有在这种基于道德性和自由之一致性的预先定义的指引下,康德才能够开始并发展对于定言命令的演绎,并且这一独断的先行的定义本身的合法性也在之后的文本中通过另一个关于自由理念的先验演绎而得到批判和证成。一言以蔽之,自由的理念不是某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概念,而且自由与道德的同一性命题也不是一个在本体界层面规定理性理念的命题。康德在这里运用的是一种依据理性的范导性原则的启迪性的先验方法。因此无论是积极的自由概念还是同一性命题都不是简单地以“前提-结论”的方式与定言命令的演绎发生关系,二者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以先验方法论为基础的互动结构。
虽然对于自由的理念和定言命令的演绎之间的先验结构的分析到此结束了,但这并不能算是彻底解决了康德伦理学就道德性的奠基而言存在的一些论证上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康德在到此为止的论证中都是通过限制实践理性的理念在经验的客观实在性意义上的有效性来完成的,那么这种无论如何都是“受限”的证明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为现实地具有规范性效力的道德法则提供证成就是一个问题。接下来康德就要通过划定实践理性的“外部界限”来为他的这一系列论证的有效性进行说明。也就是说,康德现在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对于自由理念,甚至是整个对于道德法则的证成在何种意义上是有效的?其次,本文关于自由的理念和定言命令的演绎之间的先验结构的分析似乎指向了一个事实,即康德开始于一个预设的道德的自由理念,并基于这一理念提供了对作为道德性唯一法则的定言命令的演绎,最后他又通过这个演绎反过来确证了自由理念的合法性。尽管我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构了康德在《奠基》第三章中的论证结构,但自由和道德之间的“互惠性命题”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或许还需要从康德在第三章第三节中提出的“两个世界”理论中寻找跳出这一“互惠性”的循环论证的办法。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向前走了一步:我们至少可以证明,通过一种先验方法的重构,康德在《奠基》第三章中是可以在论证层面上达成自恰的,也就是说,至少在这里不存在某个未经批判的唐突预设或是论证逻辑上的断层。这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回应那些针对定言命令演绎之可能性的批评。接下来的工作已经超出了具体的论证,而是需要进入到对先验方法本身的批判和研究中。这种关涉到不同哲学范式与立场之冲突的元哲学研究已经超出了单纯的伦理学研究的界限,因此无法在有限的章节中充分地进行阐明,而只能留待在一个关于先验观念论的更加系统性的研究中去讨论。不过这同时也意味着,康德的批评者们也无法独立于这样一种元哲学层面的研究展开针对康德伦理学中的演绎和证成的批评,因而这一结论能够有助于推进康德伦理学研究在哲学层面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而不至于迷失在琐碎的论证与观点立场之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