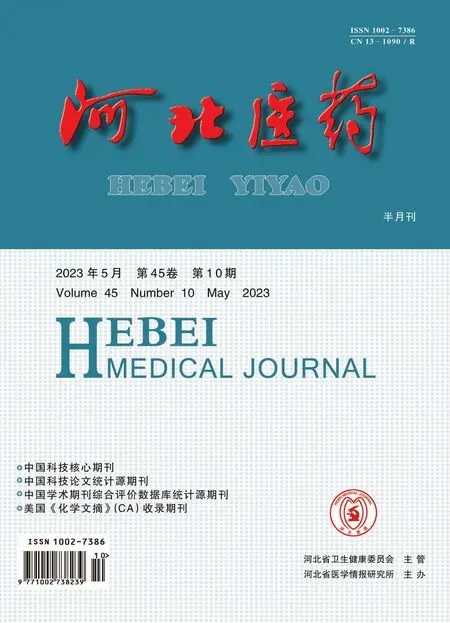miRNAs调控AMPK信号通路改善脂代谢紊乱的研究进展
刘迪 刘阳 郝珍飞
脂代谢紊乱是指当脂质合成、代谢、转运等过程发生异常时,血清中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LDL)的升高和/或高密度脂蛋白(HDL)降低[1]。肥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动脉粥样硬化(AS)等疾病的发生发展均与脂代谢紊乱相关。腺苷一磷酸活化蛋白激酶(adenosine 5’monophosphate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是细胞内的能量感受器,在机体能量水平下降时被激活,主要参与能量代谢、增殖、炎症、细胞因子的产生和细胞凋亡等过程[2]。当AMPK失调时,其下游的脂质合成与分解代谢途径出现异常,造成肥胖、糖尿病、NAFLD等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3]。miRNAs是广泛存在于生物体内且高度保守的非编码RNA。近年来发现,miRNAs在脂代谢紊乱的相关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它通过抑制mRNA的转录后翻译,实现对下游脂质代谢相关靶基因的精准调控。因此,通过抑制miRNAs,激活AMPK与其下游的脂质代谢相关信号通路,有可能成为降低这些相关疾病发病率的一种有效手段。故本文主要阐述了miRNAs和AMPK的结构与功能,研究了miRNAs与AMPK之间的潜在关系以及对它们在脂代谢疾病中的作用及机制进行综述。
1 miRNAs生物学功能
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s,miRNAs)是一种约22个核苷酸组成的小型非编码单链RNA,在真核细胞中广泛存在,它调节着人类近三分之一的基因,一个miRNAs可以调控多个靶基因,同一个靶基因也可能受多个miRNAs调控[4]。在细胞核中,大多数miRNAs被RNA聚合酶Poly Ⅱ转录成包含一个或多个茎环结构的pri-miRNAs,pri-miRNAs被RNase Ⅲ酶的成员Drosh切割成大约70多个核苷酸的茎环结构(即pre-miRNAs)[5]。随后pre-miRNAs在输出蛋白5的帮助下运输至细胞质,并且被核糖核酸内切酶Dicer切割,产生双链RNA,在ATP依赖的伴侣蛋白帮助下,双链RNA的一条(-5 p或-3 p)被装载到RISC复合物上,与Argonaute蛋白(Ago)结合产生成熟的单链miRNAs[6]。此时,成熟的miRNAs通过碱基互补配对原则被引导至目标mRNA的3’端非翻译区,抑制mRNA的翻译并促进其降解[7]。基于上述过程,miRNAs可与多个靶基因相互作用,影响了如细胞生长、代谢、增殖和凋亡等许多重要的生物学过程。
2 AMPK结构与功能
AMPK广泛存在于真核细胞,是一种丝氨酸(Ser)/苏氨酸(Thr)蛋白激酶,它具有高度保守性,由负责催化的α亚基(α1和α2);支架β亚基(β1和β2)和调节的γ亚基(γ1,γ2和γ3)构成12种不同组合的异源三聚体[8]。在哺乳动物中,α亚单位由N端激酶结构域(KD)构成,自抑制结构域(AID) 和两个调控亚基相互作用的基序(RIM1和RIM2)以及C端的一个β/γ亚基结合结构域,在KD中含有一个可被上游激酶磷酸化的关键位点[9]。β亚单位N端拥有豆蔻酰化区域,可促进AMPK结合至膜上,此外还含有碳水化合物结合模块(CBM),该模块可以使AMPK与糖原结合[10]。γ亚单位拥有4个CBS结构域,除CBS2外其余3个结构域均可竞争性的与AMP、ADP或ATP结合,以响应细胞内AMP或ADP与ATP的比值变化[2]。由此可见,AMPK在能量代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机体出现能量短缺时,AMP或ADP可与AMPKγ亚基结合,解除AID对AMPK的自身抑制作用,通过上游激酶使其Thr172位点磷酸化,进而激活AMPK途径。当细胞内缺乏肝激酶B1(Liver kinase B1,LKB1)时,AICAR、二甲双胍等AMPK激动剂都不能使AMPK活化,因此,LKB1已经成为AMPK磷酸化的主要上游激酶之一。最新研究发现,AMPK还通过感知细胞内葡萄糖水平,不需要AMP与AMPK结合即可产生激活效应,在能量应激的状态下,细胞内葡萄糖水平下降,糖酵解醛缩酶的底物1,6二磷酸果糖(fructose-1,6-bisphosphate,FBP) 水平随之下降,进而使v-ATPase活性被抑制,v-ATPase和调节因子形成的复合物发生构象变化,促使该复合物与轴蛋白AXIN结合,共同移动至溶酶体附近,促进LKB1磷酸化AMPK Thr172位点[11]。此外,钙调素依赖的蛋白激酶β(calcium/calmodulin-dependent protein kinase β,CaMKKβ)也可以磷酸化Thr172位点以激活AMPK信号通路。
3 AMPK与脂质代谢
3.1 AMPK抑制脂质合成代谢途径 众所周知,FA和TC的合成都需要乙酰辅酶a作为底物,而乙酰辅酶A羧化酶(Acetyl-CoA carboxylase,ACC)是FA合成的限速酶,它在哺乳动物中以两种不同的亚型存在:ACC1主要定位于细胞质中,可催化乙酰辅酶a羧化产生丙二酰辅酶a,随后脂肪酸合酶(FASN)利用丙二酰辅酶a合成FA;ACC2拥有一个疏水的N-末端区域可附着在线粒体的外膜上,主要参与β氧化过程[12]。有研究表明,敲除小鼠ACC1 Ser79和ACC2 Ser212这两个磷酸化位点时,ACC和丙二酰辅酶A活性增加,FA合成增强,并且对AMPK的激活剂也不敏感[13]。因此,当AMPK感受到细胞能量短缺时,通过磷酸化ACC的上述两个位点,可以抑制FA从头合成,减少能量消耗。乙酰辅酶a还通过一系列缩合反应,被HMG-CoA还原酶(HMGCR)还原为甲羟戊酸,最终合成TC。HMGCR是AMPK的下游靶点,体内外研究均表明,AMPK都通过磷酸化HMGCR的Ser871位点抑制其活性,减少TC合成,从而降低血清和肝脏中胆固醇水平[14,15]。
此外,AMPK还通过磷酸化甘油-3-磷酸酰基转移酶(Glycerol-3-phosphate acyltransferase,GPAT)途径调控TG合成,GPAT是催化TG合成第一步的限速酶,共四种不同的异构体(GPAT1,2,3,4)。有研究发现位于线粒体外膜的GPAT1占肝外组织中总GPAT活性的10%,而肝脏中,GPAT1占总GPAT活性的30%至50%,肝脏AMPK的激活使GPAT磷酸化以抑制其活性,进而减少二酰基甘油(diacylglycerol,DG)的生成,从而抑制TG和磷脂的合成[16]。
AMPK除了通过磷酸化HMGCR,ACC和GPAT直接抑制FA,TC和TG合成外,还间接通过抑制转录因子(SREBPs,ChREBP)减少脂质合成。固醇调节元件(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 binding proteins,SREBPs)是脂类平衡的主要调节者,它首先作为前体蛋白以发夹状的形式插入内质网膜上,由SCAP介导运送至高尔基体经过S1P和S2P的2次蛋白水解,将N-末端片段活性部分释放入细胞核内,并结合到核内的启动子SRE序列,启动转录程序[17]。SREBPs由3种亚型 (SREBP-1a,SREBP-1c和SREBP2)组成,其中SREBP-1c主要控制FA和TG合成相关基因的表达,SREBP2主要控制体内TC稳态[18]。在肝细胞中,AMPK磷酸化SREBP-1c的Ser372位点和SREBP2 的Ser374位点阻止蛋白水解过程,抑制转录活性,进而下调ACC1,HMGCR,FASN,GPAT,SCD1等30多个脂质合成相关基因的表达,减少FA和TC合成,为机体保留更多的能量[19,20]。ChREBP由葡萄糖独立激活,活化后的ChREBP可激活丙酮酸激酶生成丙酮酸。当丙酮酸进入线粒体时可生成乙酰辅酶a,参与FA合成[21]。AMPK通过磷酸化ChREBP 的Ser568位点,抑制脂质合成[22]。此外,AMPK还促进活化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1(sirtuin 1,SIRT1)去乙酰化,抑制核内SREBP-1c和SREBP2活性;去乙酰化SIRT1还可下调ChREBP的转录活性,从而抑制糖类向脂质的转化,间接减少脂质的生成[23]。上述过程可能进一步加强了AMPK抑制脂质合成的能力,在能量短缺的条件下,减少ATP消耗。
综上所述,脂质合成需要大量ATP参与,而AMPK在能量短缺的条件下可抑制以下几种生物合成途径,减少ATP的消耗:(1)AMPK磷酸化ACC抑制脂质从头合成;(2)AMPK磷酸化HMGCR抑制TC生物合成;(3)AMPK磷酸化GPAT减少TG合成;(4)AMPK可通过抑制转录因子的表达(SREBPs,ChREBP)进一步加强AMPK对ACC,HMGCR以及GPAT的作用,减少脂质合成。
3.2 AMPK促进FA分解代谢途径 AMPK除了抑制合成代谢途径,还可以推动细胞利用自身储存的TG,刺激脂肪三酰甘油脂肪酶(adipose triglyceride lipase,ATGL) 磷酸化Ser406位点,促进脂肪组织TG水解为DG,随后进一步水解成单酰基甘油(monoacylglycerol,MAG),并在此过程中释放FA[24]。游离的FA与跨膜蛋白CD36结合,使组装的CD36/Fyn/LKB1/AMPK蛋白复合物中的Fyn解离,解离后的Fyn失去磷酸化LKB1的能力,造成细胞核内LKB1向胞质富集并激活AMPK,活化的AMPK会募集更多的CD36在膜上定位,促进更多的FA由细胞膜进入胞浆[25,26]。随后,胞浆内的FA被线粒体外膜的脂酰CoA合成酶1(acyl-CoA synthetase 1,ACSL1),催化生成脂酰CoA,脂酰CoA经由线粒体内膜外侧肉碱棕榈酰基转移酶1(carnitine palmitoyl transferase I,CPT1) 的帮助进入线粒体进行β氧化[27]。由于ACC1和ACC2产生的丙二酰辅酶A是CPT1的有效抑制剂 ,因此,AMPK还间接调控了CPT1的活性,AMPK通过磷酸化ACC,降低丙二酰辅酶A浓度,使CPT1活性增强,促进胞浆中更多的FA被运送至线粒体进行β氧化,为机体提供更多的能量[19,28]。研究发现,NAFLD患者肝细胞中CD36棕榈化程度加重,导致肝脏FA氧化率下降,造成细胞内脂质累积;而抑制CD36棕榈化,可促进CD36充当分子桥,将FA连接至ACSL1,增强肝细胞中FA氧化,减轻NAFLD[29]。虽然CD36是否参与细胞内FA氧化以及CD36 与 ACSL1 之间是否存在关系还有待探索,但是靶向CD36 的棕榈酰化位点可能是治疗 NAFLD 的新治疗策略。
此外,当AMPK Thr172位点被磷酸化,可激活激素敏感脂肪水解酶(hormone-sensitive lipase,HSL) Ser565位点,拮抗HSL的Ser563和Ser660位点被环磷酸腺苷依赖蛋白激酶 A(cAMP-dependent protein kinase A,PKA) 磷酸化,致使HSL失活,DG的水解能力可随之降低,以减轻过量产生FA引起的毒性问题[30,31]。还有研究认为,PKA可通过磷酸化AMPK Ser173位点,对Thr172的磷酸化产生抑制,进而降低AMPK的活性,促进脂肪水解[30]。PKA和AMPK之间的这种双向协调关系对于脂肪细胞进行高效的脂肪分解至关重要,但AMPK与PKA互作调节脂肪水解的具体分子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在未来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4 miRNAs与AMPK
Ago2是Argonaute蛋白家族中唯一具有切片活性的蛋白,在体内,Ago2与miRNAs结合形成的RISC复合体,会抑制mRNA翻译过程下调其表达量[32]。研究发现,AGO2的S824-S834可被触发多位点磷酸化,进而沉默miRNAs,特异性的减轻miRNAs与mRNA的关联[33,34]。Zhang等[35]发现肝脏特异性Ago2的缺失可降低miR-802,miR-103/107和miR-148a/152的表达,这些miRNAs在体内过表达都会造成糖脂代谢紊乱。该研究还发现敲除Ago2的小鼠,ADP水平显著增加,AMPK因感知细胞内ADP/ATP比值增长而被激活,CPT1表达增加,提高了线粒体β氧化能力,小鼠糖耐量异常和胰岛素抵抗的现象有所缓解[35]。虽然现阶段miRNAs在细胞内参与代谢的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清楚,但Ago2和AMPK之间的这种联系可能成为葡萄糖和脂肪酸代谢之间的关键枢纽[36]。由此可推断,肝脏Ago2下调可沉默miRNAs,激活AMPK,增强线粒体功能,加速FA氧化,这可能是AMPK与miRNAs之间的潜在关联。当然,对此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加以证实。
miRNAs除了直接调控AMPK影响脂质代谢外,miR-122还可以结合SIRT1的3’-UTR抑制其表达间接调控AMPK。SIRT1可介导LKB1由细胞核进入细胞质磷酸化AMPKThr172位点,进行脂质代谢。当miR-122过表达时,通过抑制SIRT1的表达,削弱了LKB1进入细胞质磷酸化AMPK的能力,使脂质在肝细胞内累积,加速了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的进展。
综上所述,AMPK是脂质代谢的关键调节因子,miRNAs可介导AMPK调控脂质相关基因的表达,参与脂质代谢等过程。
5 miRNAs介导 AMPK调控脂代谢相关疾病
miRNAs在AMPK信号通路相关脂质代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miR-122、miR-34a、miR-33、miR-552-3p和miR-802等miRNAs,它们在脂质代谢过程中发挥了多种生物学效应,在脂质代谢紊乱疾病中展现出了较高的潜力。
5.1 miR-122 miR-122是肝脏中最丰富的miRNAs,占肝脏miRNAs总量的70%以上,对影响肝脏代谢功能具有重要作用[37]。Long等[38]通过体内外研究均证实了,过表达的miR-122可下调Sirt1的表达,进而抑制LKB1/AMPK信号通路,导致肝脏中脂肪积聚,最终诱导了NAFLD的发生。抑制miR-122后,Sirt1的活性增强,重新激活LKB1/AMPK信号通路,同时,SREBP-1c、 FASN、 SCD1、ACC1等脂质合成相关基因的表达也因AMPK的激活而降低,从而减少了FA、TC、TG的合成,使肝细胞免受脂质过度沉积带来的危害。故此,miR-122可能是脂质代谢紊乱相关疾病的治疗靶点,此外在一项临床研究中发现NAFLD患者血清miR-122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群,并且miR-122的增长程度与年龄、BMI、NAS、ALP和纤维化分期显著相关,提示miR-122水平与NAFLD的严重程度相关,故可作为一种用于NAFLD早期诊断和随时检测的生物标志物[39]。
5.2 miR-34a miR-34a的表达量在NASH患者血浆和肝脏中显著上调;其不仅在NASH诊断中比常规的生物标志物CK-18具有更高的AUROC,还具有良好的疾病特异性[40]。Min等[41]研究发现miR-34a可以下调SIRT1蛋白水平,导致AMPK去磷酸化,最终造成胆固醇积累。使用miR-34a抑制剂可激活AMPK信号通路,增加CPT1的表达,提高了线粒体β氧化作用。该研究确认了AMPK作为中介在miR-34a抑制剂治疗后出现的肝脏FA氧化水平升高的现象,此外,SIRT1的表达也在miR-34a抑制剂治疗后上调,进而促进了AMPK信号通路的激活[42]。虽然miR-34a可作为NAFLD相关的生物标志物,但其具体机制也不完全清楚,有很多问题仍未解决。
5.3 miR-33 miR-33家族成员miR-33a和miR-33b分别是 SREBP2和SREBP1编码基因的内含子区域,控制胆固醇稳态的相关基因转录以及脂质生物合成和运输[43]。研究证明miR-33可有效调节由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展而来的胆固醇外流现象,使巨噬细胞能够将TC从斑块中移除,通过循环HDL-C转运至肝脏,随后清除体内[44]。由于,AMPK在过往研究中始终处于维持能量稳态的中心点,miR-33过表达可直接抑制AMPK表达,增加体内TC和TG的含量[45]。同样,在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模型中发现,沉默miR-33可能促进全身氧化代谢,但同时又不会引起代谢失调,这表明,减少已知miR-33的剂量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来说可能是一种安全且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46]。此外,尿苷A可降低miR-33a的表达,增加AMPK磷酸化的表达,减少下游SREBP1-c的磷酸化,促进RCT处理巨噬细胞中胆固醇累积现象[47];由HHP处理的桑椹果实提取物同样被发现可显著抑制-miR-33的表达,提高AMPK活性,下调SREBP2的表达量,减轻脂质合成,减少血清胆固醇水平,降低动脉粥样硬化风险[48]。当miR-33被全局突变或被拮抗药物抑制时,模型小鼠的动脉粥样硬化表现出倒退现象。由此可见,直接或者间接抑制miR-33的表达增强了AMPK的磷酸化,提高了它们作为治疗代谢综合征、动脉粥样硬化和NAFLD靶点的巨大潜力。
5.4 miR-552-3p miR-552是一种新发现的miRNAs,其在生物学过程和疾病中的功能和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清楚[49]。但最新发现它的3’端前体通过抑制LXR α和FXR核移位,导致其丧失转录活性,进而显著降低了SREBF1,FASN,SCD1等糖脂代谢基因的表达,且与正常组相比,NAFLD患者肝脏中miR-552-3p水平显著降低[50]。这种降低可能与临床NAFLD的进展呈正相关,未来仍需要更多的临床样本来支持与验证。
5.5 miR-802 miR-802会呈现异常上调趋势,导致代谢异常,因此抑制miR-802的表达有可能成为调节肝脏糖脂代谢的靶点[51]。Ni等[52]研究发现miR-802在肥胖中的异常表达,有部分原因是靶向了肝脏AMPK信号通路,下调miR-802的表达,增强AMPK磷酸化水平,进而促进了糖脂代谢中SREBP-1c、FASN等关键基因的表达。故抑制miR-802可成为治疗与肥胖相关的T2DM和NAFLD的潜在新靶点。
6 总结与展望
目前,miRNAs因其广泛存在于细胞内且具有高度保守的特点而受到广泛关注,但miRNAs与AMPK之间的关系,目前还在深入研究中,并且仍有许多需要阐述的问题:(1)miRNAs虽调控代谢过程,但这种代谢程序是否调控mRNA转录、生物发生等具体机制目前仍存在盲点;(2)现有研究显示,调控miRNAs激活AMPK信号通路可能是改善脂代谢紊乱的潜在治疗方案,但调控miRNAs是否会改善AMPK信号通路的其他下游途径,如内质网应激、炎症、自噬等仍有待深入探索;(3)循环miRNAs一直被认为是良好的生物标志物,但仍需要进行更多的临床研究来加以探究。
综上所述,miRNAs在脂代谢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能是未来诊断及治疗脂质代谢紊乱相关疾病的生物学标志物和治疗靶点。与此同时,AMPK 作为一个全方位调控糖脂代谢的关键枢纽,在预防和治疗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肝脏Ago2活性被抑制时,miRNAs随之沉默,AMPK信号通路随之被激活。此外直接抑制miRNAs的表达,还可能造成糖脂代谢调节剂SIRT1的表达增加,激活LKB1/AMPK信号通路,促进其下游脂质代谢途径,减轻脂质在肝脏内蓄积。虽然这中间确切的机制尚不清楚,但通过调控miRNAs介导AMPK信号通路可以调节代谢途径,维持体内代谢平衡。为临床上治疗脂质代谢紊乱相关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