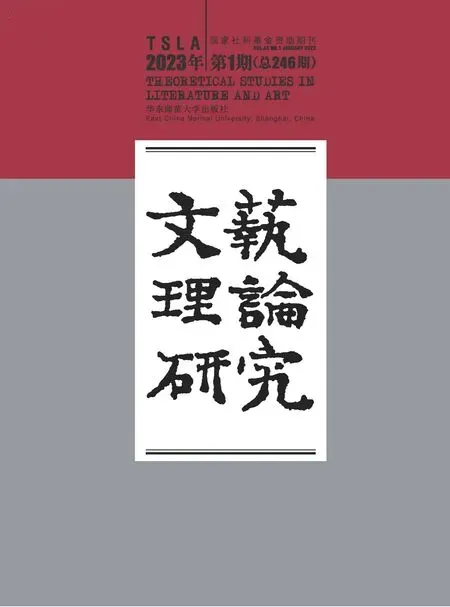晚清戏曲功能的多向度展开
——以黄燮清戏曲创作为中心
马丽敏
在中国古代戏曲家中,长时间从事戏曲创作、能够被称为“专业”作家者并不多见,黄燮清(1805—1864年,字韵珊)是其中的一位。从道光十年(1830年)二十六岁时创作《茂陵弦》始,到咸丰六年(1856年)五十二岁时完成《居官鉴》①,他的戏曲创作活动延续近三十年。这也是黄燮清生命历程的重要阶段,在从青年进入老年的漫长时间过程中,屡经坎坷的科考生涯、辗转流离的入幕经历、内外战争与天灾、疾病的侵扰之痛等,都带给他有才而不得用于世的苦闷,思想与心态始终处于纠结无奈中。凡此,不仅在其诗文中有所体现,于戏曲创作中亦可寻觅到斑斑踪迹。其中一以贯之者,首为以才子自诩与用世之志之间的矛盾;而在转换身份、改善地位的进取过程中,他有效利用了戏曲作品的交际功能,戏曲的工具性作用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惜终未能达成其用世之心;至于教化功能的强调,一方面出于文以载道价值观的因循与理解,另一方面,也缘于文体功能与现实情势之所需。对于黄燮清等晚清文人而言,以戏曲创作的方式表达对人生、时代的理解,不仅促成了戏曲功能的多向度展开,也为梁启超等学人重新审视戏曲文体的作用提供了思路,当然也带来了戏曲形态的诸多新特征。
一、 才子之名、用世之志与戏曲文体的选择
黄燮清年少而才高,道光四年(1824年)二十岁时已考取生员(陆萼庭120),声名广为流播,对自己的人生亦颇多期许。然从道光五年(1825年)至十五年(1835年)的十余年里,他六入秋闱方获得举人的身份(陆萼庭120—123),本以为顺势而为,进士不过是囊中之物,所谓“平生万里志,直欲访昆仑”(《倚晴楼诗集》21),却又六入春闱而无所收获(陆萼庭123—128)。从道光十六年(1836年)至三十年(1850年),人生又过去了十五年,已近知天命之龄的黄燮清不得不发出“计车六上不得志,扁舟散发归沧浪”(《倚晴楼诗集》70)的慨叹,最终绝意科举。
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应童子试起,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最后一次参加会试止,三十余年的科考历程,浸透了黄燮清不断自我审视、自我期许以及渴望破茧而出的冲动,也写满了难以名状的失落和茫然。如道光七年(1827年)所作《拟古》组诗之六:
驱马入平原,飞尘浩无际。夕阳自古今,莽莽动愁思。铜山苦易颓,祁连冢亦废。富贵逝浮云,豪华铄精气。寒暑数十年,蜉蝣寄天地。丈夫不自立,悠悠嗟没世。(《倚晴楼诗集》8)
天地如广漠,夕阳亘古今,策马平原的诗人因古思今,联想到自己“寒暑数十年,蜉蝣寄天地”的经历,愁思笼罩四野,悲叹渺无边际。大丈夫是否还有机会“自立”,个人实难以自主,除了慨叹时光倏然、“蜉蝣”的命运依旧外,唯有一声叹息而已。即便如此,在人生的多数时刻,黄燮清依然秉持着对自身才华的怜惜,以及为世所知、为世所用的渴望。如道光十一年(1831年)第三次乡试落第后,黄燮清作《拟陈思〈美女篇〉》:“出处有时命,无媒羞自前。托身正其始,素心良独坚。幽芳不求赏,惜此兰与荃。”(《倚晴楼诗集》14)佳人秉持本心,不屈附时俗,只是可惜兰花、香草这些美好的事物,终究无人欣赏。哀怨的情绪和愤郁的情感如此幽深,似在时刻等待一位欣赏者以及勾连彼此的媒介。
终于,黄燮清在道光十年(1830年)所作《茂陵弦》传奇中,借助一种跨文体的互文性表达,这种怜惜与渴望得到了鲜明而准确的传达。这是黄燮清的第一部戏曲作品,其中关于司马相如形象的重写与改写,刻意注入了他的个人情感,融入了有关自己未来的诸多想象。其《自序》云:
客谓余曰:“《茂陵弦》何为而作也?”余曰:“为相如作也。”曰:“相如生平惟谏猎一事差足传,余碌碌无奇节,特词章士耳,恶乎取?”余曰:“否,否!相如非词章士也,使其才得大用于时,必更有所施为,词章乌足尽相如!”“于何见之?”“即于相如之词章见之。凡人心乎天下,而所值之时与势或不足罄其志量,则其嵚崎磊落之气与夫平昔所孕之抱负,郁积至久,必磅礴倾泻于诗古文字之间,而不能自掩。相如虽事业不概见,其所著《子虚》《上林》等赋,皆有关世道者也。[……]相如之赋,名臣奏疏变格也。故读相如之词章,正可见相如之才之不尽于词章也,而卒以词章显其才者,则以武帝仅能识其词章之才,而终不能尽其词章以外之才也,抑亦相如之不幸也。遇使之然也。”曰:“子既薄相如之遇,何曲中又若深艳其遇者?”余曰:“相如之遇曷足艳,以天下正有才如相如而其遇并不能如相如者,则相如之遇未始不可为才人吐气也。”②(《茂陵弦》自序)
“为才人吐气”,毫无疑问是黄燮清创作此剧的初衷。在《自序》中,他以对话的形式自我辩难,结论是:司马相如非仅为“词章士”,其所著《子虚赋》《上林赋》等皆为有关世道者,如果其才能得大用于当时,必将有所作为;一代雄主汉武帝只识其“词章之才”,而不能识其“词章以外之才”,“遇使之然也”。尽管如此,司马相如依然是很幸运的,因为还有“才如相如而其遇并不能如相如者”,以“词章之才”名闻天下的黄燮清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位。也因此,在《茂陵弦·写意》中他再三提醒读者:“染霜毫,莫认写相思,怜才耳。”(《茂陵弦》卷上)即他敷衍相如故事的兴奋点并不在“相思”二字,而在乎“怜才”,所谓“壮怀艳思未全消,磊块何妨借酒浇”(《茂陵弦》卷下)也。
这部颇具自喻之意的戏曲作品,也获得了同人好友的广泛理解与认可,如汪仲洋所谓“惟才人乃能为才人写照”(《茂陵弦》评语)。如道光十四年(1834年),桐城古文后劲之一、时为浙江学政陈用光幕僚的吴德旋(陈用光1168,1173)为《茂陵弦》作序,直抉创作之旨:“韵珊年少才美,借《琴心记》谱《茂陵弦》乐府,即可作韵珊《感士不遇赋》观。”(《茂陵弦》序)又如《旅慨》一出瞿世瑛之眉批:“长卿词赋,大有作用,不仅华国而已。作者娴于词赋,此殆自抒胸臆。”(《茂陵弦》卷上)而道光十六年(1836年),以词作闻名的黄曾③再次为《序》,则表达了“巾褐”之辈的情感共鸣:“难平梁鸿之噫,致动唐衢之哭。虽奇数之不偶,实知音之鲜逢。则读家弟韵珊《茂陵弦》一谱,允足以慰巾褐之素心,洗风尘之白眼焉。”(《茂陵弦》序)其中“知音之鲜逢”之语,切中了《茂陵弦》为古今所有负才而失志之士发抒怀抱之肯綮。
凡此之类的评语,后来频繁出现在黄燮清其他戏曲作品的评论中,也成为有关其一生评价的关键词。如在《帝女花》诸题词中,有汪适孙云:“无双才子生花笔,天花法借瞿昙说。”(《帝女花》题辞一)李光溥《满江红》词云:“大排场,了结再生缘,才人笔。”(《帝女花》题辞一)陆《鸳鸯镜·题辞》之一云:“五十三参参未真,痴魂易堕障中尘。情场全靠仙才笔,唤醒鸳鸯镜里人。”(《鸳鸯镜》)《桃溪雪·送外》李光溥眉批云:“字字从肺腑中流出,至情奇采,非真情种、真才子不能道一语。”(《桃溪雪》卷上)不过,戏曲中的司马相如不仅文采斐然,还挥斥方遒,建有不世之功勋,现实中的黄燮清则时运不济、仕途渺茫,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才终有所遇,由时任浙江乡试主考官的翁心存(1791—1862年)慧眼识英,取为举人。(《倚晴楼诗集》2)
在不断会试的十多年里,黄燮清仍然没有中断戏曲创作,且借助戏曲表达用世之志的意图日益清晰。咸丰七年(1857年),翁心存为黄燮清的别集写序,也特别提及他当时以戏曲名世的影响:“所梓乐府倚声已纸贵一时,几于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矣。”(《倚晴楼诗集》2)的确,道光十八年(1838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入京参加会试,他都在拜访恩师翁心存时奉上所著戏曲,第一次奉上《帝女花》《鸳鸯镜》《凌波影》,并得到了“清才”(翁心存,《翁心存日记》第1册314)的评价,第二次则将刚刚完成不久的《桃溪雪》送呈恩师指教(翁心存,《翁心存日记》第2册786)。显然,并不希望他以词曲名世的翁心存,没有表现出对弟子戏曲家身份的反感,反而不自觉地将黄燮清与司马相如联系起来:“自喜月旦不谬,异日文章华国,长杨羽猎之才,此其选也。”(《倚晴楼诗集》2)如是,《茂陵弦》传奇显然也影响了翁心存的认知,黄燮清以才子写才子之创作目的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可惜,翁心存的预言也终未成真。屡上春官而不第的黄燮清,直到咸丰二年(1852年)才终于被选为湖北某地知县,而年届五十的他又因战乱不能赴任,沉沦困顿之苦几不可言说。咸丰四年(1854年)五十岁生日之际,黄燮清将自己一生际遇述诸诗笔:
弱冠骋词藻,旌鼓张一军。三十举孝廉,去踏长安春。浮名动卿相,流誉及王门。属草惊四座,诧叹笔有神。读书期用世,国器颇自珍。铅刀未一试,十载疲风尘。浮家泛江浦,更作诸侯宾。一官嗟晚遇,可治尧舜民。边烽忽中断,财虎当要津。愧乏济时策,耻作出岫云。平生苦蹭蹬,举足(愁)荆榛。行当侣白鸥,闲散不复驯。(《倚晴楼诗集》93)
“浮名动卿相,流誉及王门”的声名,“读书期用世,国器颇自珍”的志向与自负,此际皆已被“边烽”“财虎”阻断,如果不是“铅刀未一试”的梦想依然还在,或者就不会有再入都谒选的行为了。翁心存所作序中,对其“困顿沈滞以至于今也”的遭际也感慨万端:“生少以词曲名,世皆以词人目之,中岁以往益肆力于诗、古文章,世遂以诗人、文人目之,近又却尘息影,读老庄之书而溺于神仙杳渺之说,世且以有道人目之。噫!生之学愈进,而生之志亦愈可伤已。”(《倚晴楼诗集》2)的确,少负才子盛名,又怀满腔用世之志,一生都在“倚晴”④而望,却长期沉沦下僚,未能获得机会充分施展抱负。黄燮清之悲又何止是时代之憾哉!
同治元年(1862年)后,黄燮清获得了新的出仕机缘,先后得任宜都知县、松滋代理知县,然任职时间皆很短,加之年老多病,济世之志已然无力施展,人生理想也如镜花水月,徒增难以名状的悲伤。所谓的才子之名,此际真的成了一个“传说”,如孙恩保所云:“黄九词名海外传,更看雅乐奏钧天。”(《桃溪雪》题词)当时,社会动荡,战乱不休,黄燮清精心打造的倚晴楼亦毁于战火,藏书付之一炬,又饱受颠沛流离、朝不保夕之苦。⑤他关注时局,曾经发出过扣人心弦的指责:“叹当局议防议战,总无全策。征调可怜财赋尽,流离但觉乾坤仄。”(《倚晴楼诗余》187)也有过痛彻心扉的浩叹:“浩劫会有尽,剥复理亦常。时艰乐土少,忧端两茫茫。”(《倚晴楼诗集》84)尽管是着眼于时代的乱局,却只能落脚于个人生活、生存空间的逼仄,生活的挤压已经让无处施展抱负的他不再具有寄情诗文的心境,除了“却尘息影,读老庄之书而溺于神仙杳渺之说”外,似乎再无其他慰藉心灵的方式。恩师翁心存在《序》中说:“生岂遂以俯仰林壑,长吟抱膝终耶?”他坚信黄燮清并非一个“俗吏”:“以生之文采照耀,内而卿相吐哺,外而疆吏倒屣,则固未尝无知己,宜亦可以扬眉吐气,抟羊角而致青云之上矣。”(《倚晴楼诗集》2)然而,他所希望黄燮清成就的“不朽之业”最终只能被“神仙杳渺”之说取代。一代文人之悲,莫过于此!
二、 题材、副文本与戏曲的应用功能
以戏曲创作持续时间之长、作品数量之多,尤其是探索程度之深而言,黄燮清都应归属于戏曲史上少有的专业性作家。然梳理其创作的发生,除了《茂陵弦》《居官鉴》外,其他作品皆明确与他人之“命”“托”相关;戏曲创作的交际目的十分清晰,不免令人联想到黄燮清之于戏曲功能的认知及其赋予戏曲作品的工具意义。如果说道光十二年(1832年)《帝女花》的创作,有“陈子琴斋将发其郁,以观其才”⑥的因素,似乎在强调好友陈其泰(1800—1864年)敦促其创作的慰藉之意,然推之陈其泰《序》中所言“余尝过拙宜园,韵珊出所制传奇数种示余”(《帝女花》陈序)之语,则知黄燮清主动出示戏曲作品暗含的推广之意。《帝女花》完成之后,亦是如此。万立衔《题辞》有“示我黄绢词”(《帝女花》题辞一)之句,吴承勋《题辞》之《金缕曲》其二有“索我题新句。十旬来、尘笺丝砚,镇无一语”(《帝女花》题辞一)之感慨,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抒郁”方式的一种,但也表明黄燮清对戏曲的应用功能十分重视。其兄黄际清于《跋》中交代是剧“哀感顽艳,声情俱绘,一时传览无虚日”(《帝女花》跋),虽然是就剧本立意,但也说明了“传览”的主动性及其效果。如是,在经历过广泛的传播及其所带来的更为广泛的确证后,黄燮清主动将《茂陵弦》《帝女花》送呈当时的礼部侍郎兼浙江学政陈用光⑦,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呈送给与自己仕途际遇攸关的当道者,毕竟与日常朋友圈的传播不同,其中之别解更可见出戏曲之工具性所在。陈用光得阅黄燮清的戏曲作品后,作《序》给予高度评价:“(《帝女花》)苍郁诡丽,益叹其才之美。”(《脊令原》序)他也因此成了陈用光的弟子与座上客,多次参与其召集的文学唱和活动。⑧道光十四年(1834年),黄燮清根据陈用光之“命”,先后以《聊斋志异》中《曾友于》篇创作了戏曲《脊令原》,以《池北偶谈》中《碎镜》篇为题材创作了《鸳鸯镜》。二作均颇得陈用光之意,当然也获得了进一步肯定。陈用光亲自为序,云:“稿竣来谒,览其词,华而不靡,新而不凿,发乎情,止乎礼义,洵足惩创逸志而感发善心者。”(《鸳鸯镜》序)且亲与评点,如《脊令原·依叔》之眉批:“才人之笔,自具化机。”(《脊令原》卷下)又“稍加点定,促付剞劂”(《鸳鸯镜》跋),促成了黄燮清戏曲的及时出版。而黄燮清也借机广邀题写,形成了其戏曲传播的第一个高峰,如翁心存《序》中所谓:“所梓乐府倚声已纸贵一时,几于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矣。”(《倚晴楼诗集》2)这其实也真正启发了黄燮清以戏曲创作开辟人生之路的思路和机缘。
道光十五年(1835年),陈用光去世,然在同年秋天的恩科乡试中,典试浙江的翁心存走进了黄燮清的生活。因为这位学政的青睐,刚刚三十岁出头的黄燮清终于中试,才名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颂,未来的人生图景也因此更为广阔。翁心存对黄燮清的戏曲作品有所首肯,写过“拙宜乐府最清新,黄九才名迥绝尘”(《知止斋诗集》578)之句。不过,他显然更看重黄燮清的经世之才,《序》中表示“不欲生之仅以词人、诗人、文人名焉”,对他“中岁以往益肆力于诗、古文章,世遂以诗人、文人目之”,而不能得到世人认可百思不解,又无比同情:“生之学愈进,而生之志亦愈可伤已。”(《倚晴楼诗集》2)翁心存期望黄燮清有经世之作为,当一个好的官员,并积极促成此事,可惜结果并不理想。
道光十六年(1836年),黄燮清将《茂陵弦》《帝女花》《鸳鸯镜》《凌波影》,并词两卷,合刊成《拙宜园集》。他广邀师友题写,并将其与之前的序跋等一起附于戏曲文本中,这当然是带有自我设计的用心之处,序跋题词等戏曲“副文本”(杜桂萍第4版)之于社会生活结构中的交际功能因之发挥效用。梳理这些题写,诗、词、文、赋,各类文体兼具,作者则多为僚友、同门或戚旧,其中最为特殊者就是陈用光了。他为黄燮清的两部戏曲作序并予以品评,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则是“风人之旨”。如在《鸳鸯镜·序》中,他强调词曲“亦必合乎风人之旨为佳”(《鸳鸯镜》序),而《鸳鸯镜》“发乎情,止乎礼义,洵足惩创逸志而感发善心者。则是编之作,曲而进于诗矣。吾得以一言蔽之,曰‘思无邪’”(《鸳鸯镜》序),高度肯定了黄燮清戏曲的风教意义。这一观念深刻地影响了黄燮清,其在《鸳鸯镜·跋》中对陈用光“意盖为维风俗、正人心发也”(《鸳鸯镜》跋)目的之点题,以及陈用光逝世后继续刊印、创作戏曲,且强调“而师所以维风俗、正人心之苦衷,又惧其泯而弗彰也。爰毕梓事,以存师意于不忘云”(《鸳鸯镜》跋),尤其是在此后戏曲作品中表现出极为自觉的创作转向,不仅可以洞见其继承遗志、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更能说明其受陈用光功能性戏曲观念的影响之深。
不过,从对戏曲文体交际功能的认知上看,陈其泰的影响应该更大一些。当年处于科举失利郁闷中的黄燮清,或者正是因为陈其泰“虽云小道可观,亦足立言不朽”(《帝女花》陈序)这一句话,才真正认识到戏曲的应用功能。《帝女花》的创作也是这一实践的结晶。黄燮清在“宇宙皆贮悲之境”(《帝女花》自序)中摹写一段前朝的沧桑历史,传达的是“仆本恨人”(《帝女花》自序)的个人兴悲,更是看中了一个宏大叙事框架中容纳的文化情结,即关于明朝历史的不断反思;而他对这段帝王家故事所进行的桃花扇式——“事涉盛衰,窃比桃花画扇”(《帝女花》自序)处理,即陈其泰所谓“谱兴亡之旧事,写离合之情悰”(《帝女花》陈序),更昭示了其借助戏曲作品“立言不朽”的创作诉求,即“从此瓣香诗史,又添辉煌汗简之章”(《帝女花》陈序)。这一切,得益于亦师亦友的陈其泰的提点,也是随后他邀请众多友人为《帝女花》撰写序跋题词的重要原因。目前看,此剧是黄燮清众多剧本中副文本最为丰富的一部,据道光十六年(1836年)版本统计,除了《自序》《自识》之外,已有《序》二、《跋》二,题辞则多达四十首(篇),且创作时间密集。由此,足以推断黄燮清彼时急于得到确认自我的心理。道光十五年(1835年)以后所作剧本,即便序跋题词较多者如《桃溪雪》,也再未见他如此刻意地广泛求取或搜集人们的题写。
在黄燮清的诗集乃至其编撰的《国朝词综续编》中,亦可见其戏曲传播情况的记录,友人为其戏曲所撰题词、序跋等皆收入其中,这显然是有意为之。初步统计,《国朝词综续编》中摘录的同人评论自己戏曲的词作,计有十四首之多。如杨懋麟《解佩令》词题小注云:“题黄韵甫燮清《凌波影》乐府。”(《清词综》第4册474)王逢辰《念奴娇》词题小注云:“题黄韵甫《桃溪雪》院本,传吴绛雪女史殉烈事。”(《清词综》第5册6)张金镛《齐天乐》词题小注云:“黄韵珊《帝女花》院本,纪故明长平公主事,刊成见寄,辄书卷端。”(《清词综》第5册79)《倚晴楼诗集》中的相关文本则主要以诗歌为主。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舟次峡江,徐芷坪明府(燧)招集官舍》诗云:“主人记曲似张红。”诗句有注云:“予所制乐府,明府辄能背诵。”(《倚晴楼诗集》59)至同治三年(1864年),时在湖北任知县的黄燮清已垂垂老矣,尚有人因仰慕其戏曲而登门拜访,其《同年龚九会农部(绍仁)过访寓斋赋赠》诗中有注:“主政于二十年前见予所制乐府,心契已久,兹来鄂垣,迫思一面,适予以帘差回避。”(《倚晴楼诗续集》154)可见黄燮清重视戏曲作品推广所达成的效果。
统观黄燮清戏曲的副文本,尽管出自不同的戏曲文本,出自不同身份的作者之手,创作的时间、机缘乃至语境亦有不同,然序跋题词的内容其实无比丰富,颇可见创作者出于不同目的之书写策略。有心无旁骛评点文本者,也有借机抒发自我感慨、呈示才能者,而几乎在在皆是者,则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作者的溢美之意,这毫无疑问是文体所具有的应酬功能决定的。基于这一书写策略,也可以管窥到黄燮清心态、趣尚之若干。
首先,诸序跋题词皆表现出努力解读作者创作意图等倾向,尽管人言人殊,却多归于对作者之才的肯定。如《茂陵弦》传奇,黄曾、瞿世瑛两人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所作《序》,皆从司马相如之“才”映射到作者之才。黄曾之《序》云:“读曲起舞,聆音展愁,知君别寓琴心,岂抱绿绮以老。”(《茂陵弦》序)对当时已受到大吏赏识的黄燮清的未来充满期待。而文后俞兴瑞的题诗其一:“气郁凌云四壁寒,穷途狗监遇来难。分明一掬才人泪,莫作闲情绮语看。”亦是如此强调。其二:“长安风雨一鞭遥,红豆新词别恨撩。驷马期君同努力,试将题曲当题桥。”(《茂陵弦》题词)以“题曲”揭示黄燮清之于未来的期许,也与当时他受到不世之知、人生正如鲲鹏展翅之状态相关。后来,历尽千磨万折的黄燮清,其人生并未如人们所望,然有关“才”的赞许仍然构成了戏曲序跋题词的主调之一。如沈善宝为《凌波影》题诗,其三:“陈王藻采千秋擅,八斗才华又属君。”(363)彭玉麟(南岳山樵雪琴)《桃溪雪·题词》其十一:“许多绿惨红愁句,写出班香宋艳才。”(《桃溪雪》题词)曾经令他心动的古代才子司马相如、曹植、宋玉等皆成为比附对象,又何尝不是黄燮清包蕴着非凡才华的个人气质的映现呢?
其次,诸序跋题词多有文人趣味的表达,且颇多指向作者内心衷曲的信息,显然是日常交往的“留痕”。如吴德旋为《茂陵弦》所作《序》,虽然也是为“才”张目,却从才子佳人的角度入眼:“文君富家女,以一念怜才,不避夜奔之辱,柔情侠骨,非郑、卫诗人所刺者可比。予固亦好为梁、陈绮语者,若礼法之士以波荡后生责之,不敢辞其罪矣。”(《茂陵弦》序)其中对佳人卓文君的肯定正是对才子的礼赞,这与瞿世瑛《茂陵弦·序》表现出的对神仙眷侣的艳羡差可类似:“文章华国,给班管而何惭;眷属疑仙,赋《白头》而非偶。可谓清才绝世,艳福双修。”(《茂陵弦》序)体现了一般文人关于神仙眷侣的人生趣味。初看,这与黄燮清的表达似有违和之感,因为他再三强调“岂为娥眉修艳史”(《茂陵弦》卷上),表现出基于道德礼法对卓文君乃至洛神的贬斥之意。揆诸戏曲文本则可以发现,实际并非如此简单。长达二十四出的《茂陵弦》,其实以大量笔墨塑造了卓文君的佳人之美,其才貌、智慧的超群,对司马相如的仰慕等,浸淫其中的缱绻、得意少有掩饰。如《琴媒》一出,与司马相如初次相见的卓文君,如神女谪降人间:“(你看他)淡淡扫峨眉,(真个是)遥山滴烟翠。香风颤,鬓影低,(问何年)藐姑神(谪向)绮罗里。”(《茂陵弦》卷上)陶醉其中的情感充满了艳情色彩。而《奔艳》中为爱情夜奔的果决:“听素弦一曲泠泠,(便)琼想瑶思打叠并。教痴魂颠倒,如不胜情。闲来自省,自觉芳心难定。(特为你)趁微风夜游巫岭,不烦他红丝管领,权借他绮琴作证。”(《茂陵弦》卷上)《当垆》中的夫妻相得之乐:“有句双吟,调琴共抚。是乡极乐,今生合老温柔;相得甚欢,几世修成艳福。”(《茂陵弦》卷上)皆透射了作者难以掩饰的赞许、肯定。而《凌波影》作为“言情之书”,被陈其泰标举为“好色不淫”(《凌波影》序),带给阅读者的则是如是之观感:“璀璨罗衣雾縠轻,神光离合不分明。惊鸿态度游龙致,都自凌云笔下生。”(沈善宝363)以故,所谓“壮怀艳思未全消,磊块何妨借酒浇”(《茂陵弦》卷下)之“壮怀”,实际上当与“艳思”共同演绎了黄燮清生活的两个端面,只不过因为有意的遮蔽无法看清而已。如是,其内心之衷曲与创作旨归之标榜并非真正契合。
无论如何,借助于不断的自我塑造以及戏曲的广泛传播,黄燮清“才”名昭著,声动南北。安徽桐城人吴廷康(1799—1881年后)为陈用光之姻亲,应是仕宦浙江时在陈用光处与黄燮清相识⑨,其妻张氏去世后,力请他创作戏曲作品以传之:“康甫既痛其(张宜人)逝,而又悯其代己也,嘱为乐府以传之。予不文,何足以传宜人,而康甫请之坚[……]”(《玉台秋》自序)道光十七年(1837年),《玉台秋》传奇完成,吴廷康无比满意,直到光绪年间,还以此剧为核心进行以表彰节烈、维持风化为旗帜的宣扬,并借机完成了其家族史述的书写,表达其借助戏曲立言传名的本质诉求。(马丽敏174—181)黄燮清另一部影响较大的戏曲《桃溪雪》也与吴廷康关系密切。当吴廷康担任永康县丞时,访得永康才媛吴宗爱(字绛雪)于三藩之乱中殉节事迹,“惧其久而泯焉”,再四请求黄燮清“制曲以传之”(《桃溪雪》自叙)。咸丰二年(1852年)底或三年(1853年)初,在京城谒选期间,涉足舞榭歌场的黄燮清,才名为梨园艺人所知,遂又应其所请而创作舞台演出本《绛绡记》,据《聊斋志异·西湖主》改编。吴仰贤《小匏庵诗话》载,黄燮清“六上春明,与日下诸名流推襟送抱,极文酒之欢,公卿争折节下交”(张寅彭6594),这种由南到北的声名流播,表面上维系的是科举之路的柳暗花明,实际上又与戏曲创作的巨大影响密切相关。
黄燮清最终也未能获得满意的进身平台,实践其经世、治世之志,这与其戏曲创作的初衷不免疏离,也应是晚年黄燮清最终转向研读道家之说的原因之一。清初黄周星言:“嗟乎,士君子岂乐以词曲见哉?盖宇宙之中,不朽有三,儒者孰不以此自期?顾穷达有命,彼硕德丰功,岂在下所敢望?于是不得已而竞出于立言之一途[……]”(蔡毅1486)黄燮清选择戏曲亦是如此。在他对晚清社会现实关注最深的戏曲作品《居官鉴》中,曾有这样的结尾诗:“出山心事为苍生,不取人间显宦名。欲使疮痍登祍席,好施霖雨化欃枪。传家书卷惟忠孝,经世文章本性情。聊借管弦鸣吏治,他年歌舞祝升平。”(《居官鉴》卷下)虽然是为晚清官员王有龄(魏明扬 赵山林115—124)代言,更是为自己“写心”:“经世”才是人生最重要的“文章”,才是其真正的“性情”。这部最能体现其济世理想的戏曲作品,完成后却无力刊印,被束之高阁,无论是基于经济上的困窘,还是缘于兴味上的疏淡,与当年黄燮清借助戏曲创作阐扬自我的热情相比,其实都是一种不言而言的态度。冯肇曾言其晚年“自悔少作,忏其绮语,毁板不存”(《居官鉴》跋),或者印证了他对自己借助戏曲立言的悔恨。人生之“三不朽”(《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1152),对于黄燮清一类文人而言,只能选择“无所借而自立者”(钱大昕244)之“立言”,而将戏曲与诗文创作同样作为立言的载体之一,尽管在晚清时期还是一种观念开放的表现,然其工具性意义毕竟十分有限,所谓“功之立必凭借乎外来之富贵”(钱大昕244),黄燮清力图改变命运的这一规定性,反而倾其一生之力成就了自己作为戏曲家的声名。
三、 风世、济世与戏曲创作的转型
黃燮清的戏曲作品以传奇为主,真正符合杂剧之义者只有一部《凌波影》(四出)。梳理其创作,戏曲艺术上的探索固然可圈可点,但更值得关切的是其创作的“形塑”问题,这无疑是晚清戏曲研究视域中更缺乏探讨的内容。一般文人的戏曲创作,往往由自喻式演绎开始,但很快转向以风世为主旨,且以一生践行之,则当归于黄燮清独特的戏曲创作路径;其文本风格由最初的侧艳清丽很快以顺理顺情的姿态转呈质朴清雅的艺术风貌,匠心自如之运筹中亦少有违和之感,都与其良好的艺术修养、能力有关,当然也来自本人对戏曲文体的理解与热爱、家乡海盐的戏曲传统影响,而师友点拨、指导的意义更值得重视。可以说,“自塑”与“他塑”比较完美地体现在黄燮清的戏曲创作过程中,是他成为晚清戏曲作家中佼佼者的原因之一。
绾结而言,对黄燮清戏曲创作产生最大影响者是陈用光。这位在戏曲史上几乎没有位置的当朝大员,以“国彦”(《倚晴楼诗集》2)的评价介入了其戏曲创作过程。其后,黄燮清自觉借助戏曲作品参与社会伦理建设,戏曲文本成为他经世思想的重要载体。
道光十四年(1834年),初入幕府的黄燮清迅即得到陈用光的赏识,并遵其命创作了《脊令原》《鸳鸯镜》两部传奇。《脊令原》之名源自《诗·小雅·棠棣》,取“脊令在原,兄弟急难”之意,重在阐述兄弟和睦之义。《鸳鸯镜》为戒男女情爱而作,重在“惩创逸志而感发善心”(《鸳鸯镜》序)。陈用光为《脊令原》所作之《序》不仅鲜明表达了对戏曲的认知,也包含着对黄燮清以往创作的评价与规劝。原文如下:
曲之感人,捷于诗书。今有至无良者,气质乖谬,师友弗能化焉,试与之入梨园,观古人之贤奸与往事之得失,其喜怒哀乐无不发而中者,则曲虽小道,固亦风俗人心之所寄也。予视学浙江,悦黄生韵珊文而赏之,继览其所制《帝女花》曲,苍郁诡丽,益叹其才之美。爰取《聊斋》所载曾友于事,命作剧本,匝月而词成,情文朴摰(挚),类皆布帛粟菽之谈,元人中与《琵琶》为近,可想见其志性之厚,非徒侧艳为工者。异日谱之管弦,形之歌舞,使普天下孝悌之心油然以生,则感人之捷,虽诗书奚加焉。(《脊令原》序)
在这段话中,陈用光交代了其对戏曲的态度——“曲之感人,捷于诗书”,“曲虽小道,固亦风俗人心之所寄也”。如是,戏曲具有了“大道”的功能,能使“普天下孝悌之心油然以生”,可以更好地发挥教化人心的作用。更交代了其所以命黄燮清作曲的初衷:“览其所制《帝女花》曲,苍郁诡丽,益叹其才之美。”事实上,陈用光显然不仅看到了“其才之美”,更看到了其具有的载道素质,如万立衔为《帝女花》题诗:“阮家固佻达,玉茗终淫佚。讵如《帝女花》,风人丽以则。”(《帝女花》题辞一)不过,从他对《脊令原》的肯定之语,所谓“情文朴摰(挚),类皆布帛粟菽之谈,元人中与《琵琶》为近”,对比有关黄燮清之前创作“苍郁诡丽”特点的评价,以及随后所云之“其志性之厚,非徒侧艳为工者”,已经可以见出其中深意。也就是说,此际“非徒侧艳为工者”的表现,证明了“志性之厚”的黄燮清是可教之才,不会负其所望。陈用光借指定题材改变黄燮清戏曲观念的用意十分清楚,黄燮清也深得要领,不负所望,完成了第一次“形塑”的尝试。
在《鸳鸯镜传奇·序》中,陈用光则直接表达了对“绮丽淫佚之语”的批判,明确指出“虽曰体制类然,亦必合乎风人之旨为佳”。他进一步表示:
黄生韵珊,年少美诗文。出其余技,间作元人乐府,尤工言情,一往而深,渺无边际。予赏其艳而虑其流也,因采《池北偶谈》“碎镜”一则,命为院本。稿竣来谒,览其词,华而不靡,新而不凿,发乎情,止乎礼义,洵足惩创逸志而感发善心者。则是编之作,曲而进于诗矣。吾得以一言蔽之,曰“思无邪”。(《鸳鸯镜》序)
在这里,他明确表达了“予赏其艳而虑其流也”的忧虑,认为“尤工言情”的黄燮清,其文字具有“侧艳为工”的特点,所以又通过一个本具有“艳情”特质的题材进一步考察黄燮清,希望通过《鸳鸯镜》传奇的创作,淬炼其创作观念与个性。黄燮清的努力当然可圈可点,陈用光“华而不靡,新而不凿,发乎情,止乎礼义,洵足惩创逸志而感发善心者”的评价,已经体现了他对这份答卷的高度认可,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而这一认可也是黄燮清完成戏曲创作转型的重要标志。
黄燮清对陈用光的教导不仅心领神会,且以“才”践行之,验证了其“才”并非虚饰。在以后陆续推出的戏曲作品中,尽管也有所谓的言情之作,然皆不出“思无邪”之旨归。如创作于同时期的《凌波影》传奇,本曹植《洛神赋》敷衍而成,极可能演绎成一个香艳色彩浓郁的情爱故事,明代汪道昆(1526—1593年)同题材杂剧《陈思王悲生洛水》已经奠定了这一基调,然黄燮清却设置了一个具有大反转特点的结局——与曹植互诉衷情后,神女恐涉魔障,匆匆离去,而曹植亦敛神定性,尽力把持,觅径而归。这种基于陈其泰所谓“防于未然”(《凌波影》序)的构思,发乎情而止乎礼义,不能说与陈用光“思无邪”的训教无关。陈其泰《序》曰:“《凌波影》乐府之作,其诸风人之风乎?”(《凌波影》序)正是对“风世”核心主题的一种强调。通俗文学作品关注教化问题才能得以进入公共视域,并有利于流传,这是古代很多智慧文人的认知,黄燮清充分理解并践行了这一点。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陈用光为黄燮清戏曲作序时也不自觉地沿袭了明代以来的以诗论曲的模式,有关戏曲的理解和评价皆由诗出发:“词曲,古诗之流亚也。”(《鸳鸯镜》序)优秀戏曲作品的标准自然是符合“风人之旨”的诗的标准:“览其词,华而不靡,新而不凿,发乎情,止乎礼义,洵足惩创逸志而感发善心者。则是编之作,曲而进于诗矣。”凡此,并不稀奇,前辈时贤多有类似论述。值得关注的是其当朝高官的身份与地位,其一切思考皆关乎世教,践行之,并教化黄燮清一类具有“国彦”之才者同心勠力而为。其“惩创逸志而感发善心”的目的,就是通过黄燮清的戏曲创作初步达成的,而黄燮清的心领神会则充分体现了陈用光观念及其责任的完成。如在《鸳鸯镜·跋》中,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积极接受:
《鸳鸯镜》者,吾师陈石士宗伯命(宪清)作也。师视学浙江,(宪清)初以文字受知,进谒时,出所撰《帝女花》乐府质之师。师益击赏,因命构是剧。意盖为维风俗、正人心发也。稿出,师击赏如前,谓好色不淫,合乎诗人之旨,词至此可以风矣。(《鸳鸯镜》跋)
“维风俗、正人心”,是戏曲最为重要的功能。此后,他的戏曲创作专以“合乎诗人之旨”为要,在陈用光去世后也没有中断自我“形塑”的过程。
陈用光曾学诗于蒋士铨,而黄燮清的戏曲创作也明显表现出来自蒋士铨戏曲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时人已有评价。如张泰初评价《帝女花》:“移商换羽,音何促。数文心,前汤后蒋,与君鼎足。”(《帝女花》题辞一)又如《帝女花·香夭》眉批云:“玉茗、苕生,写离魂者数矣,作者直犯其叠,同工异曲,可以并立为三。”(《帝女花》卷下)汤、蒋皆为一时冠冕,以上评价不免虚夸成分,但肯定之意还是存在的。显然,其早期创作更多受到汤显祖的影响。如瞿世瑛《茂陵弦》之《闺颦》眉批:“可与玉茗‘朝飞暮卷’一曲抗行。”(《茂陵弦》卷上)《情猜》之眉批:“描写至此,真绘声绘影之笔,清远道人亦当让一头地。”(《茂陵弦》卷下)许丽京《帝女花·序》云:“哀感顽艳,则玉茗风流。”(《帝女花》序)又《帝女花·散花》眉批:“鼓荡阴阳,纵横奇肆,其才广大,其旨精微,汤临川《冥判》一出,转觉琐杂无谓。”(《帝女花》卷下)后来之创作多得蒋士铨的影响,则成为不断被言说的事实,而这个开始时间的节点正好来自与陈用光的相识。如王易指出:“(黄燮清)专学藏团(园),以《帝女花》《桃溪雪》为胜。”(419)
黄燮清对蒋士铨的接受,颇多模仿的痕迹,甚至创作缘起与时间的表达都有相类之处。如其自述《桃溪雪》创作过程:
残冬短晷,朔风号林,予适病痈,偃卧一室。支离委顿,众缘不交。由定生静,由静生感,意常郁勃,若怦怦有所动,而康甫复寓书相敦促,遂纵笔为之,日成一阕,不一月而稿成。时方严寒,冰雪之气流注纸墨,苍激哀亮,亦不知涕之何从也。(《桃溪雪》自叙)
而蒋士铨在《桂林霜传奇自序》中有类似表述:
长夏病虐,百事俱废。虐止,辄采其事,填词一篇。积两旬,成《桂林霜》院本。酷暑如炽,携枕簟就杂树下,卧而读之。侍疾者愀然而悲,听然而笑。予且不知其故也。(80)
一为寒冬,一为炎夏,同在病中,同样“由静生感”,郁积已久之情感,一泄而就,感发人心于不自觉,是黄燮清以此致敬戏曲前辈的“形塑”行为之一种。最为典型的是题材与主题。如《桃溪雪》传奇,其“凡忠孝义烈之未经表著者,必阐扬其隐,以为世风”(《桃溪雪》自叙),与蒋氏《空谷香传奇自序》中“观感劝惩、翼裨风教”(434)之创作宗旨如出一辙。吴梅总结道:“(《桃溪雪》)其词精警浓丽,意在表扬节烈。盖自藏园标下笔关风化之旨,而作者皆矜慎属稿,无青衿挑达之事,此是清代曲家之长处。韵珊于《收骨》、《吊烈》诸折,刻意摹神,洵为有功世道之作。”(195)《桃溪雪》完成后,因其风教意义确实获得了诸多赞誉。如所附孙恩保《题词》之三:“丝竹中年感慨多,冰池涤笔画霜娥。文章悲喜关风教,此是人间正气歌。”(《桃溪雪》题词)胡凤丹《读〈倚晴楼诗续集〉序》亦云:“吴绛雪者,向熟闻之,然其沈埋于荒烟蔓草间者已百余载,至今以女烈士特传,则韵珊先生之力也。”(《倚晴楼诗续集》115)然文本呈现出的黄不如蒋的特点也十分醒目,尤其是在艺术的营构方面。吴梅认为《帝女花》传奇“惟《佛贬》、《散花》两折,全拾藏园唾余,于是陈烺、徐鄂辈,无不效之,遂成剧场恶套矣”(195)。王季烈亦指出:“其词学清容,而浓纤柔靡,远不及清容矣。”(346)的确,只知道模效蒋士铨的选材、主题乃至风格,未能取得其艺术精髓,于学中求变、学中求新,是黄燮清乃至沈起凤、杨宗岱、瞿颉等戏曲创作难以创新且不能超越蒋士铨戏曲的根本原因。
道光三十年(1850年),身处家乡的黄燮清与同人相聚于倚晴楼,重温《帝女花》传奇,并以长诗表达今昔之感:“少年掷笔喜狡狯,七情簸弄成文章。褒击忠佞参予夺,歌泣儿女悲沧桑。[……]旧词新谱谐笙簧,一唱众和歌绕梁。缠绵恩爱声抑扬,感叹治乱气激昂。[……]嗟我频年游帝乡,欲抱琴瑟登明堂。调燮元化和八方,上与稷契相庚扬。”(《倚晴楼诗集》69—70)其时,尚怀“欲抱琴瑟登明堂”之志的黄燮清依然寄望于戏曲的“上与稷契相庚扬”之力,在“歌泣儿女”“缠绵恩爱”中,特意指出与其如影随形的“褒击忠佞”“感叹治乱”更为切要。此际,后者的分量与影响已然具有超过前者的趋势,这在七年之后完成的《居官鉴》传奇中呈现为更为清晰的撰写目的。是剧乃据晚清王有龄的仕宦经历演绎而成,虽仍不免渗入个人情怀的诸般寄托,却完全从现实关注的视角出之,体现了“曲中之龙门”(《居官鉴》卷下)的历史担当。剧本中,已不再见男女艳情、绮词丽曲丝毫影迹,主人公王文锡的立身行事如剿匪、赈灾、对敌作战、谈判等,皆按照其父所著《居官宝鉴》一书顺序展开,个别关目甚至如写奏议条陈一般,一一列举其具体措施。第二十六出《传鉴》【南尾声】云:“《居官宝鉴》非虚诞,燕翼贻谋启后贤。(待付与)当代龙门,(演成)《循吏传》。”(《居官鉴》卷下)以戏曲的方式塑造一位能吏的形象,注重其在处理种种困难中展现出的治世之才,并非不可,然将艺术文本当成一部传声筒式的《循吏传》构撰,则首先消解了戏曲的审美旨趣,其艺术情境之寡淡也在意料之中。除了其中含蕴的经世之心、治世理想依稀可见“黄燮清”式的表述外,“江郎才尽”的特点与戏曲艺术本质的疏离更为清晰。
黄燮清戏曲作品之于风教的认同和表达,具有顺应时代风尚的意义,这也是其“形塑”成功之所在。晚清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让很多文人看到了戏曲经世济民的功能和价值。如余治(1809—1974年),五赴乡试而不中,由是“专以挽回风俗、救正人心为汲汲”(吴师澄134),“一以化民成俗为主”,“惟以论卑易行为救世之良方”(俞樾,《俞樾全集》第13册448—449,449)。出于此目的,他不仅“用俚语别撰诗歌各种劝世”(吴师澄135),还利用当时盛行的皮黄腔创作了一系列劝善剧。创作于咸丰、同治间的《庶几堂今乐》,延续时间近二十年。余治在《自序》中表达了自己的创作目的:“古乐衰而后梨园教习之典兴,原以传忠孝节义之奇,使人观感激发于不自觉,善以劝,恶以惩,殆与《诗》之美刺、《春秋》之笔削无以异,故君子有取焉。贤士大夫主持风教者,固宜默握其权,时与厘定,以为警瞆觉聋之助,初非徒娱心适志已也。[……]乐章之兴废,实人心风化转移向背之机,亦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也。”(余治69)将戏曲的风教意义提高到与经史相同的地位,且认为其感人于无形的功能又胜于后者。又如俞樾(1821—1907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创作了两部传奇《骊山传》和《梓潼传》(《俞樾全集》第17册489—490),以经学的面貌注入现实关怀的理念,借助戏曲中人物之口,提出了自己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鸦片泛滥、黄河肆虐等重大社会问题的建议,于通经致用的宗旨中融入教育普及与救亡图存的意图,等等。与他们稍有不同的是,黄燮清的作品采用了更为传统的戏曲形式,在承载针砭时弊内容的同时,则少了一些敦厚之风,多了一些伉爽之气。如《绛绡记·探营》云:“我想这些贼寇本是苍生,若非大吏养痈,便是地方激变。先事既无觉察,到得寇势鸱张,惊慌失措。不是杀民代贼,即思掩败为功,说起来好不痛心也呵。”(《聊斋志异戏曲集》428)《居官鉴·愤边》云:“国家养士数百年,难道竟无一人制敌?说起来好不痛愤也呵。”(《居官鉴》卷上)如此犀利的批判现实精神,是蒋士铨戏曲作品中不可能出现的,也是余治、俞樾戏曲作品中难以见到的。“国病难医,那有闲情更及私。搔首皆无济,事急空流涕”(《居官鉴》卷下),这是一代文人忧心国事之心的真切表达,黄燮清没有置身于国事之外,正与其戏曲“形塑”后视野与视点的逐渐改变有关。
晚清时期,忧患丛生,报效无门,潜心问学,伤怀国事,是彼时很多文人迫不得已的生存境况。早于余治、俞樾开始戏曲创作的黄燮清从才子自诩与用世之志开始,转而正面书写经世、治世之志,于其人生、仕途终究裨益甚微。然而他对戏曲抒情写志、教化说理乃至交际应酬、批判现实等功能的实践性拓展,显示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努力,无疑也开启了审视和评价晚清戏曲创作的独特视角。当黄燮清们保持着对传统的文以载道价值观的因循与理解,遵从文体功能与现实情势之所需,拓展戏曲的工具性时,其实也凸显了中国古典戏曲的探索与创新之路。其在艺术层面上的探索如对情节结构、音乐体制、曲词宾白的理解其时已经似是而非,然戏曲以如是方式展示对生活的表达、对时代的理解,对通俗文学地位的提升是有重要意义的;而戏曲功能在晚清时期得以多向度充分展开,也及时提供了社会文化变革之所需,后来梁启超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阿英15),赋予其“改良社会”(阿英315)之巨大功用,实可以从黄燮清这里找到认知与实践之源头。
注释[Notes]
① 关于《居官鉴》创作时间,陆萼庭《黄燮清年谱》注为咸丰四年(1854年)前后(130)。魏明扬、赵山林《论黄燮清传奇〈居官鉴〉的传记色彩》一文,通过对王有龄任职时间进行考证,指出“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断定其创作时间为咸丰六年(1856年)”(123)。
② 《茂陵弦》《帝女花》《脊令原》《鸳鸯镜》《凌波影》《桃溪雪》《居官鉴》合刊为《倚晴楼七种曲》,本文所引《倚晴楼七种曲》,为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影印本。《重刊〈倚晴楼七种曲〉序》说为影印同治四年(1865年)刻本,但据冯肇曾《居官鉴·跋》所署时间,应为光绪七年(1881年)刻本。
③ 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菊人词新警诡丽,独绝一时。其守律之严,尤一字不苟。非惟才大,亦复心细。所著《瓶隐山房词》,予为手定而序之,盖词中之精品也。”(《清词综》第4册518)
④ “倚晴”为黄燮清所建楼名,取黄庭坚《登快阁》诗中“快阁东西倚晚晴”之意,后以之为其诗词、戏曲集名。(《倚晴楼诗集》42)
⑤ 吴镔《〈倚晴楼诗续集〉序》:“岁辛酉,贼陷海盐,倚晴楼毁于火,所镌诗词乐府悉归一炬,穷无复之。”(《倚晴楼诗续集》114)
⑥ 黄际清《帝女花·跋》中云:“岁壬辰,秋闱报罢,益放浪词酒,陈子琴斋将发其郁,以观其才,请传坤兴故事。”(《帝女花》跋)
⑦ 陈用光(1768—1835年),字硕士,嘉庆六年(1801年)进士,道光十三年(1833年)以礼部侍郎兼浙江学政。据《奏报到任日期》《奏为奉谕转补礼部左侍郎谢恩事》《奏报交卸浙江学政篆务日期事》等,道光十三年(1833年)三月初二,礼部右侍郎陈用光,到浙江学政任,七月初八,由礼部右侍郎转补礼部左侍郎。道光十四年(1834年)九月二十五日,交卸浙江学政事宜。(陈用光1025,1028,1033)
⑧ 黄燮清《倚晴楼诗集》卷三有《陈宗伯师(用光)招集定香亭纳凉》《围棋限“局”字,宗伯陈石士师命赋》,可见其参与了陈用光的一些诗歌集会活动。(《倚晴楼诗集》20)
⑨ 吴廷康云:“(张氏)外父砚峰公为文端公族孙,外母姚孺人为端恪公裔孙女、惜抱先生犹女、石甫先生从妹。[……]继文安者(为浙江学政)为新城陈硕士先生,先生本惜翁门下士,又与石甫丈有儿女亲,以康亦与外姻[……]先生既胎息桐城,经学深邃,大江南北讲求实学者闻风远至,康以是益得广交焉。[……]尝与海盐张石匏(开福)、黄韵珊(宪清),萧山陆次山,结诗社于中。”(《玉台秋》茹叟漫述)
⑩ 据关德栋、车锡伦《聊斋志异戏曲集·作家及作品简介》考证,从场次、曲词、说白等来看,“都说明它是一个舞台演出本”,“作者可能是应曹春山或其他昆曲演员之请而作”(7—8)。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Ah Ying, ed.CollectedLiteraryWorksoftheLateQingDynasty:VolumeofStudiesonFictionandDram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
[Cai, Yi, ed.CollectedPrefacesandPostscriptsofClassicalChineseDrama. Jinan: Qilu Press, 1989.]
陈用光:《陈用光诗文集》,许隽超、王晓辉点校,蔡长林校订。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9年。
[Chen, Yongguang.CollectedPoemsandEssaysofChenYongguang. Eds. Xu Junchao, et al. Taipei: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2019.]
杜桂萍:《明清戏曲副文本及其互文性解读——以乾嘉时期徐燨戏曲创作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1月29日第4版。
[Du, Guiping. “The Paratexts of Ming-Qing Drama and Interpretation of Its Intertextuality: A Case Study of Xu Xi’s Dramatic Creation during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ChinaSocialSciencesToday, November 29,2021:4.]
黄燮清:《帝女花》,《倚晴楼七种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
[Huang, Xieqing.TheFlowerPrincess.ACollectionofSevenDramasofYiqingHouse. Hangzhou: Xiling Seal Art Society Publishing House, 2014.]
——:《国朝词综续编》。王昶、黄燮清、丁绍仪:《清词综》第4—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 - -.ContinuedCollectionoftheImperialCi-Poetry. Eds. Wang Chang, et al.AComprehensiveCollectionofCi-PoetryoftheQingDynasty. Vol.4-5.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6.]
——:《脊令原》,《倚晴楼七种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
[- - -.BrothersinPeril.ACollectionofSevenDramasofYiqingHouse. Hangzhou: Xiling Seal Art Society Publishing House, 2014.]
——:《绛绡记》,关德栋、车锡伦编,《聊斋志异戏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01—437。
[- - -.TheCrimsonGauze.CollectedDramasofthe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Eds. Guan Dedong and Che Xilun.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3.401-437.]
——:《居官鉴》,《倚晴楼七种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
[- - -.TheCivilServants’Mirror.ACollectionofSevenDramasofYiqingHouse. Hangzhou: Xiling Seal Art Society Publishing House, 2014.]
——:《凌波影》,《倚晴楼七种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
[- - -.TheWaterNymph’sReflection.ACollectionofSevenDramasofYiqingHouse. Hangzhou: Xiling Seal Art Society Publishing House, 2014.]
——:《茂陵弦》,《倚晴楼七种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
[- - -.StringsofMaoling.ACollectionofSevenDramasofYiqingHouse. Hangzhou: Xiling Seal Art Society Publishing House, 2014.]
——:《桃溪雪》,《倚晴楼七种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
[- - -.SnowofPeachStream.ACollectionofSevenDramasofYiqingHouse. Hangzhou: Xiling Seal Art Society Publishing House, 2014.]
——:《倚晴楼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113。
[- - -.CollectedPoemsofYiqingHouse.CompilationofWritingsfromtheQingDynasty. Vol.619.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0.1-113.]
——:《倚晴楼诗续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14—156。
[- - -.ContinuedCollectionofPoemsofYiqingHouse.CompilationofWritingsfromtheQingDynasty. Vol.619.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0.114-156.]
——:《倚晴楼诗余》,《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57—188。
[- - -.ComplementaryPoemsofYiqingHouse.CompilationofWritingsfromtheQingDynasty. Vol.619.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0.157-188.]
——:《玉台秋》。光绪六年(1880年)琼笏山馆刊本。
[- - -.AutumnoftheJadePalace. Qionghushanguan edition, 1880.]
——:《鸳鸯镜》,《倚晴楼七种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
[- - -.MirroroftheMandarinDucks.ACollectionofSevenDramasofYiqingHouse. Hangzhou: Xiling Seal Art Society Publishing House, 2014.]
蒋士铨:《蒋士铨戏曲集》,周妙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Jiang, Shiquan.CollectedPlaysofJiangShiquan. Ed. Zhou Miaozh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陆萼庭:《黄燮清年谱》,《清代戏曲家丛考》。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117—137。
[Lu, Eting. “Chronicle of Huang Xieqing.”ResearchonDramatistsoftheQingDynasty. Shanghai: Xuelin Press, 1995.117-137.]
马丽敏:《〈玉台秋〉传奇及其副文本的书写与建构》,《社会科学辑刊》5(2022):174—181。
[Ma, Limin. “The Writing and Structuring ofAutumnoftheJadePalaceand Its Paratext.”SocialScienceJournal5(2022):174-18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484。
[Qian, Daxin.CollectedWritingsoftheHallofSubtleResearch.CompilationofWritingsfromtheQingDynasty. Vol.364.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0.1-484.]
沈善宝:《鸿雪楼诗选初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07—377。
[Shen, Shanbao.APreliminaryCollectionofPoemsfromtheHongxueHouse.CompilationofWritingsfromtheQingDynasty. Vol.628.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0.307-377.]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entaries and Explanations to the Thirteen Classics.TheTrueMeaningofZuo’sEditionof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王季烈:《螾庐曲谈》。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
[Wang, Jilie.CommentariesontheQuPoetryofYinlu. Taiyu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王易:《词曲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
[Wang, Yi.HistoryofCiandQuPoetry.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12.]
翁心存:《翁心存日记》,张剑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Weng, Xincun.DiaryofWengXincun. Ed. Zhang J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知止斋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423—654。
[- - -.CollectedPoemsoftheZhizhiStudio.CompilationofWritingsfromtheQingDynasty. Vol.571.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0.423-654.]
魏明扬 赵山林:《论黄燮清传奇〈居官鉴〉的传记色彩》,《古籍研究》2(2005):115—124。
[Wei, Mingyang, and Zhao Shanling. “On the Bi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uang Xieqing’sTheCivilServants’Mirror.”ResearchonChineseAncientBooks2(2005):115-124.]
吴梅:《顾曲麈谈 中国戏曲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Wu, Mei.AConnoisseur’sAppraisalofQuPoetry;AGeneralDiscussionofTraditionalChineseTheatre.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0.]
吴师澄编:《余孝惠先生年谱》,《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30—138。
[Wu, Shicheng, ed. “Chronicle of Yu Xiaohui.”CompilationofWritingsfromtheQingDynasty. Vol.633.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0.130-138.]
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张寅彭选辑,吴忱 杨焄点校,《清诗话三编》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6441—6626。
[Wu, Yangxian.RemarksonthePoetryofLittlePao’an. Eds. Zhang Yinpeng, et al.ThreeAnthologiesofRemarksonQingPoetry. Vol.9.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4.6441-6626.]
俞樾:《俞樾全集》,赵一生主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
[Yu, Yue.TheCompleteWorksofYuYue. Ed. Zhao Yisheng.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7.]
余治:《尊小学斋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53—112。
[Yu, Zhi.RespectfortheLesserLearningStudio’sLiteraryCollection.CompilationofWritingsfromtheQingDynasty. Vol.633.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0.5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