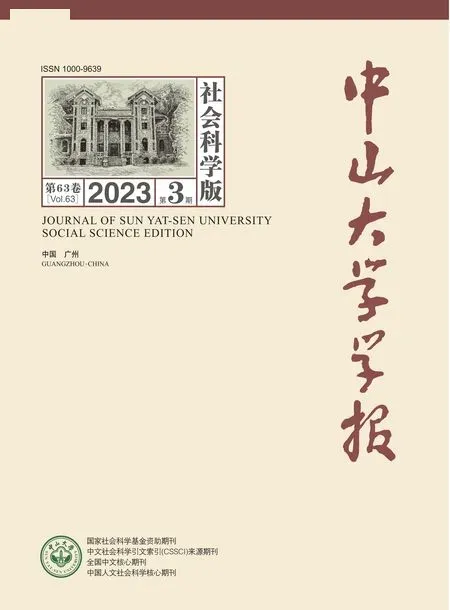赋序文体源流与功能论略 *
——兼论赋序与赋首的差别
张 巍
《文心雕龙·诠赋》对于赋的文体结构有这样的论述:“既履端于唱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①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3,285页。对此,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解释道:“赋以序为首,以乱为终。”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亦云:“言开始既于篇首冠引序,以导叙作赋之缘由;最后又于篇末系乱辞,以总束一篇之指趣也。”②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3,285页。可见一篇赋作结构上可以包括序、正文和篇末乱辞三个组成部分,以张衡《温泉赋并序》为例:
阳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远行,顾望有怀。遂适骊山,观温泉,浴神井,风中峦,壮厥类之独美,思在化之所原,嘉洪泽之普施,乃为赋云:
览中域之珍怪兮,无斯水之神灵,控汤谷于瀛洲兮,濯日月乎中营。荫高山之北延,处幽屏以闲清。于是殊方跋涉,骏奔来臻。士女晔其鳞萃兮,纷杂遝其如烟。
乱曰:天地之德,莫若生兮。帝育蒸人,懿厥成兮。六气淫错,有疾疠兮。温泉汨焉,以流秽兮。蠲除苛慝,服中正兮。熙哉帝载,保性命兮。③张衡著,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16页。
序、正文和篇末乱辞在篇章中各自发挥着不尽相同的文体功能,同时又组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有机体。当然,赋也可以仅有正文而没有序和乱辞,或者只有序和乱辞中的一个,这均视赋家创作时的具体情形而定。赋序和乱辞虽然都是有别于赋作正文的部分,但二者与正文的关系并不相同。乱辞更多的是楚辞体式的遗留,而赋序则原本有着另外的文体渊源,此后才逐渐进入赋中。赋序与赋作正文间的组合,既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也有后人合并而成的意味。对于赋序文体渊源、流变及文体功能的考察,既有助于对于赋自身文体形态的认识,也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古代某些复合型文本建构和生成方式的理解。
一、赋序与赋首的差别
赋序的问题非常复杂,这首先是因为《文选》界定赋序时,与后世的文体观念和做法存在着差异,而且历代不同版本《文选》正文及注释中的标准也不一致,这就很容易造成混乱。试以《文选》赋的最后一类即“情赋”为例,该类赋作收录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曹植《洛神赋》共四篇,每篇赋题下均有“并序”二字,也就是说编选者认为每篇赋都有赋序,但其实所谓曹植赋之序与宋玉赋之序存在着根本性差别。为了准确说明这一点,节录两篇赋作如下。先看《神女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中从略)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中从略)惆怅垂涕,求之至曙。”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886—889,896—901 页。“夫何神女之姣丽兮”等内容的引号为笔者所加。
再看《洛神赋》: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辞曰:
余从京域言归东藩。(中从略)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
《洛神赋》的赋序为全文首段,也即“其辞曰”以上的部分,与正文的界限清楚明白。而在《神女赋》中却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赋序,因此只能认为题名者将篇首宋玉与楚襄王的这段对话视为赋序。但事实上《洛神赋》是“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而作,也即借鉴了《神女赋》的写法,二者在篇章结构方面具有相似性。宋玉与襄王的这段对话,和《洛神赋》中曹植与御者的问答之辞相同,完全是赋作的正文,而不是该赋的序言。而且,从“夫何神女之姣丽兮”起到全文结束,也都属于宋玉的叙说,相当于《洛神赋》中“余告之曰”以下的内容。在现今的古籍标点中,应该加上引号③节录同书标点后的《西都赋》如下:“宾曰:‘唯唯。’‘汉之西都,在于雍州……’”(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5页)前引《神女赋》亦应参照此例。,这样读者更不会误认为前面的部分为赋序。
对于《神女赋》序的问题,历史上曾经有过激烈争论。宋代苏轼《书〈文选〉后》云:“宋玉《高唐》《神女赋》,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赋,而统谓之序,大可笑。相如赋首有子虚、乌有、亡是三人论难,岂亦序耶?”④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95,1429页。其《答刘沔都曹书》亦云:“宋玉赋《高唐》《神女》,其初略陈所梦之因,如子虚、亡是公等相与问答,皆赋矣。”⑤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95,1429页。对于苏轼的观点,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反驳道:“是未悉古人之体制也。刘彦和云:‘既履端于唱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则是一篇之中引端曰序,归余曰乱,犹人身中之耳目手足各异其名。苏子则曰莫非身也,是大可笑。”⑥何焯:《义门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82页。何焯的驳斥并没有说服力,因为《文选》认为某赋有序的话,会在题下明确标注“有序”二字,但《子虚赋》和《上林赋》的赋题下均未标注“有序”的字样,可见《文选》的编者或注者也并不认为这就是赋序。其实,南宋王观国《学林》中早已对这一问题有着清楚的论析:
傅武仲《舞赋》,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本皆无序。梁昭明太子编《文选》,各析其赋首一段为序。此四赋皆托楚襄王答问之语,盖借意也,故皆有“唯唯”之文。昭明误认“唯唯”之文为赋序,遂析其辞。①王观国:《学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20页。标点为笔者重新所加。
对此,清代浦铣《复小斋赋话》亦曰:“《登徒子好色赋》自‘大夫曰唯唯’以前皆赋也……昭明乃谓为序,真堪喷饭。”②浦铣著,何新文、路成文校证:《历代赋话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03页。章学诚《文史通义》中说得更为简明扼要:“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犹其显然者也。”③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1,87页。
《文选》编集中这种特殊的处理方式,经过《文选注》的解释阐发后,越发显得令人费解,这在其所收录的“七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文选》“七”体中收作品三首,依次题名为“枚叔《七发》八首、曹子建《七启》八首并序、张景阳《七命》八首”,其中只有曹植的《七启》有序,其序云:“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④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576页。这是非常典型的序言写法,有序和无序的区分原本很清楚。但《七发》题下李善注云:“《七发》者,说七事以启发太子也,犹楚辞《七谏》之流……八首者,第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谏,不欲犯其颜,末一首始陈正道。”⑤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634 页。中华书局1977 年影胡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排印本《文选》李善注中均无“八首者,第一首是序”以下诸句。的确,如果非得要承认《七发》确是“八首”的话,恐怕也只能这样解释,将它看作《七谏》一类的组诗。但这与后世的文体观念严重不合,而且还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依此解说,曹植的《七启》岂不是有两个序?
为了彻底清除这一认识混乱,必须对赋的体制进行深入分析。众所周知,主客问答是赋的传统写法,汉代骋辞大赋尤为如此。祝尧《古赋辨体》评论《子虚赋》《上林赋》时指出:“赋之问答体,其原自《卜居》《渔父》篇来,厥后宋玉辈述之,至汉此体遂盛。此两赋及《两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⑥王冠辑:《赋话广聚》第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52—153页。围绕主客问答的展开,全赋自然地形成了“客人发难—主人释答—客人折服”三个部分。与之相适应,为了突出“主人释答”的主体地位,全赋也就采用了“散文—韵文—散文”的结构模式。这三个部分,可以分别称之为赋首、赋中、赋尾。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指出“《子虚》《上林》《两都》等作,则首尾是文”⑦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02页。,就已经清楚认识到此类骋辞大赋分为三个部分,而且这三部分之间还存在着散语与韵语的差别。
仔细考察赋的文体缘起,可以对赋的篇章结构有更明晰的认识。赋“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⑧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1,87页。,其文体起源具有多元性,但和它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是楚辞和战国纵横家辞。楚辞可谓赋的直接源头,历代评论中往往辞赋并称。刘勰《文心雕龙》中就指出:“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⑨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274页。清代程廷祚《骚赋论》更是明确指出“《骚》之体流而成赋”⑩王冠辑:《赋话广聚》第3册,第774页。。而在楚辞《卜居》当中,就早已体现出明显的三段体结构。如其首段云: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鄣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曰:“君将何以教之?”
中间部分说:
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中从略)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
结尾如下:
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事。”①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83—186页。
这三段当中,中间一段用韵极密,并极尽铺陈之事,显然是高潮所在;首尾则用韵较疏,仅是简单记叙,分别起着铺垫和补足的作用。这些均和汉赋如出一辙。
战国纵横家辞是赋体的另一重要源头。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云:“纵横者,赋之本。”②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页。刘师培《论文杂记》亦云:“欲考诗赋之流别者,盍溯源于纵横家哉!”③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 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29页。纵横家辞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例如《战国策》中《庄辛谓楚襄王》一章,姚鼐《古文辞类纂》收入“辞赋类”中,足以说明它与赋体相近。《庄辛谓楚襄王》同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襄王不用庄辛之言,致使楚国战败;第二部分为庄辛的对辞;第三部分写楚王深为庄辛言辞所触动。
上述楚辞和纵横家辞,都和汉代骋辞大赋的结构相同。以扬雄《长杨赋》为例④《长杨赋序》的问题详见下文论述。,其赋首部分为:
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曰:“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沾而恩洽,动不为身。(中从略)”
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谓之兹耶!若客,所谓知其一未睹其二,见其外不识其内也。仆尝倦谈,不能一二其详,请略举其凡,而客自览其切焉。”
客曰:“唯,唯。”
其赋中部分为:
建议一个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阅读的课外书最低应该在500本之上,最好在1000本以上。其中包括100本以上各行各业的人物传记,来奠定孩子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基础。同时注意不但要阅读,也要写读书笔记或者书评。
主人曰:“昔有强秦,封豕其土。(中从略)”
其赋尾部分如下:
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体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发矇,廓然已昭矣!”⑤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404—411页。
这种高度的一致性充分表明,汉赋“以虚拟人物对话的散体起问、以韵文答问和以散体作结的三段形式结构”源于先秦篇章⑥萧驰:《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31页。。对于赋体而言,赋首、赋中、赋尾这种三段体结构可谓与生俱来。赋序只可能有另外的文体源头,赋序与赋首二者也绝不能被等同看待。
虽然赋中的这种创作程式相对固定,不过具体形态方面也可能发生改变。例如前引《神女赋》和《洛神赋》,就只有赋首和赋中部分,略去了赋尾,而且赋首也采用韵语。这种情况下,赋首就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赋序,但事实并非如此。王芑孙《读赋卮言》指出:
古赋自为散起之例,非真序也。《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篇,李善、五臣皆题作序;汉傅武仲《舞赋》引宋玉高唐之事发端,善亦题为序,其实皆非也。高唐之事,羌非故实,乃由自造,此为赋之发端。汉人假事喻情,设为宾主之法,实得宗于此。⑦何沛雄编著:《赋话六种》(增订本),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第16页。
可见,《六臣注文选》所载李善注中对于“《七发》八首”的解释以及何焯对于刘勰的误读,都是因为混淆了赋首和赋序的区别。其实今天看来,这二者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赋首出现在主客问答赋中,所涉及的人物多出于假托,虚拟的色彩非常浓厚,与后世戏曲中的发端部分有些相像;而赋序通常采用第一人称口吻⑧这里所说的是严格意义上的赋序,也即文人“自作”之序,详见下文。,属于作者的自我陈述,表达作者的真实情思,具备纪实性。赋序是与赋作正文相对的副文本,而赋首是赋作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自作之序与他作之序的差别
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鵩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鵩似鸮,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②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604页。《文选》中的这段记载出自《汉书》。
汉代文章许多都是因为被收入《史记》《汉书》等才得以流传保存。史家们将文章作为相关史料收入传记当中,从客观效果上来看,史书也起到了某种类似总集的功用。最先收录《鵩鸟赋》的正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还在赋前撰写了一段叙述性文字:
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③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96页。
可以看出,这段文字既是司马迁对于贾谊谪居长沙时相关状况的记述,也是对《鵩鸟赋》写作背景的说明。从行文的角度来看,它起着将传主著述与史家叙述串联起来的作用,使这二者之间的语势、语意更为贯通,使传主生前所作的文字成为他本人传记的有机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汉书》在内容上对《史记》有承袭关系。《汉书·贾谊传》抄录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对于司马迁所作的赋前这段叙述文字,班固又有意识地加以改写。比较而言,《史记》中的相关文字略显古奥奇峭,《汉书》则更为平易畅达。《文选》收录《鵩鸟赋》时参照《汉书》,《汉书》中的这段记述仍被置于赋作正文之前,全赋也被题名为《鵩鸟赋并序》。在后人看来,它自然就是作者为赋所写的序文,但其实原本并非如此。
《史记》《汉书》所采用的这种“以赋入史,以史存赋”的做法,也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编撰的其他史书所沿袭。这些史书中收录的有些赋作原本就有序,但为使赋作与赋家传记融为一体,前后连贯,依然还是需要有简短说明。将此类文字与《史记》《汉书》中的相关内容对读,就可以对“他作”之序的性质有更加清楚的认识。例如《宋书·傅亮传》中有这样的记述:
亮布衣儒生,侥幸际会,既居宰辅,兼总重权,少帝失德,内怀忧惧,作《感物赋》以寄意焉。其辞曰:
余以暮秋之月,述职内禁,夜清务隙,游目艺苑……怅然有怀,感物兴思,遂赋之云尔。
在西成之暮晷,肃皇命于禁中。聆蜻蛚于前庑,鉴朗月于房栊……岂知反之徒尔,喟投翰以增情。④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39—1340页。
显而易见,傅亮《感物赋》正文之前为赋序,赋序之前的段落为沈约所写,相当于《史记》《汉书》中《鵩鸟赋》之前的那段文字。
先唐时期,载录《鵩鸟赋》全文的传世文献仅《史记》《汉书》《文选》三种,当《文选》的编选者将《汉书》中的相关文辞节录为序后,《鵩鸟赋》就获得了新的形态。可见重要的选本不仅影响作品经典化的进程,有时甚至直接决定作品本身的面貌。《鵩鸟赋并序》其实是个复合文本,赋作正文和序文分别出自于贾谊和班固的笔下,班固所作文字又是对司马迁相应文辞的改写。而《鵩鸟赋》本身,也经历了独立存在、被收入《史记》《汉书》中并有了相关解说文字、被收入《文选》得到题名并明确标示有序这样三种不同的形态。当它最先独立存在时,当然明确属于贾谊个人的创作;收入《史记》《汉书》中之后,它的作者虽然没有改变,但其本身则变成了《史记》《汉书》的一个组成部分(片断);收入《文选》中,它又成为《文选》的一篇,作者题名依然是贾谊,但依照现代创作权的标准衡量,贾谊、司马迁、班固三人对文字均有贡献,最后又经历了萧统等人的编排,被归入《文选》赋“鸟兽”类当中。
继贾谊之后,赋作存序的西汉赋家还有司马相如和扬雄,其赋序的情形也与贾谊相似。《文选》所收司马相如《美人赋》真伪尚有争议,在此暂不讨论。其《大人赋》序云:“相如拜为孝文园令,见上好仙,乃遂奏《大人赋》。其辞曰……”①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44,535页。此段赋序最早见于《艺文类聚》,明显节录自《史记》。《文选》为类集,《艺文类聚》为类书,它也起到与《文选》相似的功用。
扬雄今存赋九篇②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扬雄《反离骚》为楚辞,不计入内。,《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酒赋》五篇有序。其中,《酒赋》在《汉书·陈遵传》中作《酒箴》,《太平御览》引《汉书》则题作《酒赋》,“所谓《酒赋序》,乃窜易《汉书·陈遵传》之文而成,固非子云之手笔”③扬雄著,郑文笺注:《扬雄文集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304页。。《甘泉赋》等四篇赋序均出于《汉书·扬雄传》,而《汉书·扬雄传》其实基于扬雄《自序》一文,类似于《汉书·司马迁传》取材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扬雄传赞》云“雄之自序云尔”④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83,2724页。,《汉书·司马迁传》中也有“迁之自叙云尔”的说法⑤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83,2724页。。不过,虽然可以视为出于扬雄笔下,但毕竟不是他专门为赋所作的序。这些文字片断能够成为赋序,依然要归因于后人的摘录。王观国《学林》中说:“扬子云《羽猎赋》首有二序,五臣注《文选》曰:‘赋有两序,一者史臣,一者雄序。’详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赋也。”⑥王观国:《学林》,第220页。其实,所谓的“第一序”可以说是扬雄文《自序》的片断而非其所作之赋序,“第二序”则是赋首。
可以说整个西汉的前期和中期,赋家们并没有给赋写序的习惯。王芑孙《读赋卮言》中明确指出:“西汉赋亦未尝有序。《文选》录……西汉赋七篇中间,有序者五篇:《甘泉》《长门》《羽猎》《长杨》《鵩鸟》,其题作序者,皆后人加之。故即录史传以著其所由作,非序也。”⑦何沛雄编著:《赋话六种》(增订本),第16页。但由于相传已久,现在人们已习惯于将这些也看成赋序。
真正意义上的赋序也即自作之赋序迟至西汉后期才出现,现存最早真正的赋序可能是桓谭所作的《仙赋序》:
余少时为郎,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部先置华阴集灵宫。宫在华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怀集仙者王乔、赤松子,故名殿为“存仙”。端门南向山,署曰“望仙门”。余居此焉,窃有乐高眇之志,即书壁为小赋,以颂美曰……⑧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44,535页。
此类赋序以作者自叙的口吻写成,与《鵩鸟赋序》等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有根本性的不同。序中交待了作者相关经历与作赋缘由,序末有提引起下文的“以颂美曰”等字样,这种写法为后世赋序广泛承袭。
班固的《两都赋序》也被看作是较早的赋序,但事实上它原本约略相当于进赋之章表奏议,例如杜甫《进雕赋表》一类。节录该序如下:
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词曰……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3—4页。
其中“臣窃见”“臣作”等字样,充分表明这是献赋时写的说明文字。对此,试与东汉杜笃献《论都赋》时的上奏之辞相比较:
臣闻知而复知,是为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陈……臣不敢有所据,窃见司马相如、扬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谨并封奏如左……②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626,1222—1223页。
更为明显的,是三国曹魏卞兰所作的《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览照幽微,才不世出……小臣区区,嘉乐无已。窃怡绵绵之属,忘愚戆之言,谨触冒上赋一篇,以摅狂狷之思。”③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626,1222—1223页。由此也可以看出,即令是作者自己所写,赋序也往往并非是赋的必然组成部分,而可能是由于某些外在原因与赋归并为一体。
赋序与赋作正文之间实质上是一种文体组合关系。文体组合意味着两种文体可以通过组合的方式生成新的文体,或者强化原有文体的功能。赋作正文需要赋序,说到底是韵文借散文对自己文体功能予以补足。韵文的本质就是通过音乐美来增强抒情性,但这会对叙事带来某种限制。在韵文之前加一段富有阐说意义的散文来交代背景,既是对叙事的补足,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起到充分铺垫以加强抒情性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韵文有序是一种文体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韵文之序也基本都是散文(无韵之文)④蔡邕《短人赋序》采用四言韵语,是极为罕见的特例。。
无论是对于赋家(作者)还是读赋之人(读者),赋序的出现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赋作正文的附属,赋序交待创作缘起,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在读赋之人与赋作正文间起到中介作用,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与此同时,它也表明赋家创作时已有一定的读者意识,考虑到读者接受的问题,预设了阅读对象的存在。
赋序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以后赋叙事性减弱而抒情性增强、集体话语色彩减弱而个人话语意味增强的创作倾向。究其本源,“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⑤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270页。。“铺陈其事”大致相当于铺叙,可以说是赋的基本手法。从汉赋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骋辞大赋产生在前,叙事性虽强但真实性反而弱,因为它着力追求文字的渲染效果,存在着不少虚构的成分。抒情小赋出现在后,抒情性和真实性都有所增强,因为它反映的是作家切实的人生感受,具备强烈的个体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加需要有赋序来说明创作缘由。例如桓谭《仙赋》虽然记叙的是神仙之事,但反映的却是作者求仙的热切向往,所谓“窃有乐高眇之志”,赋序中正好揭示了这一点。
三、赋序的文体渊源
在严格意义上的赋序也即“自作”之序问世之前,序这种文体就已经产生。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尔雅》云:‘序,绪也。’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六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⑥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第42页。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又将其细分为“大序”和“小序”两种文体:
按《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又谓之大序,则对小序而言也。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
按小序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对大序而名之也。汉班固云:“孔子纂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所意,此小序之所由始也。”然今《书序》具存,决非孔子所作……独司马迁以下诸儒,著书自为之序,然后己意瞭然而无误耳。①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第135—136页。
徐师曾对于“大序”和“小序”的区分较为模糊,按现今的观点看来,序大体可以分为书册之序和篇章之序两大类,这两类序有各自的文体渊源,其间又有交叉关系。
书册之序以《吕氏春秋·序意》篇为最早,其功能在于介绍作者身世,陈述创作缘由,解说篇章结构。先秦部分子书的最后一篇往往具有某种总结性的意味,例如《庄子·天下》《荀子·尧问》(后来的《淮南子·要略》也是同样性质),这可以视为书册之序的前身,但毕竟不够明晰且并未明确地称之为“序”。而《吕氏春秋·序意》既能总结全书交待体例和缘由,又称作“序意”,则是较为规范的书册之序。
篇章之序相传以《诗序》和《书序》为最早。《诗序》的作者今天还有争议,但肯定产生于赋序之前。《诗》的小序大多都是对于诗作意旨的阐释诠解,代表的是解诗者的审美判断与价值取向,例如《周南·葛覃》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②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8,344页。这类诗序本质上其实是诗传,讲述的是用诗之旨而非作诗之意,试将《诗序》与《韩诗外传》加以比较,就可充分明了这一点。但也有部分小序交代创作背景及写作缘由,这就和后世赋序的写法很相似。此类《诗序》中,《王风·黍离》序颇具典型意义:“《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③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8,344页。
《尚书》每篇或数篇之前也有一简短小序,是为《书序》,相传为孔子所作,在汉武帝之前就已问世。《尚书序》中指出《书序》功用所在:“《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④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6,187页。与《诗序》相比,《书序》基本都是交代史实和记述撰写背景,纪事意味强烈,例如《洪范》序中有这样的记载:“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⑤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6,187页。
《诗序》《书序》都是后人所作,而《史记》中的序和全书主体部分一样,都出于同一位作者笔下。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史记》中的序文与汉代赋序可能更为接近。
仔细区分的话,《史记》中的序也包括全书之序即《太史公自序》和篇章之序如《六国年表序》等两大类。《太史公自序》位于《史记》全书之末,为“列传”的最后一篇。吕思勉《史通评》指出:“书之有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一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⑥吕思勉:《史学四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9页。《太史公自序》也是首先交待撰述的起因,然后对《史记》中的每一篇予以简短总括,可以说其实兼有篇章之序的意味,只是篇章之序并未放在每篇之前,而是总括于全书之后。整篇序文,“概括作书之本旨,分标诸篇小序,凡一切纲领体例,莫不于是灿然明白”⑦牛运震:《史记评注》卷12,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47页。。当然这两个方面也有主次之分,《太史公自序》中最为精彩之处还是司马迁对于自己继承父志、发愤著书这一著述缘由的交待。
《史记》十表都是表格,但多个表格前面都有一段解释说明性的文字,这也被后人称作序。这类序作既叙述相关内容,交待写作原因,也包含了作者的深沉感喟。如《六国年表序》末段云:“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①司马迁:《史记》,第687,878页。《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末段亦有云:“于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②司马迁:《史记》,第687,878页。这类序作也可以被视为篇章之序,而且确定出于作者自己的手笔。
书册之序和篇章之序的区别在后世看来非常明显,但在汉魏六朝这样的写本时代,作品很多情况下都是以单篇形式流传的,而且骋辞大赋的篇幅本身就很长,就好像是可以独立成书的著作一样。左思《三都赋》令洛阳纸贵,皇甫谧为之再作序,张载、刘逵分别注《魏都赋》和《蜀都赋》《吴都赋》,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庾信《哀江南赋序》也讲道:“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③庾信著,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4页。显然是将《哀江南赋序》视为桓谭、杜预著作之序文的同类作品。由此可以推知汉代赋序虽然是篇章之序,但其实也具备了书册之序的意味。书册之序和篇章之序,对于赋序的产生都有启示和影响。
赋序虽不同于《太史公自序》一类的序文,但在自叙写作缘起方面却有共通之处。它和《六国年表序》等置于表格之前的说明文字也有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体式互补关系,只是将“散文+表格”改换成“散文+韵文”。真正意义上的赋序也不同于《诗序》,它是作者所记而非他人追述,但二者都列于篇章之前,以简短概要之散文叙说交待韵文创作相关事宜,在形式上颇为相似。赋序的产生可以说是对此前序文综合会通之后的创造,它是中国文学史上韵文自序的开端。
韵文自序最早正式出现于赋这种文体,要归因于汉赋在当时崇高的文体地位。众所周知,赋在汉代被视为最重要的文学形式,是润色鸿业的经世之文。后世“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的文学观念④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92页。,历代文集中沿用的“首赋”体例,都与此有关。也正是因为如此,汉代文人才会觉得有必要写序对赋加以郑重其事的交代。
作为最早产生的韵文自序,赋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其他种类韵文的序作。如前所述,楚辞可谓赋的直接源头,但屈宋之作均没有序,后世楚辞有序则是仿照赋序的写法。不但产生的时代要晚,而且在数量上也很少见,可以说仅是偶一为之。究其原因,楚辞重在抒发迷离彷徨之忧思,难以交代具体创作之缘由,故作序的必要性不强。汉魏六朝楚辞有序者仅寥寥数篇,如陆云《九愍序》:“昔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而表意焉,遂厕作者之末,而述《九愍》。”⑤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036页。江淹《遂古篇序》:“仆尝为《造化篇》,以学古制今。触类而广之,复有此文,兼象《天问》,以游思云尔。”⑥江淹著,胡之骥注:《江文通集汇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3页。交代的也都是己作与前代楚辞的仿效关系。可以说,赋的产生在楚辞之后,而且是受到了楚辞的巨大影响,但楚辞有序却是反过来受到赋序的触发,这确实是非常有趣的文体现象。其实,不仅是楚辞,诗、箴、铭、诔、赞、颂等韵文文体有序,其渊源也大都可以追溯到赋序。例如夏侯湛《东方朔画赞序》最后说道:“仆自京都言归定省,睹先生之县邑,想先生之高风;徘徊路寝,见先生之遗像;逍遥城郭,观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怀,乃作颂焉。其辞曰……”⑦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119页。就和赋序的写法如出一辙。
深入了解赋序的文体缘起之后,对于“自作”之序和“他作”之序的关系可能会有更清楚的认识。虽然“他作”之序的文字产生于前,但只有赋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明确树立起了自己的文体地位后,《文选》的编选者们才会以这种文体视角去看待《汉书》中的相关片断,并且将它们认定为赋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而是“自作”之序推动了“他作”之序的出现。
四、赋序在后世的新变及其文学批评功能
后世的赋序中,很多始终保留着汉代“自作”之序的原始面貌,没有太大变化。例如唐代韩愈《复志赋序》:“愈既从陇西公平汴州,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退休于居,作《复志赋》。其辞曰……”①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6页。全序仅用六个短句交代时、地、人、事等基本情况,文辞凝练,正是传统赋序的写法。但从六朝起,也有部分赋序呈现出了新的创作倾向,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篇幅加长,不像原来仅是寥寥数句。汉代赋序大都较为简短,班固《两都赋序》文字较多,但如前所述,那是因为它原本相当于进赋之奏表。建安时期的赋序依然普遍短小,曹植现存赋序十五篇都是短章②据《曹植集校注》统计。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从晋代起,有的赋序就写得很长,后来出现了《哀江南赋序》这样的巨制。纵观中国赋史,赋序可以依照论述详略或篇幅长短分为详序和略序,或称长序和短序。长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短序的消歇,二者始终是长期并存的关系。例如南朝文士很多都好作长序,但江淹就偏好短序,其《丹砂可学赋序》如下:“咸曰金不可铸,仆不信也。试为此辞,精思云尔。”③江淹著,胡之骥注:《江文通集汇注》,第46页。全序仅不过十八个字。赋序加长的途径,主要是用铺陈手法予以反复刻画,极力渲染。铺陈本来就是赋的重要特征,赋序也采用铺陈手法,使其与赋的面貌愈发接近。
其二,采用骈体或是具有骈化倾向的散体。赋从产生之日起就比散文更多用到对句,后来受骈文影响产生了通篇对仗的骈赋,古体赋对仗化程度往往也很高。采用骈体或骈化散体之序,赋序与正文自然会更为和谐一致,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不过,骈赋的序可以是骈体也可以是散体,但古赋的序却肯定是散体,不太可能出现古赋的序反而是骈体的情形,那样会显得极不协调。
其三,赋序的末尾不采用“其辞曰”“其赋曰”这样的提示性语句,而是语意完足的句子。如孙绰《游天台山赋序》末尾曰:“方解缨络,永托兹岭。不任吟想之至,聊奋藻以散怀。”④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494页。庾信《哀江南赋序》结句云:“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⑤庾信著,倪璠注:《庾子山集注》,第101页。
其四,在保留交待赋作创作缘由也即叙事功能的同时,抒情意味或议论说理色彩加强。
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正是由于赋序具备了独立的审美与抒情功能,所以需要更大的篇幅来展示,因此也就更像是一篇首尾自足的文章。例如陆机《豪士赋序》简直就是关于“豪士”的一篇专论,分析透彻,字数颇多。在这种情况下,赋序与赋作正文其实是针对同一意旨用无韵之文和韵文分别叙写。二者文体虽有别,意思却相近。清代赋选《律赋必以集》评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曰:“《文选》中之有序者,仅明作赋之旨,不事铺张。此篇写马射处,序与赋略同,不过词句变换。”⑥顾莼编:《律赋必以集》,广州:广州菊坡精舍,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所论极是。赋序与赋作正文之间主次关系不明显,倒像是并列阐述或者说相互改写。赋序的作用不再是预先提示或补充交待,而是复述与强化。赋显才学,长篇赋序同样也可彰显才学,因而带有某种炫技逞博的意味。
新赋体的出现也会给赋序创作带来新的变化。赋序在不同赋体的赋作中分布极不均衡,主要见于古体赋和骈赋,在唐代新兴的律赋中就比较少见。律赋在唐代既应用于科举应试,也见于文人私下所作,但这两种情形下都只是个别律赋有序。应试律赋有序,是出于科举考试题目的限定。例如唐开元二十五年(737)试赋题为《花萼楼赋》(以“花萼楼赋一首并序”为韵),礼部侍郎姚奕知贡举,此年进士及第者有邵轸等二十七人,《文苑英华》现存高盖等所作五首。高盖《花萼楼赋序》即云:“以待问于有司,有司盛称兹楼,并命赋之。”①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220,605页。除了这五篇赋作外,《文苑英华》中还有《舞马赋》(并序,以“奏之天庭”为韵)二首②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220,605页。。虽然现存这两组同题赋作中都仅是第一首有序,但那明显是经过编选者的删削,原本应该每篇赋都有序。考场之上时间紧张,而且律赋有序属于特例,如果没有主司的要求,举子们肯定不会特意为之作序,否则纯粹是费力不讨好。反之,如果主司命作而不作的话,那也是属于不合要求。唐代文人私下所作律赋有序者如李咸的《田获三狐赋》,该赋的赋题、题下限韵之字和赋序重复性很强,都是对赋作正文内容的概括与说明。
从后世研究者的角度看来,赋序具备文学批评功能,或者说它本身就是赋学批评的重要形式。赋序这种形式有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它是作者实施的自我批评,批评包含于创作当中,也可以说是具有批评意味的创作;另一方面,批评文字与所批评对象(赋作正文)之间是共生一体的关系。因此将赋序与赋作正文对读,颇有助于将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相互印证。赋序中的文学批评意味表现在以下多个方面。
其一,赋家在赋序中经常会列举前代同类之作,将自己的赋作置于某个作品序列当中,有时还会对它们进行比较,在推源溯流中寻求自我定位。具体来看,这或者是为了说明自己属于补阙之作,如马融《长笛赋序》云:“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赋》。” 或者为了表现己作渊源有自,继美前人,如陶渊明《闲情赋序》云:“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③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53页。或者是为了肯定自己的赋作比前代更胜一筹,如嵇康《琴赋序》曰:“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丽则丽矣,然未尽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声,览其旨趣,亦未达礼乐之情也。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故缀叙所怀,以为之赋。”④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836,1页。
某些赋序罗列前人篇名后会对赋家、赋作等再加以详细评述,类似于一篇专门性的赋学批评文章,陆机《遂志赋序》在这方面就极为突出:
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简而有情,《显志》壮而泛滥,《哀系》俗而时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练而和惠,欲丽前人,而优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虚温敏,雅人之属也。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岂亦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余备托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⑤陆机著,杨明校笺:《陆机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7页。
虽然陆机这篇赋序的写作目的也是为了表明自己“备托作者之末”,但真正吸引读者的,还是他对于《显志赋》等系列赋作的精彩点评。除却结句之外,前面的部分看起来简直就像是《文心雕龙》中的一段,也像是《文赋》相关理论观点的具体化。
赋序的这种特性,为赋集的编撰提供了便利。在中国古代诸文体中,赋体文学创作的沿袭性和题材的类似性、趋同性非常突出,赋集也适合于依照题材分类进行“类编”。《历代赋汇》这样的大型赋集采用类编体例,总体看来依然稳妥,而《唐诗类苑》和类编本《草堂诗余》就明显给人一种削足适履之感,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赋序中早已对作品归类有所交代。
其二,为了配合创作的需要,赋序中还经常提出或阐发一些赋学理论,甚至包括某些赋学基本命题。例如“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提法⑥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836,1页。,就首见于班固的《两都赋序》,李白《大猎赋序》中也将“辞欲壮丽,义归博远”看成是赋的重要特征⑦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7页。。
其三,赋序展现作家创作心态时,往往会强调该赋是受到自然环境或社会生活的触动后有感而作,充分肯定文学作品表达情志、抒情写意的功用,这与《文心雕龙·物色》《诗品序》《文赋》中的诸多论述都有相通之处,如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序》:“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①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第145页。崔湜《野燎赋序》:“仆时负谴,触物多兴。援毫斐然,岂近声律。”②李昉等编:《文苑英华》,第559,445页。
其四,某些赋序记录、评述了赋家之间赠答唱和、同题共作等辞赋创作行为,保存了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赋史资料。在魏晋时期,共同作赋成为文学交往的重要手段和文学群体内部联系的纽带,这在赋序中得到了记述和交代,如曹丕《玛瑙勒赋序》曰:“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命陈琳、王粲并作。”③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075页。陈琳同题赋序亦曰:“五官将得马脑以为宝勒,美其英䌽之光艳也,使琳赋之。”④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5页。时至唐代,文坛依然延续着这种风习,如魏归仁《宴居赋序》记录了朋友间作赋唱和的情况,其序曰:“张校书作《虚室赋》以示予,文旨清峻,玄义深远。予味之有感,聊为《宴居赋》以和之。”⑤李昉等编:《文苑英华》,第559,445页。序中表明拜读友人的佳作,才是他作赋的动因。
赋可以有序也可以无序,序可长也可短,这本无一定,完全取决于赋家的创作意愿。对于有序之赋而言,赋序问世后就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它与赋作正文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但在历代总集当中,赋序与赋作正文有时会被人为地割裂分开。一种情况是某些赋序因为艺术水准极高,单独被采录入选本,从而脱离原赋成为一个独立文本。例如《文选》和后世《骈体文钞》的“序”类当中,都收录了陆机的《豪士赋序》,以至于《豪士赋序》完整传世,赋作正文反而散佚不全。再如庾信《哀江南赋序》历来被视为六朝骈文的典范之作,并被《文章辨体汇选》等总集所收录。金圣叹《才子古文读本》中也选录了潘岳《闲居赋序》和嵇康《琴赋序》并加评点,《琴赋序》总评曰:“赋特是琴,序乃不止是琴。不止是琴,而又特赋琴。此始为深于琴理者也。细看其涉笔浅深,悉具狂简之态。”⑥金圣叹评点:《金圣叹批才子古文读本》下册,上海: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第17页。同样是将其作为一篇相对独立的作品来看待。另一种情况是省略赋序而仅是抄录赋作正文,当然题目就只能是“某某赋”了。这往往是赋序较为简单,即使略去对理解下文也没有太大影响。例如清代嘉庆年间编选的唐赋选本《唐人赋钞》中,许多唐赋就略去了原序。不过,略去的赋序又时常会被注家采纳入注释中,这样的话虽然文字内容不变,但就该选本而言,相关文字的性质已由赋序转变成为注释中的引文。
除了上述两种情形外,长篇的赋序也可能被删减后节录。清代余丙照《赋学指南》收录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并序》,题下注曰:“间从《赋苑》节略本。”⑦王冠辑:《赋话广聚》第5册,第399页。所收赋序从“于是玄鸟司历”到“景福之欢欣者也”,其实仅是原序的中间部分。
赋序和赋题均是与赋作正文相对的副文本,它们二者间的关系也颇为复杂。有序之赋反映在赋题上,表现为“某某赋并序”的字样。但在某些文献载录中,往往径直题作“某某赋”,略去“并序”二字,赋序被视为全赋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即使赋题仅是“某某赋”,它也可能依然有序。在《文苑英华》《历代赋汇》等大型总集中,如果赋作有序的话,全书目录中还是径直题作“某某赋”;书中具体载录时,题目才是“某某赋并序”或“某某赋有序”。目录中采用这样的著录方式是为了文字更为简明,但在正文中还是呈现出了完整的篇题。总之,赋作是否有序,通过题目来判定并不可靠,还是必须要看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