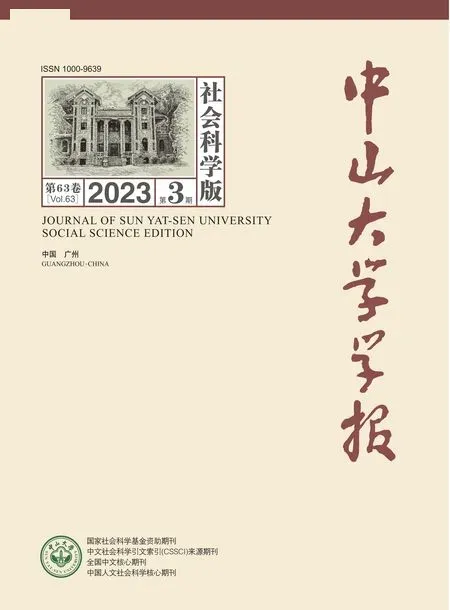文体差序格局与别集编纂 *
张德建
“差序格局”概念是费孝通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关系结构的基本概念,他说这种社会结构往往以自己为中心,“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页。。有学者指出,这个比喻既包含了对平面结构的分析,也包含了多维立体的指向,即差序格局不但包含了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还包含刚性的、等级化的“序”②刘娜:《“差”与“序”:对差序格局概念的理解与阐释》,《文化学刊》2021年第4期。。借助对差序概念的认识,我们不妨由社会学延伸到文学领域,因为文学既是一个历时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具有自主力的概念,也处于学术体系的刚性、等级化的序之中。知识体系与学术体系直接与文体的差序格局相关,本文即是在这样的整体思考下展开研讨,考察别集编纂中的文体排序变化,进而解释文体格局变化的基本规律:由复杂混融、各是其是的非自觉状态,到一定程度的身份定位与自觉,但最终仍然无法摆脱混融态势。
一、集部之混杂
集部自产生到定型,名称不一,名下所收亦杂,荀勖《中经新簿》丁部于诗赋之外,又设图赞和汲冢书,已属混杂。阮孝绪《七录》文集录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其中,杂文的性质大体属于来不及明确规范和归类的文体,如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所列③卢盛江:《集部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4页。。至《隋书·经籍志》集部分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三类,晁公武云:“自时厥后,缀文者接踵于斯矣,然轨辙不同,机杼亦异,各名一家之言,学者欲矜式焉。”①晁公武编,孙猛校:《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03页。别集是以人为单位的体制,所谓“人别为集”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3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35页。,叶适:“按《隋志》称别集之名,汉东京所创,灵均以降,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见其心志,故别取焉。”③叶适:《习学记言》卷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41页。朱寔昌《丹岩先生集叙》:“文集者,人一身之史也,终身履历于是乎见。”④黄云:《黄丹岩先生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24页。楼钥《王文定公内外制序》:“文章之作出于胸臆,读其文则如亲见其人,考其言则如生其时,不可诬也。”⑤楼钥:《攻媿集》卷52,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文集既可以得其心志胸臆,又可以窥一人之史,皆是就“一人”而论。而一人之经历多变,唐锦《陆文裕公续集序》:“平生撰著自讲筵、史局、郊庙、台省以及山川林馆之品题,祠墓金石之镌刻,与经史之折衷,古今典章之辨议,家传人诵,殆遍寰区,片楮只简,为世至宝,可谓极文章之盛矣。”⑥唐锦:《陆文裕公续集序》,见陆深:《俨山续集》,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 辑,第2 册,合肥:黄山书社,2015 年,第331页。则一人之心之史丰富多变。逯耀东认为:“关于别集与别传,别集的个别表现作者,各自与众不同。同样地,个人的别传称之为别,也有这种意味有内,所以,别传的别,可以作分别或区别解。”并指出这与“魏晋个人自我意识的醒觉,对个人性格的尊重和肯定。而且不再重视儒家道德实践的表扬,而偏重个人性格的发挥”⑦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页。,对别集流行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人别为集”就意味着以一个人的所有写作为中心编辑别集,这就与子部的按学派家法、按知识类型的分法不同,与史部按史书体式分类的标准也不同。解决的方案是史部归史部,子部归子部,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做到各归其部类。于是,集部自然不免于混杂,如晁公武所云:“内别集猥多,复分为上中下。”⑧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4上,《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淳祐本。猥杂繁多正是别集的特征。
集部非常复杂的状况,源于集与经史子斩不断理还乱的源流关系。朱一新指出“经兼子史”,“集亦子史之绪余”⑨朱一新著,吕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58页。。陈山毓《别集序》以别集为“裒所论著”,此处称“论著”而不言“文体”,其实更切近集部的性质。故集部虽为“子史之余”,但与子史相比,却又是混杂而不纯正的,故陈山毓称为“残缺”⑩陈山毓:《陈靖质居士文集》卷5,《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625页。。焦循《钞王筑夫异香集序》认为说经、著史各有专书,而集部既是“经史之杂”,是九流、诗赋之变,其内容与表达则不免与经史子有着斩不断的关系,正如文中所列,“凡足以羽翼乎经,皆经类也”,“可以待撰史者之采用,则史类也”,故以“本诸经者”为上,“资乎史者”为次,其下者为集⑪焦循著,徐宇宏、骆红尔校点:《雕菰楼文学七种》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371页。。但上、下之间又无法截然区隔。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一是刊为它集,二是创为全集,三是附刻外集,四是别集中分置别卷。第一种方式最为常见,如史部中的奏议集与诗文别集不同,单独刊刻成书者,一般入史部“奏议类”,也有很多单独刊刻或并未单刻奏议大量收入别集。第二种方式是将作者作品全部收入的全集、大全集,将不同部类刊入其中。祝尚书谓“宋人将其文集与其他专著汇刻为大全集”⑫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页。,则集部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态势,成为经史子集的总刊,突破了以文体书写为中心编辑个人作品集的限制,成为除经子注疏类以外的大全集。第三种方式是以附刻形式出现的外集、后集、别集。宋濂《守斋类稿序》:“著《释图》一,《说约》六十三,《图徽》二十一,《希言》二十四,《事剡》六十二,《治要》十八,《体卦》八,解八,辩十二,议二十四,传七,记、论、序、文、铭各三,杂著十八,赋六,骚十九,杂诗三百二十一。合三十卷,分为前、后、外三集,通名为之《守斋类稿》云。”⑬宋濂撰,黄灵庚整理:《宋濂全集》卷27,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557页。第四种方式是别集中分置别卷,王世贞《止止堂集序》:“《止止堂集》者,少保左都督戚公元敬之所著也,集之部二,曰诗文,则《横槊》一编既之矣,曰著述,则《愚愚》一编既之矣。”①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671页。
这四种处理方式努力使集部容纳更多的内容,但仍呈现出分类上的纠缠与散杂。虽有人提出集部混杂问题,但大多数人视之为当然,习焉不察,或仅就现象言之,没有深入的剖析。集部的这种混杂是一个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直到近现代,人们接受了西方文学观念,对分类上的纷杂认识得更为清晰,郑振铎指出:
中国的书目,极为纷乱,有人以为集部都是文学书,其实不然。《离骚草木疏》也附在集部,所谓“诗话”之类,尤为芜杂,即在“别集”及“总集”中。如果严格的讲起来,所谓“奏疏”,所谓“论说”之类够得上称为文学的,实在也很少。还有二程(程颢、程颐)集中多讲性理之文,及卢文弨,段玉裁,桂馥,钱大昕诸人文集中,多言汉学考证之文,这种文字也是很难叫他做文学的。最奇怪的是子部中的小说家。真正的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等倒没有列进去。他里边所列的却反是那些惟中国特有的“丛谭”、“杂记”、“杂识”之类的笔记。我们要把中国文学的范围,确定一下,真有些不容易!②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郑振铎全集》第6册,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郑振铎有了外部知识视角,故对集部的纷杂看得更为透彻,与古人习焉不察的认识自是更为全面。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一无解的局面呢?这就与书写体制的变化有关,下面将探讨这一问题。
二、从著述之文到集部之文
从书写方式来看,中国古代经历了从著述之文到集部之文的变迁,尽管在概念使用上经常混用,但概念的基本区隔还是相对清晰的。著述概念在中国古代整体上比较泛化,经过长期的演化,到清代才开始逐渐清晰,与集部之文区隔开来。
范晔《儒林传赞》:“斯文未陵,亦各有承。途分流别,专门并兴。”③范晔:《后汉书》卷79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90页。《文苑传赞》:“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④范晔:《后汉书》卷80下,第2658页。儒学传承“途分流别”,文苑亦“殊状共体”,表明学术分裂是以现象的丰富和复杂为背景的,对此需要作出清晰的分类和描述。《隋书·经籍志》“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⑤魏徴等:《隋书》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81页。,也是针对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而言的。但这也埋下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殊状共体”与“风流殊别”的问题。魏晋以来的文学批评对个性有着前所未有的重视,进而关注风格问题,盖风格正是人格的折射,风格论就是为了解决“同声异气”问题而提出的。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开始重视文体,从曹丕到陆机、刘勰在文体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为了解决“殊状共体”问题,如此,方能“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⑥魏徴等:《隋书》卷35,第1081页。。但实际上仍然没有解决著述与文章如何区别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的学术体系中,正经为渊海,子书为川流,处于思想文化的顶点,不可动摇,吴节《大学条约》一正文体条称“六经四子”为“千古立言之祖”⑦吴节:《吴竹坡先生文集》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册,第350页。。葛洪《尚博》:
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则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则林薄之裨嵩岳也。虽津途殊辟,而进德同归。虽离于举趾,而合于兴化,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焉。⑧葛洪:《抱朴子》外篇卷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58页。
以经为“渊海”,以子为“川流”,二者殊途同归。故最重经与子。葛洪:“穷览坟索,著述粲然,可谓立言矣。”①葛洪:《抱朴子》外篇卷2,第170页。凡立言皆称著述。常璩:“(李宓)著《述理论》,论中和仁义、儒学道化之事,凡十篇。”②常璩:《华阳国志》卷11,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186,196页。是以子书为著述。张华:“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曰记曰章句曰解曰论曰读。”③张华:《博物志》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页。是以子书、经解为著述。陈寿《陆绩传》:“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④陈寿:《三国志》卷57,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1年,第1328—1329页。陈寿:“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⑤陈寿:《三国志》卷2,第88页。以文学、经传、类书为著述。在汉魏六朝人看来,著述与诗赋有所不同,“(常宽)……凡所著述,诗、赋、论、议二十余篇”⑥常璩:《华阳国志》卷11,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186,196页。,即以著述、诗赋议论分称。著述和诗赋对举分称,指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和书写体式。而《曹爽传》载何晏:“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⑦陈寿:《三国志》卷9,第292页。以老庄研论、文赋为著述。班固《贾谊列传》:“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⑧班固:《汉书》卷48,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265页。又以诗赋为著述。这一时期著述与文章处于混用状态,诗赋虽有时被称为著述,但与著述的区隔亦较明显,著述主要指经注、子书、史传。葛洪指出,一面是“著述虽繁,适可以骋辞耀藻,无补救于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训,故颜闵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学本而行末”,另一面是诗赋流行天下,“或贵爱诗乘浅近之细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以磋切之至言为騃拙,以虚华之小辩为妍巧,真伪颠倒,玉石混淆,同广乐于桑间,钧龙章于卉服,悠悠皆然,可叹可慨者也”。虽然他对各科之别持开放态度,所谓“清浊参差,所禀有主,朗昩不同科,强弱各殊气”⑨葛洪:《抱朴子》外篇卷32,第258页。,但对著述的衰落和诗赋浅近深表不满,却恰好揭示出著述衰落和诗赋流行的分途别异。至后世,文章与著述也是有所区隔的,焦竑《答茅孝若》引苏辙“有文章以来无如子瞻者”,称为“真千古之笃论”,又专评其学术著述云:“公渡海几葬鱼腹,曰吾《易书》《论语传》未传也,可必不死。自信如此,《论语解》求之未得,观子由《论孟拾遗》,则又有《孟解》,未见也。”⑩焦竑:《焦氏澹园续集》卷5,《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1册,第619页。这种论述方式隐含着区隔文章与著述的意味,是后世的普遍认识。
前文所引文献中,文学、文章、诗赋、议论诸概念常混杂在一起,集部所收正是诸种作品,是广义上的文学。诗赋有独立的体式,容易区隔。诗赋与文章、议论一起构成集部之文。集部之文包括很广,基本上与后世的文章概念相近,指以文体形式书写的文字,刘劭《人物志》:“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⑪刘劭:《人物志》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9页。亦将史传纳入,其形式虽非文体,但在“属文”上又是一致的。故这里界定为文体形式的书写,古人又称之为“成体之文”,秦观《韩愈论》:
夫所谓文者,有论理之文,有论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托词之文,有成体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所作是也;别白黑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张仪之所作是也;考异同,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骇耳目,变心意,此托词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钩列庄之微,挟苏张之辩,摭班马之实,猎屈宋之英,本之以《诗》《书》,折之以孔氏,此成体之文,韩愈之所作是也。⑫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卷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51页。
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文”,论理之文、论事之文属于诸子,叙事之文属于史书,托词之文属于骚赋,最后是合具上述诸文之特点的“成体之文”,即所谓古文。但在内容上难以与经子史著述区别开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集部成立之初就无法避免混杂的问题。刘咸炘《文选序说》:“经说、史传各为成书,子家别为专门,故词赋之流专称为集,非后世杂编为集之例也。”①刘咸炘著,黄曙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文集》“文学讲义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页。以词赋专集为别集,而后世别集为“杂编”。但章学诚指出:“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相如辞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集而成文也。”②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221,590,80,639—640页。汉代著作始衰,《新书》作为子书也仍收入奏议。辞赋亦被视为成一家之言,但与诸子又相去甚远,是子部为混杂。后来才“汇次诸体”成集,章学诚《答陈鉴亭》:“诸子风衰而文集有辩、论,史不专门而文集有传、志、记、序。”③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221,590,80,639—640页。也就是说,集部之文与子史之别在文章体式,辩、论、传、志、记、序皆为文体,但在具体编纂活动中又交杂在一起。二是集部诸体与经史子有着切不断的原初关联,并成为学习典范。张星鉴《书裴晋公与李习之论文书后》:“自昌黎出,而后世之为文者,非经即史,非史即子,昭明所不选者,反为文家所习。”④张星鉴:《仰萧楼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3页。王之绩称古文多“宗经而参以史氏之精华”⑤王之绩:《铁立文起》,《续修四库全书》第17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1页。,已是古文写作的常态,故章学诚云:“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⑥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221,590,80,639—640页。三是文辞在一切表达中的必要性导致很难将集部与子史加以区隔。章学诚《与朱少白论文》:“足下当谓学者果何物哉?学于道也,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三者不可偏废也。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闲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以执一端谓尽道也。”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221,590,80,639—640页。义理、名数、文辞三者皆不可偏废,文辞之学尤不可废,道“须文辞以达之”。以上三个原因使得集部之文总是处于理不清的复杂纠缠关系之中,无法实现完全的独立。
集部既是“人别为集”,以个人为编集单位,而集部之文在体制上以文体写作为中心,二者不能达到一致和统一标准。个人的创作与研究既有多重种样之异,集部之文便难于从中获得独立性,著述之文与文体书写纠缠在一起:一方面是著述之文与文体书写并收,一方面是著述采用文体书写形式。对于这一现象,人们仍试图加以区隔。萧统提出立意与能文之别,以区别老庄管孟之流与文学⑧萧统:《文选》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页。,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叶适针对别集出现后的各种现象,提出“立言”与“为文”之别,也隐含指出著述与集部的不同:“立言”顺天之则,有“大义”表达,经子史无不如此,“为文”则弃“大义”而转向于人为,视之为古今的一大变化⑨叶适:《习学记言》卷37,第341页。。田汝成《汉文选序》:“盖能文固先于立意,而立意者未必专于为文。故议关国是,事载史官,虽董、贾之言亦所不采。若体属词章、思归藻翰,即扬雄《符命》又何择焉。”⑩田汝成:《田叔禾小集》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8册,第408页。“立意”不同于叶适所说的“大义”,但基本指向是一致的,即思想与表达的创造性,与“能文”不同。胡应麟《黄尧衢诗文序》从“词章问学”之别入,指出古人“出于一”,而今人“出于二”⑪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8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0册,第600页。,文章讨论了六经、诸子、史部、集部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子书的三大变化,表明学术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而就集部言,“唐宋而下,文不在子而集”,谈文者盛,谈理者眇,“著作既屈焉”。从学术分类上明确指出了古今学术之变,通过区别集部与经子史之异,将著述与集部之文界定清楚了。左懋第将天下之文分为著述之文、策论辞赋之文、四书六经之文、性灵之文四类⑫左懋第:《萝石山房文钞》,《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89页。,层级更为丰富。邓士亮《俞日藻集序》:“自古如《管》《荀》《吕览》《鹖□(原阙,应为“冠”)》《亢仓》《慎子》之流,呕心著撰,各成一家,宇宙内何可无此分派?第其造诣日进,手笔微异,而评者必欲以一则规之,谓某篇不相类,却似某人作,私意揣拟,迷失真相,亦足憾矣。”⑬邓士亮:《心月轩稿十七卷》卷6,《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6册,第91页。以子部为例,著述“各成一家”,不能“以一则规之”,“一则”意指思想上和形式上统一和文体上的要求。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六朝以来,人们通过诸子与文学的差异关注到著述之文与集部之文的区别,并试图使二者区别开来。徐永勋《唐宋八大家类选序》:“奏疏有奏疏之体,论著有论著之体,推而至于书状、序记、传志、辞章,蔑不然。”①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首,嘉庆乙丑同德堂刊本。指出论著与奏疏及诸体文不同。到章学诚,则清晰地提出:
后世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附于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②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五,第192页。
古无私门著述……是集部著录,实仿于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亦其时势为之也。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③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六,第222—223,225页。
从“专门之学”“私门著述”到集部之学,确乎是中国学术的一大变化,所谓“至此为一变”,一衰一盛,先后关系明晰。章学诚指出著述之文与文人之文的不同:
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譬如庙堂行礼,必用锦绅玉佩,彼行礼者不问绅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锦工玉工未尝习礼,惟籍制锦攻玉以称功,而冒他工所成为己制,则人皆以为窃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见解而议著述之文辞,如以锦工玉工议庙堂之礼典也。④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六,第222—223,225页。
从著述概念的混杂到这里已逐渐地趋于清晰,著述专指经史子著述及研究,不再与诗赋文章之文人之文纠缠在一起。但这在实际编纂活动中仍很难实现,往往有赖于编辑者观念、认识以及一般的惯例。
中国古代普遍接受的大文观,又使得这一局面益加复杂,宋濂《朱葵山文集序》认为《书》《诗》《易》《春秋》皆“天地之至文”⑤宋濂撰,黄灵庚整理:《宋濂全集》卷30,第659页。,而后世之文须以此入手求其文,则集部之文无法与著述区别开来。姚永朴指出“说理”与“述情”“叙事”之别,正是诸子、骚赋、诸史之别,而其本源皆出于经⑥姚永朴:《姚永朴文史讲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9页。。吴则礼《六一居士集跋》:“所谓文者,有曰叙事,有曰述志,有曰析理,有曰阐道。”⑦吴则礼:《北湖集》卷5,涵芬楼秘笈本,第6页。这个分类更为清晰,是依内容和手法的区分。还有更为简洁的,慕容彦逢《论文书》:“古之人无意于文,或以明道,或以叙事。”⑧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1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第450页。朱珔先分骈散,散体再分议论、叙述二类,议论近乎子,叙述近乎史:“二者每分道扬镳。”⑨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13《研六室文钞序》,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8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7718页。在大文观念下,既有合诸子、史书、文章于一体的分法,也有单纯针对文学的分法,而文学之中又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子史成分。在此观念影响下,将古今文章分为叙事之文、议论之文,言性与天道之文,可谓混杂。李维桢《五经翼序》以“谈理之文”“上者为经,次者为子”,“纪事之文”为诸史,将天下文章统分为谈理之文、纪事之文,总括经子史,而视后世之作“自为文一体”,注意到古今撰述体制的不同。又以后世观念承认经“何事不该,何文不工”,诸史之文“往往成章”⑩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0册,436页。,则经子史与“自为一体之文”又纠缠在一起。由此看来,在大文观念下,区分论理、叙事、述情的方式仍无法区隔著述之文与集部之文。
三、文集编次与身份定位
徐枋《居易堂集凡例》:“文籍重编次,编次者,前后是也。”⑪徐枋撰,黄曙辉、印晓峰点校:《居易堂集》凡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指明文集编辑中文体编排有先后排序问题。章学诚也认为总集、 别集之类例, 关乎 “编辑纂次之得失”①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6页。。别集编纂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主要有分体、分类和编年三种,俞樾指出:
诗集以分类、分体为古,编年其最后也。昭明选古人之诗,如“公䜩”“祖饯”之类,分类者也;如“乐府”“杂诗”之类,分体者也。后世诸大家之诗,如杜,如苏,其始无不依类编纂,一遵古法……自施武子注苏诗,极诋永嘉王氏分门别类之非,于是后之编诗者始以编年为正。②俞樾:《李宪之仿潜斋分体诗钞序》,《春在堂杂文》四编卷8,《续修四库全书》第1550册,第480页。
三种之中,编年和分体更为常见,又有分体兼编年。分类方式多行于总集编纂中,真德秀《文章正宗》分辞命、叙事、议论、诗歌四类,但莫如忠认为:“以辞命与叙事、议论析而三之,尤不伦也。”③莫如忠:《答吕侍郎沃洲》,《崇兰馆集》卷1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4册,第638页。认为总集编纂中分体更为合适。在别集编纂中,分类方式采用的并不多,多是以文体分编。
韩梦周:“凡例者,著书之纪纲也。凡例明则体要得,大义彰,惩劝昭。凡例不明,则前与后殊词,首与尾异法。戾书体,乖名义,丛疑起争,著书之旨晦矣。”④韩梦周:《纲目凡例辨》,《理堂文集》卷1,《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7册,第16页。指出著书须明凡例。从历史角度看,“古无专门义例之学,书成而例自具,犹之文成而法自立也”⑤章学诚撰,仓修良注:《史考摘录》,《文史通义新编》,第460页。。经部早有义例,朱次琦《朱氏传芳集凡例》:“古者著书,罕标义例。自汉有《春秋释例》(公车征士颖容撰),魏有《周易略例》(王弼撰),始以例言。至杜预序其《春秋经传集解》,谓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遂有‘发凡举例’之说。书标凡例,此为权舆。”⑥朱次琦:《朱九江先生集》卷8,《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25册,第82,82页。后世史部义例比较严格,刘知几:“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⑦刘知几:《序例》第10,《史通》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4页。但在集部之学中确实长期“无义例之学”,只有惯例。明清刊刻别集,注意编辑体例的逐渐多了起来,如吕柟《泾野先生文集》有《凡例》数条⑧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9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12,12页。。钱泰吉《跋徐俟斋居易堂集》:“集首有目次凡例十一则,亦编辑文集者所宜取则也。”⑨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卷6,《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2册,第68页。朱次琦《朱氏传芳集凡例》:“乃者家集编摩,何关著述,而抗希微尚,窃有别裁。约贡数端,用签首简。”⑩朱次琦:《朱九江先生集》卷8,《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25册,第82,82页。
别集编纂多循惯例、常例而行,相对稳固,宋高宗绍兴四年,罗良弼跋刘弇集:“合而次之,得古律赋三,宏词四,古诗一百四十,律诗一百二十一,绝句一百一,生辰诗一十一,挽诗一十三,(总三百九十三首,印本止有三十九首。)乐府六,表一十七,启五十二,(郭本黜,今附。)书四十四,序一十四,时议六,策问四十五,记十,杂著五,疏语十,祭文一十一,碑志一十二,总六百三十一篇,为三十有二卷,而先生之文略尽矣。”⑪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12“龙云先生文集”,第531页。这是诗文合编的基本惯例。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首《凡例》:“集中文有大小繁简,今依原稿订正。先序文,次记文,次书翰,次志碣,次语传,次字说,次奠章,次题辞,次跋,次策问,又次行状诔议铭箴,卷自为类,目各有条。”⑫这是一般文集编纂中文体排序的常例。
在分体编排方式中,有一个文体顺序问题,而这个问题似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王之绩《铁立文起》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诗文先后问题,一是诗文之各体编排顺序问题⑬王之绩:《铁立文起》,清康熙刻本。。陈龙正《陶庵集序例》论及分类标准与文体编排顺序:“葺茅名陶,高士为质,陶之珍于后世者,诗也,性情风节丽焉,表所归依,定诗歌第一。”“力于人伦,介于交游,不为过实之美,美必真,不为无情之辞,辞必诚。于其及人,可以知所存矣,定传、记、序、书第二。”“病而省事,病而省心,是其精神之所钟乎,于用力宜前,于登陟处后,物之大者恒为⑫ 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9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12,12页。尾,故以札纪终焉。”①陈龙正:《几亭全书》卷53,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5辑,第44册,第320页。这个标准是按照个体性情风节、交游、精神境界分排的,以诗歌为第一,传记、记、序、书第二,札记为末。但就此标准而言,作家个体性情、精神有着极大差异,则仍无法成为标准。徐枋提出了两个依据:一是多少,二是有关系。《居易堂集凡例》:“集之居前者,大约须观其全集之次,惟其所重,以其文之多而有关系者为首列,斯为得体。”②徐枋撰,黄曙辉、印晓峰点校:《居易堂集》凡例,第3—4,3页。最佳组合是二者相合,故他的集子“以书居首,盖此集中惟书为最多……似一生之微尚系焉。”但以多少为标准仅是一个量化指标,在实际操作中无法执行,因此文集编排多是以“有关系”为标准。
诗文先后表面上是习惯问题,但既是习惯,则各有习惯,差异很大,这就值得追究。从别集编纂中可以看到诸体顺序的安排有一些突出现象,如诗文先后、诗集编排、文集编排。诗集编纂涉及到赋体编排位置问题。徐枋《居易堂集凡例》:“今人文集动以赋与诗居首,此遵文选例也,不知文选固辞家之书,其所重在辞赋耳,未可概论。”③徐枋撰,黄曙辉、印晓峰点校:《居易堂集》凡例,第3—4,3页。虽然“未可概论”,但别集编纂中,常见以赋居首者,如朱右《白云稿》12 卷,卷1 为骚赋④朱右:《白云稿》,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8册,第635页。。汪克宽《环谷集》卷1 为赋,卷2 为辞、诗⑤汪克宽:《环谷集》,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4册,第132—133页。。宋讷《西隐文稿》10 卷,卷1 为古赋⑥宋讷:《西隐文稿》,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8册,第5页。。朱应登《凌溪先生集》凡18卷,卷12所收为赋居首⑦朱应登:《凌溪先生集》,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1册,第132—143页。。诗集编排多以体分,较易区隔,在长期的集部编纂活动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分体编排顺序,大体是四言、古诗、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六言及词作在后的格局⑧何诗海:《明清总集凡例与文体批评》,《学术研究》2012年第8期。。文集编排问题最多。邓显鹤《圭斋文集目录序》:“古人文集,原统诗文而言。专以文论,有诏诰、书疏、表状、论辨、说、赞、序、碑铭、哀诔各体之异。求之于唐宋古文家如昌黎集,首表状,次序记,次碑铭,次哀诔;庐陵集首书疏、表启,次论序,次碑铭,次祭文,大抵以是为叙。此本以经义、䇿对、诏诰、万方册上尊号,及表进三史大典之文次于墓志、哀词之后,而以本传、世系附录卷末,先后错乱,尤不胜纠。”⑨邓显鹤撰,弘征点校:《南村草堂文钞》卷2,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41页。韩愈、欧阳修集文体编排顺序差异如此之大,可见文集编纂中文体编排次序是一个极突出的问题。
于是,人们试图对文集编排做进一步区隔。前文引徐枋《居易堂集凡例》“有关系”之说,“有关系”须落实到作家身份,即以作家主要社会身份或不同情境下的身份追认为主。身份可界定为两类:一是文化身份,二是社会身份。较早的划分是依据文化身份进行的,如李石《策问》:“问贾谊、陆贽之学,缙绅先生喜称诵之,谓儒者之文有益于世用,不徒为纸上空言,莫二子若也。”⑩李石:《方舟集》卷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9册,第605页。孙复《书汉元帝赞后》:“史固所谓牵文义者,非儒者之文义乎?”⑪孙复:《孙明复小集》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164页。均提出“儒者之文”以为身份标志。明人亦沿此,雷礼:“其(姚广孝)论文曰:惟韩退之、欧阳永叔、曾子固真儒者之文,识者亦有取焉。”⑫雷礼:《皇明大政记》卷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09页。与此相对应,又有文人之文,吴澄《张达善文集序》:“昔之为文者曰:不蹈前人一言一句,或曰此文人之文尔,儒者之文不如是。”⑬吴澄:《吴文正集》卷1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70页。“文人之文”是相对于“儒者之文”提出的,是以“能文为本”,而儒者之文是“托辞以明理”,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但儒者也“未尝不力于文”。然而儒者之文、文人之文仍是相对粗略的划分,二者包容性过强,区隔度较低,导致身份划分上存在模糊混杂。
这种文化身份划分方式在别集体制下仍是无法真正区别开来,于是在别集编纂中,多采用社会身份或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的混融加以区隔。作为个体的人,每个人都有相应的社会身份。刘劭《人物志》:“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辨,有雄杰。”①刘劭:《人物志》卷上,第46—47页。十二流别的划分透露出社会身份的复杂性,后世划分虽没有这么多层次,但总是力图在复杂多样的社会身份中寻找、建立标准。一般而言,社会身份划分可分为两类:主要社会身份和多重社会身份②马自力提出了“角色集”的概念,认为:“社会角色发生作用时,往往并不是以单一的角色形式体现,而是多种角色或曰角色集共同起作用。”《中古文学论丛及其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11页。。孔天胤《苑洛先生文集原序》③韩邦奇:《苑洛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8册,第269页。一文中将韩邦奇的主要社会身份被界定为“儒贤”式政治官员,其文章所涉皆帝王统治、圣贤传心、人物风俗之义诸事。其中又有一个身份变化的问题,《苑洛集》卷22附跋:“先生少时锐意于诗文,既而当弘治之盛,自庆身际升平,复留心于礼乐。比登仕,则正德矣,乃幡然于性命道德之学,凡诗文则随意应答,稿多不存。”④韩邦奇:《苑洛集》卷22,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8册,第634页。经历一个由锐意诗文到留心礼乐,再到性命道德之学的变化。身份有时是固定标签,但在表现上却是多重综合互融。社会身份的多重性表现为交叉并存,二者并不矛盾,方凤《送左都御史陈公诗序》:“君子之自立也,以德行、文章、事业为之主,三者阙一不得谓之全才……今公之德之成如王文正之雅重,学之正如胡文定之醇实,政事之所在有声如包孝肃之严整,而又得乎知足勇退之义,飘然绿野之适,顾不为完人乎?”⑤方凤:《改亭存稿》卷1,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4册,第515—516页。即兼有德、学、政三重身份。蔡献臣《林次崖先生文集原序》指林希元以学术身份而言,是程朱派学者,以政治身份而言,是矢心忧世的官员⑥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12册,第10页。。这在中国古代是普遍存在的,多重身份是普遍现象,但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后世评价之中,每个人都须划定一个主要身份,成为其代表性身份。
主要社会身份划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建立有关。中国古代学术体系自宋以来,形成道德、政事、文学三分的格局。故后世的社会身份划分就依据学术三分的体系划定,李维桢指出:
昔者孔子四科,文学、言语与德行、政事各效其长,令词林四部集与经子史各诣其胜,合固双美,离不两伤。彼一隅之士,分畛域,立门户者爽然自失,孜孜然学如不及,有功于辞林宏矣。⑦李维桢:《辞林人物考序》,《大泌山房集》卷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0册,第472页。
陶望龄《邓先生潜学编序》:
古之学者,其术简,其该统博,其所就精,求之有本,会之有归……道德、政事、文章之途,常出于一。取之有要,故不烦;为之有方,故一成,而后世无以尚焉。⑧陶望龄:《邓先生潜学编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0册,第326—327页。
“三代而降,道丧术乖”,经历了一个不断分裂的过程:汉诸儒犹有“典刑气象,有足术也”,“道又下衰,于是朴学专解诂,词家工藻翰,儒林、文苑,画为二辙,况暇语道德、政事之同异乎?”至明弘正间,“修词家蔚起,吐弃故烂,更命古学,于是古文、经义之文,又判然二矣”⑨邓元锡:《潜学稿》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49册,第16—17页。。呈现为不断分裂的局面,但总体上仍不离三分格局。延伸到个体身份,即多以此划分,如刘克庄《跋刘澜诗集》⑩刘克庄著,辛更儒校:《刘克庄集笺校》卷109,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520页。将身份分为名节、学问、文章、功名四类,实际上,名节可归入功名之中,仍是按学术体系划分为三类。
现代学者也延续了古人的思路,仍是在大文观念下展开思考,并进一步上升到不同的学术层面,钱穆在《朱子学提纲》中概括了宋儒学术的三大方面:
一曰政事治平之学,一曰经史博古之学,一曰文章子集之学。宋儒为学,实乃兼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而并包为一。①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2—13,11—12页。
又云:“宋儒之经学,则多能于每一经之大义上发挥……又其次曰文章子集之学,此乃承唐韩愈之古文运动而来……惟宋儒始绾文学与儒术而一之……尤可注意者,乃北宋诸儒之多泛滥及于先秦之子部。”②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2—13,11—12页。指出宋学虽分三类,但“兼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而并包为一”,“宋儒始绾文学与儒术而一之”,又多“泛滥及于先秦之子部”。也就是说,虽作出区隔,但宋代文学表现出一种兼综融合的态势。朱刚延续这个角度,指出:“实际生存的士大夫可能各具特长,但理想型的士大夫应该是‘全面发展’的,既是政治家,又是诗人,又是学者,等等。”③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士大夫遂成为身份多元、“全面发展”的群体,王世贞《钱临江先生集序》:“先生工属文,尤好吟咏,其习先生诗若文者见之,以为才士;及诵南曹疏者,见以为直臣;及临江盱眙政者,见以为循吏。及与称乡后进者,见以为善人君子,然竟莫能以一端名先生,而先生亦聩然不欲以一端见名。”④钱琦:《钱临江先生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6册,第503页。既可以是才士,又是直臣、循吏。
在三分学术体系的强化作用下,以主要社会身份兼及文化身份为依据,别集编纂中文体编排顺序大体有三种:文人大体诗赋文居前,政治人物以对上者的奏疏一类文体居前,思想家、学者则多以书信居首。
曹金《崔东洲集序》:“尝缀其旧所为文若诗,得六百八十有奇,丽二十卷。大之而枢要,具析之而品汇彰,鬯达乎性情,渊源乎道义,窥典谟而驰风雅,因物赋形,无所沿袭,盖本其道德、事功之所衍敷而相须以不朽者,庸可以无传也邪?”⑤崔桐:《崔东洲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4册,第118页。以性情为主,以道德、事功为归依,仍定位为文章之士,故其文集编排,卷1 至卷10 为古诗、乐府、律诗、绝句、词,卷11 至卷20 为记、序、墓志铭、墓表、传、说、谥议、祭文诸体。文人别集大体如此,或赋、或诗、或文居首,诸体亦有相对稳定的排序方式,前文已有引述,此不赘述。
宋陈仁子《文选补遗》:“以为诏令,人主播告之典章;奏疏,人臣经济之方略。不当以诗赋先奏疏,矧诏令,是君臣失位,质文先后失宜。”⑥陈仁子:《文选补遗序》,《文选补遗》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0册,第3页。唐人编纂别集,就有意区别政治人物与一般文人的不同,权德舆《陆贽翰苑集序》:“公之文集,有诗文赋集,表状为别集十五卷,其关于时政昭昭然与金石不朽者,惟制诰奏议乎?虽已流行,多谬编次,今以类相从冠于编首。”⑦陆贽:《翰苑集》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2册,第575页。吴淇《凡例》:“谨照文体汇辑,以对君者居前,诗次之,余文又次之,而其中则仍各以类次。”⑧刘理顺:《刘文烈公全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4册,第16页。这就成为别集分体编纂中的常见方式,用以表明作家的政治身份。宋濂是明代文臣之首,集理学家、文人、政治家于一身,但在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中,他的第一位身份是政治家。《宋学士文集》75 卷,排列顺序就凸显了这一点,卷1 收颂、赞、乐章、诏、代皇太子书、拟诰、祭古帝王、表、书后,所收都是与政治活动相关的文体,卷2至卷5主要收录神道碑、墓志铭、修坟记、石表辞、庙碑、塔铭、武功记、寺碑,这又与他在明初写作的大量功臣碑铭等有关⑨宋濂:《宋学士文集》,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6册,第8—9页。。朱升《朱枫林集》也是这种编纂方式,卷1为诰、诏、御翰、御洒、代玉言、表笺⑩朱升:《朱枫林集》,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册,第7—14页。。苏伯衡《苏平仲文集》16卷,卷1、2为杂著,卷2又列入表文、谥册文、制诰、颂赞、荣题诸体⑪苏伯衡:《苏平仲文集》,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4册,第233页。。陶安《陶学士先生文集》卷首为歌、制奉、赋、词⑫陶安:《陶学士先生文集》,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9册,第557—569页。。杨时乔《刻吕巾石先生类稿序》:“类稿首制策,预养、从祀诸疏,终怀玉讲义,先生进退之撰备矣。”①杨时乔:《新刻杨端洁公文集》卷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9册,第708页。王臬《迟庵先生集》卷1为奏疏,卷2、3为公移②王臬:《迟庵先生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1册,第3页。。徐阶《陆文裕公全集原序》提出“以通达政务为尚,纪事辅经为贤”③陆深:《陆文裕公行远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2册,第414页。,是典型的台阁文学主张,道德、政事、文学一体,故强调陆深辅经之作,论政之文,有奏状、奏疏、策问、纪事、经筵、传记诸体,散见于碑志序记者亦具此功能。其集卷1 为册、表、赞、颂,卷2 为奏议,卷3 为序,卷4 为记,卷5为传,卷6为碑。杨闻中《新刻杨端洁公文集凡例小引》:“卷之一、二为奏疏,二、三为贺赠序,五、六为诸书序,七、八为记、为碑,九至十三为尺牍,十四至十七为律、为绝句、为古歌、词赋,十八、十九为祭文、墓铭,二十卷则以杂著终焉。”④杨时乔:《新刻杨端洁公文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9册,第623—624页。这种文体编排顺序构成了一个内在自足的文学秩序,即以忠君为首,父母公族人伦为次,研讨商榷、声应道同的交流为再次,怡情抒素的个体情感表达为末,而哀诔志铭则专为进入死亡世界的人而设。梁潜《泊庵先生文集》16卷,卷1为序,附注云“应制”,卷2为论、明本二十条有序,治本十阙五条⑤梁潜:《泊庵先生文集》,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0册,第317,602页。。梁混《坦庵先生文集》8卷,卷1为表笺、启、贺、赋,皆为公文、应制诸作⑥梁潜:《泊庵先生文集》,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0册,第317,602页。。后世视秦观为词人,很少有人认为他是政治家,但就中国古代文官体系而言,他被视为官员,故在别集编纂中虽突出他的诗赋,但文集部分却是先编入进策、进论,如嘉靖张綖本《淮海集》40 卷,卷目编次为:卷1,赋;卷2 至卷11,诗;卷12 至卷18,进策;卷19 至卷22,进论;卷23,论;卷24,传;卷25,传、说;卷26、27,表;卷28、29,启;卷30,简;卷31,文;卷32,疏;卷33,志铭;卷34,赞、跋;卷35,跋;卷36,状;卷37,疏;卷38,记;卷39,序;卷40 ,哀挽⑦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12《淮海居士集》提要,第549页。。
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些变通,根据作者的政治经历而有所调整,赵秉忠《蜞山集》12 卷,文6 卷,卷1为策问,将进士策问置于首⑧赵秉忠:《蜞山集》,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13册,年,第5页。。丁奉《南湖先生文选》8卷补编1卷⑨丁奉:《南湖先生文选》,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4册,第360—367页。,诗文各4卷,卷5、6为文之首,所收为史论,亦突出其史识史怀。或强调其突出的政绩,如黄福《黄忠宣公文集》所收卷1 为《奉使安南水程》,这与他主持安南军事有关⑩黄福:《黄忠宣公文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5册,第244—249页。。当然,这并非统一文集编排共例,大量文集仍是按照常例和习惯编排文体,如孔天胤《苑洛先生文集原序》:“大司马韩公苑洛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其一卷、二卷为叙,三卷为记,四卷、五卷、六卷为志铭,七卷为表,八卷为列传,九卷为策问,十卷为五言,十一卷为七言及联句,十二卷为填词,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卷为奏议,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卷为语录。”⑪韩邦奇:《苑洛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8册,第269页。标点略有改动。但韩邦奇为“当代之儒贤也”,又“崛蜚英于馆阁”,而文集仍按习惯编排。严嵩《钤山堂集》40 卷即按文人别集方式编排,湛若水《钤山堂文集序》:“凡为赋诗古律绝句七百八十,颂序记碑五十有九,内制讲章二十有七,杂著二十有五,铭四十有三。”⑫严嵩:《钤山堂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11册,第3,5页。但何以会如此呢?严嵩作为内阁首辅,理当突出其政治身份,张治《钤山堂集序》:“及辅今上,入而护保圣躬,出图议庶政,日不暇矣,顾其文益工,铺陈帝业,经制人文,祗应明命,陈说化理,咸中典则,虽震冲盘结,事匪故常,罔不取裁衷臆,油然有余力也,其声郁律而不恌,其出泔淡而有余,若斯者,由神情之定乎?”⑬严嵩:《钤山堂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11册,第3,5页。又说:“兹集也,其大足以定国是,贲王猷,声歌所发,亦足杼轴天人,经纬风雅,百代之下,考德业者征焉,将不流今而传后哉!”①严嵩:《钤山堂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11册,第6,6,6页。强调“定国是”“杼轴天人,经纬风雅”②严嵩:《钤山堂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11册,第6,6,6页。,突出严嵩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掌握文学权力的文坛领袖③严嵩:《钤山堂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11册,第6,6,6页。。
理学家、学者文集编排,多有以语录、书信居首。胡直《念庵先生文集序》④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7册,第327页。提出:“文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是故文非圣人不能柄也。”不得已而用之,文柄必须掌握在圣人手中。孟子之后,道术大裂,百氏杂出,“而文柄遂旁落于能言者之家”,至“近代儒者”对重新掌握文柄,“彼能言者无容喙矣”,提出“此文之别种”,强调理学家之文不同于文人之文。王阳明写给钱德洪的信中说:“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者,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⑤徐爱、钱德洪、董沄著,钱明编校整理:《徐爱 钱德洪 董沄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84页。“不在文辞体制间”正是理学与文人的区别,一旦陷于“文字为心”,“便不可入尧舜之道”。但明道与文字又并非完全隔绝,甚至可以兼而有之,马理《泾野先生文集序》列举吕柟之文,以类型论,则有讲说、赠处、庆吊、叙述记志、表诔祠祭、登临赋咏诸类,但吕柟毕竟是理学家,“泾野子则为汉之文赋,怀其史才,传其经学,而无驳杂戾道之失,工晋人书,唐人之诗,宋人以上之文,而多纯实之语,醇如鲁斋而著述则多,确如文清而居业则广,盖其学诣周之精,同邵之大,得程、张之正与晦庵朱子之匹美者也”⑥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9册,第8—9页。。虽为应世之文,但写作根基仍在思想的纯正,而不在文章体制。陈龙正《高子遗书序例》:“文字当垂,惟取益世,益世惟三,其一关切身心,其二开物成务,此易知也。三者烟霞洒落,足以澹嗜好而资清真,理义从此实,故不身心而身心,才识从此浚,故不世务而世务,不学者则以为玩弄景光,逍遥日月而已矣。此在观者自得之,先生语言文字中,往往见此,出于逍遥之口,与出于学人,自是不同,口不同也。”⑦陈龙正:《几亭全书》,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5辑,第44册,第322页。由文中所列三条,理义、身心、世务就可以融贯于一,区别于文人之文。
胡直《念庵先生文集序》:“乃征吏部曾君见台偕及门士分校语学各体,编置于前,仍其年次,俾览者知先生所得之繇。其他酬应为外集,又为别集,统凡若干卷。”⑧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7册,第327页。“语学各体,编置于前。”陈龙正《阳明先生要书序例》将王阳明之文分为四类:一曰论世,二曰统类,三曰除繁,四曰表微,其书所编一传习录,二书,三诗,四奏疏,五文移,六策序,七记说题跋杂著,八墓表祭文⑨陈龙正:《几亭全书》卷54,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5辑,第44册,第327—330页。。即以《传习录》为首,书信次之。谢应芳《龟巢稿》20卷,文部编排为书、疏、序、记、启、题跋说杂体、行状铭赞箴、祭文⑩谢应芳:《龟巢稿》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册,第117—140页。。刘魁《刘晴川集》1卷,以语录居前,后为疏、序、书、诗。刘魁为阳明弟子,故其集编排,以语录居前⑪刘魁:《刘晴川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8册,第3—9页。。金铉《金忠洁集》6 卷,卷1语录,卷2书,卷3疏、揭、呈,余为序论诸体⑫金铉:《金忠洁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5册,第89—91页。。
此外,还有一些集子不循惯例,自成一体。如方孝孺《逊志斋集》24卷,卷1至卷8为杂著,卷6至卷8所录杂著为原、辩、对、策问、论、颂、铭箴、说、字说、文、赋、祝辞、疏诸体,卷九为表、笺、启、书,卷10、卷11为书⑬方孝孺:《逊志斋集》,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4册,第6—17页。。高攀龙《高子遗书》在编排上分为“一曰语,二曰札记,三曰经说辨赞类,四曰讲义,五曰语录,六曰诗,七曰疏揭问类,八曰书,九曰序,十曰碑传记谱训类,十一曰志表状祭文类,十二曰题跋杂书类”⑭高攀龙:《高子遗书序》,《高子遗书 高子遗书未刻稿》,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页。,仍强调高氏的理学家身份。李中《谷平先生文集》卷1所收为奏议,卷2为谷平日录、私录师训,卷3 为书,卷4 为诗,卷5 为文、序跋祭文之属。而其侄孙跋:“即其集中奏疏、序、书……铭实非先生意也,先生之意乃在日用语录,是其当时一副真精神,自不可磨,真濂洛真谛,而洙泗正脉,于是摘其要。”①李中:《谷平先生文集》附录,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6册,第151页。置于首乃从俗,而最能表明其价值的是“日用语录”。与此相应,学者之集也形成了独特的编纂体例,如刘夏《刘尚宾文集》5卷,卷1为皇王大学通旨②刘夏:《刘尚宾文集》,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8册,第533页。。杨士云卷1、2为咏史,卷3为天文历志、卷4为律吕,卷5为皇极经世,卷6 为韩诗外传、说苑、阅老、庄列、庄子、太玄附地志咏,卷7 至卷10 为三言至七言律诸体,卷11、12为序题跋记诸体之文,一望而知为学者之集③杨士云:《弘山先生日录诗集十卷文集二卷》,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3册,第29—42页。。胡翰《胡仲子集》10卷,卷1为衡动、正纪、尚贤、井牧、五行志、牺尊辨,卷2为慎习、皇初诸体,卷3为择术、纪交、勖言、琴释……书后、论、说、书④胡翰:《胡仲子集》,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4册,第440—442页。。《新刊归震川先生文集》卷1为经解,卷2为序,卷3为论、议、说,卷4为杂文,卷5为题跋,卷6至卷8为书,卷9至卷11为赠送序,卷12至卷14为寿序,卷15至卷17为记,卷18至卷21为墓志铭⑤归有光:《新刊归震川先生文集》,《丛书集成三编》第5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也是刻意突出归有光的学者身份。
借由差序格局概念,我们发现,文学正是处在学术体系、知识体系的等级化秩序之中,表现在别集编纂活动中,就是以学术和社会身份为标尺,形成别集文体编排的差序格局。在别集编纂中,这种差序格局呈现为柔性与刚性并存的双重品格,一方面是大量别集仍然按照旧有的习尚编排,另一方面则是很多别集刻意在文体编排中强调身份差异。
四、文法的世界
那么,知识体系中分类明确的经、史、子、集四部为什么在集部纠结在一起而无法分开呢?除了前面谈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章写作中对文法的重视,并将这一观念推衍到经史子之中,相沿成习,形成集体认同。经史子集在文章学视域下都被视为文章,而文法即作为文章的共有要素,造成集部体系庞杂交叉,无法彻底划分清楚。
包世臣云:“天下之事,莫不有法。”⑥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艺舟双楫》第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1页。揭傒斯:“学问有渊源,文章有法度,文有文法,诗有诗法,字有字法,凡世间一能一艺,无不有法。得之则成,失之则否,信手拈来,出意妄作,本无根源,未经师匠,名曰杜撰。正如有修无证,纵是一闻千悟,尽属天魔外道。”⑦揭傒斯:《诗法正宗》,乾隆诗学指南本。自魏晋以来,便开始寻找文学之法,刘勰谓“文场笔苑,有术有门”“术有恒数,按部整伍”⑧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649、1465页。。自此以来,文术、文法成为文章学理论体系的重要范畴,韩愈“陈言之务去”⑨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第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0页。,李梦阳“文必有法式”⑩李梦阳:《答周子书(一)》,李梦阳著,郝润华校笺:《李梦阳集校笺》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925页。,方苞“义法说”⑪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8页。等,都是文法理论的重要发展。无法之文则陷于鄙陋,宋濂《徐教授文集序》⑫宋濂撰,黄灵庚整理:《宋濂全集》卷29,第633—634页。一文中列举了诸种“非文”现象,涉及表现、风格、情感诸方面,无法之弊乃至于此!可见文法作为写作手段、风格呈现和思想情感规范的重要性。文法所包含的世界非常宽泛,决非仅限于文学领域,而是包括经史子集,屠隆《文论》:
夫六经之所贵者道术,固也,吾知之。即其文字,奚不盛哉!《易》之冲玄,《诗》之和婉,《书》之庄雅,《春秋》之简严,绝无后世文人学士纤秾佻巧之态,而风骨格力,高视千古。若《礼·檀弓》《周礼·考工记》等篇,则又峰峦峭拔,波涛层起,而姿态横出,信文章之大观也。六经而下,《左》《国》之文高峻严整,古雅藻丽……贾马之文,疏朗豪宕,雄健隽古……其他若屈大夫之词赋,才情傅合,纵横璀灿……《庄》《列》之文,播弄恣肆,鼓舞六合……诸子之风骨格力,即言人人殊,其道术之醇粹洁白,皆不敢望六经,乃其为古文辞一也。①屠隆撰,李亮伟、张萍校注:《由拳集校注》卷23,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36页。
在传统文章学的认识视域中,经史子集统被视为文,六经之文为“文章之大观”,《左》《国》《庄》《列》之文与贾马词赋之文被统一纳入到“古文辞”系统之中。王志道《虚台蔡先生文集序》:“益、稷之事在《谟》,旦、说之业在《命》、《诰》。三代以来,德行政事、名卿硕辅之业,皆藏于文章中。孔氏有叙事之文焉,左氏是也;有议论之文焉,孟、荀是也。至于言性与天道,可闻不可闻,总谓之夫子之文章,而胡轻言文章哉?”②蔡献臣:《清白堂稿》卷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将所有表达文字皆视为文章,是典型的后世观念。这一逻辑建构在共同观念的作用下,统合沉淀为一种集体认同,在古人看来有着充分的合理性。在这种集体认同之下,古今既是融通互贯又是对立相异的一个范畴,将经史子视为文章典范,成为历代文章写作的师法对象,以古为师。林子应《立说》:“谓文体之工,自文法之变始,《庄子》之文,《易》之变也;屈原《离骚》之文,《诗》之变也;司马迁《史记》所录,《尚书》《春秋》之变也。然文以变而工,其去道已远,古者之文正不贵其变也。”③魏天应编,林子长注:《论学绳尺》卷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8册,第420,420页。“六经无文法”,乃无法之法,自六经之后,以《庄子》《离骚》《史记》为代表始有文法,皆源于经,各成其法。即是说,在经史子中存在着一个“文法”,他认同“文以变而工”,尽管强调“不贵其变”,但对后世而言,文法是必须的。孙矿《与李于田论文书》④孙矿:《月峰先生居业次编》卷3,《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6册,第191页。一反宋人之说,认为“六经乃有文法”,“万古文章总无过周者”,其后《论语》《公》《谷》《礼记》“最为有法”及诸“孔门文字”以至《战国策》、庄、列、荀、屈、韩、吕,再到司马迁、唐宋韩、苏,无不有法,其法递相传授,相沿不止。
方澄孙《庄骚太史所录》:“夫六经无文法也。”林子长注云:“陈止斋文,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文之正者无奇。”⑤魏天应编,林子长注:《论学绳尺》卷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8册,第420,420页。按止斋为陈傅良。这个观点提出后,人们又不断加以补充,如林希逸:“古人文字之工如此,不可谓不留意于文者,谁谓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乎?”⑥林希逸:《考工记解》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5册,第64页。强调六经是无法之法,是最高的法,如揭傒斯:“世言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不知文人莫盛于三代,文法尽出于六经。”⑦揭傒斯:《诗法正宗》,乾隆诗学指南本。陈傅良:“非无文人也,不以文论人也;非无文法也,不以文为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⑧陈傅良:《止斋集》卷5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913页。张邦纪《沈文恭公集序》⑨沈一贯:《喙鸣文集》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357册,第107—109页。指出文法始自六经,但六经之文法“不以文为法”,“文无之而非法也”,由此,六经成为文法源头与核心,通过不断地回归中心,文法得以强化。文人通过学习六经,得经之义与文之法,彭辂《西泉钱伯子集序》⑩彭辂:《冲溪先生集》卷1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16册,第155—156页。指出只有在六经的“膏泽”和“范铏”之下,进入自得之境界,方能游泳于道,徊翔文苑。
李翱《答朱载言书》:“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耽、列御寇、庄周、鹖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子、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⑪李翱撰,郝润华、杜学林校注:《李翱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84页。百家之言皆“自足以成一家之文”,故为后世学者所师。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韩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达;曾子固、苏子由自儒家、杂家入,故其言温而定;柳子厚、欧阳永叔自儒家、杂家、词赋家入,故其言详雅有度;杜牧之、苏明允自兵家、纵横家入,故其言纵厉。苏子瞻自纵横家、道家、小说家入,故其言道逍遥而震动。”①恽敬撰,万陆等标校:《恽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78页。所列诸家或得自儒、法、名,或得自儒、杂诸家,或由自儒家、杂家、词赋,或自兵家、纵横家入,或自纵横家、道家、小说家入,诸子为师法典范在这里最为突出,几于无所不包。最有典范意义的是苏轼,焦竑《答茅孝若》认为苏轼独悟庄禅,贯穿驰骋而得其精微,故得风行水上之法,能“自道”其所得②焦竑:《焦氏澹园续集》卷5,《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61,第619页。。至晚明,文坛上诸子学兴起,赵用贤着意师法诸子,王世贞《合刻管子韩非子书序》:“汝师之为诸子,于道好庄周、列御寇,于术好管子、韩非子,谓其文辞亡论高妙,而所结撰之大旨,远者出人意表,而迩者能发人所欲发于所不能发。”③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4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第576页。唐宋以来,尽管子学已经衰落,儒学强大,但诸子却反而成为文章师法对象。
佛经也具有文法价值,千光瑰省禅师云:“后阅《楞严》,文理宏浚,未能洞晓。”④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27页。苏轼《跋柳闳楞严经后》说《楞严》“雅丽”⑤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65页。。屠隆《与王太初田叔二道友》:“余读《楞严》《维摩》,神幻精光,文心绝丽。”⑥屠隆:《白榆集》文集卷10,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90册,第263页。云栖袾宏:“有见《楞严》不独义深,亦复文妙。”⑦袾宏撰,心举点校:《竹窗随笔》,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3页。均强调《楞严经》具有“文理宏浚”“雅丽”“文心绝丽”“文妙”的特点。钟惺以为《楞严经》“广陈七大圆融之满义,独拈三科见识之偏辞。若不达举一例余之法,几疑为衍文脱简之条”⑧钟惺:《首楞严经如说序》,《隐秀轩集》卷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6页。,故其做《楞严经如说》以释之⑨钟惺:《楞严经如说》卷10,《卍续藏经》第2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在《如说》一书中,钟惺“以‘括题’、‘起结’二法解读经文,又有全经大起结、伏笔、过接、炼字等其他文章特色”⑩王镱苏:《钟惺〈楞严经如说〉及其佛经文理评点》,《文学遗产》2020年第5期。,即是以文法析佛经,亦表明佛经也有文法。史传很早就成为文学的师法对象,影响颇为深远,章学诚《跋湖北通志检存稿》:“尝论史笔与文士异趋……司马生西汉而文近周、秦、战国,班、陈、范、沈亦拔出时流,彼未尝不藉所因以增其颜色,视文士所得为优裕矣。”⑪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11页。史笔虽与文士异趋,但不妨成为文士师法典范。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史子集皆被视为文章,成为后世师法典范,形成一个分类明晰,但在文章实践中却混融一体的现象,反映在集部编纂中,自然表现为混杂难分。
既皆为文章,而文法作为联络古今之关键要素不可或缺,这使得在后人的认识中,经史子集交合联系在一起。那么,文法具体表现为什么?李梦阳《再与何氏书》:“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迭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谓法圆规而方矩者也。”⑫李梦阳著,郝润华校笺:《李梦阳集校笺》第5册,第1920页。但他对法度的认识还只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强调自古以来就有“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指出“无法”“有法”,二者之间在写作实践中虽难调合,但不可否认确有基本的法度规范⑬唐顺之著,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66页。。艾南英《四与周介生论文书》:“经籍而后,必推秦汉,为其古雅质朴,典则高贵,序裁生动,使人如睹。”⑭艾南英:《天慵子集》卷1,《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7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以风格言之,亦为感受型的,很难将文法说清楚。明代流行神气说,以归有光最为有名,但神气是什么?仍然无法落到实处,只能靠读者自悟,而每个人所悟到的却不一样。尽管对文法是什么有激烈的争论,但大家都承认文法的存在。
刘永济释《文心雕龙》中的“术”云:“一为道理,一指技艺。”①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也就是说,文法除了前面所说的形式法度,还有一个道理层面的法度。方孝孺《张彦辉文集序》:“不师古非文也,而师其辞又非也。可以为文者,其惟学古之道乎!道明则气昌,气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谓类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随之,不可强也。”②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2,沈乃文主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4册,第282页。刘基《苏平仲文稿序》也强调“理明而气昌,玩其辞想其人,盖莫非知德而闻道者也”③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4册,第230页。。仅仅师文法是不够的,还要“学古之道”。在这里,“古之道”当然是指儒家之道,实际上,诸子亦各有其道,唐顺之称之为“本色”,唐顺之提倡有法,但认为法度源于“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不只是儒家独占思想权力,因为这会造成“影响剿袭”④唐顺之著,马美信、黄毅点校:《答茅鹿门知县》二,《唐顺之集》,第293页。。道理层面的法经常以明道、载道、明理等冲击形式的法度,以至于明道诸说经常独占言说空间,文法仅被视为形式之法,受到理学家的极度排斥。后世在谈到文法的时候,多指形式上的法度,忽略了“道”在文法中的重要地位,忽视了思想规范作为规训方式的作用。文法研究如果没有“道”的环节,则不能理解“无法”与“有法”的关系。
由于长期以来的道法对立,极端的主张也开始出现。钱陆灿《答许青屿侍御书》:“近年授经之暇,稍得抽寻《史》《汉》、韩、柳、欧、苏文字,而论其大略:一曰论文则文,不必兼论道也;一曰为文必本于读书也;一曰近人之论文不当日专学欧、苏,至并欲追废《史》《汉》、韩、柳也。”文中提出的三个问题实为一个,即论文不必兼论道。论文与论道自六经孔孟之后分途为二,周、程、张、朱之文为载道之器,韩、欧之文为道之所寄,宋儒不必“文传其道”,韩欧也不必“道传其文”,故他主张二者分别独立,各论其法⑤钱陆灿:《调运斋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23册,第713,714页。。尽管文法的世界是统合在一起的,但毕竟经史子与集部之文还是有区别的,钱陆灿看到了这一点,故欲将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区隔开来。他也承认韩、欧、曾、苏之文为“道之支流苗裔”,也仍然肯定“道”在文章世界中的支撑作用。这样的主张在“文以明道”的正统思想之下颇为独特。道作为法是隐性的,最为醒目的仍是显性的“文法”,钱陆灿又曰:“盖文之有规矩准绳,起讫呼应,提纲挈目,错综参伍,俱归于文从字顺,此自太史公、班固至于韩、柳、欧、苏,其道同也。”对后人而言,这套文法存在于古代各类经典之中,“今初学者于庄生之《齐物》,楚词之《离骚》,《史记》之《货殖传》《报任书》诸篇,以类而推,能识其规矩准绳,起讫呼应,提纲挈目,错综参伍,而归于文从字顺”⑥钱陆灿:《调运斋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23册,第713,714页。。在文法的世界中,“有法”“无法”永恒地纠缠在一起,一旦强调“有法”,必陷于法度的束缚,且各有法度,各是其是。而一旦归于“无法”,则自是其是,陷于混乱。在无可选择的矛盾中,只能取其中,也还是承认文法的存在。
别集编纂是一个惯例与特例并行的出版活动,其间的复杂交缠疏理起来十分不易,亦难理出清晰的历史变迁轨迹,只能发现整体视野下的变化痕迹。但正是在这种混杂混沌之中,逐渐形成一种隐性的秩序。本文借助“差序格局”概念,疏理其间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变化,观察集部如何在刚性的学术体系中自处,如何以身份定位确立别集编纂的秩序。文法有道、法两个层面的意义,但在文法的世界中,法的层面不断强化,将经史子集统合在一起,形成复杂的文学态势,也是造成别集编纂缠杂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