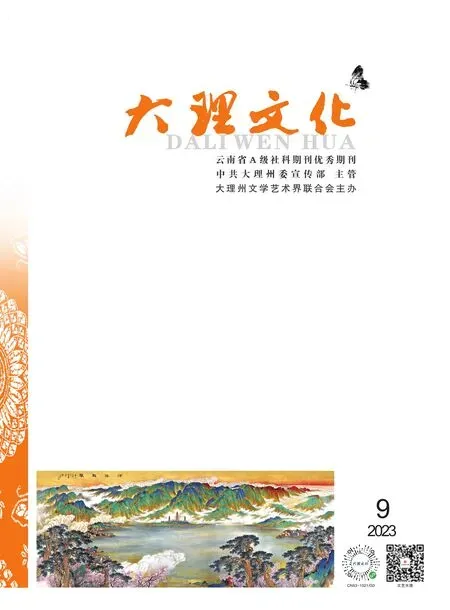如尘如归
●左中美
一
一座山立在那里,无形中,便给了人一种上山的暗示以及指引。
第一种上山的人,是住在山下的人们。
这日上鸡足山的路途中,车上有一位看上去40 来岁、普通话里带着白族口音的讲解员,其身份是鸡足山旅游公司的导游。一路上,她向一车人介绍着鸡足山的历史、传说、自然景观,每次讲解完时,总要带着一些不好意思地在后面加上一句:“你们都是大作家,比我都懂的。”听介绍,她的家就在鸡足山下的鸡足山镇上(鸡足山镇是一个白族聚居区),家里开着一间客栈。当年,她不到20 岁就到公司当导游,到现在已是20 多年了。正像先前那些驮游客上山的马匹和马匹主人们那样,这20多年间,除了休息日,在正常上班时间,她几乎每天都要带游客上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游客讲解着鸡足山。这么多年,我猜想着,她一定已记不清自己上鸡足山的具体次数了。和这位导游一样,鸡足山旅游公司的导游,大多都来自宾川当地,一年四季,他们一次又一次带游客上山,千万遍地为游客讲解着鸡足山的历史、自然与人文。
自然,当导游需得一定的条件,所需要的人员数量也有限。山下村庄和集镇(在15 年前我第一次到鸡足山来时,山下还只是村庄,尚没有形成集镇)上的更多人,便选择了上山卖东西,在山上的停车场旁卖各种小吃以及鸡足山的特产:包装成袋的各类菌干,以及笋干、地参等。停车场旁边的饭店,每上一道菜时也都要特别向客人介绍:这是鸡足山的××。往往,这些卖特产的摊子同时也都卖着各种款式、不同大小的香把,供游客们选购,带上山敬佛。
而那些单独卖香的人则上到了更高更远的地方,随着他们上得越高、走的路越远、付出的辛苦就越多,同样大小的香比在下面的价格也要更高。他们中走得最远的人,一直去到了山顶的金顶寺山门外。这些卖香的人,即便是乘上一段缆车,每日上山经营亦很不易,大多一早就要从家里出发。虽是为着经营和度日,一年四季顶暑冒寒地上山,已近乎是一种虔诚。
第二种上山的人,是那些历代的修行者。
历代以来上鸡足山或到过鸡足山修行的高僧名字,写下来有一长串:唐代的明智、护日;宋代的慈济;元代的源空、普通、本源;明代的法天、大错;清以后的虚云、自性……许多僧人远道而来,在此结茅修行,于是在这些高僧大德修行之处,一座座寺宇逐年修建起来。史料记明代的鸡足山上,“琳宫绀宇不知数,浮图宝刹凌苍苍。”有“大者七十二所塔院”,常住僧尼达数千人。至清代,“有寺36所,庵72所”,静室精舍遍布,谓“无山不寺”。
有一位意欲远道朝鸡足山的僧人,人虽未能如愿抵达,其尸骨却最终落葬于鸡足山,那就是明代僧人静闻。据记,静闻原为江苏迎福寺莲舟法师的法嗣,他禅诵达20 年,刺血写成《法华经》,发愿将此经供于鸡足山。崇祯九年(1636 年),静闻和尚同徐霞客结伴西行至湘江时,不幸遇盗落水,危难中拼力将写经举在头顶,幸不遗失。后静闻患病死于途中。临终前,嘱徐霞客将其骨灰带至鸡足山埋葬,以了其生前未了之愿。徐霞客受友之托,不辞千里劳顿,终将静闻的骨灰和血写的经书带至鸡足山,将其经供之于悉檀寺,并在山上为之建塔埋骨。
说起来,此番虽是三上鸡足山(第一次是15年前的6 月,一直上到了金顶;第二次是3 年前的3月,只到了半山的祝圣寺),却数次都未到悉檀寺,亦未得见静闻塔。此后半年,农历新春前夕,忽一日在微信上看到一段“鸡足山静闻大师铜像落成”的消息。——隔着380多年的时光,静闻和尚以这样的方式,又一次抵达了鸡足山。
第三种上山的人为数最众,那便是上山的信徒和游客。
集佛教名山的盛誉与雄险奇幽的独特风光于一身,让世界各地的无数人们不断向着鸡足山涌来。且民间传闻,鸡足山祈愿是很灵的,于是,许多人不辞远道,专程前来上山求学、求仕、求姻缘、求子。而当心愿得偿,祈求得报,那祈愿的人们便复又上山来还愿。一年又一年,山道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即便是在近两年疫情的持续影响之下,鸡足山年接待游客的统计数据仍达到了60 多万人次。而在民间朝山盛期的春节,鸡足山的游客数更是达到了日均万人以上。
相比于现今上山的便捷,一位朋友不禁感慨地忆起她30 多年前上鸡足山的经历:那时还没有上山的公路,卖香的奶奶和大妈们也都还在山脚的村庄。几个同学从山下的村庄请了香,一路徒步上山,历经大半日的艰辛跋涉,终于抵达山顶。夜里顶着寒冷住在金顶寺,一为第二日早起看日出,二来,若是当日再下山去,时间也已来不及了。“那是高中毕业的假期。几个同学就从山脚那么一路走上山去。许多地方都是窄窄的山道。寺里的被子也薄,晚上被冷得不行。”
好在第二日早晨,如愿看到了金顶的壮丽日出。
二
从金顶寺侧脚、上山缆车的终点站出侧门东行约百余米,路旁有一处大约数米、可俯瞰山下的临崖平台,因外无遮挡之物,山风凛冽。于此放眼下望,只见青山迷蒙,碧林葱郁;至远处,山色渐渐融入天际,随后过渡成了大片大片,如海浮云,如仙似幻。脚下数尺之外,即是斧削绝崖,稍稍侧身下望,不觉甚恐。搜寻近侧,不见有任何路径可下崖。然而,就是这无路可下的绝崖之上,却听说有大小数十窟历代僧人修行的静室,故而此崖又名罗汉壁。据闻,文化部门对这罗汉壁作过一些考察,那想是凭借了一些特殊设备的。而普通游客到了这里,只有临崖感佩,唏嘘抚叹。
鸡足山位于横断山脉东南边缘,属横断山块断带。远古的造山运动导致的同源熔岩多次宁静式喷发形成的玄武岩层被后期的断裂切割,产生大大小小的重叠断裂,形成了鸡足山危岩陡壁、石门石洞一层复一层的奇绝石景和独特山貌。又兼悉檀寺河纵贯其中,组合成峰险林郁、石奇水幽的独特自然风光。鸡足山的佛教文化,起于宋,兴于明。历代到鸡足山出家修行的高僧名录里,明代僧人为数最众。据大错和尚《鸡足山指掌图记》,此时的鸡足山有“大寺八、小寺三十有四、庵院六十有五、静室一百七十余所。”众多的静室,或是凿壁为窟,或是结茅作庐,或是打地为穴。在绵远的时间长河里,当一拨又一拨的修行者们觅得自性,归于大化,留下这些石壁洞窟、结庐遗址,让后来的人们依稀看见那些行至高处的背影。
罗汉壁虽无能得见,这日在山上却见到了一间倚崖而筑、半在地下的静修石室:出金顶寺山门,往左向后绕过金顶寺,从寺的西侧,沿着只能容一身、陡近直壁的“束身峡”手脚并攀而下,再沿一条腐叶掩面的蜿蜒小道西行约三四百米,便见林间现出一方朴素的小屋,独自居住于内的是一位看上去五六十岁的女居士,后来却惊讶地听得她说自己已经七十多岁,在此静居已有多年。小屋只有两个房间,作为厨房的一间开着门,可看到屋内的各样炊具。另一间关着门的,应该是起居室。屋前左侧有一座六尺来高、覆着斑驳苔痕的馒头状石堆,走近前去才发现是一间石室,一道窄窄的小木门上挂着锁,看得出已有一久没打开过了。“那里面原来是一间静室。现在空着。”女居士这样介绍。眼下,不知先前静修之人是已悟道远行,或是已然归入大化。独居于此的女居士,不知是缘于照护静修之人,又或是因某种不期然的缘起而上山来。——这一上山,竟忘了老去,不记人间日月。
过石室门前,上一道一米多高的坎,是一个向前突出若鼻状、面上宽约四五平米的石崖。应该是女居士的布置,竟在石崖前端置了一面二三十年前时兴的、现下已然没有了桌腿的长方形镶木边楚石茶几,而眼前情景,那几竟不见残,而是与石崖相得益彰,显出天地悠悠的开阔与古意来。细看那几面上的石纹,横向两侧是灰白色的“茫茫大雾”,其间以道道自然起伏的细而长的“峰峦”线,使大片的灰白显出一种立体感和层次感,有若浓雾中的群山层层向远迢递;在两侧“大雾”的正中,一道时宽时窄的青黑有若一条壮远的大江,滔滔拨开两侧群山,奔涌而去。整个石面看上去,宛若一幅航拍的万里江山图。而就在这壮丽的“山河”之上,一只如钵大小的红陶茶壶置于桌面一侧,里面以一撮红泥种了一棵微缩版的迎客松,枝上三五束“马尾”清绿朗然。
因着这一面石几,几个人于是若古人席地而坐,大着胆子凌虚笑谈间,女居士烧了水送上茶来。我们端茶坐于桌前,目光擦着壶中之松看对面的远山,视野所及处,千山绵亘,接入云天,万峰郁绿,塞天盈地。在靠近山脚一带,几簇村庄朗然散落于7月深浓的青绿之中,仿佛远远传来人间的消息。
天地浩翰,河山万里。日月精微,一壶即住。
三
华首门是鸡足山顶峰天柱峰西南天然绝壁上的一道关闭着的巨大“石门”,苍黑的石色,仿佛亘古的时间厚厚凝结在上面。石壁陡近直角,从脚下往上仰去,只见这刀削斧劈般的绝壁直摩苍穹,在那苍穹之上,便是金顶寺的大殿。我在后来回想起来时,似乎记得靠着观景平台外侧的石护栏,可隐隐见金顶寺大殿的飞檐一角露出于绝壁之上,又或者,这是我的想象罢了。

这道巨大的天然“石门”,它的确切数据是高40米,宽20米。中间一道垂直下裂的石缝,将石壁分为两扇“门”,中部有距离大致相等的微微突出部分,形若“石锁”,“门”头的“檐口”“门楣”亦清晰可辨,整座巨大的石门镶嵌于近数百平米的绝壁之上,宛若一道登天的关门。
传说,这华首门乃是释迦牟尼弟子饮光迦叶守衣入定处,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载:“迦叶承旨主持正法,结集既已,至第二十年,厌世无常,将入寂灭,乃往鸡足山。”迦叶至鸡足山后,进入禅定,奉持如来附嘱之金襕衣,以待弥勒出世而授之。迦叶最后入灭于鸡足山。后世虽有人指出,迦叶入定的鸡足山是在印度境内的摩揭陀国,并非是此鸡足山,却不能改变鸡足山千年来被奉为迦叶道场而在佛教界和佛教徒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离开女居士的崖畔小屋向东返回,经“束身峡”脚,沿斜向上的曲折石梯来到华首门下时,见这里正在进行一场诵经法会,一只长而高的案桌高置于观景平台前端的石门下,上贡之以鲜花、果品以及相关法物,一位法师在前领衔,其余四五位僧人在旁随诵,只不知所诵何经,是何法会。在诵经师徒的身后是众多斑斓的游客,有的端然坐于凳上,凝神听着诵经,有的则懒散地倚靠于石护栏上刷着手机,或是侧身向外看着风景。法案右侧不远处,石壁脚下有一处如钵大小的泉眼,听说此泉可救眼疫,于是,待诵经结束时,很多人都上前去蘸泉拭眼。
在观景平台的西侧,有一方木架瓦头、飞檐斗拱的四角正方形楼阁,阁为三层,第一层在平台之下,上面两层高出平台。在阁楼顶楼向东面对着观景平台的木壁上,居中一个直径不到两尺的圆孔:听说这楼上祀有铜铸太子一尊,临窗高立,游人有朝山求子的,便用硬币于平台上往那圆窗里投进去,俗称“打太子”,据说打中“太子”者可得子嗣。因听得此说,一些人踮脚甚至跳起上望,却并不能瞧见那窗内的“太子”。
摩天石壁华首门,洞开圆窗的太子阁,如钵大小的救疫泉,诵经的庄严僧徒,若听若离的各色游客……而我后来一直没有从手机上删去的一张图片,是来到太子阁下时在一楼的阁门前拍下的,在那上面,位于居中的是一只盈满清水的白色塑料桶,水上漂着一只明艳的黄色塑料水瓢;在这桶的左侧是一只同样的白色塑料桶,大半桶清水上面,浮着一根清绿的苦瓜和一把从这山中采来的野韭菜;右侧地上是一只水滴形的锑漏盆,里面是我说不出名字的一种绿色野菜。一段蜂蜜黄色的塑料水管从水桶的后面绕过来,管口搭在那野菜上面,看得出,有人正要清洗这野菜,此刻因有什么事而暂时走开了。在这一盆野菜的侧面和后面,分别是一只不锈钢小盆、一只红色塑料小桶、一只铅灰色带提耳的大铁桶——一面是亘古坚硬、紧紧锁住的石壁,一面是柔软和日常的韭菜、苦瓜、不知名的野菜、清水以及塑料桶,人们在中间,听经、洗眼、“打太子”,在尘界与佛界之间寻求救度与慰藉。同行的向导引传说介绍说,华首门乃“三千年一开”。“三千年”后,若是当真有人遇缘得见此门打开,只不知在那门内,是天是地?是尘是佛?
关于这华首门,有一道景观被列为鸡足山八景之一:华首晴雷。说是夏秋多雨时节,因着鸡足山独特的山体构造,远处山谷时有雷雨大作,而华首门前却晴日当空,雷声和闪电从远处山谷传来,在此碰壁后,回音反射,声震寰宇。这日上山途中,天空虽多次降下时疏时密的雨水,却一直没有雷声。此刻到了门下,雨水一时收住,远近山谷中但见浮沉变幻的茫茫云雾。
离开华首门下,石阶继续斜斜东上,可向上绕回金顶寺,又或继续东行前往缆车站。这时候,从天上又落下细密的雨丝。望身后,不见晴日,不闻雷声,只听着石崖下的人声渐去渐远。
四
金为五行之首;顶为事物本体之高,头顶、屋顶、山顶——事物至此已达到了自身的最高处。
位于鸡足山最高峰天柱峰顶的金顶寺,是鸡足山最高的寺庙,海拔3200多米。而这里,也几乎是所有上鸡足山的人必要到达的最终目的地。这其间,除了为一赏鸡足山高处的壮美风光,更多地,想必还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修行自渡。
所谓修行自渡,这里面有着层次的差别。
最初级的自渡者,不辞长路(百里、千里乃至万里)来到此地,努力从山脚抵达山顶。许多早年上过鸡足山的人都知道,直到30多年前,鸡足山还没有上山的公路,人们上鸡足山,是从山下的村庄便开始一路步行上山的,从山下上到山顶,需得历经大半日的艰难跋涉。现今从缆车起点站到终点一段,也还保存着窄窄的山道,沿着山中峡谷一路曲折上行。当中部分路段之陡窄,几乎不容二人并立。因现今的缆车路线正是沿着这一峡谷而建,故而乘坐缆车上下山时,可一路清晰看见身下的山道。偶尔,也能见有人执意在这山道上走着,或是正在努力上山,又或是已朝过了山,正身心轻快地下得山来。而今天绝大多数上山的人,只是下了缆车后从缆车的终点站走到金顶寺,总共只有数百米的石阶步道——即便是如此,人也已经到过了最高处,在某个时间里、在具体的空间意义上以及少许的精神意义上到达过了自我的高处,一些人在那高处的寺里烧了香,许了愿,在内心里,获得了某个方面和某种程度的暂时抚慰和安宁。自然,这一层的人数是最多的。
更上一层的自渡者,他们为他人铺路。鸡足山中部早年的骑马道,宽约一米二三,中间铺的是大小不一的卵石,两侧镶以面宽约20厘米的条石。马道长约四五里,蜿蜒穿行林间,直到缆车站。从缆车站往上,山路变窄,路面为土路和石条阶梯相间向前。因为地势的限制,一些地方的石阶石长不足两尺,面宽只约半脚,如此山道,行尚且不易,铺筑更且艰难,更何况这些历经久远岁月的石阶步道,在当时全靠人力修造,其间艰辛自不待言。山上尤为使人惊叹的,是金顶寺西南侧一段名为“束身峡”的石梯,因着地势,此处石梯窄只盈尺,陡近直角,以至于需要在石梯两侧焊上铁栏扶手,借以助人上下,而即便是如此,人行梯上仍不免骨颤目眩。如此“天梯”,使人不禁惊叹于修筑者之坚韧与伟力。据闻,在旧时,许多人上山铺路是作为一种自修的,所谓积德行善是也。后来的铺路者,虽或得了一些劳酬,然而,任何艰辛和执著的劳作,本已自带有修行的意味。现今的鸡足山上,历代的修筑加上今人的铺设,几乎所有的步行道都已铺筑石板、石阶——均经历凿石,运石,最后铺石成道。千百年来在这山上铺路的无数人们,经由这艰辛的劳作,抵达了某个高处的自己。
再上一层的自渡者,便于高处修寺建塔,以此为“渡口”,自渡并且渡他(第二层次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意义)。“自古名山多佛寺”,修于绝崖峭壁之上的亦不在少——以看似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达至修行之途。鸡足山金顶寺所在,明代弘治年间便建有庵,后世又陆续建有普光殿、天长阁(一曰方长阁)、观风阁、善雨亭,“殿亭四周,筑城环之,城四面架楼为门,南观云、北观雪、东观日、西观海。”纵观中国名寺之历史,几乎绝大多数都有焚毁重建的经历,其间原因,一来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木质结构建筑,火患一直是除自然灾害之外的最大隐患;二则寺庙又是终日见火之地,极易引发火害。金顶寺的历史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记载:清康熙三十年(1691 年),殿阁俱焚,只留铜殿独存(此铜殿为崇祯年间黔国公沐天波移中和山铜殿至此)。寺被焚毁之后,只在次年,便又展开了重建。重建者谁人?“总督范公、提督诺公及姚安土官与僧人重建。”不止建寺,历代的捐建者和寺僧们还在寺内建塔。1929 年以前,寺内的塔名为光明塔,1929 年得省府拨款重修后,易名为楞严塔,塔高达41 米。早先上山时,进入塔内,沿着嘎吱作响的螺旋式木梯登上塔的二层,倚围栏放眼远望,四方美景尽收眼底。现如今,历史近百年的高塔,寺里已不许游客攀登,于是,许多游客便以绕塔和在塔基上撒硬币作为祈福的一种方式。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遇。”对于大多数的上山者、各种意义上的修行者,各自所付出的努力与坚韧,大抵总是为着现世的祈愿和福报,完成的原是一时、最长也就一世的自渡,能够最后高于山,高于寺,高于塔,高于时间和生命(此世)而达至最高之修行的人想来并不多。而佛若有慈悲,我想,佛的慈悲也便在这里:人有多大的愿力,便做多大的修行;人能见多少的自性,便得多大的开阔——佛从不责难。佛默然不语。
五
客观上,对于一座山,人不论以怎样的方式去读或者去写,最终,都或难免是一场辜负。
古往今来,无数的人上过鸡足山,每个人上去,他的目光和内心读到的是他的那座鸡足山。甚至于,一个导游带着一群人,一群人听着同一段讲解词,而这讲解词落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心里),引起的感觉、想象以及思考(如果有的话)也都不一样。就是同一个人,一次一次上鸡足山,每一次也会有不同的所见和所感。鸡足山顶峰的四景,日出,云海,洱海,雪山,同样的景观,你见和我见亦不一样。
这日在山上,在前往崖畔石室的途中,道旁树下见一面石桌,桌面稍凹处积了一汪浅浅的雨水,有人因走去桌旁拍照,惊喜地在这桌面的积水里看到了斜对面楞严塔的清晰倒影,继而拍下了塔与倒影同框的绝美照片,并且想到,若是将这照片放到网上,许多人便是想破脑袋,一定也想不出它到底是在什么位置、以怎样的奇特角度拍下的。塔高40余米,而积水浅若甲盖;从石桌到高塔所在的金顶寺,中间相隔着一道深幽大箐,直线距离有数百米之遥,竟能对影同框。这样的七月遇雨的天,这样的一群行经此地的人,那样的一片雨水稍稍歇住的半晴的天色,一个人于千百世间的那样无意的一瞥,于浅浅积水里,遇见那惊鸿照影般的塔影——千般人意不可得,唯有天时成此遇。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个人所见的鸡足山,自然便有了各自不同的风貌。落到笔下,他写的云动,我写的云静;他写的花在风里乱开,我写的花在道旁一枝独秀。便是徐霞客当年写的《鸡足山志》,那也是徐霞客版的《鸡足山志》,若是,当年丽江木府不是请的徐霞客撰《鸡足山志》,而是别的某人,那便又是某人版的《鸡足山志》了。又或,徐霞客不是在1639年秋第二次上山时修志,而是在1636年首上鸡足山时所撰,那也又是另一种情绪里的鸡足山。“晓共云关暮共龛,梵音灯影对偏安。禅销白骨空梦,瘦比黄花不耐寒。”(徐霞客《哭静闻禅侣》)
今年年后,多日冷雨中,鸡足山顶降下一场大雪,宾川的师友写下一篇《鸡足山听雪》,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报纸的版面上图文相配,在那一幅以斜上角度拍天柱峰和金顶寺的大图上,洁白的雪落满山峰,覆住高塔——这又是属于他的鸡足山。在画面之外,有耳朵听到了满山大雪落下的声音。
作为一座名山,在电脑的搜索页面上,若是输入“鸡足山”三个字,会跳出来650 多万条搜索结果。这样的一个数字,它意味着巨大和纷繁的差异:这样多的“鸡足山”,它们当中没有两座是完全相同的。然而,在这无尽的差异里,或许也有一点是相同的和注定的,那便是辜负。
一来,囿于人的认知和见识的限制,每一个人所“见”、所写下的这座山都将注定是自我的、局部的和片面的,包括作为某种客观的和总括的志书。没有一个人对一座山的认知(对这座山的自然,对它的文化,对以这座山为某个切面所呈现出来的人类文明以及整个世界的性貌)可自诩为是完全和绝对的认知。由是,当你一旦下笔对它进行某种讲述,便无以回避地踏入了你的自我和片面。
二则,人无以抗拒地受限于肉体生命的短暂。人活不过一座山,大多数的人,甚至活不过一棵树,一寺宇。有许多树,还有这山上的好多寺,它们的历史往往是百十甚至数百年,而人活一世匆匆几十年,古人感叹“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的情形好一些,然能活百岁者依然寥寥。面对着时间的无限以及认知的无垠,当一个人还未来得及自见自纠自我的片面时,便难免化为了无证无错的尘土。斯时,山依然在这里,天依然在这里,那些壮阔的风景依然在这里。后来之人上得山来,唯见山之峨峨,石之苍苍;日之荡荡,月之渺渺。
那便,认了这微渺以及辜负。看天地大化,任芥子须弥,如尘如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