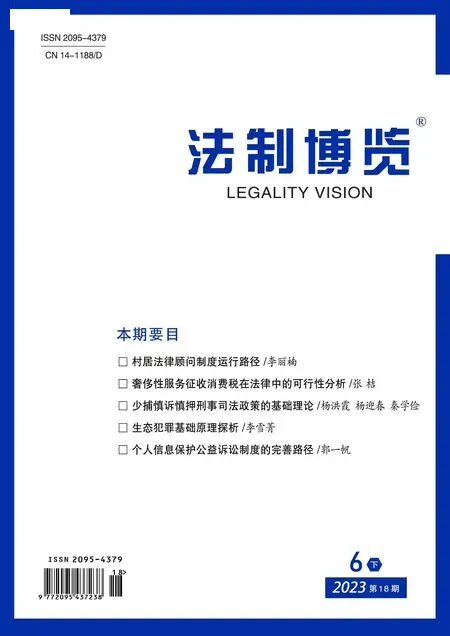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困境以及路径分析
庄海涛
内蒙古承达律师事务所,内蒙古 包头 014030
随着现代媒体的迅猛发展,我国民众已经从原本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了网络信息的发布者以及传递者。而一些发生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攻击等行为,也可以在网络平台中传递,并随着事态的扩大逐渐发酵成为网络群体欺凌的暴力现象。我国自2018 年之后,随着“粉丝经济”的持续性发展,许多偶像的粉丝群体也在持续性扩大,这也让人们所处的网络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较为严峻并引起社会大众关注的网络暴力事件。例如,网红saya 与孕妇争执事件、割腕自杀后为狗偿命等热点话题都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而这些网络暴力行为不仅在经济方面为受害者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甚至还会影响到受害者的人身安全,这种行为也显然超过了民事以及行政法律的治理范围。针对这一现象,国家网信办开始出手,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相应的刑事法律条例,规制这种网络暴力的现象。但目前,在刑事法律规定中大多数暴力现象的法律条款都是针对传统的暴力行为,不能针对网络平台中的暴力行为进行规制和管理,这也导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网络暴力行为刑法规制缺位的问题。因此,进一步探讨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有效策略,也成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一、网络暴力刑法规制当前存在的困境
(一)严重的网络暴力问题频发
数据资料显示,近年来,在我国的网络平台中一些较为严峻的暴力倾向和问题频发[1]。例如,2016 年引发全国轰动的江某遇害案中一位青岛阿姨无辜躺枪,在短时间内就接收到了来自网络渠道的辱骂信息。再例如,2018 年引发社会震惊的重庆公交车坠江案件中,无辜的轿车司机也被翻天覆地的网络暴力语言所侵害。2019 年,大连市一位13 岁的男子被网络传言认定为杀人犯,在流浪了近10 天之后出现了精神失常的现象。而如此严重的网络暴力事件,不仅意味着每一位社会公民和网络的使用者都可能会成为网络暴力的侵害对象,同时还体现出了当前网络暴力打破社会法律规则、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问题,在网络上一些不真实的消息也让原本的人伦道德被扭曲。例如,广东人肉搜索案件中服装店主人肉搜索中学生徐某,随意暴露他人消息后导致一个尚未正式踏入社会的未成年少女最终不堪精神上的重负跳河自杀。虽然在事后,服装店店主也由于在网络平台中侵犯了他人的权益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付出了12 万元的赔偿代价,但是网络中的伤害却一刻都没有停止,网民们也借助网络这一平台继续肆意诽谤和侮辱他人,完全不顾及他人的隐私和权益,企图通过法律之外的方式伸张正义[2]。这样的判决结果让整个社会处在了滥用私刑和凭个人意识随意侮辱他人的恐慌情绪中,显然,与我国依法治国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驰。根据2019 年2 月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相关统计报告,中国网民参与互联网络活动的准入门槛没有较大的局限性,而在网民中未成年人的比例相对较高,这些未成年人不具备判断是非的能力,可能会成为网络暴力事件的助推者,甚至还可能会成为网络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这一惊人的数据也凸显出网络暴力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如果网络暴力的现象无法得到有效的遏制,将会让社会陷入无序和恐慌的局面中[3]。
(二)刑法规制与网络暴力的行为特征不符
目前,在我国的刑法构架中,大多数与网络暴力有关的刑法判决都是以诽谤罪名定罪,或者是以侵犯了公民的个人隐私以及寻衅滋事罪作为判处的依据。但纵然如此,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网络暴力事件的发起者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刑法惩处。在网络信息如此发达的当今时代,考察两年前的数据发现,截至2020 年,在我们的身边,只有三起网络暴力案件最终进入了刑事诉讼的环节。这三起案件分别是2013 年广东“人肉”搜索致未成年人自杀案、2014 年云南孟某诉讼刘某“人肉”侮辱案件,以及2016 年安徽食品店主自行上诉人构成诽谤罪。然而,在这三起典型的案件中,只有广东服装店主以侮辱罪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云南的“人肉”案件以及安徽食品店店主案件法院认为并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情况,因此,被认定不构成犯罪行为。由此不难反思,如此频发的网络暴力行为却没有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是因为网络暴力行为构成的犯罪后果不严重,而是由于网络暴力行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的裁判规范不兼容[4]。
1.在刑事裁判中很难以侮辱或诽谤的罪名判定网络暴力行为中的语言性暴力现象。根据《刑法》中与网络暴力行为相关联的规定,言语上的侮辱以及诋毁是网络暴力行为的主要呈现方式,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言语暴力的形式,判处的条件,需要在公众场所随意捏造事实或辱骂他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才能被记入刑事案件中。而《刑法》条款中所规定的一些言语侮辱行为,指向的是案件中当事人的辱骂以及一些含有侮辱性的动作等行为方式,这种暴力行为带来的后果与动手暴力行为带来的后果程度相同。例如,在公众场合辱骂卖淫的女子为“婊子”等一些带有人格侮辱性的行为,就属于典型的语言暴力行为。然而,从目前关于网络暴力的一些典型案件来看,第一,关于网络平台中群起而攻之的语言暴力行为,只属于言论的自由发表,却不能等同于现实生活中对于受害者的侮辱,因此,在刑事裁判中,不认为这种言论发表行为具有侮辱的性质;第二,针对一些热门的暴力事件,很多网友传递的信息并不是凭空而来,更多的是一些自媒体为博得人们的眼球对文章断章取义并自我评判,才会导致大量的粉丝跟风指责,这种言论的发表并不是空穴来风,但这种语言确会成为伤害当事人的武器,一刀刀“割断”当事人精神的防线,但在刑法判定中,也不能将网友言论的发表等同于诽谤罪行。而网络暴力更多的是借助群体的语言攻击,对受害者带来精神上以及心灵上的折磨,只需要一些引导性的言论和跟风的谩骂,就能击垮受害者的心理防线。
2.难以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人肉”搜索性的暴力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内容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要呈现方式就是随意向他人提供公民的隐私信息,或通过贩卖的渠道提供信息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窃取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5]。但是,目前在网络中较为常见的人肉搜索暴力现象,却很难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判定标准相互对接。“人肉”搜索主要是一种过激的窥探行为,这种行为虽然也导致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在公众平台中暴露,但是与直接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表现方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例如,在网络暴力行为中,过激地查找当事人的个人信息虽然影响到了当事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当事人信息并不一定是通过非法的行为获取的。以我国的微博平台为例,很多受害者都会将个人的信息,例如,一些生活的艺术照放置在个人的主页,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的个人信息本身就是对外开放的,只要网络暴力者稍微进行查找或拼凑就能够得到较为完整的个人信息,并不需要通过非法的渠道收集或贩卖个人信息。除此之外,在开放的网络平台中,许多个人信息也会被熟悉的同事或朋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外透露,而施暴者也可以借助公众平台,轻易将获取的信息公开处理,并利用自己的道德标准衡量受害者的行为方式,进而引发群体性的围观和谩骂,这种人肉搜索所带来的网络暴力行为后果,相比于其他的隐私犯罪后果更加严重。特别是一些被侵害的对象是普通的“素人”时,当自己的信息无端被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中,其基本毫无还手之力。往往在心灵和精神处在双重崩溃的边缘时,就可能会借助一些极端的自残行为选择逃避[6]。
二、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出路探索
(一)网络暴力罪判定的过程中应当坚守刑法谦抑性的原则
《刑法》是衡量人类道德底线的基础保障法律,也是保障社会安全的底牌。为了避免刑法功能应用范围的扩大化,针对严重行为的网络暴力定性事件,也应该遵循谦抑性原则。通过细致的分析发现,刑法中所涉及的谦抑性原则,其实就是说,如果在网络侵害案件中,可以采用其他的民事或行政法律进行处罚和约束,就不必要上升到刑法。如果其他的约束手段已经无法判决时,才能够寻求刑法的帮助。也就是说,当判定危害行为是否被纳入刑法规制范围时,就必须要考虑这一危害行为是否存在社会其他法律无法有效治理的现象[7]。而目前,我国的民事法律以及刑事法律在对网络暴力行为治理的过程中体现出了无力和不足的现象,因此,需要将网络暴力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此外,在我国《刑法》中原有罪名的暴力行为特征与网络暴力行为特征不兼容的情况下,应当根据网络暴力行为的特征增设新的罪名[8]。
(二)坚持解释优先的原则
目前,司法部门的相关学者希望能够对现有《刑法》中的罪名范围进行新的解释,使刑法中的罪名符合网络暴力案件中的典型表现特征。但无论怎样寻找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还是有很多网络暴力实践行为无法与《刑法》中已有的罪名相匹配。也就是说,现有的刑法针对传统暴力行为的定义,无论怎样扩展法律方面的行为解释,都不能直接将“人肉”搜索或者群众的网络言语发表解释成侮辱以及诽谤。而网络暴力行为本身就借助了网络环境开放、自由和无限延伸的特性,网络暴力的行为又能够引起公众的围观,具有煽动言论和群体性攻击的特征,属于一种新型的侵害方式。因此,对于网络暴力行为新罪名的设定并不是对原有罪名的解释,而是要解决网络暴力行为的刑事责任追究问题[9]。
(三)以类型化的立法方式对网络暴力罪名进行条文的设置
网络暴力行为在实质上也具有网络语言攻击、“人肉”搜索攻击以及寻衅滋事攻击这三种类型。从暴力的行为角度来看,不同类型的网络平台暴力伤害的对象往往是较为复杂的群体,但事实上,这些暴力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都指向公民的人身权利。因此,将网络暴力行为作为新的罪名纳入刑法之后,应当归类于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犯罪类型中。具体来说,可以将网络暴力行为纳入我国《刑法》的第二百四十六条侮辱罪、诽谤罪之后,作为其后新的处罚条例。例如,可以将此种网络暴力行为的刑法处罚依据设定为:“通过不良的网络平台言语行为或煽动其他网友对他人进行公开的语言抨击、向外透露他人隐私信息,导致受害对象心灵精神双重压迫,对于情节严重者可以采取判处有期徒刑、拘役或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措施。”如上所述,将情节严重作为判定网络暴力行为是否为刑事犯罪的入罪依据,目的在于能够与传统的行政裁判形成对比。也就是说,对于未带来严重后果的暴力行为,可以通过简单的行政处罚予以警告。而对于一些引发社会恶劣反响的网络暴力行为,就要根据罪行追究当事人相应的刑事责任[10]。
综上所述,生活在信息互联的网络时代下,并不意味着开放的网络平台就能成为肆意释放恶意、随意评判他人并侮辱谩骂的场所,更不能成为屏幕另一端暴力行为的“保护伞”。因此,必须要根据不同的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分类处罚,并根据网络暴力行为情节的严重性进行相应的刑法规制,不要让随口而出的一句话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