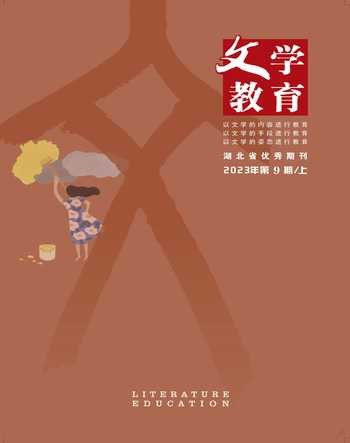从《中国文学史》看林庚文学教育的特点
于萌
内容摘要:作家进入大学后,学术研究体制和教学要求促使其重新审视传统文学、借鉴外国文学,为其深入而系统化的思考提供了重要契机。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47年,是其在厦门大学任教十年的教学成果,这部文学史因其作者特有的诗性逻辑和诗人笔法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林庚的文学教育特点,从中也可以窥见现代作家的大学文学教育工作因其文学创作经验和敏锐审美能力的直接介入,与普通大学教师的教学相比,在文学教育上所具备的全新质素。
关键词:林庚 《中国文学史》 大学 文学教育
在现代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是文学生产、传播的重要场所,塑造着新文学的发展路径。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作家兼大学教师凭借自身的身份特点,成为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之间最有力的沟通者。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各个阶段各类大学都活跃着兼具作家身份的教师,这批人参与大学文学教育,为文学教育活动增加新的质素,进而影响了新的文学教育传统的形成。
现代作家对古典文学的很多考察,最初都是为了大学文学教育的需要。这就包括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郑振铎、胡云翼、赵景深、谭正璧等许多现代作家的文学史著作。他们从为了新文学的诞生而与传统文学决裂到为了新文学的发展而重新审视传统文学,这除了与新文学自身发展程度有关,也直接源于他们所处的大学学术环境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策略。大学学术生产迫使作家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和研究文学,从文学历史、理论、思潮、创作方法等多方面对其展开研究和讨论。无论是外国文学还是古代文学,现代作家都为其注入了新的质素,切实地影响了大学文学教育的走向。林庚的《中国文学史》一书出版于1947年,正是其在厦门大学任教十年的教学讲义成果,这部文学史因其作者特有的诗性逻辑和诗人笔法呈现出独特的面貌,是我们直观深入研究林庚文学教育特点的绝佳材料。
一.林庚《中国文学史》的产生
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处于现代教育转型初期,学科建设并不完善,系统权威的教材也相对缺乏。许多大学教师都需要自编讲义,在大学执教的现代作家也不例外。现代作家的大学文学讲义既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凝聚着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也是他们文学教育理念的具体呈现。经历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史撰写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到了四十年代,文学史的编撰明显减少。相比较战前一些带有史料汇集性质的大部头史著,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呈现出注重个人文学理念和话语方式的面貌,这除了与战时环境中资料搜集不易有关,也与文学史编写观念发展以及研究者个体特征与心态相关。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无论是编写理念还是角度、标准和语言都是属于其“个人话语方式”的创作。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非常典型地诗人的文学研究。林庚出身清华大学中文系,在进入大学执教之前,林庚一直是一位纯粹的新诗人。林庚身上具有浓郁的诗性气质,1928年林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两年后转入中文系。之所以转入中文系,是因为诗给了他充满活力的感受,他也“希望通过诗歌实现人生的解放”[1]。自此林庚醉心于新诗的创作,就连毕业论文都是以一册新诗集代替。
进入大学执教是林庚研究文学的起点。其撰写中国文学史的计划也开始于他在民国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这门功课。林庚曾说:“1934年我在北京民国学院教书的时候,没有可用的文学史,我就想自己编一本,而且这本文學史能跟新文学衔接,而不仅仅是把古典文学讲完就完了。我那时是在写新诗的基础上,作为一个作家去写文学史的”[2]。林庚在解释自己编写文学史的原因时曾说:“一方面觉得大学里中文系的课程,历来偏重于旧的,而中文系学生们的期望,却往往是新的;但实际上,就新文学已有的历史与材料上来说,的确又没有多少课程可开。这事实上的缺陷,催促着我发生了沟通新旧文学的愿望,这原来正是文学史应有的任务”[3]。文学史讲义的性质也影响了林庚的撰写风格,林庚所说:“到了厦大后,我把精力集中到文学史上了,光是这些题目就很能吸引同学,所以有好些外系的学生也来听课,因为题目很吸引人。我上课时,把题目写在黑板上,写上‘文坛的夏季,台下的学生就很兴奋”[4]。从这个角度来说,作家的文学教育其实也在塑造着他们对文学的研究,无论是他们对文学的理解,还是文学研究的面貌。
民国时期,很多学科课程处于初设探索时期,教学形式和内容相对自由,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没有一定之规,陆侃如曾回忆:“自五四前后到抗战初期的约二十年左右,各校中文系课程的开设是所谓‘自由的,系主任爱怎么办便怎么办”,及至抗战时期,虽然有了部颁课程标准,但战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根本无暇严格规范大学教育,对于大学老师来说,他们就有了更加自由的教学空间。具体到文学课程的讲授,无论是进度详略还是作家作品评价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以“‘独出心裁为贵”[5]。林庚的《中国文学史》便是这种相对自由的环境中“独出心裁”的产物,是其“一家之言”。1949年后林庚曾几次想修改此版文学史,可总是感到“无从下笔”,因为这部文学史不仅仅是一部教材,更是学者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对文学的理解。针对这册文学史,林庚曾说过,“当时虽然有些想法不够成熟,有些表述也还有待斟酌,但是我的思想高度却是年轻时确立的,我从来没有超过那个高度”。对于林庚是否超过当时的思想高度还需要深入考察,但确实表明了林庚自身对这一文学研究思路的高度认同和肯定。作者以年轻诗人特有的敏锐和慧心抱着对文学的极大热情投入了文学史的写作,再加上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具有不可复制性,使得研究愈显珍贵。
二.林庚《中国文学史》的教育理念与特色
林庚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此时正是杨振声和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之初,他们激情昂扬地以“创造我们这时代的新文学”的理念改造中文系。积极地在大学提倡新文学,重视新文学的研究与创造。林庚是这样的理念培养出来的学生,甚至他的毕业论文都以新诗集的形式代替。这也成为之后林庚新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目标。从大学时期开始创作新诗起,无论是在思想意识中,还是在实际创作中,林庚一直保持着对新诗的关注,这种诗人本色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研究和教学。
林庚对古代文学生命动力的探寻实际上有着为新文学建设服务的明确意识,“展示旧的”正是为了“预言新的”。他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理念,首先来源于他新文学作家的立场,他说:“我在写文学史的时候总想着新文学的发展,总想为新文学找一些可以参考的经验”[6]。
在诗选课上,林庚曾为学生谈到为什么要学习古诗这一问题时,林庚认为中文系的学生更应该创造未来而不是研究过去。同时应警惕研究在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学习中迷失方向。林庚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同样是从建设新文学的角度出发的。对此他清楚地表示自己写文学史着眼点是在未来,是为新文学服务的。他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启蒙”、“黄金”、“白银”、“黑暗”四个时代,这其实也是依据胡适等人所提倡的进化论的历史哲学来描述文学发展的趋势,最后一章则写明了现代白话文的出现带来了“文艺曙光”。这种建构在讲授文学史发展的同时也从学理上确立了新文学的合法性。
除此之外,林庚的文学史叙述中,许多价值尺度和评判标准都是一句五四新文学的精神,林庚的文学史研究正是其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具体呈现。他从为了新文学发展而展开文学史研究的思路出发,最为看重的就是文学的创造性,这也体现在其文学教育上。他说:“我主要把重点放在创造性上,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地方,我就少讲,像汉赋,我讲得就很少,而在创造性多的地方,像唐诗,我就花很多力气去讲。所以在我的《文学史》里,对整个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的态度就是,什么时候最富于创造,我就重点强调,什么时候创造性弱了,我就谈的简单”[7]。林庚从文学本身出发研究文学,坚守文学独立的价值,在他看来文学应是无功利的:“这‘为了什么的文学在我向来好比女儿家不能自立必得出嫁”,“在宇宙间只有人会追求永久的‘真‘美,在宇宙间就只有人有那崇高不沾功利的灵魂,这追求乃使得人的灵魂无限生长起来扩大到整个宇宙中去”[8]。
林庚以自觉的文学意识去研究文学的发展历程,立足于具体的作家作品,运用敏锐的艺术感觉和发达的美学体验做出自己的文学观察与判断。他对作家作品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极富创造性,挥洒自如而又酣畅淋漓。
朱自清曾评价林庚的文学史写作:“著者是诗人,所以不免一方面特别看重文学,一方面更特别看重诗”[9]。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以文学本身为核心的,他得出的结论和观点都是紧紧围绕着文学作品,没有偏离文学的本色。林庚对古代作家文学情感和表达方式的解读是鲜活而细腻的。如他认为李白的诗“如一只金箭射在当时的文坛上”“如长风巨浪,惊醒了一代人的耳目”,“李白天才的豪放,那正是男性表现的极锋”[10]。
将体现时代特征的“思想形式和人生情绪”予以纯然文学的关照,其实也是一种创造,是对文学的文学阐释。从27岁到37岁,林庚在厦门大学任教的十年,无论是从诗人的角度还是学者的角度,林庚都处于创作的旺盛期,林庚一直提倡人的一生要多保持些少年精神,最有希望的是富于少年精神的时代[11],而这部《中国文学简史》正是一部“富于少年精神”的文学史。无论是作家的评说,作品的赏析还是创作特点的把握,文学潮流的思辨,都带有自己的诗性色彩,才华横溢,直率热烈,处处体现作者对文学的热爱与文学研究中饱满的激情。虽然对“史”的轮廓勾勒过于简略,缺少详细的考证与整理,但在作者在自己才性基础上做出的体悟与表达,更加深切与独特,也更加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林庚后来没有改写自己厦大版的《中国文学史》,只是在晚年将“黑暗时代”改为了“黑夜时代”,一字之差,其实可以看出其文学观念的变化,最初编写文学史的林庚,其目的在于突出新文学,因此采用含有价值褒贬色彩的“黑暗”来形容新文学到来之前的文学阶段,而在新文学的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多年之后,“黑夜时代”的命名更倾向于从林庚自身注重文学创造性的理念出发来理解文学。总之,林庚的诗人特质为他的古典文学教育笼上了一层诗性的光芒,随性而通脱。
宁宗一在谈到阅读林著时说“著作中盛唐诗一章中的描述简直是一首抒情诗,作者把古人的诗心、自己的激情融为一体,于是读者的心随着作者一起激荡,一起进入盛唐诗那自由、开朗、奔放的意境中去,而文学史的本相全然未曾丢失”[12]。以这种方式对文学的呈现,单纯从学术著作的角度来看,也许会被诟病史识不足,但如果回到文学史作为讲义之初的文学课程上,通过林庚充满感情而富于感染力的讲述,其取得的教学效果要远好于文学史知识的直接传达。林庚的学生曾回忆其授课时的情景,他说“二十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先生的讲课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诗人的气质和风采。先生身着丝绸长衫,风度翩翩,讲课时不读讲稿,只是偶尔用几张卡片,但是思路清晰,且旁征博引,让我们一睹文学世界的万千气象。讲到《九歌》中‘帝子降兮北诸,目渺渺兮愁予。娥娥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和宋玉《九辩》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如何开了悲秋的先声,将汉魏数百年的诗坛笼罩在一片秋风之下,又怎样余波袅袅,在此后的诗文歌赋中不绝如缕,先生用的几乎是诗的语言,而他本人便如同是诗的化身。我记得当时我们完全被征服了。全场屏息凝神,鸦雀无声,连先生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这情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诗的魅力和境界”[13]。在学生看来:“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仿佛一股诗的清泉汩汩流人你的心中”[14]。
因为对文学面貌的生动还原,更容易让学生触摸到文学发展的脉搏。在文学史教学和编写日趋工具化、学术化的今天,林庚的文学史教研工作显得更加可贵,让人向往。
三.学院背景与作家诗心的共生——林庚的学院化生存
随着作家学院化程度加深淡化创作是必然趋势,也要一些人无法割舍文学创作而离开大学讲台。能将这两种工作同时坚持下去并将其有效融合在一起的人并不多,林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对此他不无自豪:“我这个人一身有两种生活。一般人好像不大有这种‘兼差,总觉得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创作,是很远的两件事。施蛰存先生倒也是既稿新文学创作,又搞古典文学研究。他原先写小说,编《现代》杂志。但是他和我不一样,他到抗战以后就不写小说了,后来完全是研究古典文学。而我写新詩一直写到80年代。我在这两方面都没有间断,一边教古代文学,一边照样写新诗。……我和创作这方面没有绝缘,我是‘脚踩两只船”[15]。用钱理群的话来说,林庚将诗学术化的同时又诗化学术。林庚将自己作为诗人对文学的敏锐体悟充分地释放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之中。这对于教授者和接受者来说都是较为理想而又很难企及的状态。林庚在文学教育中将自身诗性的充分释放取得了成功:林庚的新诗创作从未中断;他的文学课堂极受欢迎,他到老年时仍有极佳的学术表现,成果丰硕,无论是作家、教师还是学者,林庚都是成功的。
实际上,大学任教生涯仍改变着林庚的工作重心,进入厦门大学之后,他从以新诗创作为主要工作转移到了学术研究中,这既是工作的要求,同时伴随着学院化程度加深,1937年之后,林庚把越来越多的精力转移到教学和科研之中,写诗在林庚看来也成了业余生活。虽然重心有所转移,但他依然没有停止创作,他的文学研究和创作都在不断走向成熟。
诗和小说戏剧等体裁形式规格不同,诗强调语言、意想、韵律,小说强调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诗与其他体裁在艺术价值上不存在高地之分,但诗歌更依赖于瞬时灵感的勃发,一般情况下体量规模较小,而从事其他文体形式的创作往往比诗歌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样是施蛰存、吴组缃等小说家进入大学后逐渐放弃创作的原因。吴组缃在解释自己后来为何没有写长篇时说:“1949年以后,我在学校里教书,太忙了,没有时间搞创作”[16]。在大学任教的老师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一般都利用寒暑假进行创作,在《我怎样写<牛天赐传>》中老舍曾写到:“一九三四年三月廿三日动笔的,可是直到七月四日才写成两万多字。三个多月的工作只写了这么点点,原因是在学校到六月尾才能放暑假,没有充足的功夫天天接着写”[17]。1934年12月29日,老舍在致赵景深的信中说:“以前所写的长篇,都是利用年假和暑假的工夫,因此,已有两三年没休息过。今年年假与明年暑假决定休息,所以不敢答应‘长买卖”。全年无休的工作任何人都吃不消,老舍最终还是放弃了教书的工作,全心投入小说创作之中。而一生都在从编辑和创作工作,从未进入大学执教的巴金,他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在创作活动中。他一生一共创作了20多部长篇小说,70多部短篇,还有大量译作,如此高产,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诗的创作需要作家保持高度的文学敏感性和捕捉力,但是对创作环境的要求相对不高,更适合心绪的随时抒发。郭沫若曾回忆自己写诗的经过,非常具有代表性:《凤凰涅盘》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成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那种发作大约也就是所谓‘灵感吧”[18]。可以说,诗歌的自身的特点也是林庚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中也没有停止诗歌写作的重要原因。
陈国球在《结构中国文学传统》中指出“诗人(文学创作者)一方面采纳另一方面又抗拒文学传统和它的基准,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之间永远存在一种张力……这张力令作家不停探索,直至他找到一个可以把自己构想到的方案适用于工作之上为止”。作家如果同时是学者,那么他对文学传统和基准会有更清醒深入的意识,不管是迎合还是扭转都将更有自觉性。文学研究者和创作者的职责不同。“文学研究”作为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知识或学问,“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识见和判断的体系”[19],更倾向于科学,而文学创作是一种艺术。创作是作家将自己的主观情感诉诸于文字的过程,而研究则是在占有文学材料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理智的形式”和“首尾一贯的合理的体系”[20]。理智性地探究和艺术性地创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过程。很多进入大学的现代作家,虽然有过一段时间同时从事创造和研究的情况,但是兼顾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其实是很难的。虽然如此,但“每一文学作品都具备独有的特性;但又与其他艺术作品有相通之处”,文学作品是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在进行文学研究时,除了需要运用科学的或者历史学的方法建立高度概括的法则外,还需要坚持文学理解的个人独特性。林庚就是从诗人的角度去理解“诗的特性、诗的‘肌质、诗的具体性”[21],消除了与作品的隔膜,将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和系统性较好的结合起来,而且他对文学“文学性”的卓越感悟和解读,散发着诗性的光芒,使人可以忽视其在建立普遍法则方面的相对薄弱。
大部分现代作家的文学教育,倾向于以文学的诗性魅力来感染学生,在他们看来,文学的知识部分只是开启文学大门的钥匙,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应该更好地呈现文学本身,即对文学美感的把握,以及重视文学对人审美能力的提升。这从其教学实践中自然地流露出来,并改善了教育体系中以所谓的科学方法来研究文学的痼疾。现代作家的大学文学教育工作因作家独特的文学创作经验和敏锐的审美能力的直接介入,与普通大学教师的教学相比,在文学阐释上更为具体也更加生动。
林庚身上有着坚定的诗人气质。他一直认为自己首先是诗人,“以教学为业而心在创作”[22]。在面对教学和写作更看重哪个的问题时,林庚回答“我先是诗人,后是教授”[23]。林庚在最后一次为学生授课中曾说:“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林庚正是一直保持着诗人的状态同时也以这种状态投入与文学研究和教学之中。正如闻一多评价陈梦家从文学转入考古学时说:“他也是受了我的一点影响。我觉得一个能写得出好诗的人,可以考古,也可以做别的,因为心被诗磨得又尖锐又精细了”[24]。
从这个角度说,坚持新诗创作,使林庚保持了学术研究敏感度的原因,也使其学术研究自成风格的原。林庚曾说:“我能写这样的《论诗稿》,是因为我有创作经验呀,你没有创作经验,你怎么能分析它呢”[25]。诗人的品格使林庚探索出适合自己的学术路向和独特的文学教育方法。将这种未受压抑的自然的文学创造力和想象力注入学术研究和教育的路向是成功的。林庚站在文学立场对文学潮流,文学历史的把握,不会偏离文学本身,在教学中对作品的关注,对学生的审美训练,也会曾强学生的审美能力。而就研究者而言,在长久的学术环境中,文學创作的持续也使他保持自己对文学的审美把握,不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的研究都不会丢掉文学,这也是林庚保持长久的学术创造力和学术独特性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林庚:《林庚诗文集·9》,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4页。
[2]《林庚先生谈文学史研究》,《文史知识》,2000年,第2期。
[3]林庚:《中国文学史》,鹭江出版社,2005年,第6页。
[4]张鸣访谈:《人间正寻着美的踪迹》,《文艺研究》,2003年,第4期。
[5]林庚:《中国文学史》,鹭江出版社,2005年,第6页。
[6]林多次表达过:“我总希望在研究古典文学的时候,为新文学,主要是为新诗的发展找到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林清晖:《林庚教授谈古典文学研究和新诗创作》,《群言》,1993年,第11期。
[7]张鸣访谈:《人间正寻着美的踪迹》,《文艺研究》,2003年,第4期。
[8]林庚:《星火(上海)》,1935年,第2卷第1期 。
[9]林庚:《中国文学史》,鹭江出版社,2005年,第3页.
[10]林庚:《中国文学史》,厦门:鹭江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
[11]林庚:《林庚诗文集·集外集附录(第九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4页。
[12]宁宗一:《当代意识:一种学术立场——中国文学史的教学杂感(之一)》,《文史知识》,2000年第3期。
[13]商伟:《与林庚先生相处的日子》田,《读书》,2005年第2期,第16页。
[14]马嘶:《燕园师友记》,燕山出版社,1998年04月第1版,第57页。
[15]林庚:《林庚诗文集·9》,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
[16]吴组缃:《答美国进修生彭佳玲问》,《苑外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33页。
[17]老舍:《我怎样写<牛天赐传>》,引自《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1页。
[18]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17页。
[19]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6页。
[20]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页。
[21]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6页。
[22]林庚:《悼念組缃兄》,《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
[23]曾华锋:《林间学者的诗人情怀》,《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12月5日。
[24]藏克家:《我的先生闻一多》林从龙,候孝琼,《我的老师》,四川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25]曾华锋:《林间学者的诗人情怀》《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12月5日。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现代作家兼大学教师现象研究(1917-1949)”(20YJC751040)和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新文学在大学里”(SKZ53420210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