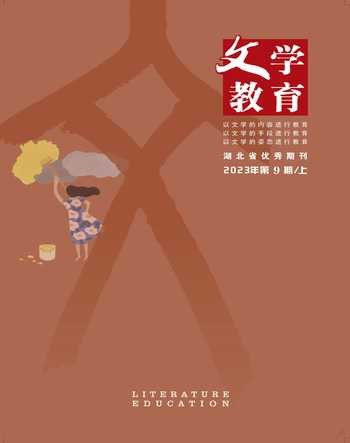论古典文学中的“镜喻”书写
王锐
内容摘要:我国的镜文化同茶文化、酒文化等一样渊源已久。并且,“镜喻”书写于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同样表现着十分多样的象意表达,主要涵括自然和人文两大方面。自然方面,如以镜喻湖、以镜喻天、以镜喻月;人文方面如以镜喻心、以镜喻虚空之境、以镜喻参照物。二者均在镜之形象性以及哲理性上进行了拓展与深化,展现出人类借镜照形的自恋心态向诗化、哲理化审美联想过渡的自觉追求,以及一种“修心”“审己”的集体无意识。
关键词:镜喻 自然 人文 本体 喻体
镜,亦作鉴,是人类社会科技发展成果之一,也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乃至精美的工艺品,迄今已有约四千多年的历史。其形制多为圆形,罕见方形、菱花形等多种。它的本质在于对光反射原理的利用,故正面可鉴人之形容、正衣冠,背面常铸有纹饰及铭文,东汉李尤遂有铭文云:“铸铜为鉴,整饰容颜。修尔法服,正尔衣冠。”(《镜铭》)
实际上,镜很早就由生活器物衍化为了一种文学意象。先秦时期,镜就被赋予了诸多的象征意味,《庄子》《韩非子》《尚书》中多能见到借镜抒劝惩和自省之意。而后汉魏六朝镜与佛教文化互动阐发义理,主要从哲学层面将镜与静心、虚空相连。至唐宋时期则更多以镜喻自然之物,后来更是活跃于明清小说创作当中。綜上,可将古典文学中的“镜喻”书写归为自然与人文两大方面,“镜”喻自然多见于诗词状景,“镜”喻人文则常携带哲学意味见于文理之中。
一.“镜”喻自然
在自然范畴,“镜”可喻指湖水、天空、月亮。原始人类起初发现可映物照形的,便是湖水。太阳光照射至湖面遂可水中成像,此为“日水成鉴”之说。据此,以“镜”譬喻湖水可谓是一种十分自觉、无意识的审美联想。天以水之对立面而衍生为本体,但“镜”却能以喻水之同理来譬喻天空——平静、澄明。以“镜”喻月则更多出于形似、色同之因。
(一)以镜喻湖
常智奇以为“日水成鉴”的自然现象,是人类审美意识发生的基础和前提[1],即人类自恋意识的觉醒和对象化的确立。基于水光反映的性质,镜与水建立起一种审美联想,既有白日照水以显影的日常功效,也有湖月相合的美景可赏。“镜”不仅可单字成象以喻湖水澄明,更是建构出玉镜、明镜、未磨镜等多种取象表达范式。李白《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五)》道:“帝子潇湘去不还,空馀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着力描绘洞庭湖山之娟秀静美。诗中“帝子”意指湘君与湘夫人。诗人伫立在舟中,环顾洞庭湖,湘君与湘夫人早已魂飞不见,空留秋草在湖间飘飖,物是人非之感、怀古思吊之情不觉间涌上心头。读至“淡扫明湖开玉镜”,不由思考是谁“淡扫”?又是谁“开玉镜”?省略的主语是否统一?“玉镜”又为何物?细读来,才发觉李白此句的高妙之处——原是月亮的清辉撒向了(即诗中之“扫”语)洞庭湖,于是洞庭湖成了“玉镜”。月光扫明湖犹如美女打开玉镜,而那远处的君山又仿佛一幅丹青画。真乃一纸明湖如镜、君山如画的洞庭夜景图!李白对绿水青山、大湖明月之境由衷热爱,甚不惜反复题写、盛赞洞庭风月,且都笔触清丽、色调明朗,一反前人状洞庭阴晦尘霾之情形[2]。并一再取明镜为喻:“水闲明镜转,云绕画屏移。”(《与贾至舍人于龙兴寺剪落梧桐枝望灉湖》)
刘禹锡《望洞庭》云:“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则写夜月之下,风平浪静的洞庭湖照物不明,犹如未经打磨之铜镜。雍陶的“应是水仙梳洗罢,一螺青髻鉴中心”(《题君山》)也展现了洞庭湖水之明、君山之青,以及湖光山水几番相合之美景。
庾信《登州中新阁诗》诗云:“石作芙蓉影,池如明镜光。”直接指出池水如同镜子一般明亮。正因如此,倒映在水中的楼船就仿佛浮游于镜中:“帐殿疑从画里出,楼船直在镜中移。”(刘宪《兴庆池侍宴应制》)沈佺期在其诗《鼓吹曲辞 钓竿篇》中更说:“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天空与人同倒映于湖上,人如同悬坐天上;湖水里的鱼儿们更是悬游于镜内。“卷幔山泉入镜中”(王维《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荷花镜里香”(李白《别储邕之剡中》)均写湖水之澄明。苏轼则以背面刻有鱼、藻之类纹饰的铜镜,即“藻鉴”为喻,其词唱道:“鱼翻藻鉴,鹭点烟汀。”可见,形制多样的铜镜进入文学意象写作后,既有譬喻取意的多意指向,亦有多样化的取象表达。
(二)以镜喻天
古代文人常在一俯一仰之间观察天地万物,正如《系辞》中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3]水是大地之景,天空虽与湖水之景相对,但二者也存有诸多相似性。所以,“镜”既可比喻湖水,也可比喻天空。
东晋湛方生有《天晴诗》云:“青天莹如镜,凝津平如研。”《说文解字》载:“莹,玉色。一曰石之次玉者。”[4]《晋书·乐广传》亦云:“此人之水镜,见之莹然,若披云雾而视青天也。”[5]可知“莹”意为光洁透明,而镜子也恰是光洁、平静、透亮。因此,湛方生此句意在说明晴朗的天空光洁透明如镜。次句“凝津”是指平静的河水,“研”应当同“砚”,意在借以状河水平静无波之景象。
杜牧《长安秋望》亦以“镜”譬喻天空澄明:“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杜牧于高秋时节登长安高楼,眺望终南山时见目下之景遂作此诗。诗首句写楼高、树高;次句借“镜”喻之象写天空光洁澄净,又因不染纤云之天空愈显其高远寥廓,故另有天高之意;末两句以终南山与秋色争高来凸显山与秋俱高。故全诗落笔实则主在秋色之高,大有“秋高气爽”之意。同时,也展现了诗人杜牧高远澄明的精神性格,高远、寥廓、明净的秋色,也正是诗人胸怀的象征与外化。若以上述湛方生“青天莹如镜”来释杜牧“镜天无一毫”,我们还可知杜牧长安登高望秋时的天气当是晴天。天气晴朗,才纤云不染、高远明净;天气晴朗,诗人心境方为爽利。
广阔无垠、纤云不染、平静的晴空易触发诗人对镜子的联想,这是基于二者在平面、光洁之特质上的相似性与互通性。苏轼《介亭饯杨杰次公》:“孤峰尽处亦何有,西湖镜天江抹坤。”李新《月下口占戏子温》:“万里层阴宿雾消,冰轮初上镜天遥。”二人同样也取象“镜”来形容当时天空之情状,即雾散之后碧空如洗,李新更是突破了“镜天之喻”的白日景象,反写夜晚雾散之后,圆月初现晴朗夜空之景。米芾于江湖楼上极目眺望之余,也唱叹道:“江湖楼上凭栏久。极目沧波,天鉴如磨,偏映华簪雪一窝。”(《丑奴儿·见白发》)
(三)以镜喻月
“中国古镜从一开始就取圆形,这是因为当时盛水的器物多是圆形。另外,人们在观察天体、宇宙自然的过程中,直觉使人感到‘天圆地方。面镜的映像是以天上的日光的灿烂为依据。天是圆的,太阳是圆的,人的眼珠是圆的。这是镜始为圆的美学基础。”[6]所以,镜多譬喻圆月,而少比缺月。
典型如李白《渡荆门送别》:“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月亮在水中的倒影好像天上飞下来的一面天镜,云彩升起,变幻无穷,结成了海市蜃楼,很有奇思。”[7]月亮不仅似天上飞镜,也像极了白玉盘、瑶台镜:“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可见月亮是圆月,而非缺月,惟月圆天清之时,月光方十分明亮。但欧阳修“江南月,如镜复如钩。似镜不侵红粉面,似钩不挂画帘头”则是少见的以镜比缺月之作。此时,人类早已远离“日水成鉴”所包含的“日神崇拜”文化,“镜喻”书写所主导的审美想象已然十分成熟且丰富多彩,但其本质仍然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内核。
以镜喻月,除形似质同之外,更有色泽上的相似性——金色,或玉色。宋代词人朱敦儒有“万顷琉璃,一轮金鉴,与我成三客。碧空寥阔,瑞星银汉争白”(《念奴娇·垂虹亭》)句。“金鉴”,即金色之镜。月光实乃太阳光之反射,反射光亮过多时则呈金月,常见为皎洁白玉之色,故月亮亦有“玉鉴”之名。后金鉴、玉鉴、宝鉴、宝镜等遂定型为月亮的借代意象。明月与明镜存在互喻性,庾信《尘镜诗》:“明镜如明月,恒常置匣中。何须照两鬓,终是一秋蓬。”则是以月喻镜的典型范例。
总而言之,以湖水、天空、月亮等自然事物为本体的“镜喻”书写是基于形象化的美学继承,凸显了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与互通。
二.“镜”喻人文
在人文范畴,“镜喻”书写主要表现在老庄以镜喻心、严羽“水月镜花”之诗论,以及唐太宗“以古为镜”“以人为镜”。这主要根源于铜镜映物无藏、像空而虚,甚可借鉴以修形貌等特点,我们也可从中窥见中国古人深远正直的自省心灵。
(一)以镜喻心
《周易·系辞》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庄子常借镜之象来比喻人心,意“借镜子的容纳性与客观性,喻示人心若如镜子般保持平静、虚空便不易受制于物,由此以提出‘虚己以游世的处世哲学”[8]。而心的喻体,《老子》多用水,《庄子》善用镜,镜实则是水的延伸,《老子》借水的流动性以譬喻心之动荡,《庄子》则用镜之静反观人心之动。《庄子·应帝王篇》有“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9]之句,旨在说明至人之心应当如镜子一般不迎不送、自然反映,只有做到内心虚静无藏,才能“胜物而不伤”。
《诗经》中实则早已出现以“镜”喻心的例子,其《国风·邶风·柏舟》有云:“我心匪鉴,不可以茹。”诗以飘荡无依的柏舟起兴作比,喻女子心境飘摇不定。缘是此女于深夜自伤遭遇不偶,道己心非铜镜,不能包容世间美丑善恶,心有怨怼却无处诉说,以致辗转反侧!老庄道家哲学正是为避免此类境况才对人心修养进行理意阐发,而光明无藏之镜则顺理成章成为了“道”理之载体。《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此乃老子思想中的重要观点——“涤除玄鉴”说,这是最早以镜喻人心与道关系的范例[10]。意即必须内心虚静,无私无欲,把内心扫除干净,宛如一面明镜,方可体悟“道”。后道教直接将道家玄理之镜引入并将其融合。
镜子除譬喻君子之心之外,还比喻詩人之心。如明代诗论家谢榛云:“夫万景七情,合于登眺。若面前列群镜,无应不真,忧喜无两色,偏正惟一心;偏则得其半,正则得其全。镜犹心,光犹神也。”[11]不仅强调了镜子“静”观万物的特点,也引出了“真”与“正”的特征,只有一颗纯真且正直的诗人之心才能描绘出客观与主观的“万景之情”。
以上展现了古代中国认为主体与客体原属一体的传统思维方式,即不视不听,静思以求,也即尚静观的哲学和艺术思维。这种虚静的心态正是进入审美境界的心理前提,诚如宗白华所言:“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12]
(二)以镜喻虚空之境
中国诗学受佛、道的影响极深,如诗论中常提及的镜中之象、水中之月,原本均为佛学术语,《说无垢称经·声闻品》有“一切法性皆虚妄见,如梦如焰,所起影象,如水中月,如镜中花”[13]。水中之月非天上之月,镜中花也非自然之花,皆乃光影投射之虚像,因此多借以比喻虚空之境,佛家常以此比拟人生虚无、万法之虚妄。南宋严羽善以禅喻诗,故将其引入诗论当中,借以比喻诗歌境界,认为诗中世界如同镜中世界,可望不可即、虚实相生、惝恍虚幻、纳万境无穷。其《沧浪诗话》曰:“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4]严羽此言旨在借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来比喻盛唐诗歌极致的境界,即含蓄深远、韵味无穷的审美特征。陆佃《埤雅·释兽》中记载,羚羊夜间休息时,以羊角挂树而足不着地,猎户于是无迹可寻。严羽以“羚羊挂角”释超然脱俗、不落痕迹之诗境,正照应了后文“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意指艺术境界和现实生活不粘不脱,若即若离才能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高妙境界。
在水中月、镜中花的比喻模式中,水与镜均为中介物质,是所隔之物,也是实际物象。语言文字同样如此,是状景映物的中介、工具,代表了“实”。但,语言文字所表达出的“意”则同水中的月、镜中的花一样,代表了“虚”,这便牵涉出“如何表‘意”的问题。故而,诗论中的镜喻理论侧重于如何展现镜中之影。如钱锺书语:“水月镜花,固可见而不可捉,然必有此水而后月可印潭,有此镜而后花能映影。”[15]诗境如镜中花,虚幻无实,又有可解与不可解之说,正如谢榛所言:“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也。”[16]基于对诗歌虚无本质的共同理解,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则采用了“蓝田日暖”“良玉生烟”的象喻模式。
“镜花水月”渐衍生为古代诗论史上一个常见的象喻,明代李梦阳也有“古诗妙在形容之耳,所谓水月镜花,所谓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后则直陈之矣”[17]的说法。
除佛学禅意、诗论,以镜喻虚空之境还多见于古典小说当中,如李汝珍《镜花缘》旨在表现镜花水月的虚幻,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也出现了诸多镜喻用例,《红楼梦》中唱林黛玉的悲剧命运时,也运用到“镜中花”这一范式。总而言之,以上均以镜象之“虚”“空”为核心展开,体现了文人选取“镜”喻体时对镜中世界的观察与认知。
(三)以镜喻参照物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三国志·孙奋传》),因此人们常借镜以正衣冠、窥容颜。女子“对镜贴花黄”(《木兰辞》),男子也常“揽镜看愁发”(李白《捣衣篇》),随着工艺制作的发展以及镜子的普遍使用,“镜”早已由器物衍化为文学意象。镜子照物无私,人们借助镜子可认清本原、真实的自己,帮助改善自身缺点。故而,镜子成了参照物,并由此衍生“借鉴”一词。
据此,镜子可譬喻各类提供借鉴改善自我的参照物,较为常见的如以史为鉴、以人为镜,这里的“史”“人”便是知兴替、明得失的参照物。如唐太宗语:“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卷七一》)魏征常以直言劝谏太宗的不良举止,就如同太宗身边的一面明镜,以致魏征死后,太宗悲叹自己已失去一面照己的明镜。这段君臣佳话十分得当地说明了人和史对君王治国的“借鉴”作用,历史如镜,可照兴替衰亡之因果,人如镜,则可见言行得失。在此之前,则有《墨子·非攻》云:“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意思是以水为镜不如以人为镜,以人为镜才能自省以知吉凶祸福。
借镜自省,功夫则在于“磨”。原因在于镜子映物,须得无尘垢,神秀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若不时常打磨以净尘埃,便会“不持光谢水,翻将影学冰”(骆宾王《咏镜》),镜中像反不如水、冰之影清晰。因而,人也应当时刻反省己心是否为尘俗所扰,是否被事物所蒙蔽,是否始终清净如一。这表明人类已由自恋心态引发审美愉悦的形式过渡到审视化的自我反思模式。
由以镜喻心、以镜喻参照物二种“镜喻”书写可知,向来以超高道德追求自诩的文学家们已自觉将“镜”纳入自我审视的范畴,由追求完美外表转为内心追求,由自我欣赏、顾影自怜扩展为群体比较,由一叶障目转为稽古振今。原始化、表象化的自我观照成功转型为向“修心”“审己”的倾斜。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无意识地将“镜”作为喻体选择的共同对象,足见镜之光明、客观照物等多样特性深刻绵长的影响。而铜镜所带来的形象审视则不以比喻模式活动于文学创作之间,更多地表现为借物抒情,即借“照镜”抒韶华不再之情,或是以带有性别身份的闺房物象进入诗词创作中。对镜中之象的意义理解则跳出了镜子本身的物象阐释。人们十分准确地把握到了照镜主体与镜中象的关联,并进一步掌握了镜象虚空的本质,随之自觉将其引入佛理阐发、诗歌理论、小说戏曲创作之中。
以“镜”为喻体,本体主要涵括自然与人文两方面。“鏡喻”书写在状自然之景时走向了形象化的美学继承,而在明人文之理上走向了哲理化的理义范式,深刻展现了中国古典文学意象中一象多意的特点,以及“立象尽意”的美学努力。其中亦见“镜”(或“鉴”)参构语词之象的多样化,诸如藻镜、磨镜客、金鉴、宝鉴等。但是,“镜喻”书写在古典文学创作中多样的象意表达,并不呈现出递进关系。先秦时期,“镜喻”书写便直接进入哲学范畴,而在后来的唐宋文学中则更多地以表象性征的方式进入状物摹景当中。
参考文献
[1]常智奇.中国铜镜美学发展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3.
[2]李德辉.李白诗歌对湖湘地理环境特征的揭示[C].中国李白研究(2006-2007年集):103.
[3]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257.
[4](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订.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06.
[5](唐)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43.
[6]常智奇.中国铜镜美学发展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3.
[7]傅德岷著.唐诗鉴赏辞典[M].成都:巴蜀书社,2017:127.
[8]赵俭杰,刘生良.《庄子》以环喻道、以镜喻心及卮言三喻[J].江汉论坛,2021(11):45.
[9]陈鼓应注释.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248.
[10]刘艺.镜与中国传统文化[M].成都:巴蜀书社,2004:171.
[11](明)谢榛著.四溟诗话[M]//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1181.
[1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5.
[13]引自朱立元.美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219.
[14](南宋)严羽撰;普慧,孙尚勇,孙遇青评注.沧浪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4:23.
[15]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1:281.
[16](明)谢榛.四溟诗话[M]//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1137.
[17]李梦阳.空同集:论学下篇[M].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