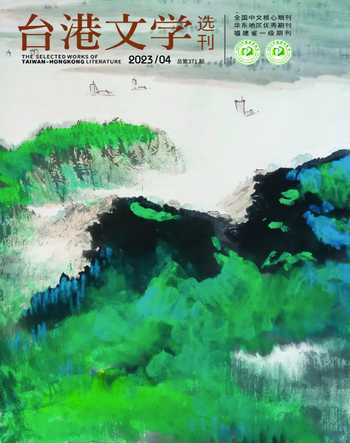寻枕记(外四篇)
朵拉
她没有特别喜欢去商场,但一到商场,她爱去床具部。
从前她喜欢换床单,人家大多两套交替换着用,她爱多买常换,亲戚朋友好奇问,她就笑,不能换人只好换床单。
近来她不是为床单去的,她在找枕头。
“高枕无忧”这老话,她不相信。她用高的枕头,醒来常感颈项酸疼,有时疼到无法转动,开车时要后退,她的头转不过去。
老人家说这叫“落枕”,人累了,睡觉睡得太沉,头没枕枕头上,歪一边沉睡时间太长,颈项被扭到。老人家说话语气轻松,似乎寻常小事,建议把枕头拿太阳底下晒,颈项马上好。
她按老人家的经验把枕头放阳光下晒一上午,转另一边,晒到太阳下山后再收回来,可是,隔天发现老人家说的话毫不灵验,她的颈项仍痛不可当。
初时没留意和枕头有关,以为自己特容易扭到筋,心里幽幽哀伤。她跟朋友提起扭筋。朋友回答,哎呀,年纪越大越容易扭到筋啦。
怎么就年纪大了?她自以为不在乎岁月流年。但这听着像间接提醒,面对镜子见额上皱纹时,感觉再扭筋的话,不得不承认年纪大了。
幸好妹妹问,是不是枕头太高了?
她的思路才往这方向忖度。买枕头时两个一起,因他喜高枕,她就随意。没主见非问题,问题是她的颈项不妥协,一不开心就以扭筋来发出不悦的抗议。
她在旅游短宿酒店,遇到软绵绵的枕头,睡得很舒服。枕在软软枕头上,仿佛有美丽甜蜜的梦。
入住酒店通常一两天就离店,总在回家后,遗憾地回忆那短期相处的软软枕头。
听到她颈项扭筋,妹妹重复提醒:“是否枕太高了?你以前睡软扁扁的枕头呀!”
一些过去岁月的喜好被妹妹呼唤出来。小时看爷爷睡赤红色长方木块枕,周边雕刻些看不懂的图案,觉得奇怪。某个下午,趁爷爷不在家,把木枕偷到自己房间躺了下,没待爷爷回来放回爷爷床上,不明白这硬绷绷的长方木枕,中间虽凹个洞,但枕着时,头颅像被悬着,爷爷怎么入眠的?
从小她的枕头都是软的。难怪她喜欢酒店那绵绵软的枕头,过去的日子虽已过去,但收藏在记忆里的老生活仍旧美好温馨。
妹妹笑她:“你试过硬枕头,知道不适合,干吗继续虐待自己?”
她决定去买个软枕头。
在商场拿起一个软枕抱在胸口,她立马爱上。
枕边的人奇怪,睡得好好的,怎么换枕头?
这么多年的相处,她已知道,所有的诉苦都像风吹过耳边,所以什么也没说。
之前她曾患失眠症,别人沉睡时,她的脑海开始上山下海。勿胡思乱想,医生劝告临睡前别过于兴奋,别联想太多。失眠的原因,可能是枕头!
断断续续服用安眠药的她想到从此不必再受失眠之苦,打从心底笑出来。
枕着软枕头,她以为会睡个好觉,做个好梦。隔天醒来,她发现颈项比睡了高枕还更痛。
像扭伤了那样,无法转头看后边,跌打师父问,感觉颈项那条筋很紧,对吗?
她忍着快掉下来的泪说,是。
跌打师父没有同情心地笑:小事罢了。不理她泪流不止,用力把她的颈扭回来。她听到“咔啦”一声,颈项的筋归位了。
这扭筋的颈项,一个月三四次,跌打师父说她身體弱,要吃补,卖她从中国进口的冬虫草、人参和其他她叫不出来的名贵药材。痛的时候,思考力转弱,师父说什么都听,重要是痛楚快点消失。
妹妹听说了,陪她去选枕头。利落地拿了一个,用手按几下,呐,就这个。
她拿过来,半软半硬,不讨她喜,可妹妹说,你从前用的,就是这样的。
她支支吾吾,犹豫不决,一想到颈项扭筋的痛,最后无可奈何买回去。
适中的枕头,果然是一颗最好的安眠药,从此再没扭到筋。
然而,她继续在商场逛荡,一定去床具部,一个一个枕头拿来按一下,抱一下,她还在搜寻一个她喜欢的软软枕头。
妹妹骂她:找到一个好枕头,就很好了。你是没事找事做?
她给妹妹看的脸色是:沮丧,抑郁,伤心。
算了吧,一个枕头,不是什么大事。妹妹的安慰没法让她开心。
难道要让一个不喜欢的枕头陪一生一世吗?
为何不能睡在喜欢的软软枕头上呢?
寂寞石子
阳光渐渐消隐去了。
草场上只有几个人,今天不是假日,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候,来运动的人就比较多。但是,最近的假日,伍爱丽都不来运动了。
草地是刚剪过的,修得整整齐齐。伍爱丽慢慢地跑着。可以嗅到草的青青味道,她深深地呼吸,再缓缓地吐着气,胸中的郁闷仿佛消散不少。
“一个人?”一个常见的中年男人,每次跑过都会互相点头招呼,但是从来没有开口交谈过,这天迎面而来的时候,突然问她。
伍爱丽点点头“唔”了一声,仍然继续她的慢跑。
往前跑去总要经过一个小小的花园,里边种满各种各类五彩缤纷的花儿,跑过去会闻到一股清香的鲜花味。她每一回越过,都下意识探头看一看,周国健喜欢的鹤望兰开花了没有?
每次和周国健一起跑步,跑到这儿,要是看见鹤望兰开花时,他就会停下来,唤她:“看,多么漂亮!”
她的笑容和花一样的灿烂:“咦,你说这花叫鹤望兰?我听说是名叫天堂鸟呢!”
“对,有人叫它天堂鸟。”周国健点头,“啊,这里有一朵是并蒂开的!”
“太美丽了!”伍爱丽遏止不住那股兴奋,她不由得吐露自己的心声,“是比翼双飞的天堂鸟呢!”
周国健搂着她:“是,是比翼双飞的天堂鸟。”
在花圃里做软体操的老太太看见伍爱丽,停下手势,问:“咦,一个人来?”
“是的。”伍爱丽的脚步加快了些。
她不想再听到同情的声音。
一个年轻人,手提着一个小小的录音机走过,在每个人都听耳机的年代,他却播着大家都听到的歌:“——这一生轰轰烈烈爱一回,看过真心真意的人,一辈子在回味,有人谈感情,求全身而退,偏偏我的,支离破碎——”
歌声随着他越走越远,就越来越淡去了。
刚修剪过的草地应该非常整齐干净,伍爱丽跑得好好的,突然感觉有颗小石子掉进她的跑鞋里头。
“啊!”她有一阵轻微的刺痛。
那颗石子却不在同一个地方刺她,因为她没有停下来,所以,跑了几步,它就移了位,这回就在脚心底下,她一开步,它就有一下没一下地让她感觉轻微的痛楚。
开始她觉得不习惯,很想停步把石子倒出来。但是,她看见又有常遇到的运动的人向她跑过来,她不能忍受一个又一个人提出来的相同问题:“一个人?”所以她不愿意停下来,她宁愿不断地跑着,让石子刺着,她继续往前跑。
石子移到脚指间的感觉不是那么痛了,她的脚指动了动,将它适当地搁在指头和指头的缝间,这样跑起来仍然会感觉它的存在,却不会让它刺得发疼。
当她适应以后,突然有一阵温暖升上来。石子寂寞,所以才跑进她鞋里的吧?
回家后,她把石子倒出来,看着它孤零零地被抛在地上,她想了一下,又将它丢进鞋里:“明天再和它一起去跑步吧。”
距 离
有时候他们约好下班以后一起去吃晚餐。
总是她先到习惯去的那家“老地方餐厅”等他。因为她下班的时间较他早,吃饭的餐厅离她的公司又比较近,所以她坐在餐厅靠窗处的那张他们首次约会的桌子旁等他。
窗外是流动的画面,那些远远近近静止不动的高楼大厦,在车水马龙间仿佛也动荡起来,恍惚间似乎它们都会走动似的,尤其是在下班时间,人来人往,车来车去,人车互相穿越着,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同谁打招呼,都是忙碌的步伐,毫不停止的人头,不会疲累的汽车,像没得歇息的时候。
也许人和蚂蚁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她望着窗框下那行行色匆匆的蚂蚁,不知道要不要叹息。
勤劳的蚂蚁知道它们是为了什么工作吗?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也许这便是它们注定的命运。
在暮色和夜雾渐渐浮游起来的时候,在闪烁的霓虹灯那五彩缤纷的光影里头,人和车都影影绰绰的,像银幕在晃动般地不真实。
她呆呆地望着,望得太久以后,眼睛有点酸痛。
就在她已经忘记自己到这儿来的目的时,突然瞧见他正朝着餐厅走过来。
在那么多的人中间,她依然一下子就把他认出来。正如她首次在舞会中遇到他时,一抬眼,她马上就做了决定,是他。
那么好看,浓眉大眼,多而密且黑得发亮的头发,看着就气宇轩昂。
那时候追求他、喜欢他的女孩子,排成队伍像条龙。大家都知道篮球健将、短跑冠军、演讲高手说的都是他。文武双全的男孩,气质特别好,既儒雅又健康的外表就已经赢得大多数女孩的心。还有他彬彬有礼的态度,不是其他那些粗鲁浅薄的男同学比得上的。
为了获得他的心,她想尽办法,引他注意,然后采取种种手段,令他自动来追她。
人家恋爱是男的付出心力,她的恰好相反,是她费的心思花的工夫,终于让种下的树开了花也结了果,大学毕业后他们宣布结婚。
二十几年的光阴走过去了。
她一直没把自己暗中使计谋的事告诉他。一定得让他蒙在鼓里,这样她的自尊才不会在他面前破碎。
他渐渐走到靠近餐厅的玻璃门来了。
她微笑地等他走进来,看着他越来越近,突然她觉得他的陌生。
半秃的头,两泡大大的眼袋,脸上几点老人斑,背也有点驼,这是当年那个文武双全的健将吗?
为什么远远地看着,他是他,近一点看,他反而不太像是原来的他了?
熟悉和陌生居然只在一线之间吗?
他站在餐厅门口寻索太太的踪迹,他们约好每个星期六到这里来吃饭的。他望过去,每次来的那张桌边,这时正坐着一个眼睛眯眯,眉毛疏疏,眼梢里满是皱纹而嘴角下垂的女人。
他的脚步慢了下来,心里稍迟疑:这个老态龙钟的女人,是他的太太吗?
嗅 觉
每次家里出现什么异味,总是胡太太先嗅到。
“又有猫在院子里大便了,臭得要命。”
“應该是有只壁虎被压在窗框边死了吧,我闻到一股味道。”
就算是非常轻淡的味道,胡太太也闻得出来。
“秦太太,你换了香水了?”
“啊!”秦太太一脸的佩服,“你的鼻子真灵敏,连我老公都不晓得我换了新品牌的香水呢!”
“你老公太粗心大意了。”胡太太得意地笑,“上回我听到他提起公司里的爱珍和小林,我即时就猜到他们中间有点不妥,果然没错,接下来不是听说小林为爱珍离婚了吗?”
“就是!”秦太太一径点头,“我当时以为你是多疑,后来林太太闹到公司里去,我老公回来告诉我,我才相信你心眼的敏锐。”
胡太太大声地咯咯咯:“什么心眼的敏锐?我这是嗅出来的。”
她说完又加了一句:“从小我妈妈就说我的鼻子格外敏感,对味道的感觉较别人要灵敏些。”
“我就不行了。”秦太太为自己的愚钝而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像曾子平和苏绫美的事,一直等到苏绫美大了肚子,又离了婚,和曾子平住在一块,我才恍然大悟。”
把眉毛挑得高高的胡太太更开心了:“可不是吗?我在公司的聚餐会上看到他们两个人的表情,就晓得曾子平和苏绫美在搞婚外情,你还同我争辩,说他们是同乡,所以交情特别好,还说什么两个人都已经结婚,曾子平是好好先生,不会背叛太太的。”
“这事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苏绫美人也挺好的,秀气又贤慧,怎么想到她也会背着她先生和曾子平搭上了?”秦太太叹气地说。然后好奇地问:“胡太太,是不是你的第六感比别人的准确得多?”
“才不是第六感呢。我这人哪,就嗅觉特好,很多事别人还不知道,我就先嗅出来了。”胡太太对于自己的这个优点,颇有些洋洋自得。
她喜欢让人家知道她有这一项与众不同的敏锐,所以时常邀请邻居的太太们到她家里来聊聊天,在闲聊的当儿,不时发表不少关于她比别人先嗅出来的真实故事。
新搬来的章太太也加入她们的聊天聚会。
章太太长得年轻貌美。眼睛亮亮的,而且眼波流转,顾盼之间,颇见妩媚的女人味,苗条修长的章太太喜欢笑,一笑起来,亮亮的眼睛就眯眯的,一副风情万种的样子。这令她在几个胖太太之间,显得格外出色。
开始的时候,胡太太还时常同胡先生称赞章太太的漂亮,渐渐地,胡先生几次下班时刚好遇到章太太在他们家,过后胡先生竟也在言谈间赞赏着章太太的明艳照人和亮丽的笑容。
“咦!”章太太说着站起来,“胡先生回来了,我也应该回去煮晚餐了。”
看着她挺直的背影,秦太太说:“章太太真是好太太,看到胡先生回来,马上就赶回家去煮晚饭给章先生吃。”
“是吗?”胡太太口气冷冷的。
为什么每次胡先生一到家,章太太就急着要回去呢?
胡太太仿佛嗅到空气中浮游着一种不同的味道,但她却说不出来那究竟是什么。
芒果的味道
住在槟城的她要吃芒果不难,这本是更北部的吉打州的农产品。
她喜欢吃芒果。
城里最近开了家甜品店,主打就是芒果。芒果西米露、芒果慕斯蛋糕、芒果流心、芒果雪花冰、芒果雪糕、芒果糯米卷等等,她最爱是杨枝金露。
第一次点杨枝金露是在香港机场。那碗甜品是芒果、柚子再加芒果汁及椰汁調配而成,芒果颗粒和柚子颗粒一起吃,入口嫩滑的芒果,清脆并带汁的柚子,微酸和香甜,两种味道汇合得正好。两个不同的人,可以很好地相处,一碗香甜的杨枝金露也许就是很贴切的比喻。
细咀慢嚼,她吃东西一向慢,尤其甜品,完全是在品味而非吃饱。可是,他三两口就把一碗杨枝金露吃光了。
刚认识的时候,一起吃饭,她看着,没说,多次吃饭之后,她就提醒他,你吃东西太快了。
只有一次的生命,生命中的一切便都值得细细品味。
她一直在寻找,找一个可以明白细致缓慢让生活益发丰富,日子有更多元层次的人。
尽管她很同情那些随便过日子,粗糙过生活的人,但要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的话,她宁愿孤独。
本来寂寞早就成为她的好朋友,习惯以后,也就不在乎,一直到遇到他。
他并不知道她喜欢吃芒果,机缘巧合,正如他们的相遇。没刻意布局,他们在聊起来以后才晓得,两个人身边本来就有很多互相认识的朋友,一次次的错身而过,最终还是碰上了。
他到北部的吉打州出差,买了芒果,带回南部柔佛,隔日到槟城去看她,带了一个芒果去。
“那么大的芒果?!”她惊呼,作了鼓掌的姿态,“没见过呢!”
切芒果的时候,她手势温柔而徐缓。想着他从北方买了,带回南部,又特地从南部带到属于北方的槟城,送她。距离不是问题,重量也不是问题,感动的是他为她带来带去。“我吃过,很好吃,就带一个给你。”这是他说话的习惯,云淡风轻,听起来变成是简单小事,似乎并非蓄意的安排。
切了三分之一,已经满满一盘。那么大的芒果,他刻意搭飞机带过来的,一想,满心感动和喜悦。把水果当正餐不是首次,但把芒果当饭却是第一次。
她边吃,边想念在机上要回去南部的他。想起刚认识的时候。不能怪手机微信,但实在太方便,根本不需要见面,一来一往的,因为距离有点远,面对着的又是机器,便以为没有关系,倾诉心事时少了戒心,等到发现说得太多,突然变成比常时见面的朋友还更熟悉和了解。
他便知道她喜欢芒果。
从北方的吉打带了芒果回南部柔佛的家,再从南部把芒果带到北方送她。
她知道为什么,当然他也知道。
他没有说,她也没有说。
“好吃吗?”电话里他问。这电话表示他飞抵南部的家了。
“好吃。”芒果的味道很甜,但无论多么甜的芒果,吃到最后,总会微微带点酸。
就算吃杨枝金露时,人人都觉得太甜,可是,真正细品,她仍吃出一丝酸味。
回想起爱情这回事,就想到芒果,真是很好的比喻。一想到他不嫌麻烦,这么远把这么大的芒果带来带去,她的心,也变成芒果的味道。
慢慢地吃着芒果,细细地品着芒果的味道,芒果吃完以后,她的眼泪流了下来。
本辑责任编辑:练建安 杨 斌
特约组稿:凌鼎年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