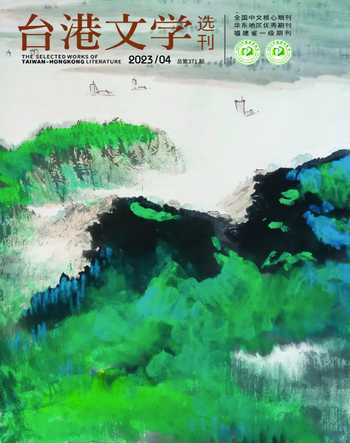一套有效的“文学化写人方法”
刘海涛
相裕亭的《打码头》《威风》成功地塑造了两个过去时代的有着独特个性和文化内涵的“盐商”,显现了他有一套有效的“文学化写人方法”。
他抓住盐商“外表与内心”不一致的矛盾性格,或者通过精选某个“单一事件”做“递进式渲染”;或者通过精选人物“不同时空但又有同一底蕴”的材料做“并列式渲染”。他常常是把人物的独特言行——也即人物独特的“现实维”这一极写足、写活;然后在作品的高潮位置上,通过“文本金句”——或者是“补叙”故事情节的留白部分;或者是让人物自己的言行以及故事讲述人的“金句式点破”,透露故事主人公内心隐秘的行为动机,让读者能够认同某类人物的“人性共同点”,感悟隐藏在故事主人公独特怪戾的言行背后的人性内涵,理解潜伏于人物矛盾着的行为内容与行为方式背后正常的“人性逻辑”。这就是从故事人物的“反常描写”到读者能“正常认同”的解读过程,当这个过程能够完成时,故事人物就鲜活地跃现纸面了。
《打码头》和《威风》情节均属“单一事件的递进式斜升”。《打码头》精选了“东家”“发草鞋、烧草鞋”等反常的让盐工们感到有玄机的故事材料,在做足了渲染、形成了悬念后,才由故事讲述人点破“东家”的内心计谋:“东家本想告诉少奶奶,海滩上的金子,都是他私下里设的套儿。那话已到嘴边了,他又咽回去了。”故事讲述人的这一“金句”,瞬间解答了前面五分之三的篇幅里“东家”诡秘地“烧草鞋”的奇特言行的内心動机,“补叙式点破”故事人物独特反常的言行背后真正的行为动机,形成了“东家”作为一个商人的外表与内心、聪明与狡诈的“二重组合性格”,这样的商人本质与本性就能够被读者认同和理解,于是当这样的“读者共识”一旦产生,盐商的怪戾和反常就能够理解了。
《威风》有点不同:一直到故事的高潮情节,故事讲述人始终不“补叙”、不“点破”“东家”通过鞋子里的一根头发捉弄陈三的真正的内心动机。故事全篇表面上呈现出的“东家”好像就是一个甩手掌柜,他放手地让陈三“站到前台”,可是一旦“东家”发现陈三能取代自己展示“威风”时,他那不能让别人冒犯自己权威的本相就显露了。但是,相裕亭高妙的文学手法,就在于把“东家”的“放权”渲染透了以后,再突然又不动声色地“收回”,作家在这里把人物的行为动机全留白了,全交给读者自己去想象,这非常符合文学故事的讲述规律——留出读者再创造的空间。他要让读者与自己共同完成一个故事人物的描写,这就是相裕亭写人的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