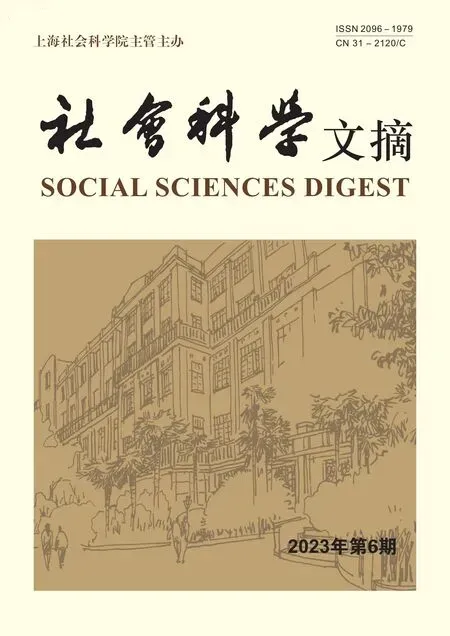鲁迅对章太炎学识的取舍
文/孙郁
一
鲁迅藏品中有一幅章太炎所赠手书:
“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卻守神,以物为量。”
此取《庄子·天运》的一段话,是他们都喜欢的句子。鲁迅得此书法,是1915年6月17日。当时章太炎被囚禁在北京,鲁迅作为弟子,多次去探望老师,可以看出彼此的感情。早有人从鲁迅的文字中看到太炎先生的影子。钱玄同、许寿裳等人的回忆录,曾介绍了鲁迅兄弟与章太炎交往的片段,这些都成为研究彼时知识人风气难得的文字。
鲁迅对章太炎的尊重,缘自对其学问的认可。他自己说欣赏先生的原因在其革命的气节上,那是叙述的策略,没有表达的还有另一部分的内容。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兄弟在《民报》听讲,随太炎先生学的是小学,乃今人所说的音韵训诂。革命的言论还不是主要的,有之,也是只言片语,或在课间偶然的对话里。在晚清的环境中,与章氏近者,都有革命之嫌,那是自然的。所以,梳理鲁迅与章太炎的关系,言革命则易简,而学问则大有深谈之处。而他们身上的庄子气味,也是颇值得后人打量的。
章太炎的文化观驳杂、丰富,其思想建立在深厚的学识中。他早期驳杂的文化观,是影响了鲁迅的。比如哲学、史学、政治学、文字学、语言学、金石学、文学的思想,都非一本正经的呆板面孔,有诸多变化的视角。在那时单调的学界,他撕裂了表达的链条,将新风引了进来。他所倡导的个性主义精神,乃夤夜的烛光,刺人耳目。太炎先生力主自由与独立精神,《明独》云“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就把奴性的枷锁弃置在一旁,是有狂傲之气的。除了此种独立精神,他还做翻案之语,对于士大夫的传统多有挑战。比如对于荀子、墨子的肯定,对于管子的认可,对于六朝以来个性化写作的赞佩,都与时风相反对。那些读史、读经的文字,都是活的,没有教条的调子,发现了诸多事物的隐秘。他批评儒家之弊,“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将孔子从圣界拉到地面,还原历史的面目。这些对于鲁迅后来的儒学观未尝没有影响。在许多文章里,他推举汉代艺术,蔑视宋元以来的文化传统,在鲁迅兄弟的文章里也都有所体现。章太炎的文化观所形成的冲击力,在现代社会久久地震动。儒道释所构建的思想之厦,因这震动而发生了倾斜。
文化的自下而上,回到内心的本我之中,对于旧传统是致命的一击,这也恰是青年鲁迅的逻辑起点。回想鲁迅早期文章,多少可以看到章太炎的影子。只是章氏以哲学精神建构自己的世界,而鲁迅则停留在审美理念的时候居多。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强调立人、个性,其实是就有《民报》文章的一种回音。他在文中寻找到了比康德、叔本华更为激越的尼采,摧枯拉朽的气韵飘动在自叙的文字间:“若夫尼佉,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尼采的引入,解决了文化上混沌的一页带来的诸多问题。章太炎在《无神论》一文讨论神与唯物、唯心的时候,矛盾之语颇多,反对有神论,又对佛教多有偏爱,思想不能统一于一个逻辑里。鲁迅的文章,逻辑性一以贯之,从超人之说过渡到“立人”意识,思想是澄明透彻的。章太炎的学说在于抗拒流俗,鲁迅信以为然,他在尼采那里就意识到“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重要性。在精神的基本走向上,他们之间的交叉性,恰好是新知识群落的一种必然共识。
二
作为复古运动的一部分,章太炎的辞章之学,起到了一种语言自觉的作用。苏曼殊等人称赞汉语优于英语,都与这个思潮有关。鲁迅最初写作使用文言文的目的,其实也呼应了复古的梦想。因为痛恨清朝文化的奴性痕迹,怀念古人的朗健自由之风,表达的格式也渐趋古奥,且以六朝之文为上。这种自觉与时代隔绝的写作,对于后来文章的变迁,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章太炎文章学观念的核心点,鲁迅是接受的。但随着探索的深入,古文的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鲁迅意识到自己老师的读者有限,文章渐渐束之高阁。考察历史的真境,就会发现,文言一致还是文言脱节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读书人。从平易晓畅的词语里表达思想,尤其是艰深曲折的思想,也未尝没有可能。待到胡适、陈独秀的白话文理念出现,加之西方审美理论的引入,他其实已认识到章太炎的局限了。
可以说,章太炎的文章在学术层面未尝没有存在的理由,且是世间高贵之作无疑,但文学艺术,则不能走这样的道路。王国维在晚清时代就在敦煌曲子词里惊奇地发现,俗语里的智慧比士大夫儒雅的语言不差,民间性的词语其实大大可以丰富文学的空间。王国维比章太炎更让后世学者感到审美上更有宽度,与他脱离儒家的雅言,能够从边缘文化入手来思考文化流脉有关。《观堂集林》对于西北边疆史的考察与论证,和他的《宋元戏曲史》一样,是从另类视角进入文化史的。在学术思考的路径上,鲁迅对于王国维的看重,也源于自己非正宗的文学感觉。可以看出,他对于语言问题,是有更多角度的考量在的。
与自己的老师不同,鲁迅后来的语言取口语与俗语者多,不像太炎先生那样留在书面语的雅趣里。周作人留学后喜欢搜集民谣与俚曲,大约受到章太炎的影响,但根本的还是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冲击。鲁迅其实也意识到,仅仅像太炎先生那样停留在学术层面,解决的是旧语境本义的还原问题,而不是当下语言新生的可能,而弟弟周作人的趣味也易将思想停留在象牙塔里,说起来也与实际隔膜。于是他走到十字街头,古语用之,俗语亦来,互动中呈现出新词语的面貌。
鲁迅的书,六朝气是在字里行间的,但不是对于古人的对应,而是今人的逻辑,那意趣在远去的世界里。所以曹聚仁说周氏兄弟可能是最接近章太炎的人,并非没有道理。在白话文里表达放大高贵、峻急的意象,章太炎并未料到,对他而言乃一个不可思议的梦。鲁迅则在翻译、创作、整理乡邦文献里,渐渐脱去古装,而骨髓中飘动着狂狷之风,那也实在让人感动。
要是细细品味鲁迅的语言,会发现其实有几种模式。一是小说语言,蓝青官话、绍兴话、古语兼用,与旧小说的士大夫气颇相反对。二是杂文中古今并用,书面语和反书面语并存,有独特的文风在。三是述学的文字,多用文言,但简朴流畅,去掉汉代语言的古奥,多了唐人朗照之气。不过这几种话语方式也常常杂用,不分彼此。《野草》的韵致就颇为奇异,尼采式的独白与佛经的顿悟在词语间跳动,看出精神的繁复。章太炎以古老的辞章谈古论今,多见奇气,思绪来自繁多的文献,乃智者的广搜博取,但那语言终究与我们隔膜。而鲁迅的词语却是从自己的体内来的,升腾的热气弥散在文字之间。
三
就学问而言,章太炎的驳杂,是弟子们难以企及的。他的学识对于周氏兄弟的影响不可低估。所涉猎的文化领域甚多,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从日本思想到印度文化,都有心得。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佛学的思索,颇有深意。
虽然周氏兄弟均没有进入梵文的领域,但章太炎的学术眼光无疑影响了二人。鲁迅与周作人还是回国之后对于佛学下了一点功夫,鲁迅后来钟情于小乘佛教,周作人在大乘佛教中乐而忘返。他们在新文学写作中自觉地融入了佛学的审美意识,尤其是鲁迅,内心的度苦思想时常在文字中闪动。而他对于中土佛教的世俗化描述,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五四以后,不同阶层的知识人对于佛教的摄取与发扬,侧重点均有不同。
章太炎治学里的佛学元素,确为其文字带来活力。文化寻根的过程,不注意域外文明的传播,总还是一个问题。中国人治佛学历史甚久,到了晚清,如何利用佛教资源,人们的看法不一。1902年,梁启超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提出自己的主张,认为“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厌世”,“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梁启超的看法,带有思考的系统性。但章太炎更注重佛教里的思想达成方式和哲学的经脉特点。他在《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中认为,佛法本不是宗教,“若晓得佛法本不是宗教,自然放大眼光,自由研究”。文章指出,中国佛法与印度佛法是不同的,但彼此可以互补。“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这才是‘善权大士’,救时应物的第一良法。”他其实在研究先秦诸子时,就运用过佛教的元素。释迦牟尼的时空观和生死观,在其述学文字里,与鲜活的自我意识是交融在一起的。
鲁迅的佛教思想哪些来自章太炎,哪些属于自悟,很难说清。一个事实是,章太炎的对于域外思想资源的看重,使他意识到,治中国学问而没有异质文化的参照,总还是一个问题。他的翻译理念,也与章太炎的摄取域外思想的方式形成对照。不过鲁迅更着重现代以来的域外资源,不太有精力去溯源佛教传统。除了抄校过魏晋时代的一些佛学资料,如《法显传》等,他的思考佛学的文字量少,但有趣的是其文章里的佛经式的词章暗含很多。
他的学生徐梵澄在回忆文字里讲到鲁迅对于佛教思想的敏锐感知和深刻认识。徐梵澄后来去印度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与鲁迅过去对于他的影响不无关系。年轻时代,徐梵澄到鲁迅那里做客,常常谈及佛教问题。鲁迅的思路是,佛教对于文化影响太深,“起初与道家相合,其次相离,各自成为宗教,便势不两立”。要了解中国文化,这些是不能不看的。
四
鲁迅对于汉字的特点别有心解,有许多地方是受到章太炎的影响无疑。《汉文学史纲要》开篇就从文字谈起,由文字而文章,将汉语书写的发生与发展,作了一种推测性描述。关于汉字出现,有各种传说,鲁迅以为“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可见,鲁迅眼里的文字是思想与情感的载体,有特别的审美意义。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鲁迅以为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鲁迅喜欢抄碑,对于字体有特别感受,故行文中三美俱在,其中之乐,自在心中。由汉字之美到文章之美,是章太炎治学里的趣味之一,鲁迅对此的领悟,也是颇为深切的。
章门弟子中对于汉字改革多有热情,钱玄同大概是最为活跃的一个人物。他虽然研究音韵训诂,但对于汉语拼音化的路是认可的。
与钱玄同比,鲁迅对于语言文字的理解,考虑得更为宽远,已经不再仅仅是从音韵训诂的层面展开讨论,而是带有文化发生学的意味。1934年,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门外文谈》,较为系统谈了对于汉字与大众语的问题。他采取《易经》的观点,认为汉字不是一个人创造的,而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一点点形成的。鲁迅在文章中强调,写字就是画画,有感知方式、认知逻辑在里,其思路与章太炎《小学略说》仿佛。不过章太炎的解释是精英士大夫式的,文字乃天才的发现,学者的气味浓浓。但鲁迅借用了人类学的观点,又受左翼思想影响,从大众层面思考汉字的来龙去脉,就水到渠成地说出,汉字改革的必然:大众的方便才是硬道理。不久,在《关于新文字》中,对于语言文字的看法不都是技术的问题,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就不是纯然的学者态度,而是左翼思想的表述。这显然比章太炎、钱玄同更为有现实的焦虑在里,但他开出的方子,显然也不太实用。鲁迅在语言文字的问题上,被难题所难,自己也陷入了困境。
关于新文化人对于语言问题的功过是非,后人已经有许多讨论,鲁迅的瑕疵也是一看即知的。泛意识形态的思路,对于实际的思想交锋有效,对于学术也是一个伤害。章太炎晚年一直强调国故研究的系统性与渐进性,鲁迅其实是陌生的。不过,虽然那么严厉地奚落过汉字的问题,但他自己对于以字为本位的汉语书写的规律,倒体味很深。古语、方言、口语的运用都很自如,也丰富了汉语的辞章之色。这是一个悖论。如果从这个层面看,他对于语言的态度,的确比章太炎走得更远。
五
从晚清的“排满运动”,到民国期间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复杂的时期。鲁迅思想恰是复杂环境下的复杂心境的反映。而章太炎遗产对于他而言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鲁迅与章太炎渐行渐远,其实是彼此寻路的目标不同所致。章太炎追求的是民族自立,恢复旧文明最为灿烂的一面。鲁迅兄弟是要吸纳域外文明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传统。他们以翻译为主业,思想与域外学术有互动的可能。而章太炎后来的思想,还在晚清的语境中黏滞。这种不同,使现代人文主义出现了岔路。章太炎的遗产也分化成多种形态并留在后人的思想里。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在学术中延续着章氏的精神,而鲁迅兄弟则在新文学创作里发扬了章氏的文明批评的思想。他们把知识用于现实的批判之途,从现实感出发去发现古人,都在大的现实语境里。而太炎先生其他弟子做的是类似古典学研究,和现实文化的距离显而易见。民国期间,知识人日趋分化,激进者有的与政治文化纠缠在一起,保守者则多在书斋里自我吟哦。而像章太炎那样学问也来得,革命也奋力的人,少之又少。他不是在历史的外面,而恰在时代的洪流之中。鲁迅对于自己老师的念之又念,实在是一种心以为然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