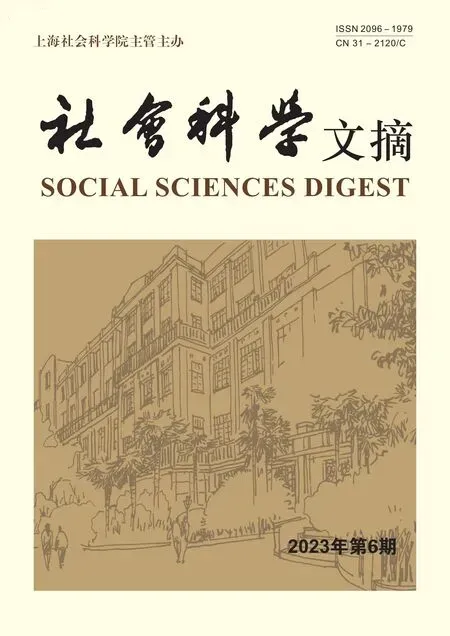日常统治与关系思维
——关于史学未来研究的若干思考
文/侯旭东
王国维先生在《国学丛刊》序文中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治学倡导融合古今中西。不过,近代学术的主流是趋新,日新月异或许有些夸大,但的确是在不断求“新”中显示学术的存在。梁启超便是开启中国新史学的旗手,1902年他发表《新史学》一文,举起新史学的大旗,对传统史学展开猛烈的批判。2022年正好是《新史学》一文发表120周年,同时也需要对120年来新史学的取向加以反思,以利未来的发展。
经过120年的发展,新史学到今天已呈蔚为大观之势。然而,研究上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随着新资料的不断涌现,宏观问题淡出而具体研究发展迅速,以致有“碎片化”之忧。如何产生有生命力、有创造性的成果,形成中国学术话语,是学界面临的严峻课题。
史学工作者具体研究方向各异,但当代的史学工作者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共性。简言之,所有的同辈学者都是在20世纪以来新史学熏陶下进入史学研究的,共享近代形成的史学思考方式。新史学与其他学科一道大致经历了学科体系的固化、大学教育体系的成型与塑造,以及若干基本观念与论断迅速被接受。前者包括进化论以及科学主义(实证方法),后者如五种社会形态说、五千年文明、专制国家论、中央集权论等。在进化论支配下,求新求变亦成为一个时代的基调。此外,史学的研究对象则基本固定为事件、人物与制度。这既见于从事具体研究的史家的论述,也屡见于史学概论性的著作。当下史学界,无论研究哪个领域,这些均构成从业者认知的基本前提与思考的出发点。
从更大范围看,学科之间的学术分工也固定化:譬如社会学研究不变的东西,研究人类的行为模式,关注的是当下的社会;历史学重在研究“变”,研究独特性,关注的是从古到今的历时性演变。因为重视“变”,产生了中国史里各种各样的变革论,发生的时间从殷周之际到改革开放,几乎每个时期都可以纳入不同的变革论中。这种分工不止为历史学所接受,社会学中也几乎成为共识。赵鼎新在《什么是社会学》中指出:“历史学是一门以事件/时间序列叙事为基础的学科,而社会学则是一门以结构/机制叙事为基础的学科。”这种分工可以追溯到社会学初创时期确定下来的分工格局。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指出:“在社会行动范畴内可以观察到某些经验式的一致性……社会学研究涉及的就是这些典型的行动模式,因此它不同于历史学,毋宁说,历史学的主题是对那些重要的具体事件做出因果说明;这些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影响了人类的命运。”事件正是体现了独特性。这种认识甚至可以上溯到西方学术奠基人之一的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就有关于历史是关注个别的说法。
以上诸点,都不能简单地视为当然的铁律,而需加以反思。这方面,也有学者做过一些工作。特别是最近30年来出现的历史人类学,走向田野,触摸鲜活的百姓生活与微观历史,在村落、祠堂、庙会与仪式中穿越古今,发现灵感,提供以普通人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观察,挑战或补充数千年来王朝立场的思考。不过,历史人类学尽管提出了很多新的研究方法,实际研究涉及的时段主要是宋代以后,尤其集中于明清与近现代时期,与其重写中国史的抱负尚存距离。那么,宋代以前的历史怎么办?如何超越断代,返回历史现场,为史学提供更具普遍意义的新可能?
转向“日常统治”研究带来的新视野
笔者2020年出版的小书《什么是日常统治史》,基于过去十多年的研究实践,对20世纪以来新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乃至西方社会科学做过一些反思,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研究提示了一些可能的做法。1999年以来,笔者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秦汉三国时期出土文书简牍,这引发了我对事务以及朝廷官府日常统治的关注,进一步推动我思考如何研究中国史乃至更一般的文明产生后的历史。
日常统治史,听起来和经济史、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或日常生活史类似,可以归为一种新的专题史;也与秦汉史、明清史、英国史、全球史一样,属于对研究对象的区分,有大致明确的边界、时间起止、空间范围。然而,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重心不在研究对象,而在如何研究。
日常统治研究不是写流水账,宋代以前的历史也无法实现,即便宋代以后资料丰富,也无须如此。需要挖掘的是,反复进行的日常统治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具体来讲,以往的研究,包括传统上的历史学研究,多强调的是变化,是特殊性,认为历史是独特的、不重复的。中国传统史学有“常事不书”的习惯,记录下来的除了制度,几乎都是各种不寻常的情况。这种记述风格亦影响到历史研究,尤其是加上20世纪以后受西方进化论的影响,学者们更重视“变”,似乎不变的东西就没有什么研究价值。而文书简牍中呈现的是另一番景象,反复进行的事务构成了吏卒工作的基调。两者并观,为我们跳出传世文献的束缚来理解过去,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与更丰富的素材。
进而言之,将史学传统窄化到关注“变”而忽略了“常”的认知方式,既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符,也与古人的生活实态不合。历史中有“变”的一面,也有更多“常”的一面,研究者不能仅仅将目光放在那些“变”上。史学也不应将这些反复发生的行为留给社会学去处理,而应吸收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与思考,扩展视域,从专注于“变”转到关注“常”。
“常”可分为常行、常情、常理与常态,不仅包括延续,还有反复、循环等,基于此,在“常”中再去观察“变”(变态,非常、异常与反常等),观察“常”与“变”二者如何互动。在这一辩证研究过程中,可以将更多的人与事,包括普通人及其行动与思考,以及精英人物的例行活动,还有双方的关系纳入视野。所谓“常”,正如萨林斯与吉登斯所注意到的,结构性关系来自例行化行动就是“常”。关注日常,将反复发生的事务与制度、事件结合在一起,可以发现认识传统的“事件”与“制度”的新角度。
“日常统治”究竟何所指?先说“日常”。“日常”重在“常”,而不是“日”。或许有人追问,“日常”是不是每天都要重复进行?实不限于此。侧重的是按照一定周期反复进行的活动,不一定是每天。如清代道光帝,他每天都要做的工作是批奏折,还有大致两天召见一次臣子,每个季度要祭祖,一年一次要审批秋决等,这都是重复进行的。不仅仅是皇帝,王朝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常”(古话称为“职分”)。即便是农民,年复一年的耕种,就是他的“常”,这也是战国以来王朝使用各种办法塑造出来并落实到现实中的,不是与王朝无关的“自然状态”。
这里所说的“常”比社会学关心的“同”的范围要大。“同”更强调统一性重复。“常”接近于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讲的“家族相似”,存在很多核心要素上的共同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小吏处理的事务,有些是按月、按时、按年重复开展的,也有内容与类别的差异,但处理过程却往往一样。如司法案件,几乎见不到完全相同的案件,但是处理的程序却是固定化的。这些都属于“常”。我们在理解“常”时,注意的不只是重复性,还包括内在的相似性。
“统治”则借助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思考,不是强调某个事件意义上,而是强调存在某种稳定的秩序,关注秩序的形成与维系(传统上称为“社会整合”,对中国而言更妥帖地应称为“国家整合”)。具体到中国,便是如何保证广土众民的王朝能够持续存在下去。这不只是靠皇帝的作用,就像自上而下书写的史书常常带给我们的错觉。笔者曾做过一些汉代与三国时期孙吴简牍的研究,能从中体会到小吏们每天的重复性工作——巡逻瞭望敌情、做砖做饭、编制文书簿籍、抄抄写写、收发传递……他们在这些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履职尽责。信息和命令上传下达,人员物资从收集、调配到使用,构成了整个王朝生生不息的基础。这是一套上下贯通、井井有条的秩序,很多数据都要定期层层汇报。类似的很多做法甚至都延续到今天。
为何是“统治”,而不是更常见的“政治”?“统治”可以做动词,暗含了过程性,同时也可以有被动式——被统治;还可以做形容词,修饰名词,如统治方式、统治机制等。“统治”一词的表现力更丰富,容得下文明产生后围绕王朝秩序的各种努力,可以灵活且充分展现秩序的建立、维持以及统治/被统治—抵抗的关系性,也可以超越以往注重独特事件、缺乏人的制度的思路局限。“政治”则几乎只能做名词,内容要单薄得多,且与现代性关联更紧密,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20世纪形成的领域划分有密切关系,而与古代王朝的实际情况有距离,不利于全面把握当时的统治。
引入“关系思维”
概念的梳理不过是为具体研究铺路,更为核心的是如何研究。虽说“史无定法”,也还是有些基本的视角值得坚持。《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中提出了四种视角:主位观察为优先,辅以客位观察;顺时而观优先,辅以后见之明;日常视角;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思维。
前面三种视角都可以纳入关系思维。具体而言,前两种视角体现了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时间三者的关系,日常视角则体现了被研究对象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与研究者的关系。关系思维体现为三种嵌套的关系[(A和B)和C]与研究者(具有时间、空间、个体差别)的关系,涵盖了前三种视角。借助具体化的关系视角,是希望我们从对象—研究者固定化的、无意识的关系状态中解放出来,发现新的研究空间。譬如大家熟悉的1838—1842年的历史就不止鸦片战争一种解法。研究需要“化熟为生”,发现“常见”背后的不寻常与将其“常见化”的力量。研究者其实就是观察者,需要在不断的思考中发现研究对象被以往的认知所压制或遮蔽的侧面,揭示新的问题。
《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的“结论”中提到“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实际上是试图突破既有领域的划分,如中国史中的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从“关系视角”重新梳理我们的研究对象。人与事的含义经过词义的考古,具体内涵更为饱满,神、事与物都包含在甲骨文中便出现的“事”的丰富含义中,因而人与事的关系可以做更细致的区分:人与人(传统意义上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关心的内容)的关系;人与神(传统意义上宗教学关心的内容)的关系;人与事(传统史学关心的内容,但含义较窄,不只是事件、制度)的关系;人与物(传统意义上经济学关心的内容)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人”,也不是西方个人主义视域下的个人或均质的人、理性的人,而是回到中国历史语境中的“不齐的人”,具体分为圣人、贤人、君子、小人。我们要研究不同位置上的复数的人与人、与神、与事、与物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关系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意在搁置西方学术传统与20世纪新史学支配下形成的分类、概念和宏大结论,返回历史现场,补充以后见之明,通过两者结合来激活认识过去的新可能。
这些关系几乎可以将所有的研究对象纳入。具体领域的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均不能停留在孤立地论人、论事(制度)层面,入手时可以依据当时研究所达到的状况有所侧重,但最后则需落实到人与事的关系上。这样就有可能将以往习得的知识分类,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学科内部的分类,放在一边。这些知识分类容易成为思考所依托的隐蔽框架,限制或支配思考。我们需要重返史料,发现更丰富的过去,为认识过去创造一些新的可能。
关系视角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自不待言,在西方学术传统中近来也受到不少关注。如诠释学理论集大成者伽达默尔指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
此外,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中江教授提出“个体的关系世界观”,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杨国荣教授提出“具体形而上学”以及他最近出版了《人与世界:以事观之》等。类似的看法在哲学界与社会科学界并不罕见,倒是史学界因对自身反思不足而显得比较冷清。
除了学理上的渊源,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源头与我们现在正面临的新的历史机遇或者变化有关。现在所处的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化急剧发展的时代,陌生性与不确定性日益增长,网络时代加速了跨地域甚至跨国界的交往,人们基于契约和作为前提的信任,每天都要和无数陌生人打交道。这种状况突破了过去的个体习惯的熟人社会。这似乎是和古代王朝不同的一个根本性变化。
其实,广土众民的王朝出现之后,类似现象也大量存在,彼时同样是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王朝的结合,只是过去的研究,除了社会史、经济史领域之外,很多领域的研究都忽略了这种复杂性,尤其是围绕王朝本身的那些研究,依然带着围绕少数人展开的思路。当下新的生活体验正激发我们去重新观察过去,发现以往被遮蔽的面相。
此外,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充斥的是反复进行的活动,真正包含事件性质的活动是罕见的少数,但既有的思路常常对于前者视而不见。历史学研究实际是身处当下的研究者和过去的对话,是不断展开的过程,也需基于新的经验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寻求新的答案。这一不断展开的过程正体现了史学的魅力和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