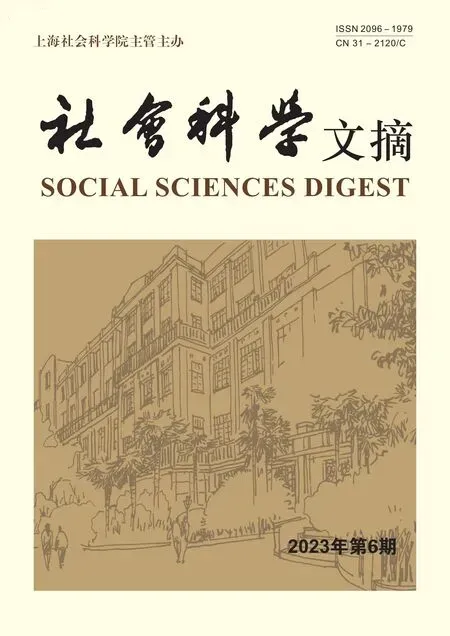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多学科交叉问题
文/董国强
当代史研究是广义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当然具有史学研究的一般特点。不过作为专攻该领域的研究者,笔者主要结合个人的经验,讨论当代史研究的独特之处。这些独特之处主要源于“新史学”——相对于“传统史学”而言——观念的影响,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的渗透。概要说来,传统史学主要关注精英人物的活动,关注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新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则主要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形塑人们日常生活的制度环境。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创新突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代史研究完全拒斥传统史学研究的观念与实践。事实上,在过去近40年时间里,当代史研究领域出现的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经典论著都可以归入传统史学研究的范畴。这里想指出的是,在当代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新的研究理念及其实践显得越来越重要。
一
取得丰硕当代史研究成果的学界前辈中,很多人曾供职于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机构,有机会接触大量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尽管限于工作纪律,他们不能公开引用这些内部资料,但大量系统地阅读相关资料,使他们对一些常见史料的深入解读能力令一般研究者望尘莫及。因而,他们可以沿用传统史学的研究路径,写出一些富含洞见、广受欢迎的经典论著——尤其是在研究高层精英政治方面。
但对许多就职于地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中青年学者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颁布之前,一般研究者无法进入各级政府的档案管理机构查阅档案资料。学术界能够看到的主要是由党政有关部门或研究机构编辑出版的各种“文件汇编”“资料汇编”等。由于这些资料汇编旨在服务政府部门的某些专项工作,所以对于一些尝试研究不同问题的研究者帮助十分有限。
《档案法》公布施行以后,上述状况一度有所改变。但总体而言,政府档案资料和其他内部文件的开放程度依然十分有限。一度开放程度较高的档案资料是教育系统、卫生系统和一些经济部门的档案。各级党政机关、公检法系统、军队系统和外交部门的工作档案大多没有开放或有限开放。近年来,一些业已开放的档案资料在检索和调阅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这种客观现实促使很多陆续进入当代史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者放弃传统史学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转而寻求其他路径和方法。笔者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方性群众运动的研究,就是从大规模的访谈口述开始的,然后才因各种机缘巧合,接触到大量档案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
二
就主观方面而言,许多中青年学者的大学教育和学术成长环境与前辈学者存在较大差异,这也是导致当代史研究在观念和实践方面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以笔者为例,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完成的。在后来的长期研究实践过程中,又逐步接受了“新史学”观念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对笔者影响最大的“新史学”论著是1989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姚蒙编译的《新史学》,后来又读到践行“新史学”理念的经典著作——乔治·鲁德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这些论著带来的史学研究观念变化是,将研究重点由精英人物转向普通民众,摒弃宏大叙事的论述范式,转而采用地方史和社会史视角,进行专题性的实证微观研究。
与此同时,尽管国内的当代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但是在国际学界,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伴随着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不断推进,早已有大量影响广泛的经典论著问世。这些经典论著的作者大多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但对初涉当代史研究领域的国内中青年学者而言,这些论著不无启发。
举例来说,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魏昂德的成名作《共产党中国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采用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专题讨论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企业内部的干群关系。他指出,“单位”制度造成了工人对单位和干部的依附性,使得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构想无法落实;干部也无权解雇不努力工作的工人,使得企业内部的一些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这样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单位内部干群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而且揭示了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和更为广泛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和塞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综合运用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专题讨论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合作社的起源和发展。由书中的翔实论述不难看出,20世纪40年代耿长锁合作社的成功经营和发展壮大的前提条件,是自愿互利原则、经济效益优先原则和依托市场机制原则。这实际上从反面揭示了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某些历史局限性。
曾任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的华人学者王绍光的《理性与疯狂》,专题讨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武汉地区群众运动的形成与发展。他在探讨群众派性斗争问题时,强调每个人的言论和行动实际上都包含着某种程度的理性判断。他综合运用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指出每个崇拜者心目中的偶像并非一个高度泛化和客体化的抽象符号,而是其自身利益诉求与是非观念的折射反映。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和中国学者李逊合著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一书,专题讨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地区的工人运动,特别注意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实行的两种用工制度以及基于籍贯和代际差别的人际关系网络,是造成工人群体内部分化的重要根源。
以上论著不仅在研究选题和理论阐释等方面具有启发性,而且在信息来源上也有很大拓展——既采用了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还采用了许多民间史料和访谈口述资料。
还有些论著在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方面的突破创新,更加令人意想不到——即使没有档案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也可以进行相关研究。
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贺萧与中国学者合作,尝试探讨不同性别的记忆差异。由于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从未进入各级党政领导机构的议事日程,所以这项研究所需要的信息不仅在一般党政机关的工作档案中难见踪迹,即使妇联系统的工作档案也不例外。因而他们不得不利用田野调查和访谈口述的方式开展研究。最终的研究成果表明,与很多人的主观预设不同,不识字的老年农村妇女其实也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只是她们的记忆参照坐标不是脱胎于主流历史叙事,而是奠基于她们自己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她们的婚姻和生育。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魏昂德采用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公开出版的2400多部新方志为主要信息来源,通过采集、整理、汇总各种数据,建立了许多数据分析模型,揭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范围群众运动形成与发展的整体态势和阶段性特点。这项研究不仅突破了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地域性限制,而且提出了许多传统史学无法提出的十分重要的新议题,促使研究者继续深化相关研究。
以上论著所展现的理论视野,提出问题以及采集和处理研究信息的方式,必然对国内初涉当代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带来启发。
三
从近20多年来的发展情况看,很多国内学者已经对当代史研究的社会史视角和多学科交叉特点有了自觉意识,在研究实作中有所践行。但总体而言,优秀作品的比重不大。
有些论文用大量篇幅阐释一些经典论著中的经典论断和经典概念,但在如何将那些论断和概念有机地融入自己的专题研究方面,则显得十分简单生硬,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两张皮”现象。在笔者看来,经典理论和经典概念的启发作用,在于引领研究者如何从不同视角去发现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选题,以及可能通过哪些新的途径去搜集相关研究所必需的各种资讯,从而揭示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面相。历史研究者的日常工作,还是搜集、整理、分析、甄别涉及具体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各种信息;史学论著的主要内容,还是基于多种信息来源的历史叙事。
对社会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广泛借鉴,看似极大丰富了研究工具箱。但在研究实际操作层面,当一个研究选题明确后,研究者能用得上的工具往往也就那么几种。
就笔者研究经历而言,除了传统史学研究很看重的文献研究方法之外,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采集、整理和使用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资料。将口述历史资料的重要性与历史文献的重要性等量齐观,主要基于两点理由:其一,1949年以后档案资料固然是各级党政机构和各类企事业单位日常工作的记录,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但这些信息的记录者主要是各级党政干部。所以,政府档案资料主要反映党政干部群体的关注、认知和行动,即使涉及一些基层实况和社会舆情,也主要来自党员干部的汇报总结。因而,来自其他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口述历史资料,可以提供与档案资料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历史叙事。其二,在当代中国的行政实践中,上级领导机关对基层工作的指导干预实际上存在着“常态化”和“非常态化”两种类型:“常态化”指导干预往往通过会议和文件方式实现,因而能够在档案资料中得到反映;“非常态化”指导干预则带有小范围、非正式等特点,很少形成正式的文字记录。因此,一些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资料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了解一些看似突兀的重要变故的来龙去脉。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要将访谈口述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手段,就必须注意访谈口述资料的样本容量和访谈对象的典型性问题。只有实施大规模、系统性、差异化的访谈口述,才能有助于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观察某一历史事件,了解不同个人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观念预设的差异。零星的、随机的、同质化的访谈口述,很难在历史研究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口述历史是研究者与亲历者合作的产物,研究者在这种合作实践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他们的问题意识决定了口述历史资料的具体内容,他们对相关历史背景和访谈对象的了解程度决定着口述历史资料的质量。如果研究者仅仅将自己视为被动的记录者,对访谈对象的口述内容缺乏必要而有针对性的质询和求证,那么就无法了解访谈对象的观念预设的潜在影响,无法评估口述历史内容的客观性和可信度。事实上,访谈对象往往会在访谈中对访谈者施加影响,试图使访谈口述资料成为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历史证言。
另外,口述历史采集的过程也是搜集各种历史文献尤其是民间历史文献的过程。在笔者的研究实践中,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包括一些系统完整的个人工作笔记、系统完整的群众组织出版物、较为系统完整的地方档案资料以及散失在民间的党内文件等,就是从访谈对象那里获得的。
四
上述各节旨在说明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对当代史研究的重要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一无是处。在笔者看来,史学研究的特点和长处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史学研究者的看家本领是档案和文献研究。“新史学”观念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任何类型的史料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都带有某些特定的时代烙印和人们的主观片面性。与此同时,各种不同来源的史料信息,往往能够凸显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认知、诉求和行动。因而不同类型和不同来源的史料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具有不可替代性。
其次,社会学研究常常将访谈口述资料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然而访谈口述资料是在历史事件和个人活动发生数十年以后形成的。至少有两个因素会影响到历史记忆的准确性:一是时间相隔久远带来的记忆模糊和记忆误差;二是访谈对象后来的人生经历和认知变化对其原始历史记忆的“污染”。而档案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都是当年形成的,始终保持着原始生态。因此,它们可以用以验证访谈口述资料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并修正访谈口述资料中的记忆误差和认知盲区。
最后,在论述方式上,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就笔者所知,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从社会现象出发,综合运用某些特定的理论框架和概念范畴,对个体和群体的思想和言行进行分类研究。所以社会科学论著往往很难呈现叙述连贯、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
正因为对不同学科的特点和长处有较为充分的认知,笔者在相关研究和著述中,一方面注意借鉴吸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概念和结构分析框架,注重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多方互动;另一方面也注意充分发挥史学研究著述的长处,注重历时性的发展线索和一些重要人物的活动轨迹,尽可能保持历史叙事的完整性和戏剧性。
总而言之,学术研究工作很少是在极其理想的条件下进行的,研究者总是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挑战。纵观古今中外学术研究发展的历史,许多新兴学科和门类的出现,就是因为传统的认知体系和研究方法无法解决研究者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促使他们在研究中另辟蹊径。一些新兴学科和门类的创立者往往出于捍卫其新领地的动机,过分强调这些学科和门类的独特之处。作为一般研究者,其实不必在意这样的学科藩篱。历史研究工作总是从某个具体选题出发的,无论哪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只要有助于解决问题,都应该积极借鉴和运用。学术研究的突破创新,往往发生在不同学科交叉的边缘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