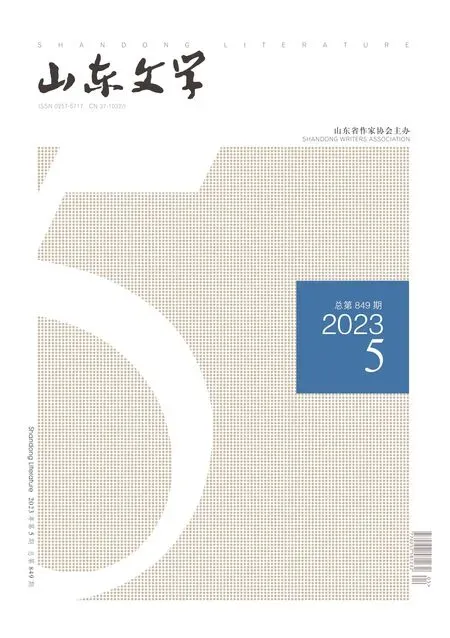潍河滩笔记
韩宗夫
潍河滩的牧羊人
牧羊者三个字听起来颇有诗意,经常出现在诗歌或圣经里,洁白的羊群与明亮的草地,映射在人的脑海中,总能形成一种超然物外的画面感。他们每天率领着一群温顺的羊儿,漫游在不同颜色的草地上,羊群如同草地忠实的阅读者,或俯首帖耳的听众,青草世界的每一种声音,它们都耳熟能详,心领神会。草地吸纳天地之滋养,每天都在蓬勃地生长,广阔而茂盛,喂养几支本地的羊群绰绰有余。
看起来,放牧付出的只有时间成本,轻松简单,人跟着羊群走便是。实际上放牧是一项技术活,考验着一个人的耐心和细心,你要注意观察每一只羊的动态,发现神态异常的羊要及时施治,这是牧羊者所应具备的本领。牧羊者也是被羊群拴住的人,天天围着羊儿转,走不开,个人生活受到限缩。
潍河滩的牧羊人一般都是五十岁上下的男性。五十是一个尴尬的年龄,外出打工已没有优势,不如在家做一个羊倌。拥有一支四十头左右的羊群已经非常客观,外加两只黄毛牧羊犬,这是牧羊者的标配。牧羊犬听话、聪明、忠诚,放牧时帮助主人驱赶羊群、提防掉队者,晚上看家护院,震慑意欲偷羊的人,是牧羊人的好帮手。
羊体味大,为了不影响乡邻,羊圈一般建在村子的边缘。羊圈是乡间最粗糙的建筑了,土墙矮屋,用木棍与铁枝组成的篱笆,围成一个半亩地的小院子。羊棚由厚厚的玉米秸秆组成,用铁丝扎牢,外搭一张防水的油毡,简单实用,只要油毡质量过硬,用个七年八年没有问题。
放牧是个孤寂的营生,是一项以慢为主的运动,他们每天率领着自己的羊群,在自然世界中漫游,每一条土路,每一块草坡,每一片树林,每一处水洼,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和羊的蹄印。牧羊者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创造财富,同样值得人们尊敬。看着自己的羊群繁衍,不断壮大,心情自然是愉悦的,想到羊群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曾经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和草原的放牧者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牧场,除了庄稼地不能去,其他地方都可以,河滩、沟坎、树林,机耕道两侧,都有葳蕤的青草存在。我去潍河的路上经常碰到它们,一拨或两拨,两支羊群隔开距离,互不干扰。
六十几岁的老蒋,是这儿羊界的权威,老头人也实诚,同行有什么事都会找他请教,诸如羊病防治、配种、买卖等,他总是看得比别人透彻,儿子成家后不想让父亲再继续从事这行业,又脏又累,无奈老蒋放不下,自己一个人吃住在羊场,他自己说,干了半辈子的事突然放弃舍不得,自己不是过清闲日子的命。老蒋现在依旧在放羊,身体硬朗,牧羊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潍河滩的青草种类丰富,北方平原上的草木几乎都能在这儿找到,水边草与旱地草,加上各种藏身其中的中药草,羊儿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当然,那些味甘、口感好的青草会成为羊儿的最爱。潍河滩的浅水湾也多,羊渴了可以随心所欲地喝水,真正的有吃有喝。
春天青草刚刚萌芽,也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憋了一冬的羊儿开始出来觅食,想吃饱肚子自然要多耗费一些时间,嫩嫩的芽尖虽然适口,但不解其饥,所以连干草根也不放过。夏天河滩上的草都长起来了,浓郁而茂密,慢悠悠的羊群可以仔细地品尝,样子更像一个美食家。暮秋后青草枯败,杨树林中满地的落叶又成为羊儿的上等牙祭,牧羊人在空闲时把厚厚的杨树落叶收集起来,装满一个个蛇皮袋,用三轮车拉回家,作为羊群越冬的储备。
我坐在河堤上的一块青石上,居高临下,望着河水出神。这块高于沙土地的青石,应该是兴修水利时留下来的吧,表面光滑,俨然已经成为我的宝座。有一支羊群正在附近觅食,牧羊人手提鞭子,漫不经心地走在前面,牧羊犬警觉地跑来跑去,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变化。羊儿们低头吃草的样子非常认真,像是给青草诊断,它们缓慢地前行,偶尔也有开小差的,跑到远处的灌木丛啃食,很快就被牧羊犬撵了回来。
天气预报有雷阵雨,今天,天空不阴不阳,有点闷,水中缺氧,鱼儿更容易上钩,河边有三五个垂钓者显然沉浸其中,之间也没有话语交流。而天空说变就变,不会和任何人商议,顷刻间阴云密布,天昏地暗,豆大的雨滴落下来,河面上浮现出此起彼伏的水涡,扰乱了钓鱼者的视线,他们被迫收拾起渔具,骑上摩托车匆匆离开。我自有准备,去自行车上取了雨伞,雨便噼里啪啦落了下来,垂钓者早已作鸟兽散……
面对从天而降的雨水,牧羊人和他的羊群却表现得异常淡定,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急于撤离的意思,视雨水如无物。对于这样的降雨他们已经司空见惯,羊群仍然在旁若无人地吃草,继续为青草诊断。牧羊人戴着一顶旧草帽,帽檐已破,这是他常规的行头,遮阳遮雨两用。雨滴落在破旧的草帽上,落在羊顺滑的脊背上,落在牧羊犬清澈的眼睛里,一切都那么坦然,呈现出大自然本来的样子。一场降雨也给羊群带来沐浴的机会,在少雨的北方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只有雨季到来的时候,才有可能不定时地享受这种免费的淋浴,冲洗掉羊群身上的污垢,重现自己宗教般洁白的形象。
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雨过天晴,天空放亮,云彩一缕一缕地飘过。河风吹拂,青草皆顶着亮晶晶的水珠在摇晃,刚下过雨的草滩上,羊群如朵朵白云在缓慢地向前移动。
沙 山
潍河东岸矗立着一座巨大的沙堆,俗称“沙山”,其高度虽不是遮天蔽日,但可以阻挡你向远处眺望的视线。记忆是可以追溯的,视线却不会拐弯,只得与沙山不停地对撞,一个庞然大物与渺小的人形对比,孰强孰弱,显而易见。沙山无疑是由一粒粒渺小的沙子组成的,它们的身上还滋润着潍河的水分,水的吸引力让它们紧紧抱在一起,暂时摆脱了一堆散沙的命运。众多的沙子团结在一起,便浮现出强大的一面,坐镇一方,俯视着脚下滚滚北行的河水。
我知道沙山后面是一片蓊郁的板栗树林,正值挂果期,此时也是树林最旺盛和最热闹的时候。蜜蜂、蚂蚁、蜥蜴来回穿梭,各忙各事。燕子低空盘旋,翅膀撩起清澈的河水,水花四溅。白鹭从沙山顶上飞过,没入树林之中,神神秘秘的,说不定又在搞事情。微风吹拂着毛毛虫一样的板栗花穗,花香浓郁,沁人心脾。那片板栗园我曾多次去过,一个新认识的朋友住在那儿,他的村庄被一片板栗树环抱着,生活在绿色的海洋之中,每天听鸟语、闻花香,想必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老刘是骨灰级钓客,兼卖渔具,我们是钓鱼时认识的,他有十亩地的板栗,除了春天施肥,秋天收获的时候忙碌一点,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树木自会按着自己的节奏生长,钓鱼便成了闲暇时的爱好,经常看见他化石一样蹲在河边,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
我居河西,与沙山隔河相望,有时亮开嗓子喊一声,对岸的人能隐约听到。晴天的时候,对岸人物活动尽收眼底,清晰可见。有雾的时候,景物便模糊起来,影影绰绰的犹如仙境。有一个老人经常在沙山周围遛狗,据我观察,他应是沙山的看护者,沙子是值钱的东西,没人看着点不行。他住着两间活动板房,整日守着一堆沙子,有难以言说的枯燥,幸好沙山后面就是村庄,人来人往并不孤单。时常有牧羊者来这儿放牧,羊儿走走停停,对眼前的沙山毫无兴趣,它们的眼里只有青草,只关心青草的鲜嫩与爽口。周末的时候,从城里过来一些钓鱼的人,把车停在沙山前面的大堤上。河道两边,钓鱼者三三两两,几乎做到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只有到了晚上这儿才会变得静悄悄,风翻动树叶的声音,河水拍岸的声音开始清晰起来,有时还能听到野鸡的叫声,或者一两声不知什么动物的声音传来,虚虚实实,河边的人家早已习以为常。
视野之内,沙山如金字塔般兀然矗立着,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蓝色的雾气在太阳的蒸腾下徐徐升起,形成了河岸新的风景。假如一个多日没有回家的人,突然看到这个凭空冒出来的不速之客,难免会怀疑自己的眼睛。与巨大的沙山对视,总有一种压迫感,没有相看两不厌的诗意。这些沙子当然是河流的一部分,如同河流的肉身,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们在河水中深藏了数千年,最后被人全盘端出,被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已无丝毫秘密可言。尽管它们只忠诚于河流,却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当河沙被掏空,河流便会变成一只巨大的水囊,盛满淤泥与各种水生物。此时,河流也开始怀疑自己身体的真实性,一个个旋转的水涡,如茫然的眼神面向天空发出深深的诘问,天空空空如也,没有答案。
河沙又被称为水下软黄金,在铺路、建筑中不可或缺,它的价值也是它的软肋,谁拥有了河沙,谁便拥有了财富。某日,十几艘采砂船挤满了整段河道,犹如黑云压城,景象壮观,一时间机器轰鸣,昼夜不舍。铲车、大头车来回穿梭,把滴着水的沙子运往各建筑工地。鱼儿们哪里见过这等阵势,惊慌得四散而逃。一条河流被现代机械开膛破肚,深睡在河水下的沙子,很快被洗劫一空,来不及运走的河沙,被堆积在潍河岸边待价而沽,形成了今日的沙山。
每一粒沙子的生成并不容易,历经水浪的无数遍打磨。河流每一时期的变迁,都会永久地铭刻在沙子的心里。自河流出现以来,它们便跟随河水的流淌而演变,岩石、水浪、风,经年累月地绞合,溶蚀,磨砺,沉积,最终形成了今天数米厚的河沙。它们沉睡在河水之下,托举着河水,供养着无数水生物、候鸟与涉禽,却没有能力对人类说“不”。河水盈亏可以依靠降雨来增补,河沙却没有再生的可能。被掏空河沙的河流,深不可测,看起来更像碧波荡漾的内湖。广袤的河滩被吞食,河道与大堤之间失去了缓冲地带,水深陡然增加了几米,深浅不一,暗流涌动,让人敬而远之。
我坐在河边,远远望着巨大的沙山,无言。我也看到了对岸的老刘,戴着一顶斗笠,在专心致志地钓鱼,沙山的投影覆盖了半条河流,老刘身在其中,已感知不到背后沙山的存在,鱼儿游到这里,明显地感到了水中的黑暗。
我知道,这个巨大的沙堆,再也不可能重返水中回到河流的怀抱。它们最终将被一点一点运走,直至与河流的联系被彻底切断。河流变得异常虚弱,浅浅细浪拍打着两岸,已经看不出是否还在流动……
丑树,或洋槐的抚摸
洋槐即刺槐,是本地最常见的树种,因其树枝上长满了硬硬的针刺而得名。在植被茂密的潍河滩,河堤上下,机耕道上,你随便一个转身,就能看见它们的身影,或挺拔,或扭曲,或旁斜,清癯俊逸,扶摇直上,把硕大的树冠送入空中。在沟渠,在河湾,在岭脊,在长满杂草的荒坡上,由刺槐组成的小树林到处都是,高高矮矮,长幼有序,一看就是有传承的一家人。它们朴实无华,适应性强,对土质要求不高,只要有一席容身之地,就深深扎下根去,然后从脚下开始,逐渐扩大自己的队伍,越是贫瘠的土地上,越少不了它们坚守的身影。
乡人们习惯称其为“洋槐”,一直这样叫,也没觉出有什么异样,以为洋槐就是它的本名,是土著。但从字面意思看,一棵树用“洋”字来命名不是没有缘由的,像“洋油”“洋火”一样,并非空穴来风。洋槐有着美洲血统,18 世纪时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入乡随俗,迅速站稳脚跟,经过三百多年的风雨磨砺,早已去掉“洋”字,成为十足的下里巴人。我们的祖先把它引种过来,定是看中了它好养活,耐干旱,繁殖快,不挑地,随遇而安的特性。在农耕时代的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使用价值,因其木质密实而坚硬,不易腐烂,可以打制各种农具,比如犁杖、马车、牛锁头、锄柄等生产工具。长得粗一些的大树,又可以制作房梁、门框、家具等。
在通向潍河的土路上,两边全是洋槐的兄弟姊妹,有笔直有弯曲,看起来各有各的想法,队形由原来栽种时的一条线,变成了后来的多维视图。一些沟壑的两侧,洋槐的生长更为夸张,有的甚至横跨在沟上,裸露着蛇形的树根,树根蜿蜒到那里,小树就生长到哪里。在高低不平的河堤上,往往你栽下一棵树,多年以后就会生成一片小树林。绿化环境,固沙封土,洋槐为捍卫潍河大堤的尊严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它们也是坟茔中的常客——除了零星的几棵松树外,几乎全是洋槐的天下,在远离村庄的野外,洋槐们撑起自己硕大的树冠,用自己的身躯为故去的先人们遮风挡雨,年年岁岁,毫无怨言。
褐色的树皮,周身布满由浅至深的纵裂纹,其丑无比,酷似老农皲裂的手掌。椭圆形、拇指大小的对生叶片,让它更加其貌不扬。除了长相丑点,洋槐大部分时间都是美的,让乡间道路绿荫成行,让各种农具遍布田间,让火车从自己的身躯上隆隆碾过……骨感的枝条疏朗向上,树冠高大圆满,叶子活泼浓绿,随风摇曳,成为潍河滩不可或缺的风景。
五月,植物的盛花期如约而至,白色的洋槐花一夜之间爆发,密叶交互之中,倒挂着一串串白得优雅的花穗,空气中飘满了一股浓郁的香气。这时最忙碌的是蜜蜂们,舍不得这么好的花期白白浪费,于是在槐花开放的这段时间里,不停穿梭奔忙,认真地亲吻每一朵槐花,意图把洋槐最美的部分酿为花蜜珍藏。自然,槐花也是可以食用的,撸一把槐花撮进口中,甜甜的馨香在齿间萦绕,咀嚼之后有一种醉酒的感觉。我犹记得小时候,母亲把红薯面粉和槐花和在一起,平摊在笼屉上蒸熟,那口感甜糯香艳,味道极好。
夏天到了,树上的知了尤为亢奋,越燥热的天气叫得越吃劲,叫得人心烦意乱,幸亏有河风送来阵阵凉意平衡一下。大批的蚂蚁爬上爬下,是在寻找食物还是在练兵?树冠之上的微生活,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更有甚者,蚂蚁依靠纵裂纹的结构,叼来点点土粒,把自己的行宫建在树上,成为高树上的居民。进入秋天,有一种虫害非常恐怖,它们噬吃洋槐的叶子,繁殖速度特快,几天时间就可以把一棵树的叶子消灭干净,而后像蚕一样吐丝成茧。这种虫子聪明得很,成茧时有一头是留口的,把丝黏在树枝上,然后一边拉丝一边从高空向下坠落,吊在半空之中荡起了秋千。那段时间,树下的空气中都吊着这种讨厌的虫子,经常碰到我们的额头,我们称它“吊死鬼”。
冬天对于树木来说是一种解脱,褪尽那些被虫害镂空的叶子,一身轻松地进入冬眠期,然后陷入沉思或回忆之中。这时我能清楚地看到洋槐那些嶙峋的树枝,纵横交错,刚直不阿,迎风招展,呈现出钢铁一般的意志。白天太阳从河东岸的树林中升起,橘红色的阳光,像温暖的血液一样传遍树木全身,给洋槐带来信心和力量。晚上,铁青的树枝刺破浓浓夜色,让薄薄的月光流泻下来,对大地进行温存地抚摸。猫头鹰神一样蹲在粗线条的树枝上,屏住呼吸,观察着大地上出没的猎物,时刻准备着俯冲而下……
人在草木中
在河边的一块草坡上独坐,像一种仪式。
我不定时来到这儿,身随心性,清心寡欲,暂时远离纷纷扰扰的世俗生活,纾解一下绷紧的神经,我的眼睛里只有流水和芦苇的影子,落入水中的云彩和天空中飞舞的白鹭。远离小镇,选择和河流坐在一起,河水的流动带来了无限可能,固有的思维被宽阔的河水打开,河水裹挟着我的思绪,流向更宽处更远处。平日坐在一只箱子里的感觉,此刻被瓦解了。我敞开衣襟,愿风也吹进我的内心,在内心深处打造另一条河流,另一片草坡。在小镇上,我也没有更多的地方可去,自享孤独,农人的心思都在土地上,商人的重心在生意上……我的心思在别处,我是一个异类,看对岸金光闪闪的沙山,看不停翔集的燕子们,看钓鱼客成功起钓后的喜悦……有时候什么也不看,也不想,望着远行的流水发呆。
我的前面是一条小河的入河口。一条小河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经过千辛万苦跋涉之后,终于抵达终点,投入到潍河的怀抱。潍河沿线,像这样的支流不下百余条,它们的流程普遍很短,没有明显的发源地,靠丘陵中一点一点渗水汇聚而成,只有在雨季,才有机会看到一条小河奔腾的样子,在乡间大地上蜿蜒前行。在旱季,小河就有断流的危险,许多支流其实就是季节河,生存下来要看天气的脸色。小河一路走来,经过无数的庄稼地和村庄,收集了丰富的腐殖质和有机物,因此,西去河口数百米,植物生长格外旺盛,甚至有些疯狂,茂密的芦苇与蒲草,几乎把整条小河覆盖。潍河滩的芦苇都是小芦苇,茎秆纤细,身姿柔软,与湖泊中高大的芦苇相比相形见绌,虽然没有多少利用价值,却成了鸟儿们的乐园,野鸡、斑鸠、窝篮是这儿的常客,经常有不知名的鸟儿突然从中飞出。
我坐的草坡上,绿色的草皮刚刚长成,开满了白色、黄色的野花,犹如夜空中的点点繁星。我的背后则是一大片盛开的格桑花,构成一条缤纷的花带,五颜六色,非常漂亮。格桑花是人工种植,花期长,从春天一直开到霜降,招蜂引蝶,非它们莫属。除了苦菜花,其他的小野花我叫不上名字来,它们各有各的媚态、颜色,精致的花瓣不尽相同,人有斗舞之爱好,花有斗艳之乐趣。苦菜是开得最为普遍的一种野花,到处都是它们孱弱的身影,从不嫌弃土地的肥沃与贫瘠,见缝插针,生长在大地的任何角落。一蓬刚刚秀叶的棉槐,挑着几截瓜蒌枯萎的秧蔓在迎风招展,这是去年的瓜蒌,虬曲的秧蔓干枯后,其纺锤状的果实随着水分的流失慢慢炸开,白色的瓤分离成无数带着种子的小伞随风飘散,繁衍特性与蒲公英相同,种子落在哪儿,哪儿就是家,不用担心后代延续的问题。不远处的一个枯树墩上,冒出了几只妖艳的蘑菇,我小时候就知道这种蘑菇是有毒的,靠自己的美丽诱使牲畜上当,枯后的样子像一摊家禽的稀便,很脏,我们也懒得去招惹它。
进入夏季,气温上涨得非常快,各种青草次第生发了出来,大地上到处都是簇新的新绿。在太阳的照耀下,青草们一天比一天进步,几天不见,绿色很快就覆盖了大片的河滩和土坡。这片草坡绿草如茵,有明显被羊的牙齿修剪过的痕迹,这时候的青草非常适口,口感极佳。羊群的队伍走过后,留下一些黑色的枣形粪便,其中一小撮正和一蓬生长旺盛的牛筋草依偎在一起。远处是一处开阔的河滩,一个大人正在陪着孩子玩纸飞机,孩子玩得很尽兴,今天风不大,不用担心纸飞机被风劫持落入水中。河边的小码头上拴着两只铁皮船,它们是养鱼人撒饵料、下网时用的,现在正紧紧地靠在一起,安静如听话的孩子。河中心的小沙洲上,已经长满了茂密的芦苇,它们正在不加控制地拔节,直至把整个沙洲覆盖。这样的小沙洲居于河心,远离人类的干扰,是涉禽歇息和繁衍的乐园。有两只白鹭时而低空掠水,时而飞上天空,无拘无束的样子让人羡慕。
每一片草地都是由各种各样的草组成的,葎草、小蓬草、车前子、曼陀罗,是这片土地的常客,决明子、紫花地丁、地黄等中药材也偶而遇见,水边的草和岸上的草又各有不同。正是这些看起来卑微的草们,织成了潍河滩绿色的地毯,跟着河水向远方蔓延,护卫着潍河两岸柔细的沙土,养育着无数的昆虫和小动物们。
麦田、蝴蝶、云雀……没有乌鸦
去潍河,必然要经过这些麦田,这儿有两三米宽的大路,也有仅供一人行走的小路。
当我从它们中间献出的小路上穿过时,满是锯齿的麦叶会不时地蹭到你的小腿,试图拦下你,你不可能对它们熟视无睹,不可能无动于衷,它们鼓足了勇气,或许有什么秘密要向你吐露。走着走着我就想蹲下来,坐到田埂上,用人的语言跟它们聊上一会,手托着那些沉甸甸的麦穗,感知它们思想的温度,静听它们茎管里生命的脉动。
临近潍河的土地,沟汊和水塘渐多了起来,把田地分割成一些小的单元,没有特别大的地块存在,不适宜大型机械作业,人工的活儿比较多,本身泥土就是消磨人的东西,翻土,种植,管理,收获,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儿。农人因地制宜,喜欢什么就种什么,可以种庄稼,也可以种蔬菜,所以一块麦田夹在豌豆地和大蒜地之间很正常。农人三三两两在田地里忙碌,有的施肥,有的喷药,有的除草,在太阳暖烘烘的照射下,汗水很快湿透全身,偶尔直起腰来,放松一下继续干。
潍河滩属冲积平原,沙性土壤非常松软,且水源无忧,只要舍得施肥,作物的收成还是有保证的。当然,这些补丁似的小麦田,和大平原连片的麦田不可同日而语,它们分散而生,在包围其他农作物的同时,也被反向包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如同穷人家的孩子也是孩子,这儿的麦田,也同样经过漫长冬季的历练,春天分蘖、抽穗、灌浆,夏天成熟和死亡,该有的经历、该吃的苦一样都不会少。
春分后天气转暖,麦子被春天的荷尔蒙刺激着,是生长得最快的一种植物,嗖嗖拔节,一天一个变化。道路两侧则长满了蓬勃的荠菜和麦蒿,荠菜作为一种野菜,近年来被人们重新认识,作为一种高档菜被请上餐桌,炸炒煎拌,各种新奇的吃法也同时炮制出来;而麦蒿显然就是麦子的陪衬,常常隐蔽在麦子中间,和麦子一起成长、成熟,毫无利用价值,被农人们嫌弃,见之必拔而除之。清明节后,大片的麦子在五月风的指挥下,前倾后仰,一刻也不消停。白蝴蝶在麦田间翩翩起舞,像一位仙气满满的小姐姐,妄图挑唆躁动不安的麦子跟它一起私奔。一只云雀受到了人声的惊扰,突然从麦地里起飞,乜斜着射向天空,然后陡然转身,朝着潍河的方向飞去。或许它正孵化自己的宝宝,只怪自己胆子太小,总担心被人发现,结果自己暴露了自己。当行人离去后,它们再悄然返回,继续孵化自己的后代。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蜥蜴还是麦田的常客,它们善于捕捉尺蠖、蚂蚱、飞蛾等害虫,在麦田里匍匐穿梭,充当了麦田的卫士。后来随着化肥农药的普遍使用,蜥蜴的生存环境遭到了破坏,致使这一物种彻底消失。今天,蜥蜴的存在已经成为传说,或许它们早已经化为一条条小龙,永久地飞行在麦田上空,收集云彩制造雨水,惠泽着家乡的每一寸土地。
当我读到梵高的画《麦田上空的鸦群》时,竟被深深地震撼了。风雨过后的瓦滋河畔,兜满雨水的靛蓝天空沉重地下坠,朝着麦田中心疯狂伸展的红色小路,剧烈地扭曲着,金黄的麦田发出最后的呐喊。低飞的鸦群环绕在麦田上空,犹如群魔乱舞。梵高借助麦地,演绎了内心复杂的情绪,希望与绝望,宁静与冲突,心灵的剧烈波动和强烈的压迫感一同跃然纸上,给人一种即将告别的悲壮情怀。
麦田成熟后待收割时的状态确实是悲壮的,绿色的麦芒已经化身为金黄的箭镞,齐刷刷地指向天空,像一种挑衅,空气变得紧张而凝重,只差一声呐喊引爆。而澄明的天空是无辜的,承受不了如此激烈的逼宫,被迫以雷雨的方式来释放内心的压力,这就是每到麦熟时节,降雨格外多的原因,增加了收获以及晾晒的难度。当天气转晴,浓烈的太阳依然毫无保留地照耀着麦地,加速了麦子迈向死亡的过程,从潍河上空飘来的漫漫水汽已经无力改变现状,反而渲染了这种相杀的气氛。
最后,直到麦子收割完毕,也没有乌鸦飞来,在麦田上空发出低沉的哀叫。
桃花无惧春风吹
从桃园归来,卸下潍河湾的风尘,我一直想写点啥,但情绪酝酿不起来,下笔时难免力不从心。好在没有交“作业”的压力,时间伸缩自如,仍有一种无可名状的紧迫感。既然,没有足够的心力去挑战那些魅惑之树,不如让它们兀自开花,兀自结果。植物的狂欢与盛宴本来与己无关,但与春风有关,与春天复苏的土地有关。春风吹呀吹,把我的忐忑都吹绿了,桃树们却一脸陶醉状,享受着春风的沐浴。
春天一旦开跑便没有暂停键,我们只有在后面追赶的份。当我下一个时间点去看的时候,万千花蕾闹春的景象早已翻篇,只有满园的嫩绿叶片和心尖一样毛绒绒的幼果,在春风的吹拂下,恣肆汪洋,开怀畅笑。那些日子,每就寝之时,我的脑海里全是桃树,顶着一树张狂的花蕾,升起一片粉色的云霞,干扰着我的睡眠。看来在交出“作业”之前,我的脑子固定是乱的,总是在混混沌沌、迷迷糊糊的意识下进入了梦乡。
梦与非梦,它们就在那儿真实地存在着,按着自己的节奏成长;思与非思,并不影响春风的深入程度,如同屠苏入口,很快就运行到身体的每一个节点,大地的生理同样如此。
我与大哥之前就是认识的,小镇很小,人与人之间碰面的机会就会增多。在小镇上待久了,有一半是你的熟人,剩下的另一半似曾相识。
我去潍河湾喜欢走一条小路,骑着自行车,在这样的羊肠小道上也走不快,也不需要走得太快,而忽视了周边植物的注目之礼。春天,植物们刚刚出世,没有一处不是新的,大地因为反复耕种而陈旧,又因横空出世的绿色植物而获得新生。每次碰到大哥的时候,只是礼貌性地打个招呼,并没有闲聊,我只知道这儿有他家的地块,具体种什么,并不知情。直到有一天我路过桃园,看到他忙碌的身影才豁然开朗——原来大哥每天步履匆匆穿梭此地,侍候的是这儿唯一的桃园。
潍河湾有大片的苹果园、核桃园、板栗园存在,桃园却凤毛麟角。并非河滩地出产的桃子口感不好,而是因桃子不耐贮存的特点,影响了它的种植面积,所以在潍河湾广袤的土地上,能存在这么一个桃园已经不错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大哥夫妻二人以经营这片桃园为主,三四亩地的园子,除了桃树,还有各种时令蔬菜,成熟后到集市上售卖,日常的开支就靠这个小小的园子。园子的外围有一圈花椒篱笆,花椒刚生出的嫩叶还没有完全展开,纵横交叉的枝柯清晰可辨。他们在园子里盖了两间简陋的小屋子,供暂住之用,农闲时还是会回到镇子上居住,这里的条件毕竟太艰苦。
桃园的北面是一片坟地,潍河沿岸的村庄,坟地大多靠近河边,河边林木茂密,鸟语花香,河水朗朗,是绝佳的风水宝地。清明时正是桃花怒放的时候,对于前来扫墓添土的人来说,热烈奔放的桃花萌生出一种悲壮气氛,故人远去,桃花相送。晚上在园子里睡觉,想必会听见各种奇怪的声音,无法求证声音的来源,心里会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并非枕着波涛睡觉那么浪漫。但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养家,问心无愧。
寒食前后,花朵们轮番开会,杏花、桃花、梨花、枣花,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地始终沉浸在浓烈的节日气氛中。那天我去的时候,大哥家正在种花生,昨夜下了一场春雨,土地湿润,正适合开土种植。我帮不上忙,就自己去看桃花,怒放的桃花夹杂着含苞待放的花蕾,妩媚妖娆,一朵桃花就是一位小仙女,向天空释放着自己的馨香。有一只大黄蜂在花朵之间飞飞停停,流连忘返,不像是在采蜜,更像是在撩妹。如火如荼的粉红花瓣,就像一片火烧云浮动在桃树之上,让人芳心乱颤。自然,这样的描写很俗套,如果有机会,还是亲临现场体验最好,视觉之美远胜于挖空心思的辞藻。
昨夜春雨,还打响了今年的第一声春雷,雷声虽然有点沉闷,但吹响了春耕的号角,预示今年风调雨顺,是个好兆头。春风吹过,树身下落满了一地凋落的花瓣,深粉浅粉,美艳一片,妖冶如美人之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