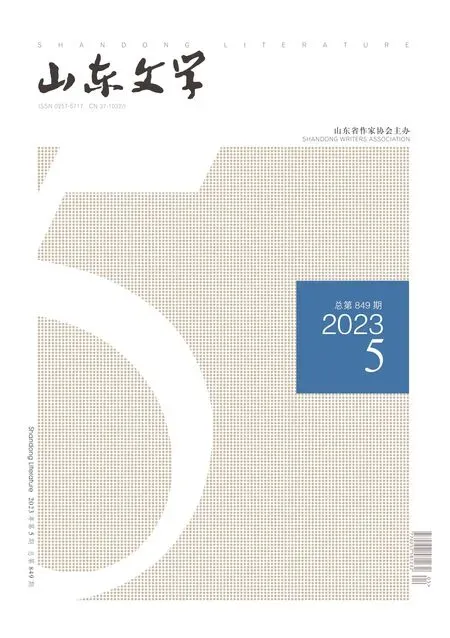叙 旧
魏思孝
应李智之邀,陈圣去外地。晚上的酒局,除了与李智叙旧外,陈圣照例也认识了两个新朋友。因席间没有异性,他们兴致索然,喝酒以及言语上多有克制。李智几番略显冗长的地主之谊的客套后,谈资顺利过渡到他和另两位的友谊及自身趣事上,气氛总算活跃了。陈圣也放松下来,享受着被冷落,不再费心去寻找话题,只是边吃边喝,听他们去说。李智劝他俩少喝点,指着小吴对陈圣说,上次喝酒,他骑着电动车掉沟里了。陈圣取出口中的肉串,回应一个吃惊的表情,问真的吗?小吴羞怯地点了下头,撸起袖子,亮出结痂的肘部。小于在旁应和道,上次喝完,我半夜起来,坐在床上吐了一被子。说完,小于拿起塑料杯,浅抿了一口白酒。李智略微无奈地摇了下头,颇有些自豪地对陈圣说,我这俩兄弟,太实在了。夜幕降临,烧烤摊亮起彩灯,食客逐渐多了。其间,下起细雨。他们合力把餐桌搬进餐馆的过道,又畅饮一番。
李智送陈圣回到酒店,烧了一壶茶,两人又聊了会。内容无他,关于小吴和小于的为人,陈圣更为坦诚地交了底。当然,碍于李智一向宽厚的性格——可以说是和善,所讲的多为赞美,男性友人间常见的词汇都用上了,比如,情同手足,肝胆相照,可以托孤。至于他们身上的毛病——酗酒、不顾家等,属于回归家庭后的私人生活,不妨碍朋友间的交往,作为外人,也没有可多指责的地方。甚至说,有这样真性情的朋友,为庸俗的日常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可以让朋友恰当地幸灾乐祸,对照之下,消解各自生活中的苦闷。他们对李智如此言听计从,尊崇其为大哥,盖因他是个有办法的人,不说是三教九流,至少政商两界都能用上劲,比如小吴在电厂的工作,就是李智给找的。
陈圣上次来——也是第一次,是三年前。当时为了陪他,李智也找了两个身边的朋友。三年前的那两个朋友,并不是小吴和小于。上次的那两个朋友,逢年过节给陈圣发来祝福的信息以及偶尔在朋友圈互赞——这就是全部的交情。这次来之前,陈圣心想还能如三年前见到这两个人,晚上入座吃饭,李智介绍小吴和小于时,他心中困惑,出于礼节并没有多问。现在,陈圣问,那两个人呢?李智抽着烟,身子卡在狭小的椅子里,艰难地挪动了下,语调得意,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陈圣早已在心里准备好了答案,只等去匹配,无非就是李智和他们这三年间发生了些不愉快,或是性情不合,被他从自己的核心交友圈除名,没有资格见到陈圣了。李智说,高传厚死了,范兴消失了。这都发生在一个月前。陈圣意识到,最近一个月,确实没有收到他俩友好的点赞互动。自然,不久前的中秋佳节,他俩也没有发来问候语。事情本身,对陈圣来说,倒不如李智的表现更可玩味,把他倾诉时的兴奋感说成幸灾乐祸并不合适,但确实在李智的脸上找不到悲戚。上次见面,他们称兄道弟的画面,还留在陈圣的脑海中。也许是酒精的刺激,或是照顾陈圣的感受,更深一层原因,对于李智来说,陈圣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既认识高传厚和范兴,又不在这个圈子里,可以毫无顾忌谈论。此刻,陈圣也突然明白,李智为何强烈邀请他过来,好久不见,甚是想念,道理也说得过去。而他口中的叙旧,并不是叙他俩的,而是另有所指。对于这三年陈圣是如何过来的,李智并没有什么兴趣知道。
晚些时候,李智离开酒店。陈圣洗漱完毕,依着床头抽烟,他并没有感受到身处异乡的孤独。从长时间的社交模式中解脱,身心自在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这个标准间内除了他,还有先前李智用语言编织的两个人的身影。高传厚躺在旁边的床上,按照李智的描述,他在喝过一场大酒后,怕回家被父母训斥,去了工厂宿舍。第二天早上,工友发现他躺在床板上,衣不遮体,脸色发紫,嘴角保持着一丝微笑。工友报警后冷静下来,顺势拍了现场照片——不知是害怕担责任,还是猎奇留个纪念。据李智了解,不少工友看到了高传厚死时的照片。一个月后的这天晚上,李智从手机里找出照片给陈圣过目。不像是死了,这是陈圣看完后的感受。至于死因,家人不愿意尸检,并无定论,对外说是猝死。陈圣点开高传厚的微信头像,他戴着一副墨镜,张开双臂,小腹露出的肚皮如腰间系着一条大鱼,站在山间一条公路的界碑前,背后的公路蜿蜒通向远处的高山。四周植被矮小,山头也并不宏大,云朵压得很低,大概是在青海或是西藏。朋友圈显示是一道横线,其余空白。陈圣还记得,高传厚的微信签名是:吃好,喝好。
三年前的那次饭局,对陈圣来说,早已记忆模糊,和过去繁多的各类饭局一样,大致是沉闷的,从没有让他静下心仔细去回味。现在,因当时在场的两个人的遭遇,他努力从脑海中打捞,希望能捕获到关于高传厚的一鳞半爪。高传厚确实善饮,举止言谈称得上豪爽,同时又特别注重礼节,对陈圣一口一个哥,并且颇为心细地关注饭局上的任何动态。陈圣作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尤其是他口中大哥(李智)的好友,但凡茶水不多,或是需要纸巾,以及服务员端来一盘菜,他都第一时间起身——足有二百斤的体重,倒茶递纸,或礼让他尝下菜。高传厚一次次起身,陈圣也只好一次次口头表达感谢。忙乱之下,这顿饭陈圣吃得身心俱疲。可此刻陈圣又不得不感慨,这是一个多么讲究礼数的人,天生就应该长在酒桌上,何况他酒量不小,说举杯,就举杯,说喝光,就喝光,没有一丝扭捏和拖沓。这么说,高传厚把自己喝死,也是他还算熨帖的归宿。一如李智在他死后,面对陈圣所下的结论,我早知道他有这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么快,才三十二,女儿还不到一岁。陈圣望着旁边的床铺,高传厚平躺着,多年如一日胡吃海塞的身躯溢出单人床,如一头快要出栏的猪(没有任何贬义)。高传厚体态臃肿,可并不笨拙,称得上是敏捷。酒桌上的他们,像是为了消暑,置身在河水里打麻将的巴蜀地区人民,高传厚每次起身去服务,在落座之际,庞大的身躯激荡着水流,令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跟着摇曳。陈圣转头看向床上的那具遗体,点头,心道,他可是消停了。
陈圣不记得范兴的长相,他望着房间,李智编织的那些话,也没有把他塑形。他消失了。三年间,范兴的父母变卖在市区的两间门头房,为他偿还了赌债。蛰伏一阵,在取得了家人的谅解后,范兴到处借贷,在各类境外博彩网站下注,没过多久,一切都不可收拾。追债的电话让身边的亲友同事不厌其烦,他适时消失。李智说,警察都找不到。陈圣多少明白了李智的感受,高传厚和范兴的悲惨遭遇,确实有一种让人无法回避的幽默。范兴到底能去哪里呢。面对陈圣的好奇,李智伸出手指,无非就那么两种。一,活着。二,死了。
起初,亲人和债主,都以为范兴没死,就是欠债跑了。这也不是第一次了。除了咒骂,也没有别的办法。这次他玩得比较大,可查的欠债已有一百多万,还有各种网贷没计算在内。李智补充道,这又过去了一个月,利滚利,两百万是有了。陈圣问,他欠你多少钱?李智说,他找我借,我没给,我早知道他这毛病了。以往,范兴躲出去,待个十天半个月,混不下去,也就回来了。这次有点久,一个多月了,没有任何消息。或许他手里还有钱,正在某处逍遥快活。要知道,疫情防控,寸步难行。一个现代人,不可能没有任何消费记录。家人报案,警察追踪不到手机,身份证也没用过。这不符合常理,除非他风餐露宿,或者偷渡出境了。李智说,也不用太悲观,他可能就是死了。陈圣还想再知道点什么,比如家人和债主们的反应,或者关于他生活上的点滴,又心想,再问下去,李智说起来没完,这已经快十一点了,他也累了,便默不作声。李智脱掉外套,又续上一根烟,范兴是独生子,还好给父母留下了个孙子,他真死了也不是一件好事,那点家底快让他给造没了,这次还债,把房子卖了,还堵不上窟窿,就算这次还了,还有下次,他改不了的,上次把小拇指给剁了,去医院接上,两三万打了水漂。陈圣附和道,他真勇啊。不是我不讲情面,李智继续说,人死债清。一番沉默,陈圣吁出一口气,可是他怎么死的呢?凶手就在这些债主里,李智说,早晚能查到的。
早上六点多,陈圣被淅沥的雨声吵醒,睁开眼,一片明亮。昨晚李智走后,房间里烟雾缭绕,为了通风,他没关窗户,更没拉窗帘。他下去拉齐窗帘,躺回床上又睡了片刻,并做了个短暂的梦。三年前,他们在餐馆喝完酒,招呼服务员把碟盘收走。高传厚喝多了,蜷曲在椅子上睡觉。李智、陈圣和范兴在打扑克,斗地主,赌钱。范兴手气不佳,总是当地主,总是输,又一次次兴致盎然,继续斗。梦里,范兴的脸只是一张完整的皮肤,没有五官。李智摇醒高传厚,问他和范兴,如果三年后,你们就死了,这三年,你们会做些什么呢?没等到回答,陈圣醒了。地灯亮着微弱的光,他胸口一阵发闷,歪头拿起矿泉水,喝了一大口,又点上一根烟,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彻底清醒过来,不知身在何处,心脏在下坠,就快要脱离身体,似乎刚才不及时醒来,他立刻会死掉。梦里的问句,也正追问着他——如果你只能活三年,会做些什么呢?陈圣下床,拉开窗帘,外面的马路上车流不息,他感觉好了许多,拿出手机,给沈灵发了条微信,说他来了,问她要不要见面。等了几分钟,没回音,陈圣先去洗漱,赤身从浴室出来后看到了沈灵的信息。她说在,问陈圣在哪里。陈圣发过去酒店的位置。沈灵说,离我家不远,你来我家吧。又问,你怎么突然来了?陈圣说,来找李智。
出了酒店,雨还在下。天气降温,陈圣穿着衬衣,昨天来时心想就住两天,也没带什么衣服。开车,上路。天空涌动着大块乌云,如初春河水刚解冻,冰面开裂,碰撞着顺流而下。市区有些拥堵,上了高架,巨大的山体出现在路的尽头,令来自平原的陈圣一阵悸动,把自己想象成蚂蚁。顺着山脚下的盘山路,又开了一会,穿过一段几百米的隧道,出来后雾气笼罩,视线变得模糊。陈圣打开空调,吹前挡风玻璃,清晰后,又关上,如此反复五六次,来到一处社区,四周有些荒凉,不时有雾气从路边的断崖升起。陈圣下车,去保卫室填好登记表。进去后,沿着道路,茫然开了一会。沈灵站在路边,打着伞,披着一件色彩斑斓的裹身围巾,见陈圣摇下车窗打招呼,伸手示意他去停车,自顾先往单元楼走去。陈圣下车,冒雨小跑过去,跟在沈灵的后面,在雨伞的遮盖下,只看到她的腰身,以及脚后跟处一道类似梵文的文身。三年前,陈圣没发现沈灵有这文身,也可能有,只是他没注意到。当时,他俩是晚上见的面,光线不好,在路边站了一会,就去公园散步,树荫斑驳,彼此的长相都没看清,何况是脚后跟。走进电梯,陈圣和沈灵相对而站。沈灵抬头看了他一眼,忙又低下说,你这人可真有意思,三年没见,突然来了要见面。陈圣说,上次你不是住在这里吧。三年前,陈圣也想去沈灵的家,没去成,具体原因他已经忘了。沈灵说,市区房子小,住不开,留给我爸妈住了。
出了电梯,先是入户的走道,因只有住户能自由进出,沈灵平时用来放鞋子和杂物,防盗门敞开着,她换好拖鞋,嘱咐陈圣不用换,没这些讲究。客厅南北通透,南边一组环绕式皮质沙发,中间茶几上放着些杂物。陈圣过去坐下,从面前的液晶电视屏上,看到自己局促的身姿,又装作自然,后仰,双手放在腹部。沈灵换好衣服,从卧室出来,一身黑色的紧身长裙,端来两杯水,坐在陈圣的左边,用手拽了下裙摆,翘起二郎腿,脸上还是她一向的平静,又问陈圣怎么突然来了。陈圣说,李智喊了好几次,就来玩两天。和三年前不同,那时陈圣确实有点事,这次单纯是来玩。至于李智,上次因陈圣的介绍,沈灵也认识了他,更为巧合的是,两个人过去在同一所中学念书。这三年间,他们间的来往更多一点。陈圣又说,早上发信息时,也想到三年没联系,就这么突然问,是有些奇怪。说三年里一点联系没有,也不准确。一年多前,沈灵问过陈圣在不在,当时她要去他所在的城市。陈圣问,当时是怎么回事?沈灵说,我忘了具体什么事,后来我也没去。我要不来,陈圣问,你今天打算做什么?沈灵说,吃饭,看电影,就这么待着吧。那我来了,你也可以这样。陈圣说完,看向沈灵。她坐着,意识到有人正在看自己。安静,也听不到外面的雨声。
十余年前,陈圣和沈灵在一个音乐论坛上混。仅此而已,也没过多的交流。只见过两次,包括这次。是老朋友,更是新相识。此刻,他们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中间隔着没有一本书的距离,各自想找一些谈资。共同认识的人,是一个恰当的内容。沈灵先说了一个她的好友。陈圣几年前见过一次,后来也没有交往,便问她怎么样。沈灵说,我刚才和她说,你在我家。她看了下手机,又说,这么早,她大概还没醒。说完,她笑起来,似乎已经预料到朋友的惊愕。陈圣说,她肯定纳闷,你怎么会和我有来往。沈灵说,不会的,她人挺好的。陈圣说,是我这个人不行。沈灵说,你也挺好的。陈圣说,昨晚和李智一起吃饭,知道你不喜欢这种场合,再加上都是男的,也就没喊你。沈灵问,你们几个人?陈圣说,三个,另外两个也是新认识的。沈灵说,李智认识的人可真多。陈圣问,你和李智见面多吗?沈灵说,见过几次,也都是一桌人,说不上几句话,不过他人挺好的。这时,沈灵拿起茶几上的手机,乐了起来,放在陈圣的面前。对话框的上面,沈灵发过去一张照片,是她拍的陈圣坐在沙发上的侧脸,先是问,认出这是谁了吗?知道这是陈圣后,朋友回道,向他问好。沈灵抽回手机,准备回复。陈圣拿起茶几上的杯子,喝了一口,陷进沙发。这次,他把身体的重量全都放下,没有任何的保留,如同被人从背后抱住。沈灵回完信息,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自顾说道,最近下了一些电影,还没来得及看。
沈灵年轻那会——二十岁出头,大学毕业后留在南方,工作以及恋爱。生活习性上,已经完全融入了南方,天气潮湿,饮食清淡。没有亲情的牵绊,她十多年间过得自在,感情上伤害别人,又被人伤害,留下一段婚史。三年前,母亲生病,沈灵作为独生女回到老家。母亲出院后,她定居下来。主要是南方也没什么牵挂的,沈灵作为艺术工作者,失业很久,存款几无,湿冷的气候让腰部疼痛逐年加剧,和前夫时而的纠葛,更令她失眠。每年沈灵也外出,会友或寻找素材,至多待一个星期,便回到原籍尽孝。她这样的履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再过两年,沈灵就四十岁了,她也清楚,很多事情并不是自己可以做主的。三年前,陈圣和沈灵见面时,她刚离婚不久,情绪不太好,把陈圣作为男性样本,问了他一些对婚姻的看法。陈圣那会,也正处在感情的漩涡中,对女性也多有指责。总之,对方说出的言论,总会引来奚落。不过,其中有句话,如今看来,又一次得到印证——时间是最好的良药。陈圣不知道沈灵这三年是怎么度过的,看上去已经从阴影中走出来。作为一个离异的单身女性,住着宽敞又放满杂物的房子,宁静又充沛。注意到陈圣在打量房间,沈灵解释说,没来得及收拾,你也不是外人。陈圣明白,这不是把他当做亲密的朋友。只是一句客套话。背后的意思是,沈灵不觉得陈圣的到来有多么重要——值得她去打扫卫生,以及对自己一番打扮——她确实没有化妆。
在沈灵拨弄遥控器挑选电影的间隙,陈圣观察着她,烫卷的长发垂下,嘴唇翘起,一件修身的黑色长裙,双腿丰盈,凸显出细腰。陈圣感觉自己被她身上散发的气息笼罩,回到青春期时对成熟女性的仰视中。不同于面对青春尚在的女性,只是为了占有,他完全放弃了攻击性,少不经事,缺乏任何经验,等待着被关照,任其摆布。沈灵转头问,这个电影你看过吗?屏幕上出现韩文,片头过后,黑白片,冬日的海边,一男一女在散步,长镜头。陈圣说,感觉是洪尚秀的。沈灵说,对,他的老片子。陈圣说,太闷了。很久前下的,沈灵说,一直没看,我还挺喜欢他这种风格。陈圣问,什么风格?就是看他的电影,不妨碍干别的,沈灵笑起来,走神几分钟,不影响剧情。陈圣说,还是看点别的吧。沈灵继续说,他的片子,给人感觉性冷淡。陈圣说,但他这个老男人,找了个小姑娘。沈灵说,不是有句话,男人其实很专一,他们都喜欢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吗?陈圣笑起来,还有一句话,判断一个男的是不是渣男,把手放在他鼻子下面,还喘气,就是渣男。
沈灵点开《燃烧》,问陈圣,这个你看过吗?陈圣说,看过了。沈灵说,我还没看。陈圣说,可以再看一遍。沈灵问,好看吗?陈圣说,这女的赤裸着上身跳舞,我很喜欢。沈灵说,是因为她没穿衣服吧。陈圣说,也不全是,她后来哭了,很动人。沈灵放下遥控器,陷进沙发,拿过一个抱枕,挡住肚子,那就看这个吧。电影放着。男主出来,沈灵问,这个人叫什么来着?陈圣说,名字就挂在嘴边,一时想不起来了。男主在街上遇到女主,跟着她回到住处。几天后,男主又一次来到女主的家里,女主不在,他对着窗外,心里有些躁动。沈灵说,太可惜了。陈圣问,你们女的也喜欢年轻的吧?沈灵笑起来,谁会不喜欢好看的。陈圣起身,从一侧绕过,去卫生间,经过卧室,门敞开,一张大床,床头上方挂着一块黑色的幕布。出来后,陈圣没有回沙发,走到客厅北边,站在书柜前,一排书脊边上摆放着各类卡通玩偶。沈灵走过来,当起讲解员,有些书,在市区的老房子里,没搬过来。陈圣说,书柜有点复古。沈灵说,这房子是我爸妈装修的,那会我还没回来,也没出钱,就随便他们了。陈圣问,他们平时来这边吗?沈灵说,偶尔,这边不太方便,最近我妈又住院了。陈圣问,怎么了?沈灵说,心脑血管不太好,上次也是这个毛病,我下午得去医院。
陈圣沿着书柜往北走,经过一道推拉门,来到阳台——这么说不准确,背阴,没有阳光,紧邻窗户,大致五六平米的空间,摆放着书桌和椅子,地上有几盆绿植,墙面上贴着沈灵画的几幅油彩和水墨。沈灵说,这是我的工作间。陈圣拿起画,翻看了下,有几张是关于虎的,偏向年画,又显得稚朴。沈灵说,虎年,就跟风画了几张。陈圣说,看起来真不错,给我一张吧。不行,沈灵说,我没留底稿,以后再单独给你画吧。陈圣放下画,在窗口站了一会,从这里,能看到不远处山上的松树,一片乌云正漂移过来,巨大的阴影扣在山顶上,又延伸到山腰,向这边压过来。沈灵的屁股靠在书桌上,双手抱在胸口,望向外面。陈圣回头问,你平时爬山吗?沈灵说,不爬。陈圣转身,往回走。沈灵问,你下午做什么?下午没事,回酒店,陈圣说,晚上和李智约好了吃饭,你去吗?沈灵问,都有谁?他的几个朋友,陈圣说,具体我也不清楚。回到沙发先前的位置,沈灵拿出烟,递给陈圣。陈圣点上,又给沈灵点。陈圣问,你现在还是一个人?沈灵说,没遇到很合适的。陈圣问,什么才叫合适呢?沈灵说,一到结婚就没意思了。陈圣从茶几下面,拿出烟灰缸,点了下烟灰,后仰时胳膊碰到沈灵的胳膊,汗毛扫过。他俩没动,胳膊贴近,感受到彼此的温度。
电影过半。郊外的村舍,落日余晖下,女主脱掉上衣,虚无地跳舞。柔美的胸部出现在硕大的屏幕上,陈圣仔细看完这段,问沈灵,怎么样?沈灵说,她的身材很好。是好,陈圣补充道,但不色情。沈灵问,你中午吃什么?陈圣说,你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沈灵说,不是我做饭。陈圣说,我不会做饭。沈灵说,也没让你做。陈圣问,你平时在家不做饭吗?做,沈灵说,但今天家里没吃的了。陈圣说,我以为能吃到你做的饭。沈灵说,还是出去吃吧。不出去了,陈圣说,点外卖吧。沈灵说,出去的选择多。陈圣说,在家里吃舒服。沈灵不再坚持,那你想吃什么?陈圣说,你看着点吧。
外面又下起雨,伴随轰隆雷声。窗户开着,有雨水进来。陈圣起身,把窗户关上,楼下空无一人,只有树在摇晃。沈灵走过来,这几天都有雨。陈圣说,昨天在高速上也下雨了。沈灵问,你打算待几天?陈圣说,没有其他事,明天回去。沈灵说,来一次这么着急。陈圣说,你没事可以去找我。沈灵说,可以。陈圣说,那我等你。沈灵问,你这次来,真没别的事?陈圣笑起来,真没有,你觉得我会有什么事呢?沈灵没说话,看着外面的雨。陈圣说,和你见面,算一件。沈灵说,三年不联系,说来就来。陈圣说,下次,我提前说。电影出片尾,雨还没停。陈圣和沈灵坐回沙发。沈灵又在找其他的电影,选来选去,不知道要看哪个,问陈圣的意见。陈圣说,不看也没事。沈灵俯身,手肘撑在大腿上,后背如滑坡,上面沾染着猫毛。陈圣问,你的猫呢?沈灵说,躲起来了,怕生。陈圣说,别找了,还是说会话吧。沈灵把电视关上,看了下手机,外卖还有三公里。陈圣问,如果你知道自己三年后会死,这三年你打算怎么过?她想了片刻,歪头,一脸认真地看着陈圣,眼神中看不出任何起伏,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吧。也对,陈圣继续问,那你过去三年呢?沈灵说,事情倒是挺多的。陈圣说,说点印象深刻的。你呢,沈灵说,感觉你变化也挺大的。陈圣说,我这点事,没什么好说的。沈灵叹气道,我们怎么都这样。陈圣问,什么样?老了,沈灵丧气地说,没活力,没劲。陈圣说,心里很多话,想说,又觉得说了也没用,就不爱说了。
外卖到了。沈灵开门去取,趁这空当,陈圣简单收拾了下茶几。四菜一汤,两碗米饭。味道还不错。沈灵坐沙发,陈圣坐矮凳。沈灵右手拿筷子,左手不时拂头发,怕沾染上汤汁。陈圣很快吃完了,坐回沙发,看着沈灵吃。沈灵细嚼慢咽,几乎把菜都吃了。雨停了,陈圣打开窗户,一阵风吹进来。沈灵从卧室出来,换好衣服,上身收腰的黑色长袖,下身是宽松的米色裤子。她抬起手,扎起长发,站在镜子前化妆。陈圣倚在窗边,隔着三四米,盯着她,遮瑕,打粉底,描眉,涂口红。戴上耳坠,沈灵走到陈圣面前,怎么样?陈圣说,好看。沈灵说,走吧。在门口,陈圣接过沈灵的挎包。沈灵坐在矮凳上,穿上运动鞋。电梯里,陈圣和沈灵相对而站。陈圣一阵燥热。沈灵低着头,没看陈圣。陈圣到了一楼,出去。沈灵继续向下,来到停车场。走了几步,她摸口袋,忘带烟了,又一想,车里可能有,没再回去。上到地面,陈圣的车在前面,沈灵跟在后面。出了小区,陈圣的车消失在雨雾中。沈灵想抽烟,车里没有。
晚上,李智接陈圣去火锅城,路上他简单介绍了一会要见的几个朋友。陈圣没记住名字,总之都是这座小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不禁又被李智强悍的社交能力折服,问他怎么认识这么多人?李智自谦道,都是朋友们给面子。朋友们坐满包间,虽有年长者,但陈圣作为客人,仍在主宾的位置落座。肉和海鲜一盘盘端上来,众人举杯言欢。李智比昨晚更活泼,酒没少喝。陈圣也被气氛感染,赔笑渐而真诚,等酒足饭饱要散场时,竟有些依依不舍。似乎,今晚能和这些有能力的人在一起吃饭,陈圣也没那么平庸了。走出火锅城,陈圣陪着李智先送朋友们逐一上车离开,再回到酒店。李智照例又温故晚上的饭局,都是多年的朋友,互相扶持,各方面没得说。说着,说着,李智眼里竟含了热泪,这倒是陈圣第一次见,便点头迎合,为他能有这么多交心且有能力的朋友感到高兴。后来,陈圣说起沈灵。李智说,我有一阵子没见她了。陈圣说,我还以为你们经常见。听说她要复婚了,李智说,这挺好的,一个女人生活也不容易。陈圣说,这个我不知道。李智笃定地说,是有这回事,沈灵和她前夫也没什么大矛盾。陈圣点头,那这样挺好的。第二天,陈圣吃完早饭,就驾车回去了。李智给他打电话时,陈圣已经在高速上。他颇为埋怨地说,兄弟,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说好的多待几天,今天的饭局我都定好了。陈圣忙赔不是,家里有点急事,下不为例。
半个月后,陈圣在超市买菜。李智打来电话说,人找到了。陈圣问,谁?李智说,范兴。又说,确实死了,刚才市局的朋友和我说,上午在山里找到的,现场照片我就不给你看了,传出去不太好。陈圣问,具体怎么回事?李智说,人看起来死了没多久,衣服还挺好的,没外伤,尸体也没发臭。陈圣说,这就奇怪了。李智说,看样子范兴这两个月是被人关起来了。陈圣问,怎么发现的?李智说,有人爬山,去树林里方便,蹲下看到地上有一张脸,差点没拉他头上。陈圣把手里的葱放下,不知道说什么。李智问,你最近和沈灵联系了吗?陈圣说,没有。李智说,那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