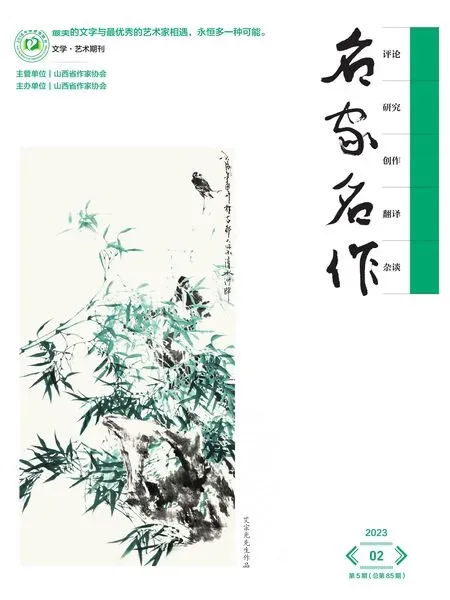模仿与背离
——论《茫茫藻海》中女主人公的文化身份探寻
张永平
文化身份问题在研究后殖民语境中边缘种族以及移民后代等对象时向来是突出的话题。乔治·拉伦曾表明“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1]。而《茫茫藻海》恰恰是以19 世纪30 年代奴隶制度解体后为历史背景的,这一时期正处于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小说中殖民主义文化与殖民地文化的冲突十分明显,因此产生文化身份问题也就不言而喻。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从一开始便是带有文化身份问题的边缘人。同样身处于英国殖民文化和西印度群岛黑人文化的中间地带,作者简·里斯何尝不是一个身份模糊不清的边缘人呢?对勃朗特所写的伯莎故事她更能感同身受,所以她说:“我想写一些她的生活。[2]”正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她能够将自己的伤疤经由创作的方式言说于众,其笔下的安托瓦内特成了作者的化身,在面临强大的殖民话语时常常处于失语的状态。如果说安托瓦内特的存在揭示了苦难的边缘人的生存状况,那么里斯的写作则是召唤和引导底层女性同胞的行动。通过书写,作者颠覆了边缘与中心的对立关系,传播帝国中心消解意识,让被殖民者冲破殖民主义的思想藩篱,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本文主要从霍米巴巴的模仿行为理论入手,认为女主人公存在身份焦虑和困惑,而这种身份问题实质上是简·里斯的一种自我投射,通过进一步探讨作者在身份上的选择与思考,以期唤醒广大边缘化女性群体,冲破枷锁以重塑女性主体性。
“模仿”一词首先是由雅克·拉康所提出的,他认为“模仿的效果在于隐蔽,正如战争中人们使用的伪装技术”[3]。而被誉为“后殖民主义三剑客”之一的霍米·巴巴将其推陈出新,运用到了文化分析领域。在《文化的定位》中,他指出“殖民模拟是一种复杂、含混、矛盾的表征形式,其目的并不是追求与背景相和谐,而是像伪装术一样,依照斑杂的背景将自身也变得不纯而斑杂,在隐蔽中保护自己,并力争威胁敌人”[4]。也就是说,殖民模仿并非是简单的模仿行为,它自身在这一过程中会不断地进行调整,一方面借鉴被模仿者有利的部分来完善自己,另一方面对被模仿者拒绝、不服从,最终指向的是产生延异、差别和超越的结果。因此,模仿行为不仅是殖民者的统治策略,亦可作为反殖民策略而为被殖民者所用,被殖民者在模仿时不是全盘接纳,而是主动并有目的地实现对内部的改造过程,逐渐呈现出与之相反的背离倾向。就《茫茫藻海》而言,女主人公从一开始的困惑迷茫,到积极主动地探寻身份,再到实现自我的救赎与超越的过程恰恰也伴随着模仿行为。从对宗主国的自觉模仿到拒绝模仿再到与之背道而驰,一点点唤起女主人公的主体意识。最终以一把火终结了桑菲尔德庄园,以此抵抗中心话语,看似极端却也真真切切地从灵魂和思想上挣脱了殖民和父权对她的桎梏,完成了文化身份的追寻历程。
一、安托瓦内特的“模仿”:主体的身份焦虑
小说开篇便将女主人公的身份困境展示出来:“俗话说同舟共济,白人们就是这样做的。但我们和他们并不在一条船上。[5]”作为克里奥尔白人后裔,她在身份的界定上含混不清。白人戏谑地将她这类群体称为“白皮黑鬼”,黑人则称他们为“白蟑螂”。女主人公在面对这样一个双重排斥的境地,不由得发出叩问:“夹在你们中间,我经常不明白自己是什么人,我的国家在哪儿,我属于什么地方,到底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5]身份的模糊性将她带入焦虑的深渊。为了摆脱焦虑与彷徨,安托瓦内特开始投入身份的探寻之中。
起初,安托瓦内特有着与当地黑人亲近的渴望。在库里伯里宅邸,安托瓦内特一直被黑人保姆克里斯托芬照顾和疼爱,对黑人文化有着向往之心。她抱着这样的想法和黑人女孩提亚很快就熟悉起来,并成为好友。可好景不长,她的真心换取的却是提亚的背叛,被其骗取身上的财产以及衣服。而安托瓦内特并没有完全丧失对好友的信任。在黑人与克里奥尔白人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梅森先生的到来进一步激化了两者的仇恨。作为英国殖民者,他来西印度群岛的主要目的是敛财。母亲改嫁后,梅森开始肆无忌惮地实施赚钱计划,而这却加剧了黑人对他们的憎恨。最终只能以暴力收尾,黑人纵火烧掉库里伯里宅邸,母亲在大火后彻底失去理智,哥哥也就此丧生。一夜之间,安托瓦内特变得孤立无援,最亲爱的家人都离她而去。在火灾现场,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和隔阂彻底爆发,两个不同的群体面面相觑,安托瓦内特看到不远处的提亚,想过去寻求安慰,可“我们瞪着彼此,我脸上是血,她脸上是泪。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犹如镜中”[5]。也正是这一刻,她才彻底明白在种族冲突面前,两人的关系正如书名一样,隔着茫茫的沧海,无论如何遥遥相对,始终无法跨越这一鸿沟,成为真正的朋友。
因此,安托瓦内特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识有了新的转折,她开始转向英国文化的怀抱,渴求获得白人身份来消除内心的不安与焦虑。就此,安托瓦内特开启了对英国的模仿之旅。一开始以梅森为代表的英国殖民者对安妮特一家的生活进行了彻底英国化改造。而女主人公也欣然接受,“我们现在吃英国菜,牛肉、 羊肉、派、布丁。我很高兴过得像个英国女孩”[5]。不止于此,她看的书也是英国的,有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诗集,也有历史小说家沃尔特· 司各特爵士所著的几本小说。她还喜欢一幅名叫《磨坊主的女儿》的英国画,曾多次谈到它,想成为画像上的英国姑娘,拥有“褐色的卷发,蓝色的眼睛”[5]。显然她在方方面面都以英国为方向标,试图通过伪装重构文化身份。看到妈妈和姨妈都选择与英国人结婚,安托瓦内特也不吝为了进一步拉近与英国的联系,决定嫁给罗切斯特。正如后殖民评论家A·敏米所述:“被殖民者认真模仿白人的习惯、服装、食物和建筑。一段跨种族婚姻是这种大胆模仿的极端表现”[6]。没有什么比结婚这条捷径来得更快,更能证明自己已然成为一名真正的英国人了。从这个意义来讲,安托瓦内特与罗切斯特的婚姻实际上是她的一种模仿行为,目的是为了构建英国身份,在表面上获得与白人女性等同的地位。可罗切斯特本就是将这场婚姻视为敛财的手段,新鲜感和欲望褪去之后,只剩下冷淡。但安托瓦内特没有停止对英国的幻想,她天真地认为“住到英国去, 我就会变得不一样,会遇上不一样的事情”[5]。可后来丈夫听信了外界诋毁她的话,他更加厌恶女主人公,毫无顾忌地与黑佣偷情,背叛她。在几次对话无果后,他将她带回了英国,那个曾是她魂牵梦绕的地方,可她却被关进阁楼中,不见天日。至此,安托瓦内特的模仿行为彻底结束,她也最终醒悟过来,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无根的边缘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融入英国社会。克里奥尔白人从早期就被视为英国被殖民对象这一点无法磨灭,也就意味着白人不可能承认他们与其拥有同等的身份。
二、安托瓦内特的“背离”:自我身份的建构
女主人公的模仿行为中也混杂着背离的倾向。婚前安托瓦内特对宗主国是出于自觉的模仿,而婚后则是她一步步解开英国神秘的面纱,使其幻想破灭,主体意识渐渐被唤醒的过程。婚后,安托瓦内特虽然对英国之外神往,却不失理性地质疑英国形象,她问丈夫:“英国就像梦一样吗?”[5]可见她不再沉溺于英国梦中,提出怀疑是开始独立思考的第一步,表明她不再是他人的玩物。而与罗切斯特共度蜜月期间,他们遇见了当地妇女卡罗琳。安托瓦内特本可用英语与她交流,却选择用岛上通用的法国腔土语。陌生语言的加入使罗切斯特处于边缘位置,殖民者中心话语权由此被削弱。这一尝试是对于英国的语言背离,是用杂糅的语言消解了大写英语的殖民作用。
婚后的罗切斯特不再对她百般殷勤,为挽救婚姻,她请求克里斯托芬用奥比巫术来挽回丈夫的心。作为虔诚模仿者的她不会不知道奥比巫术被看作邪术排除在英国文化之外。可她依旧犯了大忌,相信它的作用。对巫术的态度反映了她文化背离的趋势。露出真实面貌的罗切斯特不仅以粗暴的方式对她,还用其他名字称呼她。安托瓦内特这一名字在他看来极具异族文化特色,在发音上也是地地道道的克里奥尔式发音。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其他文化都是野蛮、未开化、低下的,对妻子名字的更改是为了行使他作为殖民者的权力。一开始,罗切斯特用“马里奥内特”称呼她,这个名字的寓意是提线木偶,显示了罗切斯特对她的绝对掌控。之后他用“贝莎”取而代之,想就此割裂她原本的文化身份,将其驯化为帝国文化下的他者。在第一次叫她贝莎时,安托瓦内特并没有顺从其心愿,问道:“我的名字不叫贝莎,你为什么要喊我贝莎?”而罗切斯特的回答是:“因为我特别中意这个名字,我把你当成贝莎”[5]。将名字更改为富有英国味的贝莎,其动机是为了更好地掌控被叫的人。随后,在听完妻子同父异母哥哥丹尼尔对安托瓦内特及其母亲的诋毁后,罗切斯特便开始诘责她。丈夫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一步步激发了她的主体性,倾覆了两人关系中安托瓦内特一直处于被动、顺从的附属地位。最后她一语破的:“我不叫贝莎。你用另一个名字喊我,想把我变成另一个人。”[5]她对名字的抵抗不仅是对罗切斯特的回击,还是对英国殖民文化重新思考与审视后做出的一次背离。
如果说前面种种模仿中产生的背离带来的影响微乎其微,那么在经历过重复的模仿行为再到多次背离,安托瓦内特不再执著于英国白人身份,其背离的结果如暴风雨一般来的猛烈。被关进阁楼后,她从此被罗切斯特剥夺了话语权。在仆人熟睡后,她逃出阁楼来到桑菲尔德大厅,借助烛光看到了她一生中珍视的一切,包括“兰花、生命树以及她心爱的画作都燃烧着”[5],她还看见提亚站在池塘边朝她招手。而这一刻安托瓦内特不再恐惧,而是顿悟和启示。她看清楚了英国虚伪的一面,意识到模仿永远都只是模仿,不可能成为真实,将身份的建构这一希望寄托在白人男性身上终究会落空。唯有自我意识的觉醒才能实现自己白人身份与黑人身份的融合,并在其中找到平衡点。因此,安托瓦内特用极端的暴力方式完成了最后一次背离行为。用一把火烧掉了桑菲尔德庄园,同时将自己葬身于此,以身体来抵抗罗切斯特对她的压迫和统治。对于无可奈何的安托瓦内特来说未尝不是个好方法,不再禁锢于“模仿者”这个单调的身份中,在大火中涅槃重生好让精神上得到解放。从模仿到逐渐背离,再到拒绝模仿走向彻底的背离,安托瓦内特最终以向死而生的姿态完成了自我身份的探索,成为一个身心都完全自由的人。
三、夹缝中生存的女性困境与出路
除了文本中安托瓦内特的悲惨命运,不可忽视的还是作者里斯的身份,因为“无论是对里斯作品中的后殖民现代主义,或是后人文主义、世界主义或是全球现代主义的认知,首先是对里斯加勒比克里奥尔白人身份的重新认知”[7]。正是里斯身份的特殊性,让我们看到了书写的多重可能,能够从多维的角度去认识后殖民女性世界。女主人公的身份界定问题在早期就引发了评论界的争议,就像沃尔夫所说:“海明威是一个了不起的旅行者,但永远是美国人;乔伊斯永远被公认为爱尔兰人;可生于加勒比海地区的里斯女士呢?她是威尔士人?西印度人?还是英国人?”[8]里斯和安托瓦内特所面临的问题都是自我身份的认同障碍。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为她们这样的女性找到一条出路,不用以生命为代价去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霍米·巴巴为解决这一困惑提出了一定的启示,他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即“即非这个也非那个,而是之外的某物”[4]。换言之,第三空间是两种文化之外的空间,但具有两种文化渗透杂糅的特征。边缘化女性群体可利用第三空间打破两种文化的对立局面,在彼此冲突与融合中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使其身份呈现出跨越种族、混杂的特征。因此,她们要摆脱自身困境的方式绝不是一味地抛弃本土文化,对宗主国文化进行东施效颦式的模仿。安托瓦内特的结局说明了一切,模仿总是无力的,它只能让模仿者一直游离于寻觅的路上,永远无法抵达终点。唯有边缘女性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因对身份的彷徨而迷失自我,在模仿中产生背离,同时又在不断背离的过程中消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最终才能产生对身份的认同感,完成自我文化身份的构建。
——《藻海无边》中“他者”的疯癫与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