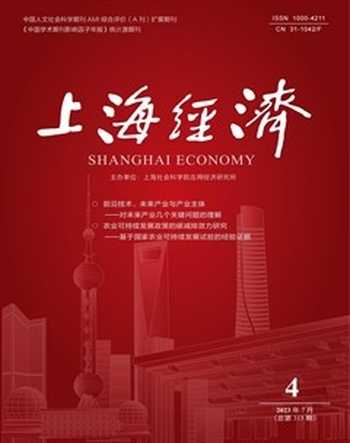美国产业政策的历史脉络、演进规律与政策启示
[摘要]2020年以来,拜登政府致力于提出一套体系化的产业政策理论,通过规则和补贴的制定,并综合各项干预措施将私人资本引向重点发展领域,引发了广泛的政策讨论。循此,本文从产业政策的主流思想、主要任务、政策领域和政策工具等角度详细梳理了美国在产业萌芽期、发展期、调整升级期和新发展时期的主要产业政策,总结了美国产业政策实践中的演进规律,并针对我国目前产业政策中的主要困境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坚持自主发展的基本原则上保持战略定力;第二,着重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运用,推进产业界自立的政策导向;第三,在政策表述、政策延续以及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政策协调等方面借鉴美国经验;第四,注重公私部门的合作,增强官民协同;第五,注重产业政策的体系性与协调性。
[关键词] 美国;产业政策;演进规律;政策启示
[中图分类号] 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11(2023)04-0010-14
[收稿日期] 2023-01-11
[作者简介]任宛竹,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公共政策,文化经济学。
一、引言
新冠疫情前后,美国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发生重要转变,拜登政府重塑美国产业政策,将亨利克莱的“美国制度”思想体系重新拉回历史舞台。拜登政府签署《美国救援计划》,相继推出《通胀削减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以法律形式强调了产业政策对美国的经济引导与干预作用,在优势领域进一步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在新兴领域确保美国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产业主导者,在关键领域构筑贸易壁垒、维护美国的产业链安全。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在报告《重构美国国家产业政策》文末论述:“中国并非产业政策的发明者,美国产业政策将确保美国未来经济保持强劲,技术领先地位得到巩固”。长期以来,美国为巩固自身全球政治经济领域主导者的地位,不仅声称未曾实施过产业政策,还主张他国消除贸易壁垒等经济干预手段,并以裁判者身份对他国产业政策加以干预和指责。因此,拜登政府重申产业政策的意义,推翻了美国先前对于实施产业政策的掩饰态度,激发了政界、学界与业界各方关于产业政策的广泛讨论。
本文对美国自建国以来实行的产业政策加以梳理,将美国产业政策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产业政策的萌芽期、发展期、产业调整升级期和新发展期四个阶段,概括了美国各个经济运行时期的主流经济思想、产业政策的任务、主要领域以及政策工具等特征,并总结了美国产业政策的演进规律。在产业萌芽期和发展初期,美国往往以直接干预手段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发展,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在技术研发与应用领域投入巨额资金。随着美国工业体系的成熟和世界领先地位的确立,美国政府逐渐转向功能性和服务性产业政策,以更为隐蔽的手段支持美国产业发展。近年来,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经济威胁,其产业政策逐渐显现更多选择性产业政策的特征,以“挑选赢家”的方式促进本国优势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无论政府主张和主流经济思想为何,美国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均运用了直接或间接的产业政策支持本国产业,并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适时调整。
中国在以往产业政策实践中大量借鉴了欧美日韩等国的产业政策经验,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往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程度、地缘政治环境等背景差异较大,仅仅对经济政策进行同时期的横向比较往往有失公允。因此,本文对美国产业政策的梳理与总结,也可以将中美产业政策的比较嵌入更为宏大的历史格局之中,而不拘泥于同期对比,具有更强的可对照性,从而为中国产业政策的实践提供启示。
二、美国的产业政策实践
美国联邦层面的产业政策由美国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共同实施,产业政策通过联邦政府机构的各种计划之间进行衔接协调,形成较强政策合力(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2018)。美国产业政策的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评估报告、政策指引。产业政策类型主要包括产业技术政策、区域政策以及其他以改善经济环境、促进就业为目的的产业政策。
产业技术政策由国防部、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农业部、商务部等机构实施;产业组织政策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各级司法机构实施;其他产业政策由联邦小企业管理局、经济发展局、农业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负责实施(周建军,2017)。同时,各个州可以制定符合本地发展需求的产业政策,包括现金补助、企业所得税减免、销售税减免或退税、财产税减免、低成本贷款或贷款担保、工人培训等免费服务等。
(一)萌芽期
美国产业政策的萌芽期是1776年至1944年二战结束前夕。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前后,英国一方面对美国采取了抬高关税壁垒、取消贸易优惠等贸易保护手段,另一方面向美国大规模倾销廉价工业制造品,使刚刚起步的美國经济陷入破产、失业加剧和资金匮乏的困境中。面对内忧外患,美国在产业发展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独立和完善的本国工业体系。
汉密尔顿的公私部门资源整合思想与克莱的美国制度等美国学派(American School)主张是萌芽期产业政策的指导思想。美国学派的主要观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推崇技术进步,追求生产效率提升。第二,放弃自由贸易,实施幼稚产业保护。第三,实施内部改革,以内需升级驱动工业化进程。美国学派的政治经济学主张是未来“生产效率-内部改善-关税保护”工业化战略思想的雏形(沈梓鑫和江飞涛,2019),是美国未来完成工业化体系建设和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指导思想,对美国产业政策的制定影响深远,并为美国应对20世纪上半叶经济危机提供了行动指南。如两次世界大战中成立的战时工业、生产委员会积极寻求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在生产与服务中的战略合作,协调商品定价与分配,使美国在战时得以保障社会需求,并为战后经济重建打下良好的制度基础。在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的同时,美国并未忽视对农业发展的推动,1933年开始美国通过立法保护、巨额补贴等政策工具扶植本国私有农业的发展。
至产业萌芽末期,基于国防需求,联邦政府意识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产业政策逐渐呈现出整合资源、推进科技边界的创新政策属性,以举国体制塑造科技前沿。如1940年成立的国防研究委员会投入巨额资金并召集科研人才,与大学和工业实验室合作开发新型武器开发。这一模式充分发挥了私营部门的创新能力,迅速重建具有竞争力的技术优势,避免在建立国家实验室等方面浪费资源。
美国依靠创新的融资和企业组织方式、合理的人才战略与产业技术政策,充分挖掘了本国市场潜力与企业家才能,使美国在19世纪末即跻身于世界工业大国和创新创业的中心区域前列。
(二)发展期
美国产业政策发展期为1945年至2007年。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拉开序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同时展开,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议题,此时的美国已从经济赶超者跃升为全球政治经济领域的主导者。根据美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与产业发展任务的差异,本阶段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应对苏联的军事威胁,美国在这一阶段加快了国防科技体系的建设,建立起了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的产业政策支持体系。第二个时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不仅需要应对苏联的威胁,也要面对日本德国等国的崛起、本国科技成果转化薄弱等问题,开始加强应用技术的成果转化,大力推行产业技术政策。第三个时期始于21世纪初,美国在恐怖主义、能源危机、经济衰退等议题的冲击下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通过扶持重点产业和实施人才战略稳固全球领先地位。
这一时期占据美国主流经济思想地位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潮,这使得美国政府不仅主张消除贸易壁垒等经济干预手段,还以裁判者的身份对实行产业政策的国家加以指责。如里根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坚持的小政府和更有限的政府,Backer(1985)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没有产业政策。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美国的产业政策并未得到外界的过多关注,美国政府甚至声称根本没有实施过产业政策。实际上,在这段长历史中,美国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实施了大量以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为主要着力点的功能性、服务性产业政策,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创造优良的营商环境,以举国体制构建了完善的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支撑机制,美国取得的经济成果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防安全的范畴(沈梓鑫和江飞涛,2019)。同时,美国也会以直接干预的方式参与经济发展,凭借自身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开展贸易保护,遏制竞争者的相关产业发展。美国在这一阶段实施的产业政策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础研究领域。美国在战后初期的产业发展战略为“先军后民、以军带民”,在万内瓦尔·布什的推动下,美国产业政策强调对国防相关的基础研究的支持,财政支持重点领域为基础科学研究、基础技术和通用技术,以确保美国是“战略技术意外事件的發起者而非受害者”。美国政府成立了高度结构化和散点化的研究支撑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这些机构成立多所国家实验室,并在计算机科学、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等领域设立高校研究的资助计划,联邦政府的研发投资始终是美国科技创新的重要来源,根据NSF数据,联邦政府研发投资占比在这一时期波动较大但始终保持在50%以上。同时,政府采购在这一时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半导体领域,发展初期美国政府对半导体设备采购占比在40%以上,最高时达到50%(马伟,2020)。
第二,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始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台了《拜杜法案》、《斯蒂文森—魏德勒技术创新法案》等一系列专利法案,以法律形式保障研究主体的知识产权财产分配,促进了科技成果在产业内的转移、扩散与商业化转化。
第三,创新政策。美国在这一阶段实施的创新政策营造了共同协作和公平竞争的创新要素市场环境,有力地促进了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与研发效率。如美国鼓励私营部门的研发创新,启动了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1982年)和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1992年),为从事基础技术和竞争前技术研发的小企业提供早期支持,通过加强小企业与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之间的创新合作,提高基础研究的商业化转化效率(沈梓鑫和贾根良,2018)。1988年开始实施的制造业扩展伙伴计划和先进技术计划,向中小公司提供一系列培训,并通过建立区域性制造业技术服务与转移中心,将联邦实验室、高校和企业中产生的新技术与方法以技术服务的方式直接转移到中小型制造企业中,加强中小企业的合作与联合研发(汪琦和钟昌标,2018)。
第四,培育创新人才。美国通过立法和战略规划等形式构建了支持基础科学和应用研究的多层次人才培养制度,如2006年《美国竞争力计划》、2007年《美国竞争法》,均强调了创新人才培养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美国政府通过加大高等教育投资、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开设科技创新教育项目、引进海外创新人才和设置奖励计划等方式吸引和培养了大量创新人才。
第五,贸易保护。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阻碍外部产业竞争者是美国这一阶段的一项重要产业政策,美国施行特殊关税制度(反倾销税和特别保障税),设置进口配额限制特定商品进口数量,签订贸易协议保护本国产业,向本国产业提供补贴和税收减免,利用反倾销措施限制外国公司在本国市场的竞争。
(三)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期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阶段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至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前夕。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意识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开始推行制造业复兴计划,应对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与重建。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以振兴制造业为基础,出台了一系列扭转脱实向虚局面的再工业化战略,同时配套技术创新与贸易保护政策用以支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从而巩固美国的国际领先地位。随后特朗普萧规曹随,延续了奥巴马的先进制造业战略,美国逐渐形成了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现代产业政策框架。在这一时期,美国实行的产业政策更为灵活多变,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发挥功能性和服务性作用,有效地规避了国际贸易法规的限制和审查,使其以更为隐蔽的形式支持美国的产业发展。这一阶段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税收减免、知识产权立法和政府投资。
1.复苏计划与创新战略
为应对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美国在2009年后出台了一系列计划法案提振本国经济,如ARRA法案(美国复苏与在投资法案)向特定产业注资7870亿美元加速经济复苏,《美国创新战略》系列构建并完善了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架构和未来向度,复苏计划与创新战略的行动重点在于对基础研究,尤其是创新链前端的基础研究给予更高的资助,促进基础科学研究、基础技术和通用技术的发展,根据沈梓鑫和江飞涛(2018)的计算,联邦政府对创新链前端基础研究的贡献度高达44.3%,对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的贡献度分别为35.5%和15.7%。这一资助結构可以在降低产业政策扭曲技术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有效提升基础研发的动能,同时,联邦政府对高校与研究机构的资助远高于对私人部门的补贴,这也使美国的创新支持政策更具有隐蔽性。除直接出资外,联邦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政策(包括研发和试验抵税)、金融政策(向开放性资本市场配置资源)和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鼓励基于市场机制的创新研究,促进技术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与扩散。创新政策支持的重点技术领域包括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清洁能源、现金车辆技术、精准医疗技术等。
2.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现代产业政策框架
美国政府在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在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确保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奥巴马的再工业化战略与特朗普的制造业回归口号一脉相承,具有较强的政策延续性。奥巴马政府的产业政策重点是构建制造业合作伙伴关系,拓展公共部门与私人领域的协同合作,注重技术领域的基础创新与长远发展,据此制定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等创新政策和行动计划。特朗普政府则更倾向于促进短期的制造业回流,通过减税、基础设施投资和宽松的金融政策创造制造业就业岗位,通过支持人才体系建设匹配先进制造业劳动力需求,推广新的制造技术激活美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
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先进制造业计划的目标是为了脱虚向实,改变美国对金融业和服务业的过度依赖,培育本土制造业,增强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与投资活力,缩小美国贸易逆差。第二,美国制造业的复兴过程,是重新融合美国的技术优势与产业优势的过程。随着制造业活动大规模向海外转移,美国的制造业规模和贡献快速下降,同时也影响到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稳定和创新研发能力,因此,制造业的复兴不仅意味着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更重要的是要促进制造业回流,吸纳本国劳动力,重新提振美国的工业创新能力。第三,先进制造业计划的方向,是争夺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黄阳华,2018)。
在基本的政策思路上,美国不是简单地通过财政、金融等措施直接帮扶特定企业,而是构建可持续的政策框架和服务体系,为制造业企业营造有利的内外部商业环境,促进以先进制造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投资。其政策框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高效的公共治理体系,以匹配和服务本国制造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二,综合多种政策工具,一方面为本国产业提供税收和投资优惠,另一方面高筑贸易壁垒,通过高关税和管制措施限制对手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第三,在国际贸易中以坚持自由贸易的口号攫取资源,争夺规则的制定权,稳固本国的领先地位。第四,完善发展先进制造的产业和技术基础设施。第五,大幅提升对先进制造技术的R&D支持。第六,坚持人才战略,大量培育和吸引满足本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所需的技能工人和专业人才。从上述分析看,后危机时代美国的产业政策与美国长期奉行的美国学派产业政策核心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3.贸易保护与产业安全政策
这一时期美国的贸易政策在特朗普政府阶段的表现较为鲜明。在传统贸易领域,特朗普政府致力于撇清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和贸易主导者的责任,认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贸易优惠有损美国的经济利益,因此进一步强化贸易保护措施,重新定义美国在全球贸易与生产体系中的权利与义务。第一,为了改善对外贸易逆差,2017年开始,美国退出或更新多边贸易协定,如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推进美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更新完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二,推行严格的技术移民政策,反对低技术移民;第三,在商品和服务贸易领域,与中国、欧盟、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不断发生贸易摩擦,在技术领域重视产业技术安全,强化对中国等国家的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保护本国关键技术的安全(闫德利和高晓雨,2018)。
与传统贸易领域不同,特朗普政府在数字贸易这一新兴领域则主张自由贸易,致力于消除数字贸易壁垒,维护美国的数字商业利益,塑造美国在数字领域的主导地位。如2016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成立数字贸易工作组,同年商务部启动数字专员项目,2018年在《电子商务倡议联合声明》中提出用数字贸易取代电子商务概念,其概念范围和定义均由美国决定(陈昭峰和张红倩,2022)。这些政策均为确保美国企业能够顺利打开全球数字经济市场,成为数字贸易领域的领先者和规则制定者。
(四)新发展期
新发展时期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延续至今,这一阶段美国产业政策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全球经济的领先地位和应对中国的挑战。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中美差距不断缩小。近年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深刻影响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国家产业策略,如“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制造2025”等,使美国视中国为政治经济威胁。在2020年前后,美国的经济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摒弃了其建国以来始终坚持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在新的立法中不断注入产业政策概念,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拜登上任后,更是推动多项产业政策提案转变为法律。拜登实施的美国新产业政策着眼于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巩固美国在全球工业和科技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提升美国竞争力,增强美国经济韧性,并与中国竞争。
现阶段实施的产业政策包括贸易、基建、创新、能源、国防和军事几个方面。第一,贸易政策,美国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促进本土生产和制造,保护美国产业免受外部环境的冲击,通过补贴、税收优惠和贷款计划加强政府购买和投资相关技术产品的力度。第二,基础设施领域,美国政府出台《美国防止性能退化法案》《能源和水基础设施法案》等相关政策,投入数万亿美元改善道路、桥梁、公共交通、清洁能源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等公共基础设施。第三,技术和创新政策,美国政府加强对技术和创新领域的投资支持,保持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等关键领域的领先地位。2021年参议院通过《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投入250亿美元规模的补贴用于半导体制造,2000亿美元用于科学和创新研究开发。第四,能源政策,包括推动本土能源生产和使用,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从而提高国内能源自给率,实现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第五,国防和军事产业,增加国防投资,加强军备,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发展,提高美国军队的战斗力。美国在原有功能性产业政策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注入选择性产业政策的特征,针对多个前沿科技产业出台对应的发展纲要,明确发展目标,并对相关产业注入巨额资金,以“挑选赢家”的方式促进优势产业的发展。
三、美国产业政策实践的效果与演进规律
(一)美国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进展
美国主流学术界在美国甚至世界的产业政策实践过程中长期持否定态度,因此,在美国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经济学家的参与程度较低。美国近年来颁布的CHIPS和IRA等重要法案,经济学家往往被认为充当旁观者的角色。(Juhász et al.,2023)但是,纵观美国产业政策的研究历史,仍然可以梳理出清晰的产业政策理论发展脉络。
1.美国产业萌芽期和发展期产业政策理论
產业发展萌芽期的主流思想为幼稚产业理论,汉密尔顿构建出一个落后国家保护本国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制造业,利用保护性政策,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揭示了古典经济理论提倡的完全市场机制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在发展落后国家经济时的不足(姜达洋,2011),使扶持新兴产业的思想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
在产业发展期的代表性理论包括新增长理论和发展型国家理论。新增长理论以保罗·罗默与罗伯特·卢卡斯为推动者,认为研发、创新与知识独占性的强弱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新增长理论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只有加大对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投入,提高国民总体人力资本水平,加大对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引进先进技术,并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才能发挥后发优势,在经济上赶超先行国家(周绍森和胡德龙,2019);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角色,建立起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维护产权市场的正常运转,才能保证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顺利进行。发展型国家的概念源自《通商产业省与日本奇迹》,约翰逊将日本的发展模式称为“计划-理性”模式:第一,政府拥有一批具有管理才能的精英官僚,具有足够的政治空间进行有效运作;第二,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顺应市场规律;第三,需要存在一个像日本通产省一样的政府机构,积极引导经济发展并落实各项产业政策。
2.美国产业调整升级和新发展时期产业政策理论
美国产业调整升级和新发展时期的代表性理论包括技术动态创新理论、隐形发展型政府和企业家型政府理论。技术创新理论(techno-innovation dynamics)基于演化经济学,以结构动态演化为视角,分析一般性的产业系统动态,而非专注于单一的企业或部门,其出发点是提高经济系统的演化能力,解决创新过程中的系统或网络失灵问题。系统失灵来自演化经济学的资源创造理论, 对系统失灵的纠正旨在促进经济行为者的知识创造、知识获取和创新活动等资源创造的行为。在演化经济学框架下,功能性产业政策居于经济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主体具有短视性,可能处于低水平的局部均衡;第二,经济个体具有异质性,市场可能会忽视一些无法达成一致的重要社会目标(如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等),因此需要构建功能性产业政策推动经济系统摆脱低水平均衡,并实现其他重要社会目标。(Smith K,2000)
在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讨论中,美国学者布洛克和玛祖卡托(2017)根据美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历史和事实的研究判断,分别将美国政府称为“隐形发展型政府”和“企业家型政府”,否认了哈耶克“守夜人政府”理论,认为美国政府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企业培育等方面扮演了市场“塑造者”的角色(周建军,2017)。例如,美国的“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和“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直接为创新型小企业提供赠款和贷款,微软、戴尔、康柏和英特尔等企业在早期发展中都得到过这两个“计划”的资助。隐形发展型政府理论和企业家型政府理论扩展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前沿,进一步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学术地位,揭示了政府在塑造和创造市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贾诗玥和李晓峰,2018)。
3.近年来美国产业政策研究动态
随着世界范围内产业政策的研究与应用,产业政策的学术含义也随之从贸易壁垒等传统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延伸至服务性、功能性产业政策,美国经济学者对产业政策理论的争辩从产业政策的存废,转为对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经验研究,对产业政策的应用持更为积极和开放的态度。政策支持者认为通过产业政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提升国家竞争力,尤其应重视在绿色转型、供应链的韧性、促进就业和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等方面的政策运用(Rodrick,1995;Lin,2012)。也有一些学者对产业政策持怀疑态度,认为政府的干预可能导致资源分配的扭曲,增加了效率和公平的难题(Ito和Krueger,1995;Lall,1996)。近年来,出现了大量文献提供了关于产业政策的运作方式、评估产业政策在特定情境下引发的经济预期反应等方面的证据,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启示。
在论述产业政策的效果与影响方面,美国学术界的研究包含了宏观经济数据分析(Szirmai et al.,2013;Rodrik,2012)、政策文本分析(Juhász et al,2022)、企业调查与案例研究(Lin和Monga,2011)等不同研究层次,评估内容包括贸易自由化、大规模研发支持等产业政策对行业与企业生产力和创新的影响,评估州和地方商业激励措施的效果(Slatery C和 Zidar O,2020)等方面。
在产业政策的历史经验梳理方面,近年的研究文献对东亚奇迹及产业政策的运用较为关注,包括东亚国家的政策规模(DiPippo, L., Li, N., and Lu, Y.,2022)、投资补贴等政策工具的运用(Barwick, P., Li, F., and Lu, Y.,2019)、政治环境与企业制度(Wade, R.,1990;Malesky, E., and London, J.,2014)等方面,并认为东亚经济政策的经验与教训具备一定的普适性。
在研究范式方面,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产业政策与行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如生产率和与产业政策使用的相关性与外部性。而近年来的研究文献则更加注重产业政策的测量和因果推断,提供了更为准确和可靠的评估产业政策效果的方法,包括自然实验(Aghion et al.,2015;Garin和Rothbaum,2022)、随机实验(Bruhn and Gallego,2012;Atkin et al.,2017)、断点回归(Diewert et al.,1990)等因果推断技术。
(二)美国产业政策实践的效果评价
美国的产业政策在历史中起到了推动产业发展、提升国家基础创新能力、增强国防安全等重要作用,但是同时也给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美国产业政策的开展,学界和业界对产业政策的评估随之持续。如1976年,兰德公司发布的《联邦资助的示范项目分析》,评估了联邦机构在20世纪60~70年代发起的24个技术示范项目,其中有10个项目成功,9个失败,5个未知,失败的原因包括倚重大型项目、给予项目时间不足、技术尚未成熟即进行公示等。1982年,理查德·R·纳尔逊在《政府与技术进步》中研究美国的公共政策和七个行业的技术进步,认为美国政府支持基础研发的创新政策是最为成功的产业政策。2021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了《美国50年产业政策评估(1970-2020)》,回顾了美国在贸易、补贴、创新支持等领域的产业政策,评估了其中的部分重点项目,并重点关注了东亚,尤其是与中国的经济博弈。根据以往产业政策评估研究的梳理,美国历史上实施的重点产业政策包括公共研发、贸易措施、促进就业三大领域。
第一,大规模的公共研发项目。威尔逊(1982)认为美国政府刺激工业创新的最佳方式是研发支持政策,尤其是政府资助非专利研究、知识产权分配政策以及政府购买。这类产业政策有助于向前推进技术边界,使美国本土制造业与服务业更具创造力和竞争力。根据以往评估,当美国的创新政策更具选择性特征时,这一类政策往往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技术创新的周期长,预期回报不确定性较高,使用挑选赢家的政策在商业竞争激烈的应用技术开发行业很難获得成功。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21)对美国政府历史上以技术创新为目的的补贴措施进行评估后发现,面对前沿技术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若将公共资金集中于一两家规模较大的项目,正如将鸡蛋投放于一个篮子中,往往以失败告终;若以散点式的方式对多个企业同时进行补贴,则更容易成功。
第二,以保护幼稚产业为主的贸易措施。美国政府在钢材、纺织品和服装、汽车装配和零件、半导体、太阳能电池板等众多产业均实行过贸易保护政策。贸易措施之所以广泛施行,是因为贸易措施相较其他的产业政策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不受到联邦预算的约束。美国的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国产业,并吸引大量海外生产商在美国落户,但是,贸易措施的施行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一方面,贸易措施虽然具有非预算性,但是将成本转移到了家庭和企业用户上,使其承担更高的支出成本;另一方面,过于依赖贸易保护和产业保护,限制境外企业的投资和进口行为,有违国际贸易的自由公平规则,引发贸易摩擦,使国际关系更为紧张。值得指出的是,贸易保护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产业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应该注意避免其过度使用和不当实施,以免造成负面影响。美国产业政策在制定时需要更加综合考虑其他政策领域,以确保国内产业的发展与国际贸易规则相协调,并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国际经济体系。同时,注重提升本国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将有助于提高产业的自主可控性,从而更好地应对全球经济挑战。
第三,就业支持政策。2021年拜登在国会首次演讲中宣称,就业是他的基础设施建议和“购买美国货”任务的核心内容。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在摩擦就业领域进行工作重组,可以有效支持失业工人再就业。但主流的经济学思想认为支持就业不应是产业政策的职能。以支持就业为目的政策评估结果更为模糊,如各州为吸引投资纷纷推出补贴优惠政策,区域引资竞争使得就业补贴政策从国家层面衡量时正负效益相抵,成为零和博弈。促进就业的产业政策也可能会引致额外的社会成本。例如,一些企业可能出于政策需要而雇佣失业工人,而这种举措可能导致下游企业面临更高的投入成本。因此,中央政府应采取服务性和功能性产业政策,这些政策可以通过提供STEM课程、职业教育和劳动培训计划等方式来促进就业。这些政策的目标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技能水平和竞争力,使失业工人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并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这样的产业政策更加注重长期效益和可持续性,有助于提高整体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
(三)美国产业政策的演进规律
1.产业政策需要不断调整升级
从美国的产业政策实践中可以看到,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跟随本国和全球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做出调整。产业政策的最初存在的价值在于应对市场失灵,在市场调控无法触及的领域对公共资源和市场要素加以引导和分配,从而促进经济的健康运行。但是经济运行的现实更为复杂多变,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产业政策的体系、重点和实施方式必须适时进行调整(黄群慧等,2019)。
一方面,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经济增长的固有模式,衍生出了新的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点,尤其是当代正在经历的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变革,对产业政策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提出了挑战。数字经济改变了企业依赖价格机制和供求关系确定产量和价格的方式,转而采用“数据驱动法”获得供求均衡数据(吴军,2016)。
另一方面,生产网络和产业集聚模式的转变,影响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行为范式、经济组织结构以及生产模式等产业组织要素的变化(杜传忠和宁朝山,2016),需要政府在产业政策中支持和鼓励跨界合作,通过提供跨产业的合作项目资金,建立合作平台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交流与协同。
2.产业政策由纵向体系转变为横向体系
在全球产业演进的历史中,产业政策的特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第一,产业政策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逐渐密切和本国经济体系的成熟,从保护主义转为开放政策,早期的产业政策通常具有保护主义倾向,避免本国幼稚产业受到国外竞争的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贸易自由化的增加,许多国家转向更为开放的政策,鼓励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
第二,产业政策从选择性产业政策过渡到功能性产业政策。早期产业政策往往给予特定产业或部门优惠支持,随着产业的演进和经济结构的复杂化,以及新兴经济发展的巨大不确定性,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功能性产业政策,注重整体经济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但是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局势的紧张和逆全球化的趋势,产业政策更加强调本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政策体系又逐渐强化了选择性产业政策工具的运用。
第三,产业政策由重视资本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过去的产业政策通常注重资本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工业化和制造业的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投入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概念,基础和应用技术研发与创新成了产业政策的重中之重。
第四,产业政策的实施从单一产业到关注多元化产业集群。历史上产业政策的实施往往着眼于发展单一产业或特定产业集群,随着经济的复杂性和全球供应链的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多元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性,现代产业政策更加关注多个产业的发展,以降低经济的风险和依赖程度。
第五,产业政策向横向产业政策的转变,与本国政治体制变迁、政府决策效率相伴相生,产业政策的功效有赖于政策的延续性。一方面,产业的发展与本国的公共治理效率相互促进,公共治理效率和经济现代化的统一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产业政策缺乏长期规划,过于依赖于短期刺激措施,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容易导致政策效果的短暂性和不稳定性。在美国产业政策实践中,政治斗争干扰对产业政策的实施产生较强的负面影响,甚至决定产业政策的成败。政府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利益分配可能会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容易导致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3.大国的产业治理模式特征存在独特性
第一,大国在实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具有经济规模优势。相比与小国经济,大国经济体、超大规模经济体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具有诸多不同,其调整的理论与机制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超大规模经济体具有规模优势、研发成本的分摊优势、产业体系完整性与多样性优势等,这些为产业机构的调整提供了更大的腾挪空间,形成经济发展的雁阵模式。雁阵模式的产业升级是推进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的大国效应可以通过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动态循环推进雁阵模式产业升级进程,地区间分工经济的实现提高了雁阵模式产业升级的经济效率与质量。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依据不同的决策区间,科学选择扶持与调控模式,合理定位其不同角色,从而推动产业升级(纪玉俊和张莉健,2018)。
第二,大国经济体具有多层级的央地关系。多层级的央地关系有利于制定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对多样化区域发展战略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中国和美国等大国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的潜在优势,本身存在多层级的央地关系,地方竞争也在中国经济与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能够容纳多种战略的存在,这是大国产业升级过程中并行不悖的路径,包括自主创新战略、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自主可控产业体系的构建战略等。然而,多层级政府关系也使得决策执行机构过于复杂,容易造成区域之间的无效率竞争。
四、美国产业政策实践给我国的政策启示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与美国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制度、文化等方面不尽相同。但通过对美国产业政策的回顾,以及产业政策效应的分析,仍能为中国提供宝贵的经验:
第一,我国必须在坚持自主发展的基本原则上保持战略定力,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做好事前评估。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支撑,也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的关键。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其可能产生国际影响的事前评估。中国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坚决维持自主发展的基本原则,但在政策表述、政策解读和对外宣传中应尽可能地考虑国内外的舆论反应,并提前设计应对预案,争取政策的解释权与正向的舆论引导,创造有利于我国产业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二,着重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运用,推进产业界自立的政策导向。美国和中国的产业政策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产业政策多是直接针对产业界内部实施资金补助和供需匹配的政策,扶持产业发展,政府直接作用和介入产业发展。而美国的产业政策以更大程度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为前提,多数围绕强化环境政策、提出城市规划和产业指导、对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进行鼓励和保护等间接引导政策。我国的产业政策也应该转变思路,从环境和外围条件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提供竞争机制,推行产业界自立的政策,这样政府调控产业可以进退自如,不被束缚。
第三,借鉴美国在政策制定方面的丰富经验。在政策表述、政策延续以及和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政策协调方面,美国政府积累了大量的成功案例,如2018《先进制造业领先者战略》提到了扩大国内制造业供应链能力,而《中国制造2025》表述语境是努力提高本土产品市场份额,这就往往成为中国政府干预市场的把柄。美国产业政策的政策延续性较强,我国要从国家层面加强统筹规划,滚动制定发展战略,使各种发展要素相互配套。
第四,注重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增强官民协同。美国在产业政策实施初期,就具备功能型产业政策的特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依靠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合作持续推动关键领域的创新和竞争力的提升,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和创新的动力,同时市场的灵活性和竞争性使得创新得以迅速应用和商业化。这种合作模式在美国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美国政府与私营部门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合作开展太空探索,带动了航天技术、卫星通信和航天工业的迅速发展。
第五,针对大国治理特点,加强产业政策的体系性与协调性。我国产业政策具有点多、面广、量少的特点,中央与地方、地方产业政策之间的协同性较弱,需要借鉴美国政府机构协作和政策协调的经验。可成立各种协调机构和委员会,如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业政策委员会等,负责协调不同产业政策之间的冲突和重叠。在政策制定中注重政策整合和交叉支持,鼓勵各利益相关者参与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制定横向产业政策,涵盖多个产业领域,以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美国政府还会对现有的法规和政策进行评估和调整,以适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和需求。
参考文献:
[1]Aghion, P., Dewartripont, M., Du, L.,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 2015(07).
[2]Cimoli, M., Dosi, G., Stiglitz, J. E, The Rationale for Industrial and Innovation Policy[J]. Intereconomics, 2015(03).
[3]E. Kilcrease, E. Jin, Rebuild: Toolkit for a New Amerian Industrial Policy[R]. CNAS Reports, 2022.
[4]Hufbauer G C, Jung E, Scoring 50 years of US industrial policy, 1970-2020[R]. Peterson Institute Press: Special Reports, 2021.
[5]Lin JY,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R].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2).
[6]M. Rasser, M. Lamberth, H. Kelley, R. Johnson, Reboot: Framework For a New American Industrial Policy[R]. CNAS Reports, 2022.
[7]Réka Juhász, Nathan J. Lane, Dani Rodrik, The new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policy[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3.8, https://www.nber.org/papers/w31538.
[8]Rodrik D., Geting Interventions Right: How South Korea and Taiwan Grew Rich[J]. Economic Policy.1995(10).
[9]Rodrik D., Why We Learn Nothing from Regressing Economic Growth on Policies[J]. Seoul J. Econ. 2012(2).
[10]Slatery C, Zidar O., Evaluating State and Local Business Incentives[J]. Economic Perspect, 2020(2).
[11]Smith K, Innovation as a Systemic Phenomenon: Rethinking the Role of Policy[J]. Enterprise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Studies, 2000(01).
[12]Soete, L., From Industrial to Innovation Policy[J].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 Trade, 2007(07).
[13]杜传忠, 宁朝山, 网络经济条件下产业组织变革探析[J]. 河北学刊, 2016. 36(04): 135-139.
[14]干春晖, 王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回顾与展望[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 39(08): 3-14.
[15]黄群慧, 余泳泽, 张松林, 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08):5-23.
[16]纪玉俊, 张莉健, 全球价值链、行政垄断与产业升级[J]. 产经评论, 2018. 9(06): 21-33.
[17]贾诗玥, 李晓峰, 超越市场失灵:产业政策理论前沿与中国启示[J]. 南方经济, 2018(05):22-31.
[18]姜达洋, 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溯源[J].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 2011(03):63-67.
[19]沈梓鑫, 贾根良, 美国小企业创新风险投资系列计划及其产业政策——兼论军民融合对我国的启示[J]. 学习与探索, 2018(01): 120-129.
[20]沈梓鑫, 江飞涛, 美国产业政策的真相: 历史透视、理论探讨与现实追踪[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06): 92-103.
[21]盛斌, 陈帅, 全球价值链如何改变了贸易政策: 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和启示[J]. 国际经济评论, 2015(01): 85-97+6.
[22]汪琦, 钟昌标, 美国中小制造业创新政策体系构建、运作机制及其启示[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8(01): 160-169.
[23]吴军, 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J]. 张江科技评论, 2019(01): 80.
[24]楊继东, 刘诚, 产业政策经验研究的新进展——一个文献综述[J]. 产业经济评论, 2021(06): 31-45.
[25]周建军, 美国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从产业技术政策到产业组织政策[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7(01): 80-94.
[26]周绍森, 胡德龙, 保罗·罗默的新增长理论及其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因素中的应用[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04):71-81.
Historical Context,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U.S. Industrial Policies
Ren Wanzhu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200020, China)
Abstract: Since 2020, the Biden government has been committed to proposing a systematic industrial policy theory that guides the direction of private capital towards key development areas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f rules, subsidies, and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which is sparking extensive policy discussion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reviews the United States' main industrial policies during the stages of forming, development,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and new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instream ideas, primary objectives, policy domains, and policy instrumen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ary pattern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address the main challenges in the current industrial policy of our country. Firstly, it suggests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to maintain strategic consistency. Secondly, it emphasizes the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industrial policies to promote a self-reliant policy orientation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Thirdly, it advocates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 in policy articulation, continuity, and coordin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Fourthly,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and enhancing government-business synergy. Lastly, it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systemic and coordinated industrial policies.
Key words: America; Industrial Policy; Policy Im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