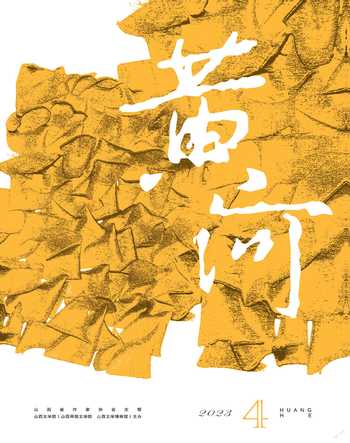费城的冬天
费城的冬天真是冷。我很怕冷,每天必须裹在纯毛大衣里,把领子竖得高高的,还要系好围巾,戴一顶大帽子才能出门。
我喜欢海城。海城并不临海,客观地看并不秀丽,我喜欢那里完全是因为它的冬天一点儿都不冷。你到大学宿舍里接我,我披一件棉夹克就跟你出去。你推着自行车,左手把着车把儿,右手放在车座上,我在你右边,我们并肩在林荫道上慢慢走。我还记得你那辆自行车是黑色的,在十几年前的国内,那种变速的登山自行车还比较罕见。后来它被人偷走,我心疼了好一阵子。你倒是无所谓,说不就是一辆自行车嘛,再买一辆好了。可我不一样,我要求所有我喜欢的人和物要一直陪我到永远。这样一个看起来简简单单的要求,事实上是多么奢侈,我当年并不知道。
走着走着,我突然生起气。当时正好有辆公共汽车在前方不远处停下,我拔腿猛跑几步,跳上车。
记不得是为什么生气,冲你发脾气不需要太充分的理由。十几年前的我就这么任性,脾气坏得不得了,稍不顺心就七情上面,由着性子胡闹。父亲一再教导我要学会制怒,好朋友们也多次善意规劝,我早应该改了的,奈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而你呢,唉,你对我,除了纵容,还是纵容。
那夜我跳上公车后,气鼓鼓的,也不知道过了多少站,偶然一扭头,骇然发现你在车如流水的街上不顾一切地狂蹬自行车,死盯着公车。
“你不要命了!”我下了车,瞪着你,气急败坏地说。
“对不起。”你大汗淋漓,喘息未定。
其实你没做错任何事,根本用不着道歉。你就是这样毫无原则地纵容我的跋扈和蛮横,表现出和你将近而立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的痴迷和狂热。
是的,你曾经是那样爱我。
我们走入灯火通明的夜市,我看到一件洋装,是用相同花纹的紫色和白色软缎拼接做成的,小折的裙摆渐低渐宽,款式大方新颖。你见我十分喜爱,就为我买了。
“怎么总是爱穿紫色呢?”你问,你的眼睛看着我,笑起来露出整齐的白牙。
我也不知道。在你这样问我前,我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种偏好。后来看到一本杂志上说,喜欢紫色的人大多性格敏感固执,情绪容易冲动,真是我的绝妙写照,可惜我一直没机会告诉你。
买衣服后,我说肚子饿了,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吃炒河粉。我很好吃,不过我们通常很少去装潢豪华的餐厅,我偏爱夜市路边的小吃摊。
母亲三番五次地警告我,那些小吃摊上的东西极不卫生,吃了要得这种那种病。在母亲的视线外,我不想千辛万苦地做所谓的“淑女”,特别是在你身旁。我无拘无束,把手臂搁在桌上,便埋头狼吞虎咽起来。
所以你每次都抢在我坐下前,把油腻腻的桌面仔细擦一遍,以免我弄脏衣服。
你总能注意到这一类被我忽视的生活细节。一切完结后,我想到的全是你为我做这些琐事时的情景。当时我认为是理所当然,事实上能为我这样一个人做到如此地步的男人竟是少之又少。
“好不好吃?”你笑着问我。
“好吃!”我嘴里塞得满满的,不住地点头。
那时我们的日子才刚刚开始。虽然我时常和你闹别扭,但心中是快乐的,彻头彻尾的快乐。我没有担心过你我的将来。我欠缺未雨绸缪的习惯。
更何况,周遭的朋友都说我们是“天生一对”呢,我们还是因为这种“谬论”才相识的。
雯君是我大学室友,我们无话不谈。当时,她经常告诉我关于她哥哥的一些事,毫不掩饰地宣称,她哥哥的成熟、耐心、体贴,是上天为我造就的,她想要我成为她嫂嫂。
我嗤之以鼻,笑话她有“荒唐的红娘情结”。我正值花样年华,在大学里左右逢源,约会多得分身乏术,哪里有余暇顾及她那與我素未谋面的哥哥?雯君煞费苦心,为你我制造一次又一次的见面机会,因我始终不肯配合,屡屡功亏一篑。
可是,也许所谓“命中注定”就是如此吧,狂妄自负如我,最后也没能躲过她的处心积虑。
那个夏日的午后,雯君打电话来,约我到我们常去的那家咖啡屋碰面。我当时正在练琴,一口答应,对后来要发生的事没有任何预感。待我走进那家小咖啡馆,看到你在座,不由得为雯君的坚韧不拔感慨不已。
成天听雯君念叨,我心中对你这个人多少有些好奇。在雯君的描述里,你无疑是天底下硕果仅存的好男人,可我并没有如她预期的那样,对你一见钟情。
显然,雯君也没少在你面前提起我。在咖啡馆几个小时的闲聊中,究竟是什么使你对我动了心呢?你立刻开始向我发动了全面进攻。雯君欢喜之余,全力以赴地推波助澜。
而我,曾在雯君面前那般嘴硬,为了自己的虚荣和自尊,也不可能轻易服输,直到那个中秋之夜来临。
那晚的明月明亮如镜,在记忆中特别大特别圆。你开车带我到郊外的湖边,那里是一大片竹林,地上干枯的竹叶铺成厚厚的地毯,散发着温润清凉的气息。
我们席地而坐,你把月饼切成小块,又破开一个柚子,掰了一片,择去籽儿,递到我面前。是因为月下的湖光太迷离,抑或是竹叶间的微风太轻柔?我在那一瞬间突然觉得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其余万事都是细枝末节,都无关重要。
那婆娑的竹影下,你第一次吻我。那感觉出乎意料的甜蜜,我顾不得造作,顾不得虚荣,一头栽进你温柔的包围。此后,我们在各种场合出双入对,摆出一派非君不嫁、非卿不娶的架式。
到头来你娶我嫁各不相干,唉,这是命中注定的吗?
闲时,你带我到你的公寓,做饭给我吃。你烧得一手上好的湖北菜,我特别喜欢吃你做的鱼。你在厨房忙碌的时候,从来不用我帮忙,我坐在客厅,喝着你为我烧好的咖啡,看看电视,读读小说,或者就蜷缩在那儿什么事也不做。
你说你喜欢我安静得像小猫的样子。
在别的男生面前,我不见得如此。和你相比,我确实很小,比你小了十岁,个子也小一大截。你是因此才觉得照顾我是你的义务吧?我也是因此才那么依赖你。
我们在一起,是如此和谐温馨,却遭到我父母的强烈反对。
他们毫无理由地认定,已经工作多年又年长许多的你来约会尚在大学念书的我,目的无非是想骗取我年轻幼稚的感情。而且,他们说,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
“将来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的!”母亲断言。
“你胆敢继续和他来往,就不是我女儿!”教授西洋文学的一贯温文儒雅的父亲也咆哮起来。
我哭泣哀求,希望他们至少先见你一面。可是没有用,他们铁青着脸,拒绝给你任何表现诚意的机会。
我从小是个顺从听话的孩子,从来不曾违抗过父母的旨意,小到穿什么衣服配什么鞋子,大至上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我无一不听命于他们。父母也一向宠爱我,我实在没想到和你的恋爱会成为他们眼中不可饶恕的弥天大错。
我必须承认自己是懦弱的。我缺乏忤逆父母的勇气,又没有干脆放弃你的决心,一会儿希望你的存在是一场梦,一会儿又希望父母的震怒是一场梦。不幸的是,这些偏偏都是最真切不过的现实。我左右为难,无法取舍。
这时候,多亏有雯君帮忙,我们才能不时地见一面。我父母并不知道她是你的亲妹妹。
我开始变得恍惚困惑,你对我越是温柔体贴,我越充满末日来临的恐惧,先前那种单纯无虞的快乐再也找不回来了。
大学毕业前夕,六月底那个酷热的周末,太阳白晃晃地照着。雯君约我到你家,然后你骑着摩托车,载我到西山。西山算是海城唯一的风景点,通常游人比山上的树还多,但那天不是节假日,周围见不到几个人。
沿着青石板的阶梯前行,我们的速度很慢。我戴着淡紫色宽边的大草帽,穿同色绣花的丝质洋装,夸张地大叫大笑,摆很多姿势让你给我拍照,努力迎合你要我暂时忘记一切烦恼的要求。
“不要爬栏杆!小心!”你扑过来搂住我。
其实那一瞬间我真的很想跳下去,趁你还在我身边。脑海中幻化出你横抱着我的尸身缓步下山的画面,那种凝固的地老天荒、那种冻结的海枯石烂、那种令人荡气回肠的凄凉美丽久久萦绕在心头。
所以,如果能重来一次,请你不要阻拦,让我跳下去。不为别的,只为让我们的感情永恒不变,成就一段鲜艳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传奇。
可惜那天你不许,你把我拖下栏杆,抱在怀里。你必然是读出我的思想,才会厉声对我说:“一定要坚强,一定要活下去。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我再也忍不住,伏在你胸前痛哭。我已经预感到即使活下去,与你厮守终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你也有同样的预感吗?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一刻你的眼圈竟也泛红了。
西山之行,果然成了我们最后的相聚。
事情后来的发展一点也不新奇。我父母说送我去旅行,其实是他们策划良久的釜底抽薪之计。等我明白过来时木已成舟,他们就这么把我送到美国。
你曾说过,好想把我变成一个拇指大小的娃娃,装在口袋里,随身携带。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把小娃娃拿出来,迎风一晃,我就能够恢复原样,给你制造无尽的麻烦和无尽的喜悦。可惜这个构想当时没有付诸实施,如今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从此,我在苦寒的费城,孤独地想你。我父母轻轻地一挥手,在你我之间划下一道鸿沟,中间隔着的不止整整一个太平洋,还有匆匆飞逝的折磨人的岁月。我只能写信给你,虽然信件传递的总是过时的心情和感慨,可最起码我能大大方方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担心会惹得什么人因此而生气。除了不能见面外,我们的关系重新获得无拘无束的自由。
我喜欢看你的回信,你的字很大很整齐。你说,我每天念书念得太辛苦,再不能让潦草的字迹枉费我的精力。你对我还是一如既往地体贴,你的痴情在白纸黑字上一目了然。
费城的冬天真是冷。那时,我在学校附近租的公寓很小,整个房间只有一张床,书本纸笔散乱在地上。为了节省煤气费,暖气只开到最低限度,我在房间里也穿着厚厚的毛衣。每每斜倚在床头细细读你的信,细细回忆,闭上眼睛,依稀又回到从前,又闻到夜市小吃摊上叫人垂涎欲滴的香味儿,而你就在身旁。
我喜欢海城实在比费城多得多,可是我一直回不去。读书的时候没有钱,工作后又没有时间。太平洋毕竟是地球表面最大的一片水体,要飞越它,无论主观愿望多么强烈都没用,还必须具备很多很多客观条件。
后来,我毕业了,有了工作,换了一间更大更体面的公寓,而你的来信慢慢稀少。我的心情在越来越空荡荡的信箱前渐渐黯然,渐渐萧条。
其实,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恋人就是这样慢慢疏远的。
有一次雯君到香港出差,打电话来。寒暄过后,她语气含糊地劝我要多为自己打算。我不是笨人,明白她的劝说不是空穴来风。想到你的耐心和体贴如今都用来宽容另外一个女子,我不是不伤心,不是不难过,但我不许自己追问,也不许自己哭。
时间是最有效的漂白剂,再华美鲜艳的感情也经不起它的腐蚀,总要归于苍白暗淡。
父母写信给我,提起你去看过他们,在我拿到硕士学位的那一年。他们对你的印象不坏,说你懂事成熟,和他们原来武断的想象完全不是一回事。你终于得到他们公平的评价,也算是出了积郁多年的一口怨气吧。
可又有什么用呢?你那天是携着你新婚的妻一道去的,我们的结局早已不可逆转。
你的笔迹在我的信箱里完全消失了。雯君偶尔跟我联络,也绝口不提关于你的任何事。我想你一定很忙,建立一个家庭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你的地址和电话就此在我的通讯录里成为一个整齐的定格。在感情上,我始终是任性而自私的,我决定不再使用它们,不再想关于你的任何事。
没想到今天居然会收到你的信。
拆封前,我审视信封上的笔迹好久好久,很诧异你居然还会想起我。收信地址是我几年前的旧住处,居然也能辗转到我手里。
在信中,你写着:我终于明白,你才是我永远的最爱。
以前,看见这样深情的字句,我會哭,现在大不一样,我不会轻易动感情,在我的衣橱里也很少有紫色。
关于你自己的近况,信中说得十分隐晦,似乎你和你的妻已经离婚,又似乎还没有。总之,你对自己目前各方面状况的不满、不快、不甘,非常明显。
其实,“快乐”是对生活近乎贪婪的要求,我现在的生活就无所谓快乐不快乐,日子也这样一天天过下来。
费城的冬天仍是一贯的冷,现在不用节省煤气费了,我的小家坐落在费城东北郊,室内温暖如春。我穿着黑色圆点的丝衬衫,从落地长窗看出去,松树枝头的冰凌在阳光下一闪一闪。一只小松鼠在后院的雪地上东张西望,不慌不忙地觅食。好一个安宁素静的世界!
我的心情十分平静。
两岁的女儿从玩具间跑过来,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在写信。是写给外婆的吗?她把胖乎乎的小手指头噙在嘴里,又问。我俯身抱起她,笑着回答说,不是,这封信不写给任何人。
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
在来信的末尾,你问我可不可以原谅你。原谅你什么呢?你并没有做错任何事。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们这些凡人从来拗不过命运。
那件紫白相间的洋装已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我穿上它的第一天,雯君为我在大学校园中拍的照片仍挂在墙上。
照片上,我的头顶有一树紫薇花正开得热闹,宽大的裙摆在绿色的草地上铺开成一个闪亮的圆,我披着长发坐在圆心,树上撒下的花瓣落在发上裙边,我笑得十分灿烂,一种心无城府的快乐。
女儿不止一次问我,照片上的人是谁?她始终不相信那是她妈妈,她不知道她妈妈也曾有过那样华丽丰满的青春,也曾有过那样单纯真挚的欢颜。
弃我而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如今,你在没有冬天的海城,我在酷寒的费城,中间隔着的不止一个太平洋,还有岁月,以及我们早已分道扬镳的心。
【作者简介】江岚,博士。现居美国,从事域外英译中国古典文学、国际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出版学术论著《唐诗西传史论》(中文版2009,2011;英文版2018)、短篇小说集《故事中的女人》(2009)、长篇小說《合欢牡丹》(2015)、有声书系列《其实唐诗会说事儿》(2020)。编著“新移民女作家丛书”十二册及海外华人文集《讲述华裔》《四十年家国》《故乡是中国》《离岸芳华》等。现为美国人文社科华人教授协会会员,先后当选六届理事会理事,兼外联部主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终身会员,历任三届理事会理事、副会长兼外联部主任;海外女作家协会终身会员。
责任编辑:柏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