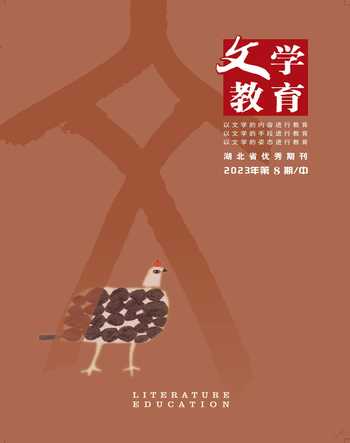英汉语非作格动词与论元关系分析
陈凯伦
内容摘要:本文讨论比较了英汉语非作格动词的定义和异同,详细分析了非作格动词与论元结构的关系:英语中非作格动词的论元位置较为固定,一般位于动词前;汉语中非作格动词的论元位置较为灵活,既可以位于动词前也可以位于动词后。在非作格动词接宾语现象中,汉语非作格动词的论元结构不发生变化,而英语非作格动词论元结构的变化主要在语义和句法层面:句子主语集致事和施事于一体,而宾语则处于受控制与服从地位;致使化非作格动词句的句法生成以及物性动词为起点,在此基础之上投射出及物性轻动词v,并由v负责引入新的施事外论元。
关键词:非作格动词 论元关系 英汉对比
自非宾格假说 (Perlmutter 1978) 提出以来,非作格动词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 (Kuno 1987; 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95; Goldberg 1995; Rosen 1996; 沈家煊 2006; 韩景泉、徐晓琼 2016; 付义琴 2012等)。现有研究主要针对非作格动词致使化现象、非作格结果构式和非作格动词带宾语等语法现象,而较少关注英汉语非作格动词与论元的关系。因此,本文比较英汉两种语言中非作格动词的异同,拟从语义和句法两方面展开分析,试图解决两个问题: 1) 英汉语非作格动词与动词论元的关系;2) 非作格动词论元结构变化及其原因。
一.英汉语非作格动词的定义
Perlmutter 的非宾格假说认为,根据能否带宾语,动词可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而根据动词出现的句法结构及词汇语义,不及物动词又可进一步分为两类,即描述无意愿控制动作的非宾格动词和描述有意愿控制动作的非作格动词。其中非宾格动词的语义特征可以概括如下:带语义受事,表非自主地发出感官刺激,表存在和发生,表时体概念,表持续。与此相反,非作格动词往往指涉活动,表达具有意志的自主行為或者非自主的身体活动。
1.英语非作格动词的定义
英语非作格动词从语义上说包含一个主语,该主语主动触发或是主观上负责由此动词表述的行动,它有一个语法主语,但无宾语。而非宾格动词的主语是经过移位生成的,在深层结构中是宾语。Perlmutter结合动词的语义内容对英语中的非作格动词进行如下总结:
①描述意志或意愿动作的动词:work,play,speak,frown,think,ski,etc.
a.言语方式动词,例如:whisper,shout,mumble,etc.
b.描述动物声音的动词,例如:bark,neigh,whinny, quack,meow,etc.
②某些无意识的身体过程:cough,sneeze,hiccough,sleep,cry,breathe,etc.
在管辖和约束理论框架内,Burzio认为非作格动词无论在深层结构中还是在表层结构中只有一个作主语的域外论元,主语是动作的发出者,充当施事角色。从 Chomsky 最简方案框架下看,非作格动词可以描述为NP [vp V],即非作格动词基础生成于VP嵌套内v的补语位置,非作格动词的主语基础生成于VP嵌套内v的标示语位置,即非作格动词的主语在S-结构和D-结构中都处于IP的指示语位置,构成NP+V的形式。如:They swam. They在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中都做主语,具有施事的性质,因此动词swim是非作格动词。
2.汉语非作格动词的定义
在深层结构中,汉语非宾格动词的唯一论元处于宾语位置,而非作格动词的唯一论元处于主语位置。但在表层结构中,汉语非宾格动词的论元既可以留在宾语位置,也可以移至主语位置;而非作格动词的论元通常都出现在主语位置,构成NP+V的结构,比如动作动词“哭、笑”就是非作格动词,它们通常不能出现于V+NP的结构,比如可以说“她哭了”,但不能说“哭了她”。当不及物动词表达无内在终结点的事件时,鲁雅乔、李行德 (2020) 根据施事性及致使类型对不及物动词进行分类:在表达无终结点事件的不及物动词中,如果动词未标明事件致使类型,则该动词为非宾格动词;如果动词表达由内因引起的致使事件,该事件由施事引起,如跑、走、跳等,或是由不具备施事性的内因引起,如咳嗽、打哈欠等,该类动词均为非作格动词。
3.非作格动词的范围及其变化
非作格动词具有赋格能力,尽管它的论元结构中没有可以赋格的内部论元,但它可以把宾格赋给非词语搭配的名词词组,即非作格动词其实在一定的条件限制下可以带宾语。具体表现为,英语中非作格动词结构NP1+V+NP2中NP1是域外论元,是有生命的施事角色,NP2是开放的,有附宾语的潜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接纳同源宾语,如:
(1) a. Bill sighed a weary sigh.
b. Sue slept a sound sleep.
汉语的非作格动词结构NP1+V+NP2中NP1也是有生命的施动者,非作格动词常与时间成分一起使用,在汉语中主要是与完成体:“了”或者“过”甚至还有存现句中的“着”连用。NP1与NP2之间是自由的,两者之间不存在从属或者制约之类的任何关系。如:
(2)a. 娜娜哭湿了手帕。
b. 他们办公室接连感冒了三四个人。
二.英汉语非作格动词的异同
1.英汉语非作格动词的异
英汉两种语言中非作格动词的一个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其句法行为上。英语非作格动词的句法行为较为稳定,其唯一论元在表层句法结构中一般位于动词前充当主语,较之英语,汉语非作格动词的句法行为较为灵活,其论元在表层句法结构中既可以位于动词前也可以位于动词后。当论元位于动词后充当宾语时,须符合以下条件:句首一般有话题,论元一般表数量成分 (如: 她们班哭了三个孩子)、对比成分 (如: 这个沙坑跳了五个男生,那个沙坑跳了三个女生)、或处所、方式 (表活动方式的非作格动词与方向性补语共现时)、 时间、对象或工具的光杆名词 (如: 他经常跑上海)。(朱秀杰、王同顺 2016)
英语的非作格动词单独使用时不用于使役结构,然而,当后面接有趋向补语或者结果补语时则是可以的。英语中表示结果的补语经常由形容词或者副词充当,补语跟在名词或者代词的后面 (如3a、b)。英语非作格结果构式中的结果谓词总是作述语,结果谓词可以是主要动词后名词成分的述语,也可以是非宾格动词主语的述语,但不能是非作格动词主语的述语 (如3c)。
(3) a. You may sleep it well.
b. The dog barked him awake.
c. * The dog barked hoarse
Levin and Rappaport Hovav出于对上述的解释,提出了DOR原则,即结果谓词是宾语名词的述语,结果是宾语指向的结果,而不管这个名词成分是否是主要动词的论元。但是,汉语的情况有所不同,表示结果的补语通常由形容词或者动词充当,补语直接加在动词后面(如4a、b)。DOR原则在汉语非作格结果构式中不是那么严格。阚哲华 (2010) 就指出汉语不及物结果构式中,假反身代词是可以缺少的,并且结果是与主语直接关联的,而这在英语中是不合法的(如4c)。如:
(4) a. 娜娜哭了。
b. 娜娜哭湿了手帕。
c. 他站累了。
2.英汉语非作格动词的同
英汉语非作格动词最主要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描述有意愿控制动作的动词,从语义上说包含一个主语,该主语主动触发或是主观上负责由此动词表述的行动,它有一个语法主语,但无宾语,主语是动作的发出者,充当施事角色。其次,在范畴语法中,对于包含结果短语的英语句子的处理办法 (如3b) 与汉语类似的句子的表层形式相似,这种技术手段在范畴语法中叫“嵌入”。汉语中的结果结构的表层表达式是动词直接和表示结果的补语组合成述補短语,再加上后面的名词词组。这也就说明汉语的结果结构的表层表达式直接反映了动词、补语和名词之间的关系,是范畴语法中的“嵌入”这样的技术手段理想得到的结果。
3.英汉语非作格动词的比较
英汉语非作格动词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句法行为上:英语中非作格动词的论元位置较为固定,一般位于动词前;汉语中非作格动词的论元位置较为灵活,既可以位于动词前也可以位于动词后。在非作格动词致使现象和非作格动词结果构式中,英汉语两种语言也存在着不同之处。而从语义上来看,英汉语非作格动词都是描述有愿控制动作的动词,只包含一个主语,充当施事角色。在致使型结果结构中,对于包含结果短语的英语句子的处理办法与汉语类似的句子的表层形式相似。
三.英汉语非作格动词与论元关系
1.英语非作格动词与论元关系
英语中非作格动词的论元位置较为固定,一般位于动词前,非作格动词有且只有一个外论元却无直接内论元,无论在深层结构中还是在表层结构中都处于主语位置,充当施事角色,即构成 NP+V的形式。尽管非作格动词后面没有可以赋宾格的内论元,但其具有赋格能力,可以把宾格赋给非词语搭配的名词词组,存在非作格动词致使用法。如:
(5)a. The man walks his dog everyday.
b. *The parents played the children.
韩景泉,徐晓琼 (2016) 认为 (5a) 中的“walk”经历了一种致使化或及物化操作,其结果是将不及物性施事动词即非作格动词转变成了及物性致使动词。而 (5b) 又说明了非作格动词作致使用法面临一定的限制条件。本文将于下一章从语义和句法两个方面说明其中变化并进行详细分析。
2.汉语非作格动词与论元关系
汉语中非作格动词的论元位置较为灵活,既可以位于动词前也可以位于动词后,也就是说非作格动词其实在一定的条件限制下可以带宾语,如名词词组或者量词词组,构成非作格动词带宾语的语法现象。但是汉语中单个非作格动词与结果补语构成动结式复合词后,其论元结构并未发生变化,他们的词性也并不会因为他们后面加接结果补语而发生变化。以 (5) 中a、b为例,a中“哭”单独使用时是非作格动词,只有外论元,没有内论元,不用于使役结构。在b中,“湿”是表示结果的补语,与“哭”组成一个动结式复合词,“娜娜”是外论元,“手帕”不是“哭”的内论元,而是“湿“的是外论元。可以看出,(5) 中的非作格动词的论元结构是一致的,并未发生变化。
3.英汉语非作格动词与论元关系的比较
英语中非作格动词的论元位置较为固定,一般位于动词前;汉语中非作格动词的论元位置较为灵活,既可以位于动词前也可以位于动词后。英语非作格动词发生带宾语现象时会经过致使化或及物化操作从而从不及物性施事动词转变成了及物性致使动词,而汉语中非作格动词的论元结构并未发生变化,词性也不会因此改变。
四.论元结构的变化及分析
1.论元结构变化
英语非作格动词致使化之后,其论元语义上发生的显著变化在于丧失了施事论元的典型特征,即不再具有意愿性,不再是行为事件的主动发起者,也不再具有完全控制行为动作的能力。相反,它已成为了受控制的致使对象,不仅语义上具有典型的受事特征,而且句法上也与受事一样充当了致使句的宾语。如:
(6) a. The horse jumped over the fence.
b. The rider jumped the horse over the fence.
从 (6) 中可以看出,原来的施事论元“the horse”已失去了施事的地位,但出现了一个集施事与致事于一体的外论元——“the rider”,不仅是致使动作的主动发起者,还是最突出的直接使因,全程主导动词所表达的整个事件。虽然句子宾语“the horse”也是直接参与者,但它属于致使的对象,始终处于受控制的被动与服从地位,缺乏独立自主意愿和独立自发行为。这也表明了“jump”由a句中的非作格动词转变为b句中的及物性施事动词。
2.变化过程分析
一个特定具体的英语致使句子能否成立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语义上能够与人们的世界知识相容;二是结构上能够通过句法机制的推导 (胡旭辉 2014; Rappaport Hovav 2014)。
从语义层面来看,致使化施事动词句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致使宾语一方面既具有参与行为动词的内在能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但另一方面同时又缺乏独立自主意愿,是事件中完全受句子主语控制的被动参与者。致使宾语的这一特点又反过来要求致使主语不能仅仅是致事,而且必须是具有掌控宾语对象能力的施事。
从句法层面来看,韩景泉,徐晓琼 (2016) 认为,致使化施事动词句的结构生成不涉及非作格动词的非宾格化,而只涉及到非作格动词的及物化。以 (6b) 为例,根据“合并条件” (Radford ),动词“jump”先与PP间接内论元“over the fence”合并,构成V“jump over the fence”,然后再与NP直接内论元“the horse”合并,构成VP“the horse jump over the fence”。接下来VP与及物性致使轻动词v合并,由于v具有强语素特征,须吸引实义动词“jump”的显性移位与之嫁接形成v-V结构“jump the horse over the fence”。一方面,直接内论元“the horse”从及物性动词“jump”处获得结构宾格的赋值,另一方面及物性致使轻动词v引入致使外论元“the rider”,构成 vP“the rider jump the horse over the fence”。 在与过去时态中心语T合并后,“jump”拼读为“jumped”;外论元名词组“the rider”与时态中心语T形成一致关系,取得结构主格的赋值,并通过移位进入T的指示语,即句法主语位置,完成句子结构运算。
本文通过比较英汉语非作格动词的定义和异同,探讨了英汉语非作格动词与论元结构的关系:英语中非作格动词的论元位置较为固定,一般位于动词前;汉语中非作格动词的论元位置较为灵活,既可以位于动词前也可以位于动词后。其中,汉语非作格动词在致使结果构式中论元结构并未发生变化。而英语中非作格动词发生致使化,动词的语义结构和句法性质均发生了本质变化:句子主语集致事和施事于一体,而宾语则处于受控制与服从地位;致使化非作格动词句的句法生成以及物性动词为起点,在此基礎之上投射出及物性轻动词v,并由 v负责引入新的施事外论元。
参考文献
[1]付义琴,2012,从语法史角度看“一元动词带宾句”现象 [J].《外语学刊》(2):35-39.
[2]韩景泉、徐晓琼,2016,英语不及物性施事动词的致使用法 [J].《外语教学》(4):6-10.
[3]胡旭辉,2014,英语致使结构: 最简方案视角下的研究及相关理论问题 [J].《外语教学与研究》 (4):508-520.
[4]阚哲华,2010,《致使动词与致使结构的句法-语义接口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5]鲁雅乔、李行德,2020,汉语非宾格与非作格动词的句法及语义界定标准 [J].《当代语言学》 (4):475-502.
[6]沈家煊,2006,“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兼说汉语“糅合”造句 [J].《中国语文》(4):291-300+383.
[7]朱秀杰、王同顺,2016,中国学生英语中不及物动词的及物化现象研究 [J].《外语与外语教学》(3):6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