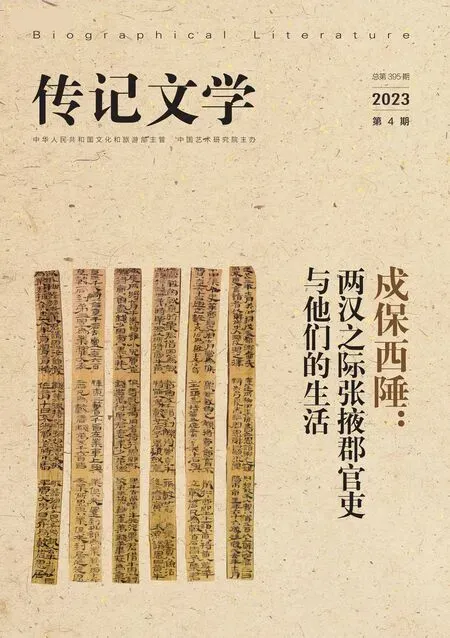导语:从小历史到大历史
斯 日
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处于不同阵营之下的传记和历史,其实是“智识”上的邻居,都以人的行为以及人所组建并生存于之中的社会为关注和研究对象,都以叙事图式来组织和建构对人类社会过去史的阐释,二者应是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关系。当然,传记和历史在最初的产生以及相对漫长的时间里,确实打造了携手并进、共谋发展的理想状态,为人类历史叙事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现代学科的产生及其细分,二者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历史有意疏离甚至逐渐抛弃了传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来自于史学学者对传记的“偏见”,他们认为,传记只围绕个体生命,视野过于狭窄和个人化,无法涵括、反映和研究整体的、复杂的社会发展史,更有甚者,指责传记是文学叙事的一种,有虚构性,背离历史事实的核心概念,并将传记归入到小历史的范畴里。从此,传记与作为大历史叙事的史学之间关系开始疏远,传记甚至在主动或被动中渐渐减少关于历史时代发展方面的叙事,越发呈现个体生命史化趋势,随之变成当下我们阅读最多的个体生平叙事文体,虽丰富了个体生命时间的线性叙事,却丢失了本应与个体生命史息息相关的宏大历史叙事。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但历史的发展之路充满了多样性和复杂性,有时也会呈现迂回往复的现象,这既是历史的本质,也是其魅力所在。传记的小历史和史学的大历史之间关系亦如此,或者说,二者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分道扬镳之后再次呈现出彼此融合、相辅相成的趋势。学界曾认为,在与政治史叙述过程中形成的传记的小历史与史学的大历史之间的界线已然建立,尤其是受现代学科细分影响,传记扮演小历史的角色,无法参与大历史的叙事,二者之间形成牢不可破的泾渭分明关系。但是到了当代,更准确地说是从20 世纪30 年代开始,尤其是二战之后,一直到70 年代以来,随着大众社会的崛起以及意大利微观史学观的产生和发展,传记和历史之间渐渐打破了固有僵化的二元对立关系,小历史与大历史再度联袂叙述人类历史进程。传记所叙事的个体生命的小历史,以其重返历史现场的真实性、细节性、生动性有效弥补了大历史叙事在总体史视角下所忽略或有意摒弃的社会发展中多元构成元素及其历史上的存在面貌,尤其是小历史叙事让一些在大历史中被遮蔽的小人物、边缘人以及女性重返历史现场,还原历史本来的完整面貌,让历史不再只是帝王将相和英雄伟人的历史。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鲁西奇的《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等“小历史”的叙事,令我们再次感到,历史并不是冷冰冰的政治、军事、经济发展史,而是有着人自身情感、心智、温度的叙事。当下史学界所热议“历史的传记转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当然,需要补充的是,这样有温度的历史叙事中,除了作为小历史的传记之外,同样受到史学有意排斥的社会学也在扮演着与传记一样的角色,林耀华的《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马乔丽·肖斯塔克的《妮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重访妮萨》等社会学著作打破历史、传记、社会学之间被学科切割的分界线,在一个个生命史叙事中重现了微观但反而更加真实、更具说服力和生命力的历史事实,由此也带来社会学的传记取向。
学术研究应重点关注和回应当下现实。我刊2023 年第4 期特别推出“戍保西陲:两汉之际张掖郡官吏与他们的生活”封面专题,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焦天然博士依据居延出土汉简所记载的史料,讲述西汉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至东汉和帝永元十年(公元98)之间发生的历史。这里讲述的历史是以往大历史叙事中所阙如的或记载不完整的,我们所不熟知的,造成这样的原因有二:一是历史文献资料的不完整;二是受大历史观的局限,正史中有意淡化、遮蔽甚至抛弃对个别边缘地区以及基层小人物事迹的载录,其中后者为主要原因。所幸地不爱宝,从1927 年开始陆续出土的大量简牍相对详细地为我们重现了两汉时期河西地区戍役基层军事组织中军人生活史,弥补了大历史中相关内容的缺失。焦天然博士从大量汉简中择取部分简牍,讲了三个故事,既有大历史叙事,如汉代西北防线军事要地张掖属国都尉窦融十余年的经略河西史;亦有小历史叙事,如中层官吏张获与粟君的职业生涯史和周育、冯匡、薛隆等处于最基层组织的小吏日常生活史;既有对正统史学研究中“二重证据法”的坚持和运用,更是依据出土简牍中散乱的档案文书、私人信件等,钩沉出边防军事组织中基层吏卒的屯戍生活,从而使我们了解两千多年前守边普通军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这些有血有肉的生命在大历史叙事中曾只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这样的叙事是历史的传记转向,也是社会学的传记取向,目的是要真实还原历史更加完整的面貌,少了这些小人物,历史就不完整,体现了作者从小历史叙事达到大历史研究的宏阔学术视野。
打通历史、传记、社会学边界的著作的频繁产生以及其所引发的影响力,促使我们思考:在现代学科细分化格局下,如何叙述人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其实,历史、传记、社会学,作为叙述和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学科,三者之间关系并非如表面所呈现的分化状态——被分割在三个不同学科领域里,各自独立,各自体系化——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三者之间关系是开放式的,因为人及其社会的实际状态是整体的,社会并非被分割成历史的社会、传记的社会、社会学的社会,等等,诸如此类的独立空间只是我们在学科研究视野下将社会进行分割,并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研究和阐释,这也是当代人文学科研究时常陷入瓶颈困境的原因之一。鉴于学科之间壁垒越建越高、研究效果则越来越弱的现状,已有国内外学者在呼吁打破学科之间的僵化观念,推进跨学科研究。意大利微观史学家、微观史运动发起人之一乔瓦尼·莱维在《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一文中所阐述的正是其中一种代表性声音:“如何在不忽视个人和社会状况的情况下实现一种普遍性的概括?或者反过来,如何在描述社会状况和个人的同时不放弃对普遍问题的理解,不落入类型学说或典型事例的窠臼?”
我们不应该为学术而学术,而应该为人生而学术。关注个体生命,关注普通的边缘小人物的生命,关注微小社会集体和族群,并非是无关紧要或是不具备宏大历史价值的,目光向下的历史研究更能够深入到历史社会的最深处,更能够揭示历史复杂而多元的事实,使我们在一个个普通然而活灵活现的生命史叙事中触摸到历史的温度。在这个意义上,传记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历史学、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的重视,甚至使之不约而同都产生了传记转向。对传记叙事和研究而言,这种转向虽然是我们乐于看到的但并不是最终努力的方向,应该说这是一个过程、一个方法,抑或说这是传记与其他学科携手并进,一同叙述人类自身历史的一个有心智、有情感、有温度的途径。因为有温度的历史叙事,才是好的历史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