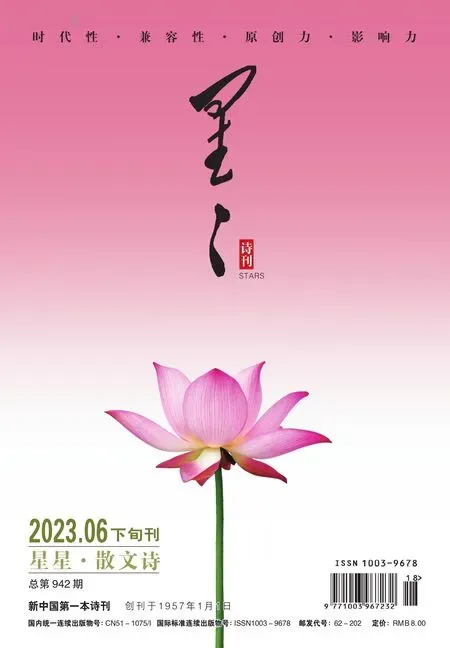和我一起奔走的故乡(组章)
王德宝(四川)
身体里的故乡
算起来,故乡在他只叫得出名字的地方生长,拔蒜一样拔起来,装进了行囊。
故乡和他一起,几十年下来,变化的只是口音,和打量故乡的目光。
行囊里的故乡依然保持着他离开时的模样:柴犬凶猛,炊烟懒散,张大爷的目光还在关注叶子烟的烟灰为什么没有以前白,李大娘掰开小孙孙的口腔,嘟囔牙齿为什么长得和其他娃娃不一样。
这个故乡没有人衰老,更没有人死亡,所有的土地都用来栽种乡亲们的愿望:桃花红,杏花白,田边地角即使起争吵,听起来也跟唱山歌一样。暂停在那里,并且美好。
他觉得自己只是一条蚯蚓,只能在现实里踩出一条小径,供自己来来往往。
外出受伤,他也会呼喊,但他的声音好像都是喊给自己听的一样。
不像在故乡,表情有人关注,呼唤有人应答。
这个时候,他就会坐下来,解开行囊,认真端详故乡的模样。
刘娟娟递上他想要的橡皮擦,让他擦掉大意留下的污迹,给他重新开始的机会。
他会开心地接受父亲的呵斥,让那个刻骨铭心的声音永不消失。
他会快步去接过母亲身上的柴火,不让那个大山一样沉重的东西,把他的母亲一点一点地摁进土里。
刘大伯会走家串户来理发,还原他身上的倔强和朝气。
炊烟还在房顶溜达,在山坳里反反复复吐槽每一个相似的早晨和黄昏。
他打开门窗,问好走进眼里的每一块田地,问候路过的每一个人。
他看到他们都把笑容转过来,就像他们看见的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希望。
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任何举动都堂堂正正,充满底气。
故乡,长在他的身上,跟他一起走南闯北。
他知道,这样的故乡永远不会老。即使他老了,故乡也不会。
“退休”的父亲
打完最后一田稻谷,父亲洗脚上岸,放下裤腿,大声地对母亲说:“我要退休了!”
父亲的决定通过母亲的电话,很快就传达给了外地的儿女。
父亲不愿意再侍弄那些让他又爱又恨的田地了!父亲的这个决定让老家那晚的炊烟东倒西歪,充满了犹豫。
变卖了家里的农具后,父亲很快就和母亲搭车来到绵阳,住进了儿女们给他们租来的房子里。
母亲依然在为她和父亲的一日三餐奔忙。父亲则穿上了他卖完稻谷后买的一件黑色风衣,竭力装扮成一副城里人的样子,每天在白云洞的公路边,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
“当了一辈子农民,这才是我想要过的日子。”父亲说。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目光落在路边晾晒的花生们身上,好像在分析它们的成色和品质。
没过多久,父亲就打起了富乐山的主意。
他和母亲在山顶找到了一块被人撂荒的土地,开始拔草、翻挖,然后种上了花生。
周围的土地都有归属,所以他们对这块开垦的土地非常在意,过几天就会爬上去拔拔草,看看花生苗的长势。
有时候就会和关注他们动静的我在山顶不期而遇。
“没法浇灌,长势如何,有没有收成,只有看老天爷的意思。”父亲说。
我看到父亲古铜色的脸上,依然保留着故乡雨打风吹的痕迹。
我知道,父亲即使穿上了城里人的衣服,他也无法在这个城市里安生。他还是想找一片土地,把他从老家带过来的那颗心,认真种下去。
父亲的提议
父亲又早早地钻进了被窝里。
母亲刚刚给他洗了脚,擦拭了一遍身体。衰老,不但消解了父亲的火爆脾气,还消解了他生活自理的愿望和能力,这让我对八十岁的理解感到有些泄气。
母亲站在洒了一地的洗脚水里,感到有些体力不支。我知道,她并不比父亲年轻多少,同时还疾病缠身。伺候这个男人,更多是出于她的生活惯性,还有她理解的责任。
衰老,已经让父亲对这种状况感到心安理得。
他不知道我心里的担忧和恐惧,不知道我在担心他们的这种状态还能持续多少时日。
父亲微笑着仰起头,说他过几天要回老家去。“老家的土地再不种点啥,今年又长不出来啥东西。”
愿望产生动力。我不会阻止他产生愿望的机会。
“等天气再暖和一点回去吧。”我说。
在春天种下希望,这是每个人都想做的事情。
父亲觉得这一生最好打交道的,还是土地。
土地不会和他胡搅蛮缠,不会把黑的说成白的,把他的付出贬得一文不值。对于父亲来说,他对土地的感情跟对母亲一样深。
在回老家这一点上,母亲很认同父亲的提议。尽管自己疼痛加身,她还是想跟在父亲身后,照看父亲的身体。爱皱眉头的母亲一直担心,父亲的身体有一天会不响应父亲的提议。
挂在墙壁上的马灯
穿过无数岁月留存下来的马灯,像标本一样挂在墙上,被来来往往的风和走近的目光打量。
曾经的光芒和它的主人一样,已经被过去的黑暗带走了。
那些让马灯想播下的光明,如今在我们的生活里,已成为日常。
马灯被保存下来应该是刻意的,被挂在墙上应该是刻意的。
今天来打量它的目光当然也是刻意的。
刻意去想象一下那些拎过它的手。
刻意去琢磨一下它当年挡过的风雨,以及被黑暗吞噬的光芒。
刻意去记住它照亮过的那些理想。
退后一步,我们就能看到,马灯和挂它的墙壁一样,只是今天的一个小点,能够放大的只是一些想象。
今天的阳光,早已浩浩荡荡地开过来,占领了这个世界的所有地方。
那些让马灯痛苦的黑暗,其实早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被认养的葡萄
藤蔓刚刚用嫩芽拟出成长计划,它这一年就被人买走了。
种葡萄的人当了掮客,美其名曰“认养”。
葡萄也因此多了许多主人。
再有脾气的葡萄也无法负气出走。
它只能在它生根的地方,埋下自己的愿望,然后按照主人们的想法,认真成长。
长叶了!
开花了!
挂果了!
主人们的惊呼和欢叫,并没有让葡萄安于现状。
它用硕大的叶片,接住一段又一段炽热的阳光,然后摊在手上,慢慢端详。
它在琢磨,还需要多久,它才能摆脱被人认养的现状。
没有人知道,栽在葡萄园里的葡萄,也想自由生长。
盖头山上看茶
苔子茶长在盖头山上。
上山去看茶,必须穿过阳光,穿过林荫,接受山风的指引。
苔子茶一垄垄地列队,在山坡上欢迎我们。
倾斜的茶壶在山顶上,似乎正在倾倒泡好的岁月,斟给远道而来的我们,也斟给飞鸟和流云。
我们没有采茶。
我们穿行在茶树中间,听茶树讲自己和春天的故事,也听管理人员讲茶叶的未来和过去。
茶叶在笑,我们也在笑。
跑来跑去的风,把我们的笑送到更远的山上。我们看到,周围的山都有了明媚的表情。
茶香是在山上长出来的,是在清风明月里酿出来的。
我们觉得周围的大山和头顶的阳光也是茶客。他们的口味比我们都重,他们不分晨昏地吮吸芳香。他们泡下的也不只是茶叶,还有茶树在坡坡坎坎上经受的日月。
那种味道应该比采茶人的山歌更悠远、更绵长,比采茶妹流转的眼波更明亮、更动人。
离开茶园的时候,我们看到阳光已经掀开这座山的盖头,让我们看到了擂鼓镇的脸。
我们看到更多的人离开擂鼓镇,走向盖头山。
掀开了盖头的盖头山,目光炯炯,向来来往往的每一个人都展开笑颜……
老去的翅膀
翅膀在天空中老去,在飞翔中老去。就像我的嘴巴在别人的唾沫横飞中老去,在自己喋喋不休的话语中老去一样。
我喜欢的那些鸟儿,又离开树枝,跃上了天空。
天空里有游移不定的云朵,有突然钻出来的阳光,还有其他的翅膀。
我拿不准它们是冲着什么去的。我只看到它们的翅膀,闪着银色的光芒,似乎想把背后的乌云擦亮。
阳光沉甸甸的,总是斜斜地落在我们的背上、肩上,还有脸上,好像在提醒我们,它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我体内有阳光带来的温暖。我把温暖带进目光里,又送到天上,送给那些翻飞的翅膀。
那些翅膀还在盘旋,还在凝聚俯冲的愿望。
我相信,激励它们继续前进的,一定还有其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