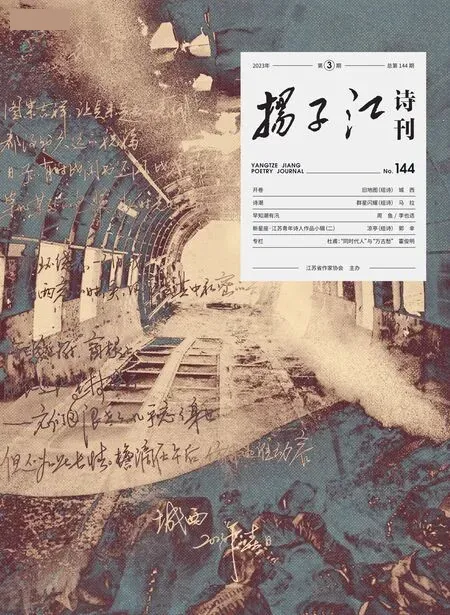以但丁为终点(组诗)
施茂盛
在那不可知中
请从这垂立的湖面取回那条绝径,
让我深陷一种不可知中。
临渊的白鹭,诫句般刺目。
落暮披覆,就像这世界的遗稿,
带着我的体温,完成它最后的叙事。
我失神良久,在渺远的万有引力中。
星辰与星辰之间,风携带着
一座座自转的旋涡,在经过我。
每一颗随之涌来的芥粒,
似乎都有内生未解的结构。
而天幕即将被凿开,它的拱廊
也第一次露出精准的抛物线。
在它密集的顶点,我深陷
一种不可知中。像白鹭一样我
腾空跃起,垂立的湖面扑面而来。
此刻,我舌苔下压着的那颗
蓝色药丸开始缓缓融化。
舌苔下压着的群山也在融化。
一首诗
我多么羞涩:在某日黄昏,遇上一首诗。
它颤抖地从我身上掠过,减速,然后降落。
我得以看清它苦闷的五官扭曲在一起;
呵,苦闷。有时候它在这些诗行中,
加重了灵感,就像一杯清水掺进水银。
我们开始谈论它。顺便谈论它经过的事物。
在它的源头,我们探望到瞬间的星空,
薄霜般闪烁着人性晶莹的光芒。
我们可以把它的秘密,当作俘获的经验,
就像它自然而然有它存在的虚无之美。
老人们也开始加入我们的队伍。
公园里,割草机裹着暮色,在草坪上突突向前。
一排灌木有意将它引向更深的思虑。
但他们更多是陷在此处。言语间,
似乎为另一个宇宙如何运行烦恼不已。
我理应独自一人走完园林深处的通幽曲径,
希望因此解开它的修辞之累。它碰巧有一个情节,
将词语固有的念想,鼓得像神的斗篷。
只是天色已晚,我再也没有向前跨出一步。
当我返回它醒来的地方,它却仍然不置可否。
远郊的天气
远郊的天气会有些变化,
我在院子里为一棵柿树支起防鸟的纱网。
那棵柿树已显青黛轮廓,
不久,它将奉献硕果。
但极有可能来不及摘几只送客,
它自酿的蜜已悄然改变了它的时序。
黄昏寂无声息的停顿中,
我透过厨房的窗台观察着。
它在吐纳,被自己的呼吸渗透。
想它去年此时的疏松,
棘球撞飞天葬师之后,钢铁的骨骼快速收拢拧转,重新化作了六只节足,撑着唐飞霄的身体,正正地落在天葬台上。
似乎随时都有新的主题跃出——
嫁接过的骨头仍有俊秀的嫩枝生长,
叶上汇聚着雷同的露珠,
树冠蒸腾四周涌起的雾气。
而我内心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新意,
它蒙受的恩典都来自旧知。
差不多已延续多年,一棵柿树
在另一棵的心境中梳理自己,
它映照的天空裸露着深秋的裂痕。
以但丁为终点
凭空移来一些惊雷。
与此同时,紧固的泉眼松开,
开始完成它的第一次喷薄。
我接受着星尘的信息,
这迷失已久的脑电波终于到来了。
那位蒙昧的主宰者,
正在修订着语言;
他需要通过重新学习,
回到那晚霞中。
我的屋宇被云间的雪照彻,
庭院里落满松子。
造访者会越来越多,
但许多人都失去了源头。
而诗人位列银河岸畔,
他们以但丁为终点。
垂直而下
对秩序那种精准的爱,
来自于在星辰与星辰之间的隐忍阅读。
这些像补丁一样钉在
穹顶的星辰,
是穹顶的青冈与湖泊。
我行了三千里路,
用铜打的牙齿一颗颗咬过。
地上,大风将村庄重新排列了一遍。
今夜浊气倾空,清流灌顶。
我觉得我已值得一死。
但我克制着,
想让鞭策的肉体先经过。
顾城
反复梦见镜子,梦见水银晃动。
即将烂掉的脸枯荷般晃动,
看上去似乎有着语言的业障。
他说过些什么?舌苔下小塔翻倒,
在他生前压住身体内不断涌出的草茎。
他司空见惯的身体存在过吗?
总会有为数不多者
从落日的窗前看见,柳色在不确定中加重。
柳色,此刻它亲手毁掉筑于湖心的
宫殿,毁掉镜中掘出的墓床。
花是斧的轮回,而斧
在镜中抱冰而卧。
此去经年,他已嗅出病虎的味道。
一只孟加拉病虎在奥克兰,
反复梦见脊背上移动着一座致幻的花园。
极简的灵魂戴着这顶繁复的帽子。
还养了一群乌托邦的鸡,而它们
又将在该死的砍柴声中疯掉。
从未有人怀疑一切已隐含其中,
他也不断屈从于身体浓缩为一个器官。
世界仅仅是开始,
他那么兴致勃勃,几乎裂成最后的两瓣。
镜中果真有他所梦见的:
比如他在新年的院子外杀鸡,
比如他沐浴在宗教的烂泥地里。
快雪的弹奏
那夜,极简的肖邦俘获了快雪般的灵感,
恰巧可以替换旧谱中过于局促的和声。
波兰后来的那些诗人,也曾借用过它,
但对这一脆弱的命题都未有更细微的呈现。
虽然他们尝试过要将善意化为普遍的良知,
深刻的境遇却又动摇了他们的心。
那个年代,即使是在去往巴黎的途中,
他也不能完全感知任何来自未来的预兆。
在那天幕间,星云稀薄,气团蜂拥,
真正的灵验也没能给他带来更多宽慰。
一路上,他挑剔的指尖传递着新的信息,
从风暴中刨出的耳朵被这旋律所发现。
这些,是否都属于一种奠基性的工作,
让一架钢琴戛然而止。现在它腾空而上,
像巨幅披毡,静静地笼罩着教堂。
而那弹奏已经历一场快雪被凝固下来。
叙述
主人公想打开他那册手抄的书卷,
以为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机缘,
所以他为他安排了这次与访友的叙旧。
那是完全不同的一场对话。
他谦逊,但又不完全为了赞美。
大部分时间他仅在他的语调里存在。
你知道,这还不足以让他
从现有的素材找到继续的由头。
他需要完成一种更为有效的尝试,
好让他有所心得的风格得以确认。
只是,他是否需要这一气氛,
在新的场景中依然保持着意味,
他不能肯定,他也无所期许。
他们效仿着,又互相动摇,
已然成为这一秩序的某类模型。
窗外,月光像一匹白马在肆意奔驰,
而且还在不断提速,斗转星移。
他们在言不由衷中结束了。
似乎因为负疚,他许予他良愿——
可靠的叙述保存在不确定中;
若干年过去,你会发现它仍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