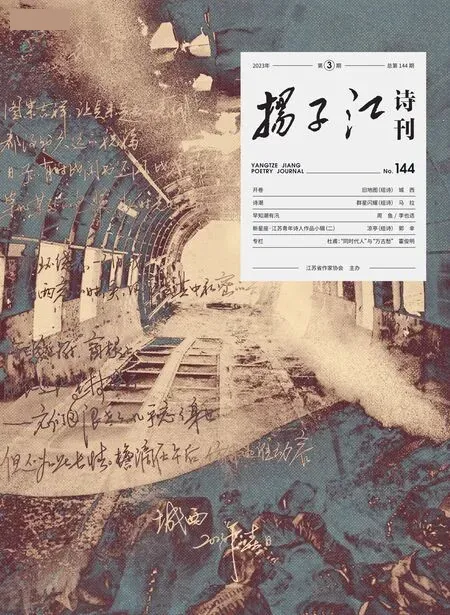群星闪耀(组诗)
马 拉
山林不远
玛丽亚·索去世了,享年101 岁。
中国最后一个女酋长,她生前常说:
我的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非常爱它们。
玛丽亚·索的女儿得克沙·何说:
母亲一辈子生活在山林里与驯鹿为伴,
带领着使鹿的鄂温克族从原始社会步入今天。
在一段采访视频中,玛丽亚·索
唱起了鄂温克歌谣《古佳耶》:
“可爱的孩子们从那么遥远的地方
来到敖鲁古雅,看望我这年迈多病的老人,
你们这些心地善良的人啊,
就像天上飞来的吉祥鸟。”
她也为未来担忧:一想到鄂温克人没有猎枪,
没有森林,没有收驯鹿的地方,
我就想哭,做梦都在哭。
钱不重要,大自然里什么都有。
大兴安岭深处的根河,我在秋天去过那里
白杨树身上涂了一层白粉,阳光
照在金黄的落叶上,草场上码满草垛
牛羊在山坡上云朵一样移动,缓慢悠闲
雪还没有落下,鄂温克的山林不远。
玛丽亚·索奶奶,生前我无缘看望你
死后,我们拥有同样荒芜的雪原。
那时空中飞来白鹤,它们对着河流祈祷:
愿我的族人打到更多的灰鼠,愿驯鹿
多生养,愿每一只驯鹿都转世为我的族人。
和鱼虫鸟兽谈论母亲
大多数鲨鱼一出母腹,
便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还有更多的鱼类,
尚未成为受精卵,
便开始独自生活;
它们终生在水中游动,
视水为真正的母亲。
唯有大地上生活的鸟兽,
噬咬双亲带血的慈悲,
偶尔是父亲。母亲更为常见。
它们终有离开的一天,
彼此不再相见,不再想念。
我,人类中的一员,
(万物之灵——我们如此幻想
是语言还是工具让我们自信?)
在母亲子宫着床那一刻起,
母亲便爱我,用羞涩的少妇之心
用中年的劳累愁苦,用
老迈的芥子般的祈求和热望;
我无法像鱼虫鸟兽一样离开,
母亲也不能,水和盐
都在我们体内,甚于血。
离别终将到来,母亲
你别难过;你让我哭着出生,
我用眼泪送你回去,这一生够了;
来生我有别的约定,幸亏遗忘
这浩瀚的大海收纳了一切,
你沉默不语,我也不发一声。
人类群星闪耀时
诗人和君主有过同样的梦想
他们找来最硬的石头刻字
到山巅之上淘洗灵魂
这无谓的,徒劳的蠢行。
有一天,语言点亮黑暗的尖刺
比黄金更持久的声名让人着迷
诗和律法写下,英雄的歌谣写下
语言迷舟从远古漂流至今,
船上历代的灵魂依然鲜活,再也不会死去。
谁发明了永生之书?文明中的无名氏。
在两只雄鸡和两个黎明之间,
人类中最伟大的那个人抽象出数字“2”
他没有留下阴影、手稿,甚至性别
创世的名声归于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
笛卡尔、牛顿也必须献上敬意。
这群谜一样的天才负责翻译大自然,
灵魂与道德的基本法同样出自他们之手;
语言尚无形体,巨石还未承载意义
盗火者听到呼喊,他还不是诗人。
人类有过爱智慧的黄金时代,
在古希腊,年轻的征服者亚历山大说:
我若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是第欧根尼。
疑问集
诗人热衷于谈论死亡
还有艺术家——形形色色的艺术家;
但必须将诗人和宗教人士单列,
他们,比别的人更愿意以身赴死。
死亡到底有何意义?人类如何感知?
没有答案,这是神秘的难题。
有没有鸟儿在飞行中坠落?那一瞬间
死亡是留在空中,还是和肉体一起着地?
死亡会是一颗止痛药吗?缓解诗人丰富的痛苦
有人说:意义才是归宿,哪怕它只是猜想;
正如东西方的神都不会死,有稳定的外貌和喜好
一样爱着受苦受难的凡人。我不反驳,
也不否认,我看到一个抱着孩子的农妇
她面容愁苦,上帝给了她和圣母相似的表情。
诗如何在
一首诗的意义在于如何说出。
在于呈现大海中为什么涨满蓝色的水,
在于讨论海鸟为何都是灰白色,
它们为什么没有热带雨林中鸟类的斑斓色彩。
我去过很多海边的小镇,渔民的汗水
有和海水相似的咸度,肤色却与海水迥异;
他们和我共享一个太阳,金黄色的光线,
潜伏的巨大鱼群,一粒粒游动的诗。
诗的意义在于,水中的盐,盐中的咸,
正如沙滩的意义在于接纳贝壳与石头的碎屑,
这是伟大的爱,它将死亡转化成诗意;
谁没有爱过海滩?孩子们热爱沙子,
这是人类的天性,诗歌中原始的部分。
没有人能命令鸟儿停止扇动翅膀,
没有人能阻止诗进入旷野中雪白的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