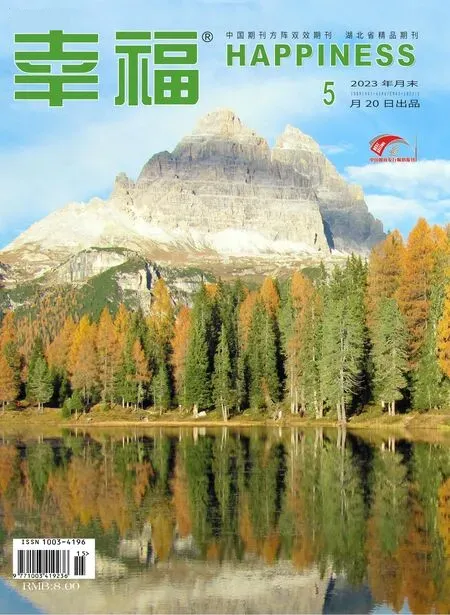以书佐酒
文/胡新波

下酒菜,莫过于花生米、茴香豆、萝卜干等口味咸重的小菜。在李白处则较为直接,《梁园吟》云:“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李白是直接将盐巴拿来下酒,虽令人瞠目结舌,也可见佐酒之物无论古今,都是偏咸偏重的可食之物。
四川的苏舜钦却不一样,他是以书佐酒。根据元人陆友的《研北杂志》记载:宋人苏舜钦特别喜欢饮酒。有段时间他住在岳父家,每天读书都要喝上一斗酒。他岳父让人过去观看,就听到苏舜钦在高声朗读《汉书·张子房传》,读到“良与客徂击秦皇帝,误中副车”,便感慨可惜,遂大饮一杯;待读到张良与汉帝君臣相对,更是抚案感慨“君臣相遇,其难如此”,便再饮一杯。苏子美的岳父听下人描述也是抚须大笑,感慨苏子美有这样的下酒物,喝一斗也确实不多。
以书下酒心先醉,拈笔评花字亦香。少年时代的苏舜钦饮酒充满了快意,读书有酒更助雅兴,书能读一担,酒能喝一斗。同时代的陆游也是苏舜钦的知己,陆游在《雁翅夹口小酌》中写道:“欢言酌清醥,侑以案上书。虽云泊江渚,何异归林庐。”读书是雅事,饮酒也不俗,人生两大乐事同时搭配,酒入肠胆,诗文入心,绵绵的酒意穿透肺腑,更是能激发一腔诗情,幽情与雅趣皆无穷也。
饮酒和读书,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的修心习惯,也可以说是精神寄托。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传》,写的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陶渊明想必也有不少时候在读书时饮酒,在饮酒时作诗。李白斗酒诗百篇,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王勃闲居饶酒赋……可见诗与酒在文人心中向来是不可分割的伴生物。
苏舜钦文思敏捷,中进士后担任蒙城知县,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他甫一上任,便大刀阔斧“窜一巨豪,杖杀一黠吏”。在其职场生涯中,也是数次上书言事,通过《上三司副使段公书》《上范公参政书并咨目七事》《乞纳谏书》《诣匦疏》这些文章,向朝廷针砭时弊,直言不讳地陈述彼时皇帝和朝廷的不足和问题,也凭此得到范仲淹的赏识并被委以重用。此时的他,官居高位,常有人宴请,青年苏舜钦的饮酒,多半是酒酣胸胆尚开张,豪情万丈,壮志在酬。
没多久,苏舜钦在“进奏院事件”被敌对的党派弹劾监主自盗,最终被革职成为庶民。遭遇职场滑铁卢的苏舜钦迁居苏州,建了一座沧浪亭表明心志,自诩为沧浪翁,闲暇之余更是痴迷饮酒。苏舜钦在《对酒》中写道:“丈夫少也不富贵,胡颜奔走乎尘世!予年已壮志未行,案上敦敦考文字。有时愁思不可掇,峥嵘腹中失和气。侍官得来太行颠,太行美酒清如天,长歌忽发泪迸落,一饮一斗心浩然。嗟乎吾道不如酒,平褫哀乐如摧朽。读书百车人不知,地下刘伶吾与归。”兴许是借酒消愁,酒后便可放浪形骸,忘却俗世的烦恼,达到一种更为超然忘我的境界,与青少年时的饮酒相比更添了三分惆怅、七分悲凉。
沧浪之水亦是尘世之水,清与浊,代表着这世间之酒的度数几何。书是文人的根骨,酒是文人的命运;书是文人的肉体,酒是文人的灵魂。不如归去,且与太白行吟,且去南山赏菊,且摘桃花卖酒。无酒不成文,一笑杯自空;提壶抚寒柯,快哉天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