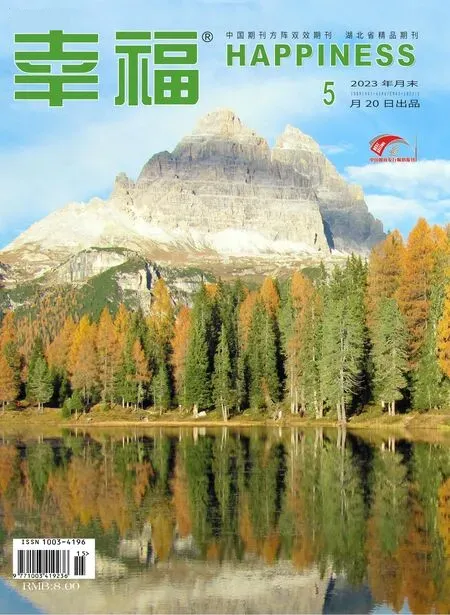雪夜和一首古诗
文/张爱国
落日圆硕,大漠铺金。稀疏的草依稀呈带状,灰白色的草叶如利剑,直指穹苍。大漠的秋天,辽远开阔。大雁还舍不得南去,优哉游哉地飞。见到地上的人马,它们放慢速度,降低高度,盘旋,欢叫。
“哦,大雁恋人呢!多少天看不到一个人,这是高兴,想亲近人。”卢纶勒住马,仰头向大雁挥手、呼叫。大雁似是明白人的意思,伸开长长的羽翅,缓缓落下。红日迫近地平线,大漠显得愈发雄壮。
明月升起时,卢纶看到了营帐。
“谁是李将军?”卢纶骑马径入大帐。帐内,几个兵士围坐在一盏昏黄的油灯前喝酒。
“这儿没将军!”一个黑瘦的说。几个人举碗一饮而尽,放下碗,几双筷子同时伸向他们面前唯一的碗,又同时缩回。卢纶看到,碗里只有几粒黄豆。
“在下卢纶,得大将军令,来此察看营寨。”卢纶跳下马,“谁是李辉?”
“大将军的人果然威风。”黑瘦的那位起身,斜着眼睛看卢纶,嘴角露出轻蔑之笑,“文人吧?我大唐军人的威风,你装不来!”
“你就是李辉?”
“说吧,大将军有何军令。”
“军令?就你们,有军令又如何?”卢纶看向另一侧横七竖八呼呼大睡的兵士。
一个兵士“噌”地跳起,被李辉重重按下。“给卢判官看茶。”李辉吩咐道。
一个兵士抓起地上的酒坛,倒出一碗酒,起身往卢纶手里一塞。
“我不喝酒。”卢纶摆手。那兵士将酒碗往地上一蹾,径自坐回。
“二清子,我大唐兵士不许无礼!”李辉弯腰端起酒碗,双手捧到卢纶面前,“卢判官,喝吧,解渴。”
卢纶接过酒碗,喝了一口——哪里是酒?是碜牙的水!凑到眼前一看,浑黄如泥浆。卢纶大惊,看看李辉,看看还在若无其事喝“酒”的兵士们,又看向躺在地上的兵士们——他们衣着单薄地躺在黄沙上,沙上连一根草也没有。
卢纶缓缓向李辉一叉手,深深一鞠躬:“李将军,我……”
李辉拉卢纶坐下:“卢判官,兄弟们已断粮三天。夜间气寒,卧睡的草也烧光了。”
“我在都护府里也听说李将军和兄弟们艰难,却不知如此。”
“卢判官,你从都护府来,你说,大都护是不是忘掉我们,再也不管我们了?”兵士们起身围上来,纷纷说,“皇上和朝廷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一阵风卷进来,卢纶不禁浑身一凛,扭头看去,营帐北角已被卷起。帐外,刚才还是月华如练照如白昼,现在却黑漆漆如坠无底的地狱。卢纶虽然在都护府待了半年,对北地的天气有所领教,但这势头还是让他感到惊惧。
“兄弟们,都护府里也不比你们好多少。”卢纶重重一叹,垂下头,“自天宝之乱以来,三十多年了,朝廷、皇上、我大唐,都不再是……”
“大唐真的不能雄起了?卢判官,听说朝廷要撤除北庭都护府,真的吗?”
“真的如何?假的又如何?我前几日还和大都护说,都护府一撤,这广袤的北地,从此就不再属于我大唐。北地虽大,哪一寸不是太宗以来我历代君王和千万子民流血丧命换来的?然这一路所见,尤其看到你们,我想,撤就撤吧,早些撤吧!”越发猛烈的风吹进帐内,卢纶紧了紧身上的衣服说,“毕竟,大唐已不是昔日的大唐。你们,也不是昔日的大唐之兵。”
“卢判官,你什么意思?”众人怒问。
“临行前,大都护再三叮嘱我,要你们务必小心。近年,北方之敌已然觉察出我大唐已非往日,蠢蠢欲动。可你们竟毫无戒备,使我能策马直入,若是敌人突袭……”
“判官大人不知,今日下午李将军就……”众兵正说着,李辉突然站起,倾耳听向帐外。众兵立马闭嘴,屏住呼吸。卢纶不知所以,也屏住呼吸。
“雁鸣?”一名兵士低声道。
“雁起!快!迎敌!”李辉话音刚落,身旁众兵和一直酣睡于黄沙上的兵士已一个个兵器在手。卢纶站起的同时,他们已集合于帐外,且全部端坐马上。
卢纶快步走出,漆黑死寂的世界里只有风声,还有高飞于头顶上的大雁的惊叫声。大雁有近人而宿的习性,这营帐四周都宿有大雁,大雁的警觉性又远高于人。“原来夜宿的大雁竟是他们的哨兵。”卢纶明白了。
“将军,敌人知道惊动了我们,已退回。追?”兵士问。
“追!”李辉令一出口,火把点起,照亮了一张张杀气腾腾的精瘦的脸。卢纶突然发现,他们的身上、手握的刀枪和弓箭上,已落了一层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