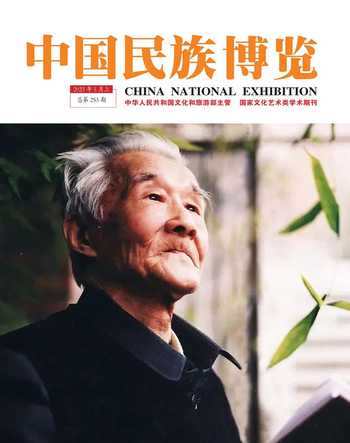柳公权“心正则笔正”说探微
李永祺
【摘 要】柳公权为中晚唐时期著名书法家,其书法骨力十足、雄健挺拔、静穆而朴厚、华贵而庄重。“心正则笔正”是他的代表书学思想,要求书家在书法作品的审美基础上起到“言志载道”的作用,以体现书家个人风采和魅力,以窥汉唐一脉磅礴恢宏的“正大气象”。
【关键词】柳公权;心正则笔正;正大书风
【中图分类号】G6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3)09—028—03
一、言志、载道:柳氏书学观的溯源
唐代颜真卿是继王羲之之后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在唐初尊王、崇王、学王的盛况下,以端庄遒劲、雄浑开张之风改变了魏晋二王一路“书贵瘦硬”的审美导向和书风格局。苏轼评价:“鲁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此处“新意”指的是颜书一扫清瘦秀美之风尚,以恢宏堂正的“正大气象”改变了一个时代的文艺风尚。柳公权作为晚唐的书法大家,其书法在习承了这种刚健昂扬、端庄朴厚、气势阔达的“正大气象”而略有改变,因而被后世称之为“柳体”。他的书学思想“心正则笔正”不仅是书法临习上的审美要求,还是对书家人品道德修养上的基本要求。
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记载:“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1]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立德立品是学书之关键。历朝历代虽不乏文人志士在文章武功、品德风尚、琴棋书画等方面有所能者,但立德立品更加让人仰慕倾佩,见其作,更欲想其人,更欲望其风采,遂人书千古不朽。
就现存可考资料来看,立德立品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扬雄的“心画”说。他在《法言·问神》中明确提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这里的“书”是对“言”进行系统的书写记录活动,也泛指一切书面记载,开启了后世“以书喻人”“书如其人”的理论源头。虽然书学立德立品的观念被扬雄的“心画”说正式提出,但是其思想的哲学根本与先秦诸子的“文艺观”密不可分。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明诗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强调诗既有教化作用,也为政治服务,书法文字亦是如此。《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说明诗的教化与人的道德修养息息相关,只有“正心诚意”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中言:“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可见正心的重要。孟子在孔子的思想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发展,提出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立图回归作者创作时候的原初状态,寻求当时的心境。至汉代《毛诗序》中“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将情志统一,把人的情绪、思想作为艺术创作时灵感来源的本质力量,可见作者“心正”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至汉代,经世致用的理念也对“心画”说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汉书·董仲舒传》:“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2]这与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观念不谋而合,前者直接点明为君者当心正以定天下,后者则借助书法要义暗传做人与为君之道。
降及唐时,虞世南在《笔髓论》中点出:“心为君,妙用无穷,故为君也。手为辅,承命竭股肱之用故也。”[3]他认为在书法创作中书家应当保持心平气和、绝虑凝神,以达到心手相应的状态,不然就会使字欹斜不正、志气不和,有失端稳,无法达到“无为”之妙、“冲和”之美。而虞世南身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最终官至青光禄大夫三品散官和弘文馆学士荣归致仕,其文其书影响深远。柳公权面对唐穆宗请教用笔问题指出“心正则笔正”或许受其影响。
二、久居侍书:柳书的“正气”来源
柳公权,字诚悬,公绰弟也。柳氏一族家学严谨,极重礼法。其兄柳公绰秉性中正,以孝闻名,对柳公权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影响。
柳公权弱冠之年擢进士及第,三朝侍书,久居侍书之位,其书法因骨力劲健、雄健挺拔,字与字之间蕴藏的“正大气象”备受时人所爱。《新唐书·柳公绰柳公权传》记:“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外夷入贡者,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4]《唐文拾遗》卷六一载佚名所作《上柳侍郎书》载:“艺奋神工,时推妙翰。凤弯异态,龙虎殊姿……。往者事相公尝谓侍郎能以书谏者,今则行执陶钧,坐登台辅,终提一笔,以绝百僚,后之来者,延颈而俟。”可见柳公权在当时书坛之地位,名响海外,甚至世卿贵族面对碑志刻石选择时,不求柳书就要背负不孝的骂名。
《新唐书》称柳公权“有锺、王、欧、虞、褚、陆诸家法,自为得意。”[5]史书记载柳公权书风受到锺、王、欧、虞、褚、陆诸体书法,未曾言明是否学习过颜真卿的书法。而“颜筋柳骨”一说开始于宋代苏轼“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成为定论已是范仲淹在《祭石学士文》中“曼卿之笔,颜筋柳骨。”其族兄柳宗元好友刘禹锡则认为柳公权之书出自柳氏家学,在《酬柳柳州家鸡之赠》写到:“柳家新样元和脚”即认为柳公权之书受柳宗元影响,且胜过宗元之书。而柳宗元年长柳公权五岁,在书法上凭借章草闻名于世,留有《永字八法颂》。赵璘《因话录》卷三《商部下》云:“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于章草,为时所珍。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长庆以来,柳尚书公权又以博闻强识,工书,不离近侍。柳氏言書者,近世有此二人。”[6]史料并无记载柳公权习于柳宗元,但其年龄相仿、且同宗同族、相隔不远,在早期习书经历上可能多少受到些许影响。
而柳公权的书法也受到中晚唐“官楷”的影响。唐常常组织大量门下省、弘文馆等官方书手或民间写手进行抄书,这些职业书家的作品被称为“官本”,作为全国标准当作范本分发各地,所用字样必然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和权威性。而书手面对同行竞争也必须不断提高自身水平,以保证自己的职位和待遇。凭借柳公权的身世,早期学书有可能接触到真正的宫廷写卷,即使拿不到第一手“官本”,也可以通过民间写卷学习书法。
致仕后,柳公权的侍书身份使他有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及一手资料对书法进行深入探究。而面对大量达官显贵的求书购字,必然要求每次创作保持高度的认真和负责,使得柳公权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水平。而作为弘文馆的一名职业书手,奉敕书写碑石具有极高的严肃性和纪律性,不仅要求文字规范无错,还要保证书体的端庄静穆,不可率性而为以落官方权威。故此,楷书成为柳公权花费大量时间反复揣摩、深入研究的书体首选。
而在书写作品时,柳公权对毛笔的使用提出了“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的要求,这也使得他的书风与其他写手并不相同。由于使用长峰书写,柳公权的用笔极为精致准确,其字体结构近乎完美,可以称得上无懈可击。在其《谢人惠笔帖》中写到:“近蒙寄笔,深荷远情……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管不在大,副切须齐,齐则波碟有凭,管小则运动省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润自由……”[7]可见柳公权在书写过程中通过不断探索寻得属于自己的书写方式和用笔方法。《历代名画记》中有云:“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8]元代盛熙明在《法书考》中指出:“书以骨气为体,以主其内,以肉色为用,以彰其外。气宜清,色宜温,骨宜丰,肉宜润,不失其所。”[9]这里的“骨气”是一种气韵,是书家字里行间对生命气息的捕捉和体现。而柳公权之书骨力十足、雄健挺拔,静穆而朴厚、华贵而庄重,瘦长而非羸弱,开张而非恣肆,亦如威武和平之师昂首挺胸、敦厚而又纯美。正是如此骨力让笔画之间源源不断的传递出“浩然正气”,这股“正气”与他的书学思想“心正则笔正”相互交融、相互依存,构成了超越书法之外“言志载道”的“正大”气象。
三、心正、笔正:后世书学地阐释与发扬
柳公权提出“心正则笔正”的名言,成为被后世传为“笔谏”的佳话。对于“心正则笔正”的书学思想,后世书家有着不同的阐释和发扬。在书法创作上,清人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云:“古人谓心正则气定,气定则腕活,腕活则笔端,笔端则墨注,墨注则神凝,神凝则象兹。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此正是先天一著功夫,省却多少言思拟议,所谓一了百了。”[10]在书法内核上,出现了“人书同构”“以人喻书”“书如其人”的书学理念,点明了书家人格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要求书家注重个人修养和品德内涵。
苏轼在《东坡题跋》中提到:“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雎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11]苏轼认为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不只是劝谏君王,而是“理”当如此。这个“理”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一种崇高壮美的精神风貌,体现着儒家的谦雅、魏晋的飘逸、汉唐的雄风,无处不展现着磅礴恢宏的“正大气象”。如明代项穆《书法雅言》所说:“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闲圣道也。”[12]清人刘熙载《艺概》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13]书法作品不再单单是文本内容的传递,而是通过笔墨书写呈现“载道言志”和视觉审美两种体验。“载道言志”关乎书家的思想学识和道德修养,视觉审美则是由汉字本身决定的。早期汉字具有明显的象形性,随着书体向实用性发展,汉字结构由象形转为抽象,笔顺的产生赋予了书写独有的时间性。书法作品同时兼具造型性和时间性,使得观赏者能够通过对笔迹进行还原,再现书家书写时的原初状态。《颜氏家训》:“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历代书家其作品风格迥异,或流美、或遒劲、或雄强、或秀丽,尽管他们风格不同,但是“心正则笔正”的观念一直悬而未决,比如赵孟頫、董其昌、王铎等著名书家作品很难通过单一标准进行判定。王铎作为降臣入清为官,深受时人与后人非议,大多认为其气节不足、立场不坚,但观其书法大字连绵雄健,小字清新雅致。可见“心正则笔正”一说与现实生活并不完全相符,或许与书家通过笔墨抒发在作品中排解现实生活的苦闷之情,将内心情感寄托于艺术作品,宣泄现实世界无法满足和无法实现的内心需要息息相关。
由此,“心正则笔正”成为古代文人志士的一种理想化状态,书家希望将现实与理想、感性与理性进行和谐统一,完成“人书同构”的终极理想,实现作品中的“正大气象”。正如白宗华所言:“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14]然而“心正则笔正”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书写技巧上的问题,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魏晋时期“性轻躁,趋势利”的潘岳写出了清高出尘的《闲居赋》,在文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淡泊名利、忘怀凡俗、超脱世外之人。可见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书法作品,其艺术风貌并不能完全对应作者的才貌性格,道德伦理无法成为评判审美高低、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否则“以人论书”“以人废书”,就会导致书学思想和作品出现伦理化、简单化,从而忽略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
四、结语
“人书同构”的书学思想随社会历史变迁和文艺思潮的代兴而不断更迭,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理论特色和关注重点,柳公权“心正则笔正”是对“人书”关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奠定了重要作用。这与传统“文艺观”所倡导的“正大气象”相一致,强调文人注重自身人格修养,强调作品“言志载道”,为后世书法创作和书法内核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和指导。而“心正则笔正”所包含的“知人论世”的评判标准,赋予了书法活动上更加丰富多元的理论认识,但也应当注意“以人论书”将美学与道德混为一谈,是对书法艺术在审美发展上的一种弱化和制约。无可否认柳公权“心正则笔正”是一种积极昂扬的精神面貌,以开阔的胸襟、乐观的思绪和端庄华贵风采书写属于磅礴汉唐的“正大气象”。
参考文献:
[1][3][10][12]上海書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2](汉)班固.前汉书(卷五十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5](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一百六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8.
[6]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8.
[7]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七一三)[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8](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9](元)盛熙明.法书考[A].四部丛刊续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34.
[11](宋)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A].苏轼文集(卷六十九)[C].1956.
[13](清)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4]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