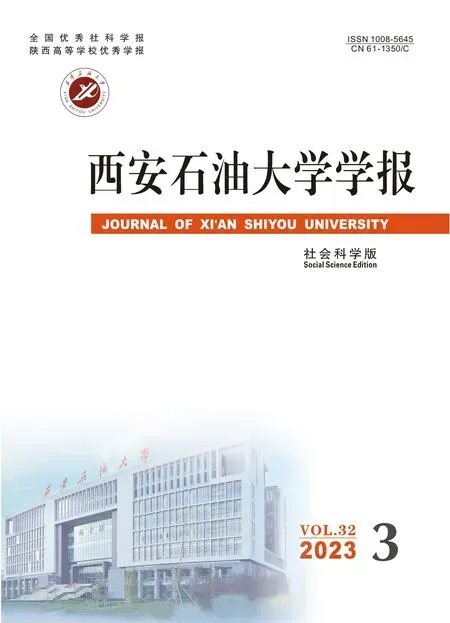论抗战散文对“十七年”散文的影响
郭大章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1 抗战散文概述
1.1 反映抗战的全面和真实
抗战散文是配合着抗战而产生的,遵循的是“一切为了抗战”这个原则,其反映抗战的深度、广度以及真实程度,已成为其优势和特色。抗战散文对抗战的反映是很全面的,几乎涵盖了该时期的大部分社会现实,可以说是对抗战的“全方位覆盖”:既有详细描写战争中残破的国土和荒芜的家园的,也有真切表现人民困苦不堪的生活和日军残酷暴行的;既有对中国军民抗战的直接展现,也有从侧面描绘抗战事迹的;既歌颂了抗战时期的各种英雄,也暴露了抗战时期真实存在着的各种黑暗;既展现了军人的风采,也刻画了民众的形象;既描写了中国的抗战,也涉及到“外国”的抗战;既突出了普通军民的英勇,也反映了贪官污吏的无耻,同时,还刻画了不少国际友人的形象,可谓包罗万象、兼收并蓄。
除了反映抗战的全面而外,抗战散文还披露了诸多历史细节,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同时还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我们可以从厂民的《重庆片段》和齐同的“山城小集”系列散文里,还原出战时陪都重庆的种种真实“现状”;可以从漆林的《谈贵阳》里,了解到战时贵阳的交通不便和文化禁锢等“战时历史”;可以从李育中的《四月的香港》里知晓战时香港的旧貌,从彭桂蕊的《绿云下的缅宁》里了解战时西南边境的概况……从抗战散文所展现出来的这些“史料”中,一个活生生的“战时中国”便呈现在读者面前,形象而生动,真实而详尽。
1.2 “政策”遮蔽了“文学”
“抗战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一切为抗战服务”成了人们必须遵循的原则,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学。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政府的贤明领袖们提出了新的口号:‘集中全民力量,争取胜利’”,而且,“我们中国文学既然是中国的文学,既然是中国现阶段的文学,他便要受中国的社会条件与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不能成为超社会、超历史的东西,这是显照的事。”[1]1578-1579
于是,在“政策”的干预下,我们的作家便无可避免地失去了创作的“自由”,其创作出来的作品便成了“政策”的“传声筒”,成了抗战的“宣传机”,“政策”完全遮蔽了“文学”,文学成了“抗战”的文学,成了“政策”的文学,文学变成了“战争”和“新闻”:为了更好地表现抗战时期的方方面面,很多文学作品往往以最“简单”的办法,直接去“描摹”事件,甚至不经过任何的文学“加工”,就把眼见耳闻的事件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没有一点儿曲折和手法,用干瘪的叙述、“简单粗暴”的语言来“记流水账”,以此作为“真实”的抗战的反映,更有甚者,甚至直接照搬照抄报纸上的新闻事件,以此来突出作品的“真实”和反映现实的“力度”。
如任钧的《“安哥拉”的点和线》里,为了讲述战时“壮丁”一事,作者在其中一节里用了这么一个开头:“下面是随手剪下的最近登载在此间各报的有关本省征调壮丁问题的电讯和通信……”[2]519-520然后便是摘录于各个报纸的新闻的摘抄,最后加上几句感叹便算完事,如果不是事先知晓这是任钧发表的散文作品,读者甚至会误以为是打开了某份抗战时期的旧“报纸”,在看其中的抗战旧“新闻”。
1.3 “公式主义”:“概念化”与“模式化”
抗战散文的特殊作用使其掉进了一个“政策”的“陷阱”,大部分作家都被这根“抗战”的“绳”极其严重地束缚着,于是,其散文作品便变成了“抗战”宣传的工具,显得“千篇一律”,本该丰富多彩的散文创作,却变成了“概念化”和“模式化”的代名词。所谓“公式主义”,老迟生曾这样解释:“‘公式主义’就是‘幼稚’的同义语,‘公式主义’的作品所能把握的只是最一般的最基本的东西,这种作品,只是一些简单的标记,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不甚近似的模糊轮廓而已,这样的作品摆在最丰富的现实面前,他是显得过于贫弱,过于幼稚了。显然地,这样的作品只能做普列哈诺夫氏‘符号论’的注脚,而谈不上什么能动的‘反映论’,如果想让他去完成反映现实,推动现实的任务,自是一个过于勇敢的企图。”[1]1577
首先,是人物形象的“概念化”与“脸谱化”。“描写义勇军,前线的英勇将士,一定把他写成高大的身材,坚强的体魄,严肃而沉毅的面孔。几乎个个都是中世纪的骑士英雄一样;描写敌人的个性,一定把他写成无理性的凶暴,脸肉横生,手上长了毛,用尽魔鬼野兽等字眼”[3]116,完全把人物的“典型化”变成了作者“理想”中的“概念化”与“脸谱化”。
其次,是散文内容的“模式化”。抗战散文绝大多数都有着相同或者相似的内容,要么就是描写战争对我们的家园造成的伤害,要么就是刻画敌人的凶暴残忍,要么就是赞扬中国军民在抗战中如何英勇杀敌等等,从而形成了极其严重的“模式化”。
再次,是抗战主题的“政策化”。由于战时的特殊政策,导致抗战散文都具备了抗战“武器”的作用,其主题也就具有了强烈的“政策色彩”。“不论作品底取材怎样不同,而它们底终极的意义却自然而然地会归结到一点——目前‘高于一切’的抗敌救亡”这个“总方向”上来。[4]39“不管任何一个典型,结局一定要归结到革命”,“‘最后胜利’便成为作品的一个必然的结局。不管作品里真实的本质方面应不应该如此。作者势非勉强虚构,有一条积极的尾巴不可。”[3]116-117
2 对“十七年”散文的影响
2.1 政治文化背景的“延续”
抗战散文对建国后“十七年”散文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政治文化背景的“延续”上。在抗战时期,文学肩负着“为抗战服务”的政治功用,因而,抗战时期的散文创作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政治有时甚至会凌驾于文学之上,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这一切都是由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造成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不仅开创了中国20世纪历史的新纪元,也标志着中国文学从此迈进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然而,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里,散文创作却并没有“新”起来,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承袭着抗战时期散文创作的老路,与政治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形成了建国后“十七年”散文创作的鲜明特征,即“一元化”散文创作。
新的国家制度和文学政策决定了新中国一元化时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框架,而“十七年”散文创作也必然会在这一框架和政策下进行。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确定了新中国文学发展的总方向和基本方针,那就是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在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新中国的文学始终是沿着这一方向前进的。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召开,会议的主题是繁荣创作,把创作的“任务明确化”,确定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要求是“塑造新的英雄人物形象”。与此同时,从1949到1966这17年间,新中国在文学、思想领域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讨论,出现了以政治干涉文学的“左”的倾向,这些讨论,最后都基本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批判运动,给“十七年”散文创作带来了十分深远而消极的影响,体现出了“十七年”散文中政治对文学的强势干预。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建国后“十七年”散文便呈现出一些固定的特征:始终与政治以及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紧密相连,突出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强烈的革命激情;内容比较集中,歌颂新中国、歌颂社会主义、歌颂英雄人物、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成为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主潮;“重大”题材成为散文创作的绝对中心和首要选择,等等。无疑,“十七年”散文的这些特征都与政治有关,可以说都是政治和文学调和的结果。
我们先以“十七年”散文中的几位代表作家及作品来看看“十七年”散文与政治的关系。在“十七年”散文中,最出名且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莫过于“当代散文三大家”了,而他们的散文作品都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杨朔的散文虽然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但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二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是赞美祖国锦绣河山和劳动人民美好心灵。毋庸置疑,杨朔散文的这三个方面显然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其散文“只着意对现实生活中的光明与美好事物的赞美,而忽视了对社会生活矛盾的思索”,刻意“为我们酿造出生活的诗意之‘蜜’”[5]91,其实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政治的某种“迎合”。
秦牧是一位涉猎广泛而且长于思考的散文家,“他的散文题材多样,知识丰富,有独创的见解,文采动人”,“极为重视作品的思想价值”,有着鲜明的主题:“为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摇旗呐喊,为荡涤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污秽而斗争”[6]5;有着鲜明的创作倾向:“鞭挞丑恶事物,用‘寒光的匕首’,颂赞美好事物,如‘余音袅袅的洞箫’。无论‘像是蜜蜂从花丛酿蜜’,还是‘像蜜蜂必要时奋力的一刺’,都表现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7];而且,秦牧认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对社会没有使命感,对人民没有责任感,是断然写不出优秀的作品,对他所处的时代,也是起不来什么积极作用的”[8],这些都说明了秦牧的散文有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与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刘白羽一直坚持着文学的革命功利观,把文学看作是直接参与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的一个有力武器,强调文学积极的社会效益。因此,刘白羽的散文有着“歌颂时代与鼓舞人心的基调”,形成了“投身时代洪流,适应现实斗争需要”的特征,不管是揭示生活底蕴和人生真谛的散文,还是描绘祖国大好河山和讴歌劳动人民的散文,都“具有比较宏阔的历史空间感”,“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接的构思框架上,以崇高美为支柱,用辉煌而粗犷的材料建构起他的散文形象系统”[5]96,“贯穿在他作品中的鲜明主题,充溢在他作品中的强烈的时代精神,燃烧在他作品中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激情,弥漫在他作品中的独具浪漫主义特征的历史画面和生活气息,都深受时代的推崇”[9]266,使得“浪漫主义气质和革命战争生活”成为了其“散文审美品格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5]93,其散文成了“诗意与政论的完美融合”,有着政治追求与思想追求和审美追求“同一”的特点。
很显然,由于受时代的局限,杨朔、秦牧、刘白羽三个人的散文“都是以‘政治第一’为标准”的,他们虽然“也倡导‘表现自我’”,但“这个‘自我’却浸透政治色彩”[10]151。而且,除“三大家”散文以外,“十七年”时期其他作家的散文创作也与政治联系紧密,“事实上,那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几乎所有散文家都是首先从政治和时代的要求出发,确定自己写什么、怎么写,表现出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作品力求有‘充实的政治内容’,主题思想是某一政治内容的结晶,而‘抒情’‘诗意’‘形象’等等,则都是表现这一政治内容的方式、手段,或‘载体’”[5]74,比如菡子,“我极盼自己的小说和散文中,在有充实的政治内容的同时,有比较浓郁的抒情的调子,并带有一点革命的哲理,追求诗意的境界”;比如李若冰,其散文“以反映大西北拓荒者和建设者生活为作品内容”,“永远是祖国大西北壮丽的风光和英雄的建设者们改造山河的壮举”;比如吴伯箫,他的散文作品多是对延安生活的追述和对社会主义新事物的热情讴歌,其“散文的主题永远都是‘继承革命传统,积极投入祖国建设’”[9]234-236等等。
因此,可以说,“十七年”散文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时代散文的总体特征,“十七年”散文“虽然题材、形式、手法各有不同”,但却“一直未能完全摆脱‘左’倾思潮的阴影”,一直“坚持文学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方向”,形成了“顺应时代精神,符合政治潮流”的主题[9]214-219,而且,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有时甚至出现了以政治代替文学,否认文学创作规律的“左”的倾向,“简单化的‘为政治服务’定型思维模式,代表着那个时代作家的共同审美理想”[10]151。这一切,都和“十七年”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关,可以说,“造成这种后果的因素是多元的,其中,政治因素无疑是重要的”,“散文在后来的发展中,愈来愈重视和强调散文的宣传功能及社会教化作用,散文流派纷纷消解,题材亦趋单一。一些散文作家亦受当时政治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纷纷放弃自我,或自我政治化,作品趋于大众化”[10]150。在这一点上,“十七年”散文和抗战时期的散文,无疑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都是“政治”干涉着“文化”,都是“政治”凌驾于“散文”之上,有着政治文化背景的某种“延续”,所不同的,只是政治文化背景的具体内容而已:“在时代生活背景上,英勇悲壮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翻天覆地的国内变化,具有着同四十年代战争生活颇为近似的氛围与节奏,激动着作家去‘为时代留影’,‘为英雄作传’。”[5]4
“十七年”散文中这种“与政治有关”的散文并不是某个作家的独创,而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而且,这种散文政治化的倾向远在抗战时期便产生并“繁荣”起来,只不过在“十七年”时期,散文政治化继续风行一时,并且“发扬光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十七年”时期散文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无疑有着抗战时期散文的某种潜在的影响。
2.2 概念化与公式化:某种散文写作范式的开启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得知,抗战散文创作其实是有着极其严重的概念化与公式化特征的,散文内容的“模式化”,塑造人物形象的“公式化”与“脸谱化”,以及散文主题的“政治化”等等,都是抗战散文概念化与公式化写作的某些固定套路,这些概念化与公式化的固定套路写作,其实无形中已经开启了某种散文写作的“范式”,并一直影响到了建国后“十七年”时期的散文创作,使得“十七年”时期的散文也呈现出极其严重的概念化与公式化写作特点,从而成了某种散文写作“范式”的延续。
2.2.1 散文内容过于集中的“模式化”
建国初期,中国人民亲眼目睹着祖国的日新月异,感受着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沉浸在一种亢奋的狂热中,社会的变革和建设的成就,促使人们对新生的社会充满激情和信心”,因此,在这种氛围的感召下,作家们必定会歌颂美好的新生活,“用文学唤醒人们对新生活向往的激情”[6]5,于是,“十七年”散文的内容便主要围绕着歌颂祖国建设、赞美祖国风光、歌颂各类英雄人物展开,很快形成了内容过于集中的“模式化”的颂歌型散文主潮。比如,杨朔在《茶花赋》里以童子面茶花象征祖国欣欣向荣的面貌,在《荔枝蜜》里以赞美小蜜蜂来歌颂普通劳动者的无私奉献精神;刘白羽在《灯火》里借“灯火”抒发新生活是从那“暴风雨历史深处”发展而来的深刻思索,在《长江三日》里借长江夜航表达其“激流勇进”的勇气;吴伯箫在《记一辆纺车》里借“一辆纺车”歌颂艰苦奋斗的传统精神;袁鹰在《青山翠竹》里将革命的井冈山精神赋予那“青山翠竹”,等等。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这些散文在风格上各有不同,但在思维模式和表现内容上却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功利和对建设“大事”的关照,这样,便形成了“十七年”散文忽视作家个体的思想与感受,而热衷于豪言壮语式的歌颂赞美的特点,使得此时期的作品基本都局限于一种“统一”的思想模式,削弱了散文内容应当具备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变成了过于集中的“模式化”。这和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散文有着某种无法回避的联系,抗战散文强调散文的教育功能和战斗作用,强调对“身外大事”的关照,具有光明乐观的颂歌基调,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刚健的战斗风格等等,这些都和“十七年”散文的“模式化”有着相通的地方,可谓是“十七年”散文“模式化”的某种“起点”。
2.2.2 塑造人物形象的“公式化”与“脸谱化”
抗战散文由于其特殊的历史作用,其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都有着“公式化”和“脸谱化”的特点,于是,散文中的人物形象成了某种特定的类型,而且这些形象大都具有共同的“形象特征”。
而“十七年”时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建国初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人民当了家作了主,散文创作的重心便自然放到了对大的历史进程的表现,以及对革命和建设中的英雄人物的赞颂上来,“这些英雄人物是时代的象征,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他们不仅成为那个时代的榜样,直至现在,他们依然激励着年轻的一代”,但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和狂热的感情”,“十七年”散文对这些英雄人物的描写却过于理想化,“他们是以‘完人’的形象出现的”,另一方面,为了衬托这些英雄人物,又把反面人物刻画得一无是处,形成了“把英雄人物当‘神’供奉,把反面人物视‘鬼’鞭挞”的特殊现象。散文中的人物形象完全“模式化”和“简单化”,“各种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状况,都视他的阶级状况而定,他的形象都是事先框定好的,只要对号入座就行了,几乎千人一面”,英雄人物形象就是“高大全”,就是“完美”,使得“散文整体创作模式化,个人风格单一化”[9]256-257,而其中的人物形象也成了“公式化”与“脸谱化”,没有了任何本应属于人物形象自身该有的“特点”。
对第①层级案例的资料收集整理可见,乡村民宿建造呈现3种模式:对老民居进行改造(暮云四合院、慢屋·揽清等),偏重参考当地民居进行解构抽象后新建(即下山),又或者偏重结合对场地条件的认知来进行新建(40英尺)。以上可看出乡村民宿的设计现有代码2)包含了当地传统民居的本体与其抽象内涵、场所条件。从符号学角度来说,人们对传统民居的印象已经形成一种现有意识,是隐含于人们大脑中的惯用语体系,是一种既有信息的来源。此外,地块的现状条件(包括地形、气候、文化等)作为一种长久渗透生活的要素,也是乡村民宿表义设计中必不可少的历时性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七年”散文和抗战散文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其实是有着某些方面的“一脉相承”,在“十七年”散文身上有着抗战散文的某些影子,是抗战散文的“延续”。
2.2.3 散文创作技巧的“公式化”和“模式化”
抗战散文中,由于各种无法回避的历史原因,散文创作技巧比较单一,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公式化”,给读者一种“千篇即一篇”的感觉。在这一点上,“十七年”散文也有类似的表现,仔细阅读“十七年”时期的散文,我们就会发现,“十七年”散文的创作技巧其实是有“模式”可循的:首先,“在开头上,或‘开门见山’,或‘设悬念’”,以便引人入胜,比如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和《菜园小记》、郭沫若的《访沈园》、冰心的《一只木屐》、峻青的《秋色赋》、韩少华的《序曲》等等,其开头都属于“开门见山”式的写法,简洁而精彩,读着读着才会渐入佳境;其次,“中间的行文精心布局,力求波澜起伏,开阖顿挫,严谨中求自由,统一中有变化,大有苏州古典园林的‘曲径通幽’之趣”,比如杨朔的“绕弯子”,造成“峰回路转”和“柳暗花明”的变化,刘白羽的“今昔交织和顺逆转换”,秦牧的“‘滚雪球’式结构”等等;再次,“那一时期散文的结尾,大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与开头照应,二是‘卒章显志’”,比如杨朔的散文结尾大都会有一段直抒胸臆的“升华主题”的文字,等等。于是,我们看到,那一时期的散文在结构上就形成了“开卷之初必设‘悬念’,中间铺陈故作曲折,结尾之际必现身说法,加以‘显志’的尾巴”的所谓“三大块”结构模式,你行我效,遂成俗套,“使本来应该自由灵活、丰富多姿的散文结构陷于僵化与雷同”[5]77-82。
因此,在散文创作技巧的“公式化”和“模式化”方面,“十七年”散文也未曾摆脱抗战散文的影响,有着“千篇一律”的特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抗战散文的“翻版”而已。
2.3 批判现实:“暴露讽刺”型散文与“干预”型散文
“暴露讽刺”型散文在抗战散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极大的篇幅,无疑是抗战散文的重要代表,体现了某种创作方向,而在“十七年”散文中,也有一种“干预”型散文,是“十七年”散文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显示出鲜明的特色。
“‘三家村’基本上是一个学者型的杂文家集体”,他们的杂文“涉题广泛”,并且“自成一个较完整的体系”,其重要功绩,“是将鲁迅那类偏重考据的杂文延展扩大,创造出针对面更宽的新时代知识性杂文”,“其主要特征是知识材料的高度密集和尔雅谨严的书卷气息”,“在广泛介绍文化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的同时,对现实中的某些消极面、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堪称新中国一元化时代杂文的典范”,“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许多文章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9]251。自然,这类针砭时弊的杂文因为有违当时的政治潮流,注定要面临被封杀的命运,1966年,“三家村”杂文及其作者以“反革命”的罪名遭到彻底批判,“十七年”时期的“干预”型散文便从此沉默,直到新时期文学的到来。
除“三家村”杂文以外,“十七年”时期还有黄裳、唐弢、马铁丁等人的杂文,它们都是“十七年”时期“干预”型散文的代表,在批判现实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比如黄裳,“他认为建国以后出现了‘杂文的沉默’,有必要通过‘杂文复兴’,运用杂文的‘热情的讥讽’,来‘纠正过失’,改善工作现状,‘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比如马铁丁的杂文,“在实际创作中,把彻底的批判精神、辛辣的嘲讽和抨击,用于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对某些社会现象及弊端”进行揭露和批评,“目的是治病救人,使革命事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9]248-249,等等。
批评现实的“干预”型散文,和居于主流地位的歌颂型散文一起,共同构成了建国后“十七年”散文中不和谐的“二重交响”,这类散文虽然不合时宜,有违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气,但以非凡的清醒和睿智为人民立言,干预现实的阴暗面,扮演了勇敢的探求者的角色,传达了别样的思考和见解,显示了另类的思想和主题,带有鲁迅文风的面貌。在这一点上,“十七年”时期“干预”现实的散文,和抗战时期散文中的“暴露讽刺”型散文的作用几乎如出一辙,可算是“暴露讽刺”型散文的某种“继承”和“延续”。
我们知道,自抗战时期《文艺阵地》首倡“暴露讽刺”文学并以其创作实践来践行“暴露讽刺”理论以来,“暴露讽刺”文学便开始在中国文学中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抗战散文对于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具体到散文领域,抗战散文中的“暴露讽刺”散文也无疑影响到了后来的“暴露讽刺”散文,而“十七年”散文中的“干预”型散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暴露讽刺”散文中的一种,因此,我们说,在散文批判现实这一方面,“十七年”散文中的“干预”型散文,必然存在着抗战散文中的“暴露讽刺”散文或多或少的影响。
2.4 散文创作队伍:作家成分的“同一”构成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散文作家的队伍,其实基本上是从“国统区”左翼文学运动中成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受文化宣传工作的锻炼而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和记者,他们是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崛起和壮大起来的,“在作家成分的构成上,经过革命战争的锻炼,善写战地通讯报告的能手如魏巍、刘白羽、杨朔、华山诸人,分明都是建国初期我国散文、报告文学创作队伍的中坚力量”,因此,“他们的作品势必导引和影响着当时创作的整体风貌”[5]4,而且,像“十七年”时期的刘白羽、唐弢等散文作家,其本身就是抗战散文创作中的重要力量,而他们在建国后“十七年”时期继续散文创作在精神上还带有战时文化心理的某种“延续”。同时,一个成熟的散文家的创作风格,在短期内也很难发生改变,这些因素也必然会导致“十七年”时期的散文创作带有抗战散文的某些影子。
与此同时,“十七年”时期仍然是一个生活巨变的时代,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建设,都标志着“十七年”时期的“不平凡”,因此,社会生活形态以及人们的心理状态便有着同抗战时期极其相近的紧张而热烈的节奏与气氛。现实生活一方面使散文家无暇去做冷静的思考,另一方面又为其准备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散文家们似乎只需要做一个“现实生活的实录者”就能够创作出不错的作品,“于是我们看到:那些从战火中走过的散文作家,此时的写作可谓是就熟驾轻;而对于那些来自国统区的作家来说,这种‘实录体’式的散文样式,无疑也是歌颂新生活、描述新时代的最便捷的形式”,“回顾这一时期的散文,基本上还保持着‘通讯’‘报告’‘特写’的格局,纪实性散文多,狭义的抒情散文,或曰‘美文’的少”[5]8-9,这自然不是某个散文家的独创,而是那个时代的特有产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散文通讯化的倾向,远在抗战时便产生了”,只是在建国初的“十七年”时期,“散文通讯化继续风行一时”[10]151,这不能不说有着作家成分“同一”构成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说,抗战散文对“十七年”散文的影响还表现在散文创作队伍的稳定和延续,抑或是作家成分的“同一”构成上。
3 结 语
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从“五四”至今,有其自身的流变过程,而抗战散文和“十七年”散文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的发展历程中,也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研究抗战散文对建国后“十七年”散文的影响,能够将其作为一个反观现当代散文的参照物,探究“五四”散文在走向“十七年”散文的过程中,是如何在不断承继传统的同时,又不断产生裂隙和变化的,唯有明晰这继承和变化,才能打通现代散文研究和当代散文研究间的空白,对现当代散文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抗战散文是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年”散文亦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们也是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抗战散文对“十七年”散文的影响为突破点,去观照建国前散文发展中经常被忽视的抗战部分,观照现代散文后期整体的文化格局及其走向,厘清抗战散文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史上的独特作用及重要贡献,以及“十七年”散文对现代散文的某种承袭,无疑是补充中国现、当代散文史部分材料及内容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