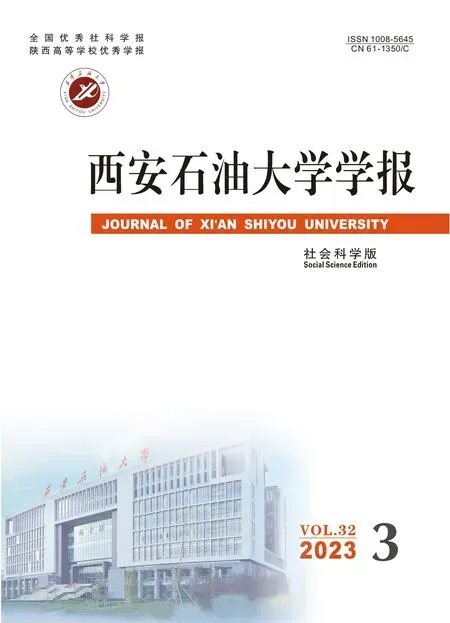由象至道:张载“大心体物”的展开及其境界
王 龙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34)
0 引 言
张载是关学的创始人,也是北宋时期儒学转向的中坚力量,其思想结晶体现在晚年的扛鼎之作《正蒙》一书中。此书字字珠玑,精石精诚,为后世历代学者所称道,王船山、王植、李光地等纷纷为其做注,足见其影响之深远,已成为今人研究张载思想的重要文献。在其第七篇《大心》中,张载开篇便申明宗义提出“大其心”的观点:“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见闻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1]17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张载于此提出了体物的话题,并且指出体物的关键在于“大其心”。张载的“大心体物”之论明显受到了孟子思想的影响。但今人研究此篇大旨时多从“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的知识论以及“存心尽性”的心性修养论出发,注重对既存结果的阐释,而缺少对大心体物实现过程的分析。鉴于此,本文所要做的就是尝试解决这一问题,并申论其所至境界。
1 立乎其大与尽心知性:“大心体物”说的思想渊源
何谓“大其心”?关键在于对“大”这一语辞的理解。张载在解释孟子“美”“大”“圣”“神”含义之时,把“塞乎天地之谓大”当作对“大”的注解,“塞”在这里为充满之义,即是说充满天地的状态称为“大”。按照古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大其心”中的“大”应作动词理解,依此则“大其心”可理解为充满天地其心。但客观地将心充满天地绝无可能也不现实,所以只能反溯到人自身,从人的主观体验出发,令“我”的“心”充满天地,与天地及天地间的万物融合为一。“大其心”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这近似于一种自我体认的情感体验。至于孟学渊源,比对新编校的《张子全书》可以发现,“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整段是对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2]327一句的注解,被收录在新辑佚的《孟子说》中,即它同时存在于《孟子说》和《正蒙·大心》篇中,这是最直接的文本印证。
除此之外,“大心体物”说在思想上与孟子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在《孟子·告子上》中记载有公都子与孟子的一段对话:“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2]313孟子在这里提出了“耳目之官”和“心之官”的概念,“耳目之官”不具备思的功能,会被物所蒙蔽,本质上仍是一物,在与外物接触的时候就会为外物所囿而被牵引;“心之官”则不然,它具备思的功能,这种功能是禀天所得的且为人生来所有,人具有此功能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抉择性,孟子主张“先立乎其大者”所意指即在于此。事实上,张载所说的“见闻之知”即指通过耳目之官获得的认识,而其“德性所知”则是指通过心之官所获得的认识,所以张载有言:“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1]17同时张载讲“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也与孟子的“此天之所与我者”有异曲同工之处。牟宗三先生亦曾指出张载的“大心”说受到了孟子“先立乎其大者”思想的影响:“此言大小显本孟子大体小体之分而来。”[3]457综上所述可以得知,张载的“大心体物”说是对孟子“尽心知性”和“立乎其大”观点的统贯与融合,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体物的论说。
2 “大心体物”的展开:条件、局限及其实现路径
体物要有体物的主体,即何者体物,这个体物者可以看作能动的主体“我”。这样一来就形成“我”通过“大其心”来“体天下之物”的模式,但何以能够体物、体物会遇到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下文所涉及的主要内容。体物要有体物的主体“我”和对象“物”,在张载这里“物”即包罗万千的“象”,而“我”则包含心和身之耳目两层含义。相应地,张载的体物也有两层内涵:一是作为身之器官的耳目与“象”接触,形成对“象”的客观认识,这是认知知识的扩充,即张载的“见闻之知”。二是从由性派生出的“心”出发,能动的体认“我”与“象”之间一体共融的关系,形成一种感性的直觉。对于前者容易理解,即指张载所说的“人谓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1]18对于后者则需说明“心”何以能够如此?这要从“心”与“象”的内涵出发来理解。在张载这里,“象”不仅指存在于天地之间有形有相的万事万物,还包括絪緼化生中动态的气象。张载讲:“气本之虚,则湛本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1]3(《正蒙·太和》)“利者为神,滞者为物。是故风雷有象,不速于心。”[1]16(《正蒙·诚明》)“气之苍苍,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1]263(《张子语录·语录中》)从日月星辰的显著之象到无形有象的风雷,可以预见由无形的湛虚之气产生的正在生成有形有相事物的动态气象的存在,所以在发源的意义上“心”与“象”是同源的、共生的、同质的,都是由气之感通而产生,两者是一体的,正因为如此就为“心”能够体“象”提供了潜在的可行性。而从“心”的方面来说,张载讲:“性,源也;心,派也。”[1]447又讲“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1]3王船山在注解此句时言:“秉太虚和气健顺相涵之实,而合五行之秀以成乎人之秉彝,此人之所以有性也。原于天而顺乎道,凝于形气,而五常百行之理无不可知,无不可能,于此言之则谓之性。人之有性,函之于心而感物以通,象著而数陈,名立而义起,习其故而心喻之,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故由性生知,以知知性,交涵于聚而有间之中,统于一心,由此言之则谓之心。”[4]33三者统观而言可以看出,张载的“心”是从属于“性”的,“性”作用于“心”,通过“心”感通外物,同时反过来“心”也有涵养“性”的功能,于此才有尽心知性之说。而“性”又是原于万物始源之天且顺应气化之道的,这就赋予“心”一种先天的感知能力,因此“心”才可以能动地体认天下万物及其与“我”之关系。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以“心”体天下之物的过程中,不可忽视“身”也即耳目的作用。张载讲:“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谓因身发智,贪天功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异相形,万变相感,耳目内外之合,贪天功而自谓己知尔。”[1]18又讲“耳目虽为性累,然合内外之德,知其为启之之要也。”[1]18可见在张载看来,人的身体器官及其功能,是天神秀造化的结果,因此人作为万物之一员,与天下之物是虽万殊而相互感通的,耳目在人与万物的感通之间起到了媒介或者说触发、引导作用。虽然如此,但普通人自身确不自知,这是视天功为己力的表现。总的来说,张载的体物既包括由耳目器官得来的见闻知识的扩充,也包括在此基础上人心对物我关系的体认思考,两者之间不是割裂的,前者对后者有触发、引导作用。
至此,张载“大心体物”说的主客观因素都已具备,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依此体天下之物,原因在于:一是物的无限性。“今盈天地之间者皆物也。如只据己之闻见,所接几何?安能尽天下之物?”[1]270天地之间尽是物,个人的见闻之知不足以覆盖天下之物。二是耳目能力的有限性。“天之明莫大于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几万里之高也;天之声莫大于雷霆,故有耳属之,莫知其几万里之远也;天之不御莫大于太虚,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极也。人病其以耳目见闻累其心而不务尽其心,故思尽其心者,必知心所从来而后能。”[1]18日之明亮与雷霆之声以耳目的感觉能力可以认识到,但日与雷霆的高远则非耳目能力之所及,这体现了耳目作为知觉器官的有限性。对此应当采取“尽其心”的方式,也即张载所说的“大其心”,即针对物的无限性与耳目器官自身的缺陷等客观因素,考虑从“心”的主观因素角度来解决,这也是张载大心体物说的应有之义。但从这一角度来体物仍存在问题,即张载指出的“大其心”要克服“成心”或者“私意”问题,解决办法是“时中”和“化”。“无成心者,时中而已矣。”[1]18“化则无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谓欤!”[1]18可以看出“化”是消除“成心”的实践路径,“时中”是无“成心”时的一种状态,通过“化”的方式消除“成心”可以达到“时中”的状态,那么反过来能够做到保持“时中”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无成心”了。然则“时中”是一种什么状态,“化”又是一种什么方式呢?
《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20又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2]21它追求的是一种中和的状态,张载的“时中”概念即脱胎于此。张载在《经学理窟》中提及“时中”概念道:“时措之宜便是礼,礼即时措时中见之事业者。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但非时中者皆是也。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又不可一概言。如孔子丧出母,子思守礼为非也;又如制礼以小功不税,使曾子制礼,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时中之义甚大,须是精义入神以致用,观其会通以行典礼,此则真义理也。行其典礼而不达会通,则有非时中者矣。”[1]73这段话在首句中揭示了“时中”的合宜特点,而在末句中揭示了“时中”的会通特点。因此张载的“时中”具有合宜和会通两重含义,可以说“时中”的状态是一种在灵活变通的机制中追求合宜的状态。接着就其“化”而言,“化”在张载的哲学体系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它包括天之“化”和人之“化”两个向度,这里是就人之“化”的方面来说的。张载在《神化》篇中讲:“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其在人也,知义用利,则神化之事备矣。德盛者穷神则知不足道,知化则义不足云。天之化也运诸气,人之化也顺夫时;非气非时,则化之名何有?化之实何施?”[1]9“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长,顺焉可也。存虚明,久至德,顺变化,达时中,仁之至,义之尽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继其善,然后可以成之性矣。”[1]10-11从“人之化”的角度来说,依“推行有渐为化”一句可以看出“化”具有时间上的延展性,它强调一个长期性的过程。而从“人之化也顺夫时”“顺焉可也”两句可以看出“化”的另一个特点即是“顺应”,由此可以推断“化”是指能够长时间地保持顺应外物或者说随时应物,因时因事制宜,这样一来就是“时中”的状态了,所以才有下文“顺变化,达时中”一句,这也再次验证了上文提到的通过“化”的方式达到“时中”的状态这一观点。把“时中”和“化”结合起来看,张载的“无成心”可以理解为长期地处于灵活变通的机制中以合宜地随时应物,这样一种心境也是“大其心”所要追求的状态,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时中”和“化”是“大其心”可言说的理解路径。做到了这些,就可真正体天下之物,从而进入“道”的境界:“成心忘,然后可与进于道。”[1]18
3 “天道”境界:“大心体物”的终极指向
“境界”一词本义指疆界、边界,是一个地理概念,具有哲学意味的“境界”一词来自于佛教,意指佛徒修行所达到的境地,在此之前的中国文化中要想表达同类意涵是不谈“境界”这一语辞的,而是用“境”来指代,如庄子《逍遥游》“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中的“境”字即指于此,这里的“境”字还包含有道德和价值判断的意味。可以看出,在中国哲学中虽然对“境界”一词的使用较为晚起,随着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才使其得以可能,但是对“境界”一词所表达的哲理意涵共情的理解,却是早已有之。蒙培元亦曾指出:“中国哲学是境界论的。所谓境界,是指心灵超越所达到的一种境地,或者叫‘心境’”。同时又指出“ 境界是心灵存在的方式。境界的实现,既有认识问题,又有情感体验与修养实践的问题。”[5]75-76冯友兰则从“觉解”的角度出发阐释“境界”,其在《新原人》中说道:“人对宇宙人生底觉解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底意义,亦有不同。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底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6]526相较于蒙培元的人的主观实现,冯友兰则侧重于主客的互动去实现境界,但两者的核心旨意概为相同。以此来观照于“道”,可以说所谓“道”的境界,不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去定义“道”,由此达到这一标准,就是达到“道”的境界了,而是基于个人对宇宙人生的生命体验,进而形成对“道”的理解感悟,或是一直保持对“道”理解体悟的一种状态。然则何谓“道”,抑或何谓张载所论之“道”?
诚然,“道”是中国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陈立胜认为道在儒道二家均是创造性本身,其本质就是创造、生成与变化。道之为创造性在根本上是一“变易”、一“过程”而非存有、实体,同时这种道之“变易”“过程”并不是盲目的、无序的,这个变动不居的生成过程正是宇宙生命生生不息的过程,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过程。[7]9-10显然这只说出了“道”的一个侧面,对于“道”的内涵,冯友兰有更具体的阐述。冯友兰在《新理学》中把“道”的含义归之为六:一是道即是路,引申为人在道德方面所应行之路,即伦理道德规范。二是道即普遍真理或最高真理、真理全体。如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三是道即道家所谓道,靠其自身能生万物,自身无性能使物有性。四是道即动底宇宙,与上文陈立胜所立意处相同。五是道即无极而太极之“而”,意为“大用流行”、大化流行。这里冯友兰把“无极”看作真元之气,把“太极”看作“理”,“无极而太极”意谓气大化流行于理中,才有此说。这类似于朱子所谓理气相依,理乘气动。六是道即天道,指宇宙间一切事物所依照之理。[6]70两者统合观之,对下文我们理解张载所论之“道”大有裨益。“道”是张载著作中常见语辞之一,在《张子全书》中俯拾皆是,鉴于文本的相关度,兹取《正蒙》中要者列举几条以供申述之用:
1、“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简者坤乎!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不如野马、絪缊,不足谓之太和。语道者知此,谓之知道;学易者见此,谓之见易。”[1]1
2、“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1]3
3、“运于无形之谓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1]7
4、“惟神为能变化,以其一天下之动也。人能知变化之道,其必知神之为也。”[1]11
5、“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诚身,不过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诚之为贵。”[1]14
6、“尽其性能尽人物之性,至于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诸道,命诸天。我体物未尝遗,物体我知其不遗也。至于命,然后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1]15
7、“体物体身,道之本也,身而体道,其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于身,則藐乎其卑矣。能以天体身,則能体物也不疑。”[1]18
8、“以我视物则我大,以道体物我则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于道,大于我者容不免狂而已。”[1]18
9、“体不偏滞,乃可谓无方无体。偏滞于昼夜阴阳者物也,若道则兼体而无累也。以其兼体,故曰‘一阴一阳’,又曰‘阴阳不测’,又曰‘一阖一辟’,又曰‘通乎昼夜’。语其推行故曰‘道’,语其不测故曰‘神’,语其生生故曰‘易’,其实一物,指事而异名尔。”[1]57
上述9条所述角度不同,反映出张载所论之道的几个不同面向:第1条“太和所谓道”一句,旨在用“道”来指谓“太和”,而“太和”是气絪缊化生相荡不息的和谐状态,它向下散殊可象,向上清通无形,所以这里的“道”是指气絪缊化生相荡不息的太和状态,明白了这一点才可谓知“道”。第2、3、9条归为一类,此3条都涉及气化运行,内容上可视为对“道”的指名及其特性的规定。由“由气化,有道之名”可知这里把气的阴阳化生运动现象整体称为“道”,这类似于冯友兰的“动底宇宙”义。同时这种气化现象是无形的、不著痕迹的,是形而上的、兼体阴阳而无累的,这是对“道”的特性的描述。第4、5条归为一类,两者都是“之道”的句式结构,这里的“道”可理解为原因、原理、法则之义。无论“变化之道”抑或“长久不已之道”,都旨在表达变与化的原理、法则,以及天之所以长久不已的原因、道理,无特殊含义。第6、7、8条都是关于体物的话题,都涉及物我的关系问题,内容上具有相关性,所以其所谓之“道”应为同义,同时这也与本文的主题最为关切。这里的“道”应当指天道,即冯友兰所述第六义,宇宙间一切事物所依照之理。解题的切入点在第7条,“体物体身,道之本也”一句有两层意思:一是向外体认外物、向内体认自身要以“道”为本,依“道”而行。二是从体与用的角度出发,“物”与“身”都是用,而“道”是体,依此则此句意为“道”是“物”与“身”的体,这是“道”的根本属性。所以能够做到以身为物,“身”与“物”等均是“用”,应身接物均以“道”为体,依“道”而行而不累于物,则其“为人也大”。这即是第8条所说的“以道体物我”以及“君子之大”,可见这里的“道”已是一个悬置于上的绝对的本体。而从“以道体物我”和“以天体身”的比附出发,可知“道”与“天”是等同的,所以毋宁说这里的“道”是指“天道”,是物我所遵循依照之理。这也就解释了第6条中“性诸道,命诸天”一对子出现的原因:“性”与“命”共同加之于物我之一身,所以不会出现“道”与“天”两个至上的本体,“道”与“天”只能为一物,这即是“天道”。所以“性诸道,命诸天”这句话应当是互文的关系,意为性、命依之于天道。至此,可以得知张载之“道”指气絪缊化生相荡不息的太和状态,指气的阴阳化生运动现象整体,指原因、原理、法则之义,指天道,是物我所遵循依照之理4种含义。
然则当我们讨论“道”的境界,或是张载所说“进于道”时,我们所认知的“道”是一个给定的尺度或标准,这就存在“一”与上述的“多”之间的矛盾。但仔细考察张载之“道”的4种含义不难发现,气絪缊化生相荡不息的太和状态只是气阴阳化生现象整体的一种特殊情况,后者的外延要比前者大,因此第一义可归为第二义中。依照此例,则第二义、第三义的外延要比第四义天道小,也可以归入第四义天道之中,但要指出这里第二义和第三义是不交叉的并列关系。至此,张载之“道”可以归结为最本质的“天道”,张载之“道”的境界即是“天道”的境界,张载之“进于道”即是进于“天道”。所以丁为祥、吴震等人甚至把张载的学说归之为“天论”或“天道本体论”。但正如前文所言,“天道”的境界无法用清晰的标准去界定,同时当我们说某人达到了这一境界时,作为亲历者的某人是无法向外界言说的,即使他作了生动的类比,外界同样也无法感同身受。所以我们只能转换视角诉诸于每个个体的自我身心体验,这时所谓“天道”的境界,即是个体对“天道”的身心感悟,并时刻保持着对这种感悟的敏感。而在张载看来,这种境界就是内外合一、物我合一的状态,此即张载所言:“合内外,平物我,此见道之大端。”[1]81张载所谓“进于道”即进于此。事实上,真正能达到这种物我合一状态的唯有圣人,《大心》篇首章早有揭示:“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1]17,可见在张载这里“进于道”、成性与成圣三者通为一体,成性才能称为圣人,圣人才能把握天道。所以当我们说“进于道”的“天道”境界时,实际亦是进于圣人境界,而这一切都需要“大其心”的工夫来实现,这不失为对“大能成性之谓圣”意涵的完美诠释。
4 结 语
张载的大心体物之说除了通过作为身之器官的耳目与“象”接触,形成对“物”的客观认识,实现认知知识的扩充之外,还强调通过“时中”和“化”的方式从由性派生出的“心”出发,能动的体认“我”与“物”之间一体共融的关系,形成一种感性的直觉,最终实现对“天道”的身心感悟,达到一种内外合一、物我合一的“天道”境界,亦是圣人境界。正因为如此,张载转向了对佛教以天地日月为虚妄思想的批判。在张载的大心体物之说中,“象”是客观的存在物,它由太虚之气感通而聚生成,虽然出于“象”的无限性和耳目能力的有限性,不能穷尽,但可通过秉承于天道的“心”的感知能力去体认,因此张载所认知的宇宙是真实的。针对当时学绝道丧的历史现状,张载痛心疾首,因此其对佛教的反对与批判,态度是坚决的,措辞是严厉的,显示出强烈的“为往圣继绝学”的道统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