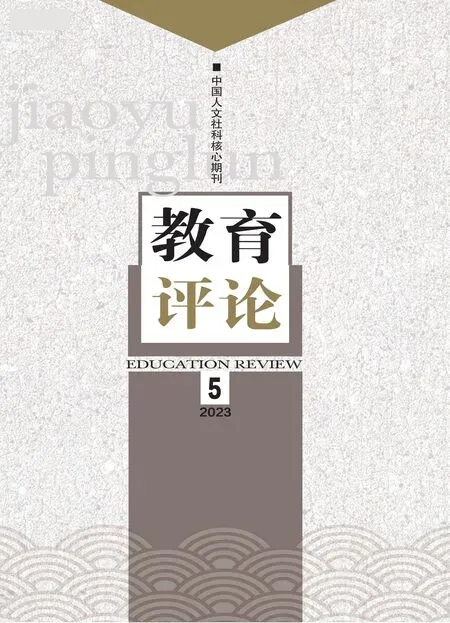陈鹤琴“五指活动”课程实验的历史考察与实践反思
●刘军豪
陈鹤琴是我国著名儿童教育家,我国现代幼教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其创建了“活教育”理论体系,具体包括三大目标、十七条教学原则、十三条训育原则、学习的四个步骤、五指活动等。[1]“五指活动”是“活教育”理论体系的内容构成,陈鹤琴曾在《怎样编排幼稚园的日课表》(1948)、《幼儿园的课程》(1951)中将“五指活动”定位于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原则,提出“幼稚园的课程全部包含在五指活动中”[2],并主张采用单元制教学法支撑幼儿园“五指活动”课程的具体实施。
“五指活动”是“活教育”课程组织形式的创新与发展,旨在摆脱传统课堂“学科教学”对儿童发展的束缚,开展“活动教学”,激发儿童热情与学习主体性、主动性。[3]鉴于“五指活动”提出时间稍晚,陈鹤琴对“五指活动”论述有限,且“五指活动”课程实验时断时续、经验总结不足等多种因素,关于“五指活动”的研究仍有待完善。本文聚焦“五指活动”课程实验的历史回顾与反思,探索将“五指活动”还原到“活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呈现“五指活动”在小学教育、师范教育、幼儿园教育等多个学段的课程实验,由此完善“五指活动”课程实验的历史研究。
一、“五指活动”的提出是“活教育”实践推进的阶段性产物
(一)陈鹤琴“活教育”口号的提出及早期实践困境
“活教育”口号的提出是陈鹤琴对中国传统旧教育批判反思、对欧美新教育理念吸收改造,顺应抗战现实需要,进行教育本土化实践探索的结果。1940年4月25日,陈鹤琴在江西遂川儿童教育座谈会上以“什么叫做‘活的教育’”为主题的演讲是“活教育”运动的先声,其首次明确提出“活教育”。[4]10月1日,陈鹤琴创办的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江西省立幼师”)开学,“活教育”实验开始。1941年1月,陈鹤琴主编的《活教育》月刊创刊,其在发刊词中提出要变腐朽僵化的传统死教育为生机勃勃的崭新活教育,“利用大自然、大社会做活教材”“在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要有活教师、活儿童”,初步奠定“活教育”的理论基础。[5]
“活教育”早期实践不仅面临经费短缺、物资匮乏的外部困难,而且面临经验有限、迷茫质疑的内部挑战。其一,由于幼师预算经费被严重缩减,加之抗战导致物资短缺,首批入校的幼师生承担了筑路、拓荒等创校任务,“活教育”早期实践集中体现于师生的集体劳动与生产生活。[6]其二,“活教育”虽已提出利用大自然与大社会作为“活教材”的课程论,但实际课程编制仍主要基于“部颁新课程标准”,呈现出改良主义倾向。“活教育”也面临质疑批判。面对将“活”等同于“浮、乱、散、私”的问题,雷震清确立了“活”的六大要件,以辨析其区别。[7]蒋村夫以“莫冤枉了活教育”为题,回应了“活教育是乱来的”“活教育是不根据课程标准的”“活教育老师是偷懒图闲的”等质疑。[8]“活教育”早期实践因尚未探索出一种真正能体现“活教育”精神的教育方案与路径,而致其囿于理念,难以落地。
(二)“五指活动”提供了“活教育”深入推进的课程路径
为推动“活教育”由理论走入实践,探索“活教育”的落地实施方案,1942年10月,陈鹤琴从“活教育”目的、实施对象、组织、课程、教师、设备等维度对“活教育”实施问题进行完整阐释,拟定“活教育实施方案”。然而,此时“活教育”课程编制仍延续“部颁新课程标准”的分科形式,只是更强调“活动”“工作”,并探索“单元教学”“活动中心”编制方式的融入与创新。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以下简称“幼师附小”)和江西省立南昌实验小学(以下简称“南昌实小”)开始承担实施“活教育”方案和实验计划,为“五指活动”的提出奠定实践基础。
“五指活动”首次提出于1944年2月的“活教育”实验推行筹划会议,会议聚焦“活教育”课程设置与教学实施问题,探讨以课程教学为路径推进“活教育”的深入实施,会议制订了“五指活动实施大纲”,出版了《活教育》的“五指活动特辑”,标志着“五指活动”的系统提出及实验开启。虽依旧以“部颁新课程标准”为参照对象,但“五指活动”打破了传统分科形式,将传统科目重新整合为健康、社会、科学、艺术和文学五项活动。“五指活动”是“活教育”实验过程中的一种课程创造,是“活教育”实践推进的阶段产物,同时使“活教育”理论有所依托和彰显,从课程维度提供了“活教育”深入推进的方案路径,纾解了“活教育”的早期实践困境。
(三)作为“活教育”内容构成的“五指活动”意蕴及内涵
“五指活动实施大纲”是“五指活动”课程的行动纲领,其明确了“五指活动”课程的目标是“建立中国儿童教育新方案”,强调“从儿童生活出发完成儿童的完整生活”。“五指活动”教学强调“采用集体教学,集体创作的方式,废除科目名称,按照各组活动的内容,将原有科目归并实施教学”[9]。健康、社会、科学、艺术、文学五项活动均制订了详细的活动实施大纲,完整诠释了“五指活动”落地实施的诸多细节问题。此外,大纲主要局限于小学阶段论述“五指活动”的实施,尚未明确“五指活动”是否适用于其他学段,且对“五指活动”之间内在关系的阐述有限。
陈鹤琴参与了“五指活动”概念的提出,主导了“五指活动”实验的推进,对“五指活动”内涵进行拓展与完善,并将“五指活动”明确为“活教育”理论体系的内容构成。陈鹤琴倡导以“五指活动”编排幼稚园课程,强调“五指活动在儿童生活中结成一个教育的网,有组织、有系统,合理地编织在儿童的生活上”[10]。陈鹤琴将幼儿园“五指活动”课程内容界定为儿童健康、儿童社会、儿童科学、儿童艺术与儿童语文五项。[11]其中前四项活动的内容与“五指活动实施大纲”近似,并结合幼儿园的教育教学实践具体划分为饮食、睡眠、朝夕会、周会、动物饲养、音乐、图画等,第五项活动则将名称由“文学”调整为“语文”,包括儿歌、故事、读法、谜语等。陈鹤琴将“五指活动”拓展到了幼儿园,论述了“五指活动”的内部关系及其与儿童生活的联系,立足于“五指活动”概念本体阐述其基本内涵。
二、“五指活动”实验是贯通多学段的“活教育”课程实验
(一)“五指活动”课程在小学阶段的初步探索与实验
“五指活动”课程最初以小学为实验场域,后逐渐拓展到幼师、幼专、幼儿园阶段,从而使“五指活动”课程呈现出多学段贯通的特点。“五指活动实施大纲”主要是针对小学,幼师附小主任杨士枬拟订了小学低、中、高三阶段的“五指活动”时间表,阐释了“五指活动”在小学阶段的课程实施。[12]虽已拟订“五指活动实施方案”,但由于日寇进犯江西,幼师附小被迫南迁,“五指活动”课程实验在迁校流亡途中间断开展,直到抗战胜利,才在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以下简称“上海幼师附小”)得以延续推进。
杨士枬认为“五指活动”是“一种整个的、统一的、生活的、实践的课程,采用的新教材必须要含有民族性、时代性、现实性、技术性的特点”,其同时提出了“五指活动”在小学阶段实施的基本主张,涉及课程选择、科目编排、教育过程、教学方法、活动场所等。[13]上海幼师附小也是“五指活动”课程实验的重要场所,其将“教室”改名“五指活动场所”,并开展了以“上海研究”大单元教学活动和“对日和约问题”时事座谈会为典型代表的课程实验,系统探索了“五指活动”在小学实施的路径。[14]“五指活动”课程在小学阶段的实验使“五指活动”得以丰富与完善,并为其他学段“五指活动”课程实验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五指活动”课程在幼师及幼专的逐步拓展与尝试
江西省立幼师也是“五指活动”课程实验的重要场所。“五指活动”课程在小学试行后,“已大加扩充,并且应用到师范学校和专科学校里”[15]。对于“五指活动”在幼师及幼专的实施,张文郁提出“在中等教育阶段,一般课程还是照旧,但把公民历史地理归并成‘社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归并成‘自然’,国文课程实行分组分类集体教学,英文采能力分组教学。在高等教育阶段,以幼师专科而论,在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间,把一般基本学程,归并成‘社会与人生’‘自然与人生’和‘文化与人生’三种,为替代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社会,经济……诸种学程”[16]。
1947年2月,陈鹤琴担任上海市立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女师”)校长,女师采用“以‘五指活动’为主的课程编制”,具体将女师课程划分健康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文学活动五类,以科学活动为例,其包含“自然与人生”和“心理与人生”两种,前者又涵盖生物、数学、理化、天文、地质科目,后者涵盖人生心理、儿童心理、学科心理科目。[17]女师以“五指活动”为主的课程编制是对江西省立幼师“五指活动”课程实验的传承与延续,其侧重点是在组织形式上对课程进行归并,用“活动”替代“学习”,将繁杂琐碎的分科科目统整于儿童生活需要,强化各科目间及科目与学习者的联系。陈鹤琴同时主持开展了幼专、幼师与附小协同实施的“上海研究”大单元教学活动,“‘上海研究’之配合五指运动,由社会活动开始,科学活动继之,其他总其成”[18]。“上海研究”大单元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多学段协同实施“五指活动”课程的范本。
(三)“五指活动”课程在幼儿园阶段的有效渗透与彰显
江西省立幼师在创校之初即建立了附属幼稚园,聘任钟昭华为主任,与江西省立幼师、幼师附小等共同承担“活教育”实验任务。“五指活动”课程同样在幼儿园进行了实验推广。陈鹤琴主张根据“五指活动”编排幼稚园日课表,强调“五指活动包含了各种课程,和儿童生活打成一片,也可以说是儿童的生活课程……用五指活动来昭示幼稚园课程的整个性和联贯性”[19]。鉴于学前教育的基础性地位与幼儿发展的整合性特点,“五指活动”课程事实上最适宜在幼儿园进行实验,历史证实“五指活动”最终在学前教育得以传承延续。张晗等提出“(五指活动课程)是幼儿园课程中国化、园本化、科学化的典型样态”[20],凸显了“五指活动”课程在幼儿园教育中的适宜性与必要性。
“五指活动”在幼儿园的落地实践依托于“单元课程”的创造与实施。唐淑认为“五指活动是单元课程在活教育思想中的新发展”[21]。陈鹤琴提出幼儿园在实践“五指活动”课程时,宜“采用单元制,各项活动都围绕着单元进行教学”[22],实验实践中,陈鹤琴将幼儿园繁杂多样的课程内容在单元主题的引领下,整合归并为“五指活动”,并以活动项目的方式来制订幼儿园的一日生活时间表。“五指活动”课程是陈鹤琴幼儿园课程思想的一种延续与创新,单元课程提供了“五指活动”课程在幼儿园落地实施的路径。“五指活动”在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附设幼稚园的实践同样“采取的是单元制的教学”。陈鹤琴虽肯定“五指活动”课程适宜于幼儿园教育,且明确以“单元课程”作为“五指活动”课程的组织形式,但“五指活动”课程在幼儿园中实验的史料相对比较有限,陈鹤琴对“五指活动”与“单元课程”关系的阐述仍显不足。
三、陈鹤琴“五指活动”课程实验的理性反思与现实启示
(一)“五指活动”课程是“活教育”的实践创新,指向儿童完整生活的完成
“五指活动”是“活教育”实践推进的阶段产物,是“活教育”理论体系的内容构成,也是“活教育”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路径创新。对“五指活动”课程的理解必须置于“活教育”理论发展的背景下。一方面,“五指活动”是“活教育”理论的承继与延续,彰显了“活教育”的目的论、课程论与方法论,体现了“活教育”的教学原则,推进了“活课程”“活教材”“活教法”的研究。另一方面,“五指活动”课程是“活教育”理论的实践与创新,从课程维度探讨了“活教育”的实施路径,克服了传统分科教学的弊端,强化了课程间的内在联系,凸显了课程与儿童生活的关系。
“五指活动”课程强调“从儿童生活出发完成儿童的完整生活”[23],彰显了“活教育”以儿童为中心的基本主张。“五指活动”课程编制中“以学科为标准的课目弱化了,而强调以儿童的某一活动为中心去组织相关的教学内容……突出了儿童在活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24]。对于“五指活动”课程内部的逻辑顺序,张文郁从作为个体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指出人一方面是生命体,而生命体以健康为首要前提;另一方面,人的生活离不开社会,社会是人存在的场域。此外,为更好地认识与理解自身与世界,科学的活动同样不可或缺。除了认知的需要,人还是情感的动物,人对于艺术和美的活动有内在渴望与需求。而“文学活动殿后,是含有一种整理和保藏的作用”[25]。张文郁从人的生活活动出发,以“儿童完整生活”为指向,探讨了“五指活动”课程的逻辑顺序,彰显出儿童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 “五指活动”课程本质上是以儿童的日常生活为中心进行组织编排的课程,是从儿童当下的现实生活出发,并指向儿童完整生活实现的课程。
(二)“五指活动”课程聚焦传统科目的整合归并,实验兼具革命性与妥协性
“五指活动”课程克服了传统科目细碎、割裂的弊端,强调儿童主体性与课程整合性,关注课程间的有机联系与相互渗透,实现了课程组织方式的根本变革。陈鹤琴认为,传统以课节制度为表征的班级教学课程“看起来头昏脑晕,非常繁杂琐碎而没有系统”[26],相互割裂的科目内容不仅脱离儿童生活,而且相互之间缺乏联系。“五指活动”强调以“儿童生活”审视反思传统课程,重新整合科目内容,使零碎的外在科目成为系统的儿童活动。为此,有学者提出“我们对于五指活动的了解,不能以一种改良主义的眼光去认识,而必须以一种富有革命性的情绪去了解,才会明白五指活动,它不仅是课程的改造,而且是制度的改造”[27]。“五指活动”课程实验具有革命性,这种革命性体现于其对传统课程组织方式的颠覆与创新,体现于从“科目课程”到“儿童活动”的转型与尝试。
“五指活动”虽在课程组织方式上进行了变革与创新,但在课程内容上仍以调整与修订为主,呈现出改良主义倾向。“五指活动”课程仍以“部颁新课程标准”为参照对象,并未完全打破以“科目”为形式的知识体系。“五指活动”课程是在传统科目基础之上的一种提炼与建构,而非对科目本身进行打破重构,并未实际触动科目的知识体系根基。同时,“五指活动”课程实施是以单元主题为路径载体,是陈鹤琴单元课程的延续与创新。单元课程与“五指活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课程模式,陈鹤琴并未对二者关系进行阐述,以致“五指活动”与单元课程的差异,尤其是相比单元课程的进步意义尚未完全彰显。“五指活动”课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折中妥协性。
(三)“五指活动”课程实验实施中面临争议与挑战,但依然被承继并延续
“五指活动”课程在实验实施中面临诸多理论争议与现实挑战。“五指活动”课程是否适合从幼儿园到幼专多个学段,“五指活动”课程实施如何有效彰显各学段特殊性及处理学段间衔接问题。“五指活动”虽事实上成为贯通多学段的课程实验,但其是否适宜于多学段,如何匹配各学段学习者身心发展特点等问题并未被有效论述。同时,“五指活动”课程实验时断时续,并未得到系统完整实施,相关实践经验也未得到有效提炼。其中,上海市立幼师及其附小、幼稚园的“五指活动”课程实验被认为是“硬套上去的”[28]“雷声大,雨点小”[29]。曾参与“活教育”筹划会议的陈锦枚提出,作为一种实际行动的“五指活动”至少将面临家庭、教师、教材三方面挑战。[30]
“五指活动”课程实验虽面临理论争议与实践挑战,但其本身所蕴含的革新取向和进步意义仍然在新时代得以承继与延续。一方面,以赵寄石为代表的学者面对幼儿园分科教学的弊端,充分汲取“五指活动”课程理念,开展“幼儿园综合主题课程”研究,以儿童活动为中心,建立学科间的有机联系,形成了幼儿园教育的整体结构。唐淑则认为渗透式领域课程的创造性建构同样汲取了陈鹤琴“五指活动”课程的理念精髓,延续了“五指活动”课程的组织原则,凸显了课程间的联系与渗透,强调课程与儿童生活的密切关联。以上彰显了“五指活动”课程在幼儿园课程中的传承与延续。另一方面,幼儿园“五大领域”的概念提出与实践推进也体现了对“五指活动”课程的继承。蔡军等指出:“《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是对五指活动的继承和发展,《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是对五指活动的发展和创新。五指活动理论通过《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彰显了新的时代价值。”[31]“五指活动”课程在当前依然具有参考意义和传承价值,对“五指活动”课程的研究应走向深入与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