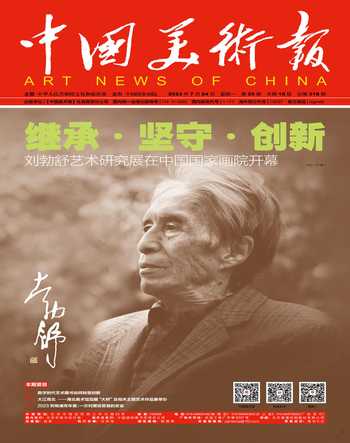2023利物浦双年展:一次对黑奴贸易的反省
李苑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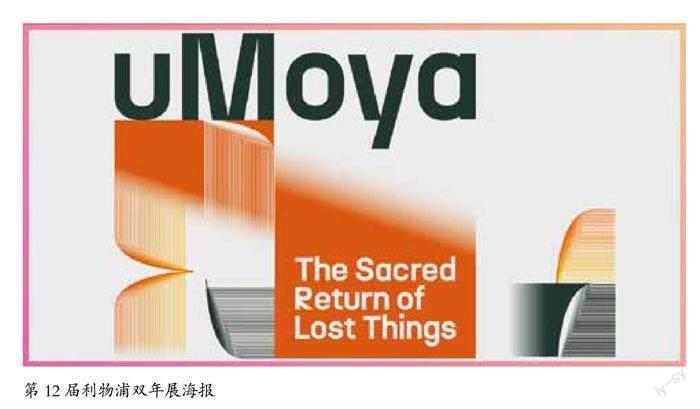

2023年的夏天,当刺眼的眼光直射着利物浦的斯坦利码头,艺术家赖莎·卡比尔(Raisa Kabir)将芦苇制成的绳索从港口浑浊的绿色水面中拉出,解开每一根线,准备编织。卡比尔持续进行的行为表演为今年的利物浦双年展定下了基调,即缓慢地、刻意地揭露这座城市曾经黑暗无情的帝国时代的历史,并讲述这段历史的深远影响,从而反思、修复长期以来人们在精神上所失去的东西,为理性的回归腾出空间。
第12届利物浦双年展的主题来源于祖鲁语——“乌莫亚:失落之物的神圣回归”(Umoya:The Sacred Return of Lost Things),其中的“乌莫亚”即为“呼吸”“空气”的意思,所暗示的意义不言自明。利物浦是17、18世纪罪恶的跨大西洋黑奴贸易的中心城市,整个城市直到工业革命发生时仍然笼罩在奴隶贸易的乌云之中。本届利物浦双年展中的多数作品由非裔、亚裔和印第安土著艺术家创作,呼应了展览的主题,也把历史血淋淋的伤疤再一次揭露在英国观众面前,时刻提醒着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如巴西艺术家伊萨·多·罗萨里奥(Isa do Rosário)那件亮蓝色的纺织物作品《与死神共舞在大西洋上》(Dance with Death on the Atlantic Sea),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上面有一幅幅的素描。这些极具表现性的笔触唤醒了人们内心的恶魔——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布料上的黑点代表了在贩奴过程中失去了生命的黑人。
在南非策展人汉尼斯勒·姆邦瓦(Khanisile Mbongwa)的策划下,来自25个国家的35位艺术家的作品在8个画廊、博物馆和其他室内场所,以及5个室外场所展出。除了奴隶贸易,作品还反映了殖民主义对本地社区环境的影响。他们不寻求视觉上的冲击,而是精神上的觉醒和激励。姆邦瓦呼吁,应该重新认识非洲祖先的智慧,认识土著们如何学习、治疗并传播经验。
关于奴隶贸易最为直接和明显的作品是在烟草仓库展出的宾塔·迪奥(Binta Diaw)的《土壤合唱团》(Chorus of Soil),这位塞内加尔裔的意大利艺术家利用土壤“绘制”了一张18世纪布鲁克斯贩奴船的平面图。这艘贩奴的商船从利物浦出发前往非洲西海岸,并在1782年至1804年间将5000名奴隶运往加勒比海地区。漫步在作品之中,是一段令人悲愤的旅程,因为这艘船可以装载454名非洲奴隶,而每个男人只被分配了约0.7平方米,每个女人只有0.6平方米的空间。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这些奴隶绝没有被看作是人,他们只是和香料或咖啡豆一样的货物。这个近乎1:1比例的贩奴船的复制品,表面还生长了植物的嫩芽,每一根嫩芽都代表了1791年中所逝去的一个人。
在泰特利物浦美术馆,美国艺术家陶克瓦斯·戴森(Torkwase Dyson)巨大的装置作品探索了黑人解放、生态和建筑之间的交点。《液体之地》(Liquid a Place)是由钢铁、黄铜、镜面和石墨构成的,其几何形状让人联想到船体或是墓碑,令人忧伤。
本届利物浦双年展中,巨大的体量成了一个关键词,很多作品占用了大量的地面和墙壁空间,甚至用氣味占据了整个展览空间。在棉花交易所展区中,一股油气味从朗吉斯瓦·格昆塔(Lungiswa Gqunta)不规则形状、发光的绿色地板雕塑中散发出来,让人想起南非民众抗议中使用的汽油弹。同时,危地马拉艺术家埃德加·卡莱尔(Edgar Calel)的《古代知识形式的回声》(The Echo of an Ancient Form of Knowledge)则让泰特利物浦美术馆弥漫了一股菠萝的香味,因为艺术家用石头上的水果和蔬菜纪念了他的祖先。
悲悯的气氛和灾难的隐喻在此次利物浦双年展上无处不在,这也是姆邦加的意图所在。鲁迪·洛伊(Rudy Loewe)色彩明快的装置绘画《清算》(The Reckoning)表现了看上去欢乐的场景,就像卡莱尔的作品那样,围绕着“供奉”的概念,并通过建造神殿来纪念祖先。阿尔伯特·伊博奎·科扎(Albert Ibokwe Khoza)的“神龛”上有一堆牛骨,周围环绕着水果、饮料和蜡烛。这是为了纪念萨拉·巴特曼(Sarah Baartman) ,一位科伊霍伊族妇女,她的身体被认为是怪异的,19世纪曾在欧洲各地展出,以获取门票收益。
救赎的问题高于一切。用策展人姆邦瓦的话说,“我们如何从灾难走向生机?”对于西方文明中最具争议的历史污点,利物浦双年展的自省态度还是令人欣慰的。近年来,“关怀”“悲悯”已经成为策展人的时髦词汇,正如在利物浦发生的那样,作品和空间都令人感动,然而当年的污点、资本家的贪婪却早已被写入了历史课本。策展人和艺术家们没有忘记历史,他们在利物浦的艺术实践,至少算得上一次难得的反省和心灵的修复。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